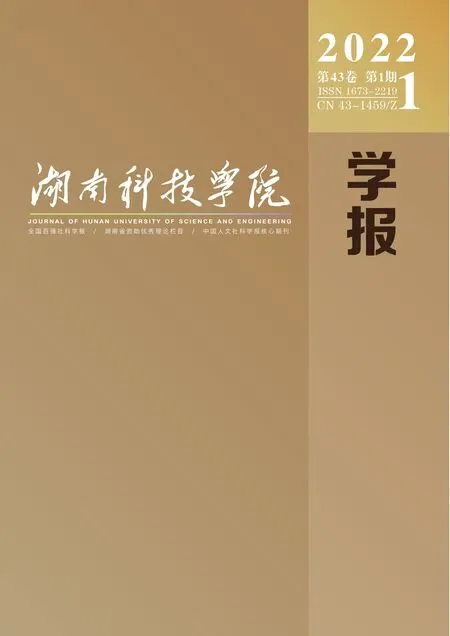贬谪文化视域下的柳宗元山水游记创作——以《永州八记》为例
高胜利 郭晓芸
贬谪文化视域下的柳宗元山水游记创作——以《永州八记》为例
高胜利1郭晓芸2
(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
柳宗元作为中唐贬谪文人的代表之一,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往永州,这是其命运的转折点。他将视野聚焦永州的山水景物,创作了一批寄寓情怀的山水游记,并开创了以山水游记体物咏怀的写作范式。《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与审美情趣的结晶。其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结合起来,不仅客观描摹永州的自然山水美景,而且在描写中注入自我的寂寥意绪,并借助对山水的审美观照来表现悲天悯人的情怀。《永州八记》填补了贬谪文学中山水游记的空白,为贬谪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柳宗元;贬谪;永州八记
柳宗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也是元和时期贬谪文人的代表之一。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被贬到偏僻的永州做司马。但他并未放弃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反而关心现实并写出大量文章与政敌进行斗争;与此同时,他又因不得重用而抑郁、痛苦,只能以奉佛、游山玩水来排遣苦闷。在他的散文作品里,以政论文、寓言以及山水游记成就较高。《永州八记》不仅以清丽俊秀的语言描写了永州的自然山水,而且寄托了被贬谪后的凄凉情怀。遭遇贬谪的悲愤不平,孤独寂寞,凄楚忧伤,和对于生命的执着,对于理想的追求,构成了贬谪文学丰富多样性的内涵。有鉴于此,文章以《永州八记》为切入点,透视中国古代贬谪文化影响之下柳宗元及其山水游记创作的情形,并试图进一步深入探讨背后蕴含的人文情怀与思想内涵,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一 贬谪文化及其对作家的影响
(一)贬谪文化的渊源
中国的贬谪文学以屈原为开端,在唐代元和年间、宋代元祐年间达到高潮。被贬的士人通过文学创作,抒发对于人生遭遇和不公平待遇的不满。贬谪的遭际使被贬的文人性格和心态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创作出了抒发其内心感受的“不平之鸣”。中国贬谪现象渊源已久,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文字记录。《尚书·尧典》记载有对“四罪”的惩罚:“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1]孔颖达《尚书正义》认为根据个人犯错误的情节来看“不忍依例刑杀”,所以才“宥之远方,应刑不刑,是宽纵之也”。此后,便形成古代一种贬谪弃逐景观,从伯奇、屈原、贾谊、司马迁一直到唐宋以后各代,成为了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文人被贬后的人格自由被扼杀,从而造成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打击与变化。在不同的历史视点上,中国古代文士被贬谪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正如尚永亮先生所言:“作为维护封建政治的工具,刑罚本是用以惩治不法之徒的,但结果却有大量正道直行、疾恶如仇、直言敢谏、勇于革新的士人成了它的牺牲品。”[2]从先秦到唐宋,士人被贬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四点:才高被嫉、参与改革失败、进谏惹怒皇帝、卷入党争。由此可见古代贬谪文化成因的内外因素:一是士人本身的强烈参政意识和对人格、品节的持守,这是士人被贬的内因;二是当时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存在是重大外因。所以才会有被贬谪后士人的身份心态的变化,他们不仅是有责任心的封建官员,更是以手写心,尤其是写这种高级生命体验的失意文人。
(二)贬谪文化对文人心态及创作的影响
以屈原被楚王流放为开端,贬谪文化对文人的心态变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贬谪文化使士人产生了自我保护的意识,导致了被贬后文人的关注对象从社会转向自我。他们既有报国之心又对自己的遭遇感到哀怨乃至不满,所以进行抒发自我不平之情的文学创作。屈原感叹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从而创作了感人泣下的《离骚》。毫无疑问,在唐代表现最突出的士人当属柳宗元。柳宗元早年参与政治、革除民弊,直到贬官永州后开始大量创作文章。其思想中有佛学影响下的消极出世观念,虽然减少了对君主的依附心理,但增添了对个体自由、对民生的关注。另一方面,在古代政治体制之下,很多文化、社会、朝政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唐以后直到北宋的激烈党争,士人在朝堂的浮沉变换中逐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和位置。以中唐的白居易为代表,到后来的欧阳修、苏轼,士人似乎在贬谪后找到了文人与朝臣两种角色之间的平衡。迨至宋朝,刘禹锡、柳宗元的宗儒思想已经完全被宗禅以及追求“趣”的美学追求取代了。面对遭遇,士人追求随遇而安的自由。然而被贬文人的共同点都是以文学作为自己情感抒发的窗口,正如纪昀在《月山诗集》序言中所说:“三古以来,放逐之臣,黄首或牗下之士,不知其凡几,其托诗以抒哀怨者,亦不知其凡几”[3]。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是在此种情形下创作出来的,这是其被贬谪后的凄楚悲苦心态的流露,也是其抒发抑郁情怀的媒介。
二 《永州八记》的创作背景
(一)山水游记的发展
以山水为题材的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很大比重,虽然古诗中早有对山水景物的描写,但多是以创作背景出现,并未形成独立的山水审美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与人双向互化的玄学促进了山水审美思潮的觉醒。山水诗经过陶潜、大小谢的发展已经逐渐成熟化。在对晋宋时代地理志的发展总结以及山水景物的描写手法和语言的学习吸收中,郦道元写就了《水经注》这样的集文学和地理学为一体的优秀作品。这种将自然景物当成知音的认知,对于确立古人新的审美对象,有很重要的意义,对后代古文家的游记类散文有很大的影响。到了唐代,盛唐的山水诗创作形成流派,创作成就蔚为大观。文人以诗心来感悟自然之美,在作品中创造出幽美深远的意境,为山水游记增添了浓浓的诗意色彩。同时,古文运动与文学复古潮流的逐渐兴起,也对山水游记散文的成熟有很大影响。元结的《右溪记》《苗圃记》等作品启发了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散文创作。在此背景下,柳宗元将自己作为诗人的诗意与文体革新代表的理论成功结合,创作出了山水游记散文中的翘楚——《永州八记》。当然,《永州八记》的创作过程与柳宗元的宦海沉浮尤其是被贬谪到湖南永州的经历密切相关的。
(二)柳宗元的宦海沉浮
河东柳氏为中古时期的名门望族,其与“薛氏”“裴氏”并称为“河东三著姓”,但到柳宗元时家族早已衰落。贞元九年,刚满二十岁的柳宗元登进士科,后因其父亡故守孝三年,待服丧期满后担任了秘书省校书郎一职。二十九岁时他又考中博学宏词科,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后来调补长安附近的蓝田县尉,两年后调任到朝中做御史台的实习属官。柳宗元走的是一条在唐代十分“正规”的升官之路,这样的经历使他更切身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吏治的腐败。顺宗即位后朝政把持在王伾和王叔文政治集团手中,作为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柳宗元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到达其事业的巅峰。然而永贞革新很快失败,包括柳宗元在内的革新派党人遭遇打击,他们先被贬为很远州郡的刺史,尚未到任又由刺史加贬成司马,这就是中唐时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谪永州这是柳宗元命运的转折点,而在永州的生存境遇则是《永州八记》创作的直接动因。
(三)永州境遇及其写作意图
尚永亮先生认为:“当生命由一个极点向另一个极点骤变的时候,由于有了正向的、高层级的生命体验作参照,则负向的、低层级的生命体验便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乃至痛苦倍增。”[2]89在柳宗元的记载中,永州位置偏僻,“可垦乃石田之余”,风俗奇特。他到达永州以后,只能“居龙兴寺西序之下”(《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且是病魔缠身,其在《与李翰林建书》中写道:“行则膝颤,坐则髀痹”。此后很长时间里“痞气尤甚”“动作不常”(《与杨京兆凭书》)。他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对永州的生活感到绝望,在给朋友的信里倾诉“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与萧翰林俛书》)。他在永州没有担任实职所以就无法施展抱负,又遭受朝廷中敌对势力的流言诽谤。他排解苦闷的方法无非是“发愤著书”与寄情山水。据《旧唐书·柳宗元传》记载:“在道,再贬永州司马……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4]他与当地的百姓、青年学子交往,可是他压抑在心底的伤感、不平依旧困顿着他的内心。幸好永州的佛教繁盛,他到达时便居住在龙兴寺西厢,与寺里的住持重巽为邻。他拜重巽为师,或是邀请他讲演佛道,或是自己在净土院苦读佛经。中唐时期,强调“顿悟”的南禅宗崛起,为柳宗元渗透了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排除杂念方能忘记痛苦的思想。柳宗元本人的思想中还有老庄的痕迹,道家的“小大之辩”讲究宇宙的大而人的渺小,强调个人在宇宙中可以忽略不计而达到物我两相忘的境地,这也使柳宗元稍微排解了苦闷,也影响到他散文中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境界。《永州八记》中构建的物我合一的境界正是柳宗元永州生活境遇的反映,他渴望借助山水消解苦闷,于是在描写景物中寄寓自我的情怀,这也是《永州八记》的艺术特征之一。
三 《永州八记》的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
(一)《永州八记》的特点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创作的山水游记,他在《愚溪诗序》一文中说自己虽然与世俗不和但是“亦颇以文墨自慰”。《永州八记》为人称道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作品的艺术性:他不是单纯地描写山水,而是将被贬谪后的凄楚心境和永州的山水景物联系到一起,从而抒发自我的悲愤情怀,真可谓是“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
1.游记而带骚体。柳宗元被贬谪的“南荒”永州位于今湖南省永州市,他在被贬途中路过汨罗江口时写过《吊屈原文》。他的经历和屈原是有些类似的,因此柳宗元感同身受地将屈原视作自己的知己,同时也影响了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柳宗元在其《永州八记》里所表达的愤懑不平和他长期以来形成的“辅时及物”的思想,是对屈原《离骚》中关心民生疾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甚至那种以永州山水景物寄寓自身不平的写法都与屈原“香草美人”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贬谪而使自己有限的生命的价值锐减,同时还有生活的绝望等种种因素,使得《永州八记》中有很浓重的被抛弃感、失去自由的拘禁感以及怀才不遇的生命荒废感,这也正是其山水游记中带有牢骚之怨的重要表现。
一是偏远之地的被弃感。永州在唐代为南方“蛮荒”之地,作为中原人的柳宗元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永州八记》里的山水景物总给人一种“凄神寒骨”的感觉。在《自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柳宗元描写道:“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有这样孤寂凄清感受的原因是他知道自己的艰难处境,一旦被贬在此,此生只怕是无起复之可能。《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壬午,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4]418随着时间的推移,柳宗元仅存的希望变成了绝望,其《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写“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又通过“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与“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的强烈对比,表面上描写了小丘不被重视,实际上是他自己被抛弃的感受以及坎坷命运的写照。
二是行动不自由的拘禁感。柳宗元感觉自己是一个“罪人”,在永州的贬谪生涯让他有身处“囚笼”的不自由感。而造成这样拘禁感有三点原因:其一是永州的地理环境多石多山:“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小石城山记》)。四面被“穷山恶水”包围,加之虫蛇奇多,天干物燥又遭遇失火,这种荒凉压抑感使得他无法喘息。其二是朝廷的律令使这种拘禁有了“法律”层面的限制。《唐会要》卷四一记载:“流人左降官称遭忧奔丧者,宜令所司,先听进止。”[5]柳宗元的母亲死于永州,他也只能“灵车远去而身独止”(《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上》)。其三是被贬谪时间较长,无法回归长安与朝堂的失落感造成的拘禁之感。这也是他《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中所说的“欲采蘋花不自由”的感觉。所以他在《石涧记》中追问“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来表达自己缺少自由的无奈。
三是怀才不遇的生命荒芜感。柳宗元在“八司马”中最有负罪感,对现实挫折的抗争以及挣扎未果的结局让他感觉到怀才不遇的苦闷。他甚至产生了归隐的想法,但这都是一种对苦难的心理防卫。这在《小石潭记》中确有体现:“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这种因“静”而“不可久居”正是作者在精神的矛盾折磨下而产生的性格异变,他忧郁、冷漠,甚至由外向的性格而逐渐退为内向。他在永州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他心目中的雄心壮志甚至逐渐都被残酷的现实所消解。《袁家渴记》中有“皆永中幽丽奇处也”地感叹,柳宗元身在永州,他本人也是“幽丽奇处”,这正是自己满腹才华而不得施展的一种物化表现。柳宗元那些看似乐观豁达的文字背后,彰显了他边缘化的境遇。如在《钴鉧潭记》中说“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在结尾表达哀怨之情却用一个“乐”字反衬出来,真是让人觉得泪随声下。所以苏轼才会评价柳宗元“忧中有乐,乐中有忧”(《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他无法做到真正的淡化与超然,独自游览山水时正是他内心最孤寂的时刻。“久为簪组累”的背后是更沉重的心情;寄身佛教、盼望归田实际上是心灰意冷。
2.天人合一的山水意境。王立群先生认为好的山水游记需要三个要素:游踪、景物、情感[6]。《永州八记》开创了山水游记的新体例,借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概念来描述他的进步性就是他写出了“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7]。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图貌到纪游。此前的山水散文都是单纯地描写山水之美,状山水之貌而少游览性描写。《永州八记》打破了这种图貌的写法,既写出了游览之乐又结尾抒情,让人觉得身临其境。《永州八记》中引入作者游玩的踪迹、景观等进行重点叙述,继承了前人在山林中获得静谧与欢乐的思想,同时又是散文领域的重大开拓。关于游踪的描写散见于各篇中,如先在《钴鉧潭记》中说“钴鉧潭在西山西”,紧接着又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写自己八天后又“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钴鉧潭”。由西山游览到钴鉧潭,再由潭水向西走,便能寻得小丘。从元和四年的深秋开始写起,他由心有不甘、浑浑噩噩转变为寄情山水、享受生活。这八篇游记仿佛是一本“永州旅游攻略”,带给读者的是新奇的美学体验。西山之特立、袁家渴的风以及小丘之石,都让人觉得有人文色彩。柳宗元对于景物的描写也是林纾所说的“穷形尽相,物无遁情,体物直到精微地步矣”[8]。
二是由景观到意境。柳宗元对笔下的景观不仅仅只是精细地描写,其建构出来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这正是《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说的“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写《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小丘之石:“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几个比喻便将无动感的石头写得活灵活现。在写《小石潭记》的鱼时,则是:“皆若空游无所依”“佁然不动”“似与游者相乐”,这样的意境不能不说是“著我之色彩”。作者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将有生命的鱼写得更加有情致,动静结合,让人觉得仿佛可以与作者共情。再如写袁家渴的风“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袁家渴记》),一系列动词的使用使得无生命之物有形有色、有了动感。林纾在其著作《柳文研究法》中有“文有意境,是柳州本色”这样对柳宗元清新细腻的文笔的欣赏和称赞。
三是作品的哲思理趣。在《永州八记》中最能表现出哲思与理趣的就是对小石潭中鱼的细致描写:“皆若空游无所依”“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小石潭记》)。这样有趣的描写让人联想到《庄子·秋水》中记录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那场论辩。在《小石城山记》中作者写道:“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然后知是山之特立”“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这样的语言既是对自己身世的感叹又是对不公的命运、对造物主的质问,发人深省。此外,作者还有对生命短暂、山水永恒的思考,《石涧记》中作者一连提出“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两个问题。这样的语句也蕴含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生命体验,真可谓是“一切景语皆情语”。
3.语言特色。《永州八记》的语言特色鲜明,其表面语言之美与内在表情达意都体现出了作者观察之细致及语言驾驭之能力。作者讲究内在的“意”与语言的“畅”相结合,形成清新隽永、自然流畅的散文风格,其游记散文的语言之美可以说是“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一是语言细腻优美。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作者先远后近、逐次描写了眼中的西山:在法华亭远望时“始指异之”,进而一路过溪登山“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接着写了从西山高处向下望所看到的情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最后写了自己的感悟。这样细致地描写,不仅是写西山,更是在表达作者之“特立”。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作者随着自己的脚步而变换对小石潭景物的描写,还没看见小潭就已经先听到其泠泠之声。接着写小石潭的清澈,又用工笔细细描绘岩石的各种形态:“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小石潭记》)语言细腻而又逼真。
二是节奏韵律明快而有变化。柳宗元虽然倡导古文运动,但在其《永州八记》中还是借鉴了骈文写作手法,将对仗句用在散文中,使得文章骈散结合,节奏明快,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写小石潭周围“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仅用十二个字就写出了周围景物的“幽”,与前文的诸多句子相错落,读起来朗朗上口。
三是语言的“峻洁”及对散体文的突破。柳宗元突破了以往散体文学模仿先秦两汉的局限,使得重实用写政治的散体文变得文学化、议论化。《永州八记》以准确、简洁的文字表现了他含蓄、自然的散文风格和与文章之“峻洁”相统一的人格情调。例如《石涧记》中连续有六个“若”字的使用:“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真可谓是清新隽永、明朗轻快。对此,孙琮《山晓阁选古文全集》评论道:“真是洞天之中有无穷洞天,福地之内有无穷福地”。
(二)作者心态与情怀的展现
柳宗元在永州的八篇游记一气呵成,带给人以美的艺术体验,然而其中也蕴含着作者的凄楚悲苦心态与抑郁情怀。柳宗元被贬后在反思中坚持理想,他执着地“发愤著书”就是由于不甘心而产生的反击。《永州八记》中作者剖析心灵世界,从文本的角度去解读,便可以显露端倪。作为一个“闲人”,柳宗元可以自在赏玩永州的山水。可是在这看似游赏的背后,是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对自身的隐喻。《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结尾的“心宁神释”与开头“恒惴慄”的忧惧相对比,写出了山水自然对柳宗元的治愈之感。游览永州美景是为了抒发自己心中的不平之气,而对小丘“所以贺兹丘之遭也”(《钴鉧潭西小丘记》)的同情也是对自身遭遇的感慨。他虽然无法挣脱命运的负累,但是在游记中对造物主提出了“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批评(《小石城山记》)。他对小石城山奇特的景色有细致地描写,然而又因此生发出无尽的情思。到小石潭游览后写到同游的人“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明明有多人陪伴,可是他依旧觉得“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这正是一种无人可诉说的悲凉之感。他努力想要从自然山水中得到救赎与解脱,可终究自身的性格以及内心的矛盾让他“惶惶不可终日”。柳宗元心中的抑郁情怀与悲愤心态正是通过他这些描写永州山水游记的文字表现出来的。
(三)作品的文化意蕴
文学作品是作者个人精神世界的反映,我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作者将个人意志和精神通过作品表现出来。柳宗元在永州创作出来的山水游记以及其他的寓言、诗歌,都是他内心的一面镜子,反映出中唐时期一个被朝廷遗忘的孤独的文人的心灵世界。作为贬谪文化的产物,《永州八记》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柳宗元本人与他的作品,真正合二为一,表现出韵味无穷的悲剧美,《永州八记》可以说是柳宗元悲剧人生与审美情趣的结晶。《永州八记》是柳宗元与天抗争、与命运抗争甚至与自我的负面情绪抗争的产物。他渴望用“乐山水而嗜闲安”来对抗“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送僧浩初序》)。但他终究还是一个有理想与抱负的文人,他要“经世济民”救百姓于水火,他内心时刻处于矛盾纠结之中。他回避、排斥,可是他还是得面对。终其一生,柳宗元都未能找到“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双全之法。他是不豁达,但他没有沉沦。相反,他通过《永州八记》来抚平内心的愤懑与不满。这种寄情山水的做法,以细腻锤炼的文笔将自己真实的情感通过山水来展现,以及他对山水游记体例的开创,都为中国古代社会的贬谪文化以及贬谪士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文学的阅读活动中,读者的阅读鉴赏可以使文本实现其更高的价值,正如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所言:“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9]。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之所以在后世不同时期受到审美接受者的高度赞誉,正是因为作者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结合起来,不仅客观描摹永州的自然山水美景,而且在描写中注入自我的寂寥情绪,借助对山水的审美观照来表现一种永恒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综合上述考论,柳宗元以《永州八记》为抒情载体,表现了对被贬谪弃置的不满,为广大希望建功立业、革故鼎新的士大夫发声,为后世的贬谪之士提供了以文学方式解决精神难题的范式。虽然柳宗元并没有因为纵情山水而获得旷达快意的人生,但他看到了山水游记的价值并将这类文体带上了时代的舞台。他用手中的生花妙笔真实记录贬谪后的心境,表达了深切的人文内涵。他通过清幽而又哀怨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忧患意识和高级的生命体验,填补了贬谪文学中山水游记的空白,为贬谪文化甚至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应当受到重视。
[1]尚书[M].曾运乾,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67.
[2]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3-89.
[3]爱新觉罗·恒仁.月山诗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04.
[4]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18-4214
[5]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67.
[6]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1-5.
[7]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8]林纾.柳文研究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120.
[9]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6.
2021-06-13
2019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先唐吊文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9W160)。
高胜利(1982-),男,河南周口人,文学博士,运城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文化与戏剧影视文学。郭晓芸(1999-),女,山西临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I206
A
1673-2219(2022)01-0030-05
(责任编校:呙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