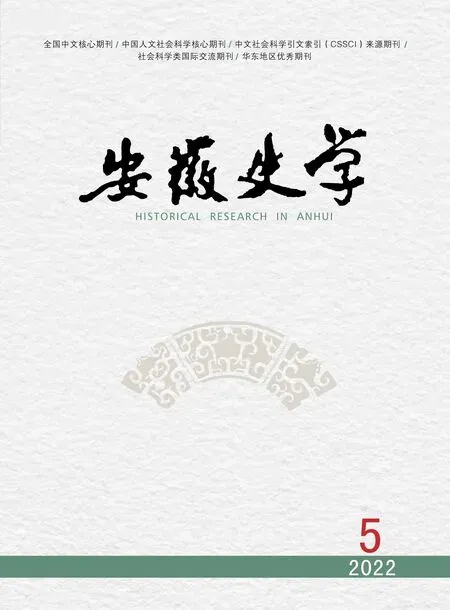铁路开通与晚清北京官员出行
——以《徐世昌日记》为中心的观察
迟云飞 丁高杰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自人类有文字或图像记录以来,可借之以观察人们的出行方式,无非是步行、乘轿、乘马车、骑马、乘船等方式,迟缓且辛苦,故慨叹行路难,可谓不绝于书。铁路修建以后,人们的出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快捷、便利,且较舒适。关于近代铁路史的研究,已取得非常丰硕的成果,但通车以后人员的来往如何利用新式交通工具,以及新式交通对人们工作、生活的影响,则关注不够。(1)笔者以“清末铁路”“徐世昌”“清末北京”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均无关于乘火车出行的论文。有关徐世昌的著作,如最新的李泽昊《变局·能臣·转机:徐世昌新政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亦未涉及此问题。铁路史的研究状况,参见岳鹏星:《当代大陆学人与中国铁路史研究》,《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7期。本文拟以徐世昌等官员的日记为线索,探讨晚清北京开通铁路以后,人们出行方式的变化,也希望借此观察晚清最后十年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更进一步,笔者还想探讨徐世昌乘火车的目的与活动,与他的工作、生活甚至时局有何关系。迄清亡,北京有几条铁路已经开通:一为京津铁路,此路可连通东北铁路;一为京汉铁路;一为京张铁路。另有北京到通州的京通支线,永定门到南苑的主要是军事用途的轻便铁路。本文的探讨即主要以此数条铁路为基础展开。
一、现代交通的曲折接受
铁路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无需赘述,但在19世纪后半,则有一个艰难的接受过程。
以北京而言,早在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Trent)就在宣武门外修了一条约一里的展览性铁路,但“见者骇怪”,被清政府勒令拆除。(2)曾鲲化:《中国铁路史》上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98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第26页。此事比上海吴淞铁路事件要早十余年,显示其时国人尤其是官方完全不能接受铁路。之后,为是否修铁路,清政府官员中曾反复辩论,尤其京师通铁路,阻力更大。直到甲午战败,修铁路方渐成共识。
历经千阻万难,1896年京津之间的铁路终于建成,次年6月通车,称津芦铁路。初计划由天津至卢沟桥,后延伸至永定门外马家堡,是为京津之间运行最早的铁路。(3)关于津芦铁路的争论及修建,详见张海荣:《从津芦铁路看甲午战后清朝改革的再启》,《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又,关于“芦”字,书“津芦铁路”时,暂从当时写法。
京津铁路通车,即为官民广泛利用。袁世凯驻天津小站练兵,需常到京师,其往返就是乘火车。1898年政变前夕,袁世凯奉命觐见,于9月14日“由天津乘第一次火车抵京”。在京期间,谭嗣同走访袁世凯,游说其发动政变推翻慈禧太后统治。9月20日袁世凯请训后,当日乘火车回津,抵津时,“日已落”。袁连夜向荣禄告密,造成政变规模扩大。(4)袁世凯:《戊戌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9—553页。又,《戊戌日记》内容是否可信,及袁与政变的关系,历来有争论,但其乘火车的记述当不致失实。可见京津火车刚开通,就与重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
京汉铁路(初称芦汉铁路),从卢沟桥到汉口,1897年开工。该路开建后便将陆续修成的路段通车。徐世昌1900年曾数次乘火车往返北京、定兴之间。戊戌政变后,铁路又遭保守人士非议。义和团起,有口号曰“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5)张守常:《说〈神助拳,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已修成的部分芦汉路及车站遭到严重破坏,待到局势平静以后方再修建。
经过庚子事变的大动荡,1901年以后已基本无人再反对修铁路,重要标志便是慈禧太后也乘坐了火车。1901年10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自西安“回銮”,从陕西西安经河南到直隶,都是传统旱路,一般乘轿而行。虽说不像离北京时仓皇、狼狈,又有地方官竭尽所能供奉,但长时间在路上,其实还是比较辛苦的。他们10月6日自西安启程,11月12日方抵开封,历时一月有余。之后在直隶段行程中,他们从正定(今属石家庄)乘火车至保定,再从保定乘车至北京,不仅轻松舒适快捷,费用也省了不少。徐世昌一路随扈“回銮”,从保定回京也是乘火车,他黎明登车,午后到京。(6)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1902年1月9日,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508页。保定距北京约三百里,若无火车,乘马车或骑马至少应走三天(后文介绍的曾国藩用了四天时间)。
1902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准备次年拜谒清西陵。为此次参谒,专门修了新易铁路,即自芦汉铁路线的高碑店新城至西陵所在的易州(易县)良谷庄,全长78里,并有桥梁两座,用银60万两。据负责验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报告,此78里,约行六刻钟,即一个半小时。(7)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117—118页。帝后参谒西陵是1903年4月5日出发,15日回京,来去共10天。新易铁路工程当时经济价值不高,不过也算清廷彻底接受了铁路。而且如果不乘火车,沿途要修建驿站、行宫,花费恐会远超60万两。
铁路这种现代交通方式终于被国人接受,如果从1865年拆毁英商的一华里铁路算起,到1901年慈禧太后乘火车,竟然经过三十六年,令今日治史者感慨。
二、无铁路时代:行路难
在观察和讨论京师官员的出行前,这里先就无铁路时官员如何出京做一个对比,笔者选择比较熟悉的任京官时间较长的曾国藩。曾国藩于1838年考中进士,任职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任京官十四年,其间只有两度离北京。据曾氏日记和黎庶昌为之所作年谱,中进士当年曾国藩请假回乡(返乡行程不详),之后于1839年12月7日自湖南湘乡启程返京,一路或水路乘船,或旱路乘车,1840年1月5日到汉口,3月1日方抵京师。用时几近三个月。1841年1月,曾国藩之父到京短住,5月4日离京回家,用时三十余日到达湖南省城长沙,曾国藩在家书中称“真极神速”。(8)邓云生编校标点:《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页。今人读来,只能一笑。
1843年,曾国藩奉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他8月3日从京师出发,一路风雨兼程,每天都走百余里,四天抵达保定,十五天到正定府(今属石家庄)。以后经获鹿、井陉进入山西,再走陕西。在陕西因病耽搁数日,9月27日抵成都。如此急行,用时亦近两月。回京时,11月12日启行,又经陕西、山西、直隶,1844年1月10日方抵北京,用时又是两月。(9)《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174—第181页;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页。可见无现代交通工具时行路之难。当时曾国藩已是高官,一路有官驿站和熟悉的官员照顾,一般百姓,行路当更难。此后直到1852年受命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八年半时间里曾国藩的职位不断升迁,当过礼、兵、工、刑、吏五部的侍郎,但没有跨出北京一步。究其原因,除了曾国藩较穷外,主要是当时的交通条件。
火车未开通之前,徐世昌亦是如此。徐世昌1886年赴京参加会试,他2月27日自开封出发,一路多乘船,3月14日抵天津,用了16天。(10)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34—35、336—337、338、343、369、388、389—390、434、463页。当年徐中进士,开始任京官。
徐世昌虽在京任职,但家眷长时间在直隶定兴,因此常往返北京、定兴之间。今日看定兴似与北京近在咫尺,但当时乘马车仍需两天才能抵达。如1896年7月6日,徐世昌从北京“黎明起,料理登车”,次日“酉初抵定(兴)寓”。(11)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34—35、336—337、338、343、369、388、389—390、434、463页。归北京是7月28日“晨起,登程。晚宿窦店……雨后泥潦,甚不易行”,29日“傍晚到京”。(12)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34—35、336—337、338、343、369、388、389—390、434、463页。1896年9月徐世昌接其母到京,因其母年老体弱,“乘肩舆”,从定兴到京用了三天。(13)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34—35、336—337、338、343、369、388、389—390、434、463页。这年其母去世,次年徐送其母归葬河南卫辉,回京时乘马车,1897年5月14日从河南辉县启程,用十一天方抵达定兴。(14)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366—367页。又,现在从卫辉到北京,乘普通快车大约8小时,若从新乡乘高铁,到京只需3小时。1901年徐世昌随慈禧、光绪回銮,有时打前站。据其日记,从河南卫辉到直隶保定,他走了十四天。(15)徐世昌1901年12月26日日记。
当铁路部分开通后,徐世昌出行多倾向乘火车。
1897年,受袁世凯约请,徐世昌到天津小站任“总理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京津火车也恰在这年通车。徐世昌到天津赴任即是乘火车,这也是他第一次乘火车,他在日记中称“火轮车”,6月29日“午正后开车,戌初刻即抵里门”。(16)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34—35、336—337、338、343、369、388、389—390、434、463页。以现在计时算,大约七个小时。
中历光绪二十三年底到次年初,徐世昌离军营到定兴过年,他赴定兴时绕道北京,1898年1月14日“晨起,检行装……登火轮车,申刻到京”。(17)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34—35、336—337、338、343、369、388、389—390、434、463页。用时不过半日,然后用两天到定兴。过年后,徐世昌不经北京乘马车直赴天津,一路走得很辛苦:1898年2月2日午启行,宿新城县(今高碑店市新城镇);次日半夜(丑初刻)即启行,晚宿信安;第三天还是丑时出发,傍晚抵达天津。自定兴到津用了两天半。(18)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34—35、336—337、338、343、369、388、389—390、434、463页。
1899年芦汉线部分开通后,徐世昌6月从天津回定兴。为了乘火车,他于22日从小站到天津,然后23日从天津乘火车绕道北京,在丰台换车,总共大半日即抵达定兴。(19)1899年6月22日、23日日记。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432页。返程时7月19日从定兴到京,“辰刻登火轮车,午刻到丰台,饭于广安栈。稍歇后乘汽车到马家堡,乘新设电气车到永定门,甚轻便。”(20)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34—35、336—337、338、343、369、388、389—390、434、463页。一句“甚轻便”,揭示了铁路带来的便利、快捷。
从上面的叙述可见,庚子事变以前,徐世昌乘火车次数不多,但与马车相比,明显可见火车的迅捷。而且他走过一次从定兴沿传统土路直接去天津后,再不肯走传统土路,而是宁可绕道北京换车转赴天津,虽路途远些,但因有火车,还是比直赴天津便捷得多,且较舒适。
义和团蜂起时,破坏了涿州、高碑店等地的铁路,1900年6月,徐世昌之妹在定兴去世,因义和团阻路,只好绕道回定兴,即使奔丧急行,仍用了一天半才到定兴。(21)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34—35、336—337、338、343、369、388、389—390、434、463页。这年中他又曾往返定兴,即使骑马,也要两天。可见铁路中断造成的不便。
三、徐世昌的铁路旅行及内容
1902年初回京后,到1911年底止徐世昌的日记相对完整。此时期徐世昌乘坐火车比较多,又恰好主要在北京任职,因此本节的讨论主要以此时段为主(去掉两年东三省总督时期,此时期不算京官)。与此同时,1901年以后,徐世昌迅速升迁,1909年初到1910年8月,他还担任了一年半主管铁路的邮传部尚书;1911年成立“皇族内阁”时,任内阁协理大臣,算是汉族官员中职位最高者。
徐世昌是京城高官中乘坐火车较为频繁的一位,据笔者粗略统计,此期间徐世昌直接乘坐火车计43次(一般往返只计一次,又去掉任东三省总督的两年),1902年到1911年底,平均每年5次以上。若往返算两次,则平均每年可达10次以上。此外,徐世昌1907年6月到1909年5月任东三省总督(实到任及交卸月份),此两年中虽曾多次乘火车,但非京师官员,不在研究范围。
考察徐世昌乘火车的目的,首先是政务活动,这在徐世昌的火车旅行中占了绝大多数。清季十年,徐世昌的任职很广,涵盖政务处、财政处、练兵处及军务、邮传部等等,他的火车政务旅行也包括了这诸多方面,以下大体按照时间和重要性考察。
1.会见袁世凯
徐世昌乘火车的活动中,第一类的事情是常去见直隶总督袁世凯。徐与袁的特殊关系学界已熟知,不赘述。而他频频去见袁世凯,尚有公开的理由。庚子事变中,守卫京城的军事力量溃散,清廷命袁世凯从其部下武卫右军中抽部分兵力守卫京城包括皇城,由老将姜桂题统领。1902年1月,袁世凯请徐世昌任“总理北洋留京各营营务处”,即负责驻京北洋部队的管理。(22)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508、534、46页。11月,徐再兼任“右军执法营务处”。(23)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508、534、46页。这样,徐世昌与袁世凯有更多公开的正式的政务联系,可以很方便见袁世凯。此外,1903年12月清廷成立练兵处,袁世凯为会办大臣,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负责日常事务,需要更多见实际主持练兵处的袁世凯。徐世昌日记记录,12月27日他被任命为练兵处提调,当日即与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开始工作。31日,也即任命四天后,徐世昌又与上述三人一同到天津拜会袁世凯。在津停留一天半,大部分时间是与袁世凯“久谈”。(24)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2册,第33、11、88页。笔者据徐世昌日记统计,自1902年5月,到1907年6月赴东三省总督任(25)1907年9月袁世凯任军机大臣离天津,徐再回京任职袁已被免职。,五年间徐世昌乘火车或到天津,或到保定,见袁世凯达18次。考虑到此期间袁世凯亦经常到北京,两人见面更多。尤其后文要介绍的徐世昌与载振到东三省考察,来去均在天津与袁世凯多次久谈,改东三省为行省的建议,恐怕就是他们商议后做出的。徐世昌赴东三省任时,三省巡抚都是袁世凯系的人(奉天唐绍仪,吉林朱家宝,黑龙江段芝贵)。(26)段芝贵因丑闻未到任,代以程德全。为与在我国东北的日俄驻军抗衡,徐世昌又奏请将北洋第三镇带往东北,再从二四五六镇抽调部队组成两混成协开赴东北。徐袁关系,是晚清历史重要一页,铁路旅行,成为他们交往沟通的便利工具。书信、电报也可以沟通,但总不如面谈更顺畅、深入,且无泄密之虞,故火车旅行,也见证了徐袁的密切关系及其影响。
2.筹建户部造币厂
1903年4月22日,清政府成立以整顿财政为目的的财政处,并钦派庆亲王奕劻和另一位军机大臣瞿鸿禨负责。4月27日,又命徐世昌与陈璧、毛庆蕃“为经理财政提调,创办京师铸银钱厂”。(27)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2册,第33、11、88页。当时直隶等数省已经自行铸造银、铜币,便利商业流通的同时,也成为这些省财政的一大来源。而财政处提调们的第一项任务,是筹办中央的铸造银、铜币工厂。5月1日,徐世昌即与陈璧同赴天津,考察袁世凯命周学熙所办的直隶银元局。关于厂址,清廷原拟设于京师,徐世昌等在京师考察几处地方后,觉得都不合适,而后清廷决定,将“铸造银钱总局”设在工业较发达、燃料原料也便利的天津。仅据其日记的记录,1903年5月到1905年6月,为银钱厂事,徐世昌至少9次到天津。1905年6月10日,银钱厂开工生产(28)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2册,第33、11、88页。,不久正式定名“户部造币总厂”。同年由财政处奏请,清廷命户部造币总厂及直隶、江苏、湖北、广东各厂按照统一的规格铸造银币,是为清末新政中试图统一货币的努力之一。无铁路时,天津到北京至少要三天,有时需四天(29)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1册,第508、534、46页。,如果不是铁路提供的便利,徐世昌很难反复到天津考察。而造币厂这样的重要机构,清政府往往希望就近控制,如果不是铁路提供的便利,清廷不会同意将其设于天津。
3.检阅、考察军队
如前所述,徐世昌1903年任练兵处提调。此后他曾任多个与军事有关的职务:1904年至1905年任兵部左侍郎(先署后实任),1905年为会办练兵大臣,1906年一度署理兵部尚书。由此,徐世昌的出行常与军队特别是新军事务有关。其背景,就是日俄战争前后,清廷加紧了新军的建军和训练。1904年8月,清廷命徐世昌每隔二十余日到保定校阅京旗常备军一次。按徐日记的记录,1904年9月中旬到年底就有三次,1905年两次。举1904年9月16—21日的一次为例,徐世昌16日中午到保定就立即召集京旗常备军军官“询问一切”,并到各营视察。此后三天连续看京旗常备军训练,又检查其营房、军马、随营学堂、士兵住处,甚至还观看野外演习。不仅检查京旗常备军,还检查驻保定的新军第三镇及夏辛酉所率山东先锋队操练,还有冯国璋所办北洋陆军学堂、将弁学堂。(30)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2册,第56—57、68页。时间更长的一次是1905年3月27日到4月21日,这次检阅长达26天,徐与兵部尚书长庚同行,他们先后到了永平府的迁安县、天津府的马厂,最后一站是保定府。检阅归来,徐世昌上了一个很长的奏折,详细报告了三镇军队的情况。由于日俄战争陆战就在中国东北,清政府虽宣布中立,但军队高度戒备,徐世昌检阅的三镇中,驻迁安一镇、驻保定一镇更是增设后勤保障马匹车辆,并配备修理军械的随营军械分局,处于临战状态。从徐世昌的奏折看,三镇的编制体制、士兵的训练、演习等,远优于以往的湘淮军。其缺点主要是武器较多依赖进口,规格不够统一,给后勤保障带来一定困难。(31)徐世昌:《复奏陆军三镇考验情形折》,《退耕堂政书》卷1,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23辑,第59—69页;参见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2册,第75页。我们观察,乘火车出行,大大便利了练兵处官员对新军的检阅和监督,也意味着便利了中央朝廷对新军的监督、督促。1905年10月以后,徐世昌先后任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与京畿一带的军队关系少了,但1911年3月(时任军机大臣)又曾与载涛等一同乘小火车到南苑看禁卫军操练。
由于铁路的迅捷与相对舒适,徐世昌无论是到保定还是天津,大多是到达当日即开始各种活动,上已述及。又如1905年1月26日到保定检阅旗兵兼看第三镇(良弼同行),当天即到军营并接见军官,以后每天都在军营考察。1月30日回京,当天即到练兵处办公。(32)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2册,第56—57、68页。如果没有铁路带来的便利,不可能有这样的工作节奏。
4.未成行的出洋考察
1905年7月16日,清廷命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出洋考察政治。考察政治者,实为考察宪政,以便为清政府能否实行立宪制度提供建议,出洋五大臣可谓重任在肩。9月24日,徐世昌等五大臣及随员,一行浩浩荡荡,到前门车站等车,准备转道天津出洋,不料突遇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徐世昌日记写道:“至前门外车站,送行者甚多,周旋良久。登车后将发,忽炸弹爆发,烟气迷漫,车胎震损。泽公(载泽)、绍越千(绍英)各受微伤,仆人王顺受伤较重。车外弊踣三人,送行者受微伤甚多。随员萨荫国一家数人受伤,有死者。车内轰碎一人,系施放炸弹者。朝廷维新百度之始,忽有此暴动之事,良可怪也。”(33)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2册,第90页。又,“弊踣”,原文如此。此事轰动中外,出洋考察也暂停,这是徐世昌最尴尬的一次乘火车经历。半个月后,清廷成立巡警部,徐世昌出任尚书,清廷另派尚其亨、李盛铎代替徐世昌和受伤的绍英。各大臣考察回国后,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为晚清政治的一大变动。
5.东三省之考察与建省
东三省为清朝发祥之地,日俄战后,为抵制日俄的侵略,清政府加强了对东北的经营,撤换盛京将军增祺,以较能干的赵尔巽任盛京将军,甚至让汉官程德全任以往只有满人才能担任的黑龙江将军,又裁盛京五部侍郎,并努力推行新政。但是清廷觉得还不够,1906年10月,时任民政部尚书的徐世昌奉命与奕劻之子商部尚书载振一同到东三省考察。两人11月12日乘火车离京,在天津停留数日后赴东北,在东三省考察将近两月。他们先后到了盛京、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省会)、吉林(其时吉林省省会)等地,1907年1月4日方回到北京。他们奏陈东三省形势:“自日俄战定,两强势力分布南北。一以哈尔滨为中心,一以旅顺、大连湾为根据地,囊括席卷,视同固有。名为中国领土,实则几无我国容足之地。且其开拓展布,有进无退,恐不数年间,而西则蔓延蒙古,南则逼处京畿。”他们认为,“必须大加改革,于用人行政诸大端,破除成例,以全国之人力财力注重东陲,乃可望补救挽回于万一”。(34)《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退耕堂政书》卷5,第215页。1907年4月20日,清廷改东三省为行省,任命徐为东三省总督,三省巡抚亦皆为汉族官员,改革动作之大,清代罕见。
东三省土地辽阔,超过世界上多数国家,此次考察,徐世昌、载振交替乘火车、马车,而能做如此大范围的考察,实依赖铁路提供的便利,若无铁路,这样的大范围、多地的考察很难进行。
6.查验铁路及铁路工程
1909年,徐世昌由东三省总督转任邮传部尚书,5月24日接任。清季邮传部主管轮、路、邮、电诸政,而铁路是邮传部最主要的事务之一。据徐世昌的日记,他乘火车考察铁路及铁路工程有七次。最引人瞩目的是主持京张铁路通车典礼。
1909年10月2日,京张铁路通车典礼在南口举行,徐世昌亲往主持。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外官商约数千余人,观者如堵,亦一时之盛举也。”他当天早晨由西直门站乘车赴南口,主持通车典礼后,当天返回北京,还能在晚上去探望生病的张之洞。(35)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2册,第212、211、215页。西直门站到南口近50公里,徐世昌还要由宅邸到西直门站,如无火车,决不能做到当日往返。
当时也有报纸报道,当日早,西直门站热闹非凡,京师参加典礼者由此出发,火车头上用松枝彩花装饰为龙形,车身亦有彩绸及花环绕。中外来宾达万余人,嘉宾分乘六列火车到南口,第一列八点半发车,九点四十五分到南口。另有一列从张家口到南口。午后一时典礼开始,徐世昌首先演说,强调京张铁路工程由“中国筹款自造,而工程亦全用华员经理,绝不借才他邦,此为本路特异之点”。演说还由译员当场译成英语。报纸评论:“为我中国铁路界从来未有之盛事。”(36)均见《京张铁路开车纪盛》,《顺天时报》1909年10月3日,第7版。京张路的经济价值不如京汉路、京津路和修建中的津浦路,其战略价值高于经济价值。通车典礼之所以如此隆重,除了炫耀清政府的政绩外,更多的是宣示中国对蒙古地区的主权和清政府巩固边疆、抵制沙俄对蒙古地区渗透的决心。
7.游玩
交通条件,是旅游活动得以开展的要素之一。徐世昌也有过多次乘火车到北京周边纯游玩的记录,可说是那个时代的火车旅游。徐世昌乘火车游玩,主要是在1909年回京任职以后,专程外也有公务之余顺便游览。按他的记录,1909年9月到1910年底,共有四次。第一次是1909年9月,徐世昌到张家口察验京张路工程,分别到张家口、张家口鸡鸣山(下花园车站)、南口,然后从南口“偕同人往谒明十三陵,畅游半日”,当天自南口赶回北京。日记虽未明言,但从文意可以看出,他乘坐的是专车,这是高官特别是邮传部尚书特享的便利条件。(37)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2册,第212、211、215页。如果说上次是顺便游览的话,1909年11月1日则是专门的游玩:徐世昌一行“乘火车到黄村下车,游西山诸古刹,晚归”。(38)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2册,第212、211、215页。同游的那桐记录更为详细:“黄村下车,易小椅登山,香界寺早饭,游龙王堂、秘魔崖,半山红叶一抹斜阳,秋景极为鲜艳,真乐事也。”(39)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643页。这次一同游玩的,除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桐外,还有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邮传部侍郎汪大燮和沈云沛、按察使李经迈(李鸿章之子)、那晋(那桐之弟)。结伴同玩既是观赏人文自然景色,也是一种交际活动。这次活动的发起者是邮传部的两侍郎。另一次是游览居庸关、八达岭,也是与那桐、世续及邮传部两侍郎同行。游览的地点也很有意思,那时的高官,多科举出身,既是高官,也是文人,他们游览的去处,往往是古刹名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历史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兼顾。由于职务的限制,徐世昌没有较长的假期,故游览限于北京周边。
8.接送站——交际的延伸
铁路的开通不但大大便利了人们的出行,还衍生出了接送站活动,徐世昌的日记中,就记录了很多接送站活动。接送站活动,有的是政务必须,有的纯属礼节或事务性的,更多的是一种联络感情,即私人交往。徐世昌是极活跃、善交际的人,接送站也属于交际的一种,甚至还有几次专门到车站会晤路过北京换车的朋友。
这里仅举一例讨论其作用和影响。日记显示,仅宣统年间,徐世昌到车站接送载洵、载涛兄弟就至少有五次。众所周知,载沣摄政以后,北洋集团与少壮亲贵矛盾凸显,袁世凯被免职,一些与袁关系密切之人也被罢免。而徐世昌却能安于其位,又和一些亲贵至少表面上维持不错的关系,徐世昌接送载洵、载涛兄弟即可见其一斑。徐居高位,既为袁世凯了解政局提供方便,也为将来袁世凯出山——某种意义上也是为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与袁世凯集团的妥协埋下伏笔。
四、其他官员对铁路的利用
为了侧面印证铁路开通后的出行情况,我们再参以那桐、恽毓鼎、汪荣宝几位官员的日记。
那桐,官至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其官职和政治地位与徐世昌相近。清末那桐乘火车没有徐世昌多,但也有不少记录,特别是到火车站送行。那桐日记第一次记到火车站是在1901年5月26日,系为侵华联军日本军官福岛安正送行。此时清廷已内定那桐为赴日道歉专使,故其与日人联络较多,日记中那桐尚称火车站为“火车栈”。(40)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第377、385—401、459—467、655、665页。以后,醇亲王载沣作为道歉专使赴德,去与回那桐都到火车站送迎。1902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回銮、载振出京考察,那桐均到车站迎送。前述 1903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拜谒清西陵,那桐也与群臣到火车站送行。那桐在外务部任职,所以到车站迎送外国人更多。笔者粗略统计,从1901年到1908年4月,那桐到车站迎送达26次之多。
晚清那桐有两次出使日本的经历。第一次是专为日使馆官员杉山彬被杀事道歉。1901年8月17日,那桐启行,他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轮船到日本。完成使命并在日本考察后,乘船直接从日本回天津,再从天津乘火车回北京。火车、轮船转换,完成了这次跨国旅行。在他的日记中,仍称“火车栈”。(41)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第377、385—401、459—467、655、665页。1903年4月,那桐再到日本参加在大阪举行的赛会(商品博览会),系与载振同去,来往仍是火车转道天津。那桐等在大阪又先后考察造币局、炮兵工厂、火车制造厂、军队,之后到东京参观银行、学校、农事试验场等,并访问日本大藏省,其间曾拜会日本天皇。此次到日本,与1901年的道歉专使不同,纯为了解日本及世界的发展而来,当然与第一次赴日一样开拓视野,了解到很多新的事务,感受到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载振归来,奏请设立商部,并担任了第一任商部尚书。这也是清季旅行的一段历史。有趣的是,此次去时那桐日记还写作“车栈”,回来时改为“车站”,此后便一直用“车站”。(42)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第377、385—401、459—467、655、665页。
那桐乘火车的公务旅行没有徐世昌多,但北京周边游玩不少,游玩后常记下观感和心情,此点前已述及,又如“花木甚佳,小雨如沐,爽气宜人,为近日第一快心事也”。(43)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第377、385—401、459—467、655、665页。那桐似乎更喜欢和家人一起游玩,可以不用应酬,比较放松,如1910年8月27日与家人到居庸关、八达岭游览,当日记“天气佳,山色好,无外客,真有趣也”。(44)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第377、385—401、459—467、655、665页。
恽毓鼎的官职远低于徐世昌和那桐,但他担任的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属皇家近臣。在恽的日记中,也有不少利用铁路的记录。
1903年,恽毓鼎任会试同考官(当年在开封考试),此时京汉路未全通车,他赴开封时,先乘火车到保定。3月12日出发,下午一点半火车开行,七点钟到保定,恽毓鼎还记下了他乘坐的头等车的票价为五元八角。(45)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211—216页。次日从保定出发,改乘马车,3月28日方抵达开封,无火车路段整整用了15天。(46)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211—216页。
京汉铁路通车后,铁路更被广泛利用。1911年,恽毓鼎回江苏常州祭祖。他先乘京汉路快车到汉口,2月21日登车,次日即抵汉口,然后乘长江轮船到南京,再乘沪宁铁路火车到常州。走了个“L”字形,整个行程用了七天。此路线比较走天津到上海的海路,不会有晕船之类的苦恼,相对较舒适。回京时走的相同路线,用了八天。(47)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23—530、430、315页。前述曾国藩说他父亲回乡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为“神速”,事隔六十年,两相对比,真有天壤之别。
汪荣宝,是进入清政府任职的留日学生中极活跃的一位,先后任民政部参议、左丞,还有宪政编查馆编制局正科员、修订法律馆第二科总纂等职,又为资政院钦选议员,官职不算很高,但很重要。笔者仅介绍编纂宪法过程中汪荣宝和李家驹的出行。1911年,汪荣宝奉命参与起草宪法,为避开各种事务及应酬,专心纂拟,汪荣宝与另一位负责起草的宪政编查馆提调、学部侍郎李家驹数次离京编纂。汪荣宝1911年7月6日记到南口:“十一时,诣西直门车场,少选,柳溪(李家驹)院使来会,以十二时四十五分发,二时四十三分抵南口,止华洋旅馆。”(48)韩策、崔学森整理:《汪荣宝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8、288—289页。8月18日,汪荣宝与李家驹再乘火车到周口店,在上方山兜率寺住了五天。(49)韩策、崔学森整理:《汪荣宝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8、288—289页。第三次,为了起草“领土”一章,汪荣宝与李家驹居然到泰山。当时津浦路天津到泰安段已通车,只济南黄河桥未成。他们9月12日出发,当日到天津;13日乘火车到黄河北岸,乘轮船渡河到济南;14日乘火车到泰安,当日即登达玉皇顶住下。他们在泰山顶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并将宪法草案大体完成,21日方下山,仍经济南、天津回京。这种特殊的起草工作,只有有了铁路以后,才能达成。
上述诸人,徐世昌生于1855年,那桐生于1857年,恽毓鼎生于1863年,李家驹生于1871年,汪荣宝生于1878年,可见火车是青年到中年的人都乐于乘坐利用的。
本文前面提到,当时京张铁路的战略意义大于经济价值,但笔者也看到了很有意思的利用方法。1909年3—4月,恽毓鼎时任大同知府的朋友翁斌孙(翁同龢之侄)因事到省城太原。大同到太原,直线距离只有二百多公里,但其间山峦重重,非常难走。故翁不从大同直接向南到太原,而是向东北到张家口,走京张铁路到北京,由北京乘火车南下到石家庄,再乘正太线火车到太原。回大同也是从太原到北京,再由京到张家口再到大同。(50)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23—530、430、315页。此行虽绕了一大圈,但因有火车这一现代交通工具,仍比从大同向南穿越大山便利舒适。
铁路、轮船不仅便利了人们的出行,对人们其他方面的生活也改变不少。这里仅举一例,恽毓鼎1906年7月12日记:“至编书处。李新吾携鲜荔支分饷,乃新自上海冰护运来者,红肌白肉,汁甘而肥,胜罐装者数倍。今日水陆交通,凡东南鲜物如鲥鱼、枇杷之类,皆得餍北人口腹,吾侪此等际遇殊胜古人,所恨者无古人太平世界耳。”(51)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23—530、430、315页。
余 论
近代中国交通的发展,包括铁路、轮船的开通,其影响是巨大的,以笔者的了解,除了商业、经济这些人们关注较多的话题外,城市格局的变化、人口的流动,乃至国人观念的变化,都是极为深远的。理论上的探讨、数字的呈现相对较为抽象,而笔者在阅读日记的过程中,有十分形象的感受。仅就上述官员的活动就可以看出,铁路的开通,改变了官员们履行政务的模式。
观察铁路旅行,还有一个当时乘车者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即时间观念、效率观念的变化,以及生活节奏的调整。没有现代交通的时代,人们的出行,尤其是远途的旅行,只能有极为粗略的规划,很难精确到哪天到哪里、办什么事、见什么人。旅行中哪怕是常见的小病如肠胃不适、感冒等,都会对旅行的节奏产生影响。本文所介绍的曾国藩的旅行,便是如此。有了铁路以后,人们抵达目的地,或从目的地返回,大都会确定在哪一天,乃至一天中的哪一时。徐世昌的多次政务出行,大多是事先规划好在目的地每天的事务、要会见的人,事毕即打道回府。再加上电报的应用,从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已变得很轻松。以徐世昌和载振到东三省考察为例,他们到天津时,直隶总督袁世凯率僚属迎接,次日参加工商学界的欢迎会;到盛京时,将军赵尔巽率僚属迎接,甚至还有日本驻军军官来迎,到行馆又马上会见美、日领事等外国官员。(52)吴思鸥、孙宝铭点校:《徐世昌日记》第2册,第132页。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的活动也与此类似。之所以能如此,电报的传递信息和火车的准时到达,缺一不可。即此一端也可看出,铁路旅行无形中改变了利用者的时间观念,办事的效率也远非无现代交通时可比。公务旅行外,徐世昌、那桐等乘火车郊游的时候,除极少的专车,也必须遵守列车的运行时间,否则游玩的计划便无法完成。而有的日记,甚至直接写下乘车和到达的时、分。
写到这里,笔者觉得还可仿效当下的时髦语言概括:“铁路改变工作,铁路改变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