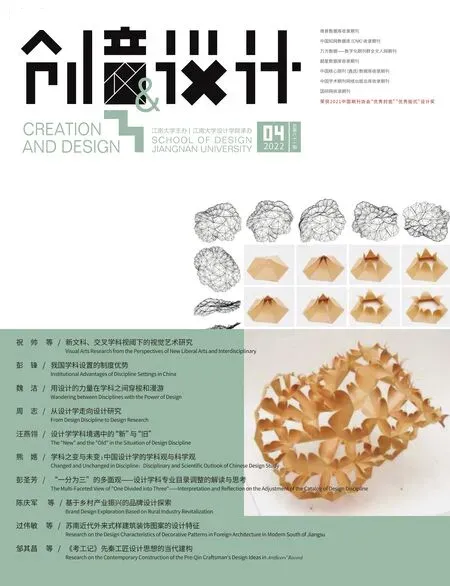设计学学科境遇中的“新”与“旧”
文/汪燕翎(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
在“新文科”建设全面部署的背景下,“设计”这一天生具有交叉特质的学科,无疑会在新一轮改革中迎来巨大震荡。新《艺术学门类一级学科调整方案》实施后,各高校将面临教学模式革新和研究范式创新。在全新的语境中,如何有效地协调好新旧方案间的冲突,解决好设计学不同知识层面和专业门类之间的衔接组合,依然是困难重重。本人作为旧文科时代成长起来的设计学人,从多年一线教学的经验和观察出发,为新方案实施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与建议。
一、如何有效融合设计研究的“学”与“术”
这次学科调整中设计学被一分为三:一是将设计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同其它艺术理论研究一并归到“艺术学”一级学科名目下,授予学术学位;二是将设计与其它艺术研究分别归入不同的实践门类,授予专业学位;三是将设计放入交叉学科,可授工学和艺术学学位。调整的初衷是为了打破现有设计人才培养的壁垒,同时也更好的统筹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之关系。但新方案的设置将设计学的“学”与“术”截然分割开来,并明显有着“术”对“学”的挤压,“工”对“艺”的统领。学术学位的培养被压缩到“艺术学”一级学科下,专业学位的培养在一级学科“设计”下被放大,“交叉学科”目录下虽同时可授工学和艺术学位,但所谓的“交叉”有着工学强势的引领态势。百余年前,蔡元培先生就对学术有过清晰的界定,学为根本,术为枝末,学是研究,术是方法,需要两者并行,共存互动。中国的设计艺术自从纳入硕博士研究生培养序列以来,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设计学人才培养上“学”与“术”分割的弊端,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设计艺术人才的质量。但新的学科调整方案,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各个不同艺术门类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一刀切式的“学”“术”两分,势必会给接下来的人才培养带来许多具体的问题。譬如,报考设计史论的同学,可能要面临必须参加整个艺术理论的综合考试,要和舞蹈理论、音乐理论考察同一套理论知识。而事实上,设计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要回应的是设计问题,要解释纷繁世界中设计与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而非回应抽象的,从概念到概念的艺术学理论问题。再譬如,设计实践的硕士想要选修设计史论的课程,视觉传达的学生想要保送设计史方向,他们的目标均不能实现,因为学校的研究生管理系统严格按照学科分类来确定老师、学生和专业的对应关系。即便是“新文科”时代,计算机算法也只能按照学科分类来指定路径。因此,在具体实施层面,“学”与“术”的断然切割很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与“新文科”的建设初衷背道而驰。
邓小南老师在谈到北京大学“新文科”建设时曾说,一流大学不是指许多个一级学科和一流专业的叠加,而是“学”与“术”的有机融合。需要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彼此的融汇互通,才能架构起一种更为合理的新文科关系结构。同样,“新文科”语境下的设计学建设,不能仅仅是工科、文科和艺科的简单交叉,而应该使其成为理论与实践、学术与专业、学科与学理的有机整合。只有在“学”与“术”合理的关系结构中,设计学才能实现其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整合,而不会变成以交叉为目的的对问题的切割。因此,在新的学科方案实施中,“学”与“术”的整体性依然应该被高度重视。在学位培养中,专业类设计硕士的培养应以完成社会层面的设计任务为导向,对成果的考核也应以社会反馈为标准,不鼓励以论文发表、课题申报和考博为目标。在博士层面的培养阶段应尽量避免将设计学的学理、史论与专业截然分割,应该继续坚持以学理探讨、理论建构为培养的主要目标,避免产生一大批只有创作经验而无理论建树的“设计师博士”。在交叉学科的设计学学位培养中,应明晰工科、文科和艺术在“设计”这一学科中可交叉和不可交叉的部分,避免出现各种学术评审的越界和各种杂交课题的泛滥。
二、如何融入中国设计学学科发展的经验与规律
学科的分化和融合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它其实也是一个从未间断过的,不断整合中的过程。一直以来,中国的设计学人和学界都在推动着设计学科的分化融合,创造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学科传统。在中国设计学成为现代学科之路上,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工艺美术史与图案设计进行的系统深入的探究。有改革开放之后一批海内外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从现代设计教育、设计门类研究、设计历史与理论出发,对中国现代设计学进行的全面推进。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后在几大传统艺术院校中进行的学科改革,开始招收艺术类学术型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中国艺术学的中坚力量。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大都是这一次学科改革中脱颖而出的人才,他们多有创作实践背景,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学术型训练又塑造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和理论体系。今天中国设计学发展枝繁叶茂,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几次学科改革的成效,几十年来,无论是图案学、工艺美术学还是设计艺术学,中国设计学在学科不断的分化融合中始终保持自身的活力和张力,也成为中国特色的艺术学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新方案在具体实施中,应尽量保持与上一轮学科分类的连续性,这不仅是因为目前中国高校设计教育的师资和现实条件还不允许设计学脱离“艺术学”这一大学科背景,还在于设计之所以为“学”,有其从实践到理论再到价值引领的内在脉络和结构层次,很难由工学的学科逻辑来支配。明晰“设计”这一新学科与“设计学”这一旧学科之间不可切割的内在联系,注重“设计”与曾经的图案学、工艺美术学、设计艺术学在学理上的绵延,是建设中国特色的设计学科要坚守的道路。在设计人才培养过程中,高低技术、新旧媒体的等级观念不应该成为划分学科属性的标准,今天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传统的印刷术与制瓷术在本质上都是技术革命,都是媒介革命,都是推动设计变革的力量。但无论设计的知识如何更新,认知如何迭代,科技和经济始终是双翼,对民生世界的洞察、理解和改造才应该是中国设计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这一点,正充分体现在中国现代设计学发展之路中。
三、如何纠正目前设计人才培养的问题
我国的设计学发展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不同地域、不同院校、不同专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发展动力都不尽相同。从2005年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的试点,到2011年艺术学成为独立门类以来,还有诸多积累的问题未被消化。譬如,每年五六月的答辩季我们很熟悉这样的现象,一些设计学博士生学术训练薄弱,普遍缺乏文科的表述能力、辨析能力和反思能力,难以将实践经验上升为学术思考。而专业硕士论文又恰恰相反,他们不是缺乏学术规范,而是普遍套用一份规范的,貌似科学的模版。但这个规范的文本中呈现的大多是无价值的设计,甚至是伪设计。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专业硕士实施过程中积累的问题都还未解决就推出“专业博士”,这种无“学”无“术”,或者“学”“术”倒置的现象是否会在更大范围内呈现和蔓延?造成更大的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
面对设计人才培养已经出现的乱象,不宜急于采纳统一的新文科评价标准,更不易匆忙推出专业博士。学科建设与发展应该与中国复杂的设计学发展现状相适应。顶层的任务可以交给有实力的学校,由它们去完成国家战略层面的课题,完成高级别的跨学科合作。而底层的任务则应该回归设计的本质使命,对设计学科最终端的千千万万教师和学生而言,纷繁的社会需求和现实问题自然会让他们的设计过程涉及到多学科。设计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应该回到设计为民众服务,为现实服务,为生活服务的底层逻辑上。而高端设计类人才“专业博士”的培养,则应该给予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并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条件与标准再推行,或先在小范围进行试点,再推行不迟。
四、如何平衡“新文科”和“旧文科”
旧文科强调“分科治学”,新文科强调“学科融合”,旧文科强调思辨,新文科强调实作。在“新文科”语境下,新方案中的设计学毫无疑问要被赋予“新”的身份。但“新文科”建设的“新”,不仅是人文研究与科学、技术融合的“新”,更要重申对文科本身理解的“新”。文科教育的本质是要提供一种知识创新的素养,洞察问题的能力,构造和想象的能力。其实,旧文科中的哲学、语言、历史、文学、考古等早已是多种学科融会一炉,正是这些传统文科本身的思想力和创造力使得新学科交叉领域不断产生创新火花。以历史学研究为例,即便是面对今天学科跨度最大的领域——数字人文,要在关联数据架构中组织和析出可靠的历史信息,对材料的辨析与学术的洞察依然是最核心的能力。反观今天诸多的设计学研究,无论是学位论文还是项目申报,许多题目常常冠以热词“新文科”,而其研究内容即无文科的方法也无文科的思维,如果研究者连文科的基本视阈都还未形成,就来谈“新文科”,那这种研究也只能是新噱头,不可能真正做到为技术赋予智慧,为科学植入人文。
清华美院的向帆老师曾经分享过一篇IEEE视觉化会议中的获奖论文。她形容这篇短论文在奇葩论文季如一股清流,让她倍感愉悦。这是一篇关于一个命名为“世界山水”的研究项目的论文,作者是帕森斯学院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他从公开的数据库中下载了曼哈顿区域相关建筑数据,然后将这些不同的建筑数据转化为中国画青绿山水的形态,进而探讨人类和自然的终极关系。这个研究有着非常明确的设计思想和视觉化的设计方法,但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或新文科的理论,第一本文献是苏利文的《山川悠远:中国山水画艺术》,第二本文献是当代艺术家马岩松的《山水城市》。而这篇论文的作者,本科毕业于清华计算机系,研究生进入帕森斯学习数字艺术。严格意义上,他并非新文科方案中培养的设计人才,但他的“世界山水”则体现了旧文科滋养下的个人志趣和素养。
五、结 论
综上,几次学科目录调整,从“设计艺术学”到“设计学”再到“设计”,呈现了设计研究从分科走向融合的过程,也呈现了设计研究被逐渐工具化,“术”科化的过程。而新文科的建设,一流大学的建设,设计学科的建设,不仅要依靠学科体系的顶层设计,也要依靠底层实施中看不到经验传承和文脉绵延,才能形成真正的交融和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