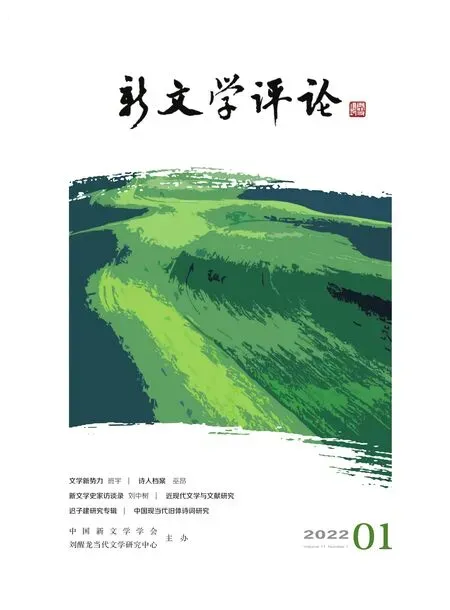从悲壮的群体命运到虚无的个体生存
——班宇小说阅读札记
□ 任 瑜
一
如果已经读过《冬泳》和《逍遥游》两部作品集,那么,我们谈论班宇的小说,就可以从《枪墓》开始。因为,《枪墓》虽然不是班宇最知名、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但它无疑是一篇具有阅读吸引力的、内容和指涉都足够丰富的作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班宇写作的成熟度;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我们谈论班宇小说提供一个可靠的方向指引。
就《枪墓》本身而言,它是个包含了多重故事的文本:叙述者“我”本人的经历,“我”所写过的故事以及“我”所讲述的故事。在这个多重文本中,叙述者“我”,在自己的经历和所讲述的故事中穿梭,最终将两者重叠——原来,“我”所讲述的故事,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如此,小说在结构上有了完满的发展和收尾,故事的内容和内涵也有了丰富的层次。当然,这种多重文本的巧妙组合,作为一种叙述方式,或者说,叙事技术,在当代小说的书写中并不鲜见。所以《枪墓》对这一方式的使用,虽然是自然而成功的,却也不是它值得被关注的主要原因。我们之所以要在回顾班宇小说的时候先从《枪墓》说起,既是因为它的文本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和风格,更是由于它在文本中对作者本人的某种指涉——如果留心的话,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的某些情节和细节中,看到与作者班宇自身的写作相对照的一些映射。
那些情节和细节是这样的:“我”曾经写过几篇小说,讲的是发生在北方的惨烈的故事。比如,出租车司机遇害后被投入枯井,无意中撞见父母秘密的少年被父母杀害。这些小说引起了女孩刘柳的注意。一次“我”和刘柳相聚,她要求“我”再讲一些“北方故事”,“我”回答说,那些刺激的故事已经没有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日常的故事。刘柳却说:不要这个(日常),要出人命的那种。因为,“冰天雪地,白茫茫一片,总得有点不一样的色彩点缀”。于是,“我”又讲了一个渐渐变得刺激起来的新故事,而刘柳在“我”的讲述中睡着了。几天之后,刘柳又提起这个故事,并说,“怎么你故事里的人,我都认识”。
认识是必然的。刘柳来自齐齐哈尔,“我”和“我”的故事来自沈阳。一个北方写作者所写的在生活中发生过的故事,让一个听闻过此类故事的北方读者感到熟悉并有所共鸣,当是题中应有之义。《枪墓》中“我”和刘柳关于北方故事的对话及相关描述便是如此自然地发生和发展的,并且巧妙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它们构成并联结起了小说中的故事,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同时还颇有意味地概括出了作者班宇在写作上的一些特点和方向——文本中的“我”所写、所讲的北方故事,在内容、风格乃至设计和规划上,恰恰和班宇本人的写作相似。
从这个角度来看,《枪墓》的指涉其实已经溢出了文本,将读者和作者也牵扯了进来。“我”和“刘柳”,作为文本中的虚构人物,也具有了现实性——“我”就是作者班宇,“刘柳”就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我”曾写过和即将写下的北方故事,就是班宇创作的小说;刘柳对“我”的故事的共鸣和期待,也正是我们对班宇写作的感受和反应。如此一来,《枪墓》作为文本,多少有了些类似元叙述的性质。不过,对于我们的阅读而言,小说有没有元叙述的意味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对此刨根究底。毕竟,就如另一篇小说《双河》中那个落魄作家“我”所说,像这样的术语和概念,不过是作品完成之后被生拉硬拽套上去的,又何必多加谈论呢。
值得一提的倒是,就在这篇《双河》—— 一部以一位失意写作者为主角的小说——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指涉。不过其中涉及的,是较为具体的创作方法和感受,并没有像《枪墓》那样对“自己”的写作做宏观上的概括。所以,还是《枪墓》更有助于我们对班宇作品进行具体的讨论。
确如《枪墓》所言,《冬泳》和《逍遥游》两个作品集写的都是北方故事,是班宇对北方这块肥沃而寒苦之地的冷静描绘。故事中的人物都是会令刘柳这样的北方人觉得似曾相识的普通人,而故事的内容,也正像《枪墓》中说的,有“刺激”(惨烈)的,有出了人命的,有相对日常的。比如《冬泳》和《枪墓》的故事透着暴烈和血腥,《盘锦豹子》《肃杀》《空中道路》《梯形夕阳》《工人村》《夜莺湖》《逍遥游》《双河》《蚁人》则是表面平静实则暗藏苦痛甚至涉及人命的北方日常。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就不难发现,尽管都是北方故事,《冬泳》和《逍遥游》对一些元素的选择和处理,以及呈现的取向和特征,还是有微妙变化的。甚至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遗憾和不足,也表现得不尽相同。
二
小说集《冬泳》中的作品,有一个令人难以忽视的特点:时代元素凸显。显而易见,在这些作品的写作中,班宇有这样的意图:将时代和社会背景具象化、情节化。具体而言,就是将具有时代印记和历史影响的事件与状况嵌入人物的故事之中,将情节直接与某些标志性的大事件或社会性状况连接起来。从我们读到的效果来看,这一意图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在这部集子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涉及影响深远的社会性变化,比如东北的衰落、产业的调整、企业的改制和破产;几乎所有的故事中都有数件具体、明确的时代性事件或轰动的社会性事件,比如下岗潮、再就业,以及足球联赛、非典、高考变革、彩票买卖、抗洪救灾、刨锛帮犯罪等等。
为什么要在以普通人为主角的小说中如此直接地写出历史性的事件和状况?当然是为了更为直观地呈现身处其中的人们——特别是小人物——受到的影响和人生的转变,这其实就是北方故事的主要内容。不管是《盘锦豹子》中的姑父、《肃杀》中的肖树斌和“我爸”,还是《空中道路》里的李承杰、班立新,《梯形夕阳》中的“我”,都在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大潮冲刷之下,身不由己地改变了人生的道路和状况,在愈来愈沉重的生活中挣扎,最终殊途同归,生命力逐渐干瘪。《空中道路》中的缆车之行,就是对这些人物命运的隐喻:人生的道路一度安全而顺畅,似乎还会一直如此,但突然之间,故障出现了,将他们卡在时代的关口,生活摇摇欲坠,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克制着无奈、愤懑、恐惧和苦痛,尽力地,也可以说是顽强地,活下去,或死去。
时代元素的加入,是为了突出在时代变化和社会变迁之中几乎无路可走的人们,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无从把握,他们在外部强力面前的脆弱、破败和坚忍。在具有历史性的时间段中遭遇并承受这一切的,当然不会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许多人,甚至几代人。所以,《冬泳》中对人物的描写,可以看作是用个人来折射群体——那片土地上诸多的同命运的普通人、小人物。这些北方故事,写“刺激”的死亡也好,写无奈的日常也罢,表达的其实是群体命运中个人的承受,反映的也不仅仅是个体的命运,更是时代洪流之下一群人的遭际和境遇,是群体性的命运和境况。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不是有意,《冬泳》就是班宇以克制的冷静和直观的冷酷,为这块黑土地上失去的活力和尊严奏出的一曲挽歌。
不过,遗憾的是,在这挽歌之中,我们看到了一群人,却没有看清一个人。因为,他们作为个体的面目是模糊的、类似的。这也许是时代元素强化之下的后遗症。对事件、情节的强调,让叙事停留在表面,没有更多的能量和空间去描绘人物。注重社会的、外界的、命运的力量,会让人物和读者陷入这种力量之中任凭宰割,人物不能拥有丰富的人的个性,读者也不能走进他们的内心。结果就是,我们可能会为了人物的命运和故事而震撼、震动,却没有被感动。这与作者在写作时情感的克制和表达的冷静无关,只不过再一次证明,不管什么样的故事,一旦人物缺乏了所应有的复杂性和个性,就很难深深地打动我们。
从一个更为感性也更为严苛的角度来说,写作,即便是现实主义的写作,重要的从来都不是怎么讲故事,也不是讲多大或多小的故事,重要的是,就如E.M.福斯特在夸赞霍桑、福克纳、弗兰纳里·奥康纳等人时所强调的,描绘出具有复杂性和个性的人物,让读者永远地被感动。
三
《逍遥游》所呈现的特点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种阴郁而无望的美学风格。
不管是作者的有意营造,还是自然而生,这种风格的形成和凸显,离不开两个元素——死亡和虚无——的氛围加成。
文本中的死亡戏码,本来就能够自然、有效地造成灰暗阴郁的氛围,更何况《逍遥游》中还有那么多与死亡有关的感觉和印象,足以为小说笼罩上一层又一层的冷峻色调了。说起来,早在《冬泳》中,班宇就写过不少死亡:突如其来的谋杀、被掩藏的误杀、影响深远的意外之死、罪恶的劫杀等。显然班宇一直不惮于多写死亡。到了《逍遥游》,死亡的分量好像更突出了。难道真就如《枪墓》中刘柳所说,写作,还是要讲那些出了人命的故事,要为这“白茫茫一片”的世界“增加一点色彩”吗?
也不尽然。其实,在《逍遥游》中,死亡事件的数量可能并没有增加,不过是死亡的样态更为丰富了——看得到的,想象中的;具体的,抽象的;逼近的,遥远的;意料之中的,猝不及防的。比如,《逍遥游》单篇中有轻描淡写的病故,有虎视眈眈的死亡威胁,还有虽生犹死的生活状态;《夜莺湖》中有神奇失踪的死亡;《渠潮》有消失式的假死,万里高空之上的自尽,造成误会的棒杀;《双河》中有报复性的自杀和复仇的他杀;等等。此外,死亡的发生也显得不可预测,仿佛随时会出现在文本的开端、结尾、中间,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在阅读的时候总是觉得,死亡的阴影似乎无处不在,而且神出鬼没:有时是大剌剌地横梗于头,有时是静悄悄地埋伏于视线之外,有时是一点一点地冒出来,有时又像终点线一般隐隐约约地悬在远方。如此种种,让死亡的声势变得愈发浩大,以至于在没有死亡出现的时候,它也潜伏在我们的潜意识甚至是预期之中。
这样的效果说明,死亡元素在《逍遥游》中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和强调,正如《冬泳》中对时代元素的突出和强化。看到班宇如此得心应手地书写和使用死亡,令人不由想起女诗人普拉斯的一句诗歌:“死亡/是一门艺术,像别的一样。/我干这个相当在行。”①说班宇已经把死亡变成一门技艺,并不算夸张。
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那些死亡,更多是美学意义上的必需,而不是道德或伦理意义上的必要。当死亡成为一门技艺,它也就沦为了一个文本工具——是故事情节和叙述线索的推手,是文本腔调及情感色调的涂料。《逍遥游》就是这样,死亡元素在文本中实现的,主要是自己的美学职责,达到的也主要是叙事的美学效果。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死亡本是宏大、深刻的,包含着一个写作者所需要的无限话语,但在这里,它被工具化了,它所包含的美学价值之外的其他可能,都被遮蔽了,或者说,被舍去了。
所以,即便有着浓重的死亡阴影和诸多的死亡事件,也很难说班宇的小说是死亡主题。那么,《逍遥游》真正的主题又是什么呢?应该是与死亡相对相依的生存,是人物存在的境况和生存的样态,也就是帕慕克所说的,“主人公的生活,他们在小说世界的位置,他们以一定方式感知、观看并介入世界的方式”②。
实际上,《逍遥游》所书写的也只有一种方式:溺水式的、苟延残喘般的生存状态。从《双河》《逍遥游》《渠潮》《蚁人》中,看不到多么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也找不到什么高大上的灵魂,只有狼狈、杂乱、茫然的日子和得过且过、疲累又淡漠的状态。大家都是在生活重压之下、在不可承受之轻中的普通男女,落魄、失意,不抱希望。对于这个无序的世界,要么是厌倦的、被动的,要么是卑微的、逆来顺受的;要么徒劳地坚持,要么默默地沉溺。他们的姿态和行动似乎都在说,既然生活已经如此,命运也是定数,那我们还能做什么?这就是《双河》中“我”所回忆的和前妻一起的生活: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一切仿佛都搅在一起,生活混杂无序,几近无解,不可调和”③。
作为《逍遥游》的主题内容,对这种没有生机和活力的、虚无主义式的个体生存的描写和展现,让小说获得了更强烈的阴郁而无望的色调和效果。毕竟,相比死亡的阴影,无解的虚无主义具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因为虚无的生存比死亡更黑暗、更可怕。
虚无色彩的存在也解释了为什么小说中会出现那么多的死亡。芝加哥学派的批评家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谈到虚无主义文学时曾说:“……虚无本身不能得到描绘,更不用说得到戏剧性的表现了,而文学作品又必须总要表现某件事,或正在做某件事的某个人……那么就不必惊奇,我们看到许多迷惘的人物,置身于毫无希望的情境之中,这些人物唯一的发现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发现,他们最后的行动是自杀或者其他绝望的表示……”④也就是说,死亡不仅是美学的需要,也是在宽泛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必然结果。
在死亡和虚无的双重加持下,《逍遥游》那阴郁无望的美学风格便鲜明地凸显而出。有意味的是,阴郁、无望、冷酷,作为班宇有意追求的美学效果,还有着明确的地域性,它们可能是最适合北方故事的美学风格。北方的这片黑土地所滋养和培育的东西——顽强的生命力、低伏的生命,严酷的环境、热情的生活,萧索、沉默与生机、蓬勃,如此等等,纠缠在一起,形成了具有荒诞色彩的组合,其中的残酷和黑暗,与那种阴郁无望的色调,有一种天然的贴合。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简直可以把《逍遥游》的美学效果,视作另一种黑色荒诞的哥特风格,可称为“东北哥特风格”。
不过,或许是班宇对这种风格的营造太过成功,有时不免令人生出疑虑,关于小说文本的价值表达究竟指向何处,关于班宇到底怀着什么样的感受和意愿写下了此类美学风格的作品。我们只是希望,他对这种“东北哥特”的书写,会像康拉德书写黑暗那样,“行走于深渊边缘却不会坠入其中”⑤。
四
如果粗率地概括一下,我们可以说,《冬泳》是反映时代之中不无悲壮的群体命运,《逍遥游》则是书写带有虚无色彩的个体存在。从情感的角度来看,从《冬泳》到《逍遥游》,有一种从愤懑的绝望到平静的无望的转变。这是我们对班宇小说的感受和解读,当然很可能是误读。但无论如何,《冬泳》和《逍遥游》让我们认识了班宇的写作,既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些特点和风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写作上的成功及遗憾。
在有些作品的写作中,班宇似乎很清楚想要达到的文本效果,也很成功地实现了欲求的效果:选择可用的元素组织情节,保持一种语调进行叙述,插入“刺激”性的事件,在合适的地方添加修辞性话语,努力营造某种超越性的诗意。如此,小说的故事和内涵有了,“实”与“虚”也完备了。可是,这样写作班式的精心设计,是不是有模式化的嫌疑呢?
再继续问下去,写作有模式吗?或者说,小说有模式吗?从文本分析的解剖式批评、小说修辞学以及写作课的存在来看,小说显然是有写作模式的。既然有模式,那么,掌握了一套话语模式,就足以成为一名小说写作者,甚至是成功的小说写作者,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从更为传统和保守的文学观念来看,模式毕竟是小说中属于美学范畴的一个层面。如果像纳博科夫那样,把小说视作纯粹的艺术品,那么,仅仅追求美学效果也就足够了,模式可以产生美学效果,也就能够产生艺术品。然而,小说之为文学,文学之为“人学”,又体现在哪里?艺术的生命的力量又从哪里诞生?我们真的能够相信,从模式的缝隙中,可以开出动人的花朵来吗?
提出这样的疑问,当然不是否定班宇的写作,而是对班宇的写作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其实,从《山脉》《安妮》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班宇对变化和开拓的尝试。这些尝试和改编,即便不将之视为所谓的“瓶颈的突破”,至少能够表明班宇在写作上不故步自封的追求。既然如此,我们作为读者,对他的写作产生更大的期待,也算不得虚妄和严苛。
在对小说的释义五花八门甚至自相矛盾的今天,对于一些写作者来说,批评家珀西·卢伯克那并不完美的古老观点,依然能够提供有益的启发:“直到小说家把他的故事看成一种‘显示’,看成是展示的,以致故事讲述了自己时,小说的艺术才开始。”⑥
注释:
①转引自乔治·斯坦纳著,李小均译:《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6页。
②奥尔罕·帕慕克著, 彭发胜译:《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③班宇著:《逍遥游》,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3页。
④韦恩·布斯著,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273页。
⑤伊塔洛·卡尔维诺著,王建全译:《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页。
⑥转引自韦恩·布斯著,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