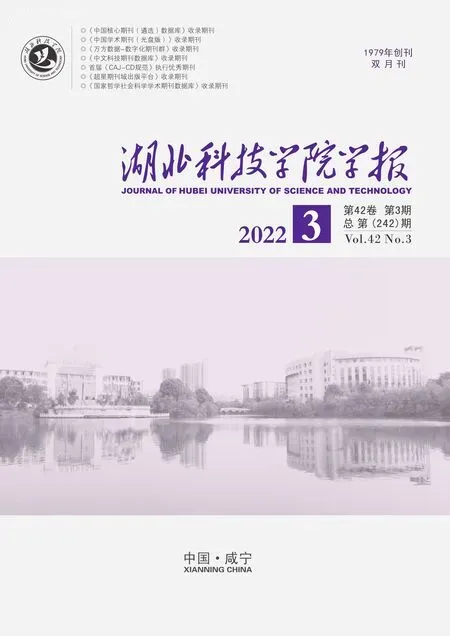我国学者的《瓦尔登湖》研究兴趣驱动因素探讨
董丹萍
(云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从1984年起,《瓦尔登湖》逐渐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兴趣。2004年后知网每年发表数十篇相关论文。2013年《瓦尔登湖》研究达到顶峰(发表论文67篇),之后一直保持较高位波动。《瓦》文研究方兴未艾,呈现出清晰的脉络,体现了时代对于国家和个人的召唤。本文对《瓦》文研究进行脉络梳理、从国家议题和个人审美两方面分析其研究兴趣背后的驱动因素,探究学术研究与时代大环境的互动。
一、《瓦尔登湖》研究的脉络
我国学者的《瓦尔登湖》研究呈现出几个清晰的脉络。第一个、也是最显著的脉络是自然思想、生态伦理、现代环境运动[1-9];以及生态文学及其影响研究[10,11]。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于文夫和龙其林都获得了中国社科基金的资助,他们在各自项目研究中都将《瓦尔登湖》当作重要研究课题[12-15]。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体现了时代的重大议题,有关《瓦尔登湖》生态角度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瓦尔登湖》的生态翻译学研究视角[16]。第二个脉络探索《瓦尔登湖》所呈现的儒家、道家、禅家、甚至墨家等中国古典思想文化元素[17-21],呈现出视域融合、开放包容的跨文化互动。第三个脉络是文学审美视角,从心灵审美、平行文学、生活哲学的视角来研究[22-24],探讨《瓦尔登湖》与现代中国读者的精神契合之处,比如简化生活、诗意栖居。第四个脉络是译介和传播研究[25-33]。第五个脉络是综述[33-37]。当然还存在其他研究角度,比如叙事学、文学的哲学性、解构主义、政治哲学等,但是比较零星,这里就不赘述。
二、我国学者对《瓦尔登湖》的研究兴趣驱动因素
(一)打破《瓦》文的寂寞
为了促进《瓦尔登湖》在中国的传播和译介,相关研究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脉络。知网上可查到的最早一篇发表于1984年的《瓦尔登湖》研究论文关注徐迟译本的错译和注释过少的问题[25]。何怀宏1988年提出:“想为一本寂寞的书打破一点寂寞”[38](P104)。2003年,曹亚军对2002年之前的梭罗研究进行了统计,发现文化传媒上对他是“负接受”,而严肃学术界对他是“零接受”,他指出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梭罗时代类似,梭罗所传递的信息不应受到漠视[32](P52)。2005年,李静用功能对等理论分析了《瓦尔登湖》三个中译本的翻译效果[26]。2006年,刘曼使用多元系统理论对三个《瓦尔登湖》中译本进行分析,提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不同地位影响了其翻译策略;翻译策略反映的是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翻译规范,并无对错之分[29]。2018年,赵黎明对徐迟译本直译手法所造成的错误进行了分析。[28]
(二)中西方文化视域融合
我国学者对于梭罗素来有一种亲切感,因为他“不喜欢希伯来的圣典而偏爱东方的典籍”[39](P38)。《瓦尔登湖》广征博引,融入了古希腊罗马神话、印度佛教和我国的儒道思想,让我国学者感到自豪。刘略昌(2015)认为徐迟在翻译《瓦尔登湖》时其实不仅是在传达原文信息,更多是巧妙剖白心迹,进行自我言说[40]。这其实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视域融合,在观察欣赏自然的时候,梭罗借中国典籍言说超验主义思想;中国学者又何尝不是借《瓦》文研究倡导中国典籍和传统文化,呼应了加强跨文化交流、扩展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重大议题和心理诉求。
1.《瓦尔登湖》挪用的儒家元素
《瓦尔登湖》糅合了大量儒家名言,多是挪用。比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被梭罗用于强调不可将自己的想象当作自己的认知;又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梭罗用这句名言来说明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生命境界。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同上,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梭罗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众人关心的是汲汲营营,而非生活的本质。又如“神鬼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 “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这几句被用来阐释超验主义自然观。 “德不孤,必有邻”,梭罗引用来说明远离社会、与自己思想为伍的人是不会感到孤独的。在评论自己不愿交税而被捕入狱的事件时,梭罗也引用了孔子的话,“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表明对允许奴隶制存在的美国政府的反对。梭罗还引用曾子名言,“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来表达反对饕餮、大吃大喝的态度。 “三军可夺其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来说明个人独立思考的重要性[17](P103,104)。被挪用后,这些名言与儒家主旨相去甚远。
谢志超[41]指出,梭罗采用《四书》的 “君子观”来阐释个人主义思想,但这二者终究“貌合神离”:个人主义对于我国儒家思想是一个水火不容的概念。梭罗认为个人必须放弃俗世所规定的“自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他从未娶妻、从不投票、拒绝向政府纳税、对社会持一种拒绝的态度。而儒家的君子价值却围绕个体对社会群体所应尽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就揭示了文化DNA的区别。
催生《瓦》文的社会与催生儒道等思想的我国传统社会之间有着天差地别,在各自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大不相同。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19世纪美国和封建主义经济繁荣的传统中国文化之间,一个追求个人主义和文化独立;另一个则追求集体主义和文化巩固。《瓦尔登湖》所宣传的超验思想认为人类灵魂与超灵能直接沟通,个人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来寻求真理,蔑视与否定外部权威和传统;在梭罗的个人实践中,所导致的极端负面情况包括道德感的严重缺失、疯狂自恋、对他人无感,同时又故作神圣姿态、对社区公众持居高临下的说教态度、拒绝社会生活、甚至拒绝生活本身的物质和人际需求、而追求一种精神的纯洁性[42]。与之相反的是,传统儒家思想则强调个人对社会群体所应尽的道德责任与义务,从个体自我修养出发,最终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我修养始终指向社会群体;当然如果发展到极端,可能会出现个人受到压制的情况。
程虹[43]提出美国学者看重的是梭罗的独创性、自然文学写作、超验主义、公民良知和坚持己见的勇气。可以看出没有一项与我国儒家思想有关。
一些学者会进行平行类比。比如,冒键[19]在梭罗身上看到了颜回的安贫乐道。谢志超[41]认为梭罗对美国文化的影响是通过书信、随笔、日记和演讲等这些方式来实现,并非通过一套完整系统的超验主义理论,这一点和孔孟相似。
2. 《瓦尔登湖》折射的隐逸文化
李冬君[44]认为我国古代的山水画家荆浩可以视为梭罗的精神先驱:他们从社会体制中退隐,寻求个人精神的独立。周晓立对比了我国隐逸文化和梭罗的“隐居”行为。他选择了明末袁宏道的话来说明我国隐士是出于对官场的失望而被迫离去,“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每照须眉,辄尔自嫌,故园松菊,若复隔世”[18](P110)。相较而言,梭罗是主动进行生活试验,探寻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简朴美妙。刘略昌[45]对梭罗隐士观进行了辨析,认为梭罗根本就不是、也从来没有自称为隐士。之所以会出现梭罗是真假隐士的论争,更多是文化的折射。
3. 《瓦尔登湖》呼应的墨、禅、道家思想
邓艳艳[46]认为梭罗在精神上与我国禅宗和墨家气质相近。汪愫苇[47]将梭罗和庄子作品中的寓言手法进行了比较。张明,许小花[48]认为梭罗的自然生态伦理观和庄子的“尚美、简朴”思想有着共性。
以上研究是从“契合”“共鸣”的角度进行平行对比甚至类比,就好似文化棱镜中漂亮的色彩,体现了文学经典在跨文化视域融合下的奇妙折射。
(三)应对全球性环境挑战
1. 《瓦尔登湖》生态伦理研究
从1996年开始,我国学者就已多次提到《瓦尔登湖》对美国现代环境运动的影响[49],但是我国基于生态诉求的《瓦尔登湖》研究直到2002年南北的一篇文章才真正开始。南北[1]提到《瓦尔登湖》属于美国出版的环境主义者书架丛书,在漫长的岁月中被称为“绿色圣经”; 《瓦尔登湖》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在于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环保问题,包括我国的黄河断流和沙尘暴的肆虐。南北表达了对于环境保护的强烈诉求,将之作为《瓦尔登湖》在我国传播的意义:有助于铸造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伦理,建设自己的绿色家园。同年,北大苏贤贵[2]从自然思想和非人类中心的生态伦理两方面探讨了梭罗对现代环境运动的影响。邹建军,白阳明[5]提出梭罗对自己的地理漫游进行了细致书写,体现了“生态自我”的觉醒,克服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开始认同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乔婧[6]有关《瓦尔登湖》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获得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项目“宁夏环境保护执法问题及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机制研究”的资助。
与《瓦尔登湖》相关的生态研究还获得了国家社科资金的资助;比如包庆德,宋凌晨[50]的“生态哲学基本范畴研究”(11BZX02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他们的论文《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生态主义思想评析——纪念亨利·戴维·梭罗200周年诞辰》发表的期刊《鄱阳湖学刊》是国内首家综合性生态学术期刊。
2.生态诉求的文学呈现
《瓦尔登湖》得到了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和国家社科基金的大力支持。比如龙其林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13FZW051);赵树勤、龙其林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编号:06BZW056)将《瓦尔登湖》作为研究重点,认为《瓦尔登湖》对我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9]。
张丽军[10]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古代人的万物有灵论将自然环境置于人类的道德关怀之中;而近代的机械论宇宙观则将人类从自然中割裂开来,使其沦为任人宰割的客观存在。文艺复兴运动将人从教会统治下解放出来,开始歌颂各种欲望和享乐,金钱和物质的欲望开始挤压人的情感空间,人在无意识之中遭遇到了“降维”打击,成为了“单向度”的存在。由此,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后,个人对他人、生活和世界失去了信任,找不到可以回归的精神家园。个人不仅感觉他人就是地狱,甚至自我也是地狱:个人与自我开始分裂和疏离。
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诞生的根源。张丽军将生态文学[10]定义为诞生于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现代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背景下,描写人与自然关系、映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对自然、人、宇宙进行审美观照和道德关怀、呼唤人与自然、与他人和宇宙融洽和谐、追求自由与美的文学。生态文学分为亲合和疏离两种,亲合生态文学包括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美国的自然文学。疏离生态文学的经典之作是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无论是疏离、还是亲合,自然都被推到了文学舞台的中心位置,成为了一个精神主体。正是在梭罗这里,美国自然文学演变成了生态文学。梭罗被称为:“生态文学的开创者”[10](P27),因为在梭罗的笔下,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机的,整个世界就好似活生生的诗歌。人与自然的交往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交往。
(四)构建心灵家园
很多人在寻找《瓦尔登湖》并感觉他们真的非常需要这本书,徐迟对此的评论是:“物质越丰富,梭罗的名声也随着他所厌恶的物质而增长。”[51](P70)当人们开始感觉到物役的痛苦,就会想办法寻求某种逃离和解脱,至少是心灵上的解脱。
1.诗意栖居的心灵共鸣
《瓦尔登湖》与我国文学、甚至人文精神的某种心灵契合、趣味相投、审美一致等,是学界最常见的评语。林语堂认为,“就其整个人生观来说,梭罗在所有美国作家中最具中国情趣。作为中国人,我感到与梭罗心心相通。我可以将梭罗的文字译成中文,把它们当作中国诗作向国人展示,没有谁会发生怀疑。”[52](P122)何怀宏就如同写自己的散文诗一样,再现了《瓦尔登湖》自然栖居的诗意,“他爱给他的生命留下更多的余地。他有时坐在阳光下的门前,坐在树木中间,从日出坐到正午,甚至黄昏,在宁静中凝思,他认为这样做不是从他的生命减去了时间,而是在通常的时间里增添了许多,超出了许多。”[38](P108)在某种意义上而言,《瓦尔登湖》构成了世外桃源一样的文学存在、心灵世界。
2. 活在当下的生命之美
梭罗最不愿看到的是,春天已经来到了,而人们居然还停留在冬天, 因此他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保持警醒,始终让自己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上,他的写作让读者在司空见惯的场景和日常的消耗里,抬头看见一颗青翠欲滴的树[53]。
3.自然文学的亲切与呼应
苇岸[54](P284)激动地宣布:“我对梭罗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语言分为有机和无机两种:无机语言是指与工业文明相呼应的文字表述,其特征是抽象、思辨、晦涩、空洞,深奥到了自我封闭的程度,而有机语言是指文字仿佛是活的生物,有着血温,富于质感。梭罗的文字散发着清新而葱茏的植物气息,他的文字中流淌着生命的汁液[53]。
4.阳光下的劳动与健康
刘海燕[53](P40)强调劳动的重要性。她提出,“那些最具有平常心的事物,才是尘世间最直接的温暖……使人的生活和思考沐上了一层阳光的质地。”在她看来,《瓦尔登湖》中所体验的,就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生活、以生活为基础的艺术,正如从事体力劳动的托尔斯泰、亲手种植数百颗向日葵的黑塞那样。
(五)《瓦尔登湖》对现代人的精神意义
1. 《瓦尔登湖》是现代心灵疲累之极时的有效慰藉
《瓦尔登湖》号召世人简化生活、摆脱物役,不再迷失在自己所制造的种种虚假需求之中。在现代都市丛林中生活的人,在读到梭罗有关做不完的苦役、忙不完的粗活、跌价的劳动、被剥夺的时间、几乎成为疾病的忧患焦虑等评论时,对自己的压力、委屈和劳累肯定会有所释然。对自己所极力追求的东西,也许就会问上一句:有必要吗?值得吗?值得的话,自然继续拼命,万死不辞;不值得的话,则会退而思之,放弃因虚荣、贪婪等导致的无谓的追求。
包庆德,宋凌晨[50]将《瓦尔登湖》所揭示的劳动异化现象与马克思理论进行联系和研究,他们指出私有财产和独立精神的缺失会造成劳动的异化,即梭罗时代的人盲目追随新教工作伦理和传统生活方式,最终导致劳动对于人而言已经成了外在的、甚至敌对的存在,在劳动中人们无法肯定自己的价值,反而会否定自己;在劳动中人们无法感到幸福,反而是感到非常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备受奴役、折磨和摧残。总之,要时刻警惕物质主义、道德上的盲从行为,并随时审视自己当下的生活是否值得,必要时,简化自己的生活,进行精神和心灵的追求。
2. 《瓦尔登湖》是平衡个人立身处世的精神基石
梭罗在美国独立日搬入林中小屋,是为了强调个人精神独立,鼓励个人摆脱文明社会的物役,从个人的工具定位中脱离,不再成为填充各种社会岗位的棋子,而是努力寻求人之为人的完整性,让人再次成其为自己。
(六)美国文学研究
《瓦尔登湖》和梭罗一直是外国文学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刘略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是《跨文化传播中的镜像变异:基于<读书>杂志的梭罗真假隐士论争再思考》[45]。赵莹,张建国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当代科学散文的生态批评”(13BWW046)从物质生态批评视角对《瓦尔登湖》进行再解读,提出施事能力是人类和非人类的自然都具有的能力,是物质之间的内在互动,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的自然,都有生成意义的能力。他们都是文本的描述对象,同时本身也都是文本。即一切物质都能叙事。大自然本身具有语言,具有叙述能力[55]。
千禧年后,硕博生开始参与《瓦尔登湖》的研究[7,10,11,26,31,41,43]。硕博论文有两个特征:首先,对学术规范有了严格要求,尤其是文献检索方面有了极大提升。其次,脱离了千禧年之前十几年中“共鸣、契合、呼应、亲和”等思路,对《瓦尔登湖》所代表的外国语言文学展现了真正的兴趣,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张丽军[10]将《瓦尔登湖》作为生态文学的重要著作,来研究人类生存困境的艺术预演。程虹[43]将《瓦尔登湖》置于美国自然文学传统中进行考察,强调梭罗参与自然、实践自然的经历对美国后来的作家们产生了比爱默生更大的影响,比如美国自然文学作家Joseph Wood Krutch 认真采纳了梭罗的建议,以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为自己的写作对象。事实上,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自然为主题、在不同地理环境中写作的自然文学作家群。他们有着强烈的位置感,与脚下的土地联姻,描绘自己的精神家园。
(七)反思批判
程映红[56]将梭罗的“隐居”思想和其生活事实及在当地人中的口碑进行了对照研究,发现所谓 “隐居”根本是闹剧:梭罗的木屋被公路、铁路包围,邻里亲朋的住所都在散步距离之内;“隐居”的两年期间,梭罗几乎每天都要到康科德镇上去,随时会回到父母家中,他的亲朋好友更是随时探望,经常聚会、野餐。在隐居之前,他和朋友一起钓鱼野炊时不慎引发森林大火,毁掉了三百英亩林地,引发本地人强烈不满。他选择在美国独立日搬入木屋,更是故作姿态,意在减弱在本地人中的恶评。通过传记研究发现《瓦尔登湖》并非是在隐居期间所写,而他在文中却称在写《瓦尔登湖》的时候他是在森林里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只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来养活自己。(虽然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瓦尔登湖》的成书和文字的书写是不一样的,《瓦尔登湖》最初的记录形式是日记。)通过种种对比描述,程映红成功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梭罗形象:一个游手好闲、在本地闯下大祸、在文字中“过甚其辞”、“故作姿态”、甚至达到“虚伪”程度、本地人眼中绝非圣贤(如果不是痞子的话)的文人。
程映红[56]不仅意在指出梭罗的虚伪,更意在指出现代人在“隐居”话题上的虚伪。他们越来越热衷的乡野游与其说是对“单纯和简朴”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新形式的奢侈和贪婪。程映红对“隐居”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她并不认为现代人类是孤独的乡野生灵,而是城市的社会的动物。
不过程映红似乎混淆了梭罗其人和其书,模糊了现实与理想或者思想的界限,其假设是有某种理想的人则必然百分百践行着自己的理想而且是该理想在人世的象征和化身。这个假设忽视了人之为人的局限:身在人世,必然犯错,但是他的思想或者理想仍然可以为他人提供指引。正如,汪跃华[57]所坚持的,梭罗走下神坛,并不能抹杀《瓦尔登湖》对人生清醒的反思;理想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可以指引人类的精神生活。张克峰,徐晓雯[58](P38)也强调:“作家的光辉当然要靠作品”。“因人废文于文学批评无益”。何怀宏[59]更是提出程映红的预设立场使其描述并不可靠,有更多的美国传记作家“如实直述”,直接或间接地反驳了针对梭罗的各种嚼舌和谣言。因此,这种批判的声音很快在学术界被淹没下去。
三、结论
本文是对1984-2019年期间知网《瓦尔登湖》研究脉络的评述,提出我国学者《瓦》文研究一方面是国家层面上应对全球环境挑战、促进跨文化交流、大力推广中国文化、推行外国文学研究三大议题的影响,激发了有关译介和传播、生态、中国文化元素、美国文学等主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读者个人层面上努力摆脱物役、寻求宁静心灵、享受自然文学的追求。我国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保护、快速现代生活对个人所造成的压力等会继续存在,《瓦尔登湖》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继续成为我国各个学科的学者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2020年《瓦》文研究确实也在延续以上的主题[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