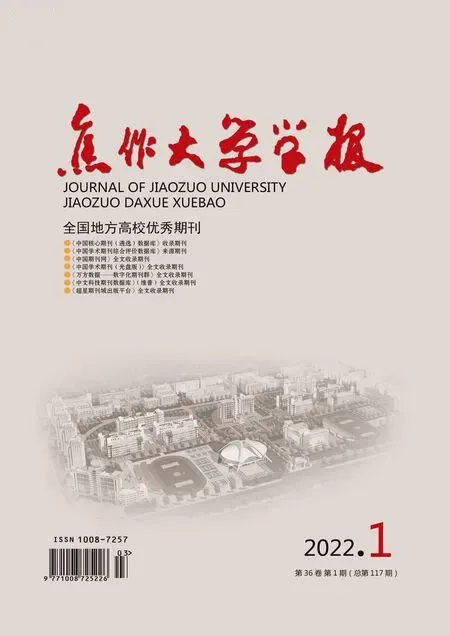我国《民法典》中居住权制度完善研究
郭 放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1.《民法典》居住权入法的现实意义
中国《物权法》未设置居住权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其一,建国以后,中国民法研究者对日本的民法典研读较多,受日本的民法并未设置居住权的影响,尽管借鉴了大陆法系民法制度,但也只是承袭了地役权制度,而并未继承居住权等人役物权制度。其次,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迈入市场经济时,我国的法治进程也在不断进步。然而当时有房产的人还很少,房地产行业也比较落后,无法设定居住权,更没有涉及有关居住权的纠纷,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好先制定比较成熟的、社会急需的法律制度。对于居住权这种暂无较大适用环境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暂时予以搁置。最后,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很多中国家庭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父母大多尽其一生财富和积蓄为子女购置房产,子女承担起赡养父母晚年生活的义务。而西方国家与我国不同,很少有类似我国养儿防老的观念,家长往往将子女抚养成年后就不再供养他们,没有把财产留给子女的传统。因此,许多西方国家都继承了罗马法中的居住权等人役权制度,以保障相关弱势群体的生存需要,这也是我国一直未设立居住权的原因之一。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居住权编入《民法典》物权编第14章,作为我国司法人身财产权的一种。中国居住权保障制度的形成有着不能忽略的现实意义。其一,让我国所有公民都住有所居,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民生政策,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且国土资源有限,房屋建筑成本高、房价居高不下,想通过所有权来满足全体人民的住房需求是不现实的,居住权的产生可以在尊重所有权人意愿的前提下,合理分配房屋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提高不动产的利用效率,进而满足住有所居的社会需求。其二,居住权的设立为相关的司法实践提供了立法依据。在裁判文书网站搜索以“居住权”为关键字的民事案件后发现,与居住权相关的纠纷在逐年递增,随着带有投资性质的居住权的发展,居住权纠纷的类型以及当事人的诉求也越来越多。而在《民法典》出台以前,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关于居住权的规定,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只能援引一般民事法律原则或债权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由于缺少明确的立法,相关案件的当事人无法得到物权上的保护,法官的裁判往往也有较大争议,无统一适用的标准。《民法典》物权编居住权制度的产生,使司法实践有了统一的立法依据,有助于提高我国司法权威性及公信力。其三,居住权的设立可以完善我国的物权法体系。在《民法典》出台以前,我国《物权法》中对用益物权的保护条款,仅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自然资源使用权这类有关农业的用益物权,然而不动产除了土地外,还包括土地上的定着物,即房屋,缺少关于房屋的用益物权无疑是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不足。特别是我国还采取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还排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很成熟的物权类型,于立法体系而言很不妥当。对于中国人役权和地役权之间的二元体制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实行的是财产权和他物权的划分结构,而在他物权中又包括了用益物权和担保财产权,所以就把居住权重点放在了用益物权体系中亦无不妥之处。
2.我国居住权规定存在的问题
2.1 投资性居住权的缺位
尽管法规中并未具体提及投资性居住权,但投资性居住权却在社会中客观存在。在海南三亚市区,当地政府有土地但没有资金,项目投资方有资金但没有土地,政府和投资方合作开发房地产,在此情形下政府拥有房产所有权,而投资方在一定年限中获得所投资房产的居住权,待约定期限到期,政府完全拥有该房产权。这个模式既解决了开展房地产合作各方的短板,又同时减轻了当地就业压力,推动了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从而达到了各方的协作共赢。除了“政府——投资方”合作模式之外,来自欧美的时权式酒店在中国也同样具备了很大的投资潜力市场,它将与房产业、酒店行业和旅游产业相结合,以适应投资需求多元化和房地产产业多样化。在时权式酒店模式下,酒店企业管理层向投资人出租酒店某个时段的所有权或居住权,投资人就能够在该时段利用酒店收益。随着三亚、深圳等城市建成时权式商务酒店后,大部分的经济发达城市,尤其是海滨城市都将陆续引入这些时权式商务酒店。另外,在婚姻家庭关系、遗产等法律社会关系中,也可能存在允许投资居住权人通过居住权获利的情况。投资性居住权适应商业社会规则,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也会在商业社会实践中更加普遍。
2.2 居住权设立条件缺失
《民法典》的第三百六十六条和三百七十条规定,对居住权的确立大致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依双方当事人所订立的契约而获得居住权;其二,由住宅产权人通过遗嘱行为为特定人设立的居住权。《民法典》未规定依法律规定设立居住权的方式,实属不妥[1]。《民法典》把居住权的具体创设权力更多交给了各相关方当事人,以保证双方自愿,但又不能兼顾对住房弱势群体的特定权益保障,这也不可避免地会和政府保护特殊群体权益的立法宗旨相悖,而没有对特殊群体的更具体化的保障条文和便利规定,无疑为另一方当事人继续侵犯弱势群体的权益,带来了巨大司法风险。
2.3 居住权利效力可否及于第三人
对于居住权的效力范围,我国法律没有进行规范,但需要关注的是,存在居住权关系以外的其他权益关联主体,以及他们如何才能享有与居住权人在一起居住的权益。在一些情形下,为了适应居住权人的一般生存需要,居住权人必须和其他人同居住,也就是在所有权人所有的房屋之上共同行使居住权人所拥有的权利。例如,居住权人年迈或者患病,需要保姆或者医护人员的照顾才能维持正常生活,这意味着居住权的行使主体不限定于形成居住关系的居住权人本人,还有可能是与居住权人具有家庭成员关系的人或构建服务关系的人员。有的学者认为基于维护居住权的设立初衷以及功能范围,其权利人的家人以及为权利人及家庭提供服务而与权利人一起生活的人员,都有权使用设立居住权的住宅[2]。
3.《民法典》居住权实现路径的完善
3.1 设立投资性居住权
设立了投资性居住权,就可以将居住权转移、承继,并允许有居住权的单位房产租赁,以维护居住权人的权益。而所有者与居住权人之间也可以利用居住权分担购房压力和风险,以达到对所有者的财富利用多元化与居住权人的正常生活之保障。故对建立投资性居住权的相关法规,笔者认为,投资性居住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产权人的融资需要,更偏向于推动产权人的财产运用方式多样化和发展资本金融市场贸易,设置投资性居住权的法律范围应该不局限于上文所说的设置投资性居住权的特殊情况。
3.2 明确居住权设立原则和条件
此次《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实际是指意定居住权,亦即通过采用契约遗嘱等方式,以充分代表双方当事人的意志。由于合同法具有自治性质,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性难,对约定内容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经常出现,在这过程中,弱势群体往往居于劣势地位,很难以通过公平方式与房产所有人签订公平契约,居住权也难以实现。我国学者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也曾提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设立居住权的方式,即法定居住权,认为法定居住权仅限于无偿设立的方式,且通常情况下只出现在婚姻家庭领域,因为该权利的设立目的只是为了解决赡养和抚养的问题,所以为了将法定居住权与《民法典》物权编规定的意定居住权区分开来,应设定法定居住权,以保证婚姻家庭中的法定无偿居住权与物权编中的意定居住权在法律规范方面的协调[3]。《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以裁判方式为当事人设立物权的,物权自裁判文书生效时发生物权变动效力,为人民法院以裁判方式确立当事人的居住权提供了制度支撑[4]。同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明确立法原则,基于居住权仍属财产权,需要完全尊重住房所有人的财产权,从而明确了在设立居住权时以意定设立为原则,以法定设立为补充的基本原则,在各方当事人确实无法取得合意且弱势群体的基本居住权益也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由弱势一方当事人提出,人民法院综合各种因素对居住人的住房困难进行审查与判断,从而采取强制措施为其在住房上设定居住权,以维护其最基本的居住权益。
3.3 扩大权利效力以及客体范围
一般认为,居住权的主体为自然人,但是由于居住权的行使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涉及设立居住权的主体以外的自然人,其行使主体的范围得以扩张。对于居住权行使主体范围的完善,曾大鹏认为,应根据不同的行使条件对居住权的行使主体进行划分,分为居住权主体与实际居住人两种形式,居住权主体应当承担居住权关系中设立的所有权利义务,其有权在所涉客体之上接纳具有家庭关系的必要共同生活人以及服务人员。实际居住人相当于居住权利的间接性受益者,不能够将此类人认定为居住权人。笔者认为无需对主体进行区分,规定居住权人必要共同生活的人可同样享有房屋使用权。居住权人当然地拥有居住于客体之中的权利,但是对于居住权涉及的具有家庭的必要共同生活人以及必要服务人员等人的居住范围,应当进行大体上的设定,以免居住权人滥用其居住利益而分享其权利。与其共同居住的人是居住权效力的享有者,却不完全等同于居住权人。因此,对于居住权的行使主体,笔者认为,居住权的效力可以从指定居住权人扩大到必要共同居住人,共同居住人的范畴为与居住权持有人同住的近亲属,以及与其必要同住的保姆、医务人员等。
4.结语
《民法典》设立居住权制度,体现法律保障特定自然人的居住权益,也增强了房屋的利用价值,更确切地说,是保障了社会中特殊弱势群体的居住需求,也丰富了房屋利用形式的多样化。
综上所述,尽管《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规则内容不够详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进一步解释条文应有的涵义,但是居住权的权利实践已经为之后的司法或者立法提供了基础,因此,国家应尽快出台居住权实施细则,弥补居住权规则现有的漏洞。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居住权的行使,才能真正实现房屋本身的价值,保障社会低收入群体拥有长期稳定的居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