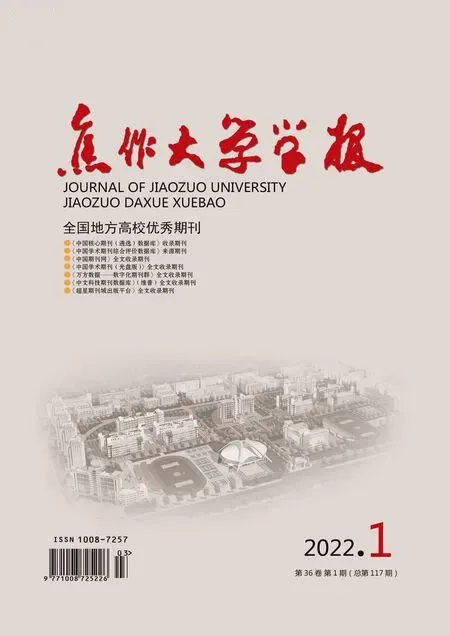网络直播营销活动法律监管困境与对策
刘 莹 张 欣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 淄博 255000)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短视频软件逐渐兴起,人们可以通过软件平台拍摄各种视频,扩大社交范围,网络电商抓住机遇,网络直播带货快速兴起。近期媒体曝光的网红以假当真销售奢侈品直播、糖水燕窝等翻车事件层出不穷,可见作为新兴的商业模式,网络直播营销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也带来了监管漏洞、多头执法等负面影响。
1.网络直播营销活动法律性质认定
2020年11月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要求压实网络平台法律责任,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进行宣传、推广,构成商业广告的,应按照《广告法》进行管理。这里以“构成商业广告的”用语规避了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法律性质认定,即将类似活动的界定留给了各级监管部门。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性质界定,笔者有以下看法。
首先,以传统电视广告为参照,其发展由早期按秒录制播出,逐渐发展到长达几十分钟视频介绍推销产品,或者专门请明星代言,为产品、服务的推销录制节目。对比如今流量变现的营销模式,商家将产品售卖的目光转移到移动客户端,通过短视频软件现场直播进行推广,夺人眼球。以传统广告与网络直播营销相比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可以理解为广告商业模式的创新,其本质、目的相同,并不违背2016年公布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中关于商业广告的认定,而且,《广告法》对商业广告的界定并不区分信息传播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差异,只要属于该法第二条第一款中的“一定媒介和形式”即可[1]。其次,以《广告法》总则中规定的适用本法情形为依据,分析网络直播营销活动是否属于商业广告。
从《广告法》总则的法条中,可以概括出商业广告的三个构成要件:以推销产品或服务为目的;针对大量不特定主体推广;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形式传播。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主要以社交平台为媒介向不特定用户群体推广直播,并在直播窗口与短视频购物窗口提供便利的一键式购物链接,同时兼具了三种构成要件,完全符合以规制、约束商业广告为目的《广告法》。至于网络直播营销活动是否需要完全符合法律每一具体法条的规定行为才能合法有效,《广告法》针对这一新型商业模式立法是否“过时”一类问题,并不影响我们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属于商业广告的性质界定。
2.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存在的法律监管困境
早期计算机互联网时期,广告大部分以短视频或者图片方式在各类网站中出现。如今互联网的应用传播方式由计算机的固定端模式转变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的移动端模式,视频平台大量涌出的同时,信息也飞速交换传递。但是平台视频上传内容鱼龙混杂,直播营销套取流量变现,随之浮现一系列监管问题。
2.1 事前准入审核与事中监管的力度不严
事前准入审核与事中监管的主要力量是平台自身,作为网络直播营销的主体,商家和主播的数量远远超过直播平台的数量,把控违规商家的难度要明显高于把控违规平台的难度。政府部门不可能全面监督管理到每一个商家企业。但是目前平台对商家、带货主播的准入审核标准过于宽松,事中监管存在被动性。
由于平台中的广告主体身份复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某一商品的宣传主播,存在隐蔽性强的特征。只要通过平台设定的系统审核标准,广告主体都可以上传视频,而且审核标准往往很宽松,对于平台而言,事前审核识别尤为艰难。实践中,为规避风险,商家、主播拍摄日常视频获取关注度后通过直播的方式宣传、销售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对于消费者而言,通过自媒体平台买货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直播间互动了解下单,二是在销售者拍摄的小视频下方点击购买链接。对于第一种方式而言,抖音、快手等新媒体软件为了增加带货直播间的人气,设置了短视频引流直播间来助推主播卖货。对于第二种短视频,卖货设置了feed流、Dou+来加热短视频人气,两者区别在于feed流针对企业,而Dou+针对个人,这种付费流量推广实质上是一种竞价的方式。相比之前网站以及平台发布广告必须得到行政许可、审批的前置条件,对于非特定类广告而言,竞价方式跳过监管大幅降低了广告准入门槛,准入门槛降低的同时也反映出事前准入审核标准宽松。对于事中监管而言,表现出监管部门被动监管的现状。由于网络直播具有实时性、海量化特征,监管机关不可能全部及时审核直播内容,在耗费人力、财力、精力的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工作的效率,并且监管人数与直播人数天壤之别,实时监控并不现实。事中监管大部分通过用户举报、消费者投诉等形式实现,并且虚假交易、刷单等行为很难发现,由于技术手段落后,监管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时,行业协会作为平台自我规范调控机制对于网络直播的健康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需要重视行业协会自我监管。
2.2 监管部门监管内容交叉,监管主体不明晰
由于网络直播营销活动所涉及的直播内容、商品、服务涵盖范围广,监管责任主体包括公安部、工信部、新闻出版署、文旅部等中央监管主体以及地方对应的监管部门,会导致监管部门监管内容重叠、多头监管的情况出现。以法律而言,《广告法》第六条分别规定了国务院和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主管国家、本区域的广告监督管理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广告管理相关工作的职责。法条规定存在两个模糊之处,首先,对于有关部门没有具体规定;其次,对于广告管理相关工作没有界定范围。并且,第五十三条规定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违反本法的行为。这里还是存在一样的问题,作为广告的举报部门应当穷尽列举,不应当以有关部门模糊而过。《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了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互联网直播服务信息内容的监管职责,作为网络直播另一负责机关,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的职责。
网络广告管理相关工作分布范围广,所涉及的信息内容丰富,监管内容交叉,导致有管理职权的监管部门多而杂,监管系统的庞杂会造成多部门配合不佳,互相推诿,都具备监管职责而都不愿意揽责的情况出现,没有确切的监督管理工作责任分配。
2.3 跨区域、跨平台导致监管执法困难
实践中存在由于网络直播带货发布地与实际成交地相分离,以广告发布地为始点呈点状向全国各地散射的情形,导致异地监管部门涉地区面积大、范围广。此外,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又分为两种:一是卖自己的货,自产自销没有中间商;二是卖他人的货,作为主播代理销售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交易平台产品。相比较第二种更难监管,由于责任主体增加,导致取证调查更加复杂困难。除了跨区域,跨平台也为监管执法增加了难度。现实中许多灰色产业,比如小作坊化妆品、高仿鞋、精仿包不敢光明正大打广告,往往都是拍摄含有商品的视频,以正常视频掩盖商业广告的本质,以前期投入资金做推广,将视频号推广出去,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积累到一定量获取信任后,通过建群、私聊等方式添加私人QQ、微信等聊天账号,更有甚者为了降低被查处风险,选择蝙蝠等加密聊天软件销售非法产品以逃避监管。由于跨平台的隐蔽性,监管部门不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出查处,而且能否适用《广告法》等规制广告的法律法规都不能确定,放过了钻法律空子的漏网之鱼,导致消费者出现由违法商品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
3.完善网络直播营销活动法律监管的相应对策
3.1 加强行业协会对平台的监管力度,分担政府监管压力
对于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监管,行业协会对平台的监管地位应当得到重视。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2],对政府而言,其严格的监管体系可以从根源上拒绝违规平台与商家、主播等网络直播营销主体,分担政府的监管压力;对企业而言,违反行业协会的规定与法律规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取消交易资格、罚款等一系列处罚。由于社会监督只发挥辅助作用,不能更好地配合行政机关监督管理,会导致类似民事诉讼中“不告不理”的局面产生,社会监督只有在政府部门发现问题要求其配合时才开始发挥作用,存在一定的惰性。以合作监管模式替代原来由政府主导、社会监督辅助的模式更有利于我国网络直播营销行业的发展。
首先,应当通过国家立法来确立行业协会的监管地位,使得行业协会的监管有强制力保障。2020年6月,中国广告协会发布了《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该《规范》属于行业协会自律文件,虽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但是对电商直播营销的监管方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义。同年10月,抖音、快手以及京东联合签订了《网络直播和短视频营销平台自律公约》,三家企业在北京监管部门的指导下,为净化网络营销树立了榜样。但是这属于自发组织的自律公约,直播涉猎的平台范围广,平台自律没有强制性,应当通过立法来确立行业协会监管地位。此外,政府监管部门应当同平台建立信息共享与信用评级机制来实现合作监管的落地。由于直播具有实时性的特点,货品的交易、商家资质等信息,应当及时共享以保障政府监管的及时性。美国企业的信用评级机制主要由专业的资信公司负责评估企业信用,在企业信用审查的过程中排除了政府的干涉,由第三方机构提供公平的信用评级。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可以仿效美国的经验,与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信用评级,对信用级别低的媒体平台进行相应惩处,从而倒逼直播平台加强自身的监管。
3.2 健全网络直播营销相关立法,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业发展
由于《广告法》2015年修订,短视频软件于2015年以后才兴起,法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网络直播营销活动所涉及的法律包括《广告法》《电子商务法》《个人所得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部法律,并且各法对于新兴媒体带货营销没有系统的规定。目前,针对此类问题已经通过部门规章、法律文件的方式弥补上位法的规制空缺,通过对直播营销系统性专门立法来解决目前涉及网络直播营销法律体系庞杂的问题。
建立我国网络媒体电商立法,首先需要明确网络直播营销的定性,明确直播平台、商品服务经营者与主播等直播营销主体的责任,《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虽然作为不具有强制实施力的行业规范,但其规定了平台、商家、主播等带货主体的责任可以为电商立法所借鉴。首先,直播主体分类的方式对于网络直播营销立法有着积极影响,这种以纠纷主体为分类依据的章节排布指向性明确,针对不同责任主体出现的不同问题都可以找出相应的法律规范。其次,建立电商专门性立法必须强调全方位监管新格局,强调平台监管职责,加强社会协同监管。网络带货借助了平台直播的方式,而直播内容又受到文化、广电等行政部门的管制,这里存在的交叉问题错综复杂,许多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都涉及了各种对网络直播内容有监管职责的部门,但对于直播营销活动来说,究其本质还是以营销为目的的商业广告行为。虽然直播的内容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的特征,但是,究其电商立法的本质还是营销。国家应当负责监管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应当负责监管的具体实施[3]。由国家与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挑起监管直播营销的重担,从立法上确立行业协会与电商平台对直播内容、商品、交易记录等信息共享、自我监管结果上报等责任,引导网络直播营销健康发展,形成政府主导、行业自我监管、社会协同监督的多元化监管新格局。
3.3 建立相关执法机关联动机制
对于跨区域、跨平台的监管执法问题,由于涉及地域广、参与机关多、工作交叉复杂,应当从横向关系上进行解决,这里就需要建立起执法机关联动配合机制。由于电商卖货是由商家向全国发货,具有由点状向全国大范围散射的特性,虽然有权管辖的机关表面似乎许多,但是确立管辖权后,基本由少数特定地区管辖,对于违规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查处可以遵从一主多辅、各司其职的方式,在以市场监管部门为主的情况下,公安部门、文化部门、互联网新闻宣传管理部门等网络监管部门相互配合,对证据、法律依据等信息进行实时共享,加强执法合作。对于掩盖广告性质,逃避《电子商务法》《广告法》规范的宣传、直播内容,在违法行为被发现后应当由负责部门调查取证,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由市场监管部门作出处罚。以市场监管部门为主的牵头执法避免了多头执法的乱象,同时也规避了互相推诿的情况出现。在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问题上,明确负责问题的主管机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络监管部门等应通力合作,将网络直播带货纳入法治化监管轨道[4]。
4.结语
伴随着5G的出现,网络智能会呈高速发展趋势,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发展方向也存在多种可能,我们需要对直播营销电商准入、直播营销事中监管以及违规结果执法的整体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结合《广告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拟定网络直播营销立法,构建立体化多方位监管体系,以期高效、全面地完善网络直播营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