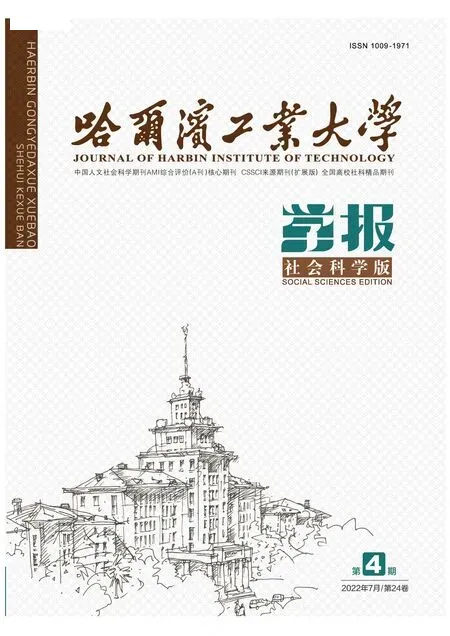举业成功:《聊斋志异》科举书写的另一面
许 虹,鲁小俊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聊斋志异》向以对科举流弊的揭露而闻名,《叶生》《考弊司》《冷生》《司文郎》《素秋》《于去恶》《王子安》《何仙》《贾奉雉》《书痴》等脍炙人口,故事中的主人公或因考官昏聩而怀才不遇,或遭黑暗势力碾压无力反抗,或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行为异常,这些作品数量虽少却用力甚深。 学界对《聊斋志异》科举问题的探讨,大多着眼于此①一般认为,《聊斋志异》在科举批判方面的深刻性与局限性并存。 如马振方《抨击科举痛快淋漓——〈聊斋志异〉主题一解》(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3 期)提出:“既看到它的多种弊病和八股文的无用,同时又对只有八股文才能取得功名恋恋不舍。”聂绀弩《略谈〈聊斋志异〉的反封建反科举精神》(载于《文学遗产》1980 年第1 期)也认为,蒲松龄反对靠旁门左道考取的科举八股,但不反对凭真才实学考取的科举八股。,并将其与同为讽刺科举的《儒林外史》相比较②如王昊《热腔骂世与冷板敲人——〈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态度之比较》(载于《明清小说研究》1999 年第4 期)指出:“蒲松龄是以‘个中人’的心态,控诉着科举的不公,热腔骂世,冀望改良;吴敬梓则以‘过来人’的心态,暴露着科举的腐败,冷板敲人,与之决绝。”。 我们发现,一方面,《聊斋志异》批判科举的篇章大多悲叹科举失败,以其浓郁的悲剧色彩和反复渲染的“才命两相妨”论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科举成功③古代科举难度很大,得一秀才已属不易,且科举过程漫长、名目繁多。 齐如山《中国的科名》认为:“大多数的读书人,只若中了秀才,便已心满意足,自以为交代过了排场,可以说是对得起父母妻室,这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来。”(参见齐如山著、梁燕主编《齐如山文集》第9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本文定义的《聊斋志异》中科举各阶段(秀才、举人、进士等)的成功,既包括一次性的成功和落第后的成功,也包括现实与虚幻中的成功。 即只要主人公实现了自己的科举愿望,便为科举成功。的叙述实际上数量更多,甚至以科举蹭蹬而闻名的叶生、王平子、郎玉柱等,也都被着意安排了较好的结局:只要砥砺不懈,本人或儿孙总会小有斩获,真正偃蹇不遂的很少。 关于这种矛盾现象,可供参考的观点是蒲松龄对科举失望之余,尚怀有一丝希望①如赵伯陶在《聊斋志异详注新评·素秋》中说:“俞慎最终能够乡试中举,无疑是作者对科举尚怀有一丝希望的体现。”(参见蒲松龄著、赵伯陶评注《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同时也是中国叙事文学“大团圆”结局的需要②如 郑红翠在《浅谈〈聊斋志异〉故事类型与大团圆结局方式》(载于《蒲松龄研究》2003 年第1 期)中指出:“《聊斋志异》继承了中国叙事文学的这种传统,它的故事结局或是夫妻团聚、母子兄弟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或是一男兼得二美、终得荣华富贵、终于得中金榜或子孙高中,或是终于得到子嗣,总之是善恶有报,美满幸福,皆大欢喜。”。 也许可以补充的是,《聊斋》寓意深远,主题的多样性同样值得关注。 作者之于科举的态度是复杂的,前后存在变化③如张丽敏《蒲松龄科举态度三变》(载于《蒲松龄研究》2008 年第4 期)认为,“(蒲松龄)最初对科举制度的依赖发展到中期对它的质疑,再到后期对其进行讽刺、抨击”。,举业失败或成功也都是他的精心安排,构成了类似史传文学的“互见法”。 具体而言,《聊斋》全书近500 篇短篇小说中,涉及举业成功的约90 篇,占18%左右,各卷的分布情况较为均匀,后期略高于前期,其时当是作者对科举制度有了更多的思考。 取得的科举功名则以秀才、举人、进士为主,鲜有小说戏曲式的“金榜题名中状元”,体现出作者清醒的现实主义认知。 这些故事里的科举成功是一面镜子,照射出人世间的幸福与苦难,有时作为标签以迎合世俗观念,有时用作催化剂使情节进一步发展,本身并不是主要表现的对象,故用笔不多。 但就主题的表达而言,举业成功的情节设置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意义。
一、圆满人生的世俗情怀
早在科举处于发展期的唐代,士人便以“进士擢第”“娶五姓女”“修国史”为人生三大荣耀④唐高宗时宰相薛元超曾言:“吾不才,富贵过人。 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参见王谠撰、周勋初校正《唐语林校正》卷四,中华书局2008 年第2 版),可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样的高远追求未免不切实际。 流传更广的“人生四喜”降低要求,定义了芸芸众生的幸福:“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其中“金榜题名”泛指科考成功,与有“小登科”之称的“洞房花烛夜”并列为人生两大美事,常见于小说戏曲。 这一点《聊斋》也不例外,“蒲松龄常将青云有路与佳人在室视为满足人生的两大愿望”[1]。 蒲氏的科举道路异常坎坷,将婚姻家庭与举业成功相结合,并对这类故事中的科举充分关注,正寄寓着他对圆满人生的无限向往。
作者笔下的婚姻,以“一夫双美”的形式最见圆满。 它侧重于表现婚姻多样化带来的甜蜜温馨,彻底满足了失意文人的白日梦,功名的获得是为了锦上添花。 《竹青》篇的鱼客穿着神衣在自家、神女住处两地往返,尽享齐人之福,长子十二岁就中了秀才。 《陈云栖》中,真毓生娶的两位女道士分别精于琴棋书画和家政,后来孩子们都中了秀才,有一个还中了举人。 《莲香》的故事较为曲折,也更为感人,莲香、李女为了与桑生成婚,“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⑤本文所引《聊斋志异》原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2 版。 以下不再一一注明。,两世情好化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慨,桑生同样成了举人。清代何垠注云:“莲以怜称,李以履者,同归于桑,曰相连理。”莲、李二人之名,本身就包含着美好的寓意。 仙凡狐鬼组成的“一夫双美”形式世所罕有,人间难寻,作者极力展开丰富的想象,呈现出奇异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夫双美”模式外的婚姻通常回归到现实人生,突出的是女性对于科考成功的作用,而不局限于描写她们的美丽多情。 这些女性或是包揽家中杂务,不使丈夫分心,或是对科考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堪为良师益友,举业成功被设定为共同的奋斗目标。 《红玉》中,红玉一人承担起振兴家业的重任,吩咐相如“但请下帷读,勿问盈欠”即可,半年后果然“人烟腾茂,类素封家”,相如当年便中了举人。 又如《书痴》中,颜如玉一再用自己的飘然离去相威胁(其实每次都藏在《汉书》第八卷,类似于捉迷藏),纠正郎玉柱的种种“书痴”行为,并教其下棋、弹奏与饮博,促使交游,于是郎“倜傥之名暴著”,成了进士。 颜如玉洞悉世情,对症下药,自然事半功倍。 此外“颜如玉”系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年轻美貌女性的代名词,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 蒲松龄将其缥缈朦胧的形象具象化,向往之情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婚姻之初,作者就埋下了科举成功的伏笔。 无论是神仙鬼怪还是世俗凡人,大都愿意以预言科举的形式择婿。 狐仙封三娘自告奋勇为范十一娘挑选如意郎君,路上“见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饰,而容仪俊伟”,认定是“翰苑才”,遂极力劝说她嫁给这位贫而多才的秀才孟安仁,此后孟果然官至翰林(《封三娘》)。 邵女出人意料地给家有悍妇的柴廷宾作妾,是因为断定“柴郎亦福相,子孙必有兴者”,之后儿子果真成为翰林(《邵女》)。 从女性的角度考虑,想要为自己找到一个最好的依靠,想要获得当时社会最耀眼的荣光,这是人之常情。 聂小倩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实欲依赞三数年,借博封诰,以光泉壤。”既然有这样的心理诉求,也就进一步推动了《聊斋》中婚姻家庭与举业成功的结合,盖“异史氏”所云“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是也。 相比盲试官,这些女子更能“识英雄于尘埃”,具有一定的代偿意义。
然而将婚姻家庭与科举功名相联系,固然包含着作者对圆满人生的无限向往,更多地是由世俗观念所决定的,落魄一生,作者必然会发现现实中有诸多的不圆满。 因此一些看似美满的爱情故事也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风格上多为哀感顽艳,“这种哀伤忧郁的情愫其实是《聊斋志异》所有涉及幽冥之爱的共同基调,即使是那些终于成了好事的爱侣也依然笼罩在或浓或淡的凄凉之中”[2]1614。 作者对科举成功同样流露出矛盾心理,在真切认知与世俗观念间徘徊,最后只好对两者的巨大落差尽力调和,试从两方面论述:
一方面,蒲松龄常借鬼神之口否定读书人汲汲于科举功名的丑态,但仍自觉为世俗凡人安排功名得中的结局。 《云萝公主》中的安大业考中举人,以为仙女云萝公主会替自己高兴,谁知公主愀然不乐,认为功名“无足荣辱,止折人寿数耳”,叹息“三日不见,入俗幛又深一层矣”。 于是大业不再以科举为念,后文却又叙及其长子十七岁及第。 《素秋》借蠹鱼精之口道出科举的实质是“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戚于得失”,不过科举不顺的俞慎最后还是中了举人。 神仙鬼怪的想法往往超凡脱俗,因为他们有能力也有资本抛却功名利禄,作者就让他们做了“反科举”的代言人。 可是对于世俗之人来说,科举是当时中下层读书人彻底改变自身命运、追求幸福的唯一渠道,生在世间,有“俗骨”也好,无“仙品”也罢,只能如此。 而且在儒家的入世观点看来,“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圣贤”,向往治国平天下。 古代读书人“入则儒法,出则释道”,蒲松龄虽然在出世、入世间有着些许迷茫,但内心依然坚持儒家立场,“他对神仙的向往,只是为了更有力地批判现实的黑暗,表达对美好理想社会的追求”[3]。 因而科举成功被作为家族使命以继承,一代代绵延不绝,只有在已取得功名或功名被寄希望于下一代时,当事人才能游离于这种世俗观念,说出“功名傀儡场中物,妻子骷髅队里人”“不但无意于功名,亦绝情于燕好”之类惊世骇俗的话。 《聊斋》的这种世俗情怀绵延不绝,直至晚清,仍有《儿女英雄传》与之遥相呼应。 其作者虽然同蒲氏一样对科举弊端、官场黑暗有着痛切认识,如故事一开头,就安排安学海“无端的官兴发作,几乎弄得家破人亡”[4],但举业依然被视为“养亲荣亲”的头等大事,最后学海之子坐拥三美又探花得中,实现了作者梦想中的圆满人生,也将此类故事生发到了极致。
另一方面,从宋元戏曲到明清小说,往往将婚恋故事中的科举功名写得轻而易举,动辄状元及第,《聊斋》则显得日常化而非戏剧化。 元代文人尤其热衷于状元戏的创作,“有元一代,戏曲大放异彩,其中涉及中状元情节的剧作多达四十余部”[5],未免将中状元看得太过容易,王实甫《西厢记》里的张生就曾夸口:“小生这一去,白夺一个状元,正是‘青鸾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6]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同样不甘示弱,主人公大多闪耀着状元光环,形成了“私定终生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俗套。 而《聊斋》中的科举功名仅以秀才、举人、进士为主,鲜有“金榜题名中状元”的结局,能考上秀才、举人便已可喜可贺,也许更符合实际。 据笔者统计,《聊斋》近500 篇故事中,只有《元少先生》一篇的主人公中了状元,清吕湛恩注云“(韩元少)名菼,号慕庐,长洲人。 康熙癸丑会、状,官至礼部尚书”,实系真实人物改编。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聊斋》的科名往往是“未完成”状态,一般提到某家孩子中了秀才便匆匆结尾,至于将来止步不前还是一路中到状元,全凭读者自己想象,也就巧妙地回避了问题。
二、劝善惩恶的道德意旨
《聊斋》开篇《考城隍》,即阐明“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道理,劝善惩恶的宗旨十分明显。 《清稗类钞》亦称《聊斋》为“愤世语也,劝世文也”[7]。 首先,劝善惩恶源于史传文学传统。 “正统的史传作者总是将垂鉴资治与抑恶褒善紧密结合,运行着‘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机制。”[8]从主观角度考察,受史传文学影响是作者自觉模仿与接受的结果,有“修国史”的愿望驱动在其中;从客观效果来看,将史传文学劝善惩恶的思想纳入作品中,也可以提高历来被轻视的小说地位。 其次,劝善惩恶是时代特色。“纵观清前期的小说论坛,‘教化’说始终绵延未绝,至乾隆则尤盛”[9]。 随着儒释道三教合一,劝善惩恶成为当时劝善书沟通三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蒲松龄认为“佛曰‘虚无’,老曰‘清净’,儒曰‘克复’,至于教忠教孝,则殊途而同归”[10]109,也肯定了这一点。 因此《聊斋》抒“孤愤”以外,融合了与劝善惩恶相关的儒家的福善祸淫、仁孝忠义,佛教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以及道教的行善立基、善恶承负等等,以神道设教。
《聊斋》劝善惩恶内容的展开与科举相关。这种观念由来已久,相传科举时代乡会试时,会安排专人在至公堂前大喊“凡平常有阴德之人必有尊神来呵护,文章虽不好,也可得中。 凡有损阴德之人必有鬼神来报仇,文章虽好,也可以被黜”[11]。 小说中行善的报答往往包含科举成功,究其原因,一是行善所得的馈赠通常从实际需求出发,在功名、财富、子嗣、长寿、妻妾、免灾等诸多愿望中,功名是多数人梦寐以求的:在宗法制和官本位思想影响下,功名可以光宗耀祖①参见袁了凡撰、尚荣等评注《了凡四训》(中华书局2013 年版):“中国古代实行封建宗法制,同时也盛行官本位思想。 个人如果做了官,就可以为自己的宗族和祖先带来荣耀,家族其他成员可以因此得到种种实惠;官做得大了,已经故去的祖先还可以追加各种谥号、美名。 所以中国这种高官厚禄、光宗耀祖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12],对于读书人来说更是最高肯定。 科举获胜还能促进其他愿望的达成,书中常赖以推进情节。 如奚大男弃家寻父,是为大孝,他及第前的寻亲徒劳无功,但做官后不久即因公务之便父子相逢(《大男》)。二是蒲松龄科举失意,笔下的人物因行善而取得功名,可弥补其现实中的缺憾。 三是科举历来受到重视,虽然明清时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了重商言利倾向,如徽地“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13],但蒲松龄仍然遵循士林传统②参见赵伯陶《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前言》:“有论者喜以卷七《黄英》中陶家兄妹‘以东篱为市井’之行为证明作者商人意识的流露,然而若从小说的主要倾向加以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作者企图用陪衬法来突出马子才安贫守道的儒家风范的执著可爱,况且令菊花之精灵艺菊贩菊,纯属自家神通,与社会中汲汲逐利的行商坐贾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将科举功名视为毕生追求,进而影响了《聊斋》中人物命运的设定。
在《聊斋志异》的世界里,高尚的品德能促使科举成功,尤为突出的是行孝和报恩。 “善之尤者为孝”[10]109,蒲松龄“以孝谨闻,固至今啧啧人口也”[14],可知于孝道身体力行。 《聊斋》写了不少孝子的故事,《青梅》中的张生最为典型,他“据石啖糠粥”却以豚蹄奉养父母,因伺候卧病的父亲而“便液污衣”,后来果然科举连捷。 比张生更为艰难的是钟生的抉择,能“知人休咎”的道士告知其正处于两难境地:功名与尽孝只能二选一。钟生当即表示情愿抛弃荣华富贵,最终感动冥司,母亲延寿一纪,钟生本人也中了举人(《钟生》)。两生皆因纯孝而及第,带有表彰性质。
难能可贵的是,蒲松龄对“孝”存有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愚孝。 《珊瑚》中,安大成刚出场时一味偏袒母亲沈氏,不知体恤妻子珊瑚,幸而珊瑚以德报怨,加上沈氏姊的一通数落,终使沈氏省悟,一家重归于好。 后来大成夫妇有两个孩子中了进士,篇末特意说明“人以为孝友之报云”,科举功名作为善报已得到公认。
孝道立足于亲缘关系,报恩则不限亲疏。 不过在作者笔下,若生时无法报答,来世托生为子也当相报,“盖生佳儿,所以报我之缘”,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换。 报恩故事里往往包含有知己之情。 《雷曹》中,乐云鹤与夏平子是莫逆之交,夏平子不幸早亡,乐云鹤主动承担丧葬费并恤养其家人,后夏平子为报知己之情托生为子,十六岁便进士及第。 令人惊讶的是,乐云鹤与夏平子之前“名并著”却“潦倒场屋”,两人大半生都无法企及的愿望,竟因报恩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这样的安排,可看作是批判科举与劝善惩恶双重主题的结合。 《褚生》篇将报恩同科举联系得更为紧密,为了报答知己,甚至可以代为考试:褚生是鬼,先代知己陈某通过了乡试,又托生吕先生家以报师恩,十三岁就中了秀才。 他先后报答了同学之情和师生之谊,是蒲松龄笔下的道德典范,有深意焉。
从惩恶的角度看,作者设计了这样的果报规则:若命中官运亨通但后天品德败坏,功名就会受到影响,轻则降等、重则除名。 但只要痛改前非,仍然能够有所挽回,有“鬼神许人自新”之意。 相比劝善,惩恶与科举的关联稍弱,因为无论是从道德还是法律上来说,它都应当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不过对于读书人来说,若因失德而失去既定功名,仍然有着强烈的警示意义。
“恶之大者在淫”[10]109,喜新厌旧是作者着力抨击的恶习。 《姊妹易嫁》写毛公幼时即有异兆,考前也有神灵给旅馆店主示梦,于是飘飘然想要换个更美貌的妻子,不料邪念一生,立刻被冥司黜落,幡然悔悟才得以中举,盖即佛家《惟无三昧经》所云“一念善者亦得善果报,一恶念者亦得恶果报。 如响应声,如影随形”[15]。 据《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姊妹易嫁》本于宋代钱易《南部新书》,《新书》全文仅68 字,并未叙及冥报,可见是作者的特意安排。 另一篇《阿霞》写景星偶遇“丰韵殊绝”的阿霞,欲与之成婚又怕妻子不容,干脆把十年来“未尝有失德”的妻子休了,于是报应接踵而至:原本他祖德深厚可中亚魁,结果不但被冥中削去禄秩,连阿霞也另嫁是科大捷的郑公子。更糟糕的是,此后景星薄幸之名流传,直到四十岁上才得以与“甚丑悍”的缙绅家婢成婚。 万幸的是,祖德绕过他传给了儿子,高中进士。 结局看似圆满,其实何尝不是为了反衬他人生的失败。 细论之,是否将恶念付诸行动,是两者科举结果相异的根本原因。
流风所及,就连讽刺科举的名篇《司文郎》也有惩恶之意。 该篇虽然深刻揭露出考官“眼鼻俱盲”的特点,最后仍将落第原因归为个人道德:原来王平子不第的原因是曾误杀一婢,因为坚持行善补过,又中了进士。 但文中隐约可见作者对于由道德决定科举功名的怀疑:傲慢无礼、胸无点墨却得以高中的余杭生,众人皆不知其究竟何德何能。 作者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只好用儒家的自省精神一再寻找考生自己的原因:“当前踧落,固是数之不偶;平心而论,文亦未便登峰。”最后还宕开一笔,安排数年后王平子与余杭生重逢,此时的余杭生“极道契阔,深自降抑,然鬓毛斑矣”。 在充满了岁月沧桑感的叙述中,科举功名已不值一提,最重要的是余杭生的品行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宋生、王平子、作者乃至读者的疑问,却没能得到真正解答。
这种困惑正是蒲松龄对道德教化指导思想的怀疑。 他没有像前代劝善书那样强行用“有益于人,则殴人、詈人皆善也”[16]136的歪理为“某人恶,而家门隆兴”[16]135辩白,反而在开篇就宣称“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也不赞同道德是决定科举成败的唯一因素,更倾向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天命观,“一知,二安,三不受”[17]。 对于命运的安排,他的认识有着古代士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色彩,命好固然可喜,命不好也应当不挣扎不反抗,益自进德修业,不断砥砺前行,“即明知不可,而注定之艰苦,亦要历尽耳”。 如果生前没能考上,那么死后也要通过帮助别人考上以证明“非战之罪”。 在开篇《考城隍》里,蒲氏还抒发了对“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的向往,相信人间不会永远黑暗。
可惜的是,《聊斋志异》之后仿作频出,道德教化的用意日益明显,成为此类书籍跳脱不出的窠臼。 例如,《谐铎·扫帚村钝秀才》一文盖仿《聊斋志异·叶生》而来,《叶生》未说明叶生不第的原因,只是简单归结为命运,《扫帚村钝秀才》却将科举不第明确归为道德有失,一切都向劝善惩恶看齐:“少时不谨细行,有惭名教,以至困场屋五十馀年,未得一掇科第。”[18]164另一篇《谐铎·大士慈航》认为“士子守身,一如妇人守节,立志不坚,稍有一蹉跌,堕入墨池,西江水不能涤也”[18]183,将失德比喻为失贞,说教色彩更为浓厚。 仿书中成就较高者《谐铎》尚如此,其余可知。 故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认为:“可是到了末流,不能了解他攻击社会的精神,而只是学他的以神道设教一面的意思,于是这派小说差不多又变成劝善书了。”[19]
三、举业成功的荒诞与虚无
在科场坎坷一生,作者最不平的就是考官眼盲,优劣不分,也即各篇反复提及的“小惭小好,大惭大好”,“陋劣幸进”却“英雄失志”,“黜佳士而进凡庸”。 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偶然“戏于落卷中,集其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在考场违心落笔,竟中经魁(《贾奉雉》)。 在能以鼻代目的瞽僧看来,余杭生的文章臭不可闻,竟成举人(《司文郎》)。 考官们不仅评卷的能耐有限,出题的水平也不敢恭维,《聊斋》有很多碰巧看到原题甚至答案而考中的情节,严肃的考试被解构为押宝。 《叶生》篇云:“公子名再昌,时年十六,尚不能文。 然绝惠,凡文艺三两过,辄无遗忘。 ……生以生平所拟举子业,悉录授读。 闱中七题,并无脱漏,中亚魁。”闱中首场围绕“四书”“五经”出题,确易重复,但总不至于到“闱中七题,并无脱漏”的地步。 结果部分考生仅仅凭借一点好运气加上好记性,就在偶然间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成功率更高的是多种科举捷径。 《僧术》通过给冥中使者行贿得到功名,曲折地反映了人世间的肮脏交易。 而一种名为“纳粟”的交易,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某乙》不无讽刺地写道,某人窃巨资起高楼、购良田,不仅替儿子纳了贡,还得到了邑令赠匾“善士”的殊荣。 “纳粟”尚属官方认可的行为,同时存在的还有种种“暗箱操作”,《素秋》《阿宝》便提到过“买关节”的行为。 最可悲的是,一些有学之士也被逼无奈,不得不依靠捷径。《贾奉雉》里的郎生劝告贾某,“天下事,仰而跂之则难,俯而就之甚易”,如果不这么做,便是“少年盛气”。 《书痴》中颜如玉的办法是教导郎玉柱学习琴棋书画、扩大交游圈,“倜傥之名暴著”之后,中进士就容易多了。 《叶生》《促织》《龙飞相公》等篇中,举业成功的关键是使学使知名,殊途同归。 从这些描写来看,现实世界的科举称得上是一片黑暗。
那么科举成功以后又如何呢? 事实上除了少数人青史留名,多数人于国于家于己都令人失望,“一切都已不是来时的梦中之路”[20]。 很多人考取功名是为了光宗耀祖,可即便科举成功,这样的希望仍会落空。 《太医》中,孙进士病重时念念不忘“生不能扬名显亲,何以见老母地下乎!”太医告知其皇后旦晚临盆,诰赠可得,但不可食熊虎肉,不料孙误食熊膰而殁,没能等到。 作为普通官员,更常见的问题是挣扎于宦海沉浮,《叶生》《娇娜》中的丁乘鹤、孔雪笠皆因忤上官被免,实无罪过。 为官本应造福一方,《郭安》中的昏官却胡乱判案,被讥为“此等明决,皆是甲榜所为,他途不能也”。
现实人生以外,作者开辟幻境,以更为奇特的方式表现科举功名的虚妄。 《续黄粱》写曾孝廉高中时一梦做了二十年太平宰相,然未几便被劾充军,顷刻间凄惨万分。 一般认为从唐代沈既济《枕中记》开始的千古“黄粱梦”至此作结,不同的是后者的梦境更为阴森恐怖:入地狱、下油锅、上刀山,极尽夸张之能事,强化了由功名心带来的一系列悲剧。 另一篇《王子安》以白日梦的形式,让“困于场屋”的主人公科举连捷,梦醒方知为狐所弄。 文末“异史氏”指出,现实中的功名其实也不过如此:每次考中的喜悦“不过须臾”。 十数年寒窗苦读,得到的竟是须臾之欢欣,可悲可叹。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21]。 在佛家看来,幻由心生,世间一切都充满了虚无缥缈,科举功名更是如此。
如果就此断定《聊斋志异》中全是对科举荒诞虚无的失望,那么我们也许只看到了作者科举态度的一个层面。 因为他一方面站在考生的立场讥讽考官眼盲及种种不公,另一方面又从考官的角度着眼,认为他们情有可原。 《三生》中,作者借阎王的问话让考官们自我辩解,较为客观地写出了衡文时的不可抗因素:令尹称“上有总裁,某不过奉行之耳”,主司亦辩白“某不过总其大成;虽有佳章,而房官不荐,吾何由而见之也?”他们在主观上实无恶意。 《聊斋志异》中虽有贪污腐败,但并无“爱少贱老,不肯一视同仁”[22],客观现实就是“试官棘闱校文,原系暗中摸索,不能预知其平日为学为人如何”[23]。 最后阎王为了使两人不再冤冤相报,判兴于唐来世为令尹之婿,令尹又千方百计使之“得志于名场”,如此才化解了兴某三世的怨气,真是莫大的讽刺。 又《王子安》篇末“异史氏曰”描绘“初失志”的丑态云:“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烛之。”作者直接登场,否定了考生落第后骂考官的恶习。 其实这也是蒲氏的自我反思:“蒲松龄的为人处世风格前后有着明显变化”[2]1598。“从一生的轨迹看,他是越到老年越是自觉地向儒家的正统回归。 他是以‘盛德’之名而终老的”[2]1599。 试看其词作中曾痛斥考官为“天孙老矣”[24]4“糊眼冬烘”[24]4,甚至欲将其骷髅“抽刀脔切”[25],实乃失意狂生兴于唐们的翻版。
科举本身以外,作者写出了受其影响的社会人生的多个方面,荒诞依旧,对世态人情不无感慨。 “明季科甲最重”,功名往往造成权力与地位的巨变,撼动本不可能被撼动的一切,比如左右司法。 《贾奉雉》的主人公虽然为官清廉,但无赖子孙“窃余势以作威福”,亦能“横占田宅”甚至强抢民女,从反面论证了权势之大。 一如蒲松龄《上孙给谏书》中所言“凡一人之望重,则举族之人,多窃其声灵,以作威福。 力之大者,则把持官府;力之小者,则武断乡曲”[26]。 又《张鸿渐》中,张鸿渐因代同学写状告官被迫逃亡,但儿子中举后,他不仅可以不再逃亡,当年与里中恶少的矛盾也迎刃而解。 《曾友于》中的友于父子中举,亦如此摆平了一桩斗殴至伤的案子,使对方“皆为敛息”。
亲情异化也因举业成功这一催化剂而愈见分明。 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展,在世人追名逐利的同时,传统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胡四娘》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程孝思未第时遭岳家欺侮,“群公子鄙不与同食,仆婢咸揶揄焉”,连读书也不得清净,时而“众从旁厌讥之”,时而“群又以鸣钲锽聒其侧”。 其妻四娘亦遭家人冷嘲热讽,被戏呼为“贵人”,二姊竟至以抉眸为赌注,认为程某贫贱终生。 等到程孝思捷报传来,适逢胡家为三郎举办婚礼却未请四娘,登时演出了一场闹剧:“姊妹惴惴,惟恐四娘衔恨不至。 无何,翩然竟来。 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 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众人奉承之处,堪与《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一节相媲美,但多了一份处变不惊的冷峻。 而且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并未结束,四娘离家时“独拜李夫人及三姊”,程孝思同样与胡家兄弟恩断义绝,相见如陌路之人。当大郎为了二郎的人命案子向四娘求情时,即便四娘最后暗施援手,兄妹相见时也已无亲情可言,隐含着作者作为读书人的清高气节。 这在倡导中庸之道的蒲松龄笔下很是罕见,在其他明清小说中也不多见。 不管是归诸考生个人的天命和品行,还是认为考官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蒲松龄对科举不公尚有一丝缓和的余地,可是对于世态人情,我们读到更多的是他的无可奈何。 在当时社会,如果无权无势,那就只有举业成功一条道路来获得别人的尊重,即便亲人间也只能如此,时过境迁,更为沉痛。 另一篇《镜听》所附“异史氏曰”直抒胸臆:“贫穷则父母不子,有以也哉!”与《战国策》中苏秦的感叹一脉相承。 至此作者由科举不幸广及到了对人生不幸的关注,深刻揭露了举业成功背后的荒诞与虚无,体现了更为深沉的人性思考与社会关怀。
概而言之,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深刻批判了科举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这部分内容通常以科场失意为主旋律。 但就数量而言,举业成功的故事其实更多,同样值得关注,也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作者对于科举的复杂感情:既认为功名虚幻不实,无足荣辱,又坚信唯有科举成功才能使人生圆满;既认同科举的道德决定论,又隐约对此表示怀疑;既相信功名命中注定,又固执地践行人定胜天的思想;既痛恨考官眼盲,又批评考生戾气太重,申明误判并不是有意为之;既对科举不公表示愤恨,但更愤恨的实际上是世人的趋炎附势,为此他抗争到底,不肯原谅。 随着主题的转换,书中的科举考试难度忽高忽低,情感也随之变化。 蒲松龄为科举执着奋斗了一生,对其有着切己体会,书中的科举情节无论成败,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也都寄寓着他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