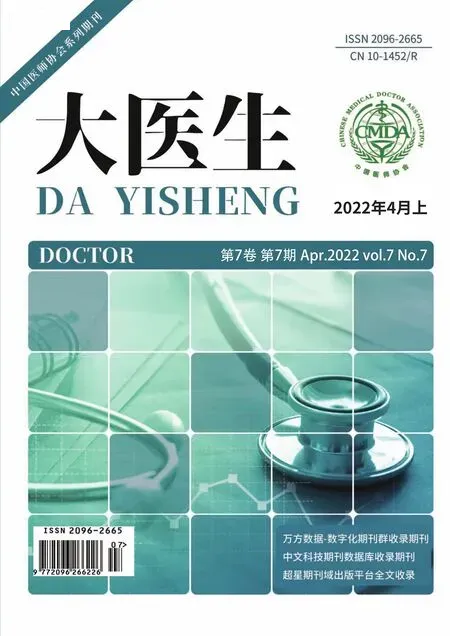伴有儿童情绪障碍的抽动秽语综合征1例
彭 灿,俞 洋,汤超华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广东佛山 528041)
抽动秽语综合征(tourette syndrome,TS)是一种神经发育性疾病,其在儿童中的患病率约为0.3%[1],临床表现为不自主的挤眼、摇头、耸肩或躯干扭曲等动作。约30%的患儿由于喉部肌肉抽动而发出怪声或无意识刻板地咒骂。由于伴有突然且不规律抽动,导致患者出现社交障碍、身体不适或情绪障碍。TS常并发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焦虑、抑郁及其他精神症状。TS的治疗和管理首先要评估抽动频率和严重程度及是否并发其他精神症状。临床上经常使用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YGTSS),评估抽动症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2]。如果抽动症状对日常活动无严重影响,可以暂时不采取常规药物干预。如病情需要,综合行为干预疗法(CBIT)可作为初始干预手段,如果这些干预措施不成功,则可以进行药物干预。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10岁,学生,因“不自主发声、扭脖4年余,加重伴心情差2个月”(病史由患者母亲代诉)于2021年10月19日到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住院治疗。患者于2017年渐出现不自主发声、伴有频繁眨眼动作,难以适应小学生活,每天哭泣,持续时间约2个月,后渐适应学校生活,抽动症状仍持续存在,家属带其至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就诊,诊断为“抽动障碍”,给予“硫必利”口服,患者服用后自觉乏力较明显,抽动症状缓解不明显,后至佛山市中医院就诊,诊断为“抽动障碍”,给予中药治疗,治疗1年后症状较前缓解,间断复诊,服药不规律,1年前患者症状出现反复,不自主发声,声音较前增高、耸肩、扭脖动作频繁,后再次至佛山市中医院就诊,具体诊治,改善不明显。2021年8月,患者自觉学习压力较大,担心自己不能完成作业和考试成绩,容易紧张,心情差,情绪低落,时有觉得同学在背后说自己坏话,易激惹,稍有不顺心,便大发脾气,偶尔会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声音,但又看不到人,抽动症状较前加重,家属带其至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诊断为“抽动障碍”,给予“氟哌啶醇片’等药物治疗,患者抽动症状较前减轻,仍自觉紧张担忧,心情差,并伴有心慌、腹痛等。近1个月家属担心药物不良反应,自行停药,患者症状持续存在。于2021年10月19日至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就诊,门诊以“抽动障碍”收入院。既往史:无特殊。个人史:生于原籍,足月顺产,1岁说话,性格内向,生长发育与同龄人无异,与家人关系可,学习成绩一般。月经史:未来初潮。无阳性家族史。入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T:36.7 ℃,P:97次/分,R:20次/分,BP:104/64 mmHg(1 mmHg=0.133 kPa)],心肺腹未见明确异常,神经系统检查未见明确异常体征。入院精神检查:意识清,定向力准;年貌相符,衣着得体,检查合作;接触主动,问话能答,问答切题,语量少,语音可,语速可,思维联想稍显缓慢,可出现可疑幻听,情绪低落,易紧张担忧,易激惹,意志活动诚退,频繁不自主发声、抽动,自知力部分存在。入院前辅助检查:2021年10月20日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胸部CT示胸部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拟肝S4a肝内胆管小结石可能;入院后考虑诊断:“①抽动障碍;②儿童情绪障碍”。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YGTSS-运动性抽动治疗前评分14分、YGTSS-发声性抽动治疗前10分。多动症诊断量表测评(SNAFIV-26)[3]评分4分。儿童孤独症筛查量表(ESAT)[4]评分3分;儿童适应性行为评定量表[5](CABRS)评分118分:韦氏儿童智力测验[6]评分94分:头颅CT、脑电图、肝、肾功能、电解质、甲状腺功能未见异常。入院后予利培酮口服液的剂量1 mL/d、舍曲林50 mg/d。第5天患者尖叫发声及耸肩动作频率较前稍减少,将利培酮口服液增加至2 mL/d,同时联合CBIT进行心理治疗。第10天患者尖叫声基本消失,但偶有耸肩、撅嘴等症状,同时闷闷不乐、不愿动,将利培酮口服液增加至3 mL/d、舍曲林增加至75 mg/d。第17天患者能主动与医生接触,对答时间有笑容,患者尖叫声基本消失,但偶有耸肩、撅嘴等症状。之后继续予CBIT。第18天时患者主动接触,对答时间有笑容,平时未再出现发声及抽动,但紧张时偶有撅嘴。将利培酮口服液增加至4 mL/d,同时加强CBIT。23天后患者尖叫发声及耸肩、撅嘴基本消失,复查YGTSS-运动性抽动评分5分、YGTSS-发声性抽动评分4分,同时为患者办理出院后续,后续定期门诊复诊。出院后患者生活自理、能回归校园。
2 讨论
TS又称妥瑞氏综合征,平均发病年龄为6~7岁,10~12岁时抽动最严重,通常在青春期或之后有所改善。60%~75%的TS儿童患有ADHD,27%的儿童合并OCD,32%的儿童有强迫行为,25%的儿童有自伤行为,约30%的TS的患者会出现焦虑和抑郁[7]。伴有焦虑症的患者高危年龄期从4岁左右开始,伴有情绪障碍患者的高危年龄期从7岁左右开始。同时,抽动严重程度与抑郁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大约10%的TS青少年患者有过自杀念头和企图,这通常发生在愤怒和沮丧的情况下。尽管自杀意念与抽动严重程度之间没有相关性,但焦虑和抑郁的存在会增加抽动障碍患者的自杀风险。瑞典的一项大型流行病学队列研究显示,患有TS的成年人自杀和死亡的风险是一般人群的4倍[8]。因此评估抑郁和焦虑症状很重要,尤其是在有抑郁症家族史的患者中。
抽动障碍的治疗和管理首先要评估抽动频率、严重程度及是否存在合并症。临床上经常使用YGTSS评估抽动症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2]。当抽动导致身体、情绪或社会功能受损时,应考虑药物或行为治疗。治疗的目标是减轻抽动症状,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对于TS的治疗,可分为药物治疗及非药物治疗两大类。
有研究表明,TS的发病机制可能与多巴胺功能异常有关[9]。多巴胺D2受体阻断剂(如典型和非典型的精神抑制药)可将抽动的严重程度降低约70%[10],并比其他药物更有效,但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不良反应,如镇静、代谢综合征、静坐不能、肌张力障碍、尖端扭转型室速等心血管不良反应。氟哌啶醇及利培酮作为多巴胺受体阻滞剂的代表药物,在临床中被广泛使用。氟哌啶醇是一种被证明对控制抽动有效的药物。有研究显示,氟哌啶醇在最大剂量下可减少高达91%的抽动[11]。但氟哌啶醇因其较高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使用受到限制。本例患者曾服用氟哌啶醇治疗,但因副作用无法耐受,导致治疗停滞。于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予利培酮治疗后患者抽动症状较前改善,未见明显副作用,患者及家属均比较满意。
利培酮是治疗抽动最常用的处方药,可能与其低剂量时是一种5-HT2受体拮抗剂,高剂量时起D2拮抗剂的作用,同时还对α-2、D3、D4和H1受体具有中等至高亲和力有关[12]。由于其对多种受体的影响,利培酮可有效降低TS患者的攻击性行为和抽动严重程度[13]。但利培酮的不良反应较多,包括镇静、锥体外系症状、体位性低血压、高催乳素血症和体质量增加。其他药物治疗有α2受体激动剂(可乐定和胍法辛等)、抗癫痫药物(托吡酯、左乙拉西坦等)、苯二氮䓬类药物(氯硝西泮等)、γ-氨基丁酸受体激动剂(巴氯芬等)及其他多巴胺受体阻滞剂(阿立哌唑、奥氮平、齐拉西酮、喹硫平等)。
CBIT是基于抽动抑制的行为疗法,作为非药物治疗有其独特的优势[14]。以基于功能的评估和干预与习惯逆转训练(HRT)为核心,习惯逆转训练包括抽动自我觉察训练、竞争性反应训练,通过这些训练破坏抽动循环机制,抑制抽动。这两种形式的训练对运动性抽动和声音抽动效果较好。通过系列技术帮助患者意识到抽动的发生,进行竞争性反应训练来打断和阻止抽动。自我觉察训练包括自我觉察和识别早期感觉和抽动的发生。竞争性反应训练是运用患者主动自愿动作竞争抽动的减少或消失,服用抗抽动药物的参与者和未服用抗抽动药物的参与者都对CBIT有效果。
其他非药物治疗方法已用于治疗抽动,包括维生素、按摩、瑜伽、针灸、催眠和生物反馈。同时肉毒杆菌毒素注射剂也已用于治疗痉挛和运动障碍[15]。对于有严重自伤性运动性抽搐的患者,应考虑使用肉毒杆菌毒素治疗。
TS是一种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诊断通常较简单,可以通过了解患者的病史及观察临床特征进行诊断。但因为常并发OCD、ADHD、儿童情绪障碍及其他精神障碍,使TS的治疗变得愈加复杂。目前对于TS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利培酮、氟哌啶醇、可乐定、氯硝西泮、胍法辛等)及非药物治疗(CBIT、维生素、肉毒杆菌毒素及深部脑刺激等治疗等),均有较好疗效。希望通过此病例分析,提升临床医师对共病儿童情绪障碍的TS患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