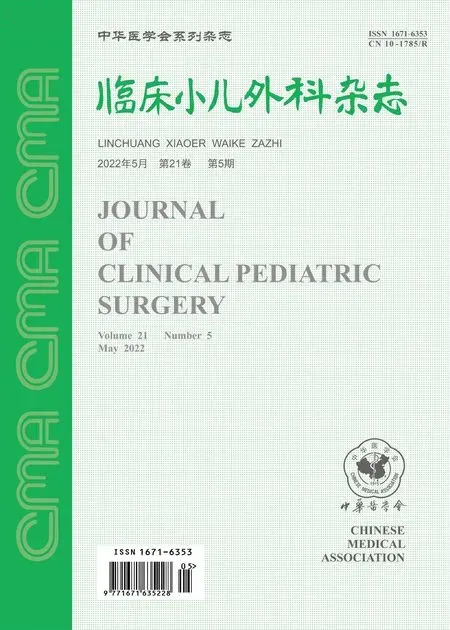扩大儿童肝脏移植供体来源途径
高伟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儿童器官移植科,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天津 300192 Email:gaowei_tjfch@163.com
肝脏移植是终末期肝病、部分代谢性疾病及肝脏肿瘤的有效治疗方式[1]。目前儿童肝移植受者的20年生存率达79%[2]。在欧美国家,儿童肝移植供体来源以尸体肝脏为主,而在亚洲国家以活体供肝为主。有文献报道,由于缺乏足够的供体,12岁以下儿童肝移植候选受者中因死亡或病情恶化未及或不宜行肝移植,而自肝脏移植预约等待人员名单中被移除的比例高达6.8%[3]。
为了增加供体来源,近年来扩大标准供体的使用越来越多(扩大标准供体是指过去认为不能用的供体,经供体可用标准范围扩大以后认为其可用,但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一类供体;在过去扩大标准供体也被称为边缘供体,近些年由于供体短缺问题严重,边缘供体的使用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同时供体肝脏的获取以及保存技术也在不断革新,且效果满意,因而扩大了儿童肝移植供体来源。
一、扩大标准供者肝脏的应用
(一)低体重、低月龄婴儿供体的应用
对于月龄较小的肝移植受者,由于其体重较小,获得年龄及大小匹配肝脏的概率较低。低月龄低体重供体应用于临床有一定的风险,主要表现在肝动脉血栓、小肝综合征、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的发生率明显增加,致使部分肝移植中心放弃了这部分供肝的应用。
成人肝移植中,肝动脉血栓形成可导致缺血性胆道病的发生率升高,是影响移植物存活率及患者生存率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儿童供体肝移植,尤其是低月龄、低体重儿童供体肝移植,这一结论并不完全适用。本中心一项关于体重低于5 kg供者捐献肝脏肝移植的研究提示,虽然肝动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相对较高,且导致了较高的胆道并发症发生率,但低体重供者肝移植并不会降低移植物存活率及受者的生存率[4]。同时,使用低体重、低月龄供体肝脏时供肝重量与受者体重比(graft-versus-recipient weight ratio,GRWR)相对较低,同时不增加小肝综合征风险,这可能也与我们选择了体重很低的受者相关。到目前为止,关于儿童供体月龄与体重的下限尚无统一标准。根据我们既往的经验,对于年龄小于1个月或者体重小于5 kg的供者,其临床应用仍存在一定的风险,建议在有经验的儿童肝移植中心选择性应用。
(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在器官获取之前有心脏停搏的过程,这段时间由于供体器官没有血液灌注(即供体热缺血时间),加重了移植后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导致DCD供体的移植肝原发性无功能发生率增加,在DCD供肝应用的早期阶段,成人DCD供肝肝移植受者的死亡率及缺血性胆道病的发生率均高于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供肝肝移植受者。随着对DCD供体的认识,通过避免使用高龄供者,缩短冷、热缺血时间等措施,DCD供体取得了与DBD供体相似的效果,但受者术后仍可能发生缺血性胆道病、静脉血栓形成及移植后急性肾损伤[5]。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UCLA)一项关于儿童DCD供肝应用的研究表明,儿童DCD供肝肝移植的远期预后与DBD供肝肝移植无显著差异[6]。DCD供体的选择有一定条件,需要供体热缺血时间少于30 min,冷缺血时间少于8 h,且需要有经验的医生在器官获取手术中评估供体肝脏质量。由于部分DCD供体肝移植术后移植肝原发无功能、移植肝功能延迟恢复及缺血性胆道病的发生率相对较高,原位常温机械灌注(normothermic machine perfusion,NMP)可以改善移植肝脏的功能,且NMP在保存供体的同时,还能用于评估供肝的功能[7-8]。NMP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型器官保存技术,在DCD供肝等扩大标准供肝的保存上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虽然在儿童肝移植领域报道尚少,但仍有较大的应用前景。
(三)ABO血型不相容供肝
ABO血型不相容供体虽然不是肝移植的禁忌,但其有增加急性排斥反应、肝动脉血栓及胆道并发症的风险。红细胞抗体是导致上述风险升高的主要因素。ABO血型抗原主要分布在肝脏血管内皮及胆管细胞上,能与红细胞抗体结合激活补体系统,最终导致膜攻击复合体的形成。对于低年龄的儿童受者,由于其抗A和抗B抗体滴度均处于低水平,且其补体系统发育不完善,因此ABO血型不相容的供肝对肝移植预后没有影响。我们的经验表明,对于2岁以下儿童,控制红细胞抗体滴度在低于1∶32的情况下不会增加肝移植术后并发症的风险[9]。随着利妥昔单抗的应用,年龄较大的儿童也可以安全应用ABO血型不相容的供肝[10]。
(四)乙型肝炎核心抗体阳性供肝
将乙型肝炎核心抗体(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HBcAb)阳性供者作为肝移植供者,在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儿童肝移植受者术后新发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的发生率达38.5%[11]。2014年欧洲肝移植指南明确指出,HBcAb阳性供肝仅推荐用于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受者或者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及HBcAb均为阳性的受者[12]。
但是在中国,一般人群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阳性率为5%~6%,而HBcAb阳性率更高,估计在30%以上[13-14]。在我们中心,HBcAb阳性供者占43.6%[15]。儿童肝移植受者较少出现HBcAb阳性,如果放弃使用HBcAb阳性供者,则将失去近一半的供体。为此,很多移植医生探索了HBcAb阳性供肝肝移植术后新发HBV感染的预防方案,包括给予受者强化乙肝疫苗接种、肝移植术中及术后给予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hepatitis B immunoglobulin,HBIG)、肝移植术后给予核苷类似物、乙肝疫苗等措施。我们在应用HBcAb阳性供肝时,术前常规给予受者乙肝疫苗接种,使乙肝表面抗体滴度>1 000 IU/L,术后根据乙肝抗体滴度给予HBIG和(或)核苷类似物,采用此预防措施后,肝移植术后HBV感染的发生率降至3.6%[15]。对于新发HBV感染的儿童,在给予核苷类似物联合或不联合干扰素治疗后,71.4%的患儿HBsAg转阴。因此,在有效的防治措施下,HBcAb阳性供肝可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供体来源。
(五)脂肪供肝的应用
脂肪供肝的应用是肝移植术后原发无功能及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一般认为,轻度至中度脂肪供肝不会影响移植物存活率及受者的生存率,而重度大泡性脂肪肝会导致移植物原发无功能的发生率增加。
Irie等[16]报道12例儿童活体肝移植,其中9例供体大泡性脂肪变程度达34%~66%,3例供体大泡性脂肪变程度>66%;11例受者肝移植术后脂肪肝程度短时间内减轻,1例肝移植术后早期脂肪肝程度没有减轻,但随访6年仍存活。由此可见,中度至重度大泡性脂肪肝也可用于儿童活体供肝移植,肝移植术后脂肪肝程度可在很短时间内减轻。但在使用脂肪肝供体时,需要控制冷缺血时间尽量较短,宜选择相对年轻的供者,肝移植术后需要密切监测血糖及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六)杂合子基因携带者活体供肝
1989年,澳大利亚Strong等[17]成功完成了世界首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将供者肝脏的左外侧叶移植给一个胆道闭锁患儿。早期活体肝移植选择供者为完全健康的成人。相当一部分儿童肝脏移植患者患有遗传代谢性疾病,这部分患儿的父母可能为杂合子基因携带者,经过基因检测后,有些杂合子基因携带者虽有缺陷,但其肝脏酶活性足够代谢,需要时也可以作为活体肝移植供者,如克里格勒-纳甲综合征1型、威尔森病、氨甲酰磷酸合成酶1缺乏症、丙酸血症、精氨酸琥珀酸尿症、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酪氨酸血症、Alagille综合征患者[18-20]。在儿童活体肝移植中,腹腔镜供肝切除术以及机器人辅助供肝切除术的开展,促进了活体供肝捐献率的提高[21-22]。
二、通过技术创新扩大供体来源
(一)劈离式肝移植
1988年,德国的Pichlmayr教授完成了世界首例劈离式肝移植[23]。劈离式肝移植是将一个完整的供肝劈分为2个或2个以上解剖功能单位,分别移植给2个或者多个受者,直接增加了供体数量[24]。劈离式肝移植的最大受益者是儿童。但是在早期,由于技术不成熟,劈离式肝移植受者生存率显著低于全肝移植受者,且再移植率及胆道并发症的发生率均明显升高。在体外劈离及活体肝脏移植技术的基础上,原位供体肝脏劈离逐渐开展,并且取得了优于体外劈离的效果。随着肝脏劈离技术的改进,劈离式肝移植受者生存率与全肝移植受者无显著差异,且儿童劈离式肝移植受者的再移植率低于全肝移植者。
既往认为,小于10岁的儿童供体不适合行劈离式肝移植手术[25]。为进一步扩大供体来源,我们尝试对小于7岁的儿童供肝进行劈离,并分别移植给两个儿童[26]。技术的进步使儿童供肝的劈离成为可能,与全肝移植和成人供体劈离式肝移植相比,儿童供体劈离式肝移植的预后良好,具有相似的患者生存率、移植物存活率及外科并发症的发生率。但儿童可劈离供体的年龄和体重下限目前仍无定论,由于技术难度较高,我们建议最低体重应大于15 kg。
(二)多米诺供肝的应用
多米诺肝移植是将肝移植受者的肝脏作为另一个肝移植手术的供体。这使得使用一个常规供体可以完成2个肝移植。世界首例多米诺肝移植于1995年在葡萄牙完成[27]。在行肝移植治疗的单基因遗传病患者中,有些患者肝脏的结构及功能是正常的,常见可作为多米诺供肝来源的疾病有家族性淀粉样多神经病、枫糖尿病、纤维蛋白原Aα-链淀粉样变性、血色素沉着病等[28]。
1998—2017年,多米诺肝移植注册系统(Results from the Domino Liver Transplant Registry_fapwtr.org)共有1 254例多米诺肝移植注册[29]。其中大多数多米诺供者是家族性淀粉样多神经病患者。在一项使用枫糖尿病患者肝脏作为多米诺供体的儿童肝移植研究中,多米诺受体远期预后良好,并且没有新发枫糖尿病[30]。在多米诺肝移植的基础上,多米诺辅助式肝移植、交叉辅助式肝移植也可增加供体来源,但由于这些疾病的发病率极低,能增加的供体数量也较少[31-32]。
(三)大体积移植物的处理
在儿童肝移植中,使用“大肝”的问题较为常见。通常认为当GRWR>4%,即认为是“大肝”[1]。使用“大肝”最直接的问题是腹腔关闭困难,影响移植肝血流,还会增加腹腔间隔综合征、移植物功能不良、肾损伤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在使用大体积移植物肝移植时,对于关腹困难的病例,可以采取延迟关腹的方法;另外也可以通过使用减体积及肝段移植来克服大体积的问题。“大肝”的应用会增加肝移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但不会影响移植肝存活率及受者生存率[1]。
根据本中心的经验,儿童肝移植中,GRWR并非供体选择的决定性指标。如果因“大肝”导致腹腔难以关闭,或者对门静脉及肝静脉血流造成影响,可以通过移植物减体积的方式来解决大体积移植物的问题,包括解剖性减体积及非解剖性减体积。前者包括S2段、亚S2段以及改良S2段供肝等,后者主要是通过切除肝左外叶外侧或者下侧边缘部分来实现[33]。
在肝移植等待系统中,优先度较低的候选受者等到捐献供体的概率有限,扩大标准供者肝脏的应用会增加其等到供肝的概率,但同时会增加移植物原发无功能的风险。所以当器官捐献足够多时,要减少这类供体的应用;而在供体短缺时则要增加这类供体的应用。这类供体的应用和分配原则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其他可以利用的供体包括冷缺血时间较长的供体、合并肝脏良性肿瘤的移植物、高胆红素供肝、废弃肝脏等[34]。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器官捐献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近期有报道对于既往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器官捐献者,如病毒PCR阴性则可以安全获取器官;并且尝试使用新型冠状病毒阳性供者的肝脏,而受者并未被传染[35]。同样,近期异种心脏移植的临床实践也为儿童肝移植带来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