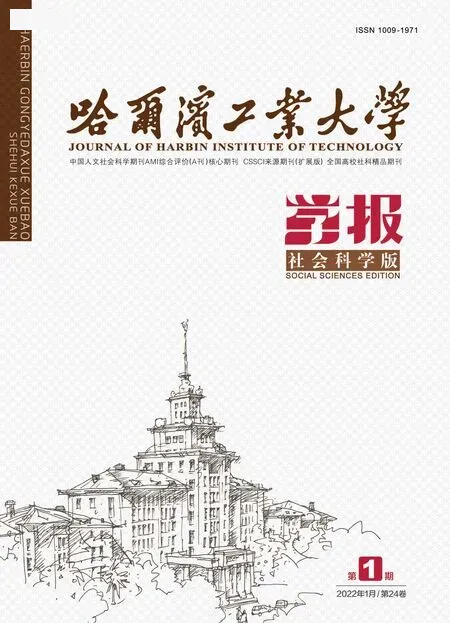场域视角下的“十七年”少儿科幻文学
姚利芬
(中国科普研究所 创作研究室,北京100081)
引 言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文学,鲜有不以少儿为潜在阅读对象展开创作的作家。 其中的代表作有郑文光的《太阳探险记》(1956 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迟叔昌的《割掉鼻子的大象》(1956 年,《儿童文学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叶至善的《失踪的哥哥》(1957年,《中学生杂志》)、童恩正的《古峡迷雾》(1960年,少年儿童出版社)、萧建亨的《布克的奇遇》(1962 年,《我们爱科学》)等,赵世洲、鲁克、王国忠、刘兴诗、嵇鸿、李永铮等作家也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了作品。 十七年间的科幻作品多以“参观记”和“侦察记”两类叙事模式展开,具有文字简易明快,有趣、活泼、热闹,故事结构明晰等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特点。 那么,当时的科幻作家缘何会选择面向少儿读者群进行创作,中间经历了怎样的“生产”过程,又是何种动因促成了这种“生产”?
本文以布迪厄的场域视角切入对“十七年”科幻少儿转向的考察。 场域、惯习和资本是场域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 场域是由权力(或资本)栖居的各个位置间的客观历史关系构成的虚拟空间;惯习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工作、社交等社会化历程中,经由主动学习和环境熏染而将知识价值内化并强化、体系化了的社会习性;资本则指有形或是无形劳动的积累,涉及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1]。 场域理论涉及对行动者位置关系、地位、角色的描述。 本文将从场域关系视角蠡探“十七年”期间政治、经济、科技等场域对科幻文学的建构,以期更好地重返历史现场,观照其生成过程。 接下来将考察科幻文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报刊、编辑、作家、评论家等)为了抢占资本,控制场域的合法逻辑而形成的制衡关系,探讨科幻文学场域作家惯习的成因及其结构,爬梳诸种力量如何通过竞争、互动、生成等行动,为科幻文学的少儿转向营造文化空间。
一、政治场域主宰下的科幻文学
“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特定时代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占主导地位的产物,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是其表现的基本形式。 政治性高凌于各场域之上,“它通过革命实践、社会改造等形式,整合了晚清以来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的各场域。 科学场、教育场、经济场等社会场域在这一过程中几乎被剥夺了独立性。 即使是布迪厄看来最可能具有自主性的文学场也概莫能外”[2]。 科幻文学(主要的文学形态为科幻小说)作为文学场域中的子场域,同样依附于政治场域。
政治场域的强大力量决定着其资本的类型及效力,驱动不同资本之间的转化。 以科幻小说的创作动机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作者或是出于消遣自娱,或是基于改造当下及对未来世界的梦想,或是缘于对科学的兴趣……科幻创作能力作为一种个体性文化资本更多是为了满足知识分子阶层社会性或是精神性需求。 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科幻场域的行动者——作者,更多开始对标国家意识形态需求来调整创作活动。
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方向——文艺服务的对象应当是工农兵人民大众——这成为指引新中国文艺事业和文化建设前进的灯塔。 随着1949 年新中国成立,文艺界进一步明确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评价标准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从宏观上确立了政治领导文艺的合法性。 科幻文学不可能再按自身的逻辑发展,也不得不面对“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方向性问题,在政治场的虹吸效应下,强化科幻的科普功能、更好地服务人民大众成为当时的选择——当然,科幻科普功能的强化与教育启蒙等目的亦不无关系。
政治性是“十七年”科幻作家创作中时刻注意的问题。 踩红线的例子在当时偶有发生,但很快被纠正。 1958 年12 月出版的《少年文艺》杂志刊登了一篇“编者按”,提到该杂志10 月号发表的一篇科学幻想小说中,对未来社会形式的预言是错误的。 王国忠1963 年发表的科幻作品《黑龙号失踪》,出版8 个月便因内容涉及政治敏感问题而禁止发行了。 这种“警觉”说明幻想话语的政治暧昧与危险,以及政治对文学的主宰引致的无处不在的占位行动。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受到政治的驱动。 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政治对科技的影响无疑是较为突出的,进而也对科普创作、科幻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1949 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四十一条到四十三条中指出: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将“爱科学”列为国民公德之一;努力发展自然科学,普及科学知识。从科技政策发展的轨迹来看,自1956 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再到一系列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十二年规划”“十年规划”),科技事业渐次步入一个有序、蓬勃发展的时期。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普及宣传教育也被纳入重要工作,儿童作为未来的主人翁成为被科普的重要群体。 科学幻想故事、科学童话等科学文艺所涵及的对象,因其通俗、生动、有趣,能使少年儿童、需要被扫盲的成年人对科学产生兴趣而成为被积极推广的对象。 谈及当时科学幻想文类的作用,刘兴诗称,其重在普及身边“实实在在的,有用的,近距离的科学”,“现在没有以后有,最好是很快就有”①此为刘兴诗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述。 刘兴诗称20 世纪60 年代初,《少年文艺》的编辑刘东远找他约科幻稿件,刘东远解释他们需要的科幻作品就是在科学的基础上稍微幻想一下,其中涉及的想象需要是“现在没有以后有,最好是很快就有”的科学。的科学。当时科幻创作的标准是所涉及的科学发明或想象是否有用,是否有利于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是否有利于激发起读者向科学进军的热情,想象力反倒是退而求其次的元素,用刘兴诗的话说,“当时的科幻想象更像手榴弹,而非远程洲际导弹”。②此为刘兴诗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述。
1955 年,《人民日报》、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作协”)作为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发声的重要代理者,先后发出了号召作家创作少年儿童科学文艺读物的倡议,成为作家创作遵循的重要风向标。《人民日报》于1955 年9 月发表重要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指出:“中国作协应当配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前身),展开科学家和作家的有效合作,每年为少年儿童创作一些优秀的科学文艺作品,从而解决少年儿童科学读物乏味枯燥的现状。”[3]我们注意到,社论传达出四层重要的意涵:一是提到中国作协应当配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推进创作的开展,共同完成意识形态宣传;二是提倡科学家和作家合作创作的模式,主动开展创作;三是创作面向的读者对象是少年儿童;四是特别提倡创作科学与文艺相结合的作品,以解决科学读物枯燥乏味的困局。
中国作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动文学工作、引领作家创作的重要机构。 当时的作家必须取得合法的写作身份,要在组织单位内,不可游离于体制之外,这种制度格局赋予中国作协强大的象征资本。 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推动下,作协于1955 年10 月发出了鼓励作家创作适宜少儿阅读的科幻作品的指导意见,并在第十四次理事会主席团扩大会议(1955 年召开)上,讨论通过了繁荣少儿文学创作的计划。 对科学文艺类作品的创作,作协“提倡作家、科学家、历史研究者联手,为少年儿童创作鲜活有趣的科学文艺作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名人传记等。 提倡形式、体裁灵活多样的作品,要广泛发展科幻小说、科幻故事、诗歌、剧本、游记等样式”[4]。
《人民日报》、中国作协的先后发声,赋予了包括科幻在内的科学文艺作品在儿童文艺中的合法身份,也使得1955 年成为一道分水岭,自此之后科学文艺创作出现一派繁荣景象。 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刊出了大量不同体裁的科学文艺作品,涉及科学故事、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寓言等。十七年间的科幻小说绝大部分是1955 年之后发表的。 由上,在国家级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人民团体(中国作协)的呼吁和引导下,文化资本实现向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科学文艺倾斜。 或者说,为文化资本的转换提供了保障和条件。 科幻文学也在文学场域与科技场域的交接处应运而起,并着力以少儿为读者对象,将科学普及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践行。
二、行动者对科幻文学少儿转向的推动
根据布迪厄的观点,斗争中的行动者及各种机构相互间权力关系的状态,即某些特定资本的分布构成了场域空间。 文学场域的主要行动者有文学创作者、出版机构、文学价值的评判者——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有生命的人以及没有生命的打字机、笔、纸和桌子等均为行动者,据此理论,我们且将有生命的个体(作者、文学代理人、评论家等等)和相关机构(出版社、书店等)视为文学场域的行动者。 行动者为了取得“合法”身份,抢占空间,获取资本而展开斗争。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科幻文学场域中有代表性的几种行动者:报刊编辑、评论家,关注诸种力量如何相互作用,其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如何形构了科幻场域的少儿转向。
(一)报刊编辑
“文化大革命”前,全国专业少儿出版社只有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两家,两家出版社的“掌门人”当时分别是叶至善和王国忠,被业界称为“北叶南王”。 他们不仅身体力行进行科学文艺创作,还带领团队出版科普读物,以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少儿精神产品为旨归,新创《我们爱科学》等科普期刊。 两家机构积极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将发展包括科幻类文体在内的科学文艺类作品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落实,成为重建“十七年”科幻文学场域的关键行动者。
当时刊载科幻作品的平台主要以少儿报刊为主,例如《我们爱科学》《中学生》《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等。 报刊出版部门在“十七年”科幻文学场域重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项:
其一,对“十七年”科幻文学的策划组织。 当时科幻文学被打包在科学文艺所辖门类中,与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相声等一并扶植提倡。 稿源大多非自投稿件,更多是被“定制”出来的。 在1949—1980 年的三十年间,编辑常常是落实主流意识形态的先锋队。 在发展科学文艺作品、激发少年儿童的科学兴趣方面,《我们爱科学》《少年文艺》等少儿报刊的编辑是将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落实的。 他们经常主动出击,特约一些有自然科学背景,或是已经有科普作品发表的作者撰写稿件。 报刊在组稿行动中,完成了科幻文学场的“占位”。 因此,当时的作者经常是科学文艺类作品的全能写手,迟叔昌、萧建亨、郭以实等当时较为活跃的作家不仅创作少儿科幻作品,还发表了很多适合少儿阅读的知识性科普作品、科学童话甚至科学相声等作品。
其二,对所刊发稿件的筛选、改写和加工等。编辑是把控科幻作品生产活动的行动者,他们有权决定让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等科学文艺作品以何种面孔走近少儿读者。 编辑秉持的科学文艺观、对科幻文学的态度、对某位作家“设计”等因素都会对读者的文学立场、趣味、喜好施以影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那时的科幻文学又是“编辑的文学”。
据《我们爱科学》初创时期的责编郑延慧回忆:“当时的少儿科普处刚开始开疆拓土,稿件一来较缺,二来需要着力打磨,使之符合少儿的阅读习惯。 当时的科技工作者一般都不是为少儿而写作的,从他们那里约来的稿子,编辑必须做一番‘粉饰’编加,才能将作者的意思通俗地传达给儿童。”[5]叶至善当时负责《我们爱科学》的稿件终审,对当时发表的作品均严谨编校。 在《我们爱科学》杂志对稿件加工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少儿编辑作为科幻场域的控场力量,先是为少儿科幻作品划界,设定创作方向,例如建议作者创作“近未来”的、有效普及科学知识的作品,进而对作品进行编辑润色加工,使之进一步迈向编辑眼中“标准化的科幻”,助力作家“通过斗争以维持和提高自己在这个场域中的位置”[6]。 这些编辑在“十七年”科幻文学少儿化的过程中倾其资本,其斧凿之力甚至有些用力过头,以至编辑“变身”为作者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孕育了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编辑型作家”。
(二)评论界中的行动者
1.鲁迅、高士其等科学文艺的旗手
在科幻文学少儿化的进路中,文学价值的认定者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鲁迅和高士其是其中的代表。 鲁迅一贯重视提升少年儿童的科学知识修养,认为科学文艺作品创作融科于文、生动活泼,儿童及一般成年人读者均易于领会和掌握,应当大力发展。 鲁迅作为拥有强大象征资本的文化旗手,对科学文艺的积极姿态无疑会产生很大影响。 在《月界旅行·辨言》中,他对科学文艺特点及其重要意义的论述亦成为重要的话语资本,不断地被后人征用。①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写道:“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一不终篇……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
高士其是继鲁迅之后提倡科学文艺最重要的一位旗手。 他深受鲁迅、陶行知的影响,早在1933 年就开始为儿童写作。 他曾在陶行知主办的自然学园里,与同仁共同创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写儿童科学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亦不断地为科学文艺摇旗呐喊。 他在科学文艺理论与创作方面皆有所建树,不仅创作了大量细菌题材的科学文艺作品,还发表了很多科学文艺理论文章,在科普创作界影响力极大。 高士其认为,少儿兴,科技兴,则国强。 只有从小培养少儿对自然科学的热爱,才能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旧貌焕新颜,走向繁荣富强,抵抗列强的侵略和欺侮[7]。
鲁迅、高士其作为享有极高知名度和地位的文学价值认定者、“超级行动者”,负载的象征资本是巨量的,也引来一批后效者。 王国忠1962 年出版的《谈儿童科学文艺》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论著,书中阐述了科学文艺的特点、功能,科学与文学结合的途径、方法,并结合中外创作案例,分别对科学故事、科学童话、科学诗、科学小品、科学幻想小说等展开了详细的论述[8]。
这些文学价值的认定者提倡涵盖科幻小说在内的少儿科学文艺,共通的原因是科学文艺作品是丰富的,具有多极化指向的,能满足科学、文学、美学、政治的多维教育需求。 倡导科学文艺还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关,民族的自立富强从来是权力场的超级信仰。 因而,在文学秩序重建的过程中,赋予文学以教化少儿、富国强民的使命,更容易在权力场胜出,给民众以精神抚慰,从而拥获足够的象征资本。
2.科幻相关称谓的儿童化意涵
布迪厄主张研究文学现象必须语境化、历史化。 同一词语由于具体语境不同,理解不同,其传达的含义可能不同。 中国作协的指导意见中对科学文艺作品所涵盖的体裁做了进一步说明,其中将“科幻小说”与“科学幻想故事”并提。 那么,“科学文艺”作为涵盖了诸多文类的总体性概念,其波及的场域是如何规约着科幻小说创作的?“科幻故事”相较“科幻小说”而言,在“十七年”期间各类评论中是更多被提及的指称。 二者不仅时常被并提,甚或互相通约。 “科幻故事”的指称隐含了怎样的意涵,反过来,又怎样导向了科幻创作的少儿化倾向? 接下来将分析文学场中关于“科学文艺”“科幻小说”“科幻故事”等指称及其意涵,以窥其妙。
科幻小说在“十七年”期间被提倡,常常是被打包在科学文艺之列来提及的,而“科学文艺”潜在的阅读对象指向就是儿童。 郑文光认为“科学文艺”的概念最早源自苏联,原意指伊林式的、专为儿童创作的明白易懂的文艺性科学读物(伊林的《人和山》《十万个为什么》等作品早在民国时期便悉数被译入国内,其文善于用文艺笔墨书写干躁无味的理趣和奥妙复杂之物,被称为“通俗科学文艺”“儿童科学文艺”等)。 “科学文艺”这一称谓在“进口”到中国后,涵及的文类范围呈扩大态势,科学小品、科幻小说、科学诗以及科学曲艺等都列其范畴,其命名也被当作一种总体性指称屡屡提及。 然而,当时特别是在20 世纪50 年代,作家及评论界对于科幻小说的文体特征更多是语焉不详的,直到20 世纪60 年代,一些嗅觉敏锐的作家才对科幻文学的文体特征有所察觉。 到了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1980 年郑文光撰文《科学文艺小议》明确指出,科学文艺所涵文类广泛,一部分是文艺性知识读物,譬如科学小品、科学故事;另一部分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以科学童话和科幻小说为代表。 科学文艺实际上并不完全属于儿童文学。 以文艺形式讲述科技知识,不应当成为统领创作方针,其在指导创作实践上已经产生了有害的影响[9]。 当然,这是后话,既然把科幻小说列为科学文艺的范畴,科幻文学创作规范依循科学文艺作品的一般特性尤其是伊林式的“儿童科学文艺作品”来进行创作亦无可厚非了。 即要创作一种基于科学事实,而非一味全做空想、面向儿童展开的幻想式作品。
当时流行的“科幻故事”的指称也在某种程度上导引了科幻文学儿童化的走向。 在科学文艺的子类中,科幻故事、科幻小说经常混提。 尽管在儿童文学的语境中,“故事”和“小说”常是通约的,但叙事焦点不相同。 “故事”以“事”为思维的焦点,一般有精彩的情节,紧张的节奏;小说重于写“人”,并借心理活动描写、对话描写和场景描写等对人物形象进行勾摹。 “故事”相较“小说”,形式上更通俗、自由、活泼,也是儿童文学门类下最为习见的创作形式。 实际上,当时的媒体评论对《失踪的哥哥》《割掉鼻子的大象》《活孙悟空》等作品更多指称为“科学幻想故事”①关于“科学幻想故事”的提法很常见,《我们爱科学》《少年文艺》等主要发表科幻作品的阵地在文章类别标注中更多将科幻作品归类为“科学幻想故事”。 其他高士其《让孩子们获得丰富的科学知识的滋养》(《人民日报》1962 年6 月10 日第5 版)、彭伯通《电脑和人脑》(《人民日报》1957 年3 月13 日第8 版)等文章均更多地使用“科学幻想故事”的命名。。 指称的使用隐含着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权力场对科幻相关文类的期待:面向儿童或是相当于儿童阅读水平的读者群,以通俗易懂、活泼有趣的科幻故事来普及科学知识。 不过,一些评论者还是隐然地察觉到了“小说”“故事”的文体差异,高士其试图从读者年龄层上将科幻小说与科幻故事廓清——他认为科幻小说面对的读者对象是年龄较大的少年儿童,而科幻故事面对的是年龄较小的儿童[10]。
三、编辑型作家群惯习中的少儿基因与科普基因
从教育背景来看,“十七年”时期科幻文学作家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呈现出了相对一致性。集中于理工、农学、经济等专业,中专/高中或是大学教育的经历为创作提供了基本的科技知识储备。 学科背景对于作家而言,是内在于其精神品质之中的文化资本——不断地积累、演变,并演化为创作的能量。 赵世洲指出,那一时期创作科幻小说的人多数是从写科普作品转过来的。 可以肯定地说,科幻小说的起点是科普[11]327。 由上可知,这些创作者大部分有着理工科背景,或是对科学充满兴趣。 郑文光本身就有着天文学家的身份,并在科研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种科学家的身份极易使得他在初始从事科幻文学创作时创作出姓“科”的作品。 再如鲁克,他虽然毕业于浙东中学,没有在大学某一专业深耕过,但是他童年时期便喜欢观察自然,这种对科学的热忱一直持续一生[11]189。 他秉持科幻要植根于科学和社会的观点,小说中所写到的科学要有根据,反对片面追求曲折离奇的作品,主张对少年儿童的智慧启蒙,这使得他的作品一直恪守科学的底线。 如此,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科幻文学作家,一方面在科幻作品中勾勒着未来科技发展的种种现代化幻影,另一方面以此践行着对民众、尤其是少年儿童的科学启蒙,而能最大程度展现未来丰富样貌的故事结构莫过于《小灵通漫游未来》式的“参观式”叙事模式。
从作家工作经历来看,多数有过编辑、教师、科研等经历,编辑型作家群现象较为突出。 作家的成长离不开个人的精神劳作,但也往往与他人相互影响进而形成群体。 “十七年”科幻文学作家群的形成离不开编辑对作家的带动与影响,“左手编辑,右手作家”的现象尤为常见。 据笔者统计,当时较为活跃的郑文光、叶至善、迟叔昌、童恩正、刘兴诗、王国忠、赵世洲、郭以实、萧建亨、嵇鸿、鲁克等11 位作家,半数以上都有过编辑工作经验。 例如,王国忠曾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第三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后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郭以实主编《科学儿童》《少年科学画报》,曾在商务印书馆任科普编辑。 这些有着少儿科普期刊或少儿科普图书从业经验的编辑,在科幻文学作家资源青黄不接的情况下,更容易操刀从事科幻文学创作。 他们秉持“编辑也应当有创作的本领”的理念,认为编辑从事创作是体会作者甘苦、与作者建立共同语言的途径。 这种职业经验使得他们创作的出发点和旨归都倾向于围绕少年儿童、普及科学打转。 编辑型作家试图将政治启蒙和科学启蒙合二为一,在功能上实现对少年儿童的教化。编辑与科幻文学作者联手创作的情况当时也不鲜见,例如《割掉鼻子的大象》即是作者迟叔昌与编辑叶至善(于止)合作完成的。
这种特殊现象集中出现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文坛缺少科幻文学创作者,而少年儿童又是急需被科普的对象。 当时的报纸期刊普遍面临的窘境是,文学时事方面的、无论是原创抑或是翻译稿件,都不缺作者,唯独科学方面的撰稿者稀缺。 由编而写,经历身份地位变化的同时,其惯习也因场域变化或是行动者地位的变化而被持续、开放式地构建。 兼具二者身份的作者既充当科幻文学创作规范的制定者,又充当规则示范者,这一类作家无疑对那一时期科幻文学写作范式的构建有强力的形塑作用。 科普编辑的职业为科幻文学的发表也提供了便利,他们常常在科普类刊物中拿出大量篇幅来发表作品,也带动了科幻小说的科普化倾向。
除了上述惯习推动,像当时盛行的凡尔纳的科幻文学作品和以伊林为代表的苏联科学文艺也影响着科幻文学创作者的惯习养成。 凡尔纳作品笔调活泼风趣,情节婉转,人物形象饱满,熔知识性、趣味性、冒险性于一炉,洋溢着“人定胜天”“科学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深受少儿读者的喜爱。 这种凡尔纳式的创作基调影响并建构着科幻文学创作者的习性,并成为“十七年”少儿科幻文学作品的集体气质。 迟叔昌和鲁克都表示曾受凡尔纳影响。 迟叔昌称,因为协助妻子的翻译工作,他帮忙抄写凡尔纳的译著,其间对其小说的构思之精妙拍案。 苏联科学文艺作品的输入助推了中国科幻作品的儿童化与科普化。 自然科学的普及在苏联被视为共产主义教育中尤为重要的板块,而科学通过文学艺术走向大众化一直是苏联推崇的重要途径。 高尔基提出科学幻想读物必须具备科普功能,这种创作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 伊林、齐奥尔科夫斯基等苏联作家的作品在1949 年之前就被译入,特别是作为“儿童科学文艺作家”定位的伊林影响了郑文光、赵世洲、嵇鸿等科幻作家。
余 论
本文试图重回历史语境,尝试从场域关系视角探索“十七年”的科幻文学生成,重回新中国成立之初科幻文学栖居的政治权力场域生态,展现各种力量的倾向和角逐。 突破了以往较为单一的分析视角,呈现了“十七年”科幻文学的场域生成。 我们可以窥见强大的政治场域如何渗透于科幻文学场域,成为“计划制科幻”的强大推手;场域中的行动者诸如期刊等生产机构及编辑,以鲁迅、高士其为代表的文学价值认定者在科幻文学少儿转向中的作用。 从科幻文学相关的命名指称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语境命名背后的“占位”过程。 从教育背景、所受影响等方面剖析科幻文学创作者惯习中的少儿基因,同时观照当时较有代表性的编辑型作家群,则可以更好地深入到创作者的成长肌理层。
我们注意到,中国科幻文学在“十七年”时期少儿化转向的产生并非偶然,科幻文学场是一种科幻文本构成的关系场,其少儿化转向是作家、评论家、编辑、出版机构、研究者的关系场共同促成的结果。 换言之,在少儿科幻文学的生产、传播、实践和衍变中,既有作为制度化环境作协、报刊、文学市场和书报检查制度的影响,又有作为文学场域的成员(作家、编辑、批评者等)的活动,几方力量构成了一个网状的文学场域。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自主性较强的科幻文学,此时更多受意识形态的强力规约,并为几方力量所形塑。
纵观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幻文学,虽多为科普式科幻文学,也有跳脱出“少儿科普式”范畴,文学性、科学性俱佳之作。 童恩正创作于1960 年的《古峡迷雾》即是此范例,它取材于考古学上的真实课题:古巴人失踪之谜,并由此抛出巴王因逃避战争之难(巴国被楚国消灭)而到黄金洞后神秘失踪的诱饵,进而引出后人洞里探奇而发生的故事。 这部作品突破了当时科普式科幻故事的藩篱,开始像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了,是文学场域逐步自主化的开端,也成为中国科幻小说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部作品。 一些嗅觉敏锐的作家如叶至善、萧建亨、赵世洲等均渐察觉到了科幻文学创作的错位,这种洞察和反思也成为科幻文学摆脱少儿化和科普功能束囿的开始。
而今,科幻发展声势益炽,科幻与科普经常并提出现,科幻这个“灰姑娘”真正实现了“独立”。少儿科幻文学亦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门类蓬勃发展。 此时,返归“十七年”时期的科幻文学发展社会政治语境,有助于我们回望来时路,重温科幻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的蹒跚学步、再到渐次转型的历程,看到中国科幻文学在场域中诸种物象的碰撞、博弈间如何实现了突破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