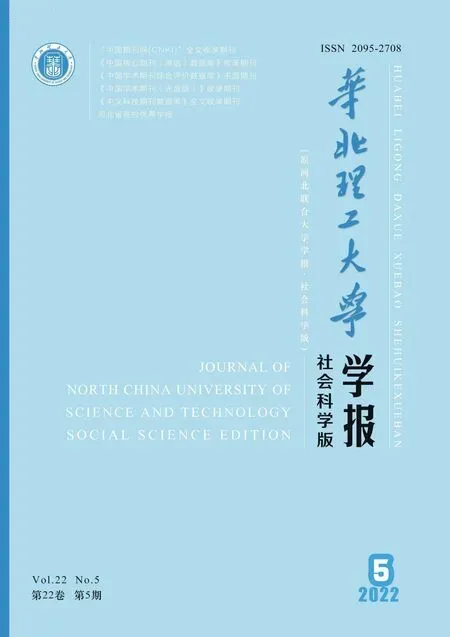双重想象中的中国
——《碧奴》中的风物意象群及其翻译
苏剑光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4)
2005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了“重述神话”项目,邀请世界各国作家以神话故事为原型,进行现代语境下的重述。“重述神话”作家们面临着三个挑战:1.如何赋予古老的神话原型以现代阐释,寄予其深刻的文化与精神内涵,为现代读者构建一个精神港湾;2.如何体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达到与世界其他民族沟通交流的目的;3.如何结合作者自身的写作风格和审美个性,拓展文本的思想和文化深度。
作为参与项目的四位中国作家之一,苏童以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故事为原型,带着对历史、神话、女性的人文主义关怀,运用一贯细腻多姿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不远千里为夫送寒衣,一路上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最终得知丈夫死讯而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形象——碧奴。虽然名为“神话(myth)”,《碧奴》实是对“孟姜女哭长城”这一民间传说(folk tale/legend)的现代阐释。其中对碧奴——这一由神到人的女神形象的塑造,对民众生存状况的描写,对权力和人的异化的讨论,充分体现了“重述”实践的现代性。作品中体现出的包含于中华民族古老神话的道德感,与自然、鬼神、人和谐相处的世界观,国人面对重重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对全人类苦难和生存的哲学思考,是“重述”实践对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诠释。整部作品洋溢着的浓浓的中国水墨画韵味,富有深刻文化含意和审美意境的“意象”群,则是作者苏童个人写作的印记。
意象“通常指创作主体通过艺术思维所创作的包容主体思绪意蕴的艺术形象”,“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中国学者陈铭与杨义共同构建了关于“意象”的概念,即:1.意象可以由创作主体通过结合个体经验、发挥想象力创作出来;2.意象包含了创作主体个人的独特思想和审美;3.意象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4.意象独具中国文化特色,是中国叙事文学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叙事文学的主要特征。中国先锋派作家苏童深谙意象运用之道。“他独有的民间化写作立场,诗意的、富有古典意蕴或者哲学内涵的意象”[1]构建了丰富的小说精神内涵,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具有东方意蕴的审美体验。
一、《碧奴》中的民俗风物意象与东方神秘审美语境下的中国形象
在我国四大民间故事中,孟姜女的传说见于歌谣、叙事诗、戏曲、宝鉴等各种形式。其中关于时节、动植物、生活习俗、鬼怪巫术、丧葬习俗等方面的风物随着故事的传播和历史的沿革逐层叠加,比白蛇传、牛郎织女和梁祝要更为丰富。作者苏童从传统中汲取养分,以这些风物为素材,构建了一系列的意象群。它们在文本中时而光彩夺目,时而藏起光华,成就了《碧奴》的神话性,同时也织就了故事的叙事框架,为读者提供了东方审美的对话渠道,营造了独特的审美氛围。初读是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感,然后是“神话”般的奇特夸张,细细品来,在民俗民风中处处蕴含着的东方神秘感令读者回味无穷。
《碧奴》中多姿多彩的意向群的构建无疑是作者独特写作风格的体现,同时也是评价“重述神话”写作实践的一把标尺,它以独特的东方神秘审美为刻度,来衡量《碧奴》的成功与否,即其必须是“神话的”,也必须是“东方的”。相信这是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神话为谁“重述”?对中国读者来说,苏童创造的一系列民俗风物意象伴随着整个阅读体验,帮助读者体会到深刻的精神和文化认同感,这样的重述是有意义的;对西方读者而言,阅读《碧奴》的过程首先也应该伴随着奇特的东方文化体验,继而是对中国文化异质性的发掘和思考,这样的重述译本才是有价值的。《碧奴》的中英文版本的读者也许会在头脑中构建出细节有别的中国形象,比如中国民俗、中国女性、中国的动物、植物,但是不同的阅读体验最终应该引导中西方读者走向同样的精神和文化维度下的同一个中国。因而,面对着英文版的《碧奴》,评论者应该手持同一把标尺,为的是构建一个统一、完整的中国形象。
《碧奴》2007年由著名翻译家葛浩文翻译的出版,一度获得广泛好评。好评中不乏“感激之情”,这位翻译了众多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著名译者,帮助中国文学“走了出去”;另一方面,译文本身符合英语读者对语言的诉求,在“词汇量、平均句长、词长、缩略语的使用方面看,都带有非常明显的英语原创文本特征[2]”。然而,译本是否忠实地描绘了其中的风土人情、民俗风物意象呢?是否引领读者享受到了独特的东方审美呢?是否能够帮助读者进一步体会到作者苏童想要传递的民间哲学思想呢?我们有必要对比原著和译作,围绕着送寒衣、鬼怪巫术、动物植物这三类有着鲜明民俗特色的风物意象,分析它们所蕴含的意义,判断它们对于构建富于东方审美意境的中国形象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进而完善对《碧奴》英译版的客观评价,发掘“重述神话”书写实践的深远意义。
二、《碧奴》中典型风物意象的翻译及其民俗寓意
(一)时节风俗——送寒衣
《国风·豳风·七月》反映了周代早期农民的日常生活情况,曾提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意思是说从九月开始天逐渐要冷了,人们该添置衣裳,抵御严冬了。原著中,碧奴得知其夫岂梁被抓到北方大雁山修筑长城,时值秋天,于是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九棵桑树,换来三筐丝,为岂梁做了冬衣。处于农业社会的秦汉时期,人们的生活无不围绕着“时节”,到什么时节穿什么衣裳,继而形成了“节”,即寒衣节。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人们特别注重祭奠先亡之人,谓之送寒衣。同时,这一天也标志着严冬的到来,所以也是为父母爱人送御寒衣物的日子。
熟稔中国文化习俗的国人会很自然地理解“送寒衣”的桥段。这一构成故事主线的行为动机如同中华民族的其他节日一样,已经成为国人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反映出中华民族遵循自然规律、敬重天地万物变化的世界观。中国读者不会执着地纠结为什么送衣服而不是送银钱等别的东西,也不会讥笑讽刺碧奴不远千里非要“送衣服”给岂梁。习俗往往与禁忌有关,又往往要求一些仪式性的行为和某种特定的物品,这些行为和物品寄托着对亲人和爱人的祝福,帮助他们驱邪避祸。人类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历程伴随着这样的仪式和禁忌,不同民族的仪式和禁忌恰恰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特征和内涵。《碧奴》中的“寒衣”不再是一件冬季衣物,在碧奴不远万里送寒衣的坚持中,它衍生为农业文明中具有仪式感和禁忌色彩的东方意象。
在葛浩文的英译版本中,碧奴依时节而行的行为被译为“take him some winter clothing”和“just a winter coat for my man”,后文“寒衣”变成了一个“包裹(bundle)”,其间没有任何关于“送寒衣”的注解。风俗和风物意象顿时丧失了依附,变成了没有任何文化负载的“行为”和“物品”。碧奴带着这个“包裹”行路千里,坚持要把它送到夫君手上。一路上“包裹”数次险些被抢,有几次碧奴甚至要为了这个“包裹”丧命。丧失了“送寒衣”的民俗意义,“寒衣”在西方读者眼中必然被类化为一个必须要实现的目标,目标和衣服的文化转译的失败,让碧奴在西方读者心理有了死板执拗的负面印象,而不是如苏童所说,碧奴有一颗“淳朴的心”,通过她可以获得“对于苦难和生存的认识”,更不用说最后蜕变为一个女神了。
(二)鬼怪巫术——巫女与鬼魂
人类发展早期,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某些现象的无知,人们逐渐形成了对鬼神的信仰和崇拜,其中也夹杂着一些鬼怪巫术、生活禁忌和关于巫婆神汉的轶事。小说里的柴村是苏童杜撰出来的有着奇特风俗的地方,是“一个女巫的村庄……因巫女而为人们所敬畏,柴村的女儿经其实是一部巫经,神秘而阴沉。”[3]。碧奴想去大燕岭寻夫,走之前去了趟柴村,咨询柴村巫女此行的吉凶,巫女“cleverly avoided giving Binu an answer; instead, they examined her tongue and cut off a lock of her hair, which they held over a flame with a pair of tongs … knelt on a straw mat, placed bleached tortoise shells in an earthen vat, and then emptied them back out, all the time chanting incantations.”(机敏的回避了碧奴的问题、她们检查了碧奴的舌头,剪下一小撮她的头发,放在火上烧烤……然后跪在草席上,把龟甲放在土盆中,又摇出来,同时口中念念有词。)[4]
然后建议她不要去,否则会“中途患病而亡(be struck down by illness on the road and die on the plain.)”这些巫女们自称有些法术,能够“神灵出窍,行去遥远的北方(they had travelled great distances north on spiritual wanderings)”,其中一些人还能“用乌鸦的羽毛辨识方向(had used the feather of a crow as a compass)”。巫女们的这些“神迹”并没有出现在中文版的《碧奴》中,而是由译者葛浩文在译本中讲故事补充完整。
就“巫女”、“巫术”意象的翻译本身而言,秦汉时期确实有巫女的存在,她们用龟甲占卜吉凶,这符合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定,也符合当时的风俗人情。译者在这里做补译处理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则原文内容较为平淡,“巫女”和“柴村”的形象在西方读者眼中借此变得更加丰满起来;二则西方读者对于东方的鬼怪形象一贯有着浓厚的兴趣,译者对细节的添加无疑满足了他们的某种探奇心理。这样的翻译作品有其好的一面,有助于西方读者体会原著中的鬼怪意象;然而添油加醋的描写鬼怪巫术,让国人有一种译者在故意兜售东方文化产品的感觉,甚至可能令西方读者留下落后、愚昧的东方印象。
葛浩文对鬼怪意象的翻译处理还有文化错置的问题。千里为夫送寒衣,一路上碧奴经历了艰难困苦,也遇到了鬼灵精怪。过了百春台,碧奴被一个鹿人卖给了官府,稀里糊涂成了秦素的寡妇。秦素是衡明君的门客,生前是个小偷。车夫无掌拉着秦素的大棺材,碧奴是亡者之妻,鹿人假扮成亡者孝子,前往秦素的故乡七里洞哭丧。碧奴夜晚和棺材一起在麦子地里,和里面秦素的鬼魂讲话,还梦见了镰刀鬼,为她收割了麦子,醒来时看到周围一捆捆的都是麦子。“鬼”在中国民间习俗中既是禁忌,也是众多民间故事的主题,他们多数怀有执念,夜晚出没于阳间伺机报仇或戕害世人。秦素的“鬼”和“镰刀鬼”是很鲜有的善鬼,和碧奴聊天,为她割麦。葛浩文将这两者翻译成了“Qinu’s ghost”和“Harvest ghosts”,前者一直念叨着自己的故乡七里洞“Seven-Li Cave”;后者“all carrying scythes, floated up in the night … threw bundles of oats at her feet.[4]”。国人落叶归根的信仰是秦素的鬼魂执意归乡的源头,对于这一点西方的读者在理解上可能有障碍;镰刀鬼割麦子的桥段具体有什么意义确实首先需要向作者苏童求证,但是无论如何葛浩文译本中的“Harvest ghost”和其“all carrying scythes”的形象都与西方死神的形象合二为一。西方的镰刀鬼不但用镰刀收割麦子(也有玉米等其他农作物),也用镰刀杀人,“收割”亡人魂灵,是一个邪恶的形象。此“镰刀鬼”必然不是苏童笔下怜惜碧奴心酸,为她彻夜割麦的善良的“镰刀鬼”的意象。
(三)动物植物意象——自然风物与苏童杜撰的“马人”、“鹿人”
动植物是中国民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有的象征吉祥如意,如蝙蝠、梅花鹿、寿桃谐音福、禄、寿;梅、兰、竹、菊为花中四君子,象征高洁的气质;有的暗含着某种禁忌,如柳、桑、槐、杨。小说《碧奴》因中英版本的不同,使得不同读者对其中的动植物意象有着不同的解读。
小说中出现的第一类动植物意象是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如青蛙、白蝴蝶、螃蟹、黄鸡、葫芦、桑树、菖蒲等。省去几种仅仅提及的不谈,青蛙、葫芦、桑树在小说中作为有特殊意义的意象而存在。碧奴在去板桥雇马的路上遇到了一只青蛙,是一位儿子被抓去修长城的母亲的亡魂所化,她一路跟着碧奴,希望沿途可以找到自己的儿子。在中国民俗文化中,青蛙或者蟾蜍有着吉祥的寓意,青蛙也象征女性的子宫,在母系氏族文化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葫芦与“福禄”同音,可以辟邪护身,也象征夫妻好合。碧奴认为自己是一只葫芦,在出门给岂梁送冬衣之前,她找到一只葫芦,并迫切的想要找到一个向阳的好地方,把这个葫芦埋起来。在碧奴心中,埋藏葫芦的仪式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安葬自己的过程,以保证自己死后有所依托,不会变成一个孤魂野鬼。而作为岂梁象征的桑树,一般被认为是长在野地里的树木,这暗含着岂梁无父无母的境遇。在英译本中,青蛙、葫芦、桑树等单纯作为动植物出现,被译为“frog, gourd, mulberry tree”。结合小说前文的阅读经历,英译本读者可以形成这样的理解:
1.成为葫芦和桑树是碧奴和岂梁的宿命。在《哭泣》这一章,作者描述了北山人养儿育女的习俗:
“男婴的来历都与天空有关,男孩们降生的时候,骄傲的父亲抬头看天,看见日月星辰,看见飞鸟游云,看见什么儿子就是什么,所以北山下的男孩,有的是太阳和星星,有的是苍鹰和山雀,有的是雨,最不济的也是一片云,而女孩子临盆的时候所有的地屋茅棚都死气沉沉,做父亲的必须离开家门三十三步,以此逃避血光之灾,他们向着东方低头疾走三十三步,地上有什么,那女儿就是什么,虽然父亲们的三十三步有意避开了猪圈鸡舍,腿长的能穿越村子走到田边野地,但女儿家的来历仍然显得低贱而卑下,她们大多数可以归于野蔬瓜果一类,是蘑菇,是地衣,是干草,是野菊花,或者是一枚螺狮壳,一个水洼,一根鹅毛,这类女孩子尚属命运工整,另一些牛粪、蚯蚓、甲虫变的女孩,其未来的命运就让人莫名地揪心了。”[3]
这种习俗被忠实地翻译并保留在了英译本中,帮助读者理解了到,故事中的桃村里,每个人都与大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
2.葫芦和桑树注定相依相伴。英译版中的这样描写了碧奴嫁给岂梁之前的心理活动:“because she is a gourd, and gourds hang from mulberry trees!(她是葫芦,注定挂在桑树枝头!)”[4]。至于对其他动植物意象的理解,不但英译本读者,中国读者也可能产生误解,以为他们的作用如迪士尼童话电影中动植物的角色一样,插科打诨而已。
小说中出现的第二类动物意象是作者苏童杜撰出来的“马人”“鹿人”“野猪人”。王公贵族喜好骑射,“不骑射,毋宁死”,而马匹都被国王征用,便有门客创造了很多射猎方法。百春台有“马人”为马供人骑、“鹿人”假扮鹿供人射,贺兰台有“野猪人”练习滚坡。他们不用服兵役,每天练习作为各种动物的技艺,渐渐变成了那种动物。“马人”为四大王公服务,地位高尚,受人敬仰;“鹿人”是被射猎的对象,地位较低,但是“马人”的事业要从“鹿人”开始。瘦长腿的男孩子们被选为“鹿人”,逐渐形成了团体,表现好的会得到面饼子作为赏赐。
英译版的小说在“Deer-boys”和“Deer King’s Grave”两章着重描写了“鹿人”的生活,讲到了碧奴误入了“鹿人”们的居所,他们原本要把她作为礼物送给衡明君,后来又将她囚禁在鹿王坟守墓。故事中“鹿人”各有分工,如General Deer,Chancellor Deer。然后在“The River Bend(河湾)”一章中,译者简要介绍了“马人”“鹿人”的来历:“Riding humans for the hunts became fashionable in aristocratic circles, gaining steadily in popularity.”,又讲述了“马人”和“鹿人”在一次衡明君外出打猎时发生的矛盾冲突。原著中有《鹿人》《马人》《鹿王坟》《门客》和《衡明君》五章,对于“马人”等的由来、门客和衡明君及“马、鹿人”的关系有着清楚地交代。在一次访谈中,作者苏童被问及这些动物是否如《哈利·波特》《指环王》里的动物一般具有奇幻色彩,苏童表示对这些奇幻作品“没读过,也没有兴趣”,在写作中更关注的是“传说与现在的距离,这个尺度不能太远,但又不能太近”。很多读者将“马、鹿人”理解为“阶级视角”,是“讽喻和批判”[6],是阶级压迫下人的异化,他们丧失了家园,忘记了母亲,努力的学习如何成为一只鹿。也有人认为“马、鹿人的忍耐,不是软弱和奴性的‘忍’,而是散发着‘原始力’的‘忍’”[7]。无疑,阅读译本的读者是无从感受这些的,中国漫长历史中王公贵族们奇异的兴趣爱好如何异化了百姓,中华民族又是如何的忍辱负重、勤劳善良,对于英译本读者来说是有些遥远的了。
三、结语
对比苏童的原著与葛浩文的译著不难发现,原著承袭了孟姜女故事的民俗性,期间穿插了大量的关于时节、习俗、鬼怪巫术、动植物等的民俗文化意向群,构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东方审美意境;而后者对原著的叙事顺序和叙事内容有着某种程度的重建,关照了英语文本的整体性,故事读起来比较顺畅。对于原著中所提及的习俗、动植物、鬼怪巫术意象译者做了“适当、适量的翻译”,就审美而言,译本确实传递了很多东方元素,如巫女、鬼怪、动物、植物等。如果考虑到整个审美意境和读者的整体审美体验,译者则打破了原著中的意向群,破坏了完整的东方意境和中国形象,西方读者的阅读体验难免有些支离破碎。由于译本中意向群的碎裂,这部“重述神话”作品所传达的中国文化独特的民俗性,作者苏童所传递的民间哲学思想和立意构建的独特东方审美失去了其思想和精神维度,最终与“重述神话”项目想要传达的深刻内涵失之交臂。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了四个要素——作家、作品、读者、世界,“长期以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多集中在作家、作品层面,对民俗研究,也相当程度上停留在民俗本身,世界成为我们研究中的薄弱环节[8]。”世界是人所处的环境,是社会,是历史,是文化,没有对“世界”的把握和理解,就没有对作家、作品的深刻理解。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下,“大历史被小历史取代;政治舞台被民间文化所取代”[9],另一方面,“西方的语言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广为流行,其他语言已经被清洗或被改造了[10]”。如何以英语这一西方语汇传达中国人的“世界”,在汉语缺席的情况下,帮助西方读者解读中国文化的风物民俗意象,直至深入到民间哲学的层面,并最终通过对中国叙事作品的艺术审美来构建中国形象,是包括葛浩文在内的译者们所面临的问题。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和精神宝库,千百年来,通过阅读不同民族的神话故事,全世界的人们了解不同民族的起源,发现其中的共同之处,同时也意识到本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在全世界文化通过沟通和交流、不断深度融合的今天,全球化“看似繁荣,”背后却是“单一和贫乏……。而跨文明思潮则是一种对单一的反动,它以求异作为研究单位,是在保持文明差异基础上追求一种异中之和或者是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11]”。“重述神话”项目首先应该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在通过现代阐释为本民族读者提供精神养分的同时,构架起一座民族文化沟通的桥梁,为不同文化互补短长。中国神话通过“重述”的走出去,需要参照以往文化产品走出去的经验,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接受和英语文本的特点,更需要帮助读者发现独特的东方话语,构建独特的东方审美体验,最终呈现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