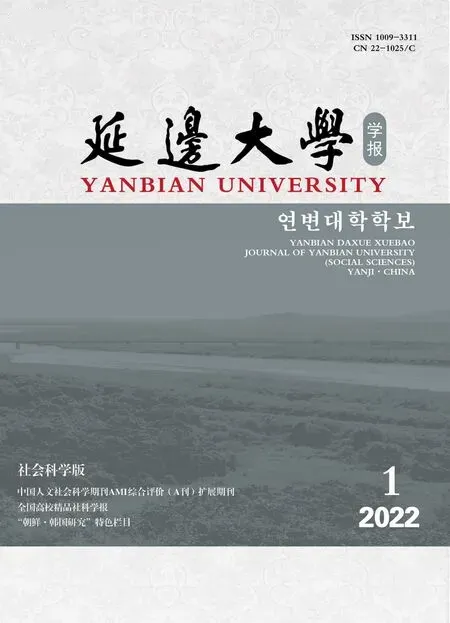从抵牾走向认同
——清代朝鲜使臣燕行诗中的盛京书写
杨柳青 温兆海
明清时期,朝鲜作为藩属国定期派遣使臣出使中国,历时长达五百余年。使臣出使期间创作了一系列记录中国体验的使行作品。(1)明代朝鲜使臣出使中国所作的使行记录多称“朝天录”,清代开始使用“燕行录”一称。目前,学界也有用“燕行录”来统称明清此类文献的说法,本文中“燕行录”特指清代朝鲜使臣撰写的使行记录。17世纪中叶的明清易代,对朝鲜传统的华夷观念产生了剧烈而持久的冲击。燕行诗作为“燕行录”中的重要文类,与中朝历史紧密相涉,书写着使臣燕行道途的所见所闻、对明朝的眷恋追思、对清朝的百感交集以及行走异国的羁思情怀等。这不仅是其时历史语境下的真实史料,也是使臣文化心态最直观、最生动的复现。
“境接华夷经战伐,地连幽蓟阅兴亡”,(2)[韩]李德寿:《西堂私载》,《韩国文集丛刊》(186),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180页。清代盛京(即今辽宁沈阳)具有其他燕行沿途城市不可比拟的“历史—地理”双重特殊性。作为明清鼎革的最直接见证,盛京经历了从“朝天”到“燕行”的骤变,亦是朝鲜由“思明”向“北学”转变的历史缩影。燕行诗中的盛京,是清朝“首业之地”,是燕行必经之城,是历史凭吊之所,极为完整、清晰地投射出朝鲜使臣对清意识的嬗变脉络及轨迹。事实上,作为文学体裁的燕行诗,“体现了对历史复杂性的表征、认知与判断”,(3)汪正龙:《重审文学的历史维度——兼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第174-182页。保留了使臣的集体记忆,成为其思想—心灵史的有力见证。本文以朝鲜使臣盛京主题燕行诗为线索,钩沉明清鼎革以降二百余年间盛京书写流变,通过探求其中所表达的情感及思想关照个体和时代。在论证清代朝鲜使臣对清意识之递嬗的同时,借此管窥两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变化与发展,以期探究他们对东亚格局变动的认知与反馈。
一、敌视与贬斥:一代衣冠从此异
清初,朝鲜遣使是在清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含怨忍痛、迫不得已”的政治表态。朝鲜朝自建立之初就与明朝确立了宗藩关系,仰慕其为中华文明上国。经历万历年间的“壬辰战争”,朝鲜更加感激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以拯救其于危国边缘的“再造之恩”。(4)[韩]洪大容:《湛轩燕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43),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79页。明亡后朝鲜坚持“尊周思明”,此时期的朝贡旅程、追思明朝、“悲情想象”成为盛京燕行诗主旋律。
都城在他国注视者的目光下易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天命十年(1625)后金迁都于沈,天聪八年(1634)改“沈阳”为“天眷盛京”。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沈阳遂称清开国之都。同年12月清出兵朝鲜,次年(1637)朝鲜降,签订城下盟约对清纳贡称臣,与明的宗藩关系就此彻底切断。此次“丙子战争”给朝鲜带来沉重的打击。清代盛京虽先为朝贡中心后为陪都,乃是燕行必经之城,然对清的敌视与怨恨,令使臣对这座城市充满了蔑视。“由南门入,左右市廛一如汉制,驱入东馆即锁门”,(5)[韩]李景稷:《赴沈日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15),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26页。清初“燕行录”中对盛京城寥寥数语的记载,排斥与反感之下漠不关心的态度跃然纸上。
至于清初的盛京形象,又将如何呈现在被迫踏上燕行之路的朝鲜使臣燕行诗之中呢?崇德四年(1639),申濡“以(朝鲜)侍讲院文学,陪从沈馆”,其间作《沈中杂诗四首》,从自然环境写起,层层递进描绘出“胡兵”遍野的肃杀情景,刻画出争战中求生百姓的苦难生活。其中两首兹录于下:
万古辽阳塞,清秋朔漠庭。天文西见斗,地理北通溟。
水带城阴黑,烽连野戍青。传闻选车骑,毡幕遍郊坰。
羌妇含愁思,胡兵半渡辽。哭夫云髻剪,送葬纸钱烧。
汉将久无敌,单于犹自骄。连年未解甲,杀气满层宵。
(6)[韩]申濡:《沈馆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21),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2-23页。
其组诗中带有贬斥色彩的词语反复出现,通篇充斥着蔑视与仇恨的控诉。事实上,“窟”“穴”“巢”等字眼频繁出现在清初使臣诗中用以指代盛京。此前,1637年入沈的燕行随员金宗一就写道:“安能扫却连城窟,挟鸟归来汉水都”。(7)[韩]金宗一:《鲁庵集》,《韩国文集丛刊续》(27),首尔:景仁文化社,2006年,第196页。金堉1644年也曾在沈馆有如出一辙的慨叹:“何当迅扫毡裘域,包虎深藏退日戈”。(8)[韩]金堉:《潜谷遗稿》,《韩国文集丛刊》(86),首尔:景仁文化社,1992年,第33页。暗示渴望明朝能够力挽危局,可见朝鲜正强烈期盼大明能够武力复国。时间的流逝也并未使他们淡忘仇恨,到了“辽沈中原失,于今岁六旬”的1683年,沈城依旧被谢恩正使金锡胄愤恨地注视着:“渐营新窟穴,犹壮旧城闉”。(9)[韩]金锡胄:《捣椒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24),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5页。
倘使称谓意味着固有偏见,那么对现地体验的书写,其敌视、贬斥之意则更为明显。“霜寒狐貉冻,风急槖駞鸣。剑气奔星落,弓声过雁惊”,(10)[韩]申濡:《沈馆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21),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3页。申濡通过连续渲染出的萧瑟意象来凸显战地之凄凉情景,意欲烘托其笔下城池“杀气满层宵”的肃杀氛围,实则更似其心理情感的外在投射。1637年,金宗一则表达得更为直接:“行八日得达于沈,未及数十里,望见黑祲团结直上,盘空涨天,乃沈都也”。(11)[韩]金宗一:《鲁庵集》,《韩国文集丛刊续》(27),首尔:景仁文化社,2006年,第222页。“黑祲”为黑色之气,意指不祥天象。几十年后,战事远去的沈辽已是民康物阜,金锡胄眼中景色却依旧一派萧索苍茫:“塞日翻成祲,边风易作尘”,诗中自注曰:“是日,白虹贯日”。(12)[韩]金锡胄:《捣椒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24),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5页。白色的长虹穿日而过,古人认为此天象是君王殒命、大变将至的预兆。足见金锡胄对清朝、清帝的厌恶与咒詈,他亦力图通过天气、景物等的描绘,展示清朝危在旦夕的征兆。至此,关于盛京的意识形态描写,已成固有书写模式,演变为使臣心中“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隐喻。他们一边揣测清朝的气运,一边祈祷大明的恢复,这是在政治上配合清朝的表面下,内心却拒绝接纳和妥协的一种发泄方式。对“皇明中华”恢复的强烈期盼不止体现在朝鲜使臣诗文中,更是其君臣上下的一致立场。1686年,朝鲜肃宗曾对大臣说,“自古匈奴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1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三·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125页。“城郭空留恨,山河尚带羞”(14)[韩]洪柱元:《无何堂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续》(30),首尔:景仁文化社,2006年,第532页。“畴昔皇华凡几过,旧时城郭已全非”,(15)[韩]崔锡鼎:《椒余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29),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03页。17世纪的使臣,多次显露对明亡的惋惜追忆之情。清入关后推行高压政策,钳制之下的举国学人士子多不敢秉笔直书。而反观朝鲜,其对清履行外交的文书似无僭越,然其内心的抗拒与鄙视,君臣上下对清“朝而不宗”的应对策略,都在燕行诗中展露无遗。
17世纪朝鲜使臣对盛京的实地体验,往往沉浸于个人历史情感,使相关书写只有情感投射而缺少现实描摹。这种集体书写背后蕴含着深层文化意蕴,反映了使臣的强烈“华夷”观,强调明之“正统”,将清视为“夷狄”。清建立之初的几十年,朝鲜朝廷充斥着攘夷复仇的气氛,孝宗更曾倡议“北伐”并暗中备战,想以此光复大明。这一时期使臣诗中的盛京多呈现意识形态功能的负面形象,承载着对清的敌视与贬斥。这些文本带有浓烈的历史意识,传达的信息在后续反馈中不断得以强化。直至17世纪末,此“垄断”式书写,随着康熙帝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并进一步对朝鲜推行“怀柔”政策而渐渐出现转变。
康熙二十五年(1686)夏,谢恩使书状官吴道一将抵盛京之际,联想以往“燕行录”中此地种种描述,不禁慨叹“此行何事不伤心”。(16)[韩]吴道一:《燕槎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29),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9页。然而真正入城,眼见的却是“画阁连空”“关外富商”“夹路银幡”……大为震撼的吴道一,摆脱前人之“悲情想象”,忠于所见所感,赋诗《沈阳感怀》云:
周遭城郭带山河,画阁连空粉堞峨。关外富商争绾毂,云南名士半移家。
横风玉勒花骢闹,来路银幡锦肆夸。此地经过偏有感,野梨江上泪添波。
(17)[韩]吴道一:《燕槎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29),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60页。
这绝非一首普通的燕行感怀诗,透过字句直抵内心,便不难感知清朝的日益强盛昌隆带给一位朝鲜使臣的心理震撼与冲击。8年后的1694年,他再次赴燕则感叹:“从古地形辽左大,即今天府沈阳雄”。(18)[韩]吴道一:《后燕槎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29),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23页。诗中称沈阳为“天府”并承认其“雄大”,这是对此前使臣诗中一贯贬斥书写的极大挑战与重要转折。吴道一笔下全新的盛京形象,发出了朝鲜使臣心理转变的先声,尽管在一片鄙视否定之声中显得单薄乃至突兀,却埋下了转机开始的细微伏笔。
二、直视与鄙夷:纲常终得赖谁存
从17世纪末进入18世纪,“康乾之治”下的清朝,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无不日益强盛繁荣起来,这令使臣开始关注起现实盛京。燕行诗内容也从单一的历史情感抒发,扩展到对城池建筑、军政设施、社会经济、人文风俗等的全面观察,盛京书写随之立体丰富起来。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正三年(1725)的燕行随员赵文命。其《沈阳杂咏十绝》等诗以及记录道途见闻的《燕行日记》,角度宏观、观察细微,为认识这一时期的盛京提供了宝贵史料,如有:
粉堞峩峩十里回,三层楼阁郁崔嵬。
陪都一一皇居样,左右衙门五部开。
(19)[韩]赵文命:《鹤岩集》,《韩国文集丛刊》(19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443页。
这是盛京城给他的直观感受,并提到陪都地位,对此他在另一首诗中又评骘道:“奉天都统僭如君,关外雄藩盖此云”。(20)[韩]赵文命:《鹤岩集》,《韩国文集丛刊》(19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443页。盛京战略地位重要,八旗精锐咸聚,其诗云:“山海以东千里土,黑衣全属沈阳军”“门外寻常列甲兵,双双戈戟雪霜明”。(21)[韩]赵文命:《鹤岩集》,《韩国文集丛刊》(19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443页。赵文命对军事颇为关注,路逢盛京甲军“押领载银车八辆”,曾询问军士银俸问题。“又见数三甲军驱近百匹马群而去,无羁无絷,而略无横逸,低头垂鬣,如争一路”,遂称赞“胡儿御马之能也”。(22)[韩]赵文命:《鹤岩集》,《韩国文集丛刊》(19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601页。而诗句“百队旗亭次第开,商车日日响如雷。长帘云自牛庄至,大布皆从锦卫来”(23)[韩]赵文命:《鹤岩集》,《韩国文集丛刊》(19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443页。则是对繁庶市肆经济的观察。
盛京在诸多方面都给使臣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城池规模之宏大,军政设施之完备令其倍感惊异。明朝设“沈阳中卫”属辽东都司,规模甚为有限,而经清几十年间数次修缮扩建,城池宫阙、军政设施皆已相当宏伟坚固。1721年,谢恩副使李正臣提及此地军事实力时这样描述:“马畜千群皆可战,铁城重壁不须关”。(24)[韩]李正臣:《栎翁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续》(53),首尔:景仁文化社,2008年,第12页。如正使李德寿笔下“关外雄藩说沈阳,峥嵘危堞拂云长”,(25)[韩]李德寿:《西堂私载》,《韩国文集丛刊》(186),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180页。这般描述正逐渐成为使臣书写盛京城的共识。书状官李喆辅则尤其对城池工事之坚固赞不绝口称“最是内外城制整齐坚致”,以至自愧不如而感慨“观此而乃知我国城筑,真儿戏耳”。(26)[韩]李喆辅:《丁巳燕行日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37),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48页。不仅如此,盛京地区经济的繁盛也被格外关注。清入关后,其作为陪都政治功能相对弱化,逐渐转向以经济为中心。市井奢丽、商铺林立、杂货诸肆、人声鼎沸,发展为关外最大的贸易中心、货物集散地,具有浓厚的商业氛围和显著的地方特色。(27)刘铮:《燕行与清代盛京:以〈燕行录〉为中心》,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第128页。1729年,金舜协记载:“(盛京)左右市肆其架屋之绝妙宏壮难皆称之,而廛房所在货物可谓壮矣。初见辽阳其市肆之盛倍蓰于我东矣,今见沈阳又倍蓰于辽东,可见其大小之悬殊”。(28)[韩]金舜协:《燕行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38),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31-232页。城中街道蔚然兴盛的商业景况令使臣眼花缭乱:“迟迟驱入市坊隈,着处繁华锦绮堆。十字街头楼阁出,三重城里府衙开。群胡骇见衣冠集,行贾携将物货来”。(29)[韩]赵文命:《鹤岩集》,《韩国文集丛刊》(19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443页。1732年,李宜显亦诗云:“沈府重关内,边城列堡前。高闳堆玉贝,华肆绘金仙”。并特别自注云:“沈阳以繁华称”。(30)[韩]李宜显:《壬子燕行诗》,[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35),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31页。
以上所述是使臣切实感受到盛京的繁华富庶后,进行的丰富记述。然而,物质层面的直面与正视,尚不能抵消文化维度对清的鄙夷与不满。究其原因,是维护程朱理学的朝鲜士大夫阶层在18世纪仍深受“尊周思想”与“华夷观念”影响,使其常对沈地人文风俗等加以质疑与批判。类似“贾毂近轿腥触鼻,邮人劝马唤惊眠。殊方饮食难调胃,酒是驼酥肉是羶”(31)[韩]李正臣:《栎翁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续》(53),首尔:景仁文化社,2008年,第12页。的表述亦频频出现在诗中。赵文命在沈就曾作《可怪》一诗:
可怪夷风尽染华,看来一一与人差。家唯供佛宁祀祖,夏或披毛不着麻。
剃发乳儿皆戴笠,白头村女亦簪花。唯存一事如唐法,客至寻常进茗茶。
(32)[韩]赵文命:《鹤岩集》,《韩国文集丛刊》(19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444页。
他眼中的盛京地区,汉人男子剃发胡服,满族老妇亦涂粉簪花,全国上下皆崇佛淫祠,已然不再是过去“中华上国”的形象。赵文命由此认为原本的华夏大地“夷风尽染”,早已风俗不纯。
18世纪以降,在清强大的军事力量、稳定的社会政治、雄厚的财力物力面前,朝鲜逐渐在政治上开始承认清朝。这也使燕行使臣得以正视盛京,震撼于它的繁荣与兴盛;然而进一步了解其民风民俗后,崇奉朱子学的他们又充满了鄙夷之情。这种政治与文化上的矛盾态度,使其笔下的盛京书写多样而复杂。他们更加坚信“中华”已辱没于“夷狄”之手,认为朝鲜坚持正宗的礼仪成为中华文明的守护者,因此竟发出“纲常终得赖谁存”(33)[韩]李世白:《雩沙集》,《韩国文集丛刊》(146),首尔:景仁文化社,1995年,第418页。的诘问。通过塑造“夷俗尽染”的清朝社会,来反衬其作为中华思想继承者的“优势”地位,“小中华”意识因文化上获得的优越感而进一步加强。朝鲜“比17世纪更加彻底地体现出要将作为‘华’的朝鲜与作为‘夷’的清朝区分开来的强烈的华夷分离意识”。(34)徐东日:《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49页。
然而,即便是在日趋自闭于“小中华”的朝鲜内部,依然有燕行使臣萌发了新的觉悟。1728年,正使尹淳亲眼见识了“沈阳大都会,巫闾大气势”,又慨叹清朝“城池民物市肆之钜丽繁华”,进而产生“回思我东,若井底观天,迫隘不能容也”的反思,在细心观察清朝诸多先进的民生制造之法后,甚至提出“一一取法以来,亦经世之一助”(35)[韩]尹淳:《白下集》,《韩国文集丛刊》(19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346-347页。的想法。可见,在正视清朝发展的基础上,朝鲜开始注重将“自我”与“中华”进行比较,转向内在关注的思想渐现端倪。当然,这种对朝鲜主流传统华夷观的挑战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尹淳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朝鲜政学界的强烈批判与打击。
三、“思明”到“北学”:苟利于民而厚于国
历史行至18世纪下半叶,百年已过,清朝非无灭亡之兆反而愈发昌隆,而固守传统华夷思想的朝鲜却停滞不前、民生凋敝。在不可回避的巨大现实落差之下,一些使臣带着疑问踏上了燕行之路。1778年,谢恩正使蔡济恭在《盛京行》中,不仅详细描绘了盛京商业繁盛、财物积聚的盛况,更提及了其武备强大、地位尊崇的优越,诗中有句云:
黄瓦鳞鳞间碧瓦,中天赫日照行宫。别起牌楼十字街,列肆济济分西东。
高揭标号金作榜,锦绣珠玉堆玲珑。天覆地载生万货,光怪昼夜霏彩虹。
五部衙门郁相当,沈阳将军官最雄。一路东走接灵塔,车输白金齐华嵩。
有时皇帝谒陵至,飞腾万骑争虎熊。万国使者问安来,跄跄执玉趋走同。
(36)[韩]蔡济恭:《含忍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40),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45页。
18世纪下半叶愈加繁昌的盛京,带给朝鲜使臣全新的视域与体验,使他们更加感受和见识到清朝的鼎盛伟业。洪大容、朴趾源等有识之士敏锐地意识到“小中华”思想的局限,使他们积极反思、寻求富国裕民的途径,价值观念也由此转向。这是朝鲜关注点明确向内转移的时代,新的华夷观念与“北学”思想应时而生。
乾隆三十年(1765),时年34岁的朝鲜文人洪大容,抱着愿见天下奇士的目的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其《燕记》记述了在中国的诸多见闻,回国后,又在撰写的散文《医山问答》中进一步提出了“华夷一也”和“域外春秋”的观点。洪大容思想的转变,对后来“北学派”的诞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7)王国彪:《朝鲜“燕行录”中的“华夷”之辨》,《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第33-49页。朴齐家受洪大容思想影响,于1778年至1801年间4次出使燕京,力主朝鲜“利用厚生”,大力倡导“北学”中国。他著述的《北学议》标志着北学思想体系的确立,促进了“北学派”的形成。1780年,随使团赴燕祝寿的朴趾源,也是18世纪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朴趾源在《驲汛随笔》中称“为天下者,苟利于民而厚于国,虽其法之或出于夷狄,固将取而则之”,(38)[韩]朴趾源:《燕岩集》,《韩国文集丛刊》(252),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177页。旗帜鲜明地阐释了北学立场。
在“北学”思想与新型华夷观影响下,朝鲜士大夫在政治、经济上更加肯定了清朝的优越性,因而怀有“利用厚生”“富国裕民”之目的观察体验中国的使臣逐渐增多。从“思明”到“北学”,盛京书写也完成了由鄙视到直视、最终以肯定为主的转变。1782年,副使洪良浩出使清朝时,作《盛京》诗云:
白头山下射雕归,黄草岭前万马肥。大漠飞腾龙虎气,雄城睥睨帝王畿。
云生黑水成丰沛,天送长星入紫微。席卷八荒高一榻,福陵梓树已盈围。
(39)[韩]洪良浩:《燕云纪行》,[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41),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9页。
1789年,金祖淳更强调了盛京地理位置与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地利谁如古范阳,盘辽枕海设坚墙。赢输满汉分形日,先后熊袁掎角场。五部留司规密勿,八旗诸族号精良”。(40)[韩]金祖淳:《燕行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65),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45页。清历代统治者对盛京皆极为重视,不仅是清人将其视为“根本之地”,更在于其地理的特殊要位。朴趾源的《盛京杂识》中对此分析道:“沈阳乃其始兴之地,则东接宁古塔,北控热河,南抚朝鲜,西向而天下不敢动,所以壮其根本之术,非历代所比故也”。(41)[韩]朴趾源:《燕岩集》,《韩国文集丛刊》(252),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162页。突出了盛京对周边地区强大的连通与牵制作用。可见,此时期使臣已不单着眼于关注现实盛京,更试图探究其历史渊源。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使臣关于盛京的历史意识,一方面体现在对盛京本身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对朝鲜馆、“三学士”殉节处等遗迹的瞻仰与凭吊。“丙子战争”后,朝鲜向清纳贡称臣,并送昭显世子及凤林大君等至沈阳为质子。此外,力主抗清的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人在沈阳被杀,号称“三学士”。崇德五年(1640),“丙子斥和”的朝鲜大臣金尚宪又遭清朝追究,押拘于沈,其间创作了大量诗歌,命名《雪窖集》。此后,每当朝鲜使臣踏入盛京,这些记忆与想象中的“历史”便一次次重现。“翻思丙丁岁,清血自沾濡”,(42)[韩]柳命天:《退堂集》,《韩国文集丛刊续》(40),首尔:景仁文化社,2007年,第408页。按:“濡”为“襦”之误。盛京因而成为燕行途中最为特殊的历史凭吊之所,使臣于此地常借诗抒发内心的悲愤与缅怀之情。1680年,副使申晸作《沈中感旧》,咏诗志感以缅怀朝鲜孝宗,诗云:
王孙芳草未言归,曾作咸阳一布衣。
自是天心元有定,箕封休运属龙飞。
(43)[韩]申晸:《燕行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22),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39页。
诗中引战国楚太子“咸阳布衣”之典故,抒发了对当年孝宗入质沈阳这一史实的悲愤哀怨之情。正因如此,即便后来朝鲜馆已是“旧馆荒凉败壁空”,却依旧是使臣“城南驻马徘徊久”(44)[韩]金兴庆:《燕行诗赠季君》,[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65),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96-397页。的彷徨踟蹰之地。除对孝宗的缅怀外,讴歌金尚宪、“忠烈三学士”之诗作亦甚为多见。“西河馆里再拘时,往事犹征雪窖诗”(45)[韩]李世白:《雩沙集》,《韩国文集丛刊》(146),首尔:景仁文化社,1995年,第419页。“雪窖遗篇今尚在,鸿泥陈迹杳难攀”(46)[韩]崔锡鼎:《椒余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29),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04页。等即是对金尚宪的悼念。1749年,书状官俞彦述则对三学士倍加推崇:“闻昔西门路,三人共杀身。魂应为赵鬼,名足并殷仁。柴市风犹冷,燕山草不春。蛮夷亦嗟叹,东国大明臣”。(47)[韩]俞彦述:《松湖集》,《韩国文集丛刊续》(78),首尔:景仁文化社,2009年,第327页。可以说,“冠盖迢迢入沈阳,至痛在心人谁识”,(48)[韩]黄景源:《江汉集》,《韩国文集丛刊》(224),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45页。恐怕正是使臣入沈回忆起这段历史时的真实写照。过往历史不会改变,但“注视”与“想象”历史的人在变。在18世纪“北学”思想影响下的朝鲜,这段历史也因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鞭策激励着朝鲜不断反思、寻求进步。
18世纪下半叶的“北学”思想积极拓展了朝鲜士大夫阶层的视域和思想,促使后人积极思考、探索前行。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北学”思想自身存在着局限性,事实上也并未得到大规模的实践,更没能完全取代传统的华夷观。但传统华夷观在朝鲜的影响却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其对中朝关系的影响日趋衰微。而这一时期使臣燕行诗中对盛京以肯定、赞扬态度为主的书写,在众多“燕行录”文本中如同一面明镜,清晰地映射出朝鲜使臣情感与思想的转向,这也标志着朝鲜深度完成了从“思明”到“北学”的重大历史转变。
四、羁思与交流:他乡一醉葡萄酒
经过18世纪中朝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受“北学派”促成的良好人文交流环境的影响,朝鲜文人积极接触清朝学术和思想,在19世纪与清人展开了密切频繁的多角度、深层面的互动交往。在此氛围下,使臣面对盛京的心态也更加客观与平和,19世纪的盛京终于以一座普遍意义上的异国城市形象出现在燕行诗中。他们以探寻的目光注视这座城市,以兴奋的笔触描绘异域景物风俗,同时抒写着羁旅之苦与思乡情怀。而与盛京地区文士的相识与交往,也进一步体现了中朝两国平等相待的深层次人文交流。(49)金柄珉:《文明对话:中韩人文交流的历史与展望——以中国与韩国的人文交流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7-25页。
嘉庆十年(1805),书状官姜俊钦抵达盛京。异域的韶光春日、灯火炊烟,令他生出许多思恋亲友故土的离愁别绪,《浑河》一诗即写尽了羁旅途中对归国之期的殷殷期盼:“白塔斜阳万里,浑河春水千家。东归政在何日,落尽关山杏花”。(50)[韩]姜俊钦:《輶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67),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3页。1829年,译官李尚迪随冬至使一行入燕。天气转寒舟车劳顿,行至盛京,再难掩对亲友的思念之情,遂赋《沈阳示谦受》,诗云:
耶里江西落照移,暝尘蓬勃掩车帷。
他乡一醉葡萄酒,今夕孤吟雨雪诗。
(51)[韩]李尚迪:《恩诵堂集》,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第14页。
数日颠簸于暝尘车帷,望着眼前的浑河落日,孤高旷远之中的漂泊旅人倍感寂寞苍凉。此情此景唯有将这愁思倾注至杯酒,寄托于诗情,以期他乡一醉解千愁。1835年冬至使书状官赵斗淳,记录了羁旅思乡之际收到兄长书信的惊喜与欣慰:“看云步月意何如,地北天东梦到疏。可是今程奇事在,沈阳城外见家书”。(52)[韩]赵斗淳:《心庵遗稿》,《韩国文集丛刊》(307),首尔:景仁文化社,2003年,第77页。几十年后的1869年,“行迈支离不暇闲,四旬才到沈辽间”(53)[韩]李承辅:《石山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续》(131),首尔:景仁文化社,2012年,第359页。的冬至正使李承辅,其使行之路却因年迈而愈显苦楚与艰辛,衣食住行无不令他倍感磨难:“人间难事路为难,今日餐如昨日餐。晓角每憎惊睡起,重裘莫御逼肌寒。纵然车卒驱豪快,其奈轿夫告苦酸。原隰只缘王事竣,敢言气力向衰残”。(54)[韩]李承辅:《石山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续》(131),首尔:景仁文化社,2012年,第359页。如此,使臣在沈期间,多借诗抒写其羁旅之困苦与思乡之愁绪,“今夜知应中野宿,吾生自信任浮萍”(55)[韩]申锡愚:《海藏集》,《韩国文集丛刊续》(127),首尔:景仁文化社,2011年,第552页。“清宵孤客立,候月上东台。秋思前年似,乡愁此日来”(56)[韩]李田秀:《入沈记》,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二辑·第十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5页。等,皆是此般情感之倾诉。
使行之途固然奔波艰辛,但从中体验异域风土人情却也不失为旅途的趣味。1828年,朴思浩诗云:“盛京自古繁华地,绣错雄都百物丰。虹际双龙开复道,云间五凤绕行宫。一城堤柳烟丝绿,万户盆榴雨叶红。余取葡萄酒十斗,赤栏桥畔访梅翁”。(57)[韩]朴思浩:《燕蓟纪程》,[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85),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68页。此诗景中寄情,字里行间透露出抵沈后轻松愉悦的心情以及对沈城风物细腻新鲜的感受。1858年,谢恩副使金永爵亦有诗句:“沈阳儿女满头花,雪白双骡驾绣车。路遇朝鲜年使至,琉璃罩眼暗窥些”。(58)[韩]金永爵:《邵亭稿》,《韩国文集丛刊续》(126),首尔:景仁文化社,2011年,第340页。笔调柔和轻快,以细腻的笔触描摹出盛京儿女的俏皮与娇羞,塑造出充满生活气息的满族女子形象。次年2月,燕行归途,金永爵更难掩从容忻悦之情,写下一组别具韵味的组诗《沈阳归路》,其云:
围墙累甓屋无梁,日日驴车载粪忙。塞上沙田多瘠薄,春来犹得种高粱。
赴市村翁鬓发星,挂驴钱吊买鱼腥。新春拟课儿孙读,更购新镌三字经。
(59)[韩]金永爵:《邵亭稿》,《韩国文集丛刊续》(126),首尔:景仁文化社,2011年,第341页。
这是一组反映乡村生活的诗作,既是一幅风景画,又是一幅风俗画。诗中采用白描手法勾勒出大环境,“围墙”“驴车”“塞上”“沙田”,有静有动,寥寥数笔便生动描画出当地的特色风土人情。从诗中亦可见村民生活忙碌充实,精神愉悦且上进。金永爵笔下的盛京郊区,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诗中通篇洋溢着积极祥和的氛围,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写者对异国乡村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欣赏。
除上述表达羁思与描绘风貌的诗作外,在盛京地区与清朝文人的交游唱和诗也占有很大比例。这是由于,在前期北学派文人的持续引导和影响下,朝鲜文人开始怀着体验学习先进文化的心态出使中国,并积极了解清朝学术思想、加入文坛活动。此后,朝鲜政学界要人金正喜、申纬等随使团进京,拜翁方纲为师,为其后两国文人进行更为深广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在这种大环境下,盛京燕行诗亦见证了中朝文人之间蓬勃广泛的深入交流。1812年,申纬赴燕驻留盛京期间,与时任盛京将军的和瑛相见并进行了诸多交流,其《题沈阳将军和太庵(宁)西藏赋后》云:
将军棨戟盛京城,早识西藏赋有名。
一自鱼凫通鹿马,万重山里万重程。
(60)[韩]申纬:《奏请行卷》,[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67),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72页。
和瑛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曾任副都统,充西藏办事大臣,任职8年。《西藏赋》是其撰写的描绘藏地宗教民俗、地形物产等的长篇散文。可见申纬不仅知晓和瑛其人,更对其过往经历及文学创作颇为了解和赞赏。另一首《太菴席上,贈奉天府尹工部富侍郎(俊)》则叙述了申纬等使臣参加了和瑛宴席,结识工部侍郎富俊并对其称赏不已:“侍郎英竗气如虹,茶果留人廨宇中。简选名卿须重寄,文渊文溯两京雄”。(61)[韩]申纬:《奏请行卷》,[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67),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72页。申纬作为朝鲜著名文人,在沈期间即表现出对清人学识风度的赞誉有加,并热衷展开积极深入的交流。1828年,朴思浩《赠缪楳澥公恩》一诗,也记载了他与当时盛京名士缪公恩相识相交、依依惜别的真挚情谊:“沈河风日丽,老树自生花。怊怅令人别,关山度岁华”。(62)[韩]朴思浩:《燕蓟纪程》,[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85),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68页。如果说结识新交令人欣喜无比,那怀念旧识就显得尤为惆怅了。1831年,谢恩正使洪奭周借诗抒写,道出岁月匆匆、故人不再的怅惘与悲戚:
辽鹤重来岁月深,异方何处更披襟。
拦街短发皆新面,只觅清心一粒金。
(63)[韩]洪奭周:《渊泉集》,《韩国文集丛刊》(293),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年,第103页。
此诗题云:“沈阳城中,有李维翰、潘文典、冯好善三人,皆廿九年前谭话唱酬者也。今问之,皆无知者”。可见二十九年前在沈城中与三位清文人的推诚相与,给他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与期许。洪奭周未能与知音重逢,然而朝鲜使臣与盛京文人的友好交流却得以不断传承。三年后,使臣赵斗淳在沈阳“文昌阁下,遇一少年”并与之笔谈交流。他称少年“极清楚”,“以学生业来游是学”,并记下少年近作一首:“惯听风信频栽竹,欲养诗心学种梅。为移小竹衣全湿,贪看闲花屐尽泥”。他赞少年“语虽浅近,颇有才致耳”,更为其赋诗:“可爱南城徐少年,眉清目秀玉生烟。笔端应问捷如响,更写新诗三两篇”。(64)[韩]赵斗淳:《心庵遗稿》,《韩国文集丛刊》(307),首尔:景仁文化社,2003年,第77页。足见对此少年的喜爱赞赏之情,同时也反映出使臣与清人的交流并不局限于官方,民间交流亦日渐活跃。
综上,“羁思”与“交流”已成为19世纪盛京燕行诗的创作主题。诗的内容从18世纪多描绘城池、市肆、庙宇等地理景观,转变为更加倾向记录内心情感及在沈交游历程等。可以说,朝鲜使臣对盛京的感受,已由18世纪偏重观察外在形象的“游历式”表面体验,转变为19世纪深入内部的“浸入式”互动交流。至此,有关盛京的书写,个人情感再次回归。然而此时,是真正从个体出发的人生体验与性情体现,已不同于17世纪因明亡清替而产生的关乎家国兴衰与历史意识的集体情感抒发。
五、结语
本文对“燕行录”文献中盛京燕行诗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展现了自17世纪清初肇始到燕行末期的19世纪,朝鲜使臣出使经由盛京时强烈而独特的情感宣泄,发掘出相关书写背后的驱动力与民族文化心理。并将宏大叙事下的“长时段历史观念”与注重细节的“异域文化自身发掘”相结合,(65)张伯伟:《汉字的魔力——朝鲜时代女性诗文新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162-183页。清晰地反映了清代中朝关系和文化交流在东亚政治格局变动下的巨大变革与考验,揭示了个人情感、民族思想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这一方面折射出以往两国的历史、文化关系,另一方面,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本文的研究对当代东亚价值观重构与东亚新秩序构建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关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