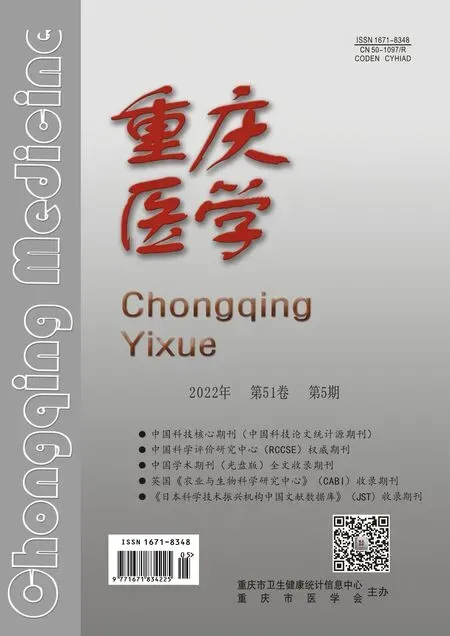血清HBV RNA在抗病毒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张 琪 综述,秦 波 审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 400016)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是一个全球性健康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道,全球约有2.57亿慢性HBV感染者,每年约有88.7万人死于HBV感染相关疾病和并发症,尤其是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1]。目前用于治疗乙型肝炎的抗病毒药物主要包括两大类:核苷类似物(nucleoside analogues,NAs)和干扰素(interferon,IFN)。随着它们的广泛应用,HBV的复制得到了有效抑制,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也得到了改善。
肝内共价闭合环状DNA(covalently closed circular DNA,cccDNA)的持续存在是导致HBV感染慢性化的主要原因。肝内cccDNA的清除意味着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完全治愈[2]。NAs或IFN均无法直接作用于肝内cccDNA,因而完全治愈几乎无法实现。目前多以临床治愈作为CHB治疗的理想终点,即治疗后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和乙型肝炎病毒DNA(hepatitis B virus DNA,HBV DNA)持续消失、乙型肝炎e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HBeAg)转阴、伴或不伴HBsAg血清学转换,而无论肝内cccDNA是否被清除[1-3]。肝内cccDNA的存在使得达到临床治愈的患者仍面临停药后复发的风险,因而大多数CHB患者需长期甚至终生服药。
理论上,监测肝内cccDNA水平对评估CHB患者病情及评估抗病毒治疗疗效均有帮助。临床工作中由于肝穿刺难以推广,肝内cccDNA的监测困难重重,亟待寻找可以反映肝内cccDNA存在及活性的新指标。血清HBV RNA就是近年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作为一种新型血清学标志物[4],已被证明是包含前基因组RNA(pregenomic RNA,pgRNA)及其剪切变异体的病毒样颗粒或衣壳抗体复合物。而pgRNA由肝内cccDNA直接转录形成,因此,血清HBV RNA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肝内cccDNA存在与活性,且在反映抗病毒治疗应答及预测停药后复发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血清HBV RNA的来源及性质,血清HBV RNA与肝内cccDNA的关系,以及血清HBV RNA在抗病毒治疗中可能的作用进行综述。
1 血清HBV RNA的来源及性质
HBV是有包膜的DNA病毒,其基因组为部分双链环状DNA(relaxed-cirular DNA,rcDNA)。HBV通过与肝细胞膜上的钠离子-牛磺胆酸-协同转运蛋白结合进入肝细胞。进入肝细胞后,rcDNA在细胞核内以负链DNA为模板形成cccDNA,接着以cccDNA为模板转录形成3.5×103、2.4×103、2.1×103、0.7×103这4种不同长度的mRNA。其中长3.5×103的pgRNA作为模板,在聚合酶作用下逆转录形成rcDNA,同时募集乙型肝炎核心抗原(hepatitis B core antigen,HBcAg)形成核衣壳。这些含有病毒基因组的核衣壳一方面可以获得病毒包膜后形成完整的病毒颗粒,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进入肝细胞核作为肝内cccDNA储备。
自1996年在慢性HBV感染者血清内发现HBV RNA以来,血清HBV RNA的来源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最近WANG等[5]证实血清HBV RNA实际上是由未经转录或部分转录的pgRNA经衣壳化、被HBsAg包裹所形成的病毒样颗粒。JANSEN等[6]通过使用去污剂破坏HBsAg包膜,并利用HBcAg特异性抗体行免疫沉淀,进一步证明了血清HBV RNA与病毒样颗粒的关联:即血清HBV RNA存在于含有衣壳和包膜的病毒样颗粒中。随后,PRAKASH等[7]也通过梯度分离和核糖核酸酶实验表明,血清中的HBV RNA存在于病毒样颗粒中,其结构类似于含有包膜、携带HBV DNA的传染性单颗粒。同时,该研究还发现血清HBV RNA是多聚腺苷酸化的,具有基因组长度。BAI等[8]实验则发现血清HBV RNA主要由pgRNA或被聚合酶水解形成的pgRNA剪切变异体组成,在长度上具有异质性,从3.5×103到数百个核苷酸不等;主要以衣壳-抗体复合物形式循环,少部分以病毒样颗粒形式循环。而针对这些病毒样颗粒的研究显示,NAs治疗下血清中的HBV RNA病毒样颗粒缺乏传染性,其中3′-末端截短体的形成可能是造成这些病毒样颗粒复制缺陷的主要原因[9]。
因此,血清HBV RNA实际上是包含pgRNA及其剪切变异体的病毒样颗粒或衣壳抗体复合物,目前的研究显示在NAs治疗时这些病毒样颗粒不具有传染性,而在未接受NAs治疗的患者中,HBV RNA病毒样颗粒是否具有感染能力仍需进一步研究加以证实。
2 血清HBV RNA与肝内cccDNA的关系
前述已提及pgRNA由肝内cccDNA直接转录而来,因而血清HBV RNA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肝内cccDNA存在与活性。GIERSCH等[10]研究发现未经治疗的HBeAg阳性的HBV感染小鼠的血清HBV RNA与肝内cccDNA水平相关(r=0.89,P<0.001)。WANG等[5]使用恩替卡韦/拉米夫定阻断体外细胞和转基因小鼠HBV DNA聚合酶的逆转录活性后,发现pgRNA病毒样颗粒水平上升,提示NAs仅阻断rcDNA生成而不影响pgRNA合成,因而提出NAs治疗下血清HBV RNA水平仍可反映肝内cccDNA存在及转录活性。
GAO等[11]关于HBeAg阳性CHB患者的一项队列研究显示基线肝内cccDNA水平和血清HBV RNA水平相关(r=0.25,P=0.02),但较HBsAg与肝内cccDNA相关性低(r=0.36,P<0.01)。NAs治疗后,肝内cccDNA下降水平与血清HBV RNA下降水平相关(r=0.28,P<0.05),但低于与HBsAg(r=0.38,P<0.01)和HBV DNA(r=0.35,P<0.01)下降的相关性。CHEN等[12]研究认为与HBV RNA和HBsAg相比,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相关抗原(hepatitis B virus core antigen associated antigen,HBcrAg)与cccDNA有更好的相关性。研究共纳入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的85例HBeAg阳性者和25例HBeAg阴性者,经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HBeAg阳性者,血清HBcrAg、HBsAg和HBV RNA均与肝内cccDNA相关,其中血清HBcrAg(β=0.563,P<0.001)与cccDNA的相关性优于血清HBsAg(β=0.328,P<0.001)和HBV RNA(β=0.180,P=0.003)。在HBeAg阴性者,只有血清HBcrAg与肝内cccDNA水平相关(β=0.774,P<0.001)。上述研究均表明血清HBV RNA与肝内cccDNA相关性较好,但其并不是用于反映肝内cccDNA的单一优势指标。
血清HBV DNA联合HBV RNA在反映肝内cccDNA活性方面显示出优越性。HUANG等[13]研究发现CHB患者的血清HBV DNA联合HBV RNA对于反映肝内cccDNA水平(r=0.412,P<0.001)优于单用HBV RNA(r=0.363,P<0.001)或HBV DNA(r=0.367,P<0.001)。进一步分层分析显示,这一现象仅在HBeAg阳性者中存在,提示血清HBV RNA联合HBV DNA在反映HBeAg阳性者肝内cccDNA活性方面具有优势。
因此,血清HBV RNA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肝内cccDNA存在及活性,但或许不是反映肝内cccDNA的最优指标。如果能将血清HBV RNA和HBV DNA或HBcrAg、HBsAg等指标结合在一起,肝内cccDNA水平或许能更可靠、更准确地被反映出来,但血清HBV RNA具体该如何与其他指标联用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3 血清HBV RNA在抗病毒治疗中的应用
3.1 血清HBV RNA可反映抗病毒治疗应答
多种研究表明基线血清HBV RNA可预测抗病毒治疗应答。LUO等[14]经过回归分析发现血清HBV RNA是预测HBeAg血清转化和病毒学应答的独立指标。基线血清HBV RNA<4.12 log10拷贝/毫升的患者更易实现HBeAg血清学转换(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为80%)。JANSEN等[6]一项研究包括86例接受聚乙二醇干扰素(pegylated interferon,Peg-IFN)和NAs联合治疗的患者,该研究显示低基线血清HBV RNA水平可以预测HBeAg阴性患者联合治疗应答效果(OR=0.44,P=0.19)。
除基线血清HBV RNA水平外,抗病毒治疗过程中血清HBV RNA水平及其变化也能预测抗病毒治疗应答情况。VAN CAMPENHOUT等[15]对76例接受Peg-IFN单独治疗、55例接受Peg-IFN联合拉米夫定治疗的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治疗第12、24周的血清HBV RNA水平显示出预测HBeAg血清转化的良好能力(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0.75,P<0.001)。治疗第12周血清HBV RNA>5.5 log10拷贝/毫升可协助早期辨别30%的治疗无应答者(阴性预测值>90%)。GAO等[11]则发现NAs治疗96周后,实现HBeAg阴转的患者血清HBV RNA水平明显更低(P<0.01),而在基线、治疗后第48、72周时两组血清HBV RNA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笔者研究后认为两个研究在时间上显示出的差异性或许与NAs及IFN抗病毒机制不同有关:NAs主要通过抑制逆转录过程实现抗病毒作用,而IFN则同时具有免疫调节及抗病毒作用,因而IFN较NAs更能有效地抑制HBV复制、耗竭肝内cccDNA储备,从而使血清HBV RNA水平更早下降,帮助更早预测HBeAg血清学转换。
血清HBV RNA联合其他血清学指标较其单一使用时能更好地预测抗病毒治疗应答。LIAO等[16]对16例长期接受NAs治疗、血清HBV DNA持续低于检测下限的HBeAg阳性CHB患者进行研究,发现9例发生了HBeAg转阴的患者其血清HBV RNA及HBcrAg水平下降更为明显(P<0.05)。表明对于接受NAs治疗且实现病毒学应答的患者,血清HBV RNA和HBcrAg有助于监测抗病毒治疗效果。WANG等[17]研究发现HBeAg阳性者经恩替卡韦治疗后,第24周时的血清HBV RNA水平是HBeAg血清转化的有力预测因子,但血清HBV RNA联合HBeAg预测HBeAg血清转化优于单用血清HBV RNA。
因此,基线及抗病毒治疗后血清HBV RNA及其变化在反映抗病毒治疗应答方面显示出一定优势。但血清HBV RNA联合HBcrAg或HBeAg等指标可能将进一步优化抗病毒治疗效果评价体系。未来以血清HBV RNA为基础的抗病毒治疗应答评价体系的具体应用需要更多的实验加以验证。
3.2 血清HBV RNA可预测停药后复发
血清HBV RNA能反映停药时肝内cccDNA状态,因而在预测停药后复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WANG等[5]对33例接受NAs治疗后达停药标准的CHB患者进行停药后随访,发现停药时血清HBV RNA阳性的21例患者全部出现复发,停药时血清HBV RNA阴性的12例患者仅3例发生复发(100%vs.25%,P=0.001),提示停药时血清HBV RNA水平是监测NAs治疗安全停药的潜在指标。另一项研究对32例接受Peg-IFN单独治疗或与NAs联合治疗后,实现HBsAg阴转、HBV DNA低于检测下限的CHB患者进行研究[18]。停药后随访发现,治疗结束时血清HBV RNA阳性的所有7例患者在停药后均出现HBsAg逆转、HBV DNA复阳,而HBV RNA阴性的25例患者中仅5例出现HBsAg逆转、HBV DNA复阳。该研究表明这些看起来实现了“功能治愈”的CHB患者,其HBV复制模板(尤其是停药时血清HBV RNA呈阳性的患者)——cccDNA,可能仍然具有转录活性,停药后仍面临较大的复发风险。SETO等[19]的研究发现停药时血清HBV RNA≥44.6 U/mL的患者停药后发生病毒学复发的风险更高(48周累积发生率为93.2%),提示停药时血清HBV RNA≥44.6 U/mL的患者不应轻易中断NAs治疗。
血清HBV RNA联合其他血清学指标可预测停药后持续应答,用于指导安全停药。FAN等[20]纳入130例治疗前HBeAg阳性、接受替比夫定或阿德福韦治疗并达到停药标准的CHB患者,发现停药时实现血清HBV RNA和HBV DNA双阴性的患者临床复发比例(8.0%)明显低于停药时未达双阴性的患者(31.4%,P=0.018),该结论在40例接受恩替卡韦或替诺福韦治疗的HBeAg阳性患者中同样适用。提示治疗结束时血清HBV RNA和HBV DNA双阴性与HBeAg阳性患者停止治疗后的持续应答相关联。FAN等[21]另一项研究对127例基于替比夫定治疗的HBeAg阳性患者进行停药后随访,发现在治疗结束时血清HBV RNA和HBcrAg均为阴性者未出现临床复发,而治疗结束时血清HBV RNA和HBcrAg均为阳性者有46.8%在随访期间出现临床复发(P<0.001),该结论在59例使用恩替卡韦或替诺福韦治疗的患者同样适用,提示血清HBV RNA联合HBcrAg可用于指导NAs治疗后安全停药。CAREY等[22]研究则表明对于在NAs治疗下、HBV DNA持续检测不到的患者,血清HBV RNA和HBcrAg仍然是反映HBeAg阴性者肝内cccDNA持续转录的灵敏血清学指标,两者同时也是预测停药后谷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及病毒学复发的重要指标。
因此,停药时血清HBV RNA水平可预测停药后复发,协助指导安全停药。相比而言,停药时血清HBV RNA阳性者在停药后面临更大的复发风险,因而不应轻易停止抗病毒治疗。此外,停药时血清HBV RNA联合HBV DNA或HBcrAg预测双阴性患者停药将更为安全,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需要进一步研究。
3.3 血清HBV RNA相关的新型抗病毒药物
由于血清HBV RNA在CHB患者抗病毒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针对阻断血清HBV RNA生成的衣壳装配调节剂(capsid assembly regulators,CAMs)也受到了一定关注。CAMs大致可分为两大类[23],一类是以NVR 3-1983为代表的苯丙烯酰胺和氨磺酰苯甲酰胺化学物,另一类是以BAY 4109为代表的杂芳基二氢嘧啶类化合物。前者可促进衣壳类似物的形成,后者则诱导和聚集异常衣壳结构。CAMs可以引导衣壳进行错误组装,导致pgRNA的包裹受到抑制,进而阻止了pgRNA病毒样颗粒(即血清HBV RNA)的产生;另外CAMs还可以抑制HBV DNA复制,导致丹颗粒的形成受到抑制。由于肝内cccDNA来源于pgRNA逆转录形成的松弛环状DNA(rcDNA),因而通过CAMs抑制pgRNA的生成或许会帮助耗竭肝内cccDNA储备,向完全治愈更近一步。虽然目前暂无相关上市药物,但CAMs药物的研究将为众多的CHB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
4 总结与展望
血清HBV RNA不仅可反映抗病毒治疗应答,还能预测停药后复发,其与HBV DNA、HBcrAg、HBsAg等指标联合使用时更具优势。目前已有学者提出基于血清HBV RNA的一些新概念,如将病毒学应答重新定义为血清HBV DNA和HBV RNA的持续丢失[24];提出“准临床治愈”概念,即血清HBV DNA、HBV RNA持续丢失伴血清HBsAg低水平[24];将隐匿性肝炎(occult hepatitis,OBI)重新定义为在HBsAg检测不到的个体血清或肝脏中,HBV DNA和(或)HBV RNA持续阳性[18]。而笔者认为,未来血清HBV RNA在临床中具体该如何应用仍需进一步大规模、前瞻性、系统性研究。此外,血清HBV RNA水平与慢性HBV感染的时期[25-26]、HBeAg状态、谷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基础核心启动子突变和HBV基因型均相关[15]。因此,血清HBV RNA作为临床标记物的使用,还必须考虑这些因素,相信未来阻断血清HBV RNA合成的多靶点药物将会为乙肝治愈提供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