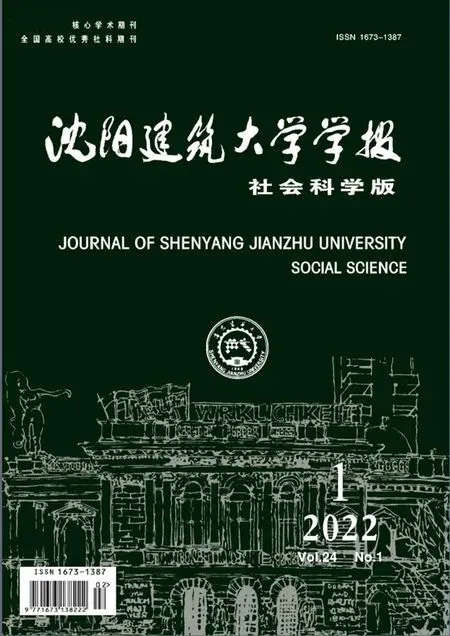从“雌雄同体”的女性形象探析奥康纳矛盾的女性观
杜翠琴,刘凤霞
(1.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45)
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25—1964)是20世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南方女性作家之一。因其作品严肃深刻的主题及独特的艺术风格,她被评论界一致公认为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最杰出的作家[1]。奥康纳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尤为突出的是一批生活在狭小天地里孤陋寡闻的妇女群。笔者以这些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奥康纳矛盾纠结的女性观。
一、奥康纳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奥康纳的许多作品都以南方农场为背景,人物主要包括女主人、她们的孩子以及黑人奴隶,鲜有男性家长的角色。例如:在《火中之圈》《背井离乡的人》《格林利夫》《善良的乡下人》《救人如救己》《启示》《聚合》等作品中,反复出现女性家长,即具有男性特征的“雌雄同体”的寡母形象,她们不再是男权社会中男性的附属品,她们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话语权,她们如同传统男性角色,独自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解读奥康纳的这些“无父”[2]文本,不难发现:奥康纳试图通过塑造这些颠覆传统的“雌雄同体”群像,对传统女性角色进行解构,从而解构传统男权话语。
因为奥康纳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对于她所处的时代而言,她在女性问题上的见解是前卫的、特立独行的。她的这种批判意识特别体现于她对传统母亲形象的深刻反思上。她笔下的许多女性形象表现出对传统女性附庸角色的抗拒。另一方面,天主教把女性定位为弱势角色[3-4],奥康纳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却不赞同女性亦步亦趋模仿男性的生活方式,试图篡夺男权传统赋予男性的角色内容与特权。但在《火中之圈》《背井离乡的人》《格林利夫》等作品中,家长型女主人公屡遭挫折失败,充分体现了她这一矛盾思想。
事实上,这些人物及奥康纳笔下类似境遇中的其他人物,并未真正失去她们的女性特征,只是有时候把自己女性家长的权力发挥到极其夸张的程度。这些女性也许显得不那么讨人喜欢,但她们在失去男主人的世界里设法生存的智慧值得赞扬。
尽管这些被苏珊娜·波森(Suzanne Morron Paulson)称之为“强势型”的寡妇都对她们的雇工极为苛刻,但在她们所共同面临的经济境况之下,她们的争强好胜是合乎情理的。路易斯·韦斯利(Louise Westling)指出,在奥康纳主要创作时期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南方对于自己经营农场的寡妇的敌意与内战刚结束时的情形一样:在那个时期,试图管理自己事务的寡妇被认为是“傲慢的”[5]。这些女性也许有意识地采取了男性的伦理标准,因此,摒弃了女性自身特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她们几乎也别无选择。
在男权社会中,为了谋求生存,《火中之圈》《背井离乡的人》《格林利夫》中的“雌雄同体”的女性人物均展示出了难能可贵的能力。这些女性坚定地认为女士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术语,她们有权享有尊敬、保护,有权占有周围人的劳动。
这些故事中的基本情节都有相似之处:这些人物都从她们的亡夫那里继承了农场,但继承的钱财却微乎其微,不得不自己经营农场,这有悖于她们成长过程中通常被训导的传统的南方淑女角色。故事中,在家庭范围内,女性的权力是毫无争议的,虽然在传统上,南方女性并不涉足公众场所或经济领域。而因为故事中的女性所继承的农场融私人与公众两种场所于一体,这些农场为她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场所。因此,每位女性都把她们的农场作为家庭的延伸来看待、经营。
二、“雌雄同体”的女性形象代表剖析
1.《火中之圈》中的科普太太
在《火中之圈》中,科普太太试图使她的3位不速之客的举止变得像绅士,期望他们表现出应有的顺从。从她的这种努力中可以看出,科普太太起初对这些孩子作了错误的判断,用一种纯粹母性的方式控制他们,这与她对工人们所采用的方式截然不同。作为一位女性管理者,她期望这些孩子对她礼貌、恭敬。因此,当这3个从亚特兰大的房屋开发公司逃跑出来的孩子拒绝她不诚恳的母性的关心的时候,她震惊了。评论家玛格丽特·韦特(Margaret Whitt)指出:“在科普太太对付那些入侵的孩子的时候,在她身上丝毫找不到威严的女农场主的踪影,她以南方淑女的身份对他们讲话。”[6]
科普太太完全有理由相信她的手段会在这些孩子身上产生作用。令科普太太困惑不解的是:她给这些孩子提供食物,尽力使家里变得温馨,但这些孩子不仅忘恩负义,还不断挑战她的经济权威,甚至拒绝承认她对土地的所有权。
尽管科普太太起初相信,正如她能够控制手下的黑人工人和莎草一样,她也能够控制她农场上所有破坏性的、非人性的力量。但从她对“火”的偏执态度中可以看出,她后来开始明白她的控制究竟有多么微弱。
事实上,由于男孩子们拒绝执行科普太太要求其去灭火的命令,科普太太最终也发现在最关键的时刻她没有任何权威。科普太太与奥康纳笔下的大多数单身母亲一样,作为有控制欲的母亲是失败的。
2.《背井离乡的人》中的麦金太尔太太
与科普太太一样,《背井离乡的人》中的麦金太尔太太最终对她的工人失去了控制,以失去她的农场而告终。吉扎克初来乍到,即帮助麦金太尔太太控制住了整个农场。因为麦金太尔太太早已厌倦了工人们对自己的不敬,当最终雇佣了一个勤劳、诚实、有见识的工人吉扎克时,她开始获得一种力量感、权威感,开始对工人行使她的权威,她宣布驱逐了一长串寄生于她的“白人垃圾”家庭。但她最终发现,她只是暂时摆脱那些无用的贫穷“白人垃圾”和黑人,因为她必须与这两类人中的男性合谋,以便摆脱吉扎克。正如科普太太偏执地认为“她在火灾中失去了一切”一样,麦金太尔太太也担心失去赋予她权力的社会秩序。由于麦金太尔太太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母性权威,她只是一个比她年长许多的男人的遗孀,而且又无子嗣,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对她来说至关重要。她能够忍受“白人垃圾”的懒惰、“黑鬼”的偷窃,是因为在她看来,那些层次的人天生就具有这些特征,这些行为只是强化了业已形成的社会秩序,即把黑人置于社会底层、贫穷白人置于中间、她自己置于最上层。
3.《格林利夫》中的梅太太
《格林利夫》中的梅太太不仅与奥康纳笔下的其他女性人物一样,不能与她的后代和工人和睦相处,而且与她笔下其他获得权力的女性一样,极其重视业已形成的社会秩序。梅太太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男性化了。丈夫去世后,她不仅接管了他的农场,也接替了他的男性角色,在周围5位男性的同化影响之下,她在生活中更加坚定不移地扮演着男性角色。同大多数男性一样,她将事业功名看作判断人生价值的惟一标准,处处表现出极强的进攻性和控制欲。当她注意到“白人垃圾”格林利夫家的男孩子们突然崛起时,担心他们可能变成一个“小团体”,因此感到不安。但不同于其他女性土地所有者,梅太太没有男人帮助她管理家务。与格林利夫家相比,她的儿女们对业已形成的秩序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他们公开蔑视自己的母亲。
梅太太与科普太太、麦金太尔太太一样,都抱怨她们懒惰、寄生虫似的雇工。但一旦这些女性失去了经济权威这个附加的武器,她们几乎无法生存。虽然梅太太极力与男权社会抗争,自以为有能力控制格林利夫,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被控制的反而是她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梅太太的失败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与她对立的格林立夫,从而肯定了男权社会,她自己却不得不面对着日益衰败的局面,直至被那头公牛顶死。笔者认为,这一暴力事件与梅太太之死隐含了奥康纳对女性主义者的警示:如果一个女人完全放弃传统女性的角色,转而在事业上试图与男性比肩,甚至试图压制以至控制男性,那她将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自由。美国评论家克莱尔·卡汉思(Claire Kahane)曾指责奥康纳仇视女性,认为梅太太是奥康纳厌女情结的产物。这样的结论显然过于表面化,梅太太的悲剧发人深省,它透视出奥康纳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的独特见解。她清醒地意识到,女性放弃自己的角色,去追求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做法极其危险,因为女性最终难以走出男权社会的樊篱。
因为儿子的冷漠,梅太太生活中几乎“没有男人”,因此,她与科普太太、麦金太尔太太一样,认为自己的农场之所以能正常运转,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独自操劳。3位女主人公都把自己经营农场的努力称之为“工作”,然而她们无一人从事真正的体力劳动。对她们而言,“工作”即是持续不断地发号施令、行使男性的权力。
奥康纳笔下大多数获得权力的女性都认为,尽管手下的工人帮助她们获得了财富,但同时也对她们的权威构成了挑战。梅太太感觉到格林利夫不愿承认她的权威,因为在她试图管教不敬的儿子们时,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而格林利夫恰巧亲眼目睹了她的窘境。而且,如果农场存在一个由黑人工人构成的底层阶级——这个阶级会对白人雇主表现出本能的顺从,那么梅太太可能会被树立为一个权威性的人物,但遗憾的是,梅太太的农场正好缺乏这样一个阶级。
梅太太叹息缺乏一个经营农场的男人,她要求格林利夫兄弟把公牛赶走,但因为她是女人,他们不理会她。显而易见,别人之所以这样对待她,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弱势”身份。由于强硬男性角色的缺失而使自己被轻视,梅太太试图借助强硬、苛刻的要求对此进行弥补。
奥康纳笔下很多获得权力的女性都是如此,梅太太也不例外,对于工人的违抗,她除了抱怨几乎束手无策。一直以来,虽然格林利夫家的双胞胎备受梅太太的 “欺压”,但他们现在摆脱了对她的经济依赖,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对她更加置若罔闻。尽管梅太太设想凭借统治农场的铁腕手段成为一个真正的权威人物,但她根本没有任何权威可言!与科普太太、麦金太尔太太一样,为了在男权社会中拥有权威,梅太太对手下的工人、晚辈发号施令、说脏话,但实际上她的这种做法极其错误。这正是奥康纳笔下被授权的女性最终的失败之处。虽然她们因为拥有土地和雇工而可以暂时行使自己的权力,但在她们竭力模仿传统男性角色时,她们牺牲了传统女性所拥有的极其珍贵的品质。当她们把传统女性的附庸角色转变为颐指气使的管理者时,她们也同样遭遇了失败:她们的雇工因为被轻视、斥责,逐渐心生怨恨,甚至对她们的命令置若罔闻。
与科普太太、麦金太尔太太一样,梅太太也发现,在关键时刻,她的工人抛弃了她:在公牛攻击她时,她要求格林利夫处死公牛,但格林利夫却置若罔闻。正如波森所指出的,格林利夫拒绝阻止公牛,以便报复这个曾经打压他而现在正在失去力量的女人。正如当时多数类似故事的结局,真正的男性力量最终会胜出。
在《格林利夫》中,通过主人公梅太太的命运,奥康纳表达了她在男权社会中所持有的女性观:女性如果放弃自己的角色,按照男性的生活方式追求与之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势必再次蹈入男权社会的窠臼,难以取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7]。
三、奥康纳矛盾的女性观
梅太太、科普太太以及麦金太尔太太仅是奥康纳小说中“雌雄同体”的家长型女性主人公中的3位。她们都极力维护她们眼中的南方社会等级制度,但正是这种对幻想的等级制度的维护导致了她们的覆灭。
这3位女性最终没能把传统上两种性别角色的一些必要特征结合起来,她们失去了从丈夫手里继承过来的对农场的控制权。实质上,她们3人最终都成为了背井离乡的人。尽管韦斯利坚持认为,奥康纳似乎想表明独立的女性权威是反常理的,因此必须被男性击碎,但事实是由于她们对于传统男权社会标准的绝对依赖,这些女性从未拥有过绝对的权威。尽管笔者并不赞同这些女性,但对于她们的命运,又怀有一定的同情。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不可能获得成功,奥康纳笔下的故事印证了这一观点,因为无论多么酷似男性的行为也无法弥补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她们为了生存必须控制的人的心目中,这些被授权的女性仍然低人一等。这反映出奥康纳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保持个性独立与自由缺乏足够的信心。
一方面,作为主要创作时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女性作家,当时如火如荼的女权主义运动激发了她的女性意识,她试图运用解构男性父权的书写策略,形成以女性当家作主的“无父”书写或对父亲形象阉割去势的叙述策略[8]。男性不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破坏者,不再是家庭的供养者和社会的中坚,而是寄生虫、“残疾的”亚当[9],因此,为了对抗、消解传统男性形象,奥康纳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众多“雌雄同体”的家长型寡母形象,以使传统男性形象边缘化,并进一步将其彻底解构。
但另一方面,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她已经“内化”了“父权制度”[10-11]下的文学和宗教传统,加之当时社会的男权意识才开始瓦解,残余势力依然强劲,她又给这些“雌雄同体”的强势女性安排了失败的结局。因此,对奥康纳作品的早期女权主义解读中,很多批评家相信:奥康纳接受了文学创作基于男性特权这一观点,认为她对自己意欲篡夺这一特权的做法感到极其纠结与忐忑。凯瑟琳·海普尔·普罗恩(Katherine Hemple Prown)认真比对了奥康纳的手稿和最终发表的定稿,对奥康纳手稿中的女性形象与她们对男性形象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普罗恩指出,奥康纳的手稿及其作品中女性的逐渐失声,揭示了“她所身处其中进行创作的传统要求她必须孝忠于男权主义价值观”[12]。作为一位南方女性作家,奥康纳为了得到认可,只能委屈求全、妥协让步,以这种变通的方式与男权社会进行抗争。莎拉·戈登(Sarah Gordon)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的角度解读奥康纳的小说。戈登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奥康纳的传记材料和她的散文与未发表的信件,证实了她作品中体现的自相矛盾的思想。
四、结 语
奥康纳既试图解构传统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又顾虑重重,这种纠结矛盾在她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奥康纳笔下此类自相矛盾的“雌雄同体”的女性形象充分反映出她矛盾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