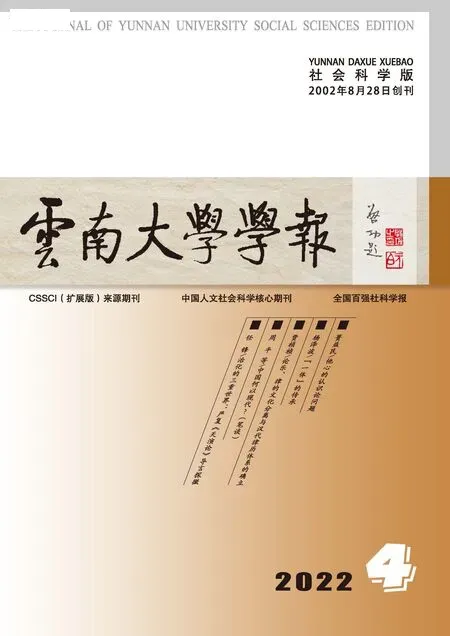中国何以现代?(笔谈)
周 平,徐 勇,肖 滨,罗祎楠,李怀印
中国何以现代的实践逻辑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430079]
“中国何以现代”的命题可以从多个维度探讨,实践逻辑是其中的重要一维。所谓实践逻辑,是事物的发展变化来自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在依据和走向。本文试图从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维度,探讨现代中国的价值与路径的形成及其特性。
一、现代中国价值的实践逻辑
对国家的认识,往往是在国家成型或者国家行动之后。这在于国家既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又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与自然形成的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更具有人为建构性,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规范,即现代性价值。而现代性价值的形成,一是问题导向,即人们在遭遇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现代性价值;二是目标导向,即人们为追求理想目的而形成的现代性价值。至于两种导向何轻何重,则取决于不同的现代化实践。
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变革进程发源于西方。西方人为追寻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理想社会,提出了诸多现代性价值观念,是典型的目标导向。中国是被动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对现代性价值的接受、吸收和运用,深受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支配,是典型的问题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 一般来讲,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导的。因此,在相当长时间,中国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主要是经济和技术层面,如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至于这一现代化会给政治国家自身带来什么变化,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
随着现代化实践的推进,国家的特性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其重要缘由是中国现代化实践中所遭遇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问题。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 随着城乡差距扩大,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严重。因此,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到21世纪初,废除农业税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农业税是长期历史以来形成的,由从事农业的农民向国家交纳税收,自古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废除农业税,意味着原有支配国家行为的“理”发生了改变。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改变,其依据何在?实践呼唤理论给予回答。由此,“现代国家”的概念与理论,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密切联结起来。
国家废除农业税改变了农民向国家交纳税收的“理”,这意味着国家的特性发生了变化。如何区分特性的变化,便有了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分。税收是国家的支柱。在恩格斯看来,“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171页。农业文明是人类第一个文明形态。由从事农业的人口交纳捐税成为国家得以成立和运转的基本条件。国家向农民收税也成为国家理所当然的行为。国家废除农业税,也就意味着支配国家行为的“理”发生了改变,国家的特性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发生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是国家的质的规定性的改变,体现着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分。国家废除农业税实际上是国家向现代转变的重要标识之一。正是因为这一标识性事件,现代国家这一命题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2)2006年,笔者在《“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建构》一文中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学议题变化,指出:“进入21世纪以后,对国家的论述逐步增多,大有‘回归国家’之势。”就笔者个人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从政治学进入农村领域,主要是研究农村基层,国家问题不是研究对象。只是到了21世纪初,围绕农业税的废除,国家问题,特别是现代国家问题才进入笔者的视野。参见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价值是认识和评价事物性质的一种标准和规范,具有引导性。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现代性要素不断生长出来,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结,形成了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引导下,国家行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废除农业税后,如何让广大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将农民纳入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正是现代国民国家的应有之义,彰显了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平等性。这些价值因素是历史上传统国家所没有的,体现了现代国家的质的规定性。
国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地域共同体的国家,一是作为政权的国家。前者是国家治理的对象,后者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作为与传统国家相对应的现代国家,也包括这两个方面。近代以来,中国便开启了现代国家政权建构的历程。特别是新中国的建立,国家政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震撼和深刻反思,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失误?邓小平认为,这与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相关。他在著名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指出,家长制、官僚主义等“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3)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之后,我国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开启了国家现代性的全面自觉。现代国家的命题愈来愈为学界所广泛关注。不仅仅是政治学,其他学科也参与进来。李怀印教授的新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便是历史学参与现代国家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作为与传统中国相对而言的现代中国,是一种具有不同于传统中国的质的规定性的国家,体现着现代性的价值。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接受了大量外来的现代性价值。但从废除农业税和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看,可以发现,中国对现代性价值的接受、学习、消化受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支配。正是因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所遭遇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碰撞的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强化人们对现代性价值的自觉意识。中国现代化实践不仅仅是对外来现代化性价值的学习和吸收,而且丰富了现代性价值,赋予了现代性价值的中国涵义。
二、现代中国路径的实践逻辑
现代性的价值将国家区分为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现代性的价值在不同国家的时空分布并不一样,其重要原因是不同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路径有所不同。决定现代国家的不同路径更在于其实践逻辑。
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性活动。这种探索和改造不是随意的,而是建立在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的。客观物质条件规定了人们实践活动的路径。现代国家建构意味着国家形态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和路径受制于历史提供的条件。
现代国家建构是伴随现代化进程发生的。一般来讲,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传统农业社会状况对于现代社会的形成和路径具有支配性作用。历史社会学大师摩尔在其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发现:“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4)[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页。正是传统社会状况及其面临的问题决定了现代化及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
英国和美国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形成了特有的现代国家形态。由于受传统社会影响较小,英美属于内生型现代化。英国在现代化来临之前,农村内部经历了商品化,圈地运动打破了传统农村经济结构,使其“没有严重的农民问题”。(5)[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29页。美国是在新大陆“空地”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国家,“并未遇到要瓦解封建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庞大而又牢固的农业社会这样一个问题”,“也从未有过像欧洲和亚洲社会那么庞大的农民阶级”。(6)[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88页。除英美国家等少数特例以外,世界上大多数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面临着庞大的农民阶级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悠久的国家,近代以来被迫开启现代化进程。现代化面临的最基本历史条件是农业社会及其庞大的农民阶级。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革命的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后建立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建立后,开始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建设,实行工业优先的战略,并因为从农业获得积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作为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未能与工业化同步改善其生活,城乡差距拉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废除农业税,对农民实行“多给少取”的政策,让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使农民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
中国农民逐步获得平等待遇的事实,反映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路径。这一路径首先由历史条件所决定。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不仅使得中国开启现代之门的民主革命具有农民革命的属性,而且深刻影响着革命之后的现代国家建构路径。新中国建立后,农民在政治上成为国家主人,但在相当长时间未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随着工业化的展开,非农产业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才有条件一举废除农业税,由以农支工转向以工支农,国家形态的现代属性得以强化。可见,现代国家的路径受制于历史提供的客观条件。这种历史条件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客观性。
实践是客观条件与人的认识和行动交互作用的产物。世界上绝大多数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会面临传统社会的影响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则有不同的路径,会形成不同的国家形态。摩尔依据大量事实揭示:“西方民主只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7)[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4页。德国和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法西斯道路,重要原因是破产的贫困农民问题。“小农们命途多舛,纳粹宣传却为小农展示了一幅理想农民的浪漫主义图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人’。农民在纳粹精心炮制的极右翼意识形态中成了关键角色。”(8)[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364页。
中国通过民主革命开启现代化大门。“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这里,农民再次作为主要动力推动了一个政党取得了胜利。”(9)[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181页。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取得了革命胜利,但同时也负有解放农民和让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的使命。摩尔曾断言:“农民早晚会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这是一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10)[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379页。但这一事实并非不可改变。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制改革,都是为了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正是依靠国家推动,才有可能实现农民全面脱贫。在中国,农民不是现代化的牺牲品而是分享者,显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行为密切相关。这种行为是传统国家不可能具有的,体现了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构成了中国的现代国家路径。这一路径具有双重超越的特点,一是超越将农民作为负担而不是动力的路径,二是超越农民成为现代化牺牲品而不是分享者的路径。这种双重超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国家的一般要求。但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自己的前提条件和目标,这就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需要。由此规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其特有路径,它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内在需要。
结 语
通过现代中国的价值性与路径性的实践逻辑维度,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何以现代”的命题。中国得以走向现代,是多种因素和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从价值看,中国从外国获得了现代理念,但这种理念的实现,取决于现代中国建构的实践。正是在现代中国建构的实践进程中,现代性价值愈加充分地展现出来,并因为中国的实践而丰富。中国不是西方现代价值的简单复制品,而以自己的实践作出特有的贡献。从路径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有自己的特有路径。这种路径来自于历史提供的条件和人的能动性。通过现代中国的路径,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有助于改变人们长期以来简单将传统作为现代中国的负资产的观念,获得历史自信。历史由此进入现代国家研究的视野。在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看来:“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11)[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9页。李怀印教授的新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及其由此发起的“中国何以现代”的讨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将实践逻辑引入现代中国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趋向,又可以深入把握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正是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践中,不断推动人们接受、确立和丰富现代性价值,促使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正是由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践,使得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形成了自己的特有路径,丰富了世界现代国家建构的形态。
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路径差异性与历史正当性
肖 滨
[中山大学,广州 528406]
《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纵向叙述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故事,在横向跨国比较中又进一步彰显出现代国家形成的中国路径。书中提出了颇为值得中国政治学界认真面对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中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如何理解、认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路径的差异性、独特性,一是如何把握、阐释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这两大问题紧密相关:由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国家形成之路有别于欧美所设定的路径,中国之为现代国家遭到不少质疑,这些质疑固然涉及“构成中国国家本身的一些最基本要素,包括它的疆域、族群构成和治理体系”,但“质疑的焦点不再是国家内部各项具体的制度,而在国家本身的历史正当性、统治能力及其生命力”。(1)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74-375页。以下凡引该书,只在文中标出页码,不再另加注释。探讨这些问题,回应如此质疑,是中国政治学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成长路径的差异性:殊途也有同归处?
现代国家形成的中国路径究竟是什么,这是该书提出和回答的核心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路径的差异性问题:如果说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路径不同于欧洲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那么,这种差异性究竟是什么?差异中是否也蕴含着某种共同性?
如果对照西方的理论范式,现代国家形成的中国道路确实不是“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理论范式所揭示的路径。诚如作者所论,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起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征服帝国”(第21页);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结果也难以满足通常所谓“民族国家”的定义,其历史经验也“‘偏离’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正常途径”(第10页):它既没有在帝国崩溃、分裂的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其领土格局总体保持完整,多元的族群被整合为一体,也没有实行西式的代议民主制,而是以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屹立于世。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尚在开启。
立足上述总体判断,该书从内外两个维度具体揭示了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路径。
外部比较。在作者看来,世界历史上中央集权的统一现代国家之形成主要有两条道路。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先行者,英法等欧洲国家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即在征服和扩张的基础上巩固其领土地盘,建立覆盖全国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构建以常备军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国家机器,消除各种中间势力,将君主对国家的间接统治转化为直接统治。这是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向地方延伸的道路,可称为“中央纵向渗透地方”之路。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后来者,中国走的是第二条道路:在群雄逐鹿的地方军事-财政集团激烈的“竞标赛”式竞争中,最为强大的一方打败所有竞争对手,最终平定天下,统一全国。这是由点(区域)及面(全国)的地方扩展道路,可称为“地方横向扩展全国”之路。
内部审视。一方面,外力影响下内生驱动为主。作者显然重视“观察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内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如何决定中国的国家转型在各阶段的走向和发展”(中文版前言,第4页),但更为强调“驱动这一演进历程的,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的不断变化的地缘格局和自身的各种财政、军事和政治资源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原动力,而不是像非西方世界的绝大数‘民族国家’那样,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外来影响的决定性支配。” (第388页)另一方面,累积演进激发突破。中国“以最接近于近代主权国家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为起点,依靠这个疆域国家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行政、财政和文化资源,缓慢、艰难但是稳步地朝着近代主权国家的方向演进”,并最终在20世纪中叶实现了主权完整、政治统一,在无数的累积、叠加中实现了近代疆域国家、主权国家和统一国家的三重突破(第262页)。
简而言之,该书所阐释的中国现代国家独特的形成路径可概括为:内生驱动为主、累积激发突破、自下而上推进、政党革命建国。具体说,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路径是,在清朝国家建设历史遗产(汉族人口的巨大规模与同质性、边疆建设以及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地方化)的基础上,以内部驱动为原动力,历经明末、清朝、民国再至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半世纪前后相继,在累积中逐步激发三层(疆域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国家)突破,在激烈的军事—财政竞争中,最终政党的优胜者通过由点(区域)到面(全国)、自下而上的扩展、推进,统一全国,以革命建立起一个主权完整、政治统一的现代国家,而政党革命建国之根由在于政党作为“克服源自19世纪后期的权力非集中化趋势和各种离心力量”的“利器”完成了20世纪中国国家转型的关键一步(第36页)。故此,在历史累积基础上的诸多突破中,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建国不仅集变革突破之大成,也是中国现代国家独特成长路径中最为关键之点。
如果把中国与英法等欧洲国家相比较,除了特殊性、差异性之外,二者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共同性,或者说殊途其实也有同归之处?其实,该书的分析架构(地缘政治、财政—军事结构和政治认同)已经蕴含着这种共同性——相同的政治—军事—财政逻辑。
地缘政治。该书将地缘政治视为理解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一元素:“事关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国力和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第14页)就现代国家建设而言,国际政治以及地缘政治所引发的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军事竞争或战争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
军事-财政结构。随着16、17世纪欧洲军事革命或军事现代化的推进,为了应对国家之间最为残酷的竞争——战争,组织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提升作战能力,是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一要务。然而,“没有军饷,就没有军队;没有税收,就没有军饷”,(2)[英]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页。因此国家必须将现代军队、财税体系、官僚机构有机组装起来,才能为确立现代国家的领土权和主权提供最为强大的硬实力。这清楚地表明,军事-财政国家(3)作者将“fiscal-military states”译为“财政-军事国家”。王绍光教授认为,“‘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作‘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且财政创新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参见王绍光:《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14页。依王绍光之说,本文将其称为“军事-财政国家”。的兴起是国家间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甚至战争威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政治认同。“如何有效利用军事和财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政治集团成员内部的认同及组织凝聚力。”(第19页)连接军事—财政与政治认同的逻辑环节是现代国家的直接统治:现代国家只有依靠官僚系统直接统治民众,才能充分地汲取财政税收以支撑国家的军事系统和行政体制的运作,而两种强烈的政治认同——国族认同和公民认同将大大降低国家机器抽取财税资源和服从国家直接统治的成本,因而国族建设和国民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
从这一角度看,在现代国家建设的早期阶段,中国和欧洲的先驱者(如英法等国)虽然道路各异、路径不同,但都遵循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国家之间因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引发的激烈竞争甚或战争威胁乃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驱动力,以此为逻辑出发点,现代国家建设展开的基本进程是,从构造军事-财政国家到强化国族和公民的政治认同,以实力维护国家主权、捍卫国家利益、增进国民福祉是国家建设的逻辑归属。
二、历史走向的正当性: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存续与新生
由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之路有别于西方理论范式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形成路径,由此也引发了关于中国现代国家本身的历史正当性质疑。作为历史学家,本书作者以30万言叙述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曲折故事,正是对此质疑的正面回击。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其精彩的历史叙述进一步扩展为政治学的理论解释。事实上,作者并未囿于通常的历史叙述,而是展现出鲜明的历史政治学色彩。
从政治学角度看,作者不仅准确地使用政治学的国家概念,从领土、人口、政府与主权四个基本元素入手来把握现代国家的形成,而且聚焦中国政治学的三大国家建构问题——中国多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前如何成形并得以维系?中国在19世纪被卷入主权国家体系之后,如何维持既有的疆域并最终在国际上获得对其主权的承认?20世纪以来的不同国家体制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何种路径而形成?(中文版前言,第1-2页)该书所构建的地缘政治、财政-军事结构和政治认同三元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展现出鲜明的政治学理论品质。
就历史学而言,作者力图走出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和“碎片化”研究的泥潭,“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究对今日中国的历史认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中文版前言,第3页)。在方法上,采用“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以三元一体理论框架为综合视角;在研究领域上,跨越专门史和通史研究的学科边界;空间视野上,注重国内与国际因素的交互作用;时间维度上,“打破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所习惯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藩篱,把近三个世纪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作为一个既有不同环节又前后贯通的完整过程”(中文版前言,第4页)。
正是站在历史政治学的高度,本书精彩地叙述了从1600年到1949年三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国家成长历程中“一波三折、三环相扣、四层叠加”的故事。
“一波三折”。所谓“一波”是指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第一波,即建立“主权完整、政治统一、高度集权”的现代国家。“三折”意味着这一波现代国家成长过程的曲折与复杂。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为例,中国三个半世纪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清晰地呈现出“三折”演变的曲折轨迹:清朝的地方化集中主义虽然有得也有失,但没有逃脱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国家分裂局面;历经民国初期的集中化地方主义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半集中主义,最终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主权完整、政治统一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目标。
“三环相扣”。第一环:“再造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这一环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关系到国家之“版图”——领土与人口,(4)“版图”乃国家之领土与人口:“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参见温春来:《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页。这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盘”;另一方面在于其涉及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比其他因素更能决定中国的疆域和治理方式”。第二环:“将疆域国家重构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这里的焦点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战略目标与政策优先项”。第三环:重整天下归于一,“重建一个高度集权的、统一的现代国家”。这里的焦点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权力架构及其应对国内外挑战的能力”,是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关键环节。上述“三环”环环相扣,紧密连接,一起完成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第一波(第11-13页)。
“四层叠加”。如果说,“一波三折、三环相扣”展现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曲折性、复杂性、连续性,那么,“四层叠加”则呈现出这一过程所形成结果的层次性、结构性、整体性。往外部看,在国际上,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下与所有其他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屹立于世界主权国家之林;就内部言,表层以党政体制为统治-治理结构,中层是一体多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底层则是延绵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是国族认同深厚的文化资源。这表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不只是国家机器的现代再造,也是中华民族的新生和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文明的开始。
从政治学理论而言,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至少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随着19世纪中国卷入主权国家体系,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中华民族“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欧、美、日控制的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来”。(5)[美]斯蒂芬·哈尔西:《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1850—1949》,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83页。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第一目标就是以枪炮、财富和官僚体系的重新组合再造一个现代国家机器,以确立中国的国家主权,确保中华民族生存下来。在偌大的地球上,让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生存下来,维护其生存权,其正当性谁能质疑?历史证明,正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结束了半殖民统治的束缚”,不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权,而且为20世纪晚期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扮演应有的大国角色、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重塑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格局。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不只是国家机器的再造,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新生:56个民族组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呈现为一体多元的格局,这也是“四层叠加”结构中极为重要的一层——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可以从“演化论”和“建构论”两种理论视角论述其历史正当性,即“将其视为历史的延续演化和主观能动建构彼此互动的产物”。(6)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83页。从演化论来看,56个民族最终在20世纪整合、凝聚为一体,统一于中华民族,这既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不断融合、一体化范围逐渐扩大的产物,也是顺应这一长期历史演化大趋势的结果。就建构论而言,从清朝开启多民族国家建设之序幕(新疆建省可视为标志性的举措)、经民国走出“排满”之藩篱而高举“五族共和”之大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之制度,(7)参见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16、252、290页。曲折、漫长的历史探索所蕴含的正当性在于努力寻求国族统一性与族群多元性的共存结构、双赢格局。重塑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不仅有充分的历史正当性,而且打破了所谓“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迷思,为人类提供了国族统一框架下多元族群和谐共存的中国智慧。
——延续中华文明并使之现代转型。“在文化的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8)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页。更准确地说,中国之为一个国家,文明共同体是其根基所在。在“四层叠加”结构中,最底层的正是延绵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正当性具有双重价值与意义。一方面,就中国自身而言,“留住我们的根”,即延续中华文明。“中国人眼里的‘中国’实则是‘中华文明’的同义词,包括诸如中国的历史、朝代、儒家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简言之,中国之万物孕育于中华之文明。”(9)[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于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国家机器或统治当局不过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而已。因此,中华文明的延续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组成部分。面对西方列强的各种欺凌、打压,经过长达数世纪的抗争,古老的中华文明幸存下来,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彰显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另一方面,从世界来看,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文明获得新生,开始其现代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面向世界文明,与其他文明碰撞、互动、交融,接纳包括主权与人权、法治与民主、自由与平等、科技与创新等现代文明的基本元素,而且以崭新的姿态嵌入世界文明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由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道路的差异性,其所遭受的质疑当然不只是国家本身的历史正当性,而且还涉及其生命力:未来中国是否能继续维持其规模之“大”和结构之“强”的格局?“进而言之,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至今有没有结束?”(第10页)这种质疑指向中国现代国家未来发展的持久性。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这种质疑冷静地视为一种警示: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虽然,无论现代国家机器的构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塑,还是以公民权利扩展为核心内容的国民建设,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成效显著,取得了长足的巨大进步,但如何在未来展现出持续的生命力,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结尾,孔飞力先生曾意味深长地写道:“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10)[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第122页。也许,在“中国自己的条件”中,最根本的条件就是以一系列结构性的制度创新,“把个人整合进国家”,寻求国家力量、个体发展和社会活力的有机统一。
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国家现代性问题
罗祎楠
[北京大学,北京 100080]
如何理解中国国家自身历史发展道路的现代性?这是历史学与政治学共同关心的问题。进入21世纪,伴随着对于“中国道路”等命题的热烈讨论,学者们聚焦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以此说明西方“现代性”政治模式在解释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局限,并证明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同样可以孕育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基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尝试从“认识论(epistemology)”的维度探讨中国国家现代性问题。本文并不只是要回答诸如现代性是什么,中国的现代性是什么,中国是不是现代国家,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国家等问题。中国国家现代性并不仅仅是关于历史事实是什么的问题,更是关于历史经验“如何”成为历史事实的问题。因此,本文聚焦于研究者“如何”呈现中国历史道路的现代性,并尝试将这一过程纳入学理分析——这便是本文提出的从“认识论视野”探讨中国国家现代性问题的含义。具体来说,本文将首先简要分析以往学术界对现代性研究中的历史“目的论”的批评,以及伴随此种批评而兴起的“历史经验主义”的研究特点及其塑造的学术生态。接下来探讨“历史解释”意识的兴起如何促使历史学与政治学者反思其研究得以成立的认识论基础。沿着认识论的思考路径,本文提出现代性研究中的“认识模式”问题,并将结合具体著作,分析认识模式的差异如何使现代国家发展道路以不同的面貌得以呈现。
一、超越“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经验主义”的局限
历史目的论(teleology)将西欧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机制(如民主化、理性官僚制、公共领域的形成)作为人类走向现代国家的普适性发展道路。持“目的论”的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缺少(或具有)机制中的哪些特点,因而中国无法(或可以)发展成现代国家。比如,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提出,中国在唐宋时期最大的变革在于君主专制体制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朝廷与地方社会的疏离。内藤湖南认为,此种特征延续到20世纪初的中国,因此中国无法自发走向现代国家。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判断来自于他心目中对现代国家如何生成的固定认识。他相信,现代政治必然产生于国民推翻君主专制政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并以此普适标尺衡量唐宋间的历史变革,发现了君主专制的出现和强化。当然,历史目的论并非等于历史停滞论。比如,另外一些学者强调传统中国已经具备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某些特点,在清代甚至更早就已经发展出类似欧洲近代早期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1)William T.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两种理解虽然对中国古代历史中有没有“现代性”各执一词,但都是以“目的论”的方式看待历史的。
时至21世纪,中外学界对历史目的论的批评日益激烈。与此种批评相伴的,是历史经验主义的兴起。“历史经验主义”学者批评“目的论”阻碍了对中国真实历史经验的探究。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经验的复杂性是任何西方理论框架没法概括的。历史经验主义者将“理论”与“历史经验”视为截然二分的领域。历史经验的发现依赖于中国史学古已有之的基本方法,如考证学、史料文献学等。经验主义者相信他们可以探寻历史经验层面的客观真实。而作为主观观点的理论要想成立,必须被这些客观经验所支撑。他们发现,所谓“理论”都很难得到经验百分之百的证明,因为中国历史的丰富性使得研究者可以找到各种经验材料去反驳某种理论。在“实证”思路下,理论难以找到容身之所。当然,所谓“理论”在历史经验主义看来,就是对历史某些整体特征的概括性描述:如“传统中国发展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国自南宋开始精英着力于地方活动以获得资源”,(2)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10页。“中国具有和欧洲近代早期类似的公共领域”等。 由于历史学者可以通过丰富的资料证明“理论”存在的错误,他们对“理论”也就难以建立起信任的态度。这样的怀疑进而促生一系列研究伦理:研究者只承认对具体历史经验研究的合理性,并有意无意地排斥对诸如“现代性”等理论命题的研究。更有甚者,通过划分出所谓“本土/外国”“经验/理论”的界限,学者得以在自我想象的中国历史“真实客观”经验中遨游。不可否认,历史经验主义切实推进了对某些局部历史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具体政治经济制度内容的考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历的还原等。但是,在历史经验主义看来,任何关于现代性特征的理论判断都无法概括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讨论现代性如同“玩理论”,必然会被历史经验研究推翻。
对于政治学来说,历史经验主义引导学者将“历史”视为构建理论的证据库。学者或者将历史资料转化为测量变量的数据库,或者是挑选历史资料证明某些理论概念。一种学术知识生产的“分层”想象由此产生。在此种分层结构中,历史学家被认为是只负责历史经验事实的考证、审核,而政治学者则负责将这些事实“上升”成为理论概念。居于“高端”的政治学者也切身感受到某种无奈,特别是当历史学家挑战他们的研究缺乏经验证据支持,或者是由于“不懂历史”运用了错误的经验证据时,(3)体现此种张力的第一个例子是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1980年对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一书的尖锐批评,参见裴宜理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杂志1980年39卷第三期的书评,第533-535。 另一个例子是Kenneth Swope对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 的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一书的批评。该文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杂志 2007年第66卷第二期,第536-538页。两个批评都认为政治学理论缺乏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正确认识。这样的分层、挑战和无奈实际源自于“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经验事实”的划界与隔膜。这种学术职业生态(ecology)成为现今历史学与政治学互动的重要样态。(4)对职业生态的讨论,参见Andrew Abbott, “Linked Ecologies: States and Universities as Environments for Professions”, Sociological Theory,Vol.23,No.1,2005, pp.245-274.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学术生态正在出现。在历史学中,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历史解释”的可能性。他们或是从阐释学角度反思历史经验组织背后的理论前见与历史解释的关系,(5)代表性的讨论参见李红岩:《从阐释学到历史阐释学:何为历史的“正用”》,《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1期;晁天义:《阐释学对历史研究的启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或是思考如何将历史事件、人物互动关系等因素纳入历史解释之中。(6)代表性的讨论,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同样,在政治学中,持“历史转向”主张的学者开始关注历史文化系统在建构政治行为过程中的底色性作用。(7)杨光斌:《历史政治学的知识主体性及其社会科学意涵》,《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期。政治学与历史学在“历史解释”问题上产生思想交汇,新的学术生态开始孕育。
历史解释工作使历史经验主义在学理上面临实质性困境。历史解释需要学者不仅仅搞清“是什么”。在构建历史解释时,他们需要把各种“是什么”的片段历史经验资料组织起来,形成对现象(如事件、制度)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的解释。这一工作的核心是建立历史经验现象之间的关联。因此,学者必然需要回答:为什么我们以“如此方式”将历史材料组织起来是合理的?为什么如此组织资料可以使历史叙事具有因果性?他们进而需要回答:历史过程中何种实质性的特征可以成为解释历史结果的原因?研究者可以通过什么样的理论视角展现这些实质性特征?要想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者便不能再滞留于自我想象的“历史客观真实”之中,而是需要将“真实”本身纳入反思与学理分析,需要自觉探究“历史解释何以可能”这一认识论问题。具体来说,学者无法再执着于“客观历史经验能否印证理论”的争论,他们需要讨论历史经验“何以能够”生成历史解释。这必然意味着,学者需要承认任何所谓的“客观”经验都难以将其自身假定为真实,因为研究者构建“客观化了的经验”(特别是历史解释)的学理过程本身才是历史的真实。(8)对“客观化”的讨论,参见许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理解的社会学引论》,霍桂恒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要想揭示此种历史真实,学者需要看到理论视野对经验构建过程的引导作用。本文提出的“认识模式”便属对理论视野的分析路径,它使“理论视野”成为可以被明晰分析的范畴。此种分析并非研究者的放飞自我,而是严格运用国际社会科学理论语言说明历史解释中“认识模式”的特点。这本身就是与国际学术共同体建立连接的过程。对认识模式的分析,打破了历史经验主义所构建的关于“客观历史经验”与“主观历史理论”的分界,以及由此分界促生的学术生态。在“认识论”视野中,历史学与政治学找到了新的交汇空间。他们不再以等级分工相互看待,而是在对认识模式的反思与创新中相互启迪、“共同成长”。(9)对“共同成长”意涵的讨论,参见许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理解的社会学引论》,第99页。学者们也将不再拘泥于“本土”和“国外”的分野,而是共同探寻可以将自身研究过程纳入明晰分析与讨论的国际理论资源。
在认识论视野中,研究将不再聚焦于如何找到片段性的历史经验证明或证伪现代国家的抽象特征(如代议民主、公民政治等),而是转为关注不同研究以何种“认识模式(epistemic modes)” 解释中国国家现代性的问题。“认识模式”指的研究者以理论组织历史事实以使之具有整体意义的方式。(10)Reed, Isaac Ariail Reed,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Knowledge: On the Use of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p.7.本文讨论的认识模式包括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研究者基于对社会行动的何种存在论(ontological)认识来构建具有解释性的历史叙述?历史离不开作为行动者的人,历史叙事总是围绕人们如何行动而展开。这里的行动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群体等。无论是将历史人物视为采取“策略手段”以满足“目的动机”的行动者,或是将人们对世界意义的不断理解视为解释行动的基础,研究者都是在依照他们对社会行动的基本认识叙述历史。他们可以将历史讲述成如“宫斗剧”一般的策略性竞争,也可以展现历史人物如何在对世界意义的图景中看到彼此的角色和位置。(11)对这两种叙述方式的详细比较,可参见Hans Joas,The Creativity of Action,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6,pp.146-195.同样的历史资料,由于研究者不同的存在论视角,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意涵。
第二,研究者如何展现历史因果过程的历史质性?所谓历史质性是历史蕴含在历史过程之中,促成各种历史现象生成的历史实在(real)。历史质性并非可以直接测量和感知,而是学者以自身的理论视角表现出的历史实在性特质。 历史质性是历史过程的理论“意义(meaning)”:研究者运用理论说明历史过程“意味着什么”。 要想完成这一工作,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比较、理论构建等方法,来合理地说明为什么某种理论可以概括历史因果过程的实质性特征。所谓实质性特征并非是可以推广的规律。对历史质性的展现也并不是要说明此种质性可以在大量的样本范围内得到验证。历史质性的研究是要展现历史案例所具有的理论特质,即说明此案例如何在某一理论系统中具有最强的典型性——或者说最能体现此种理论的内涵。这一过程同样是在展现案例的“一般性”意义,但此种“一般性”并不在于已知案例得到的理论认识可以推广到对其他案例的解释中。所谓一般性指的是,研究者运用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理论知识来表现案例的意义,从而使案例成为可以被共同体理解、反思和讨论的对象。(12)此种对一般性、典型性的认识,来自于“溯因推理(abductive)”的认识论逻辑。对此逻辑的介绍,参见Tavory, Iddo and Timmermans Stefan,Abductive Analysis: Theoriz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p.5,pp.41-44.此外,无论研究者是否同意对历史质性的某种展现,他们都相信对历史质性的理解是多元的、包容的。每一束理论都照亮了历史的一部分,也便遮蔽了另外的部分。作为历史真实的“质性”并非只是被照亮的那部分,而是研究者不断照亮历史的“过程”本身。
第三,研究者如何展现历史质性所具有的生成历史现象的因果力量(causal power)?(13)“因果力量”来自于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具体内容参见Dave Elder-Vass, The Causal Power of Social Structures: Emergence, Structure and Agen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4-5.此种“力量(或者称权力)”并非指的是一个实体(entity)依靠自身物质资源、合法性等优势使另一个实体服从意志的过程。历史质性所具有的权力在于其促生历史结果的力量。此种权力过程是依赖研究者的学理分析才能展现出来的因果过程。研究者需要分析一系列看似分散的历史现象是如何被共同的历史实在之质促生的。要想进行此种分析,研究者需要说明历史质性如何通过历史行动者显现其作用。历史质性能够解释越多的具体现象,其因果力量也就越强。(14)赵鼎新依照演绎(deductive)的认识逻辑提出,如果历史学家预先建立的机制能够解释越多的具体历史问题,那么这样的理论也就越成功。本文提出的历史质性当然可以包括对历史机制的认识,本文也认为历史质性需要对大量具体的历史现象进行解释。但历史质性是“认识模式”的组成部分,属认识论的范畴。因此,我们将质性机制“如何”解释现象纳入分析。这并非演绎(deductive)的认识逻辑。参见Zhao Dingxin,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4-27.
下面我们通过对两部著作所蕴含的认识模式的分析,说明这些模式如何塑造了学者对中国国家现代性的不同理解。
二、历史质性:中国国家现代性的展现方式
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将“历史目的论”作为对话对象。(15)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作者强调不能简单地用所谓“帝国”转向“民族国家”这一西方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来衡量中国历史,进而否认中国可以发展出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体制。作者提出解释现代国家能否产生的三个历史“质性”机制:一是地缘政治,即面对外来国际挑战,国家统治者能否制定相应的目标以应对;二是财政动员机制,即国家如何将社会经济资源通过财政税收抽取出来,使之调动成为达成国家目标的物质资源;三是政治认同机制,就是在分配社会经济资源时不同社会、政治集团内部成员或集团之间的认同和凝聚力,这种认同越强,财政和军事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就越高。(16)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第18-19页。
这一框架的提出,源于作者在政治学理论与历史研究两个领域的学养累积。作者对于国家建构三大机制的认识受到了英语世界国家建构(state-making)理论流派的影响。比如,对于地缘政治讨论受到了奥托·海因兹(Otto Hintze)、韦伯等“战争推动国家建构”理论的影响,该理论强调欧洲近代早期地缘战争推动统治者创新制度以应对战争挑战,现代国家的兴起是应对战争的结果。(17)对战争国家论的介绍,参见 Theda Skocpol, “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对于国家财政动员机制的讨论,受到了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欧洲财政国家(fiscal states)等研究的影响,这些研究关注国家如何建立政治体制以汲取财政收资源,特别是不同国家的经济条件如何促使统治者或是依赖民主体制或是依靠强制制度来获得汲取财政收入。(18)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Press, 1993.对社会内聚性与认同对国家能力的影响的讨论,受到了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学者关于社会凝聚性与国家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关系研究的影响。(19)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A theory of state”,pp.59-60.这些理论视角引导了作者整合碎片的历史经验,在经验与理论视角不断的相互启发中,将理论视角转化为“分析”历史意义的框架。(20)框架是行动者建立起对当下情境理解的媒介。它来自于行动者经历过的某种意义图景模式,行动者将此模式应用于对当下的理解中,使当下具有了意义。对框架的经典讨论,参见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6.作者详细叙述和分析了中国国家发展中的三个关键过程: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社会、内政和地缘政治危机对清朝已有的统治方式的挑战,以及清廷为应对挑战而开展的自强运动和清末新政,以及于此连带的整个社会精英的自我转变历程;(21)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第26-30页。军阀混战中“集权地方主义”的出现与国民党最终的胜利;(22)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第31-33页。国共斗争与共产党的最终胜利。(23)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第34页。作者通过将这些具体历史过程与国家建构理论参照比对,寻找合适的理论来表现历史的实在性特征。
历史质性如何促生了中国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历史现象?作者主要通过两个环节将质性机制与具体历史现象连接起来。首先,作者强调上述机制不仅仅是历史的外部形式,而且也是具体历史人物真实的行动动机。在叙述中,统治者是在自觉应对挑战,追求增加财政能力,并建立政治认同、塑造社会国家的凝聚力。三大历史质性机制被处理为历史人物在微观历史中展开行动的内在动机,由此解释了各种国家制度为什么可以发生——它们是行动者达成动机的手段。其次,作者还以上述机制来衡量历史结果:该书的历史叙事关注历史人物是不是达成了上述目的,以及他们在应对挑战、财政动员与建立社会认同方面的努力是不是具有相较于其他行动者的优势。同样,作者相信历史行动者自己也会做出类似衡量,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后续的应对行动。由此,作者依照三大机制建立起基本的历史叙事模式:为了达成上述三大目标,国家建设者既利用清代帝国原有的历史遗产,又采取一系列策略来建设新的制度,这些策略的目的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方式并没有达成原有设定的目标,这样的不足会推动历史人物继续开展行动;走向现代国家也是一场竞争,现代化目标完成不好的行动者会被淘汰;胜利者的成果由此被作为新的历史路径依赖而得到巩固,优胜劣汰使有效的国家建设成果不断累积;在一波又一波的竞争中,国家得以建立起应对地缘政治有效的财政制度与国家社会凝聚力,国家现代性在历史中产生出来。按照这样的叙事模式,作者讲述了18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在内忧外患中孕育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18世纪末开始,到了19世纪末达到极致的内外危机如何破坏了清朝财政结构中长期保持的低度均衡,地缘政治危机推动清朝统治者改革地方体制以增加财政汲取资源能力。改革影响了地方对中央的认同结构,地方精英开始要求中央给地方让权,这使“地方化的集权主义”这一新的国家制度出现,为新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走向现代主权国家开启了条件。在发展地方集权的过程中,国民党成为具有资源动员和社会认同优势的地方性力量,战胜其他军阀统一中国;但新兴的共产党有力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凝聚与财政动员能力,并在新的高度实现了突破,最终战胜了国民党。共产党的成就也塑造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态。作者把一系列具体的事件融于历史叙事,从而展现出历史机制“如何”使一系列看似无关的现象出现。正是在这样的从历史实在到现象的不断运动中,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国家从历史中涌现出来。
通过与其他著作的比较,可以看到不同的认识模式是如何引导研究者得到对中国国家现代性的不同理解。赵鼎新在《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中以不同的认识模式建立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作者首先界定了人类历史的结构性机制,将人类彼此竞争、追求战胜并支配他人视为一切社会的基本结构。作者建立起四种竞争性行动模式,将其视为分析历史现象的理想型。这四类模式共同表现了行动者(包括群体、组织乃至某种文明)如何“理解他们生活的意义,以及如何向自己和他人证明行动和目的的合理”。这四类模式包括人们追求提高他们榨取,转化,分配和消费自然资源的能力;人们的侵略性和防御被他人侵略的诉求;人们需要建立集中强制的规则来保证支配与相互合作的顺利开展;人们需要将自己的生活和行动合理化乃至使之变得荣耀。这四类行动模式使行动者可以在竞争中累积四类权力资源: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当行动者更擅长某些行动模式时,他便可以在相应的领域累积更多的权力资源。同样,当某些行动模式被一种文明中的人们所普遍采纳时,此文明也就在相应领域具有更强的权力资源,更适合应对相应的历史挑战。(24)Zhao Dingxin,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 History, p.32.作者通过这一理论框架分析中国自西周到现代的长时段历史进程,将中国传统国家发展的历史表现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这两种行动模式被普遍接受的过程。在这两种模式主导下,中国自西汉开始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儒法国家”形态。此种形态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资源的累积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样态。
作者进而强调,作为中国历史质性的儒法国家形态,可以回答一系列具体的历史经验性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国自西汉确定的政治文化制度模式可以历经不同时代的变迁,灵活应对挑战,保持相对稳定?为什么清代和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可以建立更持久的帝国?为什么中国的民间宗教可以在宋代之后更大发展?为什么明代后期的一些非正统儒学思想没有能够削弱理学的支配作用?(25)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第6-13页。作者通过对历史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与行动,展现四种行动模式及其促生的权力资源结构如何左右了具体的历史发展轨迹。
正是基于对历史质性结构的认识,作者提出传统中国与现代国家的根本区别。作者强调,现代性政治运行的社会基础在于人们普遍将“私人导向的工具理性转化为社会行动的正面价值,并服从这种理性的支配”。与之相对,儒法国家与现代性政治从基本运行逻辑和资源累积特性上根本不同。由此,该书超越具体历史现象的比较,说明现象之下中西历史的实质性差异。这显示了该书认识模式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正如作者所揭示的,在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为普遍追求的社会,即使出现某些类似现代政治的现象,但当研究者将这些现象和其他现象连接起来,或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再次观察这些现象时,他们会发现:那些看似说明中国具有现代性的片段性现象却依然是被儒法国家这一历史实在所左右的。作者因此批评加州学派依照“控制性比较”的认识模式建立起的现代性研究。后者过于强调偶发事件对于生成现代性的作用。在该书的叙事与分析中,现代性代表了特定文明形态中人们通过稳定的行动模式而长期累积的权力资源分布特性。
赵鼎新与李怀印的著作在认识模式上存在差异。首先,在存在论层面上对社会行动的理解不同。李怀印强调国家建设者具有追求国家现代性的动机,并可以不断调整自身行动而完成诉求。这是目的—手段的存在论模式。赵鼎新则并不认为不同文明的行动者具有追求现代性的共同动机。他关注不同文明中的行动者如何理解和展示其行动意义、证明行动和目的合理性。这是以“意义理解”为中心的存在论模式。对社会行动模式的不同理解也使两部著作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质性。赵鼎新的著作聚焦于行动者如何通过不同行动模式累积权力资源,以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四种类型展现历史结构,从而提出“儒法国家”这一被政治和意识形态行动逻辑主导的中国历史质性。李怀印则依照“从目标追求到结果”的方式划分出三种历史质性机制,以此作为中国历史的质性特征。其次,二者的差异还表现在如何展现历史质性和现象的关系。李怀印将历史人物的“动机—手段—结果”作为展现质性机制如何生成现象的基本叙事模式。赵鼎新则关注具体历史动态情境如何强化了儒法国家的基本结构。正是认识模式的差异,使二人对中国能否自我发展出现代国家持不同的看法。
结 语
本文从认识论视野反思了中国国家现代性的研究,分析了研究者不同的认识模式如何引导他们呈现出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对历史解释的追求,促使历史学和政治学者重新反思如何将资料组织起来以建立解释。这为学界超越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分层、隔膜提供了可能。本文提出“认识模式”以说明建立历史解释的可能方式。认识模式将学者构建历史叙事与历史质性的过程本身纳入到明确的分析之中。在认识论视野中,研究者可以克服“客观经验—主观理论”二分带来的研究模糊性与任意性。他们可以重新构建新的学术生态,在相互交流中共同成长。他们可以在不断的认识论分析与反思中,扩展国家现代性研究的界限。这便是认识论视野给国家现代性研究带来的学理意义。
革命·现代化·国家形成
李怀印
[得克萨斯州大学,美国]
一、不断演进的问题意识
现代中国到底从何而来?20世纪以来的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现代国家?今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相信所有关心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命运的人,都会有类似的发问。近百年来,有关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书写层出不穷,人们对近世以来中国历史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一个半世纪之前,面对刚刚到来的西方列强的冲击,李鸿章曾经感叹中国所遭遇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经历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实际上,他仅仅意识到,中国所面对的不再是来自北方草原的铁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边患”,而是前所未有的对手,是利用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武装起来的全新敌人,“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1)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24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25页。不过,在李鸿章看来,西方的优长也仅此而已。终其一生,李鸿章并没有看到坚船利炮背后更深刻的东西,以为只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洋枪洋舰购到手里,中国便可高枕无忧。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论规模和先进程度,一时在远东地区无有出其右者。李鸿章对北洋水师捍卫海疆的能力也信心满满。梁启超谓当时的情况,“虚骄之气日甚一日,朝野上下莫不皆然”,(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5页。可说是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清朝统治者心态的真实写照。
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到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过渡时代。他在1901年撰文指出,“欧洲各国自两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且各国的经历不同,有“顺流而渡”者如英吉利,有“乱流而渡”者如法兰西,有“方舟联队而渡”者如德意志,等等。梁氏这里所说的过渡时代,实即近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state)的建造过程。在18—19世纪的欧洲,确有不少国家完成了这一过渡,其情形一如梁氏所云,“或渡一次而达焉,或渡两三次而始达”;而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更多的国家却在艰难挣扎,“或渡一关而止焉,或渡两三关而犹未止焉”。至于彼时的中国,梁氏谓之“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292-294页。可以说,梁启超是用比较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第一人。
梁启超之后,有关近现代中国的各种历史叙事不断推陈出新,但总的来说,不外乎前辈史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开创的两种模式,也就是张闻天、范文澜等人所推出的革命叙事,以及蒋廷黻、陈恭禄等人所构建的现代化叙事。此后七八十年里,就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而言,人们只是在这两种叙事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增补而已。这两种叙事各有千秋。革命叙事的重点在于说明,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这场历史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告终,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必然选择。现代化叙事则着眼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认为现代化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化,但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发展市场经济,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大势所趋。总的来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因应不同的时代要求,这两种叙事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现代化叙事主导了民国时期的主流史学界,被广泛用于大学历史教材,而革命叙事主要用于共产党根据地的革命历史教育,在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1949年以后,革命叙事取代现代化叙事,在近现代史的书写和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现代化叙事在沉寂了三十多年后,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呼应了当时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总趋势。(4)详见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现代化还是革命叙事,都已经在学术界失去了往日的魅力,绝大多数近现代史研究者投入到对历史细节的挖掘、考证之中。近一二十年来,探索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问题以及诸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义和团、北洋军阀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著述少之又少。这些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构成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现在却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也有类似的转变。冷战时期,人们关注的同样是晚清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共产党革命,曾经是最受关注的课题。研究范式也在革命与现代化两者之间徘徊。那些同情社会主义中国的学者,倾向于从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长期趋势入手,解释共产党革命的兴起及成功的原因。更多的研究者则把近现代中国放在西方挑战与中国回应的视角下,突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冷战结束以后,人们对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宏大历史议题的关心也逐渐消退,让位于新的学术兴趣,研究重心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过去不曾注意或者被边缘化的题材上面,尤其是那些与日常社会文化生活相关的话题,是为所谓的“新文化史”“新社会史”转向。
最近一二十年又有了新的变化。除了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继续流行之外,有些人开始从跨国史或全球性的视角,重新思考一些比较宏大的议题。产生这一转变的背景,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新兴大国角色相关。背后的问题意识,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争,而是如何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的世界性大国地位是否只是一时现象,还是会持续下去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又产生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有其历史根源,当下中国经济上的成功事实上只是过去数千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领先于世界的再版而已。可以说,重新认识近代以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近代以来为何落后于西方的潜意识和研究志趣,便是所谓“加州学派”产生的背景。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正是他们所期待的:原来中国在1800年以前在各个方面并不落后于西方,在人均消费水平、人均寿命等最重要的指标上,已经与西方齐头并进;在国家建造方面,18世纪的清帝国也可与西方崛起中的财政军事国家等量齐观。用濮培德(Peter Perdue)的话说,清代国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稳定的、统一的‘东方帝国’,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国家结构,从事战争动员和领土扩张”,因此清帝国“并没有与欧洲分道扬镳”。(5)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27.
另一种倾向则折射了西方部分学者对崛起中的中国的焦虑和质疑。他们要追问的是,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否可以持续,中国的现行制度和疆域格局能否延续下去。出于这种质疑,一些人试图把清朝的历史与当下的中国加以连接,重新解读清朝国家的性质,认为清朝既不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王朝, 而是一个“内亚帝国”,这个内亚帝国由满人、蒙古人、中亚穆斯林、藏人、汉人所组成,由汉人所组成的内地各省只是帝国的诸多板块中的一个而已;满人也不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已经汉化,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了满人的主权特性,并且一直在极力维持其“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这便是近年来大行其道的“新清史”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的背后一个没有言明的臆想,就是当下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为所有其他帝国在衰落过程中都已经四分五裂,从中产生诸多民族国家,中国何以独此一家,延续了昔日清帝国的疆域,保留了清帝国的各个边疆。
新清史的兴起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回应。但总体上人们还是就一些枝节性问题展开争辩,很少从长时段的宏观史角度探索清朝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联。过去的革命史和现代化史叙事,也都无力回应这些在21世纪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崛起背景下所面临的全新议题。讲得更具体些,革命史可以告诉人们,今天中国的政权和制度形态从何而来。但这仅仅涉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即政权问题。而一个现代国家还有其他的构成要素,包括疆域、族群和主权。现代化趋势则关注体现普适主义的“现代性”各项要素在中国的移植、发育和成长,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与其他现代国家之间的趋同现象,却不能够解释趋异的方面,或者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只反映变革的滞后,最终还是要趋同,因此也不能有效回应21世纪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但应该说,现在已经有条件在这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回应。这主要是因为,经过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同行对清代以来中国经济、财政、军事和社会、政治各个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学术积累,我们对涉及中国近现代史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认识,已经有了相当坚实的实证基础。《现代中国的形成》这本书的写作,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涉及国家形成和国家转型的各项问题从比较史和全球史的视角进行了新的思考。
二、国家形成的研究方法
国家形成的研究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过去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两个流派。一派可以称之为正式主义(formalism)或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追根溯源,可以从韦伯的学术中找到源头。韦伯分析不同社会和文明,区别政治体的各种类别,倾向于从中提炼出一些普遍适用、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概念和理想形态。比如他用父权家长制和世袭君主制之类的概念来定义传统型的政治体,与这些传统形态相对立的则是现代官僚制(modern bureaucracy)。但是,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中间环节和内在动力究竟如何,韦伯并没有加以深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帕森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帕森斯同样倾心于不同社会类型的比较和理论建构,提出若干组传统与现代社会相互对立的模式变项,如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价值观,弥散型与专业型的权威,出生决定论与业绩决定论等。至于一个社会如何从各种传统取向的各种变项向现代取向的变项转换,帕森斯同样语焉不详。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把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所谓现代化,划分为若干阶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有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可以分为诸如起飞、成熟到走向大众消费等不同阶段。历史学界也有人呼应现代化理论,把历史上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划分为现代化领导的巩固、经济变革、社会整合等等阶段。现代化因此被简约为一个按照不同阶段向前推进的线性过程。对各国近现代历史的理解,只要根据公式按图索骥,找到若干具体的事实证据,分不同阶段加以填充即可,而各国现代转型中出现的挫折、倒退现象,各国转型路径的千差万别和自身特点,都被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或者忽略。缺少历史分析的深度和对各国历史演化自身动力及不同途径的把握,应该说是结构主义理论方法的最根本弱项。
另一个流派,即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正好相反。它拒绝一切预设的理论类型、模式变项或演进图式,而是从各国内部的史实出发,研判国与国之间在现代国家转型道路上的差异。这方面率先起示范作用的,当属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在这部书里,摩尔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如何相互影响、制约国家的转型路径。英国和法国之所以最终走向民主体制,在他看来,是因为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从而将地主和农民吸纳到现代的经济政治活动当中。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走上法西斯道路,则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治上的保守传统导致资产阶级革命流产或者从未真正发生,结果形成了土地贵族与弱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从而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铺平道路。中、俄两国工商业发展落后,城市中产阶级弱小,而庞大的农民群体则成为国家榨取的对象和牺牲品,结果为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摩尔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着眼于阶级关系分析,关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影响;缺点是只看到国内,忽视了国际大环境,也忽视了国家政权本身的自主性。这些缺陷要等到他的学生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来加以弥补。斯考切波对中国、法国和俄国革命的比较研究,在阶级关系之外把国际环境和国家自主性因素也考虑进来。摩尔的另外一个学生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国家形成的比较历史分析更加透彻。如果说摩尔的关注点仅仅放在民主与专制两种对立的政治形态的起源方面,斯考切波的研究只限于社会动员和革命运动的话,蒂利的研究视角则更为宽广,跟本书的主题关系也更为直接。蒂利对国家形成的研究始于1975年所编的一本论文集。他在其中强调地缘政治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西欧国家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其中一个著名的提法是“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6)Charles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2.地缘竞争对国家建造的驱动,在他看来主要是在税收方面,即为了扩大税收、支撑战争,国家不得不把以税收为主要任务的国家机器加以扩大、整合,使之走向正规化和集中化,由此推动现代国家的形成。但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单一、肤浅。所以后来蒂利又把研究焦点下沉到各国内部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特别是工商业发展上面,在现代工商业发展与政权建设道路之间找到关联,由此推出关于国家建造的三条不同路径的论述,即在工商业较发达的北欧国家所出现的资本密集,在工商落后的东欧国家所出现的强制密集,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西欧国家的资本化强制道路。后来在蒂利的影响下,更多学者投入国家形成问题的研究,以至于近一二十年来形成“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研究范式,尽管有的着眼于18世纪英国国家政权的建设,有的强调军事革命的作用,有的偏重于中世纪晚期历史遗产对日后欧洲不同地区的影响,但这些研究都认可财政军事因素在国家形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现代中国的形成》的写作同样使用的比较历史的方法,是在“财政-军事国家”的视角下展开的,但也有跟以往方法有所不同。本书的分析架构由三个支柱构成,即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前两者跟以往的比较历史方法大致相同,不同的地方在于增加第三个维度,即政治认同,也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意识形态,这是摩尔、斯考切波和蒂利的书中所没有的,但对于认识清朝以来的国家转型却十分重要。地缘政治所涵盖的是国际环境,也就是外因。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严重的外来危机,决定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战略目标,也构成国家形成和转型的契机。而这些战略目标和大政方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落实,终究还要看内因,尤其是国家政权所能掌控的财政军事实力,尤其是其财政能力。而财政能力的大小,又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和社会所能提供的可以被国家汲取的资源规模。政治认同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资源的动员和使用的有效程度。如果卷入国家建造活动的各方对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支持、认可程度较高,资源便可被有效地动员和使用,反之会阻碍目标的实现。所以地缘、财政、认同三者为缺一不可,彼此密集相关。《现代中国的形成》对清朝前期及晚期、北洋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共产党革命的重新分析,也始终围绕着地缘、财政和认同这三个要素。
三、《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的关键议题
《现代中国的形成》的写作正是在上述学术史背景下进行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要超越以往的革命史和现代化史叙事,从更宽广和更深远的历史视角考察现代中国的形成问题,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讲清楚,就不能仅仅限于政权这一个侧面,而必须照顾到构成一个现代国家的所有关键要素,即政权、主权、疆域和族群构成。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现代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三个关键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中国从清代以前的以汉人为主体、以明朝两京十三省(亦即十五省)为基础的传统华夏王朝(亦即“原初中国”),向清朝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转型,并且在18世纪中叶基本完成。之所以谓之“疆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是因为它有着固定的疆域,涵盖内地十八省和各陆地边疆(满洲、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此后直至1911年清朝覆亡,除了19世纪后半期部分边疆被列强非法侵占或吞并之外,此一疆域格局大体保持稳定。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不同于欧亚大陆上的那些军事帝国缺乏固定疆域和边界。清朝不仅是一个不同于军事帝国的疆域国家,而且还是一个“早期近代”(early modern)的疆域国家,因为它具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一个正规、有效的税收机器,一支高度建制化的常备军。这些特征在欧洲中世纪各国都是例外,而非常规,只有到16世纪进入早期近代以后才慢慢具备。18世纪中叶的清朝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最大的差别,是它不存在欧洲国家已经视为当然的现代主权概念,即在国际法框架下各国相互尊重、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18世纪中叶的清朝可以说是在所有前近代国家中最接近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体。
因此,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早期所经历的,并非海内外不少学者所认为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过渡过程,而是本书所要探索的第二个环节,即中国从一个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过程。这一转型过程的最大特点,并不是人们视为当然的一个断裂过程(即帝国的衰落和分崩离析,以及诸多民族国家在帝国废墟上的崛起),而是从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历史原因。一是清朝重视和加强边疆对内地的安全屏障作用,采取了行之有效的边疆治理政策,而不是把边疆作为榨取财源的对象。这是清朝为什么不同于欧亚大陆历史上那些军事帝国的根本原因所在。清朝对边疆所采取的是零汲取和财政倒贴的政策(内地各省才是其全部财源之所在)。朝廷对边疆的治理,重在笼络其上层精英,辅之以分而治之的策略,从而确保边疆对中央的认同和顺从。这是清朝不同于任何一个军事帝国的关键所在。另一个原因是清朝时期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和中央对各省的有效控制,使朝廷可以在无需让国家机器进一步扩展和渗透、同时也无须提高直接税(田赋)的条件下,仅仅通过提高间接税(各种商业税)即可产生足够的额外财源,以应付19世纪的外来危机。其过程可以用“地方化集中主义”(localized centralism)加以概括,即中央始终保持了对地方督抚的控制权和对地方正式上报中央的各项资源的调控能力,集中主义依然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关系的核心。这是晚清中国在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中得以幸存、并且能够保持其疆域格局的大体完整的原因所在。但其代价是权力的地方化,即封疆大吏们越来越多地掌控了地方上非正式的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提高了对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也从过去的无条件变成有条件;一旦局势失控,自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这些地方精英就会背叛中央,导致清朝寿终正寝。
因此到了20世纪前半期,国家转型的第三个环节,便是如何将一个在财政、军事、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打造为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现代国家。这一转型本身又分为三个步骤。先有北洋时期那些最具野心和竞争实力的地方势力,在其所掌控的区域内,实现行政、财政、军事资源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外竞争,追求统一全国。这方面,20世纪20年代的奉系军阀和广东国民党政权做得最为出色,最终胜出的则是在“集中化地方主义”(centralized localism)方面做得最好的广东(所谓集中化地方主义,即地方已经不再听命于中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质上是地方主义的,这是不同于晚清的地方;为了加强对外竞争能力,那些最具潜力的地方势力都在其内部从事集中化的政权建设)。第二步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权朝向统一集中所作的努力,有成有败,只能算做到“半集中主义”(semi-centralism)。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权得以在八年抗战中幸存下来,并最终以胜者的姿态完成了国家建造的关键一步,即国家主权的恢复和确认。但蒋介石始终没有解决政权的统一集中问题,无力控制地方实力派,竞争力被严重削弱,最终在国共内战中溃败。第三步则是共产党革命在20世纪40年代所取得的突破。先有延安时期通过整风在政治上所取得的高度统一集中。在占据东北之后,财政军事能力大幅提升,并且形成高度整合的机制。两者结合,使共产党的建国努力区别于国民党政权,并导致其在与国民党的决战中最终胜出。一个主权完整、政治统一的现代中国建造,因此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因此,如果从国家形成的历史谱系加以分析,可以发现,1949年以后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实际上是由四个层次构成的。它的最表层,是一个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共产党建国努力的直接结果。第二个层次,它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这是19世纪后期以来从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逐步转型的结果,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已基本完成。第三个层次,它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其族群和疆域构成而言,到18世纪50年代已经基本定型。最后,它的最底层,则是清朝以前经过数千年演进所形成的一个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原初中国”(proto-China)。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因此是一个从这一谱系的底部逐层向上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层次和含义的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这一形成过程的渐进性和连续性,而不是所谓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
当然国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自清初以来从原初型的华夏王朝国家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虽然在20世纪中叶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国家形态仍将会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适和演进,至少会沿着以下三个维度加以展开,即(1)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防战略,(2)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主轴的国家行政体系尤其是其财政构造和相应的财政能力,以及(3)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尤其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随着今后几十年间中国经济持续的转型升级和城乡社会在都市化过程中不断整合,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应该在21世纪的中叶大体完成,一部以国家转型为中心内容的中国近现代史也将可以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