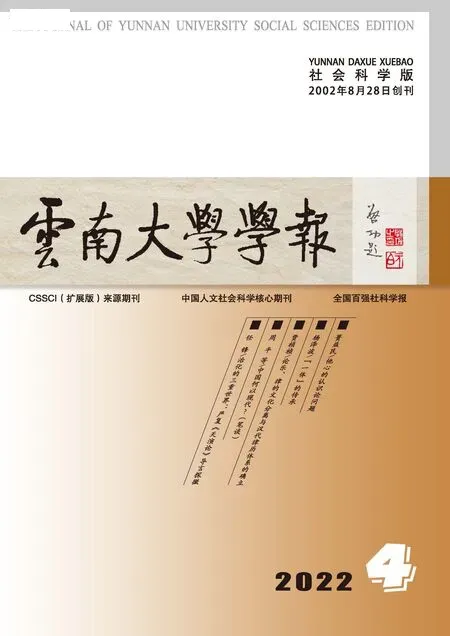身份政治:意涵及批评
吴理财
[安徽大学,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其中,女性、黑人、同性恋等社会边缘群体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求社会承认其特殊身份诉求,并反抗社会歧视和排异,于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应运而生。
并非所有与身份相关的议题都可以纳入身份政治范畴。然而,却有部分学者将身份议题和身份政治混为一谈,以致把(诸如黑人、妇女等)争取公民权利的行为或运动也视为身份政治,也有一些学者将拉美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由土著居民、农民、工人、妇女、受压迫的少数族群所发起的各种“新社会运动”贴上身份政治的标签。因此,需要辨明的是,身份政治产生于那些具有自我身份认同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宣称因为自身的特殊身份而受到社会的歧视、排异乃至压迫,要求承认他们这种特殊身份的权利,以改善他们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简言之,身份政治建基于这些社会边缘群体强烈且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没有自我认同感的身份议题不应归为身份政治。譬如,在我国有学者将农民工纳入身份政治来研究,就非常不妥。
身份政治要求人们主动建构对自身特殊身份的认同,结成特定的身份群体,要求社会承认其特殊的身份权利,并为此开展群体性行动。由其建构的群体身份,反过来又会影响乃至限制他们的社会认同。这些群体中的人的社会诉求和政治立场,往往受其狭隘的身份(认同)所局限。由此可见,身份政治的重心在于对某一特定群体的认同和忠诚,而不像公民或国民那样在于对国家或民族的认同和忠诚。(1)Howard J. Wiarda,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cience, and Identity Politics: An uneasy alliance. Burlington, USA: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4.在身份政治肇始之前,身份议题往往被限定在狭小的、特定的、小众的社会政治特殊界域里,并不处于中心地位,(2)[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身份政治与左派》,易晖译,《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更不会引起社会的瞩目。然而,迈进21世纪之后,欧美社会的身份政治愈发显著,如今被归纳到身份政治标签的议题不仅范围广泛,而且内容庞杂,甚至相互冲突。如今,身份这一概念在西方社会的日常政治讨论中几乎无处不在。在当今美国,没有一个像身份政治那样把持着公共舆论,乃至成为不容置评的“政治正确”。(3)David Azerrad, “The Promises and Perils of Identity Politics”,Https://americanmind.org, Jan 23, 2019.在一些欧美国家,身份议题成为政治论述和实践的焦点,并在其内政外交中扮演着关键角色。(4)涂锋:《身份政治第三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基于国家建构视角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
在西方,身份政治兴起伊始,就得到一些西方左派的推波助澜。对这些新一代左派来说,重要的是文化权力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不公正分配,他们关注的不再是抽象的“劳动者”的财富和普遍权利,而是特定的男人和女人的财富和权利,谁的种族、性别或教派拥有“特权”,谁没有。(5)Matthew Continetti, “Bernie Sanders’ Fossil Socialism”,FreeBeacon.com, May 29, 2015.他们不再聚焦经济不平等、阶级剥削或分配问题,而是将斗争的矛头转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歧视和文化不平等,更加注重文化性批判,热衷于文化政治,投身于“文化革命”。在这些左派的推动下,身份问题产生了大量与自由主义及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关于性别、性取向、民族、种族、文化等议题的争论,(6)Charles Taylor, The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Will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这些争论助推了身份政治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如今所有的政治几乎都是关于身份的,同样所有的身份也几乎都是政治的。(7)Richard Thompson Ford, “Political Identity as Identity Politics”,Unbound: Harvard Journal of the Legal Left, Harvard Law School 1.1 (Nov. 2005),pp.53-57.甚至有人提出,一切的政治都是身份政治。(8)Ann Friedman, “All Politics Is Identity Politics”, The American Prospect, Vol.27, No.7,2010,p.29.在一些西方国家,身份政治模糊了传统的左右之分的意识形态分野,甚至成为这些西方社会的某种“元政治”(Meta-politics)。当今西方社会的许多政治社会现象,或可透过身份政治这个棱镜得以理解或解释。
二、身份政治的主要意涵
由于英文单词identity既有“身份”,又有“认同”的含义,国内学者一般只从字面上将identity politics翻译为“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这种翻译往往使人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它,以致产生诸多误读甚至误解,认为凡是跟“身份”或“认同”相关的政治,都是identity politics。其实不然,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个人主观认同的身份政治”(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依旧使用“身份政治”这一惯常的中文翻译)。(9)何涛:《极端个人主义的“伪政治”——马克·里拉对美国当代身份政治的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6期。
身份议题由来已久,在古典政治学中就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身份政治却是步入成熟的现代性社会以后乃至转向后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新的政治现象。尽管身份政治与“身份”相关联,但并非所有与“身份”相关的议题都属于身份政治。譬如,传统政治学所关注的阶级身份、民族身份、公民身份等,严格而言都不属于身份政治范畴。阶级“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代世界中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10)[美]朱迪斯·巴特勒、[英]欧内斯特·拉克劳、[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即便是西方一些左派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把马丁·路德·金等人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视为身份政治兴起的标志,也是一种误解,因为他们当初所主张的主要是普遍性意义的、同一性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也就是要求赋予黑人完整的公民身份以及平等的公民权利。因此,有人从城乡分割体制出发将农民工的权利问题纳入身份政治中进行思考,也是对身份政治的错误理解。
在此,需要进一步强调指出的是,身份政治所“认同”(identity)的,不是启蒙运动以来所强调的那个抽象的、普遍的、一般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而是拥有某种特定特征的具体的人(譬如女人、黑人、印第安人、LGBTQ等)——“并不是要在人类共有属性的基础上纳入‘普遍人类’的范畴;也不是为了‘尽管’彼此有差异而‘尊重’对方。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尊重自己,因为自己是不同的”。(11)Sonia Kruks, Retrieving Experience: Subjectivity and Recognition in Feminist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p.85.换言之,身份政治中的“身份”(identity)与个体独特的社会经历紧密关联,特别是他或她所遭受的社会压迫的经历,以及一种在一定群体内共享的、自认为更真实的或自主性选择的可能性。(12)Cressida Heyes, “Identity Politics”,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7 Edition),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7/entries/identity-politics.而且,这种认同往往不是同一的、独一的,或者不会改变的,而是多向度的、复杂的,并且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从认同本身而言,所谓的认同必定同时和差异相对并存,也就是认同必须借着将它和他者区分开来才能存在。这样的认同通常和与生俱来没有什么实质关系,往往来自所处社会的建构,(13)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332页。由这个社会的主导文化所形塑、所定义。
首先,身份政治中认同的一般是自我建构的身份,而非自然的或被赋予的身份。对于身份认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看法:第一种认为身份是自然形成的,由性别、种族、族裔、亲属关系、习俗、信仰或文化等决定;第二种认为身份是政治国家所赋予的,譬如,公民身份、民族身份、国民或人民等;第三种认为身份是自主建构的,它是自我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的再现。(14)文一茗:《身份:自我的符号化》,《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人们通过身份来获得归属感,形成群体的凝聚力,来辨别我们和他者,表达对特定群体的忠诚,成为他们人生意义建构的一部分。(15)刘擎:《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8期。例如,卡斯特(Maunel Castells)就曾认为,“没有一种身份是本质性的”,“认同(identity)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16)[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2、3页。几乎所有身份政治者都持第三种看法,他们反对所谓的“自然的”“给定的”或“被赋予的”身份,认为这些身份都是不正义的。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们所建构的身份认同首先是一种“排斥性的认同”,“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17)[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第4页。不过,恰如英国伯明翰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霍尔(Stuart Hall)所言,我们的身份认同只能在所谓的“话语”(discourse)里面被建构。(18)Stuart Hall,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S. Hall & Paul du Gay (eds),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6,p.4.譬如,身份就是对性进行界定的话语的产物——我们是根据已经被书写为我们社会的文化传统的那个剧本底稿来演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其中,酷儿政治学就反对对性进行二元对立的同性恋和异性恋身份的划分。因此,在身份政治中,身份更主要是表演性的,身份不是建立在任何本质特征之上,而是建立在文化预期之上的一个表演。(19)[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
Identity politics中的identity,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界定或自主定义。定义是政治的一种根本权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缘起于对特定身份的不同定义而引起的社会抵抗、社会纷争或社会运动,才贴上“政治”的外衣,形成如今的“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概念。
其次,身份政治往往以特定身份群体的面目出现,要求承认其差异性身份。除了强调自我的身份认同以外,身份政治同时强调其差异性,甚至把自我的身份认同建构在这种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就像美籍土耳其裔政治思想家塞拉·本哈毕比(Selya Benhabib)所指出的:“差异问题出现,也就出现了政治,而且往往同时出现身份认同概念:只有在个人和集体与那些不代表自身利益的人之间形成差异时,他们才能发现自己的身份。”(20)转引自约翰·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丁开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50页。对于一些身份政治参与者来说,他们甚至将其差异视为本质/本真的东西,将差异作为界定自我的本源。
身份政治首先是谋求某种身份的承认(也就是“承认的政治”)。但是,这里所要求承认的往往是“差异”——“就差异政治而言,要求我们给以承认的是这个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认同,是他们与所有其他人相区别的独特性。这种观点认为,正是这种独特性被一种占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21)[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上),董之林、陈燕谷译,《天涯》1997年第6期。他们将这种忽视、掩盖或同化称之为社会压迫。因而,对于他们而言,在现今“这个社会的群体性压迫很少存在于官方法律和政策,反而是主要存在于非正式的、往往并不被注意和反思的言语、对他人的身份反应、日常互动和评价的常规实践、美学判断,以及在媒体中泛滥的笑话、图像和刻板印象。我们社会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压迫一定程度上涉及将某些群体定义为他者,特别是对他们身体的标记和锁定”。(22)[美]艾丽斯·M.杨:《正义与差异政治》,李诚予、刘靖子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1页。
在某种特定语境中,任何一种差异都可以构成一个显著的群体身份。(23)[美]艾丽斯·M.杨:《正义与差异政治》,李诚予、刘靖子译,第57页。因此,对于身份政治者而言,承认政治斗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允许差异存在’(difference-friendly) 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边缘群体,如边缘民族、‘种族’、性倾向及性别不再为了换取平等尊重,而被大多数或主流的文化规范所同化”。(24)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Verso, 2003, pp.7.因此,身份政治推动了从“分配正义”到“承认正义”、从“经济政治”到“文化政治”的转变,相应的,西方批判理论的焦点从“平等”转向了“差异”。(25)涂锋:《身份政治第三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基于国家建构视角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对于身份政治者而言,某种边缘化或“异类”身份不是被矫正和同情的对象,而是值得去自豪和彰显的价值。这些边缘群体不再希冀融入自己处身的社会主流,而是要求社会承认并尊重他们身份所承载、所表征的差异性。甚至对于他们来说,被其主流社会所忽视、排异或同化,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污名化或压迫。
一旦他们的差异得到承认,这些身份群体还会要求参与,进而要求平等地参与,并在此基础上保障该身份的(特殊)权益。美国当代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身份政治的核心是必须建立能够实现“参与平等”的身份;以“参与平等”为规范的正义观,包括经济领域的再分配、文化领域的身份承认、政治领域的代表权。(26)[美]南茜·弗雷泽:《有关正义实质的论辩:再分配、承认还是代表权?》,朱美荣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4期。不过,在当今一些西方国家,许多身份政治的诉求只是要求“承认”。
身份政治不仅对外标榜其差异性,对内同样也贯彻差异性原则。譬如,随着同性恋运动的发展,女同性恋群体开始从一般性的同性恋群体中分离出来,在运动中表达自身特有的小群体主张。在美国,从女同性恋群体中还进一步分离出了“康巴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这样的女同性恋黑人团体,(27)康巴河公社是一个建立于1974年的黑人女同性恋组织。该组织认为,早期的进步主义与女权运动倾向于把女性看作一个整体,强调女性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应该得到社会的满足。然而,这些运动无法体现黑人女同性恋这个女性整体中的少数类别,这就意味着她们的诉求实际上被忽略了。所以,她们要求突出黑人女同性恋者这个特殊的身份认同。她们独立进行发声:“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与男孩不同,我们受到不同的对待。例如,我们同时被告知要保持安静,既要‘像个淑女’,又要让我们在白人眼里不那么惹人讨厌。通过分享彼此的生活经历,随着自我认同意识的不断增长,我们认识到我们经历的共性。于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它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并最终将终结我们的压迫。”(28)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 in All the Women are White, All the Blacks are Men, But Some of Us Are Brave: Black Women’s Studies, Gloria T. Hull, Patricia Bell Scott, and Barbara Smith (eds),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1982,pp.14-15.康巴河公社1977年发表的这份宣言,(29)“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 Black Feminist Organizing in the Seventies and Eighties”, in Barbara Smith (ed.),Home Girls: 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0,p.264.被人视为美国当代身份政治产生的标志。这样一来,就会导致身份政治运动的碎片化,以及诸多不同种类的参与者为了获取新的“主体”地位而互相斗争。(30)汪越:《身份政治的理论逻辑》,《学术界》2018年第3期。
这种建基于差异性的身份认同之上的身份政治诉求,必然是多样性的、具体性的和语境性的,导致他们之间往往缺乏凝聚力。在对差异性的寻求中,因为对特定群体的狭隘忠诚感而撕裂整个共同体的统一,破坏了社会团结。(31)孔元:《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2期。这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身份政治的积极作用。
因此,身份政治难以跳脱这样一些吊诡之困: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争取平等的承认,驱动了当代的身份认同政治;但获得平等承认的渴望,可能很容易不知不觉变成要求别人承认该群体高人一等。(32)[美]法兰西斯·福山:《身份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认同与尊严的斗争为何席卷当代世界?》,洪世民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甚至在身份政治的某些实践中,主导的子群体可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将他们对群体身份的看法强加于其他成员。(33)Cressida Heyes, “Identity Politics”,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7 Edition),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7/entries/identity-politics.原本是为了消除某一特定身份的差异性权利,却刻意强调并最终确认这一身份的差异性;原本这差异性的身份是自我建构的,却认定它是本质主义的。
再次,身份政治严格而言是一种社会性政治。从身份政治原初的兴起来看,对特殊性身份的“承认”还不主要是要求“国家”的承认,而主要是要求“社会”的承认。所以,身份政治“追求的不是普世涵盖的国家认同,而是(在国家之内各个不同的)社群的认同,这样的认同是多元而分化的,更不以什么解放的目标自诩”。(34)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第325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身份政治原本是一种社会性的政治——一些社会边缘群体运用这一概念来唤醒其身份意识,维护自身权益,反抗社会不公(包括污名化、排异、压迫等)。(35)H.J.Wiarda,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cience, and Identity Politics: An Uneasy Alliance,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4, p.150.其实,所谓的社会边缘群体也是由其所在的主流社会所定义或建构的。身份政治所反抗和斗争的,恰恰是这一主流社会的定义或主导文化的建构。身份政治从对社会压迫的分析开始,以各种方式对先前被污名化的群体描述进行重新认识、重新描述或者改造。不再接受主流社会所提供的关于自己自卑的负面脚本,而是通过破除虚假意识、提高自觉意识,来改变自己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36)Cressida Heyes, “Identity Politics”,Edward N.Zalta (ed.).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7 Edition),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7/entries/identity-politics.它将这些边缘群体的“隐藏文本”显性化,甚至与社会的“主导文本”发生争夺战,由此成为这个社会文化霸权争斗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以后,“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特朗普当选总统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加速了身份政治的异化,(37)“9·11”事件表明,现代政治认同的主要源头不单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也常常是民族的、宗教的。对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者而言,民族和宗教身份才是其根本的身份标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具有分水岭意义,它带来的多维政治后果赋予身份政治诸多新的内涵。经过多年的发酵,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则被视为新身份政治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身份政治逐渐沦为政党或政治派系斗争乃至世界范围“文明冲突”的工具,于是它才从社会性政治走向政治性政治,成为当下西方政治极化的“祭品”。(38)政治极化是指政治倾向向政治光谱两端分化的过程或不同政治主张各执一端、尖锐对峙的状态。
另外,身份政治实质上是个体化社会的政治表征。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看来,身份政治的出现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产生的急剧而且意义深远的社会巨变的一个结果。在过去数十年间,当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难觅于现实生活之时,“共同体”一词就变得再缥缈再空泛不过了。在一个一切都在运动和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世界里,人们总是会去寻找可以归附的社会团体,而且他们也在某个身份团体中得偿所愿。(39)[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身份政治与左派》,易晖译,《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急剧的个体化转型和快速的全球化发展,都为身份政治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土壤和时代基因,身份政治因此可以被视为个体化社会的政治反应和政治表征。
身份政治实践特别关注个体性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身份政治运动的核心诉求在于“自我命名”的赋权,(40)Enrique Laraa, Hank Johnston, Joseph R. Gusfield,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Philade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p.10.“有权能实现他们自己的认同——处置他们自己的个人创造力、他们自己的情感生活,以及他们自己的生物性与人际间的存在等等的可能性”。(41)Alberto Melucci,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A theoretical approach”,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80(19),p.218.因此,身份政治异化的极端状况便是个人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美国政治学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认为,当代美国的身份政治其实是极端个人主义在政治认同领域的一种表现。
虽然身份政治一般表现为集体行动的形式。而且通常也是以“集体”的面目示人,但其建立的基础却是个人对自己独特身份的认同。越是进入现代性社会,个人绝不是不假思索地或者只是被迫地接受某种由外界施加的某种身份;于是,身份认同日益成为个人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或话语,这种利益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方面,而是越来越强调对生活意义的追求。(42)何涛:《极端个人主义的“伪政治”——马克·里拉对美国当代身份政治的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3期。
正因为如此,身份政治本身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这个悖论便是,身份政治本质上并非为了所有人,而是为了特定群体的成员甚或个体争取政治利益,(43)[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身份政治与左派》,易晖译,《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但是,它所运用的却是普遍主义的政治理论(如自由、平等);并且,事实上,这些特定群体的政治利益又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身份政治原本是想建构一个属于边缘群体的身份“共同体”——一个被他们视为新的安全的、可信的庇护所,(44)Z. Bauman, 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p.151.但事实上它却意味着共同体的取消。(45)包大为:《身份政治:反噬的政治及其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9期。这是多么可笑的自我嘲弄!
最后,身份政治是一种“文化政治”。就像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指出的,“身份认同”(identity)和“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二词的起源距今相当近,前者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心理学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大力宣传,(46)在艾瑞克·艾瑞克森看来,身份不仅包含个体对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还包括他人对这种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承认(Erik Erikson,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80,p.22)。在这之后,美国社会学界将艾瑞克·艾瑞克森侧重个体认同的概念发展为描述群体认同的社会科学概念,它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运动中被政治化,演化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的话语形态。后者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政治学出现后才映入眼帘。身份政治将包括性、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和文化等在内的以前未被定义为政治的生活领域加以政治化。(47)Mary Bernstein, Identity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July 2005,p.50.而且,他们的政治活动集中于文化问题,以致重写有关不同身份模式的历史或剧本成为他们的一种重要解放手段。例如,在美国,部分激进的非裔黑人学者要求重写美国历史,认为由白人主导编写的美国历史歪曲了历史事实,充斥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傲慢、偏见和谎言。
对于当今的一些左派学者而言,“正义的范围不限于分配,而是涵盖了支持或破坏压迫的所有社会过程,尤其是文化。有助于压制那些带有身体标记的群体的行为、比喻、图像和刻板印象是普遍的、系统的、相互生产的、彼此强化的。它们是文化实践的主导因素,是我们自由民主社会的一般背景。只有改变文化习惯本身,才会改变由它们产生和强化的压迫,但只有当个人对自身习惯有所意识并加以改变之时,文化习惯才会发生变化”。这便是这些左派所说的“文化革命”。(48)[美]艾丽斯·M.杨:《正义与差异政治》,李诚予、刘靖子译,第185页。而身份政治则是其“文化革命”的一项题中之意。
尽管身份政治运动源于各种身份诉求,不论这些社会运动以何种形式展开,投身“文化革命”,“参与大众话语的制定都是当代身份政治斗争的一个关键领域”。(49)[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通过参与者自身的话语实践来对抗支配性话语的压迫是身份政治的一个主要实践路径。因此,身份政治“争夺的是身份的自治及其表演体系”,以致许多修辞集中于一些口号,如增强身份意识,或对身份的骄傲。身份政治“通过它对社会形式的象征词汇的自反性关注,表征为文化性,并越来越强调公民身份”。(50)[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第145-146页。如今,“认同政治被颂扬为社会中文化与政治抵抗的舞台,而且往往还被视为是转向新型态后现代或晚期现代社会的一个指标”。(51)Kevin Hetherington,Expressions of Identity: Space, performance, politics, London: Sage, 1998,p.22.因此,有人认为,在身份政治中,“政治是且仅仅是公共意见的名称”而已,(52)[法]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页。它以解放的符号替代了实在的解放,它以“文化革命”替代了“阶级革命”。由此一来,阶级社会中生产领域的根本性矛盾再一次被身份政治的意识形态所掩盖、遮蔽。(53)包大为:《身份政治:反噬的政治及其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9期。
如今,尽管身份政治无处不在,却也有无所不包之嫌。它至少存在诉求意义、认知意义和策略意义三种身份政治。(54)林垚:《“身份政治”的歧义性》,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295960),2020年7月16日。并且,有关身份政治的社会运动、话语和理论杂糅其间,相互影响,构成了身份政治的“万花筒”。
三、万花筒般的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的发展,受到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西方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对身份政治进行了潜在的辩护。多元文化主义原本用来形容实际多样化的社会,但它也成为一种政治纲领的标签,它标榜平等尊重每一种文化和每一种人生体验(尤其是过去被忽视或低估的文化或人生体验)。古典自由主义力求保障平等个体的自主性,新的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则提倡平等尊重所有文化,就算那些文化会限制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55)[美]法兰西斯·福山:《身份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认同与尊严的斗争为何席卷当代世界?》,洪世民译。多元文化主义辩称,通过强调对族群少数派群体权利的保护,更有利于实现少数派个体成员的权利。然而,事实上二者往往存在紧张乃至冲突。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表示,自由主义者坚持只要个人权利切实得到了保护,特定族裔或少数民族就无需再被赋予其他更多的权力,这一说法站不住脚。(56)[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69页。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特定族裔或少数民族的权利得到切实保护,其个体的权利未必就随之得到保障。一些学者从文化多元主义出发,来论证身份政治的合理性,他们认定某个“身份”是由特定文化塑造的,遵从文化多元主义逻辑就必须平等对待这个差异性的身份。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却难以解决保护少数派身份群体的文化权利的同时,如何避免多元身份在互动之中的冲突。(57)陈金英:《美国政治中的身份政治问题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然而,深入地探析却发现,身份政治其实受到多种不同理论、不同流派的影响。在西方,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群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都卷入了身份政治之中,使得身份政治形成许多不同的主张和诉求,甚至相互对立、冲突。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他们从传统的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20世纪60年代,西方左翼的政治议程焦点从原来的“阶级”“民族”转向“身份”,转向受到主流社会压迫和排异的社会边缘群体,体现在争取性别平等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政治斗争中。左派成为身份政治的助推者之一。(58)Frank Furedi,“The Hidden History of Identity Politics”,Spiked Review, December, 2017.但是,他们对身份的关注,给出的却是破碎的视角,并且减损了对一个关于解放、统一的启示的需要。(59)[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第232页。原本以追求人类普遍解放为目标的左派,因此陷入尴尬境地。身份政治致力于特定群体的特殊目标,然而,“左派的政治规划是普遍主义的:它是为全人类”。(60)Eric Hobsbawm,“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Left”, New Left Review, I/217(May, June)1996,pp.42-43.一些左派沉迷于身份政治,使其陷入一种困境,“缺乏明显的办法来构建一个跨越局部边界的共同利益”,(61)Eric Hobsbawm,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Left”, New Left Review, I/217(May, June)1996,p.45.尤其是在启蒙普遍主义衰落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
正如福山所言:20世纪的政治向来是沿着经济议题界定的左或右的光谱来规划的,左翼希望更平等,右翼想要更大的自由。进步主义的政治活动以工人、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派为中心,他们追求更好的社会保障和经济重新分配。相形之下,右翼则主要关注缩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干预、发展私人产业和自由市场经济。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二个十年,这条光谱似乎在许多方面让位给由身份认同界定的光谱。左派已经没那么着重于全面经济平等,而更想促进各种被认为遭遇边缘化的群体——黑人、移民、女性、西班牙人、“LGBT+”、难民等——的利益。右派则将自己重新定义为爱国者,企求保护传统的民族身份认同(明显与种族、族群或宗教有关的身份认同)。(62)[美]法兰西斯·福山:《身份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认同与尊严的斗争为何席卷当代世界?》,洪世民译。在欧美一些国家,身份政治同样被右派所运用,因为身份政治会催生出政治正确,而对这些政治正确话语的利用如今也成为右派社会动员的主要策略。(63)[美]法兰西斯·福山:《身份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认同与尊严的斗争为何席卷当代世界?》,洪世民译。
在美国,身份政治经历了从左派的解放政治向表演政治和右派的反动政治(reactionary politics)演化的历史过程。当下“白人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它同黑人、其他族裔、女性主义、同性恋运动之间的对立和冲突,(64)当代白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相信白人受到攻击,而大范围的敌人——从女权主义者到左翼政治家,再到穆斯林、犹太人、移民、难民和黑人,都在通过各种手段密谋破坏和摧毁白人种族。[《卫报》:为什么说白人民族主义是全球威胁的一部分,凤凰网(https://ishare.ifeng.com/c/s/7ovGHGMxC0Y)]成为美国当今身份政治最新的表达形态。这种身份政治,也被称之为“新身份政治”“后身份政治”或“异化的身份政治”。由于它对所谓自身身份的“本真性”的固守和对差异的寻求,身份政治不断瓦解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消解社会团结,导致美国民主政治的“部落化”和“民粹化”,在最近十余年内引发了这些民族国家内部的“文明冲突”。(65)孔元:《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2期。
如果说,21世纪之前的身份政治更主要是一种左翼政治运动的话,那么,21世纪以后的身份政治在跟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媾和、合流以后,则滑向了政治光谱的右端。在新身份政治崛起之后,传统身份政治仍继续存在并发挥影响,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对峙加剧了西方的政治混乱。(66)徐斌、卜永光:《新身份政治兴起及其对西方国家治理的挑战》,《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许多人将身份政治纳入后现代主义进行审视。他们认为,身份政治起源于对现代启蒙普遍主义的反叛。与现代启蒙普遍主义始终相随而行的是另一种反启蒙的保守主义,它认为现代启蒙主义的普遍人性观是虚妄的,每个人首先属于特定的民族或者族群,不可能成为普遍抽象的人类(human beings)一员。而且,在现实中,普遍主义的人从未真正地产生过。这种反启蒙论述为身份政治在后现代社会的崛起播下了最初的种子。(67)刘擎:《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8期。随着现代启蒙理性主义神话的破灭,以文明的现代人自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占据着社会的“主体”,并对异类、他者实施支配和压迫,日益被揭示出来,身份政治一开始起源于那些传统上被视为“边缘人”的他者对于这种支配关系的反抗和斗争。
对于后现代的身份认同政治而言,那个虚妄的普遍主义的理性“主体”概念的解构是其理论的重要出发点。只有解构了这样的“主体”概念,才能看到现代社会微观权力关系当中的压迫现象,被这一“主体”神话所遮蔽的“他者”的形象才能得以出场,成为身份政治的主角。“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相关的理论著作在使认同政治得到表述上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68)[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第145页。
在这当中,法国思想家福柯的权力分析和话语理论对于身份政治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尤为重要。福柯对性经验、疯狂史的“考古”,对“不正常的人”、“疯癫与文明”的分析,对“生死爱欲”乃至对“生命政治”的研究,揭示了隐秘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权力运作机制,深刻而清晰地阐明了主体和他者的对立关系是如何在话语实践当中被建构出来的。不仅主体是建构的,他者同样也是被建构的,并且在被建构出来的同时就已经暗含了对他者的排异和压迫。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从福柯的理论当中看到自身在身份塑造的过程中被主流社会所规训、压迫的情形,从而产生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对于那些与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控制作战的人来说,它简直成了金科玉律。作为真正反抗规训实践的批判武器,福柯的观点成了形形色色的局部斗争的利器”。(69)[法]弗朗索瓦·多斯:《解构主义史》,季广茂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312页。
对于许多人而言,当下西方国家声势正猛的身份政治是一种深度现代(deep modern)或后现代(post modern)政治形态。(70)任剑涛:《在契约与身份之间:身份政治及其出路》,《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从本质上说,后现代的身份政治的兴起是从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当中发展而来的,通过对传统政治普遍主义的同质化倾向和对少数的排除倾向的批判,对被压迫的“他者”予以尊重和承认,并以此形成一种彻底的开放性的多元的政治民主。(71)汪越:《身份政治的理论逻辑》,《学术界》2018年第3期。因此,他们提出,认同政治必须放在后现代的脉络中来看,才能显现其底蕴。(72)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第243页。盖认同问题乃是“作为一种政治的后现代”的主要关切所在。易言之,后现代的政治问题不啻为认同问题。(73)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第243页。
四、对身份政治的批评
身份政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发展新阶段产生的一个新的政治社会现象。一方面,身份政治为社会边缘群体发声,争取特定群体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缘群体的处境,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另一方面,身份政治的文化特质使得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甚至无意识中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74)汪越:《身份政治的理论逻辑》,《学术界》2018年第3期。目前,对身份政治主要有以下一些批评。
1.身份政治是排他性政治。身份群体只关心自己,为了自己,而不是别人。这些群体组成的同盟,不是通过一套共同目标或价值维系起来,只是临时拼凑的统一,很像战争期间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而临时组成的国家同盟。当他们彼此不需要的时候,就会分裂。(75)[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身份政治与左派》,易晖译,《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这种高度排他性的身份政治,不论终极目标为何,其悲剧性在于它根本就行不通,众人只能表面上假装它是可以实现的事实……它并不是用来处理20世纪末以来种种难题的方法,只是面对这些难题时产生的一种情绪反应而已。”(76)Eric Hobsbawm,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Abacus, 1995,pp.429-430.其实,“排他性的身份政治对人们来说不是天生的;而更有可能是被外力强加的——就像本来居住在一起、互相交往和通婚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被迫分离,或者以柔性的方式分离”。(77)[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身份政治与左派》,易晖译,《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身份政治甚至导致彼此之间的冲突和争斗。“身份认同政治的动能会刺激更多同类的东西萌生,因为身份认同群体会开始视彼此为威胁。不同于经济资源的争夺,身份认同的诉求通常是不可谈判的:基于种族、族群或性别的要求社会承认之权利,是以固定的生物学特性为根据,不能拿来交换其他物品,也不容删减。”(78)[美]法兰西斯·福山:《身份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认同与尊严的斗争为何席卷当代世界?》,洪世民译。身份政治将一个通过差异寻求解放的普遍主义诉求,发展为通过差异再造新的压迫的反动政治,从而使得任何性质的和解都变得不可能。(79)孔元:《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2期。因为任何对身份的主张都必须围绕着一种结构性排斥来组织自身,身份是在一系列已被社会承认的差异之间建立起来的。身份政治的危险正在于,它将一种实际上由它与他者的对立所定义的身份,作为自我或群体的真实身份,(80)Cressida Heyes, “Identity Politics” Edward N.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7 Edition),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7/entries/identity-politics.作为自我的“本真”来加以捍卫。
2.身份政治是个人主义政治。马克·里拉(Mark Lilla)甚至认为,身份政治实际上是一种“伪政治”(pseudo-politics),因为它无法提出一种能够吸引大多数人、包容大多数人的政治愿景,相反却用无数碎片化的身份团体各自的政治愿景,撕裂了社会的团结,加深了族群分裂,使之“部落化”;而且,它偏离了权力这个政治的核心问题,沦为空洞的自我表演和缺乏建设意义的社会抗议运动,加剧了社会的对立与分裂,导致现实政治的极端化。激烈的政治对峙让政治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导致西方民主政治走向否决为上、治理为下、政争不断、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81)节大磊:《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美国研究》2016年第2期。同时,由于身份政治的冲突,使得民粹主义和怨恨政治(resentment politics)大行其道、甚嚣尘上。在这种政治极化的环境中,“否决政治”的盛行常常导致国家机器运转失灵。(82)徐斌、卜永光:《新身份政治兴起及其对西方国家治理的挑战》,《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诸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福山等身份政治的研究者常常将身份政治与社群主义联系在一起,强调身份政治的集体主义特征。不可否认身份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往往是各种身份团体,并且常常提出集体性诉求,但是,这种表面的集体主义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当这种个人主义趋向极端之时,其所认同的对象会越来越狭隘,认同的社会稳固性会变得越来越脆弱。马克·里拉认为,美国当代的身份政治其实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在政治认同领域的一种表现。
3.身份政治可能损害民主和自由。和激进左派一样,一些西方自由派分子也批评身份政治的解构力量。美国社会批评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就指出,身份政治产生于爱国主义、公民信念等普遍主义信念的解体过程中,不管其来源如何,它都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政治的,它无法真正安抚一个受伤的、孤寂的心灵,无法在一个民主政治下将少数族群的诉求凝聚成一场取得胜利的政治运动。(83)Todd Gitlin,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 Why America is Wracked by Culture War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5;Todd Gitlin, Letters to a Young Activis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127.
由于身份政治催生或制造出一种“政治正确”而威胁到言论自由,以及范围更广的维系民主所需的那种理性的论述。一旦执着于身份认同,就会与商议性的话语发生冲突。因为身份认同聚焦于特殊的人生体验,强调个体的情绪感受,而非理性检视的内在自我。身份认同可能会增强其认同的小群体(in-group)的信任,但同时却加剧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区隔和冲突,因此狭窄的群体身份认同,会危害公共沟通和真正的集体行动。(84)[美]法兰西斯·福山:《身份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认同与尊严的斗争为何席卷当代世界?》,洪世民译。身份政治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议题简单归结为身份差异,回避了严肃的政治辩论,从而降低了公共政策的质量。(85)陈金英:《美国政治中的身份政治问题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戴维·阿泽拉德(David Azerrad)因此主张抵制身份政治,不是因为它替那些受过不义对待的人鸣不平,而是因为它腐蚀爱国纽带,培育仇恨,推销文化分离主义,要求特殊待遇而非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从而对共和国的自治构成威胁。(86)David Azerrad, “The Promises and Perils of Identity Politics”,Https://americanmind.org, Jan 23, 2019.对身份的认同和忠诚,可能会压倒对规则和契约的遵守,对现代契约政治构成一种颠覆或反噬,使其陷入危机之中。(87)任剑涛:《在契约与身份之间:身份政治及其出路》,《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身份政治及其带来的“新部落主义”,则可视为对前现代政治某种程度的“回归”。(88)徐斌、卜永光:《新身份政治兴起及其对西方国家治理的挑战》,《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4.身份政治掩盖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主体性、普遍性、宏大叙事的彻底解构的结果是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代替“我们对世界的行动”,建立在话语理论基础之上的身份政治过分强调和夸大了文化领域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作用,这样只会陷入一种唯心主义之中,导致了身份政治尽管在理论上激进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在实践中却表现为温和的改良主义政治和跟资本主义制度相兼容的协商民主。西方左翼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以及围绕身份政治而展开的“文化革命”、文化斗争和文化议题的喧嚣,淹没和掩盖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身份政治既在分化又在去政治化,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破坏转移到对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文化适应上,从而维持其宰制性经济结构的不变。
西方左派的文化政治片面地强调认同和承认,却淡化和抹杀了再分配要求的正当性,产生了自我认识的“错位”——“资本主义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这些身份文化主义者却将其自然化,不顾剥削和压迫的现实,压迫工人服从于利益最大化和资本积累的要求。”(89)Alcoff L.M, Hames-García M., Mohanty S.P.et al.,Identity Politics Reconsidered. Palgrave Macmillan, 2006,p.32.身份政治将其视角始终局限在文化上层建筑上面,甚至自身成为或接合(articulate)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一部分,(90)对于拉克劳、墨菲而言,“接合现在是一种言说的实践,这种言说的实践不具有先于被接合起来的组成成份分散状态外部的组织地位,在组成成份内部建立一种关系的任何实践称为接合”。而无法引向真正基础性、制度性的变革,由此而大大消解了其自身的进步力量。(91)涂锋:《身份政治第三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基于国家建构视角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它错误地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少数族裔、女性、特殊性取向群体在统治阶层中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和话语权,就不用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92)[英]阿萨克·库马尔、戴里娅·加布里尔、亚当·艾略特-库珀,[美]施卢蒂·艾耶:《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身份政治的介入》,《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期。它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统治没有造成根本威胁,甚至帮助他们转移和模糊了真正的矛盾,把左翼政治引向了错误的方向。就像玛丽·莫兰(Marie Moran)所指出的那样,身份政治“提供了一个仍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结构保持兼容的代议制政治版本”。(93)[爱尔兰]玛丽·莫兰:《身份和身份政治:文化唯物主义的历史》,《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期。
一些左派也对身份政治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其一,身份政治刻意追求差异性,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主义理想。英国左翼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身份政治追求的是在一个给定的政治共同体内部谋求优惠、差别待遇或者寻求特殊对待,因此它是一种宣泄、佯装的政治。(94)[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9-642页。然而,左派的政治规划原本是普遍主义的,其终极目标是普遍人类的平等和社会公正。其二,身份政治不关心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斗争,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平等理想。对身份政治持批判立场的美国政治学家阿道夫·里德(Adolph Reed)也指出,左派政治的核心原本是批判和反抗资本主义,追求在经济上更加平等的进步社会。可是,身份政治不但无法实现这一点,而且为这种不平等提供了一种精英主义的辩护,它不是阶级政治的替代,而是沦为它的另一种形式。(95)孔元:《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2期。
总之,身份政治不能取代传统的公民政治。身份政治不能变成一种自恋性的肯定,不应在否定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之余,把自我认同的改变视为社会的改变,只强调某一特定认同的重要,而对构连不同认同的社会政治理论漠不关心,使其沦为“认同的反政治”。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需要持久地参与政治。进而言之,后现代的认同政治,由于它不以彻底改变国家体制为其斗争目的,也不以选举策略为唯一手段,而只是在社会中争取其特定的认同,进而形成一种具有自我解放意识的独立文化,以此来实现其激进民主的目标,因此,充其量只能作为现代公民政治的一个补充,而不应取公民政治而代之。(96)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第336、345-346页。
不过,也有不少人提出,这些对身份政治的批评,充满了偏见或误解,过分夸大了身份政治的消极作用,忽视了它的积极功能。例如,美国劳工阶层的研究者认为,身份政治不完全是对阶级政治的替代,而是和阶级政治一样,都反映和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结构。简单地将当前美国(乃至欧洲)政治中的分裂和极化现象归咎于身份政治,甚至归结为身份政治对阶级政治的替代,不仅偏颇而且有失公允,遮蔽了事实的真相。在身份政治的背后,常常能够发现更为复杂的利益冲突及其经济根源。在很多时候,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身份政治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它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运作的。比起争论阶级地位和身份政治何者更重要,了解这两者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要有意义得多。……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在真实的生活中是如何相互交织的。”(97)Alethia Jones, “Identity Politics: Part of a Reinvigorated Class Politics”, New Labor Forum, 19. 2 (Spring 2010),pp.12-15.对于身份政治,必须做出客观的评价。
五、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的调和
身份政治起源于对启蒙普遍主义的反叛,(98)刘擎:《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8期。它建基于特殊主义,强调身份的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因此它与普遍主义的公民政治不可避免地存在紧张和冲突关系。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
1.激进民主的公民。比利时政治理论家、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墨菲(Chantal Mouffe)提出一种激进民主的公民的方案。(99)Chantal Mouffe, ed.,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London: Verso, 1992.她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权利公民观”(citizenship as rights)只是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把所有“规范性”关怀都划入“私人道德领域”,使政治越来越丧失其伦理维度,仅仅关注既定利益之间的妥协。对墨菲而言,公民身份并不是自由主义所简约的“法定身份”(legal status),也不仅仅是享有法律保护、被动的权利拥有者,而是一种出于公共关怀、服从政治行动“语法”的政治身份。这一“语法”,就是“人人自由平等”的原则。只有遵循这一原则,围绕各种身份(女性、工人、黑人、同性恋者和生态主义者等)的政治运动才能关联、通约,具备激进民主的共通性,进而构成激进民主的公民。这样的公民身份并不是现成的或者被赋予的,而是“通过对公共关怀的认同行为来获得”。(100)Chantal Mouffe, ed.,“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London: Verso, 1992,p.235.公民是在各种社会运动的民主要求中所建构的一种集体性的政治身份,使各种批判性的社会力量结为联盟。墨菲对公民身份进行重新诠释和改造,她试图以新的公民政治概念把各种局部的甚至无关的社会运动集结、接合起来,形成最广泛的左翼政治联盟,从而争取激进民主力量的优势地位,在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之间建立联系。墨菲的这种激进民主的公民观,其实是针对当前的公民身份(而非身份政治)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在现实中,身份政治运动人士把“人人自由平等”仅仅作为口号,他们自己未必会遵从这一原则,各种围绕差异建立起来的亚身份群体所开展的身份政治运动往往难以通约。
2.差异性公民身份。多元文化主义与“差异政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艾利斯·杨(Iris M.Young)在其《政治与群体差异:对普世性公民观理想的批判》一文中,提出“差异性公民身份”(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的主张。(101)Iris M.Young,“Polity and Group Difference: A Critique of the Ideal of Universal Citizenship”,Ethics,1989, 99(2),pp.250-274.她批评道,那种超越群体差异的普遍主义公民观是不正义的,也是虚妄的、欺人的,因为在现存的社会中某些群体始终享有特权,而其他群体却受到各种各样的压迫,她一一阐述了剥削、边缘化、无力状态、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暴力与骚扰等压迫形式。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如果坚持主张作为公民的人们应当抛开他们独特的归属关系和经验而采纳一种普遍的观念,那就只会加强特权。因为特权者的观点和利益会在统一的公众中占据支配地位,而其他群体的观点和利益却会被边缘化而没有发言权”。(102)Iris M.Young,“Polity and Group Difference: A Critique of the Ideal of Universal Citizenship”,Ethics, 1989, 99(2),pp.257.她认为,“实现普世性公民理想的企图,就是将公众具体化为与特殊性相对立的一般性,与差异性相对立的同质性,这将使得一些群体被排斥或处于不利之境地,即使他们拥有形式上平等的公民身份”。让每个社会成员获得平等的尊重与对待是公民政治的目标,而要达成这种目标,要求我们首先承认和重视群体的差异;忽视、掩盖乃至抹去这种差异的“一视同仁”或“无差别对待”,反而背离了这一目标。对于她而言,“所谓差异是指各个社会群体固有的特殊性(particularities),也就是说,差异是不可被删减以达成统一性或不可被归为单一性的”。(103)Iris M.Young, “The Ideal of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Vol.12, 1986,p.4.因此,追求真正的平等政治,需要我们承认群体差异,认真对待他们的不利处境和特殊需求。为此,她提出,对于那些在文化上被排斥的群体,建立有效的制度性机制,以解决其需要的平等承认和平等代表的问题;同时,提供有效的支持性政策,来满足他们特殊的诸如在语言和习俗等方面的文化诉求。事实上,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确也是按照艾利斯·杨的主张去做的,但是在实践上,它要么做得不够,要么做得过多,以致无法真正实现平等政治。例如,在美国,针对黑人就业的优惠政策往往因此而遭致诟病。所以,针对这些被边缘甚或被排斥群体的特惠制度和政策必须在“差异性”和“普世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然而,这种平衡在具体实践中又往往难以把握得恰到好处。
3.求同存异。针对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之间的冲突,政治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求同存异”的方案,它强调“求政治之同、存文化之异”。它认为,在政治意义上共同的公民身份应优先于其他群体或个人身份,尽管每个人可能具有多重身份,可能归属多种群体。这种思路最典型地体现在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B.Rawls)对两类身份的区分之中,即作为公民的“公共身份”(public identity)以及作为私人个体的“非公共身份”(nonpublic identity)。但是,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做截然分离,并试图将群体身份完全限制在私人领域,这种做法既比较老套、“传统”,在许多情况下又是不可能做到的。尤其是进入后现代社会,原本比较清晰的公私领域的边界越发模糊,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身份认同及其权利要求已经进入了公共领域,身份政治亦由此兴起。因此,这种政治自由主义方案遭到了从激进的左翼政治到保守的社群主义理论的批判。当下西方社会的政治现实是,各种差异化、独异性的身份群体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诉求,并活跃在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议题之中。
4.重返公民政治。对左派与自由派沉湎于身份政治,马克·里拉(Mark Lilla)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鼓励和放任多元文化主义,过分强调文化身份多元差异,会对民主政治带来巨大威胁。以特殊主义的身份论述来塑造政治,无论在道德上多么有价值,在现实政治中,尤其就选举政治的竞争策略而言,是极不明智的。诉诸公民的共同性和社会团结,而不是强调各个特殊群体的独特差异,在当今美国变得至关重要。为此,他呼吁从身份政治的歧途中迷途知返,重返公民政治——强调基于普遍平等与自由权利的共享公民身份,并重视绝大多数人关切的问题。他对未来自由派政治提出“三种优先性”的建设性主张,即“制度政治优先于运动政治”“民主的说服优先于盲目的自我表达”“公民身份优先于族群或个人身份”,并提倡在校园中展开“公民教育”。马克·里拉的主张跟艾利斯·杨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
霍布斯鲍姆也曾提出,在单一的国家之内,存在一种包容性(comprehensive)的身份政治形式——公民民族主义(citizen nationalism),它建立在一种共同诉求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或者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至少作为想象是真实的和可欲的。(104)Eric Hobsbawm,“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Left”,New Left Review, I/217(May, June)1996,p.45.
福山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认为,若左派和右派的议程都转向保障更狭窄的群体的身份认同,那最终会危害沟通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这种情况的解方不是抛弃身份认同的理念——现代人已太习惯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思考自己和周遭社会了——而是定义出范围更大且更具整合性的国族认同,充分考量现有自由民主社会的实际多元性。(105)[美]法兰西斯·福山:《身份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认同与尊严的斗争为何席卷当代世界?》,洪世民译。他开出的药方是,美国应重新围绕其核心价值观,确立一种超越种族、民族或宗教差异的“信念式国民身份”,并通过公民教育等方式推动移民和其他族裔的同化。(106)[美]弗朗西斯·福山:《信念式国民身份——应对身份政治带来的民主危机》,甄成、张淦译,《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11期。然而问题是,当经济上的不平等得不到解决,当身份背后的阶级利益冲突无法调和,所谓构建“信念式国民身份”,不过是企图以一种新的身份政治运动来解决当前身份政治问题的饮鸩止渴式方案而已。(107)陈金英:《美国政治中的身份政治问题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通过对身份政治和契约政治的历史比较分析,我国政治学者任剑涛认为,身份政治是一种瓦解性政治,而不是聚合性政治,因其销蚀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安排的社会整体认受性,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西方现代政治大厦;身份政治以群体差异性为奠基,无法有效整合一国之内的公民身份,不能成为现代政治的有效引导力量,它对西方主流民主政治的消解作用不容小觑。为此,他提出“重申契约政治”。也就是,将公民与国家的政治立约作为人们介入公共生活、国家事务和社会政策的根本遵循,保障公民精神在公共治理中的核心地位。(108)任剑涛:《在契约与身份之间:身份政治及其出路》,《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任剑涛所提出的重返契约政治的主张,实际上仍旧是以公民政治取代身份政治的一种“传统”方案。
5.调和论。我国政治学者刘擎针对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的紧张和冲突问题,提出“调和论”。一是进一步发掘公民政治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兼容性。身份政治将自身的特殊诉求表达为公民政治的一部分,同时,公民政治积极吸纳这种差异政治的诉求,寻求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这些差异及其需要的特殊待遇。二是主张“差异化地对待差异”的原则。区别正当的与非正当的差异性诉求,对正当与合法的差异性诉求建立优先性排序,并不是所有正当的特殊要求都具有同等的优先性。三是批判性地反思身份与身份政治的极端化。群体的特殊性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必须被纳入民主政治的规范性视野中予以考察和判断。四是身份政治在实践中应当尽可能地将自身诉求的特殊语言“转译”为公民政治的语言或其可理解的语言。(109)刘擎:《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8期。其中,“差异化地对待差异”的原则富有创见,可是在实际中较难操作化。从这些论述来看,刘擎的调和论,实际上仍然是以公民政治为本,将身份政治的某些合理性诉求吸纳到公民政治之中,建构一种更加具有弹性或包容性的公民政治。
上述这些对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的调和的主张或解决方案,实际上建基于对身份政治、公民政治以及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之上:有的认为二者之间是可以协商的,有的则认为二者是对立的;有的用公民政治来包容或整合身份政治,有的则强调身份政治的差异性独特价值;有的主张重返传统的公民政治,有的则主张激进的后现代身份政治。总之,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能不能调和以及如何调和,仍然有待于未来的政治理论的创新来解答和政治实践的发展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