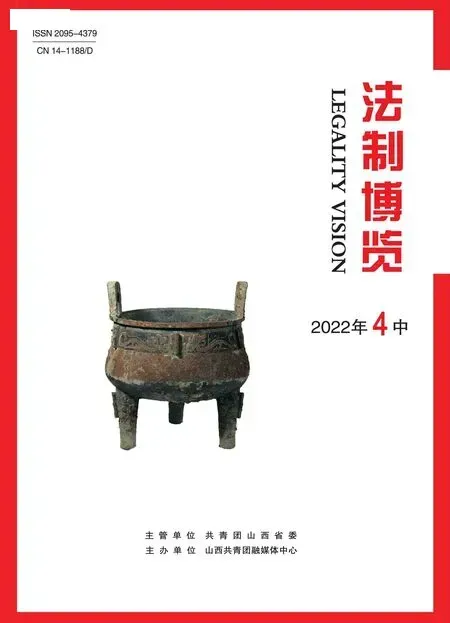企业以员工伪造的材料提起诉讼保全的过错分析及责任认定
程加干
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江苏 无锡 214028
设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胜诉判决或调解债权得以实现,这对保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能敦促被保全的当事人积极参加诉讼,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诉讼程序的推进。但在个别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恶意诉讼、恶意保全,或即便非恶意,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失,相关的财产保全行为极易对对方当事人的生活、工作以及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我们既要保护一方当事人采取正当保全行为的权利,也要规范当事人的保全行为,保护对方当事人的生产、生活不受不当影响。本文拟结合具体案例,尝试对诉讼保全行为的过错进行分析,并对责任认定问题予以探讨。
一、简要案情及观点争议
2016年1月,A公司与B公司签订设备合同1份,约定B公司向A公司购买激光切割设备2套,总价175万元。双方在末页均盖有合同专用章,B公司的盖章时间为2016年1月16日,A公司的盖章时间为2016年1月18日。合同共3页,双方于每页侧边均骑缝加盖合同专用章。
合同签订后,B公司应A公司原总经理李某要求于2016年1月18日向C商行开具转账支票2份,面额合计525000元,上述款项于2016年1月22日入账。2016年1月18日,A公司向B公司出具收条1份,载明其收到B公司支付预付款525000元。后A公司向B公司发送了两台设备,后双方因故于2016年9月20日签署退货协议,协商解除设备买卖合同,A公司向B公司退还预付款,B公司将A公司已发货的两台设备退回。
因A公司面临收购,为增加账面应收款,总经理李某以上述合同为基础伪造了相关交易材料。此后,李某涉嫌挪用资金,被依法判处刑罚。2018年,A公司在内审中发现上述交易相关材料,便提起诉讼,并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对B公司进行财产保全200万元,法院依法冻结了B公司银行存款200万元。B公司知悉被诉讼保全后,立即提出抗辩,表示相关合同已解除,其并不欠A公司货款,为此,B公司提供设备合同及退货沟通往来文件等证据,证明合同订立与解除的完整过程。但A公司坚持诉讼保全。审理中,法院向李某进行调查,李某称B公司向A公司购买过2台平面切割设备,本案合同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但前2页被其更改过。当时为了增加公司账面应收款,其更改为三维设备。但后B公司将2台设备退货,A公司也退还了货款。B公司的货款共计80万元左右,其中有30万元左右是更改后合同的预付款。2018年11月30日,李某另出具情况说明1份,载明A公司与B公司共签订过两份平面切割设备的合同,A公司现存的合同是其修改后的合同,其修改为2台三维设备,首页换样,末页签字是原合同的。预付款三十万左右系其垫付,该2台设备并未发货,A公司的验收单也是不真实的。因A公司提供的证据存在缺页、日期模糊,且没有相应送货单、验收单等瑕疵,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述判决生效后,B公司以A公司恶意诉讼保全,导致B公司资金被冻结,造成较大损失为由,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A公司赔偿其因诉讼财产保全行为造成的损失20万元。
对本案如何处理,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A公司工作人员伪造证据,A公司并不知情,A公司也是受害者,其依据现有的证据,在误解事实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是合法的,不应当承担财产保全损害赔偿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A公司以员工伪造的证据,在未经严格审查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财产保全损害赔偿责任。
二、正确理解并科学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保全错误的法律规定
讨论如何对A公司的诉讼保全行为进行过错以及责任分析,关键要对诉讼财产保全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正确理解。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这是程序法在申请人的诉讼财产保全行为发生错误时,对申请人负有赔偿责任的法律警示。但《民事诉讼法》毕竟是程序法,在审理诉讼财产保全损害赔偿责任案件中,对责任构成要件,特别是申请人过错如何认定需要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和理论,结合诉讼保全行为的特殊性,对具体案件中诉讼保全损害责任进行定性、分析。[1]
(一)要准确理解保全“错误”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过错”的区别与联系。《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表述的“错误”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过错”的语境、含义是否完全相同?为何不用“过错”替代?如果替代,则表述变为“申请有过错的”,语句不顺,原因在于过错是对人的评价,若使用“过错”一词,则正确的表述方法为“申请人有过错的,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遭受的损失”。如此替代之后,两句话的意思,出现了很大变化。可见,“过错”与“错误”两词虽无本质上的差别,但过错着重从行为人的动机方面、主观方面,对行为人进行可责性判断,重在评价人之“过”,行为人的善意与恶意对归责有重大影响。而“错误”之表述,似乎并不十分注重对行为人的动机进行价值判断,而是更关注行为的对象、方式、后果方面是否正确、合适,因此对行为的判断更加注重客观方面,根据法条的表述,只要“申请”出现“错误”,就要承担责任。在大部分情况下对此区分没有太大意义,但对诉讼保全损害赔偿案件的责任认定则是必要的,在申请人恶意进行错误保全的情况下,其担责自无需赘论,但在很多情况下,申请人似乎并无太大的恶意,恶意的诉讼保全行为可能发生错误,从而需要承担责任,非恶意的诉讼保全行为也有可能发生错误,造成他人损失,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二)要将诉讼保全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区别开来。一般侵权行为发生于公民的社会生活生产过程中,除去特殊行业对行为人注意义务的特别严格要求之外,大部分情况下,法律对行为人注意义务的要求是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而诉讼保全行为有所不同,其系当事人双方发生纠纷不能自主协商的情况下,进入到诉讼程序以后所为的一种诉讼行为,诉讼行为应当是更加严肃、谨慎、负责、适当的,且诉讼行为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所以不能将申请人进行诉讼保全行为的注意义务降低到一般人进行一般行为时的注意义务。但笔者亦不认同诉讼保全损害赔偿责任系无过错责任,因为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条规定,无过错责任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显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均未规定诉讼保全损害赔偿责任为无过错责任。因此,诉讼保全损害赔偿责任仍是过错责任,但对过错进行认定时,应当对申请人的注意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诉讼保全损害赔偿责任仍是过错责任,但对过错进行认定时,应当对申请人的注意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既要考量实际情况又要独立于前案的判决结果,来对诉讼保全行为的对与错进行评价。实践中,诉讼保全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起诉,往往提起于前案保全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或者大部分驳回之后,少见在保全申请人前案的诉讼请求得以全部支持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提起诉讼保全损害赔偿纠纷。可见,相当一部分人将诉讼保全错误与否与前案的裁判结果进行了绝对的挂钩,前案胜诉的保全就正确,前案败诉则保全就错误。事实上,前案与后案的裁判逻辑不同。前案审查申请人的债权主张是否合法,后案则审查申请人保全行为是否合法,保全金额和保全方式是否适当。①河北法院参阅案例第1号-《河北金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国兴环球土地整理开发有限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中心支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2020年11月3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34次会议讨论通过)。前后案件之间虽有联系,但非完全对等。虽前案诉讼请求得以认定,但保全申请人采取的保全措施不当,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也可以认定保全行为存在错误。虽前案诉讼请求未得以支持,但申请人进行了必要且适当的诉讼保全,也不宜认定为保全错误。因此,前案裁判结果对保全错误的认定确实存在较大影响,但绝非保全错误的认定完全等同于前案的裁判,两者的审查要素是不同的。
前案的案件类型、复杂程度对保全错误的认定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在一些极简单的民间借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法律关系简单、债权金额易确定,申请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不享有债权,但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故意提起诉讼、申请保全,损害被保全人的财产权益的,自然容易认定为保全错误。但在法律关系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类型中,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举证能力存在较大关系,对申请人保全错误的认定则不应苛刻。
(四)要有平衡保护申请人的胜诉债权和被申请人的财产安宁及自由权的理念。诉讼保全制度旨在通过限制被申请人处置财产的自由,达到保护申请人将来可能存在的胜诉债权,但诉讼保全行为限制被申请人处置财产的自由,对被申请人财产权益也会造成损害。申请诉讼保全时,申请人的债权尚不确定,因此诉讼保全保护的是申请人不确定的债权,故在审理财产保全损害责任案件中,既要维护诉讼保全制度的宗旨,又要体现对被申请人财产安宁和自由权利的关切。既非申请人提供担保即可肆意限制他人财产,亦非一旦保全与胜诉债权不相匹配就要赔偿,打击债权人的维权积极性。关键要提倡严肃、谨慎、诚信、适当的诉讼保全理念。[2]
三、单位对员工伪造证据,未经严格审查即起诉保全,构成过错应当担责
根据前述分析,结合本案的案情,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即A公司以员工伪造的证据,在未经严格审查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财产保全损害赔偿责任,理由如下:
(一)A公司依据其自己工作人员伪造的证据进行起诉并非其免责的理由。一方面,本案审查的是A公司诉讼保全行为,而非李某伪造合同行为对债权的影响,李某伪造合同材料行为并不必然导致A公司错误起诉、错误保全,是否起诉、是否保全的决定权在A公司,行为人是A公司,A公司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另一方面,法人系一个整体性的组织,其工作人员系组织的一部分,李某伪造合同等材料的行为,对外所产生的后果不能独立于A公司,A公司应当为李某的行为对外负责。
(二)A公司提起诉讼、申请保全不够严肃、谨慎,未尽到注意义务。虽然李某系A公司总经理,但人格上并未独立于A公司,A公司对李某的行为仍有管理职责,A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合同材料系伪造。即便A公司不知道李某伪造合同的具体事实,但是A公司在诉讼时不持有合同原件,且所持的合同复印件存在明显瑕疵,加之其知道李某存在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其应当审慎地审查相关交易材料,甚至仅需通过与B公司联系沟通合同履行事宜,即可知晓李某伪造合同事实的存在。但A公司在证据瑕疵明显的情况下,未审查是否存在真实交易,便提起民事诉讼,并且保全B公司大额财产,在B公司提出抗辩、指出问题的情况下,仍不审视相关证据,A公司对其诉讼保全行为不够审慎,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三)A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符合基本的公平正义。公民和法人享有财产安宁和自由的权利,A公司由于对内部工作人员疏于管理,对重要的交易材料疏于审查,对严肃的民事诉讼行为不够谨慎,在稍加注意的情况下,就可以避免保全B公司财产,A公司对其诉讼和保全行为存在过错,而B公司对此无过错,若其凭空遭受损失,而侵权行为人A公司不能予以赔偿,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事人申请诉讼保全行为应当本着合法、诚信、谨慎、必要之原则,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因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申请行为的过错与否进行认定时,应当从上述几个方面综合考量,以分析申请人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在企业提起的诉讼中,相关证据多为工作人员与他方在交易中形成,企业对员工的对外交易行为负责,对员工伪造的虚假交易材料亦应当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并本着诚信的商业交往原则,与相对方进行沟通,从而避免错误诉讼、错误保全。否则,应当就相关诉讼财产保险行为造成对方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