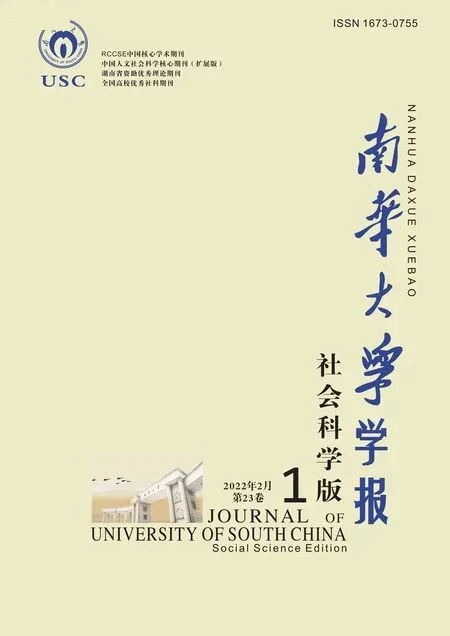王夫之对传统忠孝伦理下君臣关系的消解与重构
何小英,高卓亚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0)
早期中国的社会形态呈现出强烈的血缘化、内聚化的特点,进而形成了各级血缘性氏族、家族,以及按照“各祀其宗”“家自为祭”为主的等级化、血缘化、宗教化的文化传统。这些都对中国原初社会国家的基础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
建立在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之上的家庭结构,成为“家天下”构建国家结构的既有范式。通俗来讲,国是家的外向延伸与拓展,国与家二者的类似构架直接突出了君臣父子的秩序。家国同构的渊源让君主直接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家长制形态的“大家长”,家庭伦理的基本准则——孝,也随之映射入社会政治层面成为最高道德——忠,忠与孝为主体的伦理道德,也伴随氏族公社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成为影响深远的、具有绝对支配地位的伦理道德。忠孝伦理从某种意义上成为古代中国维系政治活动正常运行的准则,其必然导致政治活动运行受到君主个人的道德水平限制的现象。“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表面上推行“德治”,实际上真正贤能的人才很难成为君主的心腹,或者是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国家的权力中枢往往掌握在一群内心猥琐、行为下贱、思想顽愚的不肖者手中。基于对中国历代政治演变和发展的考证,目睹明王朝覆灭的王夫之,对“家天下”君主专制背后传统忠孝伦理体系暴露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深刻的认识。王夫之“哀其所败,原其所剧”,他对用以维系君主专制制度的私忠伦理的批判,也是对忠孝伦理体系君臣父子的重新构建,反映了中国的旧政治和旧经济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进步。
一 家国殊等:对传统君臣关系的消解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的独断地位,废除了与皇权制约抗衡的宰相制度,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制度兼管六部,形成国家君主一人提携天下的局面,从而也加重了对君主道德的期待。制约皇权的严密制度一经打破,让曾经用来判断道德善恶的标准也可以对政治的善恶进行评判,两个标准的趋同或同一,使道德伦理真正贯穿于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
君主与臣子之间没有了缓冲地带,臣子直接面对君主,究其本质而言二者都是凡人,仁君圣主并非政治社会的常态,趋利避害、趋生避死是人性的常态,“逢君之隐志”也就会成为臣子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常态。“若将忘祸福以抒忠,实则迎合希求为登科之捷径,端人正士固耻为之”[1],王夫之认为,如果只是将民族危亡、社会祸福作为迎合奉承的辞令,借此获得个人的利益,是正人君子为之不齿的事情。臣子寄希望于君主道德的自我形成,不如君臣之间构成互相约束,以臣子为主体达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臣子需要认识到君主权力的非神性,恪尽职守,勇于对事态表达负责任的观点;君主用心体察臣子意见的合理性,不以个人好恶而因人废言,积极采纳臣子的合理性建议。
自古以来,儒家都是简单强调臣子当以事父的态度事君,“畏大人”“为尊者讳”,既是父子关系的规范,也是君臣关系的规范,甚至也是官僚等级关系中的规范。只有“责任”与“义务”,没有“尊重”和“权力”的封建家长制宗族家庭,孝作为独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处于缺失状态,导致社会政治层面的忠,只是简单粗暴的“移孝作忠”处理,将专制政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绝对化。“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类扼杀人性、束缚个体自由的封建伦理,只能成为进一步强化封建君主专制的帮凶。“积乱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国无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岂易言哉?”王夫之坚决反对以事父的态度事君,忠孝伦理置于君臣关系层面之上的做法,已经拆解了忠与孝的捆绑。子对父的“孝”由于血缘存在无法割裂的绝对化人身依附关系,但是臣对君的“忠”需要君臣二者拥有独立人格和觉醒意识的主体。换言之就是“忠”不应是专制体制范围内对君主个人的忠诚,而是对君主所代表的民族与国家的忠诚。王夫之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忠孝伦理中二者的差异,这已经闪烁着近代启蒙思想的光芒。孝是构建家庭生活所产生的伦理德性,是自觉自然的,“事亲”是人生而有之的本性使然,是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和责任意识的体现。同样在道德与责任的共同作用下,臣子对君主所代表的民族与国家的尽忠,保证忠的对象以“公”的形式存在,这就进一步否定了君臣的主仆关系,“夫君子出身以任人国家之事,进以当宾友为礼,退以保明哲之身;所守者道也,所重者耻也,所惜者名也”[2],臣子的负责对象是民族、国家,而非君主个人,君臣之间应当以平等的关系交往,一个有尊严有个体意志的臣子,其进退的底线应该是心中的道与身后的名。臣子要用对君主个人的态度,保证现实层面无宰相约束的君主的道德约束。
天下之兴亡,并非一姓之更替,治乱就应该是君主对民族、国家尽忠的标准,即万民的忧乐成为评判君主的准则。君主应以万民的私利为私利,当万民的生命和民族的生存成为其最高的价值准则时,民族观念就被激发和激励,万民生死自然就高于一姓的兴亡。王夫之认为,“不以天下私一人”的重要前提是还天下于“公”,即君主并非天下的所有者。“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兴亡之修短有恒数,苟易姓而无原野流血之惨,则轻授他人而民不病”[3]57,王夫之由此提出“家国殊等”的主张。“家国殊等”的第一层含义并不是将家庭层面因血缘亲属产生的道德伦理直接运用到政治层面,因此“推教家以教国”的“推”重点不是朱子在性本体上的推理展开,也不是阳明在心本体上的扩展,而是以“性情会通”为基础,以“同命于天,同率于性”为开端,将天道“生生”超越善恶的绝对价值,转换为具有“继善”意义的人道实践。换言之,在王夫之看来,家庭人伦的“性情”是人道承袭天道的“继善”倾向,而不是对天道简单的服从复制,“先天之性天成之,后天之性习成之”,人道需要在“习”(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家”与“国”不是在不同层次上的重复,而是具有实践倾向性在具体条件下“分殊”,是抽象的“继善”差异化作用的体现。“孝弟慈”作为人道的实践原则不能直接用来搭建政治活动生活所需的秩序,因此用来处理家庭生活秩序的“孝弟慈”而产生的“善”,并不能直接作用于政治秩序。政治秩序追求的是对社会各个部分的“上下、前后、左右皆一矩絜之而得其平”[3]57,换言之“推教家以教国”的“推”重点是强调人道实践由家庭层面到国家层面推扩过程中必然带来的差异。王夫之借用舜的“孝”德贯彻在家庭与政治两种层面带来的不同效果,进一步说明“政治秩序需要追求实在有效的治理效果”[4]造成的差异。“如舜之事父母,必至于‘烝烝乂不格奸’,而后自谓可以为人子。其求于天下之孝者,亦不过服劳奉养之不匮而已。”[5]34舜是儒家个体德性进入圣人境界的代表,他用孝德感化自己的父母兄弟,从而达到个体自主生发出的“善”,并反过来作用于个体自身,形成德性自律,就此而言,“孝”确实可以在“身—家”层面以伦理的方式达成教化的目的。但是如果直接“推教家以教国”,在“国—天下”的政治实践中依然奉行“孝”德的伦理原则追求治理效果,即便是作为圣人的舜,也只能止步于以民的生存为准绳的“服劳奉养之不匮”。因为是由家庭伦理简单推论而来的个体道德启蒙,不符合“国—天下”的政治层面的教化目的。王夫之认为“国教在政而政皆教”,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中,教化同样是政治的目标,实现政治教化则需要从政治本身着眼,即关注以人为整体的社会的整体协调。
“家国殊等”体现了王夫之对传统君臣关系的消解,家庭层面的伦理德性不能作为家国天下的本体,君主只是民族、国家的具象化代言人,在政治社会里同样处于臣子的地位,代言人的更换不应以万民的生命作为代价,更不能假借道德的名义毁灭道德。
二 环相为治:公忠伦理的制度保障
建立以公忠伦理为基点的政治运行模式,其实质在于如何利用权力制约权力,特别是如何对君权实行有效的制约。民族国家的良性发展必须防止权力的腐败,尤其要认识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关键问题。杜绝执政者个人道德品行对国家政治优劣的影响,以往的儒家学者“推教家以教国”,他们建立的私忠伦理只是在如何维护道德礼教上用心思,他们将民族国家的命运简单寄托在君主的道德修养上,认为只要君主加强道德修养就可以维持民族国家的正常发展。其结果就是,奸诈者用道德作为沽名钓誉、争权夺利的手段,迂腐者则因为意气用事、自取其辱,成为专制强权的牺牲品,进而动摇政治的运行,影响民族国家的命运。王夫之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君臣关系不摒弃传统封建君主专制下的私忠,消解君主权利的根基——“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引申出公忠的概念,那些琐屑的道德礼教争斗只会祸国殃民。
为了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制约,同时也为了对君主的个人道德进行约束和修正。“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王夫之提出了“君、相、谏官”三者“环相为治”的顶层制度构建。尽可能地对君权进行限制,依靠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防止因为君主个人道德水平的局限破坏政治活动的正常运行。从明王朝的总体政局出发,“环相为治”的政治权力设置同样切合当时历史实际,有利于保证政府权力对公忠的负责。宰相的即废权力在君主,六科给事中分别与内阁六部相互制衡,“巨奸且托台谏以登庸”,而阁臣又借助君主的威严对其进行打击报复,导致官僚腐败加剧,民众利益受损,国家民族面临生存危机,只有监察权的谏官与政府官员争斗不休。明太祖废除宰相,罢免门下省长官,却单独留存六科给事中,其目的并非为了让六科给事中行使封驳权,恰恰是为了稳固君主大权独揽的局面,利用品级低下却手持重权的六科给事中与内阁六部大臣相互牵制的局面,防止大臣专权篡位的局面出现。因此王夫之反复强调,“谏官者,以绳纠天子,而非以绳纠宰相者也。”
关于“君、相、谏官”三者之间的关系,王夫之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君主以道德自律、言行操守,行使考察、选拔和罢免,王夫之认为宰相的设置是君主明察奸贤、洞悉民志的必要方式,遴选出一个贤明的宰相是成为贤明君主的先决条件。宰相在行使相权时既要考虑到国家社稷的安危,又要考核百官的操行,更要对万民的忧乐直接负责。宰相对君主行为品德的过失也要及时予以指正,“弼正天子之衍”;在监察他人的同时也要及时自查自省,以国家社稷和万民安危自觉进退。宰相的任命与去留虽然由君主直接决断,但宰相在“君、相、谏官”三者之间处于中枢,对上制约君主权力,对下携领百官,为百官表率。王夫之所处的时代还是无法摆脱人治的政治社会,但是宰职的设置在最大程度上限制了君主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力。谏官的职能也是两方面的,王夫之认为,谏官既可以通过发表言论在君主任命宰相的人选上同时挟持君主与宰相,也可以直接对君权和相权进行监督,纠正两者道德或行为的偏弊。
处于“君、相、谏官”三者中枢的宰相人员的选定就变得尤为重要。以人治为主的封建政治社会,无法摆脱人性本身的限制。“环相而治”的前提就是要摒弃程朱学说中的固化君臣关系,即君臣天赋关系不可改变的绝对,充分肯定“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王夫之在设计这一顶层架构时已经认识到君主的人性弊端,为了防止君主凭借个人好恶和小人刻意谄媚逢迎导致宰相之职落入非人之手,“故谏官以其犯颜无讳之危言,绳之于早,纠之于微”[5]81,宰相的人选得以任用,“木不腐而蠹不生,形不污而影不黯”[5]81。除了在宰相任命方面防止君主独断专权的情况发生外,谏官与宰相的职能也有互补之处,如有宰相无法行使其职能的情况发生,谏官可以直接对君主违背道德的决断实行直接封驳。宰相虽然对君主的道德操行直接监督,但是由于其选拔的特殊性与困难性,且宰相需要在国家社稷、生民安危层面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导致其不便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直接与君主发生争执。这就需要谏官的介入,王夫之对为臣之道的界定有“一谏而善道之,再谏而易言之,三谏而危言之;然而终不庸焉,则引身以退”[5]122,意思是如果谏官对君主再三谏言却无法被采纳,则需要毅然决然的辞官身退以保全自身的气节。但是宰相选拔的不易性导致其不能轻易辞职,所以王夫之在此借用了唐代谏官隶属宰相、接受宰相领导的模式,有效避免了宰相与谏官之间的政治内耗,进而确保二者对国家民族、生民百姓的公忠。
王夫之认识到了权力的腐败是由权力的绝对性所导致;认识到了绕过完善的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只是简单依靠对君主个人道德操守的约束,是不可能保证“君、相、谏官”三者公忠的现实。王夫之将改良甚至改革的重点指向权力机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提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臣子并不是君主可以任意驱遣的家奴,与君主是宾友的关系”[6],并引申出公忠的伦理概念,是其在忠孝伦理体系君臣父子关系重新构建上的重要贡献。
三 有天子而若无:忠孝伦理体系重新构建
中国传统封建君主专制作为单一中心的专制体制,其权力中心的更迭大多伴随着无辜者的枯骨和国家的动荡,王夫之在总结中国历史上政权变更与国家治乱的关系后,深刻认识到国家社会的长久稳定和兴盛必须建立在“置天子于有无之外”的基础之上。切断君主演替与国家政权更替之间的直接联系,国家机器的运行不以君主个人为转移,这类似现代民主法制社会政党轮替又不影响社会稳定,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还可以正常运转。王夫之所处的时代而导致的历史局限性让他无法真正洞察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完整运作方式,但是“有天子而若无”却从另一个方面间接提出了抛弃君主的人治局限,假定一个高于君主的权威存在。反对绝对君权的“私天下”,倡导“有天子而若无”的“公天下”,是王夫之政治思想的核心,这一观点与现代“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根本精神实质是相通的。
传统专制制度下,绝对君权的“私忠”对象是具体化的君主本身,而王夫之倡导的“有天子而若无”,则将具象化的权力代表——君主,抽象为由天子所代表的民族国家。“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一部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国政治史,乃是一部以天下为“一姓之私”[7]的政治史,为帝王君主者,不是“盗贼”,就是“夷狄”,都是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这种“一姓之私”的统治,何以言“公”!君主专制制度必然造成君主的极端自私自利和短视,“忌天下之贤而驱之以不肖”,其结果必然是“毒流天下”,导致“身戮国亡”的可耻结局。在强调了“私天下”的种种弊端之后,王夫之提出实现“有天子之若无(虚君)”,即构建公忠伦理体系的两个关键环节。
(一)分权制衡:削弱君主的绝对权力
在王夫之看来,宋亡于蒙古、明亡与满清,其根本原因是帝王收天下之权于一人之手,“以一人疑天下”。究其原因,地方政府徒有其表,没有实质权力,导致命令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各个环节相互推诿懈怠,互相掣肘,直接禁锢了汉民族,其自身无法实现自我巩固。对此王夫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设想,主张明确并限制中央一级的权力,扩大州、县等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尤其是县一级直接接触民众的政府机构。“唯县令之卑也近于民,可以达民之甘苦而系其情伪”,利用县级官员“近于民”的便利,从而对辖区的民众直接负责;州郡一级政府之权在于“察受之张弛宽猛而节其行政”,即管辖所治的县级长官,考察其德性操守与政绩。王夫之认为导致“懦民益困而国必亡”的结果,就是皇帝和州郡长官越过县官对民众直接管辖,“以天子下统乎天下,则天下乱”。
王夫之为了实现汉民族的自我巩固所提出的分权治理思想,其本质就是对绝对君权的反对,对“私天下”的反对,从权力结构上对君主个人的绝对权力进行限制,为“虚君”构建权力框架。秦废分封立郡县“以私天下之心而成天下之公”,是顺应时代的要求,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高度集权的绝对君权已经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阻碍。宋因专制集权而被蒙古政权颠覆,明王朝因为同样的原因导致满清入主中原,所以在王夫之看来,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加强地方的自治,“莫若分兵民而专其治,散列藩辅而制其用”,是捍卫民族生存,在民族遭受外地入侵时能够组织起有效抵抗的制度保证。
(二)“有道在此”:国家法度之下的君主
王夫之同时提出“有道在此”的假设来强化“有天子而若无”。用法律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制约,“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君主的不法行为同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在君臣关系的重构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王夫之看来,法律是联系君臣之间的纽带,君臣上下必须以道相临,坚决杜绝下对上的财物进贡,即绝“以财相接”之交,“绝交而后法伸,法伸而后道建”。权力机关“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法律对民众百姓、民族国家负责,维护民众百姓的利益,维持民族国家的稳定。王夫之借用晋明帝的例子进一步阐述法律对构建公忠伦理的重要意义。晋明帝临死前面对继任者的年幼,安排了大臣辅政,授予大臣代替君主行使相应的权力,增加了政治风险。王夫之认为,如果在君主的权威之上架设一个更高的非人的制度,不因君主的变更而变化,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延续,就可以避免人治所带来的弊端。“守典章以使百工各钦其职”,“典章”即法度,法度的权威高于君主的权威,法度之下众生皆平等;“百工”即公仆,将君主列入公仆的范围,同样是强调君主只是权力行使的代言人,集中表达生民的意志,杜绝君主因个人的条件限制做出扰乱政治社会的决策。王夫之指出国家权力的绝对中心化是导致社会动荡、国家政权频繁更迭的病灶所在,他清楚地认识到君主利用家国同构把血缘维系的孝伦理演化为情感责任链接的忠伦理,标榜“以孝治天下”致使家国不分,君父无异,主张臣民对君主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是对忠伦理的扭曲歪解。打破桎梏枷锁就必须“大反孤秦陋宋之为”,即打破君主专制的“家天下”,推行以法度为核心的“公天下”进而对国家、民族的公忠伦理才能得以构建。
如果说“有天子而若无”是“公天下”的体系保障,那么高于一切的法度就是“公天下”的制度保障。王夫之的“有道在此”的“道”就是法度,法度有别于法律,中国历代的专制王朝都有法律,王夫之提出的法度之上没有特权者或特权阶级可以肆意妄为,只有君主在法度的框架之下才有可能实现君主与臣子之间的平等,才能实现君主和臣子对国家民族的“公忠”。不能以事父的态度事君,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家族制的农业经济组织,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则是父权家长制和家族伦理的扩大和延伸。《尚书·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统治者是以民之父母的姿态出现的。“移忠作孝”“移悌作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反复强调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中国古代帝王推崇的“以孝治天下”,正是从父权家长制引申而来的。“孝乎为孝,是亦为政”,家与国不分;“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这成为正统儒家的基本的政治伦理信条。从“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进而延伸到“天下无不是的君”,正是王夫之严厉批评的主张——臣民必须对君主作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从天性之爱立论的弊病在于全然忽视了君臣关系的特殊性,父母有不是之处,生为人子不能割断与父母的血缘关系。君臣关系则不然,君主有不是之处,谏言未被采纳,为臣者可以离位而去,二者的关系也就随之消失。父权家长制引申而来的私忠,是论纲常、不论是非的畸形君臣观。为君者和为臣者内心都应存有国家民族的公忠,公忠伦理是二者平等关系的基础,即二者同为“百工”。王夫之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统中对君主道德的推崇,提出变“一家之法”为“天下之法”,用“有天子而若无”的理念构建政治与伦理分离的政治模式。
四 结 语
王夫之的公忠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人治”的专制统治,“有天子而若无”更是闪烁着“公天下”的思想光辉。与王夫之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或多或少都有“公天下”的政治构思,这就一定程度上证明王夫之公忠伦理思想有着进步性,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基础,从不同的侧面构成一种呼应形式。“这就揭去了‘君父臣子说’温情脉脉的血缘宗法外衣”[8]。李泽厚先生指出,正是明末清初的特殊时代背景,对“意向伦理”(道德动机)与“责任伦理”(现实效果)、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君权绝对性的质疑和君臣关系的平等化要求,正是王夫之认清了人际社会存在的矛盾仅仅依靠道德约束是无法调和的,传统伦理需要在政治、社会等不同领域细化拆分形成独立的形态,实现“中国式的‘政’(行政)‘教’(伦常教义)分离”[9]。王夫之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条件下,打破中国思想传统的桎梏,从传统儒家忠孝伦理中构建出“家国殊等”“环相而治”“虚君共和”的君臣伦理形态,极大地动摇了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伦理基础,是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分化的时代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