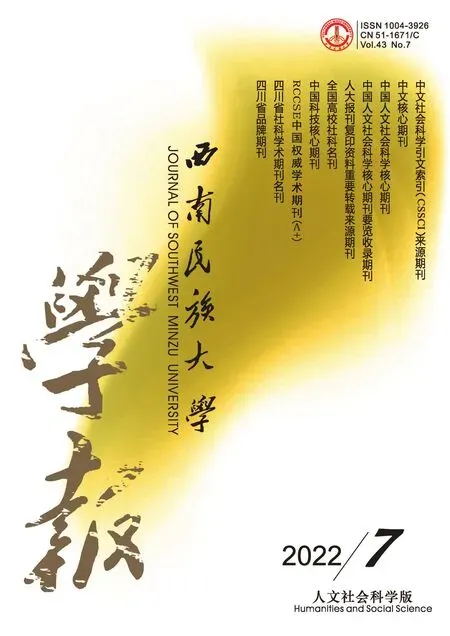中国艺术“以形写神”的美学蕴涵
汤凌云
[提要]中国艺术有“以形写神”的传统,儒释道心性论、形神观和言意观为此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形写神具有五层美学蕴涵:穷形尽相与艺术家的体物工夫有关,离不开对生活的观察和对物象的观照;传神写照是艺术创造的审美理想,有赖于审美情感的介入,需要创造意识发挥作用;随物赋形是对艺术形式法则的概括,落实在艺术家展现创造力的“写”的过程中;形神两忘指向心物交融、物我不二的审美境界,有意无意之间方为传神之妙;游戏笔墨是活泼自在、任运自然的审美情趣,在禅宗思想滋养下,艺术创造成为彰显自性的方式。以形写神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美学蕴涵和人文价值亟待传承与弘扬。
以形写神是中国艺术的审美传统之一。这一审美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经历过漫长的过程。中国早期艺术追求形似,重视对物象形体的模仿,强调“恶以戒世,善以示后”的社会教化作用。在顾恺之以前,“存形以寓教化”是人物画的主要功能,魏晋清谈盛行,“神”被纳入人物品藻范围,对人物美的关注重心从外物形体转向精神风姿。此后,人物画不再充当鉴戒工具,而更注重展露人的内心世界。在言意之辨语境下,魏晋南北朝文人重视赏玩山水之道,如宗炳讲“山水以形媚道”,从有限体证无限。魏晋至唐,以形写神在人物画领域全面展开。五代至北宋,随着山水花鸟画兴起,以形写神不再局限于人物画,而普遍渗入山水花鸟诸科。在宋人看来,理遍万物,体一分殊,天地万物曲尽其态,绘画能曲尽其态,传神为不二法门。传神不再专指人物画,山水、花鸟、景观等皆可成为传神对象。此后,明清小说戏曲繁荣,拓展了以形写神的表现空间,并为此注入了新的内涵,艺术审美实践和批评更趋丰富而深入。
以形写神深植于中国思想文化土壤,特别是受到儒释道心性论、形神观、言意观的滋养,且发展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形写神的审美传统与数千年以来的艺术创造和批评相呼应。中国艺术以形写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艺术门类有不同的体现,但也存在一些普遍性的理论特征,本文围绕以形写神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力图更加系统全面地揭示以形写神的美学蕴涵,以丰富与拓展对这一审美传统的认知。
一、穷形尽相
穷形尽相与艺术家的体物工夫有关。体物是以形写神的基础。从先秦儒家观物取象思维的形成,到宋明理学格物穷理思想的确立,都能见出穷形尽相的踪迹。它要求艺术创作之前细致体物,为传神创造条件。关于这一点,学界较为忽视,似有重提的必要。
《周易》把“神”规定为“阴阳不测”,而知变化之道;同时,先哲观物取象,依靠“形”来发挥象形作用——“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从生活世界可感之物出发,以卦象符号推演万物变化之道,由此揭示社会事理。《周易》主张道、器两分,器物与形体对应,精神与道体相连。就具体事物而言,形是神的基础,形具而神生。在荀子看来,人的身体结构就是一个小宇宙,作为完整的生命体,既有形体组织,又有精魂存焉。他主张“形神相俱”,以人定胜天、天人相分批判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并以“形具而神生”批判敬鬼神的传统,强调精神是形体的产物,依赖形体而存在。中国早期艺术受儒家观物取象、“形神相俱”思想的影响,强调艺术的象形效果和指事功能,因此,“形似”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和价值。唐宋以来,“形似”一词经常遭到文人艺术家鄙弃,被狭隘地指认为境界低下之作。这类观点也被当代学者所沿袭,“形似”成为批评的靶子,这样割裂了中国艺术史的完整性。回溯历史现场,仍有不少艺术批评家肯定“形似”的意义。为了实现写神的目标,陆机提出“穷形尽相”的说法。“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文赋》)此“形”主要指生活原型、物象形貌,而非艺术形式。他把细微描绘对象的形态特征作为目标,这可能与赋的文体特性相关。赋以铺陈之笔描绘事物的形态,需在体察物态或事理方面下工夫。文必极美,辞必尽丽。故刘勰主张感物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文心雕龙·物色》)。他列举诗词来形容植物、动物,如“皎日”“慧星”以言穷理,“参差”“沃若”以少总多,使情貌无遗。然而,物有定姿,而神思无穷,或灵感来袭,或殚思无果,因此,刘勰提倡“入兴贵闲,物色工繁,而析辞尚简”,面对季节时序更替,要追求“形似”,有赖于神思和情感发挥作用。刘勰认为情感是神用象通的结果,进而提出“拟容取心”“心以理应”等具体方法。
钟嵘论诗,也把“形似”作为诗歌批评标准之一,唐代论诗也重形似,如遍照金刚把“形似体”列为“十体”之一,“谓貌其形而得其似”。王昌龄以“物境”为诗歌“三境”其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诗格》)直至唐代,“形似”一直是艺术审美的理想,对于自然物的描绘尤其讲究逼真效果。
穷形尽相离不开艺术家对生活的观察和对物象的观照。就描绘物象而言,“体物”有着独特的要求。《文心雕龙·物色》谈景物描绘之文心,提出“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把“体物”作为“形似”的前提,并对其表现进行具体说明。追求形似,先要细致观察物体的形貌,把握其基本特征。杜甫《丹青引》评韩干“画马穷殊相”,是对其体物工夫的肯定,他还以“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评刘少府山水画,也是称赞画面意象生动逼真。牢笼百态,极尽形容,都是穷形尽相的体现。
对事物进行细致观察,对生活世界感受深切,才能穷形尽相。嘉陵江数百里山水,吴道子一日画成,主要是因为他对嘉陵江山水熟谙于心。宋代理学兴起,格物穷理成为致思的方向,也成为体物的目标。体物在理学语境下的宋代备受推重。宋代院画要求艺术家体物入微,如《宣和画谱》推崇唐忠柞、赵昌等的形神兼备之作,还记载了一些笔墨精工细致的画坛故事,宋人体物不再重复汉唐,而是融入对物性的感受和物理的追问。范宽画山水有得,他卜居终南、太华林麓,观云烟风月,“难状之景,默与神遇”,“谛视而熟察之”,寄于笔端,千岩万壑,如行山阴道中,时人称赞他善与山水传神。苏轼提出“胸有成竹”,郭熙呼吁画家“身即山川而取之”,认为“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林泉高致》)。王履《重为华山图序》:“画虽状形,主乎意,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虽然,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脱离“形”而空谈“意”,只会远离事物的面目。神在形外,形在神中,求神似于形外,取生意于形中。准确把握山川形貌,就得亲历自然山水,故而提倡“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石涛以“一画”参天地之化育,要求“搜尽奇峰打草稿”。同样是书写山川风物,郭熙吸纳山川的精华,石涛强调心物交融,与山川神遇而迹化。追溯艺术创作之源,强调对物象形体的描绘成为传神的基础,由此表现物象的精神。
中国小说对此要求更高。施耐庵《水浒传》所叙英雄好汉个个鲜活,各具性情、气质、形状、声口,令人称叹。在金圣叹看来,这是施耐庵格物工夫所致。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恕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1](P.10)“格物”本属理学范畴,金圣叹把它引入小说评点,使“忠恕”思想与格物穷理结合起来,强调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细微工夫。
体物不能孤立地看待事物,而应重视事物与其环境的联系。人物画造型,不能孤立地观照对象,而要使之置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中。环境描写对人物精神传达起辅助作用,适宜的环境有利于烘托人物的精神气质。因此,在处理人物与其生活环境的关系时,艺术家常营造特定的环境以展现人物性情。顾恺之为谢鲲画像,把对象置于岩石之间,人问其故,他说“此子宜置丘壑中”。谢鲲风流洒脱,善琴好玄,仰慕竹林七贤,性喜林泉,不屑世务。顾恺之如此构图,是想表现其高雅出尘的隐逸情怀。顾恺之评论历史题材绘画,也很重视人物与其环境的关系。他还重视细节对于表现人物精神的作用。这都要求艺术家深入生活,观察人物的言行举止,对其生活感同身受。也就是说,艺术家必须“神仪在心”,日积月累,深入生活,培养取材与表达的能力。
二、传神写照
传神写照是艺术创造的审美理想。这一审美理想源于道家的形神观。
“道”是万物之源,至精极微,唯恍唯忽,神奇微妙,莫可名状。老子讲“大象无形”,说明道超越具体形象。王弼解释说:“名以定形。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夫名以定形,字以称可。言道取于无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称最大也。”[2](P.63)道整全不分,强以为名。有形便有分,难免非此即彼,无法体证整全之道。老子由“道”引出万物变化的总规律:“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道德经》第51章)万物各具其形,只是道的作用。与至高无上的“道”相比,“形”使“物”具备特定的形态,离不开“道”“德”的充盈。庄子学派也有对“道”“神”“形”的思考。他们认为,“道”是造化的本体,“神”是道的体现,人的精神生于道,澡雪精神才能体道,形残无妨神全。神为形主,神即“使其形者”,如小猪爱母,“非爱其形,爱使其形者也”,母亡而弃之,因为形虽存而“使其形者”不存。《庄子·知北游》:“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这种事物创生原理表明,形体是万物存在的依据,“神”处于“形”与“道”之间。庄子学派的形神观在中国艺术论中得到了落实。
顾恺之画人,有时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3](P.388)这是“传神”概念的出处。对人物美的观照,并不限于视觉,但是眼睛往往是展现人物神采的关键部位,顾恺之是说,人物画创作要把握对象的个性特征。魏晋时期,人物画运笔、线条技法已趋于成熟。艺术家对“关乎神明”的身体特征颇为敏感,因为它们牵涉对象的神态、性情和气质的传达,传神旨在表现人的内在精神和个性特征。宗炳重视山水画的畅神功能,标榜超凡脱尘的风姿,提出“以形媚道”,“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画山水序》),把赏玩山水作为悟道方式,艺术由“形”“色”构成,通过“写”“貌”,传达艺术家体验的山水之道。
尽管中国早期山水画的起源与地图这类实用性图像有关,但作为艺术品的山水画毕竟区别于地理堪舆,其“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王微《叙画》)。魏晋以来的艺术家已认识到,心灵是艺术创造的烘炉,山水画以有形之象,出无形之趣,突破实用功能,展现心中林泉。笔墨因顺性情而生发,山水经受心灵而净化,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使山水生情,“神超理得”。宗炳推崇触目会心的“妙写”,突出“神”的超越地位,以传神写照为目标。《世说新语》记录魏晋名士的生活及言行,多使用与“神”相关的词汇,概述人物的精神风采。顾恺之为裴楷画像,为了表现“隽郎有识具”,便在其脸颊添三毛,使之“神明殊胜”,又“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人物的精神顿时鲜活起来。顾恺之《女史箴图》、阎立本《步辇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捣练图》等传神之作,还有难以计数的文人肖像画,对人物的神情体物入微,又不囿于细枝末节,富有个性特征,都以传神为理想。
顾恺之以人物画为例,指出写形在于传神,传神不能“空其实对”,否则,“筌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他强调赋形对于传神的意义和作用。顾恺之认为,形式是艺术家“悟对”的产物。败笔有两类:“对而不正”属于小过失,“空其实对”则丧失“传神之趣”,有鉴于此,他强调“悟对之通神”,从“目视”转向“神会”,整体上把握人物的风姿神态,通过真切感悟和深入体验,把握人物的精神特质。既然艺术创造以传神为理想,艺术鉴赏就应遵循这一规律。重视感悟和体验,所谓“玄赏”“神会”“妙悟”等说法,都与传神写照的理想有关。
苏轼对如何把人物画传神的看法极为深刻。他认为,传神之难在目,其次在颧颊,他说:“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眉与鼻口,可以增减取似也。”[4](P.401)苏轼认同顾恺之的传神原则,不过,他不认为眼睛是唯一可以传神的身体部位,这正是人物画传神要克服的难题。苏轼说,描绘墙壁上灯影,也能传其神情。这是因为,传神必须关注对象的特征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或在须颊,能否把握其特征,直接影响到传神效果,“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人中阴察之”。
中国小说也以传神写照为理想。人物形象塑造真实感人,先要把握其个性化特征。李贽评点《水浒传》时,以“传神”“摹神”“情状逼真”“有光景”“传真”等概括人物塑造,如:“描画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且《水浒》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5](P.283)小说的传神效果主要是指人物性格鲜明、形象鲜活,如《水浒传》第37回写李逵出场,用“黑凛凛大汉”形容,李贽认为“黑凛凛”这三字“神形俱现”,金圣叹讲“画李逵只五字,已画得出相”。该小说接着写宋江“吃了一惊”,金圣叹评点:“盖深表李逵旁若无人,不晓阿谀,不可以名服,不可以利动,不可以智取”,这是为了衬托李逵,不单描绘李逵的外貌,还刻画他的神态、性格和心地。人物个性鲜明、特征突出,方能传神。该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形象,如鲁智深、郓哥等的性格刻画也颇为传神,文字逼真,既“画眼前”,又“画心上”。“画眼前”是指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描绘其形体外貌的主要特征,产生如在眼前之感;“画心上”是指通过人物的语言行为表现其思想情感,洞察其内心世界。抓住人物的个性化特征,善于细节描写和场景刻画,这是小说形象传神的普遍规律。《红楼梦》同样是一部传神之作,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形象,在此不再展开。总之,人物形象生动,注重细节、场景和结构的经营,这是小说传神写照的常见手法。
传神写照离不开审美情感的介入,需要创造意识发挥作用。艺术创造有赖于审美情感的投入,故应重视移情作用。就音乐、戏曲表演而言,情感介入极其重要。中国艺术尚意重情,认为情感是艺术的底色,形式是有情感的形式,当代某些学者认为受道禅哲学影响的艺术形式消解情感表达,这是对“情感”的狭隘化理解,其实任何艺术形式作为人的创造物,不可能完全排斥情感发挥作用。“形”可作为表现动词,使形外现或彰显。《乐记》认为,音乐起于人心,受外物感动所致,音乐美的生成经历从感物到形式外显的过程,伴随着节奏、韵律的生成。声乐、器乐的表现方式有别,但无论是哪种形态的音乐,情感体验对于传神而言都很重要。音乐传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表演者对艺术精神的领悟和把握。汉代《淮南子》集中探讨形神关系,对中国艺术形神观的形成影响深远。人的精神受于天,形体禀于地,形神由气构成。形体是生命的寄托,气是生命的充实,神是生命的主宰。三者各就其位,各守其职。它承续庄子学派“使其形者”的思想,提出“神贵于形”,为中国艺术提供神主形从的理据,辨析主次分明、形神相依的关系。《淮南子》论及音乐表演时,认为乐音伴随心情,表演者得心应手,才有“君形者”,反之,“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6](P.480)这是主张情感自然,以形式充实音乐的内涵。吹竿者使工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是因为缺乏“君形者”。艺术创作要掌握规矩和技巧,但更应懂得其所以为巧。瑟无弦不能成曲,单有弦也无法成音。乐器是器乐生成的物质媒介,通晓律吕是声乐形式的基础,但仍然不够。“韩蛾、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之所以感人,在于他们“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只有体验深刻,才能寓情于声,善于调度,传情出神,才有理想佳作。
传神写照在中国戏曲领域也有体现。戏曲家以“写心”传神,精准地把握对象的精神气质,真实地表现人物的心灵世界和独特个性。中国戏曲不重故事的离奇设置,却对人物形象塑造要求极高,演员设身处地揣摩人物的性情,宛若其人,情感细腻,可以现身说法,用台词、行为和动作参与形式建构,以精彩的表演展现人物的内心生活。即使演唱同一曲,转腔换字之间,别有一种声韵,举目回头之际,独具一副神情。演员的身段和形体赏心悦目,其角色体验和舞台表现出神入化,收放自如,情态毕备。演员有较高的天赋和素养,才能把握好戏曲的精神,才能把人物演活,把故事讲好。京剧表演也不外乎此理。除了唱念做打遵照一定的程式,更要服从剧情对形象塑造、故事叙述、主题表达的需要。汤显祖称赞王玉峰扮演《焚香记》:“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何物情种,具此传神乎!”可见,成功的表演感人至深,取得传神效果。
中国艺术批评以“韵”作为传神的标准,如“韵味”“神韵”等。谢赫《古画品录》论画提出“六法”,以“气韵生动”为首,他认为不拘于“体物”,取之于“象外”,才能传神。寄微言于象外,以形媚道,神超理得,成为山水画的构图原则。超越工匠习气,不专求形似,独得于象外,为唐代以来的艺术界所崇尚。张彦远接受了这一思想,提及“神韵”等概念,并强调以气韵求其画,形似在其中。与气韵相比,形似、赋彩皆非妙处。黄庭坚以“韵”论艺:“凡书画当观韵。往时李伯时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取大黄弓引满以拟追骑,观箭锋所直发之,人马皆应弦也。伯时笑曰:‘使俗子为之,当作中箭追骑矣。’余因此深悟画格,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入神会耳。”[7](P.729)“韵”通过艺术形式自然流露出来,既非规范整齐的形式,也非酣畅淋漓的气势,需要妙悟。长期以来,有些艺术史家把艺术分为写意、写生两派,认为写意派重神轻形,写生派重形轻神,这样区分虽有一定道理,但也难免非此即彼,以偏概全,掩盖了艺术史的真相。这是因为,写生兼能写意,形神兼备,正是中国艺术家的普遍理想。
篆刻以形写神,传神为上,这已成为印家共识。徐坚说:“作印之秘,先章法,次刀法,刀法所以传章法也,而刀法更难于章法。章法,形也;刀法,神也。形可摹,神不可摹。神不可摹,譬之写真者,两人并写一人,则声音笑貌,呼之欲出,一则块然无生趣。同是五官,而一肖,一不肖,则得其神与得其形之异也。得其神,则形之清浊妍媸,不求其肖而自无不肖也。然神寓乎五官之中,溢乎五官之外,不可言喻,难以力取,古人论诗文,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正谓此也。”[8](P.349)篆刻非雕虫小技,有艺道存焉。章法写形,刀法出神,故应以刀法为上,章法为次,前者可仿效,后者不可复制。不仅如此,“神”还通向“言有尽而意无穷”,接近古人对意境的规定。总之,篆刻是在狭小空间上做大文章,它要突破空间的限制,体现芥子须弥之境,对此艺术形式当以神会,不拘形迹。这是突破物质媒材的限制,凝万仞之势于拳石,见小天地于尺幅,方寸空间韵味无穷、意趣无限。
三、随物赋形
随物赋形是对艺术形式法则的概括,苏轼是这一理论的极力倡导者。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4](P.2069)苏轼从《周易》“涣”卦象传、道家道法自然思想以及佛教形相观获得理论启发,对艺术赋形法则进行概括。
禅宗秉承般若空观,既指认形相虚空,不生执著分别,同时,它也肯定真实不离现实世界。南宗禅以“无相、无住、无念”为法旨,其中,“无相”不是否定形相,它是要求不被表象所惑,保持心境超然。禅宗主张平常心即道,认为形相是物体的外观,不是客观的实在,事物有形却无定形,有相却无定相。马祖道一说:“法身无穷,体无增减。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滔滔运用,不立根栽。”[9](P.440)以水月成相表明法身无定相,也不可执定身外之相。水月之相体性虚空,却能应物现形。马祖道一揭示形相缘起生成之理,肯定形相对于真相显现的作用。事物缘起生成,同理,艺术形式没有先天法则或固定模式,也不能依赖经典、传统和他者。从“应物现形”到“随物赋形”,实现佛理禅意向艺术形式生成论的转化。
同时,禅宗心性论发达,突出心灵的自主性,对重视创造意识的艺术观起引领作用。唐宋之际,艺术理论界出现了一股高扬创造意识的思潮。魏晋南北朝盛行“意在笔先”说,要求笔为心使,以意运笔,至白居易提出较为系统的写意理论。他称萧悦画竹逼真,茎瘦节疏,枝活叶动,其成功经验在于超越对现实之竹的模仿,遵循“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的原则。张彦远倡导“不滞于手,不碍于心”,张璪提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五代荆浩《笔法记》提出“六要”,包括“气”“韵”“思”“景”“笔”“墨”,与谢赫“六法”相比,荆浩去其“传移模写”,代之以“删拨大要”“凝想形物”之“思”;去其“随类赋彩”,代之以用“墨”,墨具五色,无需“赋彩”;用笔“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笔随心运,飞动变通;以“景”代“应物象形”,要求“搜妙创真”。可见,荆浩的笔法论涉及艺术赋形问题,肯定心灵在艺术赋形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如果忽视“凝想形物”,表意达情无从谈起。荆浩还指出,取材要精粹,所谓“删拨大要”“搜妙创真”,对材料进行加工与提炼,创造特征鲜明的意象。总之,从谢赫“六法”到荆浩“六要”,其间有一条艺术家创造意识不断高涨的思想脉络。
苏轼分析“常形”与“常理”的关系,也涉及对随物赋形的思考。他说:“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4](P.367)苏轼认为既要画形,又要明理。无常形之物,重在表现常理。宋代山水画追求理趣,理胜于形,却不离形,而应发乎自然,“无意于佳乃佳”。此“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神”。宋元之际的赵孟坚说:“古画画物无定形,随物赋形皆逼真。”[10](P.672)画无定形,形自法生。随物赋形,就是因缘成形。又如,戴熙说:“有形者有似,无形者无似。无似何画?画其神耳。”[11](P.158)根据对象的特征采用相应的表达方式,但始终以传神为目标。
以形写神,需要落实在艺术家“写”的过程中。“写”,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或表现性动作,它要求“意在笔先”“胸有成竹”,在谋篇布局、点画间架、结构安排时,融入个人体验,能应接审美情境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书画借助勾线、皴擦、渲染等手法赋形,使意象呈现神采和质感。笔墨有轻重、虚实、浓淡等的起伏变化,线条的使用要遵循随物赋形的法则。
以形写神之“写”,隐含形由心生之义。中国艺术论称赞纵横逸笔、挥洒自如、变幻不定的赋形状态。郭若虚说:“且如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12](P.468)他强调心源对于艺术赋形的意义。艺术形式发自内心,出诸灵府,各人境界有别,艺术赋形也就相应显示出个性化特征。苏轼呼吁“胸有成竹”,要求书写心志而摆脱画工习气,“取其意气所到”。在艺术赋形过程中,笔和意是心之所使,情之所发,对于艺术赋形起决定作用,如何使“眼中之竹”“胸中之竹”转化为“手中之竹”,不能按图索骥、依葫芦画瓢,而应彰显自家的性情和面目。
金圣叹拈出“因缘生法”,这一命题蕴含随物赋形的意义。他引用佛教“因缘和合,无法不有”的思想评点《水浒传》,并指出:“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龙树著书,以破因缘品而弁其篇,盖深恶因缘;而耐庵作《水浒》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1](P.314-315)应依据特定情境行文运法,没有现成的法则可循。施耐庵根据行文需要塑造各色人物,构造情节,设身处地,不落俗习,不拘俗套,展现人物的风姿神采。这些形象古无今有,生动活泼。“因缘生法”之“法”涉及艺术赋形问题。艺术形式生成应遵循缘起生成之理,随机运法,破除对陈规习见的依附,摆脱对师承谱系和身份名望的攀援。由于艺术家性情、气质、阅历、素养有异,每次艺术赋形的情境不可复制,因而无法预设普遍有效的形式法则,于是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境当下运法,触处即真。在艺术创作时,物感与情境相依,外物是触发感兴的动因,缘于当下情境,或受现实触动,表现为刹那间的灵思闪现。兴不孤起,触境方生。随物赋形这一命题表明,艺术形式生成具有当下性、条件性和唯一性,它是艺术家人格精神的投射。
四、形神两忘
形神两忘是一种心物交融、主客不二的审美境界,道家和禅宗思想为此提供了支持。道家强调,道体微妙难言,警惕语言表意的局限性。语言有一定的表达功能,可以描述事物的表象,然而,真相超越语言逻辑。语言对于体道有一定意义,但语言本身并非道。道具有无限的可能,不可眼见耳闻,无法用具体语言陈述,因为语言的表意功能有限,任何名相概念都难以体证无限之道。因此,道家主张以得鱼忘荃、得兔忘蹄、得意忘言的方式体道(《庄子·外物》)。合适的语言方式才能得意,把握事物的深层道理或得意是其目标。语言的使用在于表意,但难以传达深层事理。
因此,老子讲“吾丧我”,是为了消解小我、假我,彰显大我、真我,庄子讲“心斋”“坐忘”,也是要破除物我对立,彰显人与万物一体的状态,禅宗宣扬无言妙悟之旨,都在为形神两忘的出场做铺垫。《庄子》中的一些故事,如庖丁解牛、佝偻承蜩、梓庆削木为锯、庄周化蝶等,经常用来形容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曾无疑工画草虫,尝提及其经验:“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全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 ! ”[13](P.343)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显然有对庄子“物化”思想的演绎,艺术创作破除物我对立,消除形神桎梏,心灵绝对自由,才能游刃有余,运斤成风。
中国艺术推崇“忘笔墨而有真景”。南齐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笔相忘,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14](P.188)王僧虔确立“神采”与“形质”并重的书法审美标准,同时,他也指出达到这一境界的关键在于“忘”,心、手、书皆忘,心境放空,虚静澄明,笔墨生活。在中国艺术论中,这类说法颇为普遍,如董其昌论画:“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神之所托也。”这也是张扬自由的心境。在心手相凑而相忘的状态下,主/客、虚/实、真/幻、有/无等执念分别荡然无存,艺术方能出神入化。
中国艺术有崇道的传统。道是万物之母,也是艺术之根,道的特性被视为至高的艺术境界,艺术成为对道体的无限接近。道具有形而上意味,老子讲“大音希声”,庄子学派讲“至乐无乐”,以体道为宗旨,老庄思想中的“天籁”“天乐”,无形无声,无法以视听感官直接把握,需要用心感悟与体验,不被“形”“神”等概念以及各种知见分别所缚。书道玄妙,不可刻意求索。张怀瓘《书议》、虞世南《笔髓论》都强调书道玄妙,远离常情世智言喻,唯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方可领略“无声之音,无形之相”,也就是开启妙悟之心,当以神遇,不可力求。
中国艺术抑“画工”,扬“化工”,推崇无迹可求之境。前者难免造作,终落迹象;后者师法造化,浑然天成。这一艺术境界与形神两忘紧密相关。严羽推崇盛唐诗学,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趣。这类水中月、镜中花般的形式感,可望而不可及,迷离隐约,风姿绰约,神韵别具。它不重逼真描绘,不求精雕细刻,而讲究微妙隐约之致。严羽把“入神”称为“诗之极致”,属于崇高境界,惟李白、杜甫得之。王士祯论诗推重“神韵”,也把“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作为诗歌之极境。这种不拘形迹的意识也出现于戏曲批评领域。王骥德论曲:“佛家所谓不即不离,是相非相,只于牝牡骊黄之外,约略写其风韵,令人仿佛中如灯镜传影,了然目中,却摸捉不得,方是妙手。”[15](P.197)他以“仿佛”“约略”说明戏曲“不即不离”美感的非确定性,似有若无,似真若无,令人陶醉。中国小说批评吸收“画意外”这类画论术语,要求人物形象塑造超越语言局限,表现更丰富的意义。类似的说法,还有“神手”“化工”“出神入化手段”等,都是对形神两忘理想的认同。
中国画的没骨法有浑然天成的形式感。没骨即抹去形迹,淡化迹象。五代徐崇嗣是没骨法的发现者。徐氏花鸟不用描写,唯以丹粉点染,号没骨图。与以往的点染描画不同,徐氏没骨法在形式方面别开生面。王冕、陈淳都擅长此法。恽南田不赞同“世人皆以不似为妙”,而宣称“惟能极似,乃称与画传神”,他称“徐家传吾法”,以形写生,以花传神,其没骨花卉清新秀雅。淡化刻画之迹,是为了实现更深层次的传神。
中国艺术家主张,有意无意之间方为传神之妙。清代蒋骥《传神秘要》认为,肖像画创造既要有意,又要无意,“无意露之,有意窥之”,不落有无,心无沾滞。肖像画要求对象神情自然,艺术家用心观察与体会,才有佳构。缺少任何一方的配合,都难以传神。篆刻的审美境界有不同层级和品第之别。徐上达论印:“最上,游神之庭;次之,借形传神;最下,徒象其形而已。”[17](P.149)艺术境界高低有别,“最上”,即推重神化之境,师古而能化,浑浑融融,泯绝笔迹刀迹。这种浑融无迹之相,或称浑沦之境,超越形迹限制,正是形神两忘之境。
因此,中国艺术赋形讲究心境自在,心不离象,亦不著象。沈野论印:“不著声色,寂然渊然,不可涯涘,此印章之有禅理也;形欲飞动,色若照耀,忽龙忽蛇,望之可掬,即之无物,此印章之有鬼神也。”[18](P.75)艺术家超脱闲远,不著迹象,心无沾滞,才能臻于上乘境界。艺术赋形绝忌板结,心生板结,刻意雕琢,则会胶柱形迹,气韵生动不至。方薰说:“点笔画以气机为主。或墨或色,随机著笔,意足而已,乃得生动,不可胶于形迹。”心境通透,方能生动传神,意趣无穷。消除物我界限,摆脱形神隔阂,得之于离合之间,神会于有无之际,是其心境自由的体现。妙造于心,弄笔如丸,天真纵逸,则笔墨随心,情趣自佳。戴熙论画:“心空相不著,形槁神益腴。”心不著象,不落滞相,不即不离,形神无碍,则处处生活,真趣充满,远离俗气、匠气、滞气。心中无形无神,故能得天地之大全,显万物之真态,以玲珑活络心,造羚羊挂角相,为中国艺术所崇尚。
五、游戏笔墨
游戏笔墨是一种活泼自在、任运自然的审美情趣,深受禅宗心性论、形相观和言意观滋养。在中国美学研究界,有学者强调道禅哲学对形神关系的“超越”,完全把以形写神的思想背景归于儒家,其实这一方面是对唐宋以来部分文人家观点的沿袭,另一方面则是夸大了道禅哲学对“形”的反思,从现代意义上看,任何艺术创造都涉及形神关系的处理,只是对“形”“神”的表述方式及其内涵不尽一致,但仍属于以形写神的范畴,故对此概念不宜过于狭隘化理解。
游戏笔墨成为唐宋以来艺术家的审美情趣,深受禅宗思想滋养,丰富与拓展了中国艺术以形写神的审美传统。禅宗以“不立文字”为基本立场。语言作为觉悟的法门,属于名假施设,权宜而设,其体性虚空,不可执为实有,迷恋幻相,执以为实,便是相缚。同时,语言它并非可有可无,草木花叶、菩萨之名也得借助言说,觉悟名相本身缺乏实在意义。佛经说法是为了使人觉悟,语言可以用来标识事物或揭示一定的事理,故不应否定其作用,也不能忽视其表意功能,关键在于善于运用,摆脱语言的束缚。佛祖拈花微笑,走的是超越名相、规避逻辑之路,这就要求开启自性,复归真源,心境自在,才能领略真相。北宋文字禅盛行,从“不立文字”发展到“不离文字”,促使诗与禅的关系进一步融合,审美与禅思并行无碍。
禅宗主张参透形相的虚空不实,即色即空,明心见性。禅师在讨论人的相貌时,流露出不执形相的意识。如沩山问云岩:“药山大人相如何?”云岩答:“涅槃后有。”沩山又问:“如何是涅槃后有?”云岩说:“水洒不著。”这时,云岩反问:“百丈大人相如何?”沩山答:“魏魏堂堂,炜炜煌煌,声前非声,色后非色,蚊子上铁牛,无你下嘴处。”[19](P.724)在此,药山、百丈禅师的相貌,成为禅师参究佛理的话头,通过揭示相貌虚空不实,开启不执形相的慧心。仰山行伟禅师上堂:“直饶丹青处士,笔头上画出青山绿水、夹竹桃花,只是相似模样。设使石匠锥头,钻出群羊走兽,也只是相似模样。若是真模样,任是处士石匠,无你下手处。”[20](P.1119)他从缘起性空的立场参悟画中山色泉声的真实性,提示僧徒不被幻相所缚。在禅宗看来,绘画和雕塑只能展现人的“相似模样”,丹青妙笔也不过是觉悟法门,并非事物的真相。当形相虚空的禅理被引入艺术创造与批评领域时,促成参透艺术由心所现、视形式为幻有、以笔墨为游戏的审美情趣出场。
在佛学思想语境下,“游戏”原指佛菩萨神通变化,出入无碍,大彻大悟。游戏自在意味着心境圆活,开启生命觉慧。北宋禅门流行“逢场作戏”说,指向任运天真、心无挂碍的人生理想,或张扬率意而为的处世态度。当时,文字禅兴起,惠洪等“以笔墨为佛事”,不离文字般若而妙悟游戏三昧。苏轼文人集团推动着这一审美风尚的发展。苏轼题画:“斯人定何人,游戏得自在。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21](P.1439)米芾论书:“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22](P.973)在他们看来,艺术是本源真性的起用,笔墨是性灵的游戏,无关形式工拙。苏轼不被法缚,笔墨生活,“游戏于管城子、楮先生之间,作枯槎寿木、丛绦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盖道人之所易,而画工之所难。如印印泥,霜枝风叶先成于胸次者欤!”[23](P.299)他们注重生命体验的传达,直抒胸臆,不求人赏,以游戏法作攲侧字,以游戏法造真实相,笔墨妙契而成形。
依照佛教的说法,身心幻化,五蕴不实,相无定相,对于画像也不可执实。此类思想在宋代以来时常出场。苏轼画偈云:“此画无实相,笔墨假合成。”[4](P.644)他以笔墨为游戏,视形式为幻相,故指认变相虚空不实。徐渭跋丑观音造像时说:“至相无相。既有相矣,美丑冯延寿状,真体何得而状?”[24](P.981)这座观音形式奇特,以丑为特征,超出人们对作为慈悲化身的观音造型期待。徐渭为此辩解,认为“至相无相”,是想破除孰真孰幻、孰美孰丑的分别之见。在他看来,图像形式多样,涉及形式则如露如电,不可执实,但图像体性虚空,毫不实在,以颜色求,终不见真相,故不可判定某图为真,某图为幻。艺术家的涵养、禀赋和体验有异,只要能产生传神效果,形式本身无高低分别。戴熙甚至以人生幻化、造物若戏推论艺术的真实性,对艺术形式的本质可谓棒喝。
不仅佛教人物画像如此,就连文人写真、山水花鸟传神流露出游戏笔墨的情趣。中国古代文人写真是指以肖像画的方式为生命留影。很多艺术家佛学造诣深厚,表现不同于职业艺人的情趣和品味,呈现出鲜明的文人意识。他们不拘形迹,画枯木怪石,荒寒寂历,墨影微淡,天趣具足,其参差错落、疏野萧散的形式备受推崇。马远擅长边角小景,画面空疏淡远,夏圭多取半山之势,脱落表象之似,显现山水真态,为江山留影,令人舍形而悦影。总之,不求工拙,不计工拙,为物象传神,成为宋代以来文人艺术赋形的新趋势。
不少艺术家把形式视为表达心性、觉解人生的法门。倪瓒论画:“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它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真没奈览者何,但不知以中视为何物耳?”[25](P.302)倪瓒绘画堪称逸品,不求形似,聊以自娱。书画不计工拙,不拘常法,而境界独特,意趣逸群。倪瓒画竹表写胸中逸气,不计叶之繁疏、枝之斜直,注重其精神和寄托。姚广孝题倪瓒墨竹:“以墨画竹,以言作赞,竹如泡影,赞如梦幻。即之非无,觅之不见,谓依幻人,作如是观。”[26](P.62)就像生命缘起而成,墨竹、言赞由心而生,皆为笔墨游戏。文人墨戏发乎性灵,不涉及理路,不落知见。依禅宗形相观,应破除对形式的执著,消解陈规习法的桎梏。以艺术为泡影,视形式为幻相,心性表达便是传神。逸笔草草,随兴皴染,发乎性情,妙趣横生,文人艺术重在传达物象之“神”“意”“理”,突显艺术赋形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当下即是,瞬间生成,敞亮人人皆具的自性。
心灵是智慧之源,也是形式生成之源。在禅宗思想作用下,艺术家越发重视心源,艺术成为彰显自性的方式。色彩是绘画的形式构成因素,文人画的色彩意识受到即色即空思想的影响。马祖道一说:“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20](P.128-129)此“色”泛指事物,不能狭隘地理解为颜色,但对于理解文人画的色彩观仍有启发。唐代以来,青绿赋色受到冲击,勿施丹粉、以水墨取代五色成为文人画赋色新趋势。苏轼说:“造物本无物,忽然非所难。花心起墨晕,春色散毫端。缥缈形才具,扶疏态自完。莲风尽倾倒,杏雨半披残。独有狂居士,求为黑牡丹。”[21](P.1353-1354)狂居士画墨牡丹,以意运法,不被眼见之色所囿,以水墨荡尽色相,不渲染牡丹富贵浓艳,深解物态幻化之理。既然色无定色,那么,以红色画竹、以异色画花果,也在情理之中,文人画的色彩观流露出游戏笔墨的意趣。艺术家的独特性情往往寄寓在不经意的形式之中。他们以“墨戏”“戏写”指称艺术创造,重视美感的差异性和唯一性,以活泼自在之心感受万物,发现意义,表达瞬间即永恒的哲思。
在中国小说批评中,游戏笔墨的说法经常出现。如脂京本《红楼梦》第十七回、第十八回夹批:“花样周全之极。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无聊,撰出新异笔墨,使观者眼目一新,所谓集小说之大成,游戏笔墨,雕虫之技无所不备,可谓善戏者矣。”[27](P.445)以“善戏”概括小说,可谓确评。《红楼梦》情节是虚构的,却又合情合理,便是以游戏笔墨,叙述或然之事,揭示应然之理,有别开生面之趣。正如倪瓒画竹,不可执以为竹;徐渭画鱼,不可定作为鱼。然而,倪瓒之竹不可视为非竹,徐渭之鱼不可执定非鱼。领略艺术精神当会意于形外,妙解文心画旨,体证生命和存在的意义。
以上从穷形尽相、传神写照、随物赋形、形神两忘和游戏笔墨五个层次阐发了中国艺术以形写神的美学蕴涵,涵盖艺术创造的方方面面,渗入书画、诗文、小说、戏曲、园林等艺术领域,融入中国艺术精神,至今仍然滋养着民族文化艺术的创新,其渗透力之强,其影响力之大,理应引起足够重视,其美学蕴涵和人文价值亟待传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