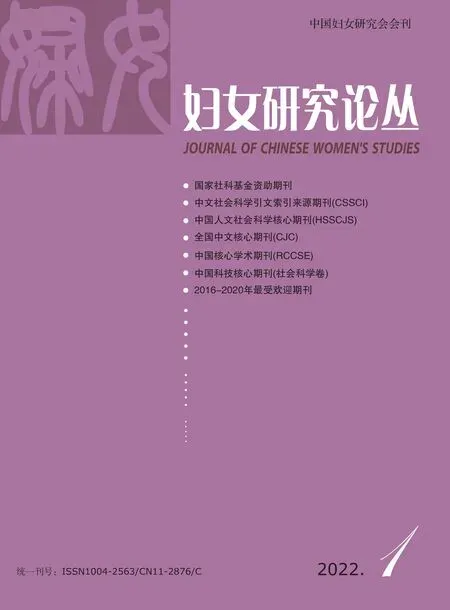现代中国女性作家与生成的现代性
颜海平
(清华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系 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4)
一、引言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在中国的流传历史长久,在现代文学中留下了深刻印记。鲁迅先生即曾引普罗米修斯为自喻(1)鲁迅先生在对翻译的深刻理解和倾力而为中,自比为希腊神话中的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了身躯。”见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页。。这位“窃火者”越过了天庭和人类的区隔,为人间带来福祉,超越以物种分类属性区隔(essentialized division)为根源的现代生命政治宰制逻辑(2)关于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权力、生命政治的“生产性和宰制性”及其近期将福柯之论扩展至种族和物种的阐释,见Key Peggs and Barry Smart,Foucault’s Biopow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与Key Peggs和Barry Smart的表述有所交叠而进一步扩展部分,参见笔者Haiping Yan,“My Dream:The Intermedial Tur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erforming Arts”,Diacritics,2013,41(2);关于对物种作为概念的近期著述,参见Dominick LaCapra,Understanding Others:Peoples,Animals,Past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对相关辨析脉落的溯源研讨,参见颜海平:《海外汉学之外的参照系》,《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6日10版。,示意着一种由跨界转换而生命绵延的驱动力。在诸多现代中国女性作家的氤氲心智和书写世界里,与此有一个结构上既呼应又不同的意象,即填海的精卫:人类炎帝的女儿名女娃,游东海而溺水;转为精卫鸟,衔木石以填大海,如同普罗米修斯,永不止息。而与普罗米修斯来自神界、以牺牲自我而拯救人类不同,精卫来自人间;经由形式和内涵的转换,与向着福祉的人类互为同在,在跨界延展中鸣叫声声,生生不息。作为来自人类、凝练人类又扩展了人类的精卫鸟,犹如人类和众生灵的融会媒介,在跨界中转换,在转换中生成,在生成中延续乃至无尽,指向一种天地间或隐或显、韧性流转的推动力(3)本文下文谈到其中含有来自西学语境被称为“从零到一”的开创性维度;在精卫鸟范式中,这一开创性维度更准确地说是一种“零一互为”的转换生成流变绵延过程。这是跨文化研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笔者将贯穿于现代中国女性作家书写的这一意象结构和过程(imaging process)及其推动力称为由跨界转换而孕育生成的现代性寓意过程,一种在中国和世界现代史上反复出现、由转换而更新的力量,一种有待认知的生命形态和历史可能(4)“寓意过程”包含能指和所指的关联性、生命形态和历史可能的互构性、话语机制和历史语境的具体性及其语境化和语境问题化的文化政治性;与数十年来在中国广为传播的显学即后现代理论(简称“后学”)及其悬置意义的功能构成生成性的对话:在吸纳其批评能量的过程中,根本性地移动其运转重心。这是跨文化研究中另一个可以探讨的命题。。这是笔者曾在关于现代中国女性作家的一本英文专著中将现代、女性、作家、中国作为相互关联的动词进行重访的缘起。作为笔者和中外同道重写现代世界文化版图、从其中物种分类为起源的生物族裔政治逻辑开始的一个尝试,该书中文版于2011年出版(5)参见Haiping Yan,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1905-1948, London/New York:Routledge Publishers,2008;颜海平著,季剑青译:《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简要回顾,并稍做延伸性思考。
二、命运:现代物种百年逻辑和双重视域
提起物种分类,人们常想到的是智人和动物的属性区分、文化和自然的属性区分。不常想到的是这样的类别区分逻辑近代以来如何主导着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内涵的世界秩序安排。这一安排,将人的丰富多彩的差异性和不同语言的流动性化约成等级性的类别,并以此来规定人类世界的地理版图和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近代以来”即是通常所说的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下简称“1648年合约”)及其“民族国家”理念法典化、合约签约各方以强权均势为基点的“国际关系”的建立和相应的“欧洲公法”统辖的现代时空(6)所谓欧洲公法(ius publicum Europaeum,“public law of Europe”,源于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提出的概念)表达规定了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欧洲国家的法律秩序,特别是治理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法,经由漫长的19世纪,其效用在变奏中延续扩展至世界范围。参见Anderson,M.,“Tou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British Passport,1814-1858”,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2010,49(2):258-282;Torpey,J.,“Revolutions and Freedom of Movement:An Analysis of Passport Controls in the French,Russian,and Chinese Revolutions”,Theory and Society,1997,26(6):837-868。。当1648年起以法典化的“民族国家”身份相互建构关系的欧洲人开始“从全球角度而不是区域(欧洲)角度看世界”时,作为在一个区域(欧洲)处理相互冲突——包括代价巨大的30年战争——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地缘政治暨(强权均势)国际法则,通过16世纪开启的殖民系统扩张,标志着所谓“欧洲主宰世界事务的时代”开始;即“欧洲诠释了世界秩序概念的内涵,并决定了这一概念的实施”的数百年(7)日本“脱亚入欧”的追求,是对这一主体定位的追求。参见[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Noam Chomsky,Year 501:The Conquest Continues,South End Press,1993。[1](PP 11-12)。置身这一世界秩序巨变中的现代中国,是一个悖论的存在:一方面无可置疑地在其中拥有着辽阔绵延、充满差异的历史时空和具体生命;另一方面结构性地被规定和区隔在这一世界秩序主导规则之外,即外在于1648年和约及其国际公法所管辖标志的“现代文明世界”。这是一个以人的生物族类(族裔、语言、宗教)和民族国家的政治分类为根据的“欧洲本体”和“欧洲之外”的互为形成、两个分类界定的“欧洲人”作为具有“理性个体”和“国家主权”的“现代人和现代人类”与“非欧洲”他者的互为定位过程。这一两分结构的文化内涵,即通常被称为“欧洲族裔中心主义”(eurocentricism-cum-ethnocentricism)的秩序逻辑及其话语机制,笔者称之为“生物族裔政治”(bio-ethnic politics)(8)笔者《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英文专著中的用词“bioethnic politics”,中文翻译使用了“生物种性政治”,以突出其自然化的社会等级机制。在本文跨界跨文化的语境中,使用“生物族裔政治”,见笔者在“澎湃新闻”的专访:《专访|颜海平:跨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始终亟需的能力》,2020年,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270157 6664440672&wfr=spider&for=pc。,意在明确欧洲族裔中心主义的逻辑基础、社会内核和历史特征,是以男性和女性、欧洲族裔和非欧洲族裔、人类与次人类或非人类、主导(主体)和被主导(客体)在天然给定属性意义上的两分区隔(9)在“1648年合约”法典化的欧洲民族国家及其后续覆盖的广义欧洲(或称西方),女性没有“天然给定、不言自明”的公民身份。英国妇女获得投票权要等到1918年一战结束,美国妇女要等到1920年。虽然已经是女性研究和广义的人文研究中的常识,笔者仍在这里提出,数十年社会性别包括社会性征学的研究早已超越女性男性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化两分法。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社会意义上的边缘化和学理意义上的分化弱化,一定程度上记录了思想的延伸,也揭示了作为一种流派和学说其中产阶层的社会起源和作为美国社会变迁转型中特定语境之产物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敏感的中国学者如戴锦华亦已提出更为丰富的范畴,如“年龄的社会性别”。在世界范围生物族裔政治逻辑激烈化和快速复制化的当下,近年来对社会性别的反思尤其值得关注,见董丽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董丽敏、凌媛媛的《女性文学研究综述(2011-2015年)》中,对生物族裔逻辑的叩问呼之欲出,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11~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93-604页。关于社会性别和民族主义及人类中心主义之关系的研讨亦值得期待。。被规定在与“欧洲本体”相对的“欧洲之外”的个体和群体,寻找在现代世界中主动定位的过程,离不开对这一结构性前提及其逻辑基础、社会内核、历史特征的移位;现代中国的一切变革,离不开这一移位,即对这一结构所规定的区隔边界的跨越;其中包括这一逻辑基础、社会内核和历史特征与中国循环千年的宗族秩序的内涵外延相互冲突和交叠连接的维度。这里跨界的内涵,是在现代世界中个体和群体的人争取获得现代赋权的生命形式和历史路径。跨界意味着两个转换过程,在跨界中转换被跨越的区隔边界及其天然化了的逻辑,在跨越中同时转换了自身的生命形式及其内涵驱动。而如何跨界、如何转换,是这一争取赋权的核心命题。“睁开眼睛看世界”,包括将“我就是普罗米修士”的马克思引入中国的志士和从“精卫鸟”连接到“众生灵”的先贤,对于所处世界的结构逻辑和百年中国的悖论处境,从各种角度认知,以各种方式斡旋,对一切如何跨界、转换的可能,都进行了探索、想象和尝试书写。
就现代中国女性的人生书写而言,这一“跨界”驱动的韧性丰富度和跨界中前景实现的不确定性成正比。处在被千年规训的依附方和欧洲现代的他者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当事人,对主动跨界的后效无法预先运算。没有穿行于结构悖论的现成地图,当事人能够做的,是在无法算计收效的时刻决定努力与否。笔者探索的现代中国女性作家对决定努力与否是明确的;她们的根据是现代人生全在于主动努力的一种确信。20世纪初最早一批跨出她们“天然”规定的区隔位置,进入并构成从中国本土到世界各国的流动的社会时空,办报、办学、办刊、办会、办医院、办商务、出游海外的中国女性,如单士厘、秋瑾、何香凝、刘青霞、陈撷芬、陈衡哲、张竹君等,各有特点;她们的共通处在于确信“尽力”。1903年的陈撷芬写道:“尽力两个字,有无穷无尽的好处在里面,与‘等’字恰恰是一反对。这用心两个字,就是尽力两个字。”[2](PP 576-577)陈撷芬的友人陈超,在同期的一首诗里,将“尽力”进一步解读示意为现代人的属性,具体内容即由“做事”而“食其力”。人之为人,不是“贵者习骄奢,贱者等奴仆”,而是“创女报,握羊毫,供报资,亲著述,同志人,习四术”,使“二万万裙钗”醒悟自身所处悖论危局的含义,从被“天然给定”的人生依附、他者族类的循环境遇中,想方设法拉开距离,甚至抽身而出,以获得对此循环和境遇正视和面对的主动性,这主动性是流动的生命力(10)参见颜海平著,季剑青译:《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丁守和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7页。这一起点与欧美女性本质主义论的重要差别在于,从源头起不提供通向两分逻辑及其同构复制的思路。。秋瑾1904年在东京求学时说:“从此以后,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情,尽力作去,譬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为人了。”[3](P 6)1910年张竹君在上海办医院时提出如何“知学、能群”,分析道:“吾女子之构成此险者,厥有二原因:盖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能群。不知学,故志虑浅薄,无以周知天下之故;不能群,故痛痒不相关,平居既不能有乐群之益,猝有变故又不能为将伯之呼。”[4](P 12)1919年冰心在北京上法庭听审时期说:“我们已经得了社会的注意,我们已经跳上舞台,台下站着无数的人,目不转睛的看我们进行的结果。台后也有无数的青年女子,提心吊胆,静悄悄的等候。我们从今日起,要奋斗!”[5](P 10)后五四时期的卢隐1925年离开北京去上海前写道:“我们豪气犹存,还是向前努力吧。我们应怎样进取?怎样预定我们的前途呢?我甚望你有以告我,并有以指导我呵!”萧红1938年在战乱的武昌评价史沫特莱的书写:“在现社会中,以女子出现造成这种斗争的记录,在我觉得她们是勇敢的,是最强的,把一切都变成了痛苦出卖后得来的。”[6](P 270)袁昌英1940年在流亡中的四川写道:“一连是五次夜袭与无数次的日袭。我们在这些无止息的威胁之中,还是继续苦斗着,忍耐着,努力自己的职务。我在上课改卷以及丧失爱妹的悲哀与其他种种忧虑里面,而能在警报声中写完这篇游记,亦可谓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的明证。”[7](P 92)当然还有丁玲的“生之热情”[8],从20世纪20年代提笔开始直到生命结束的始终呼唤(11)这种热情从丁玲早期直到晚年的文学作品和各类文体书写中运行着。参见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她们各自的具体语境和表述角度在历史的展开中多重变异,相通之处是在不确定中“尽心尽力”之辞,人生而有为、由有为而人生的学说。与传统儒家的“入世三立”有所不同,因为后者原不属于女性的人生范畴;与欧洲现代“理性主体”也有所不同,“外在于文明世界”不具备主体的族群中人,主动言说如何可能,她们原被限制为“无言庶民”(12)参见Gayatri C.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s.,Cary Nelson and Larry Grossberg,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271-313)及相关论辩。。不同不等于无关,其中的相关性及其内涵张力,在本文第二部分有所探讨。就历史生活的具体过程而言,她们跨过了既定区隔和话语秩序的边界;她们说话了,她们有所为。她们跨界转换的程度、维度、方式、风格各有不同,而跨越中的转换携带着生成性的力量,一种现代人的生命力量发生了。
决定尽心尽力与否,是人之为人的起源。从百年后的今天看来,这可以是从原本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可以说具有“从零到一”“零一互为”的创世特征。当时则无从判断。现在可以摆在眼前的女性先贤全套全集文字的出版存在,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犹如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全球不确定性和我们努力的有效性,无法确定计算。巨变中“尽力”的人们开始跨越区隔的边界,置身的是未知之域,与各种无法预设的情状遭遇。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言,秋瑾1902年随同丈夫赴京上任;乘坐轮船从上海出发,在大海中航行时,她写下“胸襟畅、眼界宽”的诗句。船抵大沽口,在海关被阻。管理海关的英国人员,要对上岸人员进行病疫查检,要求男女老幼全身脱衣。一位中国官员圆场,秋瑾得免。全船则泣声一片[9](P 1)。薛锦琴,最早赴美女性之一,1903年在旧金山接受《女学报》的采访时告诉记者,当轮船抵达港口时,“各国人尽登矣,中国人独滞船中,审之再四。夫有罪而后执其人审之。无罪何审?始知外人固以罪人待我中国人也”[10]。这些当事人不期而遇的细节,示意的是在漫长的现代文明史上,世界秩序的治理机制曾经以这样一种反向的逻辑和规定运作:在英国人员执管的海关,将被界定为“中国人”的人们,预设规定为“病疫人”的范畴。范畴规定的根据,是被界定为“中国人”本身,“病疫”成其预设标签(13)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20年3月17日6∶51发送的推特(twitter)中首次将Covid-2019全球疫情称为“中国病毒”,则是这一逻辑遥远的回声。。在同时期的美国旧金山港口,则将被界定为“中国人”的人们,预设规定为“非法人”的范畴。范畴规定的根据亦是被界定为“中国人”本身,“非法”成其预设标志(14)所谓香港人可以在全世界163个国家免签证和落地签的根据,是香港被界定为法律之域,其居住人是守法人。中国大陆受限,其根据是中国大陆人法典程度的匮缺。护照是19世纪的产物。护照的产生使用、社会性别及其全球谱系是文学与跨文化世界史研究中具有丰富生产性的命题之一。参见香港移民局官方规定,https://www.immd.gov.hk/eng/service/travel_document/visa_free_access.html。。这里对“中国人”的界定,是根据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及其欧洲公法以来从欧洲起源并扩展至世界的对生物、族裔、民族、国家的现代分类法则,通过一种理性的方式,对生物人体进行所属族裔和国家性质的分类,并由此对其中涵盖的人性作出范畴分类和相应的治理。对于被“非欧洲”的人而言,经历的是两次去除权利的过程。首先,在如此分类法对生物身体特征的度量下,他们被预设为“生理疾病”和“社会非法”范畴的存在;然后,以这样预设后的自身身体特征为根据,他们就成为生理疾病和社会非法的种群本身。一个人、一群人被预设为病疫或“非法”的存在范畴,一个人、一群人就成为病疫之身,成为“非法之人”。这里的反向逻辑及其规定运作,即为现代生物族裔政治的机制内涵。被这样的反向逻辑制约的人们,所处的即是所谓“受制于人”的被动困境。在今天的全球语境变迁中,当这样的被动逐渐化为记忆,回看现代中国在世界地理和地缘版图中的位置,其结构性特征和内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清晰具体。这是一个实在,但它不具备世界两分法则及其实施所规定的“欧洲性”以及其话语体系中的人类主体性、认知可辨性、合理合法性;其特征或者说后果是“落后就要挨打”(15)日本脱亚入欧的驱动,是旨在脱离明治精英眼中看到的中国式“灭顶之灾”。见[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如此“脱亚”全方位外科手术性的自变过程及其后续问题,参见Stefan Tanaka,Japan’s Orient: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简言之,1648年合约国之间如果发生问题包括战争,双方必须根据和约的条款限制,遵守底线和边界的规则,通过外交进行调节治理。战争与和平之间界限分明。而如果没有合约中所承认的属性及其在广义欧洲[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自1938年开始所称的西方](16)即海德格尔1938年以来所称“西方”,见Christopher Go Gwilt,The Invention of the We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32;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 I (1936-1939),Nietzsche II (1939-1946),English translation by David F.Krell,Nietzsche by Martin Heidegger,Volumes One and Two,Nietzsche I:The Will to Power as Art;Nietzsche II:The Eternal Recurrence of the Same,New York:HarperCollins, Paperback Edition,1991。的版本,经受来自合约国的种种限制包括战争是否合法(欧洲公法),就是一个不成立的问题。所谓“西方和他方”(the West and Rest)两分世界中的“他方”部分、“弱国无外交”的“弱国”部分,在这两分结构的世界及其秩序语境中,可以“合法(欧洲公法)”地被随机处理(17)参见Naoki Sakai(酒井直树),“Modernity and its Critique:The Problem of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South Atlantic Quarterly,1988,87(3)。。比如1902年在天津大沽口的秋瑾、1903年在加州旧金山的薛锦琴;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巴黎和会的顾维钧、陆征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与东京审判的梅汝璈;比如从鸦片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年中国的种种经历。
这一生物族裔政治逻辑及其具体方式,在早期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对女性特定困境的解剖中,可以找到结构性交叠的特征。或者可以说,对中国女性特定困境的解剖,使得早期“尽心力”的先贤,从开始就对这一逻辑及其特征有非常具体的把握。比如,女性思想最早的文献之一——陈撷芬的《独立篇》中,作者引出“传统”女性的形成这样一个话题,从她们生物意义上的畸形化,揭示出她们生物政治意义上的困境化:“如穿耳,如缠足,是为初级刑法。既离此初级刑法,又为次级刑法者,则为私配。并不问其女之乐否也。至有适字未嫁,而夫婿先天者,亦强女子以奔丧守节。”(18)参见丁守和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页。[11](P 27)通过对这一合理常规化的“刑法”及其施行的描述,陈撷芬揭示出一种双重运作:首先,女性身体与男性的差异,被使用和处理成生物意义上的畸形,从而将其自然化为男性主导的欲望效应和宗族地位的权力象征,被限制在社会性别化的困境里;其次,这困境被再次自然化为“畸形者”的天然属性,一种人类关系秩序安排的常道根据,“它在帝制中国的权力结构中运转,同时又是这种结构的象征”[11](P 28)。首先从生物意义上强制界定依附者的特征,其次将此作为她们天然是依附者的根据,于是她们是行走着的人性依附本身。这里的反向逻辑及其运作,穿越区隔的遥远时空,指向异形同构的欧洲起源的现代生物族裔政治;或者说,前者是解读后者的特定历史钥匙,后者是前者的现代世界版本。如果说陈撷芬描述的是旧制度的性制,那么她的描述中生成的是对生物族裔政治世界两分逻辑的现代洞识:这种双重运作的社会性别反向逻辑,是现代生物族裔政治的启动基点、各种外延变奏的机制特征(19)两者之间的不同和黏连,或者又不同又黏连的问题,是重要而复杂的命题、现代性的母题之一。天然化的后效之一,是“依附者”若开始脱离依附性,便会惊世骇俗,成为大逆不道。这当然并不是中国独有。英国开明的约翰逊博士曾经这样评论:“女人说教,犹如狗用后腿走路。做得不好。但令你惊异的是你发现居然有这样做。”https://www.samueljohnson.com/dogwalk.html。。笔者曾经观察,对根植和脱胎于帝国性制的现代中国男性作家来说,直接面对这一基点逻辑的现代版世界运作,在精神上可以是毁灭性的(20)参见颜海平著,季剑青译:《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的论述和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2页的论述。;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让他们发生了人类史上仍然有待认知的极为深刻的人性转换(21)如郁达夫的某些“自伤”(self-injuring)作品和一直被界定为“颓废文学”的男性作家作品中,这种毁灭性的负面程度及其社会性别内涵还有待开拓出面向丰富的历史阐释。而鲁迅、闻一多、胡也频、殷夫、柔石等男性作家,相互差异、丰富多维,但他们各有张力的社会变革包括两性平等的主张,均离不开他们与生物族裔政治及其社会性别逻辑的跨文化历史遭遇。他们和生成中的现代中国女性文化的关系或者说关系的形成,包括他们作品形态本身的社会性别属性,是妇女研究、现代社会性别研究的内在部分。。李大钊对卢隐的评价——“她是情感领域中的革命者”——不仅是对卢隐现象入骨三分的评定,更是他自身变革深刻度的揭示。这是如袁昌英在1934年所描述的那一种变革:“起先你感觉一种震惊,震惊之后,一种内心的平静;从平静中涌出一种力量,使你整个的性灵起了变化——真正变化你自己,而非只是变化你的意见。”(22)参见袁昌英:《论戏剧创作》,载袁昌英:《山居散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页。竹内好对鲁迅的“回心”说与此相关。鲁迅先生“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懦夫愤怒,挥刀向更弱者”之言(《华盖集》《杂感》,见《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触及中国男性如何做“现代强者”的双重挑战:对似乎不可能被克服的生物族裔逻辑政治强权运作的超克,意味着同时放弃对性别制度给予的“天然”特权;其中蕴含着对社会性别逻辑的深刻把握和艰难“回心”的过程。瞿秋白对丁玲现象的评价“飞蛾扑火”[12](PP 1-2),则几乎是对无法摆脱所处困境的被困人“尽心尽力”跨越边界之命运的寓言,甚至亦可以说是他对自身经历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某种转喻。笔者上文中提到,就现代中国女性而言,这一摆脱困境的“跨界”驱动的韧性度、丰富度和跨界中后效如何的不确定性成正比。这种无法确定后效的决定和努力可以被称为面对命运的主动过程,即面对不可知的具体决定。譬如张竹君所言:“岂天生女子必与以若是之厄境乎?推原其故,半由于男子之压制,半由于女子之放弃。”[13](PP 898-899)而无数面对不可知之命运当事人的具体决定,是“不做放弃。自重之道,必先敬其身,正其身,诚其意,凭着本来活泼的灵性,立定宗旨,死心塌地做去”[10](P 45)(23)参见侠佛:《说死活》以及前人:《自重论》,《女报》1909年第3号,第140页,引自丁守和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8-509页。。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由“尽心力”而“创人生”的确信,就是认知上对既存大局结构的盲目性,对具体成败与否的无判断。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书写历史的漫漫长卷,承载着具体的个体人生轨迹和富有概括性的社会精神现象,标识出支撑着女性跨界力量的源流,从可见的波澜起伏到隐秘的深水恒久。今天业已逐渐进入世界文化版图的中国学人回头看去,依然或者更为令人惊异的,是长卷中深邃流转的一种隐性的结构意识和日常的行为胆识的融合。比如笔者探讨过的“冰心体”。沈从文所说“以奇迹的模样出现”的冰心现象,和当时从旧格律而新文字、“在荒凉寂寞的沙漠中探险摸索”的诸多男性书写不同,所谓“好像靠她那女性特具的敏锐感觉,催眠似的指导自己的径路,一寻便寻到一块绿洲,便从从容容在那里建设她的诗的王国”[14](P 77)。而事实上,在中国军阀割据、世界战争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生物族裔强权逻辑在人类史上又一次激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出现,“冰心体”是又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绿洲”。1920年发表的《一篇小说的结局》写一个年轻女作者想讲一个欢乐重逢的故事。小说以冰心“绿洲”式白话文开篇:“明媚的夕阳,返照在一所缘满藤萝的楼舍上。”这楼舍的窗台上放着一卷稿纸;凭窗而坐的女作者拿着笔,正在想着如何书写;故事里的儿子是将要从军队回来看望他的母亲。随着情节展开,小说的形式呈现出一种双重书写。“引”的开篇句子属于第一重书写,即对小说中作者书写过程的描写,此中间隙停顿都简洁地白描出来;第二重书写则是小说中作者的书写,以援引的形式在间隙停顿中出现(小号字),示意着与小说中作者自己原来的计划、期待和希望相违背的过程:原来应该是从军队回来看望他的母亲的儿子没有出现,最后带到老太太门口的是她儿子的死讯。《结局》以让小说中作者的写作变得不可能的那种断裂来结尾:“(她)写完了,便从头看了一遍,看到末后一段,不禁惊的站起来说,‘我不是要写他们母子团聚的乐境么?为什么成了这样的结局?’便立刻将这张稿纸撕了,换了一张纸,拿起笔来要再做。但是,她再也写不下去,只手里拿着笔,呆呆的看着窗台上一堆碎纸。”[15](PP 67-68)一种类似音乐上的复调组织着全文,但在这里,一般复调相互之间的平行、对话乃至变奏遭遇了超出复调形式可以容纳的张力,成为一种可以称之为濒临破裂的紧张复调;窗台上的一堆碎纸,犹如当时濒临破碎的国土和在生物族裔强权逻辑下生活破碎化的人们。在小说中援引的作者文字和小说中作者“再也写不下去”的叙述过程之间,发生着第三个过程,即面对命运般的对书写的负面限制,拉开距离,主动反思,以继续和完成书写的过程。故事中“再也写不下去”的“她”,正是小说书写本身完成的部分。对濒临破裂人生世界的反思书写,犹如冰心作为一种写作现象以穿越世纪的轨迹所揭示的,是一种似不可为而又为之;其中蕴含着笔者称为隐性的结构意识(写不下去)和内涵是日常(始终书写)的主动胆识,前者是对人间世事权势逻辑的潜在意识,后者是与潜在意识同在的具体决定,两者构成具体人生与世界结构之间的关系;这关系的文学形式,即是笔者称为隐性结构意识和日常胆识的融合。冰心自1919年开笔,从1922年的《十字架的园里》[9](PP 348-350)到1946年的《丢不掉的珍宝》[16](PP 81-85)乃至绵延世纪的文字,包含着中国现代女性“尽心力”之学说仍然有待阐释的绵密信息;和卢隐(如《梦——夜的奇迹之一》)[17](PP 24-26)、白薇(如《昨夜》[18](PP 172-183))、袁昌英(如《生死》[7](PP 46-56))、萧红(如《黄河》[19](P 285))、王莹(如《王莹写给英子的信——十八》[20](P 31))等笔者书中探讨的众多女性和更多未及探讨的书写,一起构成犹如森林河流的深厚深邃,提示着什么是对人世间结构性的命运意识,什么是面对命运的日常书写,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对何为历史洞识、何为人生判断、何为命运本身的叩问和回应。
对百年中国现代困境世界性、结构性的隐性意识,以独特的力度、历史覆盖度和凝练度在丁玲诸多作品中运行,比如小说《母亲》“未完成时”的结构本身所包含的深长意味。再如从1931年9月到11月在《北斗》上连载的中篇《水》。《水》在国共对峙时期的政治性被首先确认,并作为从“早期女性主义”转变而来的“后期丁玲”的开端引发诸多阐释并被经常引用。就史实而言,《水》记载的困境是20世纪30年代跨越数十省的一场洪灾。就主题而言,它关注的是现代中国农村的困境和庶民在困境中萌发跨出困境的某种转换。就本文所探讨的对隐性结构意识和日常胆识的融合而言,一篇大约只有两万字的《水》(24)参见《丁玲全集(第3卷)》第400-434页。下文对小说内容的引用均来自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越过30年代具体时段边界的隐性结构,拉开了一幅世纪长卷,携带着其中具体生命意象的种种特写,从个体到群体,其覆盖幅度达到了某种史诗的规模。从行文看,《水》由两重驱动展开:一重是即将到来、突然而来、呼啸而去的洪水的过程;另一重是在巨大不确定性中生存者的人间具象,在复调式流动中展开。小说开篇即是一面呈现出“茅屋下的一户农民家庭,聚集着全村的妇女,大家都一言不发。这些妇女怀里抱着小孩子,屏住呼吸在听着什么”,同时呈现出“风在送一些使人不安的声音,不过是一些不确定的声音,或许就是风自己走过丛密的树梢吧”;一面是“身体强壮的男人,无论老幼,包括十几岁的少年,都在几里长的堤坝上添加泥土和石袋;抓紧时间,赶在洪水到来之前加固堤坝”,同时是“深夜里,人们实际上还没看到洪水的时候,洪水就到来了:飞速的伸着长脚的水,在夜晚看不清颜色,成了不见底的黑色巨流”。一面是“从几十里,四方八面的火光中,(人们)成潮的涌到堤边来。无数的火把照耀着”;同时是堤坝作为用来控制不可预知之力量的物质实体和人类社会生活之组织的象征标志,最终决口;洪水命运般地席卷着人、物、生命,而人、物、生命在巨大的冲击中、存亡不确定中,作出不放弃自身存在的努力。在这复调的双重变奏中,具体生命在聚散之间瞬间凸显,从“小到五岁的老幺”、“七岁的龙儿”、已经懂事的“毛妹”、护着老幼的“三姑妈”,还有“二哥哥”“三爷爷”“菊姐”“大福”;更有成群成批外来而又命运交叠的陌生人,源源不断。而连接并贯穿这些凸显瞬间、在洪水过程和人间具象复调中出现的第三重驱动,撑起了笔者称为在双重复调中的隐性的结构性意识,则是由最日常具体又最匪夷所思的“外婆婆”来承载的。外婆婆是一位像草木一样普遍的存在:(老婆婆)“战战的用着那干了的声音”自言自语起来:“唉,怎么得了!水不要赶来就好。我一辈子经了多少灾难。我并不怕死,我就怕这样死,子子孙孙这末一大群……”当《水》的第一重行文驱动追踪着洪水的运动和难以测定的规模的每一次变化,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第二重行文驱动追踪着水中的失去或可能失去的人生,作为第三重驱动的外婆婆在这似乎永无终结的双重变奏中持续存在着:“几十年了,我小的时候,龙儿那样大,七岁,……我那时是七岁,命却不算小,我拖到了这里。事情过去六十年,六十五年了,想起来就如在眼前一样,我正是龙儿这样大,七岁,我有一条小辫子,象麻雀尾巴,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水,水……”(25)就20世纪30年代而言,洪水具有历史的特定内容。这具体内容和小说隐性结构意识所揭示的结构性和结构化(structural and structured)的状态的关系,见颜海平著,季剑青译:《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中的丁玲章节,第298页。就像是来自和穿过历史的脉动,外婆婆描述的场景指向了现代中国19世纪中叶的时空开端,这并非偶然。就其在国际格局中的处境而言,“现代中国”在这里是一个“被外在”于“现代世界”的结构性区隔之域,其内涵是百年中国被起始于“1648年合约”和欧洲公法规定的格局中的困境。《水》中外婆婆时显时隐的话语覆盖的时空,把这困境的世界性内涵和其中生命必须转换的世界性规模,放置在了书写的中心,跨越现代世界的时空区隔,潜在地指向了现代人类的核心命题。如果说现代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在不确定的时空里,生命由转换而绵延的后效如何无法预估确定;可以确定的是转换的努力本身。置身于被现代生物族裔政治运作限定区隔的“灾区之域”,《水》中的外婆婆作为其中众生凝聚的概括,成为与规定她们命运的机制时空的斡旋,示意着一种比她们身之所限的“灾区之域”更为具体而经久的人类时空(26)在对《水》的评价中,对外婆婆意象的聚焦和深入分析还不多见。笔者意在指出,在对意象中唤起的中华民族曾经“灭顶之灾”历史记忆熟习的同时(“龙儿不喜欢外婆提他的名字……有点怕起来,有点觉得在同不祥的事要接近了,他轻轻地向哥哥们的身边移去。”见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2页),更多的深入阐释将会带来有意义的生产性。。
从今天的角度看,在历史上曾经被困锁在人类人性的“病疫范畴”“非法范畴”“灾区范畴”的生命以各种形式移动和越过这些范畴的边界和语境的过程中,当事人文字中下意识的潜形结构触及、示意出的极限限制及其逻辑机制变得不仅可辨认、可解析,而且可移位、可变革。如果说命运的定义是人世间不可预知的结构极限在冥冥中的规定,在现代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字里和历史中,具体的“尽心力”在移动结构性限制的意义上发生了,历史命运的改写在具体尽力中生成。总体而言,这不是根据有意识的宣言、目标、计划、计划实施或改写;对于如同命运一般作用的世界生物族裔政治的社会性别逻辑,她们没有提供完整的理论准则和系统的观念把握;她们所做的,是在不确定的时代里,以“人有为”而“食其力”,以做事、尽力、尽心的日常韧性,实现着她们或移动或跨过给定边界的历史存在(27)笔者从1991年初至2011年底在美国高校执教时期中,数次听到同辈学人在英美语境中对现当代中国女性百年变革基本失败的评价,还记得当时的悲欣交集之感。悲的是如此评价中的语境错置和方法误差;欣的是如此教育良好、表述清晰的女性学人本身的实存,又正是百年变革生命力的见证。。这里活跃着的是一种双重视域、一种日常有为中隐含的对结构格局未成言说的潜在清醒、一种交织着大结构潜意识的日常胆识:在这里,对时空结构权力秩序的潜在感知,没有阻止而是孕育了这跨越其限定边界而求生开拓的具体有为,以及在过程中对各种具体存在和呈现方式的把握或不自觉的发明;而这日常的有为,是一种既知晓又移动结构性限制的具体胆识。现代人的真髓,在跨越以社会性别逻辑为基点的现代生物族裔政治的边界中转换生成。跨界转换者,在未知是否可为而具体为之的过程中,所生成的精神形态及其历史积淀,构成一种历史性现代生命开创的本源(28)现代生物族裔政治的反向逻辑及其双重机制(首先是作为“必然”——历史主导力量以自身的必然对他者的建构,其次是作为天然——他者属性自然化为天然属性),对于百年中国、包括被“欧洲性”化约排斥的欧洲和西方的众生相在内的世界史上诸种人生,都有一个从无法把握言说到有效把握言说的过程(比如不仅作为个体而且作为现象的福柯等战后一代欧洲人)。这一过程目前仍在继续。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柯意义上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al life)与泛符号学的重要差异,是对能指与所指相互交涉的历史实效及其后果的面对,对历史约定俗成及其逻辑机制的具体处理。数十年里泛符号学庸俗应用的话语衍生品,以悬置和解构遮蔽了产品制造者自身在能指与所指相互交涉历史机制中的生物政治属性及其功能。当下中国女性研究中对“西方理论依赖性”的反思,包括但不仅止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反思,更不是对“非本土他者”的建构;其中生成的思想资源,是人文学各个领域世界范围跨界转换和可能生成更新的一个部分。在塑造生活时空和世界秩序意义上的“性制系统”(sexuality)、生物权力(bio-power)、生物政治(bio-political)、生物族裔政体(bio-ethnic polity)、种族与族裔(race and ethnicity)等理念的拓展成果参考之一,见Diana Taylor,The Archive and the Repertoire:Performing Cultural Memory in the America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Elin Diamond,Unmaking Mimesi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Joseph Roach,Cities of the Dead:Circum-Atlantic Perform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其中绵密的信息,邀请着更为主动的知识生产(29)其中包含的命题或可开启诸种向度,包括主体性、主观性辩证关系说。此说认为人类的主体性是生产活动、群体关系、社会生活等积淀而成;人类的主观性是语言、观念、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积淀而成,两者在辩证的张力中相辅相成。而由于主观积淀的个体或群体差异,使人有可能由突破后者而改变前者,也就是内在人性对外在人文的突破或变异。在当下世界全方位变局和跨文化多重语境的流动中,这一思路示意出一种转换尝试,即由改变生产关系而推进社会生活的历史观,转换至由历史积淀的差异性形成并在差异中生成的各种“有为”驱动而改变现代主体构成及其社会内容可能性的探索观。。
三、路径:认知、伦理与审美、生成的共同体
这一不仅在中国并且在世界语境中发生的跨界之为、开创之力,这些在“尽心尽力”中发生的女性书写,作为一种以转换为特征的经验过程,迄今还在被研讨、被凝练,已成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成为对形成知识的路径获得自觉的过程。上文提到,这里讨论的“尽力说”在话语词汇上与传统儒家入世哲学有着移用性的关联(30)这一移用历史久远、构成另一个女性研究的现代母题。就其近期的延展及对延展的研讨,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11~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而其中的核心驱动内涵属性差异深远。无论是对于传统儒学内在规定的人伦等级理性,还是对于实施这理性的机制,即自隋唐起以唯男性士绅为用的科举体系,女性书写摆脱依附的价值人生带来的是根本性的变局,是旧邦的新命。对此移用性的关联和新命的把握和思索,仍在继续(31)早期对此研讨见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及其后续著述。笔者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中对这一维度的探讨,参见冰心章、袁昌英章。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费孝通先生的“非欧洲”逻辑的中国人类学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对传统儒学多元重访带来的资源和问题,都是对这一命题在当今知识大变局中继续深化研讨的厚重资源。。换言之,内在于笔者研讨的现代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字中、已被整理和还未整理的纷繁谱系中、谱系内含的层层叠叠生活记忆中,以及所有这些被阅读和再阅读的辗转延伸中的,是一种具体历史意义上现代人的生成(32)笔者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中,对文字书写和身体形式相互间内在互为、外在互动的处理,部分是对福柯意义上生命政治说的吸纳,更多的是指向作为动词的现代中国女性历史的形成;其重心不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实体主体或者对此主体的后殖民解构,而是指向具体有为的历史生成及其生成性的普遍本体价值。。其中包含的上文所称“未成言说的潜在清醒”、一种对世界结构隐性意识中的日常胆识(quotidian insight),与欧洲起源而覆盖近代世界文化版图的理性主体及其变奏构成了对话中的差异、差异中的叩问和叩问中变革的更新能量,作为现代世界文化历史的内在部分邀请我们的再认知。简言之,此前地理大发现、印刷术发明、基督教会分裂、欧洲中世纪终结和文化巨变等过程中,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天赋人权的发明,建立了人类理性主体合法性的立论,以认知、伦理、审美乃至本体等范畴的建立宣称了人类现代话语体系的创世纪,以及其后续三百多年覆盖从典章制度到语言宗教所有面向的观念形态和话语延展(33)与话语系统相关而又不同,典章制度指向判决(judgments)、条例(ordinances)、法令(decrees)、规则(regulations)等建制机制。,构成我们称之为现代西学的基础。其中的驱动,既有与上文所谈的1648年和约的地缘逻辑暨欧洲公法的世界性扩张相随的一面,又以其内在与地缘逻辑或对峙或紧张而更为普遍性的召唤,包括法国大革命以降左翼启蒙的激情,持续贯穿于现代话语体系的变迁和延展。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诸多“后学”对此西学基础的解析成果,亦离不开这世界化的西学基础本身(34)就欧洲而言,以天赋人权理性本源为界定的“个体主权”和以语言宗教为基质的“民族国家”观念,穿插运行在1648年合约国承认各自作为国家的主权地缘政治内涵、相互以强权均势逻辑建立和维系关系的过程中。而由天赋人权到启蒙运动及至法国大革命和之后的起伏变革中,所孕育所生成包括马克思主义为其左翼的人类精神所蕴含和承诺的普遍价值追求,始终又指向对强权均势现代逻辑的超越。德里达等后学对此有多面复杂的批判性认知,同时又是对其本源结构的差异性循环。这是跨文化理论研究的又一个命题。。如果说作为现代世界结构性的部分,中国现代人的生成是承载于具体(个体与群体)生命的转换实践、面对并移动自身的社会困境及其对人性区隔的边界,其中携带的是人对自身所处困境在转换自身中的变革。有学者这样提到跨界之努力:(这跨界)“不是因为(来自)令人喜悦的创造力过剩,而是由于(来自)渴望拯救的忧伤和痛苦”[21](P 375)。也许更准确地说,在对现代困境的跨界克服中,令人苦痛也令人喜悦的现代创造可能或者得以发生。不同于欧洲语境里源自人对神的统治的觉醒驱动,这克服困境的转换创造,作为一种生成的人的现代性过程,和现代西学的基石理念即由天赋人权而理性实体,既发生对话又将其从根本上改写。
首先是对认知范畴及其内涵的改写。如上文提出,在诸多现代中国女性作家的人生书写中,运行着对现代世界区隔结构的社会性别属性和社会性别化的世界秩序逻辑的隐性意识,其隐性不是减损而是深化了这意识的理性。这种深刻的理性意识,并不就指向对所意识到的结构逻辑的合理合法化。上文分析到这种理性意识内在包含的复调式意象流转,即融合“日常胆识”的诸种具象、形态各样的“她们”,没有“理性主体”应当具有的充分言说特征,“她们”不占有将世界化为客体、将他人造成他者的谓词高地;“她们”唤起的是一种韧性的清醒:在冰心式直面“一堆碎纸”之战争世界的“女作家”、丁玲式贯穿甚至穿过“百年洪水”之困境中国的“外婆婆”和诸多差异交叠的个体和群体意象,示意着一种与身体密切互融的感知洞识、与理性意识同行而又不同于将既定世界合理化之理性驱动的一种领会知晓,以多样的形式渗透并推动着这些女性书写。身体和头脑融合的心智力量,斡旋在或催生或阻滞她们延展的各种势能场域,移动或跨过结构性划分的势能场域、区隔边界及其社会性别化的生物族裔政治限制逻辑(35)这种“感知洞识”的文化(社会)性别及其动能,作为并体现为行为(有为)的历史判断,是对百年格局及其逻辑的回应。这是一种传递与之内在共存而又不可通约的回应、一种有为的回应,由此形成、成就了具有流动性开创性的现代认知。这种开创性是通过情感的认知方式获得的,并继续被认知、被获得,也就是被发现、被重生。此类领域中的社会性别化研究已获得诸多研究成果。而对流动性开创性认知的幅员辽阔的涵盖值得进一步探索,包括在何种程度上以社会性别为杠杆的流动性开创性认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意识的结构性维度和变革能量的重心。。换言之,这种感知化的理性运行或理性化的情感意识,其内核是一种融合性的灵敏度,对“在具体的身体内并且通过身体流转而强化的情感意识(felt awareness)”,特别是对意识到结构性权力世界而又不为其捆绑的情感意识的灵敏度;这灵敏度更新日常行为、生成历史意义;“作为一种灵敏的力量,她们不是情绪或感性的冲动”;她们活跃在有意识的认知之内,或者与有意识的认知并行和穿插,而同时有别于“有意识的认知”(36)参见Melissa Gregg,Gregory J.Seigworth,The Affect Theory Reader,Duke: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要言之,她们可以成为跨过各种场域势力关系安排的边界以构成反思时空的动能;联接已知和未知之域,甚至构成未知世界本身(37)有别于当下欧美研讨重在对“感性生产及其效果”(affect theory)作为“建构他者”之“理性主体”变体的解构、意识形态的揭示,笔者对“情感意识”的理解和阐释,来自亦聚焦于现代中国女性作家书写中的内涵和特征,要义是对欧洲现代主体重心的移位,对其中“建构他者”逻辑机制的扬弃,由此形成另一种现代性的能动路径。。
情感意识,作为认知的行为和方法,在笔者研讨的女性书写中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出现:这可以是在对现代世界“尽力”把握中出现的笔者称为“选择性盲点”的奇异持续,也可以是“选择性盲点”在持续中突变为结构性洞识的瞬间。前者在最早的妇女期刊的作者中即成为一种现象。1898年创办于上海,主笔包括薛绍徽、康同薇、裘梅侣、潘璇、张蕴华、蒋豌芳、刘可青等的《女学报》,每一期第一页上方都印有“Chinese Girl’s Progress”(中国青年女子之进步)字样;作者主要从欧洲和美国寻找资源。1902年陈撷芬创办的第二份女性报刊,随后出现的更多出版物,基本如此。如何认知这类“寻找”则需要更多面向的考量。比如笔者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中所分析的1907年创办于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笔炼石(真名燕斌)的范式性。她在一篇题为《女权平议》的文章中衡量了“中国形势”和“美国形势”之间的差距,前者为“女权之最不发达者”,后者为“女权之最发达者,举一切婚姻之自由,学问之自由,生业之自由,皆未曾为男子所专利,故不难渐趋于平等之域耳”;而“彼亦女子,吾亦女子,虽种族之不同,自造物视之,则同为女子而已,彼既能复女权于既往之时,吾岂不可复女权于未来之际?”[11](P 37)她似乎不甚了解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基石的美国法典在生物族裔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属性;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自1848年开始到炼石写这篇文章的60年来,女性远远没有赢得她们在婚姻、学问、生业的自由或选举的权利;而当她们终于在1920年获得选举权时,“有色女性”却被排斥在外,这种排斥持续了漫长的岁月,直到20世纪(38)直到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the 1965 Voting Rights Act)黑人妇女才真正有了投票权。参见Martha S.Jones,Vanguard,New York:Basic Books,2020。。其根据即是前文分析的现代生物族裔政治的反向逻辑及其结构性的历史运行惯性。而中国女性属于生物族裔意义上的“有色”人种。简言之,就社会角度而言,炼石的论断似乎信息量不足,对其中至关重要的现代生物族裔政治和具体机制似乎视而不见。炼石活跃宽阔的认知视野和书写语汇中,裹挟着的这种“视而不见”,在现代中国女性不同的书写中令人惊讶地重复出现,如同一种缺席的存在、感觉得到却看不见的意识结构;笔者称之为“选择性盲点”(39)夏晓虹对晚清妇女的研究提供了严谨丰富的史料分析,提供了对早期秋瑾反满意识的重要研讨。早期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反满意识与笔者本文讨论的现代生物族裔政治逻辑的区别在于,前者源于传统中国儒汉观念,还不是现代生物分类界定意义上的族裔政治。比如在对日本歧视中国学人的批评中,秋瑾始终没有将日本作为不同“种族”来看待的意识。而日本人作为不同于中国人的另一“种族”(race),则是明治以来现代日本对自身“主体”定位的基础。见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简言之,就这些书写包含的世界性认知覆盖度和思辨度而言,无论信息怎样不够充分,都无法解释这样的认知“遗漏”。换言之,“选择性盲点”无法以无知来解释,而更接近于“无视”,即一种进入了潜在理性意识但被感知层面的决定所悬置的状态、一种接近认知态度的认知方式,“彼亦女子,吾亦女子,虽种族之不同,自造物视之,则同为女子而已”;这一简明表述可以延展至全体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体上包括肤色在内的各种差异原与人性等级毫无关联,因此在这里被持续地忽略、忽视和无视了。这种忽略、忽视和无视中包含的东西,要比误读、误判或认知上的盲点远为丰富,她指向了前文所说的情感意识的核心:一种潜在地意识到结构性权力世界而又不为其捆绑的灵敏度。炼石“无视”(un-sees)内在于这种民族国家地缘政治结构中的社会性别和生物族裔的范畴;她坚持不去关注或者说实质上是拒绝去认识(也就是去接受)人类按性别、种族和族裔性划定区隔并由此构成现代世界秩序安排的合理性。笔者研讨的大多数现代中国女作家,在她们关于女性问题各自不同的表达中,都表现出她们和炼石之间“选择性盲点”的交叠或共鸣,在大量援引欧美现代认知资源的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遗漏”“忽视”“无视”其现代民族国家以生物族裔为基点的逻辑及其机制;这一过程中所孕育的主动认知的灵敏度,以其对所援引的信息的内涵移位、转换甚至置换,提供了改写现代主体认知构成运行的特殊资源。
这一灵敏度的主动认知能量,在笔者研讨的文字中随处可见。比如“选择性盲点”在持续中突变为结构性洞识的瞬间。笔者《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中分析的小说《红玻璃的故事》(1942),是萧红去世一年后骆宾基凭记忆对萧红口述的一个纪录。故事的主人公王大妈,“是榆树屯最愉快的老婆子”,她的丈夫在黑河挖金子,她女儿的丈夫也在黑河挖金子。王大妈“爱说爱笑,在屯里人缘好、生活顺”。然而隐隐中有一种“难过”在她身体里流动,一种形不成语言的潜在意识。这“难过”亦不改变她脸上的“欢笑”;从她自己为妻为母,到她的女儿为妻为母,深水一样延续着、延长着。有一天王大妈又一路笑语地去看她的也做了母亲的女儿,两人一起“吃了孩子的生日面,谈着家常话,是满愉快、满幸福的”[19](P 377)。天下雨了,女儿下暖炕,去后院收拾衣裳。然后小说的书写抵达了一个转折点。王大妈看到身边的外孙女小达儿手里玩着一个东西,笑着说“让姥姥看看”。她知道那是红玻璃花筒,“正因为太熟悉了,也没有注意”。当她闭一只眼向里观望时,突然失色,“她两只有生命力的眼睛”转而“直线的注视着小达儿”,孩子惊吓得几乎哭出来;王大妈立刻自惊说“别害怕”:
王大妈失神的那瞬间,想起什么来了呢?她回想起她自己童年的时候,也曾玩过这红玻璃的花筒,那时她是真纯的一个愉快而幸福的孩子。……(而她的女儿小时候也这样)……现在小达儿是第三代了,又是玩儿着红玻璃花筒。王大妈觉得她还是逃不出这条可怕的命运的道路吗?一出嫁,丈夫到黑河去挖金子,留下她来过这(笔者加:循环性的)孤独的一生?[19](PP 376-377)
小说从这一瞬间转换进入另一时空。回不到之前的“说说笑笑”,王大妈逐渐销声匿迹直至离世;而在她身体感知中的“难过”持续着、延长着,作为一种潜在的意识交织着一种清醒的情感对潜在意识到的内容的叩问,与丁玲笔下大洪水中的外婆婆在冥冥中相遇相拥,穿过百年中国的时空,互为见证。在这里,对冥冥中结构性势力机制深刻的理性洞识和对穿越机制、穿越生死的人性坚持,以最普通的具体意象,相望相守,互为融合。对于最普通最具体的女性意象万千变化、源源不断的理性唤起和情感揭示,是笔者阅读至今的现代中国女性作家书写的普遍特征。这里也许没有长篇系统的理论架构,也许没有登高激论的启蒙人物;有的是流水不断、水滴石穿般地没有停歇、流动辗转、不可动摇、不可阻挡的跨界之力,和在如此“尽心尽力”中生成的情感意识、认知政治(felt cognition as political epistemology)。
这样的情感认知政治催生了这些书写的审美形态,成为一种笔者在其他研讨中称作的跨界诗学(40)关于“跨界诗学”的跨国族、跨文化、跨文明动能,笔者曾经借助对欧美、中国和第三世界文学现象的探讨做过初步阐释。参见Haiping Yan,“Theatricality in Classical Chinese Drama”,Eds.,Tracy Davis and Thomas Postlewait,Theatricality,Cambridge: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2003;“Other Transnationals”,Modern Drama,2005,(2);“Transnationality and Its Critique”,Eds.,Ada Uzoamaka Azodo,Gay Wilentz,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Ama Ata Aidoo,London:African World Press,1999。,其内核是一种伦理的驱动:伦理化的认知审美,由审美而展开的伦理驱动;两者的动态结合,与西学自现代以来伦理和审美的范畴区分形成了差异对照。简言之,将女性生命摆脱出现代生物族裔政治逻辑所规定的“天然困境”的文学(审美)书写,对此逻辑既有理性认知,又有伦理超越。这一超越绝非是诉诸幻象的、不合理性的、非现实的或者“乌托邦”的界域。如冰心写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一首诗《纸船——寄母亲》:“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总是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这首诗写于1923年秋天,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史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对于冰心的个人生活同样如此。当时,军阀混战下的中国四分五裂,两次世界大战间歇的世界危机四伏,而冰心则在横跨太平洋赴美留学的途中。像我们之前讨论的海外之旅一样,这种为了寻求“先进知识”而从被动之域前往主动世界的旅行,是跨越既定秩序规定边界的尽心尽力、旅行者困境和摆脱困境的象征。她们对困境的意识孕育了她们的跨界,而跨界是改写将她们区隔于“文明人性现代世界”的逻辑规定本身。裹挟在巨变运动之中的诗人,轻柔地叠出了这些人性之船,这些小船跨越了时间化的空间,在大海中“一只一只”地连成长长的一行,唤起了“总希望有一只”抵达人类“母亲家园”的瞬间。这不是怀旧,而是前瞻;这前瞻不是单向线性的时间驱动,而是在与现代生物族裔政治逻辑机制的斡旋谈判中,对世界时空边界设置的更新移位,在更新移位中生命形态当下的转换与生成。笔者曾经写道:“对一个理性的头脑来说,这些生命之船在分裂的现代之海中挣扎梦想着彼岸的景象,本身唤起的只是无望。”[10](P 126)笔者需要对此作出限定并进一步说明,这样的“理性头脑”,正是本文分析的“情感意识”作为另一种理性构成,由对话而叩问的。这对话和叩问,旨在移动现代认知、伦理、审美诸种范畴的既定内容,在移动中生成差异性的力量;这力量可以成为吸纳、改写、融会、扬弃由这些范畴规定的现代西学及其局限的资源(41)这样的对话、叩问、吸纳、改写、融会、扬弃成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的阐释过程和作为动词的隐性结构过程。。以此对自19世纪90年代起现代中国女性作家书写长卷的重访,形成对从戊戌变法到两次大战后世界变迁的另一种视域,并由此或可呈现多重生成的现代中国文化版图,或可更新从欧洲覆盖世界的现代认知构架及其智性积淀内涵。
继言之,日常有为中对现代结构逻辑的隐性清醒交织着对大结构潜在意识中的日常胆识,两者的融合成就了现代中国女性作家的认知路径及其跨界诗学,以伦理化的审美和审美展开的伦理驱动,孕育出由跨界转换而生成的书写长卷。这一生生不息的长卷,笔者称之为生成的共同体,其中跨界流动的构成元素,以相互无法化约的形式与风格,在互为差异中互为推力、互为赋权。比如五四时期的冰心《寄小读者》所内蕴、凝聚和创建的现代阅读书写共同体,以横跨“作者读者”“儿童长者”“男性女性”“中国外国”诸种给定边界而互构互为的灵敏度,对生物族裔政治逻辑发出了举重若轻的叩问(42)如冰心本人示意,这书写全然不是“儿童文学”可以分类、归类、化约和命名。参见冰心:《我是怎样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队伍里去的》,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6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再如卢隐从1921年的短篇小说《一封信》到1934年去世前五天的《复赵清阁信》(43)参见王国栋编:《卢隐全集(卷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52-59页;《复赵清阁信》:“来示收悉,两日来复受感冒。足下如于不日来舍,当可晤谈抒怀也!如何?”载王国栋编:《卢隐全集(卷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9页。,或萧红从首发何处不详的早期小说《王阿嫂》里的小环到1941年从香港发往重庆包括给挚友白朗的一束信函(44)参见萧红纪念馆编:《萧红全集(第1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10页;萧红纪念馆编:《萧红全集(第5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97-178页。,无数多样的文本记录着横跨阶层、职业、地域、国别、年龄、性别和其他社会分类的共情维系。这样的维系在跨界转换中变奏延伸。抗战流亡最为严峻时期中袁昌英的小说《牛》(1942),写一头老水牛和一个小男孩之间无言以表的种种相互感知。有一天男孩坐在老水牛的背上去林中散步,被一只突现的老虎攻击。老水牛即刻保护男孩,和老虎搏斗,最后老虎听到猎人们靠近而转身退走,老水牛带着满身伤口用嘴把吓晕的男孩衔回了村里。家人见到回村的水牛和男孩,大惊失色,以为一定是老牛发疯伤害男孩,即用枪击毙了老牛。男孩醒来:“(看见)那头老水牛,腹部中了两枪,躺在地上,流了一大滩血。浑身筋脉索索抽搐着,正在那里挣命。……(男孩)只抱着牛头呜咽道:‘阿三,真的你要会说话就好了。’”一种古老而常新的语言,在男孩和水牛的身体中流动而共振;要求着、生成着包含认知、审美、伦理在内的现代感知共同体[11](PP 203-204)。而覆盖度更为宽阔、跨越物种的女性书写,则可以回溯到现代白话文文学的开端。1917年在美国求学的陈衡哲的小小说《小雨点》,作为早于胡适1916年《蝴蝶》的中国白话文学文本,近年来时被提及。而其中天地人间众生灵的流转交互,则有待得到探讨。小说以住在紫山巅上云里的小雨点为重心,经历了被风裹挟而去、与风伯伯和红胸鸟相遇、掉至地面泥沼的天地转换;然后在泥沼里发现了涧水哥哥,接着是河伯伯、海公公的款待。虽然海公公的家很大,小雨点还是想念家园。她在努力向着家园的途中累了,看到地上一朵青莲花提供停留之地,就在她枝叶上友情小憩。青莲花的生命期限到了,提出求助希冀:可否将小雨点吸入自己的花管以解干枯的命运,小雨点居然答应了。吸入小雨点的青莲花即刻水灵起来,并且将自己贡献给一个人类小姑娘佩戴在鬓发上,以抵达“美美与共”。人类小姑娘戴上了青莲花,但很快青莲花不再新鲜,被随意丢弃。青莲花逐渐干枯,小雨点欲再次奉献自己,但已经在青莲花管子里的她无法再起到拯救之用。青莲花安慰并承诺小雨点,明年将再次复活。青莲花消失了,小雨点发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干死池子。她恳求死池哥哥助力自己继续家园之旅;死池哥哥慷慨告知等太阳出来她就能回家。太阳公公果然出现,小雨点回到家中告知哥哥姐姐自己的人间沧桑,相约明年春天一起到地上人间去看望那复活的青莲花。小雨点是否还会和那人类小姑娘重逢,探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万物生灵之道(45)参见陈衡哲:《小雨点》,上海、北京:新月书店,1933年。故事示意出,在地上天上的万物生灵中,唯独人类漠视美美与共的生命力。?
从陈衡哲笔下的小雨点到袁昌英笔下的牛,从20世纪20年代女性新诗中的江海星辰到20世纪40年代贯穿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所有可以命名和无法命名的书写形式,唤起的超越人与人现代生物族裔政治设定的边界,包括超越人类与各种物种或存在物的区隔,不断延伸的意象谱系,提供了既啮合具体语境又转换延展的流动时空,邀请斗转星移中的差异性重访和生成性参与。将秋瑾的弹词《精卫鸟》(1905)置于这一现代中国女性书写传承中来看,其深刻度和重要性有了更多的可辨认性。从具体历史内容而言,《精卫鸟》讲述了五位中国年轻女性为走出旧制度宗族秩序社会性别的困境所做的奋斗,游学海外,以寻求自身在世界版图中还未可知的轨迹和内涵。弹词的戏剧部分,由鞠瑞、小玉、爱群、振华、醒华五位女性的相互对话构成;呈现出她们对“灾区化”的中国和动荡中的世界结构性的潜意识,由此显现她们在日常中做决定的胆识。同时,作为弹词形式特征的评述部分,如同希腊戏剧的歌队,充当了敏锐的感觉中枢,在把个人具体场景和世界巨变之间加以区分的同时又把它们连接起来,将这些女性的日常生活场景与一个全球性相关的语境并置、交叉及融合;她们既是现代世界的一个部分,又是它的具体症候。当她们最终决定实行她们的计划,跨越既定秩序的社会性别和族裔政治的极限去海外“看世界”时,她们就在现代世界的版图上开辟了一条路径,形成与现代世界肌理组织交织中的某种牵动、移动和后效深远的转换。第六回的结尾充满了弹词评书人对这种开辟怀有的兴奋之情。这兴奋为秋瑾研讨界提供了评判的根据,即弹词的基调主脉,基本是“同盟会现代国家建设的修辞形式及其可供阐释的意义纲领”(46)参见颜海平著,季剑青译:《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弹词引自第96-105页。。按秋瑾计划的二十回布局和章节而言,这一评判本身无可非议,尽管弹词只写了六回,留下后十四回没有文本身体的标题,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未完成时空。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有意识的政治设计,是以作品的文学复杂性为深层中介的。当秋瑾把整出弹词设置在中国古代精卫填海神话的隐喻之中[9](PP 463-528),精卫作为“尽心尽力”的具体意象成为本文所说的“日常胆识”和对长时段“结构性潜意识”互为见证的过程,一种孕育和寓意生成性能量的生命过程;这一生成性的能量,就本文探讨的内容而言是现代的。回到本文开头所说,与普罗米修斯来自神界、以牺牲自我而拯救人类不同,精卫来自人间;经由形式和内涵的转换,与向着福祉的人类互为同在,在跨界延展中鸣叫声声,生生不息。作为来自人类凝练人类又转换扩展了人类时空的精卫鸟,犹如人类和生灵万物并存和融会的媒介,在跨界中转换,在转换中生成,在生成中延续乃至绵延无尽,指向一种天地间或隐或显、韧性流转的推动力。这推动力所含有的“从零到一”开创性维度,内在于“零一互为”的“尽心尽力”,转换生成绵延流变的历史过程,其结构特征和文化内涵在与现代生物族裔政治逻辑的相左和斡旋中展开。
继言之,这种推动力的结构特征和文化内涵的展开,同时记录、揭示、对话和叩问起源于17世纪欧洲的现代生物族裔政治逻辑,包括其在漫长的19世纪和20世纪中覆盖世界的多重复制和不断变化的变异拷贝。当我们在追溯贯穿于现代中国女性作家书写过程中的这一意象结构及其推动力中,对丁玲现象的重访,不仅是题中之意,而且由此可能在揭示出丁玲书写的历史性和独特性的同时,或使笔者所称的“丁玲故事”及其世界性获得逐渐展开的可辨认性、合理性。一种由跨越既定边界的驱动氤氲而成的隐性结构意识,一种跨界转换而孕育生成的现代生命形态,以既啮合具体语境又转换延展的流动时空,以未成言说的清醒,横跨并携带着多重交叠中大变迁的历史语境,在丁玲作品中流转和延展:从梦珂、莎菲、韦护、母亲、野草、外婆婆、《新的信念》中的奶奶和她的全家及全村人、马辉、杨伍城、陆萍、贞贞、田保霖、黑妮,到杜晚香。作为精卫鸟鸟鸣声声、生生不息的转换流转,和世界上不同个体、民族、区域、国家、洲际的文学书写,在当下的又一轮巨变中的命运变迁相互交叠、发现连接,乃至在差异中可能的相互见证(47)世界各国学界包括欧美学界当下对复数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重访、对全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艺术谱系的全面追溯中,知识的再生产已经由后殖民的经典书写延展而涵盖全球不同语种的各个区域。参见Eric Hayot and Rebecca L.Walkowitz Eds.,A New Vocabulary for Global Modern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Mark Wollaeger and Matt Eatouch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这由跨界转换而氤氲孕育的过程,笔者称为生成的共同体过程;对其中的内涵在认知、审美、伦理和本体意义上的探讨,旨在对话、叩问、改写、移位乃至可能溢出以这些范畴的建立作为基础的西学,并宣称的作为人类现代话语体系高地的现代性本身(48)“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各流派包括汤尼·白露(Tani Barlow)对中国妇女思想历史和丁玲解读的洞见和局限,在此西学基础、现代生物族裔政治逻辑的框架中或可得到更有生产性的显示。参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11~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93-604页。。如本文开头所说,这过程以其内在于现代中国女性作家书写中的“生成的现代性”(generative modernity),指向在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上反复出现、跨越现代生物族裔政治强权均势逻辑及其各种具体版本,在跨越中由转换而更新的能量,指向她们有待认知的生命形态和历史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