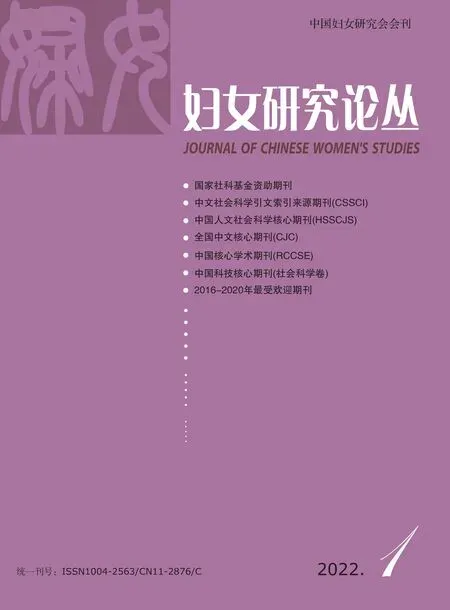老病新医:近代中国乳腺癌的治疗变革、知识传播与社会认知*
姚 霏
(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34)
医疗社会史学者李化成指出:“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公共健康史的研究领域被进一步拓宽了。这一方面是西方学术创新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新的疾病和医疗形式极大地影响到了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其中慢性病问题的凸显尤为重要。”[1]慢性疾病是指不构成传染、具有长期积累形成疾病形态损害的疾病之总称。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慢性疾病代表的癌症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方向,不能脱离疾病本身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围绕着癌症,西方社会在疾病史领域已有大量探索(1)关于西方癌症史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参见拙文《当代中国疾病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与未来方向》(《文汇报·文汇学人》2020年6月5日,第4、5版)。。
乳腺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2021年,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发表了一项基于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GLOBOCAN2020)的描述性研究。该研究分析了全球癌谱变化和中国癌症负担的变化概况。研究显示,2020年,女性乳腺癌首次超过肺癌,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癌症类型。具体到中国。2000年以来,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居高不下,且呈递增趋势。最新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国女性癌症患者中,主要癌症类型就是乳腺癌,占全球女性乳腺癌病例的18%[2]。
目前,中国学界对乳腺癌的研究涉及中西医诊断、治疗、筛查技术等的发展,停留在医学领域,很少分析乳腺癌防治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因素(2)围绕癌症,西方社会在疾病史领域已有大量探索。具体到乳腺癌领域,Ellen Leopold的著作A Darker Ribbon:Breast Cancer,Women and Their Docto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Boston Mass: Beacon Press,1999)揭示了合理化医疗保障体系建立的艰难过程,剖析了政府、企业和民众在一场关于乳腺癌的战争中是如何相互博弈的;Barron Lerner的The Breast Cancer W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以女权主义视角申斥了男权主导下的医学界在乳腺癌诊疗话语方面的垄断,随着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思潮对男权主导下传统的乳腺癌治疗话语的解构,乳腺癌治疗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James S.Olson的专著Bathsheba’s Breast:Women,Cancer,and Histor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2)中系统梳理了自20世纪以来医学界关于乳房切除手术的争议、放射疗法与化疗方法在乳腺癌临床治疗中的效用评估、他莫昔芬等化合药品的临床使用等问题;Robert A.Aronowitz的专著Unnatural History:Breast Cancer and American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讨论了乳腺癌对美国社会的影响;Ilana Löwy的论文“Cancer du sein et tamoxifène: la gestion d’une incertitude thérapeutique commentaire”[Sciences Sociales et Santé,2012,30(1)]研究了药物他莫昔芬如何被发现并投放市场,揭示了治疗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冲突利益;Macro Lacrois的A Concise History of Breast Cancer:Cancer Etiology,Diagnosis and Treatments(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13)中介绍了乳腺癌的疾病历史,并聚焦 20世纪乳腺癌在检测、病理分析和临床治疗等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Kaartinen Marjo的Breast Canc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aylor & Francis Group,2015)通过整理、运用当时乳腺癌患者的私人信件、日记和医学处方等一手原始档案发现患者并非被动的接受医生的癌症治疗方案,而是凭借自己的癌症观念和对诊疗方法的判断主动参与乳腺癌诊疗过程。此外,Sakorafas和Michael Safioleas的“Breast Cancer Surgery:An Historical Narrative:Part II.18th and 19th Centuries”[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Care,2010,19(1)]和Collins John P.的“Mastectomy with Tears:Breast Cancer Surgery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ANZ Journal of Surgery,2016,86(9)]介绍了18至19世纪乳腺癌外科手术的发展脉络,并将乳腺癌手术中存在的巨大手术感染和复发风险同医学伦理和女权等问题相结合加以考量。而在中国,虽然也有对乳腺癌外科手术历史的回顾性文章,如赵涛、郑泽霖的《乳腺癌手术的历史演变》(《中国现代手术学杂志》 2001年第4期),高根五的《乳腺癌手术的历史演变及其展望》(《医师进修杂志》 2001年第9期),段学宁的《乳腺癌手术治疗百年历史回顾与启示》(《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18年第11期)以及高金波、史雯嘉的《乳腺癌外科手术发展史》(《中华医史杂志》 2004年第3期),但这些研究很少关注乳腺癌诊疗在中国的历史情境。在中医领域,研究则更多总结历代乳腺癌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同样很少涉及医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本文将医学与史学进行学科交叉,以近代中国乳腺癌的治疗为研究对象,考察近代西方医疗技术传入中国过程中,女性身体疾病观念、中医治疗传统、近代移风易俗和知识更新如何与之互动,以期从一个侧面展现近代中国癌症防治的历史理路。
一、“不完美的福音”: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的乳腺癌手术治疗
一个半世纪前,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广州眼科医局中摆放着一批特殊的人物油画。画中的人物身上多有形态和尺寸夸张的肿瘤,试图彰显前来求治的中国人的病态以及西医医院带给中国人的福音。
1835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广州眼科医局,标志着近代西医治疗场所在中国大陆的建立。传教士认为,医疗是接触中国一般民众最有效的途径,是打开古老中国社会的钥匙之一。鸦片战争之后,“医生兼教士来华者日多;各地西式医院,亦逐渐设立”[3](P 189)。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初,发现中国人最高发的疾病主要是眼疾、耳疾和肿瘤。与此同时,他们发现在中国社会,女性是体弱多病的代名词,又因传统尊卑观念的影响,女性健康被关注较少。传教士发挥西方医学在外科领域的特长,将女性常患肿瘤纳入早期手术的范围。
19世纪中叶后,随着人体解剖学和细胞病理学的发展以及麻醉学、无菌学的临床实践,肿瘤治疗进入手术时代,剖开身体以切除肿瘤成为西医的常用治疗方式[4](PP 66-67)。根据考古学和古代病理学研究,乳腺癌应该是人们最早尝试通过手术治疗的肿瘤,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仅医学文献中提到的手术就有帕雷(Pare,1510-1590)的肿块切除、维萨里(Vesalius,1514-1564)的局部广泛切除、塞维里努斯(Severinus,1580-1659)的切除胸肌和腋窝淋巴结的根治术以及赫斯特(Heister,1683-1768)的切除肋骨的扩大根治术[5]。19世纪初,西方医学界已经逐渐意识到仅仅通过切除肿瘤,并不能治愈乳腺癌。乳房切除术成为当时治疗乳腺癌的重要手段。英国女作家法朗塞斯(Frances)在回忆录中记录了1811年她所经历的乳房切除术。她写道:“医生迅速地割去乳房,助手们立即用所有手指压住出血处,然后很快地缝合伤口,再用5寸宽、6-8米长的亚麻布绷带加压包扎,包扎后血液逐渐浸透了所有的绷带。”[6](P 5)由于缺乏良好的麻醉、止血及抗感染措施,这样的手术必须在几分钟内“闪电式”进行,且成功率不高。从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乳腺癌手术也能看出端倪。
从1836年广州眼科医局的报告可知,该院全年收治了5名患乳腺癌的妇女,但没有关于她们病况的描述[7](P 55)。而可知的第一例中国女性乳房切除术于1837年6月开展。详细病况和手术过程被记录在《中国丛报》上:
No.3556,5月22日乳部硬癌毛氏,48岁,家靠近黄埔,是一个花匠,已经罹患乳房肿瘤6年。患病面积有4英寸宽、6英寸长、2或3英寸厚。患者已经经历了漫长的痛苦。静脉有些扩大,最靠近腋窝的部分变柔软且即将破裂。腋窝部位不受影响。患者时常抱怨有些部位尤其肾脏有些疼痛。舌头上有些恶臭,脉象自然。6月21日,乳房被切除。皮肤与腺体的粘连,将手术延长到二十分钟,患者忍受了失去性别特征的痛苦……最痛苦的感觉是由于腺体基底的神经分裂造成的。第二天发生了可疑的发热症状,但很快就消退了。她的创口迅速且完美地恢复,于8月1日出院。10月份,她的身体恢复了健康。这是对中国女性实施的第一例乳房切除术,有限的几次手术已经可以清晰地证明她们对于外国外科手术的更大信心,而且是以最大的快乐表达这种信心[8]。
从这段记录来看,手术过程由于皮肤与腺体粘连延长至20分钟。不久,患者毛氏介绍另一位患乳腺癌的妇女前来诊疗,并进行同样的手术,验证了正常手术用时更短。
No.4016,乳部硬癌的摘除术吴氏,43岁,家住黄埔,由毛氏介绍而来,对同样的疾病进行治疗……吴氏左边乳房上腺体严重扩大已经三年……肿瘤得到确诊,这种疾病严格来说对患者有很大的影响。她的状况良好。11月1日,乳房在八分钟内被摘除,患者在床上躺了二十分钟。她的坚强意志超过了我所见过的所有人。切除过程中,她几乎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下手术台前,她还带着真诚的笑容握手感谢当时在旁帮忙的人……第10天的痢疾发作阻碍了她的恢复,大概四个星期的时间恢复好了。这位女性的自然、温和与乐观感染了许多她住院期间的参观者。确实,中国人常常保持着自然的恬静性情[8]。
吴氏的病情没有毛氏严重,手术过程仅8分钟,可见手术较为简单粗糙。记录指出“切除过程中她没有发出一声呻吟”,点明当时的手术是没有麻醉药物的。两则病例各有侧重,相互补充,为我们还原了中国最早的乳腺癌手术过程。不过,即使是在当时手术技术较为成熟的广州眼科医局,乳房切除术的成功率仍不高。据该院《截止1838年12月31日的第9份报告》记载,当年所做的5例乳房切除术中,有2例失败。这不仅由于手术环境较为落后、没有麻醉和消毒,更由于患者术后只能依靠很少的药物和自愈能力支撑,一旦术后恢复不好,就极易失去生命[8]。
从留存的乳腺癌治疗史来看,19世纪中后期,外科医生已经认识到手术刀需沿正常组织切割,不可切入肿瘤。20世纪初,由中国医生开展的一例乳腺癌手术,也遵循了这一原则。熊辅龙曾留学日本学习外科,对乳房切除手术有一定经验。1912年,他开展了一例乳腺癌手术:
予遂嘱其割日不得饮食,宜空腹来。是日正午果来。于遂令女医松雪预备器械,乳部消毒,于下午一时十五分,令女医专司麻醉事……于是右手执刀,切开皮肤二处,长各五寸余,两端切开处相接作椭圆形,次以周围皮肤与筋肉剥离,又将核之周围相联之筋肉剪断,以指探之,核根已蔓延于肋骨,若再过一二月,将穿胸壁而溃肺。其时血流如注,观者失色,不敢逼视。予以最迅速之手段,一举而核出,掷地砰然。急将大小血管用线结扎之,血流稍减。次缝皮肤,因患处割去太多,几不能合……未几麻醉性去,人亦苏醒,视钟,动手时间,阅二十四分;麻醉时间,达三十六分。检麻醉瓶,用去二十七格兰姆[9](P 12)。
从这次手术来看,首先,术前有专人进行消毒,无菌法能有效避免细菌滋生。其次,术前进行全身麻醉,可以有效减轻患者的痛感并有利于医生从容手术。关于麻醉前需空腹的常识也已经具备。不过,这次手术也存在问题。早在1852年,随着乳腺癌的淋巴转移规律被发现,美国医生潘科卡斯特(Joseph Pancocast)提出不仅应该行全乳切除术,当腋窝淋巴结受累时应该行腋窝淋巴结清除术。乳腺癌手术开始切除区域转移的淋巴结,手术范围不断扩大[10](P 34)[11](P 4)。这个病例中,患者的肿瘤“大如手拳”,但从文字描述来看,医生并未探查腋窝淋巴的情况。显然,从手术室人手缺乏和止血技术落后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乳腺癌手术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19世纪末期,著名外科学家和病理解剖学家霍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和病理研究,对乳腺癌的扩散途径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乳腺癌的扩散是遵循时间与解剖学规律的,先是肿瘤细胞的局部浸润,后沿淋巴道转移,最后出现血行播散。因此,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若能将肿瘤、乳腺及区域淋巴结完整切除,患者就能获得治愈。于是他在1882年创立了乳腺癌根治术,即整块切除包括肿瘤在内的全部乳腺、相当范围的乳腺皮肤和周围组织,以及胸大小肌和腋窝淋巴结[12]。根治术开创了乳腺癌外科手术史上的新纪元,大大降低了复发率,明显提高了长期生存率,被誉为乳腺癌手术的经典术式。至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乳腺癌根治术的理念已经开始在中国外科领域传播。1924年,路福在《广济医刊》中撰文提出:“去岁于本院妇女病房计施割术者,乳癌占十分之一〇三。”[13]尽管从作者描述的23例手术中,不能看出是否实施了根治术,但从其指出的手术原则——“不但将已被侵害之乳组织,尽行割去。即未被侵之乳组织,亦当割去尽净。不独此也。即腋下之淋巴腺,在为割治之先,须细心检查,稍有变大,亦当割去。总之凡割乳癌,不可稍存姑息之心。宁使缝合之皮边不足,而不可留癌组织于内”[13]——来看,医生是否将病变部位和所有邻近组织全部割除,成为手术能否成功的要旨。另外,相关的手术禁忌和手术步骤也传入中国。1927年《齐鲁医刊》登载的《乳腺癌截除术之要点》中已经提及8类手术禁忌,同时指出霍氏乳腺癌根治术的有效性,并指出术式的调整:“大多数之外科家施手术前先将腋处完全剖开,而后截除其乳腺”,原理在于“腋处设有不能截除之淋巴腺能早看出以便中止其手术;当手术之初即切开淋巴管,则少有癌细胞散于伤口之危险,且血管亦早已缚妥,故少有出血之弊”[14]。同年,光华医校《医事杂志》亦有一则治疗妇人乳腺癌的病案,先麻醉,再采用乳腺癌根治术,自腋下开割,将受累变大的淋巴腺与乳房一起割除,最终康复[15]。不过,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没有证据表明根治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已广泛开展。
尽管经历了近百年的实践,但患者对于乳腺癌手术的感受,并不如传教士伯驾在《中国丛报》中提到的那般愉快而充满信心。手术治疗是西方医学相较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主要差别之一。中国早期医学也有外科手术传统,但随着明清之后中医外科手术的衰弱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观念的强化,手术治疗从传统中医中消退。这增加了中国人对于手术治疗从文化到情感的抵触心理。中国女性对手术常有畏惧之心。只有当病情恶化到一定程度甚至危及生命时,才可能接受这种疗法。在5707号病例中,患乳腺癌的刘福在医院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按医嘱返回家中,因突发大量失血不得已接受手术治疗:
她按医嘱返回家中,环境的变化使她好转一些;但是,在12月16日她自发性地出了12或15盎司的血,这使她非常虚弱,脸色苍白。显然,再多几次这样的出血是致命的。于是她决定在失血重现之前切除乳房,她就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好转,这是延长她生命的唯一机会。因此,12月22日,她的乳房被切除。丈夫了解到他妻子的危急情况,明白如果任由病情自行发展,一种迅速致命的结局是很可能的事,但也许摘除手术可能会成功。他作出了通常的选择[16]。
1879年,博济医院开展了10余次乳房肿瘤切除手术,从其中详细记载的5例病例来看,患者多为中年或老年,大部分患者都是在患病较长时间、肿瘤体积较大、肿瘤的生长已经严重影响生活后才就诊的[17](PP 27-28)。南通医院熊辅龙治疗乳腺癌一案中,当医师告知患者“只能施行开割之术,否则不能除根”时,“患者首肯,而心惧之,遂敷以药令归”。而后患者也是犹豫再三,才在医生的再次催促下到院进行手术[9]。有日籍西医在广州博爱会医院开展乳腺外科手术,统计了1926年至1931年5月在该院治疗的87例病例,全部患者都是中国人,他们主要来自广东以及邻近的福建、广西、浙江、湖南、江西等地。患者中,女性占到98.9%,年龄最小为25岁,最大为70岁,45-55岁占比最多;其中41.4%的人感到疼痛,肿瘤大小如拳者占大多数,71.2%的患者肿瘤已经粘连他处,83.2%的患者出现转移[18]。显然,不到病情发展迅速、疼痛难忍以及肿瘤巨大的程度,患者一般很少求助于手术治疗。
当然,这种心存顾忌的原因并非一成不变。除了对手术的恐惧,手术治疗乳腺癌的效果不佳也是重要原因。乳腺癌手术后的复发在手术治疗传入中国之初就困扰着中国患者。1879年4月8日,来自顺德的一名45岁的患者接受了乳腺癌手术,并于4月30日出院。但很快,同侧乳房又出现了肿块,在6月10日再次接受手术。在伤口愈合之前,另侧乳房又发现了肿瘤。尽管进行了第三次手术,但没有产生任何益处[17]。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梁启超记载的家人病情中。梁启超对西医的认可度很高,一度大肆宣扬西医的益处。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罹患乳腺癌去世。梁启超在《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讣告:
夫人体气至强,一生无病。民国四年冬,忽患乳癌。乳癌,诸中最酷毒者。全世界医家,迄今未得其病因及救治法,惟恃割治,割必复发,发至不能割,则束手焉。夫人自得病以来,割既两度。今春冉发,蔓及项协之际,与血管相接,割无所施。沈县半年,卒以不起。然夫人性最能忍,虽痛苦至剧,犹勉自持……最后半月,病入脑,殆失痛觉。以极痛楚之病,而没时安隐,颜貌若常,岂亦有夙根耶。哀悼之余,聊用慰藉而已[19]。
梁启超认为乳腺癌是癌肿之中最“毒”的,治疗之法只有割治。然而即使梁夫人采用西医开刀割治之法,发病后的8年内两次手术,还是复发转移,最后半年被病痛困扰,极为痛苦。同年,外科医生路福在文章中说明:“记者于去年割治乳癌二十三人中,外皮已溃烂者十五人,尚未溃烂者八人。十五人中割后因外皮不足以缝合、未收口而复发者三人,收口出院得报告而复发者四人。”事实上,手术者自己也承认:“然割之非难,而割后必能保其不复实匪易。因割时不能预知癌细胞果不散布于邻近组织也。”[13]在1925年的《中医杂志》上,中医吴承忠记述了患者金夫人的经历。金夫人因患乳腺癌“曾入某西医院,行开割之术,并去其腋下之核,剜其左臂股皮,以填补其乳际,虽觉微痛,而一星期出院矣”。然而,“金夫人以第一年三月间开割,至第二年三月病复作,较旧患处稍偏,且痛甚。久则周身经脉牵引,人瑟缩如猴,痛苦难以名状。金某见状怆绝,为之百计求医,又用按摩术,欲以减少其痛苦,并日服滋养品。至第三年三月间而亡。所费近万金”[20]。可见,西医的刀圭并非无往不利。
1928年,医学传教士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在《中国的疾病》一文中,根据其搜集的中国各省医院的癌症手术病例,对1133名患者展开统计分析,发现其中手术量位列前三的分别是乳腺癌、阴茎癌和子宫癌,分别占总病例的18.19%、14.04%和12.36%[21]。乳腺癌手术高居中国女性癌症手术前列的事实毋庸置疑。但手术治疗的创伤性和复发问题使其成为“不完美的福音”。中国女性的乳腺癌治疗显然还需要其他手段。
二、古老东方的智慧:中医乳腺肿瘤治法的近代情境
虽然《申报》等媒体自19世纪80年代起就发表《西医妙手》《西医治疾》等称赞刀圭之术神奇的文章[22][23],但是中国民众对于手术剖开身体仍怀有畏惧之心。而在癌症治疗方面,手术并非万能,术后依然难以避免复发。对此,中医始终质疑西医动辄手术的效用。有中医师指出:“人尝言,西医擅外科,中医长内术,以乳岩一证观之,又岂其然。盖西医器械虽精,手术虽工,不能揣其本也。”[20]有中医师认为相当一部分乳腺癌患者虽经手术,但不久又会再发,直至死亡。因而“乳岩之症,万万不可剖割,若行解剖,势必立毙,无一幸免,是妇人病外科系第一重要之问题也”[24]。更有人对盲目迷信手术的观点痛心疾首:“外科各病不要迷信手术,汤药消疮,百倍于刀割锯,无如人不到病时,不知求些常识,到了临头轻则连年累月的受着痛苦,或残废了终身,甚至抛妻弃子脱离了家庭而往极乐之境,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呢?每为截去肢体、剖腹、割取乳痈者难!不过乳痈割了不过是受些痛苦,不致丧生,如乳癌割了直可置人于死!”[25]中医直言西医手术带来的痛苦,且认为乳腺癌手术后更易致人死亡。
中医之所以敢于挑战西医手术的权威,源于中医在乳腺疾病治疗方面的经验。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千百年来,不少医家积累了乳腺疾病的治疗经验。古代中医对于乳房肿块常有“乳痈”“乳疽”“乳癌”“乳岩”等表述。“乳痈”第一次出现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其卷五有“葛氏治妇女乳痈妬肿”并附医方[26](P 139)。“乳疽”出于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卷四十“疽发乳候”:“足阳明之脉,有从缺盆下于乳者,其脉虚则腠理开,寒气客之,寒搏于血,则血涩不通。”[27](P 128)“乳岩”与“乳癌”则出现在南宋。“乳岩”首见于陈自明的《妇人良方》,认为乳岩初起是一结核,“或如鳖棋子,不赤不痛”,若不治疗,年岁愈长,渐愈增大,“峻岩崩破如熟榴,或内溃深洞,血水滴沥”[28](PP 449-450)。提出“乳癌”概念的是杨士瀛。他在《仁斋直指方论》的《发癌方论》一文中详细描述了“癌”的形状:“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裂如瞽眼,其中带青,由是簇头,各露一舌,毒根深藏,穿孔透里。男则多发于腹,女则多发于乳或项或肩或臂,外证令人昏迷。”[29](P 575)以上四种提法都有乳腺肿块的表征,不过,从症状描述上看,乳痈、乳疽多为乳房良性疾病,一般只要对症下药,即可痊愈;而乳癌、乳岩在医书中,有不少疑似恶性肿瘤的症状记载。
宋代以后,疡科方书中“癌”惯作“岩、喦”。元代医家朱丹溪的《格致余论》《丹溪心法》《脉因证治》《朱丹溪医案拾遗》等书,出现了对“奶岩”(即乳岩)的描述,其症状多有与恶性肿瘤相似者。如“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浅者为痈,深者为岩,不治”。“妇人此病,有月经悉轻病,五六十岁后,无月经时不可作轻易看也。”[30](P 63)[31](P 94)明清医家对“乳岩”“奶岩”病状和患病人群等认识不断深入。在病状方面,明代龚廷贤指出:“妇人奶岩,始有核肿,如鳖棋子大,不痛不痒,五七年方成疮……赤汁脓水浸淫,胸胁气攻疼痛……此症多生于忧郁积忿中年妇人。未破者尚可治,成疮者终不可治。”[32](P 519)由于奶岩后期浸淫,胸胁与乳腺癌转移症状颇为相似。基于前人对乳岩的经验,明代陈实功有一总结:“(乳岩)凡患犯者,百人百必死。”[33](P 123)此后有许多医书采用陈氏表述,如清代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1805年)、马培之的《马培之医案》(1893年)等,都将乳岩视为不治之症。甚至在患病主体方面,明清中医也已经意识到乳岩不仅是女子常患的,男子也会得此病,只是以中年丧夫的女性为多。如清代林珮琴的《类证治裁》(1851年)阐明:“乳岩……男妇皆有,惟孀孤为多,一溃难治。”[34](P 560)上述论述为中医界所共认,极具代表性。清代医家也有关于“乳癌”的记载,如“定癌散用两头尖、土楝(子)、蜂房各研。疡毒根深在脏腑,乳癌非此不能痊”[35](P 5)。马培之则在医案中阐明乳癌是一种男女皆会患的疾病,“惟妇人更多,治亦较难……癌则硬处不痛,四围筋脉牵制作疼”[36](PP 34-37)。
总之,到19世纪下半叶,中医对乳岩、乳癌的患病情况已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就患病人群而言,已能确认男女都会患该病,只是妇女尤其多发;就患病年龄而言,中年为高危期;就病因而言,多因除喜之外的六情所致,加之女性本身阴寒内盛,导致内部机制失调,“气滞血癖,日久则聚痰酿毒,凝结于乳中而成癌”[36](PP 34-37)。中医对于乳腺肿瘤的论述记载,甚至得到了医学传教士的认可。1857年,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的《西医略论》的“痈疽论”开篇,提到“痈疽”与“瘤”的区别:“痈疽亦瘤类,但瘤无毒”,“痈疽则始生即有大毒,毒非外来,实即身内所生”。不过,合信也特别说明,这里所谓的“痈疽”,除了“乳痈与中土所论同,余则异”。也就是说,合信认为中医中的“乳痈”确实对应了西医中的恶性肿瘤,而其他所谓“痈疽”并非专指恶性肿瘤,只是碍于没有对应的病名,所以“借用中土之名以立说”[37]。可见,在西医恶性肿瘤的概念传入中国之初,医学传教士认为中医已经发现了乳腺癌。
在治疗方面,中医仰仗传统经验,主要遵循对症下药的原则。总的来说,在中医看来,乳房属肝,生瘤主要是由于忧忿郁闷、肝火旺盛,因而如果发现得早,建议对症用疏肝理气、凉血散结以及调补气血、养心安神的中药方为主要调解,再外敷药膏,内外同治,特殊病症用以针灸亦有奇效。内服疏肝理气的方药主要是瓜蒌散、归脾汤和丹胡逍遥散。这三个药方几乎在所有的中医典籍中都有记载,主要由当归、白芍、茯苓、白术、瓜蒌、贝母、川穹、人参、枳壳等中草药佐以甘草综合组成,在乳岩初起时服用有疗效。外用药膏主要是季芝鲫鱼膏、绛珠膏和生肌玉红膏,效用在于去腐生肌,促进疮口收敛。进入近代后,中医名家马培之、余听鸿、丁甘仁等,都有治疗乳岩的医案传世,主要仍遵循上述治疗原则。如1892年出版的《外科传薪集》中,马培之给出的“治乳癌初生方”,主要即为“青皮、石膏、生甘草节、瓜蒌、橘络、皂角刺、金银花。水煎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关于乳腺癌治疗的原则仍以“解郁理气”“解郁理气、和荣化痰”[38][39]为常见。
虽然各朝代的医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总结出更适用的药方,可就治疗结果而言,大多数中药方只适用乳岩未溃烂的病者。而一旦溃烂则难治,且不可采用攻伐太过的药方。《医宗金鉴》中指出,乳岩迁延日久,“疮势已成,不可过用克伐峻剂,致损胃气,即用香贝养荣汤。或心烦不寐者,宜服归脾汤;潮热恶寒者,宜服逍遥散,稍可苟延岁月”[40](P 233)。1839年出版的《类证治裁》记载了一例医案,一名妇人患乳岩六七年,患处溃烂深凹,疼痛不堪,用八珍汤(人参、白术、白茯苓、当归、川穹、白芍药、熟地黄、甘草)缓和病情[34](P 564)。八珍汤主要用于调和,起到培补气血的作用,对病情并无明显疗效。由此可见,中医也没有治愈晚期乳岩的良方,只能做到减轻痛苦、延缓病情。显然,在乳腺癌的治疗中,中西医对晚期患者同样束手无策。
随着西医东渐的深入,传统中医医理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西方科学话语的“拷问”。1925年后,中西医界的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其后的民国社会一度掀起多次废止中医风潮。这一时期的中医界,面对来自西方医学的强势,努力与其展开对话。当时的中医期刊中可以看到不少关于中西医乳腺癌治疗得失的比较。1925年,在《乳岩证治之索引》一文中,擅长妇科的陈无咎开篇就提到“乳岩,西名乳癌……为危险病症”,“西医之经验宏富、学理明通者,视此症为畏途,群决为不治之症。其卤莽灭裂、知识谫陋者,屡而奏刀,因而致死者比比。故乳岩一症,万万不可剖割,若行解剖,势必立毙,无一幸免”。随后,作者提到中医认为乳岩是“由于肝脾两伤,气郁凝结而成……唯有内消一法,此西医之手术不如中医之汤剂也”,并给出了神效瓜蒌散、清肝解郁汤、香贝养荣汤、归脾汤、逍遥散等方剂[24]。在中医学校学习的朱秀娟,也已经能将乳岩对应西医的乳癌,而她更多看到中西医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相似处境,认为“乳岩是乳疾中最难治的一种病症。无论中医西医,都没有一种相当的治疗”[41]。
20世纪30年代之后,尽管中医治疗乳腺癌的总体理论、药方与传统时期并没有很大变化,但不少中医开始有意识地对应西医的乳腺癌治疗范畴讲述中医治法。例如,鉴于西医乳腺癌治疗集中在外科,针灸等中医外科治疗乳腺癌的方法开始在医药报刊上出现。如《妇人乳岩证之实验一席话》一文中就提到用艾灸[20]。1931年5月18日的《申报》中提到中医方慎盦用金针治愈乳腺癌的案例[42]。《针灸杂志》1933年的《乳岩重症灸力化险为夷》、1937年的《针灸验案汇编:验案一束》等文章中也记载了针灸治疗乳腺癌[43][44]。
更值得一提的是,部分中医杂志中已经出现了中西汇通的治疗乳腺癌的记录,显示出难得的融合和创新意识。1939年,沈宗吴在《乳岩》一文中提到,乳岩的原因是“与遗传及情志之郁结有关”,在“预后”中提到“初起硬块,能用内服外敷之方法消散,或外科手术摘出者良。若肿硬附着胸廓,既侵及锁骨部淋巴腺、腋窝腺,与周围血管神经愈着而转移于远隔部时不良。穿溃者更不良”。同时提到三种疗法,首先是手术。“初起即可使用全身麻醉摘出乳腺。若肿毒侵及胸肌及腋窝腺者,亦当一并切除之。”其次,作者提到了外敷法和内服法。外敷法包括“海浮散”“消核膏”“石炭酸水”;内服法包括“逍遥散”“解郁化坚汤”。当然,作者也指出,还有镭锭疗法,但“肿毒侵及腋部颈项之淋巴腺,则内服外敷剖割电疗等法,已属太晚矣”,上述治疗不过“姑息疗法,施延时日耳”[45]。这种中西汇通疗法已经有了今天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的雏形。
因为缺乏实际统计数据,我们无法得知中西医在近代乳腺癌治疗过程中的各自占比。事实上,中医的悠久传统与中国各地民众对西医信奉程度的不同,是中西医能在近代中国社会并存的重要原因。具体到乳腺癌治疗领域,由于癌症治疗的困难和西医治疗费用的昂贵,中医仍然保有巨大的实践空间。1933年《东方杂志》的“医事卫生顾问”栏目,就有读者来函询问乳癌治疗方法,并希望免费或减费割治[46]。到1941年,小报《罗汉菜》杂志征集乳岩良方,其理由即“富室尚能请西医割治,贫苦人家竟有束手待毙者……特征求能治已溃未溃效验良方,藉以公开济世”[47]。此后,《罗汉菜》上确实出现了几篇关于乳癌的中医方[48][49]。20世纪40年代后,报刊上刊登的治疗乳岩的广告,各类医学、卫生报刊“医药问答”栏内关于乳岩的提问和各种渠道流出的关于乳岩的内服外敷的民间验方、秘方,都昭示着中医治疗乳腺癌的实践仍在中国社会开展。
三、关注乳房:西医乳腺癌知识的社会传播与接受
女性乳房是生理性别的重要表征,历来都是女性美的象征。1936年,郑逸梅在《康健世界》发表《女性健康与乳房》一文,不仅罗列古往今来描述乳房美的诗词,更提到一些男性择偶或是招聘员工时即以乳房美为标准,最后指出,“女性健康美,关系于乳房是很大很显著了”[50]。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乳房是女性羞于呈现的部分。和中医主要依靠内服的治疗方式不同,西医需要女性敞开衣襟、任凭医生对乳房进行触诊。同时,切除乳房也会令女性失去性别特征和哺乳的机会,根治手术甚至会让女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这些诊疗方式同样不易为女性接受。西医要获得患者的信任,不仅要突破中医近千年来对于乳部疾病的话语权和治疗传统,更要突破中国社会对乳房问题的禁忌,让民众建立起乳腺癌“早发现,早治疗”的正确认知。
关于乳腺癌知识的传播,早在晚清时期便已开始。1892年的《万国公报》上刊登了传教士德贞的《西医汇抄》。其中指出:“乳痈,硬软嫩膜与似胶者俱有,但硬者较多,又多系本体自发,有单无双患,此者约在四五十岁之间。症状日渐加大,变疮疼甚,腋窝津液核亦被累坏肉,力与爽快俱失,貌有痈形,或遭累他部而沉入脏腑所历不过四年。男子亦间有患此者而亦多不治。”[51]1915年上海文艺编译社印行的《房中医》中,受到近代日本医学影响的中医顾鸣盛单列疾病“乳癌”,指出:“中名乳岩是也,或谓四十至四十五岁为最多云……行外科手术尽去患部则为最佳良,不然危笃。”[52](P 197)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丁种已有“癌”“乳癌”词条。1925年3月,孙中山罹患癌症的消息传播开来。《晨报》用两个整版刊登了《癌肿浅说》,其中就提出:“乳癌,乳房中生圆形结节状肿物,渐次增大,发生刺激性疼痛,往往与表面皮肤附着,乳嘴陷没”,“女子乳癌,多发于三十五岁以上”[53][54]。这虽不是关于乳腺癌最早的介绍,却是大众媒体对于乳腺癌知识的早期普及。然而,这一时期,乳腺癌还是过于陌生的名词,更重要的是,乳房还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天乳运动及其影响下的禁止束胸政令的出台,成为社会堂而皇之关注乳房的契机。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妇女以乳房高耸为耻,用布或小背心裹紧胸部,一度被视为社会流行。五四运动后,从移风易俗、妇女解放等角度,出现不少阐述束胸之害的文章。早在1919年就有人指出束胸的危害包括“呼吸不能充分,障碍肺脏发育”“障碍乳腺发育,影响直达小儿”[55]“导致乳头内陷,不仅容易因为乳腺不通畅而得乳腺炎,同时也影响哺乳”[56]。1927年起,各地陆续开始禁止女性束胸,其核心理由是“妨碍卫生并足弱种”,具体来说包括“于心肺部之舒展、胃部之消化均有妨害,轻则阻碍身体之发育,易致孱羸,重则酿成肺病之缠绵,促其寿算”,“影响血运呼吸,身体因而衰弱,胎儿先蒙其影响,且乳房既被压迫,及为母时,乳汁缺乏,又不足以供哺育”,同时崇尚欧美妇女的自然美观[57]。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借助废装饰、剪发等妇女风俗改良问题的热火朝天,束胸问题也出现在各类媒体中。其中,虽然不乏种族优生和男女平权角度的言论,但总体的宣传语境已经转为从健康出发。在众多束胸的危害中,导致乳腺疾病的说法经常被提及。1928年《大公报》上一篇名为《又一呼声:打倒束胸的恶习》的文章提出:“束胸使乳嘴凹陷,哺育子女时,婴儿吮吸不便。且往往因乳腺分泌正旺,乳汁积郁,容易成为乳痈,以致生脓开刀。”[58]1935年,有中医认为“若强事束缚,使乳不能充分发育,况乳属肝,肝主疏泄,久受压迫,则气郁不伸,久之而成乳核、乳岩等症”[59]。显然,天乳运动在女性身体解放的时代命题下,间接引导女性开始关注乳房,关注乳腺疾病。
20世纪30年代后,经由禁止束胸政令抛出的“乳房”问题,加之妇女运动的开展和健康宣传的提升,具备一定知识素养的城乡民众已经可以了解到乳腺癌的知识。一些受过西方医学训练的医生在专业报刊或大众媒体上发表医学论文或科普文章进行乳腺癌知识普及。史怡云在《癌症之预防及治疗》一文中提到了乳癌的症状,包括“乳房内部发生小肉”“乳头有异样的分泌液,尤其是混血的分泌液”“乳头凹入,周围肌肉硬化”[58]。作者指出,出现上述症状时往往没有痛感,等到有痛感时往往已经迟了,提醒读者关注乳房、有病症及早就医[60]。《大公报》副刊“妇女与家庭”和“医学周刊”一直重视癌症知识的普及。罗嵩翰在《妇女的卫生及妇人科疾病的卫生法》中提出:老年易发的疾病主要就是子宫癌、乳癌。乳癌“在病未转移于他处之前,应请医生切除乳房为是。既发转移,手术后则易再发”[61]。在《女界之敌癌》一文中作者指出,“妇女常患的癌瘤有两种,一是乳癌(普通称干奶疮),一种是子宫癌”,“世界上的妇女因为毫没有一点癌瘤知识,以致死亡者很多。所以现在的人们,人人都应有一点癌瘤常识”。随后作者指出,“妇女如果乳头上生了小结或小块,不论在什么年龄,也不必管他痛不痛,应该立刻到医师处去检查是否癌瘤”,“如为恶性瘤,尤应迅速处置,稍晚则癌瘤细胞将有散步全身之虑。所以当医师断定为癌时,乃病人之生死关头,万不可存姑息之念。自然患癌瘤者虽行手术亦不必皆能痊愈,常有复发之时。但吾人所宜知者,近年因早期手术而得救者每年已不只万千。何可畏惧此极有益之手术,而坐失良机”。最后,作者提到“乳部极为明显,凡受教育之妇女,果知注意,遇有小硬结或他种可疑即请医师检查,即不致贻误治疗时期”[62]。在《妇人的癌肿》一文中,留德医学博士谢筠寿首先指出:“大多授乳的妇人,四十到五十岁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男子发生乳癌的颇少。乳癌大多发生在一侧,在乳腺内作为一个结节,表面不平,形状和大小不一定,疼痛也不一定,颇硬固,初时硬块和皮肤及皮下组织不相愈着,随后愈着萎缩上举。但癌的种类不同,有表皮癌(硬癌)、髓样癌或腺癌(软癌),所以他的形态也不一样,当乳癌发生的时候,常常转移到腋下淋巴腺,致腋下淋巴腺肿大起来。”“表皮癌的成长缓慢,有时可能十余年之久,腺癌或髓样癌经过迅速,发生转移也迅速。”最后,作者提到“诊断愈早,手术的结果也愈良”[63]。这一时期,一些医学专家也开始在学校等地举办乳腺癌的知识讲座。1941年11月,中比镭锭治疗院的院长汤于翰就曾二度在震旦大学演讲《乳癌与子宫癌》[64]。
这一时期,城乡民众还可以通过一些家庭保健、家庭顾问手册了解到乳腺癌。如1931年出版的《大众医学》证候篇,提到乳癌最易发觉,一经发觉,就应该进行外科手术[65](P 194)。1936年出版的《夫妻顾问》这类通俗文学作品也指出乳病最普通的便是乳癌[66](P 191)。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癌症知识普及也进入公民教育层面。在校学生可以通过生理卫生教材、学生词典等认知乳腺癌。如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词典》已有“乳癌”词条;1932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初中生理卫生学指导书》,在第十七章“疾病的管理和看护”第一节“疾病的意义”中提到疾病的内因也分性别,乳癌女子为多[67](P 331)。1935年大众书局出版的《学生标准字典》,在“癌”字的解释中提到“硬而疼痛的瘤状物,如‘胃癌’‘乳癌’”[68](P 465)。1948年,教育部编订《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在课标的《修订高级中学女生家事课程标准》中提到学习内容包括“普通主要疾病之起因、症状、预防、治疗及护理”,其中就有“乳癌”[69](P 217)。
进入20世纪30年代,西医科学的发展为乳腺癌提供了更为成熟有效的治疗手段。手术在中国医院中日益成为成熟的治疗方式。1936年,《大公报》刊登的《中国人的瘤子》一文中指出,北京协和医院1936年手术的821例癌症患者中,“泌尿生殖器部的癌瘤占第一位,其次在男子为皮肤癌,在女子为乳部癌”[70]。由于乳腺癌根治术所涉组织太广,不仅伤害患者的身体外观,还可能一定程度上损伤患者的生理活动能力。好在这一时期的西方科学为乳腺癌治疗带来了新技术。1896年,美国医生格拉比(Emil Grubbe)进行了第一例X线治疗乳腺癌试验[4](PP 84-85)。乳腺癌的放射治疗在西方出现。20世纪30年代起,X线和镭锭等放射疗法成为继手术之后治疗乳腺癌的新方法在中国社会出现。1930年,中比庚款委员会拟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中比镭锭治疗院,从比利时购买了0.5克镭锭和镭锭治疗设备[71](P 81)。镭锭治疗设备的说明书中提及镭锭可以治疗的疾病,其中就包括乳癌[72]。1930年,汉口同仁医院编的《物理疗法便览》中提出X光和镭锭放射疗法对于子宫及附件癌效果最好,其次是已经发生转移的乳癌[73](P 3)。1935年的《东方杂志》“医事卫生杂志”中有来函询问乳癌治疗。生理学家程瀚章给出方案:“确系乳癌,需速行手术割除。如用镭光线照射,亦有微效。”[46]当时上海的中比镭锭治疗院已经可以开展镭锭治疗。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西方社会开始出现放疗的辅助疗法:“各国学者……对乳腺癌肿疗法的讨论问题则专注于放射线疗法应否施行于手术前或施行于手术后。”即对于不能施行手术的乳腺癌,可以先进行放射治疗,使癌肿缩小,再行手术。同时,建议对腋窝淋巴结已经浸润等的乳腺癌,手术后进行放射治疗。最后,一旦发生皮肤内的复发,也可以进行放射治疗[74]。从1942年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的论文来看,国内的部分医生也已经了解放疗及其辅助疗法的价值:“患癌之乳房完全截除术公认为最有效之治疗,癌只限于单侧乳房而无迁徙之证据时,截除手术可谓最佳之治法。如癌已侵入同侧腋窝淋巴结时,手术前先用放射线治疗,始施截除术,手术后再加放射线治疗。如癌已迁徙至同侧腋窝以外之组织,通常不宜施行乳房完全截除手术,除放射线治疗外,无他图可循。”[75]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种辅助疗法已经在中国部分医院中实施。从中比镭锭治疗院《1947-1949年经该院诊治过的癌疾患者病人数和治疗法统计表》中可见,手术和放射综合疗法已经成为乳腺癌的主要疗法[76]。可以说,放射疗法的出现为乳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癌症患者和社会大众对于乳腺癌西医治疗的接受度。
可以说,以天乳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女性身体解放,推动了社会大众特别是女性开始关注“乳房”问题。尽管乳腺癌仅被作为束胸的副作用提及,但它毕竟引发了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再发现”和对于乳部健康的关注。伴随乳腺癌相关知识的传播,乳腺癌需要早期发现和积极治疗的认知在城乡知识群体中逐渐形成。1934年,全县王秀香女士因其嫂乳房上长出肿块且不断增大、疼痛,向《广西卫生旬刊》的“医药问答”栏目咨询,医生给出了乳癌的判断和尽早施行手术治疗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王秀香在描述其嫂症状时表示,虽然自己并不清楚这是什么疾病,但“大家都说此病应速医治”[77]。可见当时部分知识女性已经建立起了乳癌尽早医治的意识。1937年4月11日《大公报》上海版的“医药问答”栏目上,有名为“方新禹”的读者来信,提到亲戚某夫人被中医诊断为乳岩,服药无效,西医诊断为乳癌,要动手术。方新禹来信询问“七年之癌系良性或恶性?割去乳房,有无危险?年虽青,体不甚健,是否可以施行手术?不施行手术,X光可治愈否?照射次数约多少?有无其他良药可治?”这位读者提出的问题十分专业,可以看出其对于西医和癌症相关问题有一定的知识储备[78]。1941年,中比镭锭治疗院印发了一本宣传册,在宣传医院擅长治疗乳癌时指出,“许多妇女自以为已有乳癌,只唤奈何,往往实际徒怀杞忧”,与其焦虑,不如到医院资讯医生或请有经验的医生触诊[79]。宣传册针对的是受众的实际需求。伴随民众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一时期的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女性对于乳部肿块的关注和担忧。这种意识的出现,显然也要归功于乳腺癌知识的传播。
乳腺癌治疗手段的更新也促成了部分民众对于乳腺癌西医治疗理念的接纳。20世纪40年代,放射治疗已经被一些患者视为乳腺癌治疗的希望。1945年,景宋在《中国的癌》一文中提到,自己“五六年前亲眼看见一位友人的母亲,患乳癌,已经割去乳房,半边身结连着一大个疤痕,但是癌病未除,在头颈上,背上,四肢上随处爆发癌疮,脓臭扑鼻,大家都明白是不会好的了,而病人自己,却是生之欲望随着病症加深而增长,越是痛楚,越要求活,迫得女婿背负着脓血蒸腾的病人上下楼梯坐车子去医院电疗”[80]。1949年,署名“大风”的作者以妻子手术割除乳腺癌后在中比镭锭治疗院照射镭锭,后又以镭锭照射颈部新生癌肿为例,认为早期的癌症都应该早到镭锭治疗院治疗,并将放射治疗作为“可免开刀手术之苦”的手段大加赞赏[81]。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取决于知识阶层认知水平和发达地区医疗手段的知识传播和接受,具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据作家李准夫人董冰记述,1947年夏天,她的嫂子就发现乳房内有硬块,“跟小拇指头肚那么大。叫我们都摸过,可硬”。董冰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当时就根据乡间经验意识到:“红肿高大,大夫不怕。不青不红,这可不是好东西。”为此,他们请过神婆,又是下神又是烧香。随着病情加重,出现了胳膊疼等症状,还到洛阳城看过中医,医生根据症状开了虎骨酒。病势日重后,只能依赖求神的方式。最终嫂子还是去世了。20世纪80年代董冰写作回忆录的时候提出:“一直不知道嫂子是什么病要了她的命,只知道人死了,很悲痛。现在想来她害的是乳腺癌,这种病在当时更没有办法。”[82](PP 124-125)显然,由于医疗水平和健康意识的地区差异,在更偏远的乡村地区,乳腺癌治疗依然充斥着各类偏方和迷信手段。1949年前,西医乳腺癌知识的社会传播与接受停留在特定地域和人群中,远远不能实现乳腺癌防治知识的社会普及。
四、结语
近代以来,西医以外来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带来一种与中医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手术成为乳腺癌治疗的新选择。然而,手术在中国的早期推广并不顺利。一方面,西方医疗技术传入中国之初,外科手术的安全性不强,中国人“不敢损伤身体”的传统观念本就对西医侵入式疗法较为排斥;癌症手术后复发率高的现实,也使得手术治疗备受诟病。另一方面,乳癌、乳岩早在古代就被中医反复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诊疗经验。相比接受完全陌生的手术,中医仍存在较大市场。
西医治疗手段要被熟悉传统医疗模式的中国民众接纳,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嬗变,特别是传统身体观念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身体是父权家庭的私有物,乳房历来被认为是私密而不可被轻易窥探的。在西医诊断治疗乳腺癌的过程中,女性必须对医生(很大概率是男性医生)“袒胸露乳”并被查看、触摸。这显然挑战了传统女性身体观。对抗这一挑战的是疾病带来的巨大身心痛苦。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癌症不同于其他疾病,早期诊断和早期发现是癌症防治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民众必须足够关注“身体”。而中国传统的尊卑观念和女性身体观,影响了女性对身体的关注和疾病的发现。20世纪20年代后日益蓬勃的天乳运动,从“妨碍卫生”和“弱种”逻辑出发,堂而皇之地对女性进行身体规训。这种规训的出发点或许未必出于传统身体观的自觉突破,但客观上借助西方医学理念实现了女性身体的“被发现”。可以说,天乳运动正是在西方医学知识的助力下对女性的身体实施“解放”,同时也将“乳房”从私领域带入公领域,成为社会讨论的话题。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各种关于乳腺癌的知识传播才得以实现,对于乳腺癌知识的接受才变得合情合理。随着禁止束胸政令的发酵和各种渠道对于乳腺癌知识的传播,不少民众意识到乳腺癌的危害和“早发现,早治疗”的意义。加之最新西方医疗技术的传入,西医治疗乳腺癌渐渐被中国民众所了解和接纳。
近代中国民众对乳腺癌西医治疗的接受,既是西医知识不断普及和西医技术不断提升的结果,也是对传统身体文化的突破。不过,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后,乳腺癌治疗的天平已经向西医倾斜,显然亦非历史事实。昂贵的放射疗法和手术并非一般民众可以负担。中医在民国时期虽然遭遇政府层面的种种压力,但因其相对低廉的就医成本,仍是中下层民众的首选。更有甚者,尽管20世纪上半叶,中西医疗在近代中国的乳腺癌治疗领域各显神通、互为补充。然而,在更偏远的乡村地区,由于医疗水平和健康意识的相对落后,乳腺癌治疗依然以各类偏方和迷信手段为主。
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1958年后中国肿瘤防治事业的起步,这种局面开始出现转变。在苏联预防医学的影响下,政府强有力地介入肿瘤防治领域。特别是自1958年起,全国一定规模的癌症普查显示,在女性肿瘤方面,宫颈癌发病率位列第一,第二便是乳腺癌。这一普查结论为乳腺癌成为新中国重点防治的恶性肿瘤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一结论建立在西医临床治疗和病理学的基础上,西医在癌症防治领域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不同于1949年前乳腺癌的根治手术仅限于某些大城市的部分医院可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般大、中等城市的医院都已普遍开展乳腺癌根治术[81](PP 4-5)。在1959年的全国第一次肿瘤学术座谈会上,来自上海、天津、北京、福建等地多家医院的近千个乳腺癌治疗病例反映出当时中国在乳腺癌手术治疗方面的成绩[82](PP 520-528)。在这次座谈会上,和西医在乳腺癌防治领域的进展相比,中医方面只有1例关于治疗乳腺癌的案例。尽管会上指出“目前由于中医中药治疗癌瘤的工作时间还短,比较系统的成熟的经验还不算多”,但从中医中药组的工作汇报来看,中医也将以往提及不多的“割治肿瘤”放在了中医肿瘤疗法的第一位,显示出明显让位于西医治疗的态度[83](P 29)。可见,即便在政府已经有意识地提出中西医结合理念的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逐渐成熟的手术、放疗、内分泌治疗、药物治疗的综合疗法面前,中医可以介入的空间越发有限,逐渐局限在中药抗癌领域。
西医在癌症防治领域的话语权渐趋稳固,这与近代中国癌症防治领域所经历的西医东渐、中医式微和身体观的现代转向息息相关。近代中国乳腺癌治疗的历史,为理解当代中国的癌症防治成就和局限提供了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