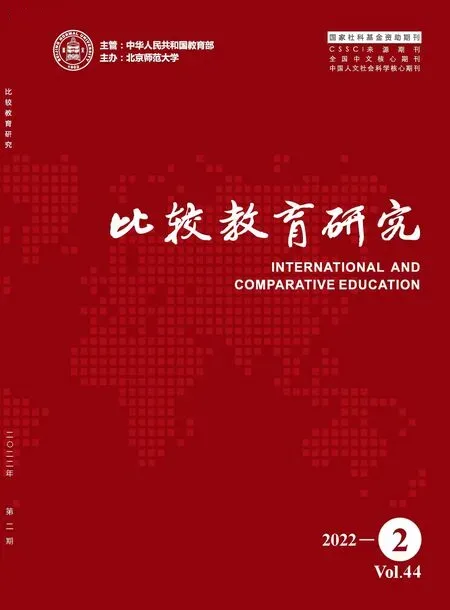当代西方学校系统变革理论:旨趣差异与变革共识
金琦钦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浙江杭州 3100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对碎片化的学校变革路径的反思,西方一些教育研究者不约而同地转向探索学校变革的系统路径,以期把握和回应复杂的变革实践。他们从系统理论中汲取知识来源,建构了各具特色的学校系统变革理论,这些变革理论在旨趣和变革逻辑上存在差异,但最终指向了一致的变革方向,折射出共同的变革价值追求。全面审视学校系统变革理论的背景、旨趣、议题和实践指向,揭示不同变革理论的差异与共性,能推动不同变革理论之间的对话,找到广泛的变革共识,进而生成整合的变革行动知识。
一、学校系统变革理论涌现的背景
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社会逐渐步入了知识社会时代,随着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相比获取知识,运用和创造知识变得更为重要。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倡导授受主义的学校教育模式已然滞后。随着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了大规模的学校教育改革运动。1983年,美国高质量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表《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的报告,提出了“做得更多”的改革策略,即更多的课堂教学、更多的基础内容、更多的训练、更多的师资培训、更多的控制等。1988年,英国出台《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on Reform Act),强调竞争、家长选择、基于国家课程的学业测量等改革原则,这一事件被视为英国乃至国际教育改革运动的“分水岭”[1]。此后,其他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纷纷出台了类似的教育改革政策,逐渐形成了一场强调标准化和市场化的“全球教育改革运动”[2]。
然而,这些大规模改革大都采取了碎片化的变革路径。政策制定者习惯把变革问题分解成可控的若干部分,试图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决问题,以达到想要的结果;他们倾向于重新设计或替换学校的关键结构,如引进新技术、运用新课程、招聘新教师等,而未能抓住学校变革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质。由于缺乏系统思维,变革政策常常难以深入和持续实施,旧有的学校教育模式依然盛行。为突破已有变革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教育研究者一直致力于探寻新的变革路径。基于对学校变革复杂性的深刻认识,以系统理论为知识基础构建变革的新路径,成为他们的共同选择,正如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所指出的,“我们被迫在所有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来处理复杂性问题”[3]。学校系统变革理论由此不断涌现。
概括地说,系统理论从三种意义上为变革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思维工具。第一,软系统思维的提出。软系统思维主张,在设计人类活动系统时,应纳入人的目的、兴趣和价值观,并始终保持开放,承认观点的多重性[4],学校变革的设计也应如此。第二,复杂性范式的形成。复杂性范式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运动,强调从分析思维转向复调思维(polyphonic thinking)、从宇宙世界转向多元世界、从普遍性知识转向情境性知识、从因果性转向涌现性等[5],这意味着学校变革应把握非线性、不可预测性、情境性、自适应等特质。第三,“简复性”(simplexity)概念的生成。“简复性”认为,简单性与复杂性之间具有辩证关系,并非只有复杂性才能处理复杂性,相反,只有简单的设计才足够开放,才能推动复杂的集体自适应行为的涌现。[6]这意味着,找到学校系统中少量的关键因素,可以凝聚复杂的人和力量,推动整个系统的改变。
二、学校系统变革理论的多元旨趣
理论的建构离不开研究者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由于研究者对现实变革问题持有不同的认识,学校系统变革理论呈现出多元的旨趣,包括“研究-设计”“理解-批判”“实施-扩散”取向。
(一)“研究-设计”取向
“研究-设计”取向旨在通过研究,为学校变革的设计提供概念“地图”,因而更关注变革的开发阶段。贝拉·巴纳锡(Bela H. Banathy)的综合系统设计(comprehensive systems design)理论便是这种取向的典型代表。作为一种决策导向的严谨探究(disciplined inquiry)活动,综合系统设计通常是从研究中汲取可用知识,并以生成产品为目的。[7]在综合系统设计中,研究团队应扮演指导系统的角色,即研究团队需要为不同层次的设计共同体提供设计所需的知识基础、资源、案例与工具等,以实现系统设计知识的最大化运用。综合系统设计理论提出了涵盖“图景创建空间”“设计知识空间”“设计方案空间”“试验与评估空间”和“建模空间”的动态设计架构[8],但其并无提供变革“钥匙”的意图,即描绘出一个新系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创新性学习环境(innov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设计框架,也体现出这一取向。为解决学习研究与教育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发挥学习研究的实践价值,OECD明确了以“学习研究”为基础的变革设计方式。[9]在创新性学习环境设计框架的建构上,OECD吸收了多个维度的学习研究成果,包括历史、认知、情感和生物学视角下的学习概念研究,另类学校教育的研究以及基于研究的教学创新成果,如问题式学习、探究式学习和项目式学习等。通过从不同的学习研究中提取出共同结论,生成“学习中心与学习者主体投入原则”“合作交往原则”“动机和情绪原则”等变革设计的核心原则。
(二)“理解-批判”取向
“理解-批判”取向旨在运用复杂系统的观点,揭示变革政策与教学实践之间的张力,进而理解学校变革的复杂性。例如,拉里·库班(Larry Cuban)基于对学校教学变革史的考察,提出了“情境限制选择”(situationally constrained choice)理论,强调学校组织情境对变革政策的过滤作用。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库班将历史的方法视为学校变革的重要分析工具,试图通过解释过去类似的情境,重新定义当前的问题,反思现有的变革政策。库班认为,历史更重要的在于发现问题,而非提出洞见。从历史的视角看,对变革而言,较之提出所谓明智的解决方案,在一开始仔细地界定问题显得更为重要。[10]因此,他一直致力于为变革问题“提供解释”,而不提供未来行动的处方。不过,在库班看来,“解释”本身蕴含着政策的“种子”,即蕴含着对于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11]
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亦致力于促进对变革的理解。基于深厚的社会学背景,哈格里夫斯的变革理论既关切教师的微观世界,又关切政策、社会的宏观世界,凝聚着对社会变革的深入洞见,并带有明显的批判色彩。哈格里夫斯从教师工作、教师时间和教师文化等维度提出了重新理解变革的诸多概念框架,揭示了学校情境对教师实践的影响。[12]他建构了“教学情绪地理学”(emotional geographies of teaching)的概念框架,指出了变革领域长期被忽视的基本方面——情绪维度。[13]
(三)“实施-扩散”取向
“实施-扩散”取向旨在直面学校变革的实施问题,致力于为变革扩散提供系统策略。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的一致性框架(coherence framework)体现了这样的取向。富兰力图将复杂的变革意义转化为“便利的语言”,提升变革研究成果对变革行动的指导效益,一致性框架正是这种努力的产物。一致性框架为整体系统变革提供了一种行动路径,包括聚焦方向、培育协作文化、深化学习和确保问责四个成分,领导力则是凝聚这些成分的关键。[14]当然,富兰也强调,一致性框架并非现成方案,而是变革者寻找自身行动路径的支架。世界银行(World Bank)提出了以学习为中心的整体系统变革路径,包括重视学习评估、依据事实行动和协调利益群体,以使系统各要素都能聚焦学习这一核心目标,形成变革的系统合力。[15]查尔斯·赖格卢特(Charles M. Reigeluth)则从价值观、原则和活动三个层次构建了系统变革的行动框架,主张根本性的变革应以特定的价值观和原则为指导,涵盖准备、设计、变革和改进四个阶段,同时应持续开展系统思维培养、评估反思、团队建设、组织学习等活动。[16]
三、学校系统变革理论的共同议题
不同的学校系统变革理论虽然旨趣各异,但共同关涉了变革价值、技术定位、变革情境等议题,并就这些议题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一)变革价值:回应知识社会
在学校系统变革理论中,变革的价值主要在于对知识社会作出“回应”,包括“应对”和“超越”知识社会两个层面。
一是应对知识社会。一些研究者将学校变革视作应对知识社会的“良方”。如巴纳锡认为,知识社会的关键特点之一是社会文化智慧与迅猛发展的科技智能不匹配。学校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之一,必须发展个人和社会的演化能力(evolutionary competence),培育社会文化智慧,发展面向知识时代的智力技术。为此,学校教育应从聚焦维持性学习,转向关注创新性学习。[17]OECD亦指出,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学习”移到了舞台的中央,学校教育必须从帮助学生掌握事实和程序,转向帮助学生学会解决问题、学会创新,并促进学生的终身学习。[18]
二是超越知识社会。哈格里夫斯认为,学校变革不仅要面向知识社会,培养学生的深层学习能力、创造力和独创力等,更要超越知识社会,承担起塑造生命、变革世界、促进公共福祉的社会使命。[19]富兰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变革的愿景是实现深度学习,但深度学习不只在于让学生“学会学习”,更在于让学生成为具有伦理精神和积极行动能力的学习者,提升学生参与乃至改造世界的能力。[20]
(二)技术定位:不同立场的批判
在学校系统变革理论中,技术之于学校变革的角色是个需要澄清的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立场展开了批判。
研究区位于桐城市西部龙眠街道龙眠村、黄燕村、风形村、双溪村及黄甲镇杨头村,地理中心点坐标为:东经116°54′20″、北纬31°06′30″。本区地处大别山东麓,属龙眠山脉,区内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海拔高度在60~900 m,其中“桐城小花”茶多种植在300~800 m的低山缓坡地带,茶园样式以斜坡茶园为主,局部山体坡度较大区域为梯级茶园,研究区为桐城市“桐城小花”茶的核心主产区。
一是技术怀疑者。一些研究者对技术持怀疑态度。库班就自诩为技术怀疑者阵营中的一员。从1986年的《教师与机器》(Teachers and Machines)到2018年《蝴蝶的飞行抑或子弹的轨迹?》(The Flight of a Butterfly or the Path of a Bullet?),从“教师是否运用新技术”到“技术是否真正改变了教学”的研究问题的转变,三十多年来,库班一直在反思和批判技术的有限性。通过考察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种新技术介入美国课堂教学的实然图景,库班指出,技术在学校教学变革上的作用是“既有也没有”(yes and no)。[21]信息技术虽然使教师的课堂教学更为高效,但并没有改变大部分教师的教学核心,技术只带来了修修补补的影响,有时甚至强化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实践。
二是技术支持者。一些研究者对技术展开批判,是为了更有效地运用新技术。如富兰虽然强调技术无法引领学校变革,主张变革须“从教学法到技术,再从技术回到教学法”[22],但他对新技术的运用持支持态度。富兰认为,现实中技术的梦想通常是失落的,这不是因为人们对技术关注过多,而是因为对技术了解过少,至今还未能充分开发技术在促进学习上的潜能。OECD也指出,技术可能再现传统的教学法,并且会出现“为技术而技术”的问题,但创新性学习环境的构建仍应发挥技术的多重作用。[23]
三是技术冷淡者。在一些变革理论中,关于技术的论述是“缺失”的,这种缺失亦体现了研究者对技术的立场。譬如,在巴纳锡的变革理论中,技术只是背景性因素。在他看来,如果仅是在变革设计中纳入所谓的新技术,仍然难以缩小社会文化智力与科技发展之间的鸿沟,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变革思维模式——“除非人们意识到必须运用新的假设,即运用系统设计这一新的智力技术重建教育,(教育的)危机将一直存在,甚至更糟”[24]。技术在哈格里夫斯的变革理论中也处于边缘地位,在其变革研究中,技术更多是作为分散变革目的的技术统治主义(technocracy)而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无视技术的解放作用,而是在于提醒人们变革应聚焦更深层的道德问题。[25]
(三)变革情境:重视文化的力量
在学校系统变革理论中,变革情境被视为影响变革实施的重要因素,如哈格里夫斯就指出,教师是否愿意支持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革情境是否具有包容性和支持性。[26]在情境的议题上,研究者主要围绕变革的文化,包括共同体、领导力、问责与评价等展开了探讨。
一是共同体构建。诸多研究者将培育共同体视作最有效的变革途径。在库班的情境限制选择论中,教师的工作情境是变革难以深入实施的根源,尤其是班级-年级制结构和个人主义的教学文化,共同助长了教学的保守性。为此,学校应通过建设教师专业共同体,培育共享教学资本,打破内部情境的限制。哈格里夫斯和富兰共同提出了“专业资本”的概念,主张通过培育教师之间的协作文化,提升教师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决策资本,增强集体能力建设,进而改善所有学校的教与学。[27]巴纳锡则主张要构建设计共同体,培育设计文化。他指出,可持续的系统设计应当由服务系统的、系统所服务的、受系统影响的人共同完成,设计共同体是教育系统设计的唯一合法环境。[28]变革的设计需采用“用户-设计者”取向,把设计系统视作“我们”的责任,而不只是专家的事宜。
二是领导力提升。领导力议题在于重新审视领导者在变革中的角色。研究者建构了多元的领导力概念,包括OECD的“学习领导力”(leadership for learning)[29]、哈格里夫斯的“可持续领导力”(sustainable leadership)[30]、富兰的“细微领导力”(nuanced leadership)[31]和赖格卢特的“参与式领导力”(participatory leadership)[32]等。这些领导力概念呈现出共同的特点:第一,强调分布式领导,即主张超越英雄型领导的概念,转向寻求理解领导力在多元个体之间的分布过程,认为“可撤退”的领导力才可持续;第二,强调学习领导,即主张领导力应始终聚焦促进学生学习的目的,尽量避免分散议程的干扰,领导者自身也应持续学习,根据变革结果调整自己的行动、信念与价值观;第三,强调文化领导,即主张领导者要培育协作和学习的文化,尊重多样性,鼓励创新和冒险,从而为变革创设条件。
三是评价与问责转变。一些研究者主张变革的评价与问责应纳入教师的视角。库班指出,政策制定者和教师审视变革的标准通常是不一致的,政策制定者偏好使用忠实度、有效性和流行度的标准,重视变革实施与变革方案的吻合度、变革实施之于预期目标的达成度、变革话语的流行性与传播性等问题。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学校和教师需要向上级负责,变革评价更多地依赖外部问责,最典型的便是运用成绩测验。然而,教师偏好适应性标准,对教师而言,根据个人经验对变革计划作出调整,使之更加适应教学现实,是主动创新的标志,而非削弱变革有效性的证据。[33]无独有偶,富兰也认为,聚焦教与学改进的专业问责对教师更为重要,外部问责应以促进专业问责为目的。当然,专业责任不能仅靠教师个体,也不能只局限于教室和学校,学校外部系统应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专业学习支持和文化支持。
四、殊途同归:学校系统变革理论的实践指向
学校系统变革理论的涌现,体现了教育研究者试图把握和处理学校变革复杂性的努力。在回应复杂变革实践的过程中,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差异化的变革逻辑,但不同的逻辑最终指向了一致的变革方向和共同的变革价值与追求。
(一)差异化的变革逻辑:“解释问题”抑或“找到方案”
在变革逻辑上,不同的学校系统变革理论呈现出两种差异化的倾向,“解释问题”的倾向和“找到方案”的倾向。前者强调变革的理解,以库班、哈格里夫斯等的变革理论为代表;后者强调变革的行动,以富兰、巴纳锡、赖格卢特、OECD等的变革理论为代表。
差异化的变革逻辑,反映出研究者对学校变革复杂性的不同回应策略。在力图“找到方案”的研究者看来,变革设计者面对的问题情境本身就是极其复杂和不断变化的,一味囿于问题的分析反而会被问题所困,难以行动,而没有行动就没有意义,正如富兰指出的,“所有真正的变革都是行动导向的”[34]。因此,变革设计者应当从“问题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把目光聚焦在寻找解决方案上。致力于“解释问题”的研究者则认为,正因为变革的情境如此复杂,发现和解释真正的“变革问题”才至关重要。若变革设计者不能理解教师产生阻抗的原因,不能意识到限制教师选择的因素,变革行动很可能是肤浅的,甚至行动要求越是明确,越是难以实施。从这种意义上看,“解释问题”的价值在于明确变革的“短板”。
差异化的变革逻辑也造成了变革评判标准的不同。注重“找到方案”的研究者认为,真正的变革应当是根本性变革。例如,在巴纳锡看来,设计变革方案的首要任务,便是“超越”现有系统;富兰亦强调要利用学校内在的变革力量,实现颠覆式创新。注重“解释问题”的研究者往往承认渐进式变革的合理性。如库班认为,能真正融入学校常规运行的变革通常是渐进式变革,这并非指学校教育实践一成不变,而是指大部分实践不会因各种改革政策的进入而彻底发生变化,即呈现出“动态保守主义”(dynamic conservatism)的特征。[35]
(二)一致的变革方向:重建文化
即使一些研究者注重变革的理解,并对渐进式变革表示认可,他们同样在探寻根本性变革的方向与路径。只是对他们而言,揭示变革情境对变革实施的限制,是探寻变革路径的前提——之所以是某些人率先发起和采纳了变革,是因为这些人面临特定的情势。[36]
在变革方向上,尽管持有不同的变革逻辑和研究旨趣,但研究者一致将重建文化视作学校系统变革的突破口,并对结构性变革进行了批判。结构性变革通常聚焦改变系统中的一些显性元素,如引进新技术就是一种典型的结构性变革,这类变革由于高度的象征价值和相对便利的实施方式颇受欢迎。[37]但在研究者看来,结构性变革的实施结果往往是表层的,要想真正改变学校实践,必须触及文化层面的变革。
富兰曾论断:“变革的过程是一场关于文化重建的比赛。”[38]文化重建归根到底指向人心智模式的改变,而这正是难度最大、最深层的变革。譬如,强调教师共同体构建的背后,是主张以专业资本的视域看待教师发展,充分考虑教师的主体性和发展性特征,而不只是把教师看作一种人力资源;强调领导力提升的背后,是对领导者角色的重新定位——现在,领导者的关键作用不在于事无巨细地直接介入,而在于运用整体思维间接地领导变革;强调问责与评价转变的背后,则是在于真正承认教师作为变革主体的身份和权利。
(三)共同的变革价值追求:统一学习目的与道德目的
不同的学校系统变革理论折射出共同的变革价值追求,即实现学习目的与道德目的相统一,以克服变革价值的个体与社会二元论。研究者们几乎都将促进学生学习视作核心的变革目的,如巴纳锡强调创新性学习,富兰倡导深度学习,赖格卢特关注个性化学习等。在知识社会的大背景下,学会学习已经成为个体生活、工作和参与社会的必备能力之一。可以说,近二十年来,学习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教育的语言。[39]然而,“学习”这一语言也存在风险,它很可能将教育窄化为一种仅仅追求个体效益的经济活动,从而曲解学习者的角色,消解教育自身的道德意义和社会意义。
从这种意义上讲,研究者并未将学习简单地定义为个体性和经济性的问题,而是将学习定义为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问题,指向更宏大的道德目的。追求道德目的正是任何教育变革产生意义的前提。一方面,学习不只是个体获取、掌握和内化知识的过程,还是个体应对社会变革与挑战的关键方式,更是个体参与民主决策和设计未来的过程,这意味着学校变革需关照到关心、参与、责任感等品格的培养,破解学习过程中的知识与道德二元论;另一方面,学习的机会始终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学校变革应具有全纳性,帮助所有学生,尤其是处境不利学生成为有能力和有伦理精神的学习者与行动者,以此促进公共福祉和社会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