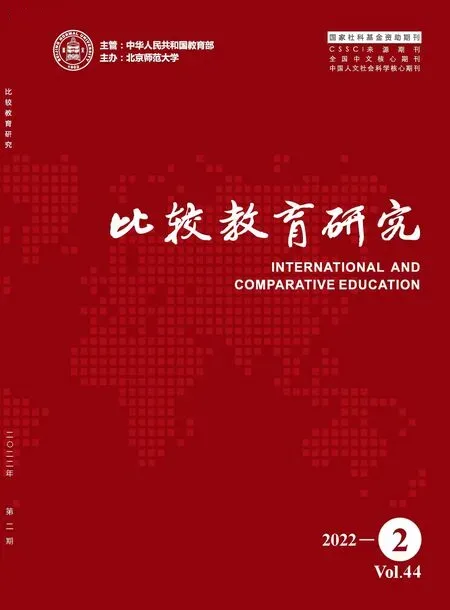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外国教育的介绍与传播
高益民,符定梦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找到救国良方,求知识于世界,很多人在此过程中对外国教育的经验给予了高度关注,而且积极进行介绍和传播,推动了中国的教育变革和社会进步。虽然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教育思想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和深入,但关于他们在介绍和传播外国教育方面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本文旨在通过考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外国教育的介绍和传播活动,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为改造中国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概念多指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进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应该包括建党初期的共产党人,但学界并无统一的界定。鉴于思想的发展与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思想转变前后的实践活动也有一定的连续性,因此在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活动时将时间跨度定得宽泛一些更为合理,本文认为可将考察范围放宽到20世纪初到大革命失败这段历史时期。
限于篇幅,本文选取陈独秀、毛泽东和杨贤江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探讨他们的教育背景、从教经历等与他们对外国教育的理解之间的内在联系,考察他们介绍和传播外国教育的主要活动、言论与思想,进而理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约一百年前在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促进中国教育的变革方面所付出的艰苦努力。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理解外国教育的条件
在民族危机加重的清末民初,全国上下都在寻求民族自救之路,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求知识于世界最根本的时代背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1]
当时教育救国的观念盛行,在学习西方的时候特别关注教育也是顺理成章的。而具体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外国教育的关注,则又与以下条件密不可分。
(一)扎实的教育基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刻理解外国教育的前提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先后接受过不同程度的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成为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精英,这是他们后来深刻理解外国教育的重要前提。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多曾接受过传统教育。陈独秀早年接受传统教育,他的老师是其祖父陈章旭,祖父去世后又由长兄陈庆元来教,陈独秀17岁(1896年)时还曾以安庆府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毛泽东从1902年开始上私塾,先后在下屋场、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颈6个私塾读了8年时间。杨贤江1903年(8岁)开始上私塾,一共读了4年。
19世纪末,新式学堂日渐增加,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民国建立后又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在这一背景下,由私塾转进新学堂或新学校而接受新教育就成为必然的选择。结束传统教育之后,19岁的陈独秀于1898年考入浙江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求是书院。[2]毛泽东则是17岁时(1910年)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后来又先后升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20岁时(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直至25岁毕业(1918年)。杨贤江12岁时(1907年)时转入初小(溪山学堂)读书,14岁(1909年)进入高小(诚意学堂),17岁时(1912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22岁(1917年)毕业。
当时很多新学校特别是高等学府名师云集,已经广泛开设讲授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课程。陈独秀在求是书院学习了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等;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受到了修身课教员杨昌济、历史课教员黎锦熙、教育课教员徐特立等名师的深厚影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中国建立最早的著名师范学校之一,杨贤江就读时的校长经亨颐延聘了李叔同等一大批国内顶级的大师在此任教。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教育经历表明,他们是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精英。
(二)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机会,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得以掌握外国教育的相关信息与资料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或以留学的直接方式,或以在国内学习的间接方式接触和了解外国教育,有较多机会了解外国教育。
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3名党员,经笔者调查,其中具有留学经历的有20人,占党员总数的37.7%。①有留学经历的人员为:陈独秀、陈公培、陈望道、董必武、李达、李大钊、李汉俊、林伯渠、刘伯垂、刘清扬、刘子通、邵力子、沈泽民、施存统、杨明斋、俞秀松、张国恩、赵世炎、周恩来和周佛海。陈独秀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1901 年,陈独秀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了5个月。1902年,陈独秀再次赴日进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了7个月;1906年暑假,陈独秀与苏曼殊东游日本;1907年春,陈独秀第四次赴日,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协助章编辑《甲寅》杂志,同时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约一年。陈独秀赴日虽然并非每次都是留学,但因此加深了对日本教育的了解,并通过日本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社会思想,特别是他阅读了大量法国政治著作后,对法兰西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3]
毛泽东曾就读的湖南省立第四和第一师范的教师中不少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如陈润霖、方维夏、孔昭绶、汤增璧、杨树达、易培基等人都是留日回国任教者。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曾在日本留学五年,在英国留学三年,他对毛泽东的求学、革命以及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直接发挥了重大影响。毛泽东热爱阅读,善于自修,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他自己也通过《新青年》等各种报刊和译著增进了对外国教育的了解。毛泽东本人虽然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他非常赞成留学,积极促进留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4]还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5]从1918年开始,毛泽东在杨昌济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具体策划,四处奔走,积极促进了湖南学子的赴法勤工俭学,他本人还曾先后四次到上海为赴法学子送行。
杨贤江就读的高等小学师资力量很强,有些教师曾留学日本,当时就引进了一些日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开设了自然课程,并在学校中传播新的社会思想。杨贤江后来就读的浙江第一师范的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的监督沈钧儒就是留日学者,他主持校政期间一度聘请了8名日本教师在此任教。改为第一师范后,校长经亨颐也是留日教育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当时第一师范的“四大金刚”——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以及艺术教育家李叔同等都是留学日本的归国人员,其中李叔同、夏丏尊对杨贤江的影响最大。杨贤江一直有留学日本的计划,或许与他们的影响有关。杨贤江最早的英文与日文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的,他在学期间已经从日文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人生》。
(三)教育工作者的经历,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外国教育的经验表现出深厚的兴趣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很多人是教师出身,这应是他们对外国教育表现出极大兴趣的原因之一。
经笔者调查,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的53名党员中,有从教经历(但不包括以学生等身份在劳动补习学校等任教的经历)的有25人,占比47.2%。①有从教经历的人员为:包惠僧、陈独秀、陈公博、陈潭秋、陈望道、邓中夏、董必武、何叔衡、黄负生、李达、李大钊、李汉俊、李中、林伯渠、刘子通、毛泽东、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谭平山、谭植棠、杨明斋、袁振英、张申府和赵子健。此外,邓恩铭、高君宇、何孟雄、李梅羹、刘仁静、罗章龙、王尽美、张国焘、张太雷等人在上学期间或毕业后曾在劳动补习学校等任过教。而在中共一大的12名代表中,有7名当过教师(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陈公博、李达和李汉俊)。
陈独秀最早的从教经历是1905年初受聘于安徽公学。1911年,陈独秀又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地理和历史教员。1912年初,陈独秀在安庆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在职期间,他在原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了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后又聘马其昶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1916年,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当上了大学教师,直至1919年。1921年初,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西南大学预科校长,并创办广东宣传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和俄语学校。中共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后,他于8月向陈炯明提出辞职。虽然陈独秀担任教师的经历断断续续,在地方主管教育行政的时间也非常短暂,但毫无疑问这些经历使他加深了对教育的理解。陈独秀晚年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虽然是学术价值极高的语言学著作,但从陈独秀在该书《自叙》中所表达的“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6]的立意看,这原本是陈独秀为中小学国文教师写的教学用书。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曾在1917年9月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国文科二年级写《国文教授案》,并进行教学实习。[7]1919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回湖南后主持新民学会会务,住到长沙修业小学,教历史课。[8]1920年9月,应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毛泽东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至1921年夏),他还被第一师范校友会推举为会长(连任两年半)。毛泽东在附小教学方面实行了一些改革,设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要学生注意社会实际问题。他题写的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礼堂,以勉励学生。为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毛泽东又把1918年4月停办的工人夜校恢复起来,还在初小部开办平民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并主持教学工作。[9]另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曾在学生组织学友会中担任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负责为工人开办过夜校(“夜学”)。[10]开班后,毛泽东还给夜学甲班上历史常识课。
杨贤江的从教经历有些特别,他在1912年高等小学毕业后就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即小学毕业教小学。1917年,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杨贤江成为南京高师学监处事务员。1921年2 月以后,杨贤江在商务印书馆任《学生杂志》编辑期间,同时还在上海大学、上海大学附中、上海景贤女中、上虞春晖中学等学校授课。
正是上述条件,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外国教育的关切有更强的内在动机,也使他们有更好的能力和条件从事外国教育的介绍与传播活动。
二、陈独秀对外国教育的介绍与传播
陈独秀第一次从日本归国之后就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教育。1902年,他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与同乡汪希颜见面时谈道:“蒙学莫急于德育,而体育次之;若智育,则成童以后未晚也。诚以德为人道之本,无德无以立,智必不醇。”[11]其中,“若智育,则成童以后未晚也”明显是受到了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少年期以智育为主”教育思想的影响。[12]
1904年,陈独秀在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一文,文中同时介绍了外国的教育情况,说“现在各国小学堂的功课,都有音乐,体操两项”。他还细致地介绍了裴斯泰洛齐(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 的教育实践,“西洋大教育家,有一个名教〔叫〕斐〔裴〕司塔尔基的,他尝说道:‘教育童子,总要顺着他的性情才好,设种种方法,惹起他的欢悦心,使他乐于受教。然后施以合宜之教育,才能够开发他固有的智能。’他这几句话,便合阳明先生的意见,正是一个鼻子孔出气。可见无论古今中外,道理总是一样。只是西洋、日本各国,都遵守裴司塔尔基的方法,幼稚园和小学堂里,都重在游戏教育法,设出种种的法子,一面和他游戏,一面就是教他学问,叫小孩子个个欢天喜地,情愿受教,没有一个肯逃学的。”[13]
同一年,陈独秀还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外国教育的文章《西洋各国小学堂的情形(一)俄国》。[14]从标题看,陈独秀曾计划系统全面地介绍欧美各国的小学教育,而以俄国小学教育为首篇。但后来《安徽俗话报》因故未能继续刊出,假使这一系列文章能按计划见报,那无疑将成为外国小学教育的系统研究资料。
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翌年更名为《新青年》)。在第一卷第二期,他便撰写了《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文中介绍了古希腊的教育、欧洲中世纪的教育,更对当时欧美和日本教育进行了分析,他对各国教育的特点进行了一一评论。他说:“现今欧美各国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偏倚,此其共通之原理也。而各国特有之教育精神:英吉利所重者,个人自由之私权也;德意志所重者,军国主义,举国一致之精神也;法兰西者,理想高尚,艺术优美之国也;亚美利加者,兴产殖业,金钱万能主义之国也。稽此列强教育之成功,均有以矜式宇内者。吾国今日之教育方针,将何所取法乎?”[15]明确提出中国应借鉴各国教育的经验。此外,在文中陈独秀还介绍了卢梭、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等人的教育思想。
1917年,陈独秀在南开学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近代西洋教育》,对西方近代教育的主要特征进行了以下概括[16]:
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
……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一不取启发的教授法,处处体贴学生心理作用,用种种方法启发他的性灵,养成他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固有的智能得以自由发展……此时意大利国蒙得梭利(Moria Montessori)女士的教授法,轰动了全世界。他的教授法是怎样呢?就是主张极端的自动启发主义:用种种游戏法,启发儿童的性灵,养成儿童的自动能力;教师立于旁观地位,除恶劣害人的事以外,无不一任儿童完全的自动自由。此种教授法,现在已经通行欧美各国……
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
……所以欧美各国教育,都注重职业。所教功课,无非是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此时学校教育以外,又盛兴童子军Boy Scout的教育,一切煮饭,烧菜,洗衣,缝衣,救火,救溺,驾车,驶船等事,无一不实地练习……
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
陈独秀对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主张极为推崇,他认为“所以杜威到中国来最精要的讲演,却不在伦理学,也不在社会学,是在教育学”。[17]陈独秀非常赞赏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他认为新教育的根本精神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平民的、而非贵族的。[18]陈独秀说:“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社会要是离了教育,那人类的知识必定不能发展,人类知识一不发展,那国的文化就不堪问了……可见得教育要趋重社会不能趋重个人。”[19]陈独秀还非常赞赏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学生本位”“做中学”等教育主张,他同样认为这是“新教育底精神所在”[20]。陈独秀也非常赞成杜威“学校即社会”的观点。他说:“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21]陈独秀认为:“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22]
三、毛泽东对外国教育的介绍与传播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通过《新青年》等报章杂志对外国教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并进而在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传播关于外国教育的知识。
1917年11月,毛泽东在办“夜学”时,就在《夜学日志首卷》中介绍了欧美的经验:“殴<欧>美号称教育普及,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褓姆有院,聋盲有院,残废有院,精神病者有院,于无可教育之中,求其一线之可教者,而不忍恝置也。”[23]这里除了夜校制度外,还谈到了保育院、福利院等制度,可见当时他对欧美的福利与教育制度已有非常细致的了解。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自由主义、平民主义以及工读新村运动等各种外国思潮与主张对毛泽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毛泽东不仅广泛学习这些思想和主张,而且还努力地将它们用于实践之中。毛泽东1919年曾设想邀请朋友在岳麓山建设新村,在新村实现边“工”边“读”的理想。[24]他当年12月在《湖南教育月刊》发表的《学生之工作》中介绍了这些流行于俄、日、美、法等国的思想与实践。“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25]他认为:“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赏,吾人改而吸赏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26]他还具体设想,新村中建立花园和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27]。毛泽东认为,当工读完全整合之后,学校原来的手工科和体操科等科目可以相应废除。
对于外国教育思想,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还是杜威的教育学说。杜威1919年4月到中国之后,在各地作了200余场学术报告。毛泽东1920年在上海期间参加了由黄炎培主持的杜威演讲会。1920 年10月,杜威等文化名人到长沙演讲,毛泽东不仅参加了演讲会,而且做了蔡元培、杨端六、吴稚晖演讲专场的记录员。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介绍健学会会则规定要“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28],列举了该会组织的演讲,如“采用杜威教育主义”[29],并对此予以肯定,认为“则传播之快,得益之大,当有不可计量的了。”[30]1920年7 月31日,毛泽东在《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一文中说:“美博士杜威东来,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而吾县深闭固拒,对于外间情势,若罔闻知。主持督促之人,既固陋而寡通,尤昏愦而无知。思潮不能顺应,教育因而失败。”[31]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谈到近代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新思潮“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32]1919年9月1日,毛泽东撰写了《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这些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以及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第一项就是教育问题,包括17个具体问题。如教育普及问题(强迫教育问题)、中等教育问题、专门教育问题、大学教育问题、社会教育问题、国语教科书编纂问题、中等学校国文科教授问题、不惩罚问题、废止考试问题、各级教授法改良问题、小学教师知识健康及薪金问题、学制改订问题等,第16个具体问题是大派留学生问题,而最后一个问题则是他单列的“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33]。虽然这个“问题研究会”后来没有成立,但从中可见毛泽东对教育问题所做的思考。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办了“文化书社”,11月10日,他写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向大家推荐重要书目、杂志和报纸,在他推荐的61本书中,仅杜威一个人的作品就有《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杜威现代新〔教〕育的趋势》《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4本,在同一作者的书目中是最多的。在这个书单中,他还推荐了《柏拉图之理想国》《心理学大纲》《现代心理学》《社会与教育》等教育学和心理学图书。[34]
四、杨贤江对外国教育的介绍与传播
杨贤江1917年秋至1920年在南京高师工作期间比较集中地思考教育问题,而且与陶行知等教育家接触甚多。杨贤江1921年2月开始做《学生杂志》编辑,结识了沈雁冰、董亦湘等人,并常在一起做翻译工作(次年由此二人介绍入党),这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他的外国教育研究。从杨贤江关于外国教育的文章发表时间来看,第一个比较集中的时期正是1920年至1922年,第二个集中的时期是1927年至1929年他在日本避难期间,这一时期他直接地获取了不少关于外国教育的日文资料。
杨贤江对外国教育的介绍与传播主要是通过《少年世界》《教育杂志》《学生杂志》《时事新报·学灯》等报刊。根据任钟印编《杨贤江全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杨贤江共发表关于外国教育的文章39篇,其中发表在《少年世界》4篇,《学生杂志》2篇,《时事新报·学灯》1篇,而发表在《教育杂志》最多,共计32篇。
杨贤江的文章涉及的国别非常广泛,如介绍美国教育的有:《美国学术界现在的趋势》《美国和智利之交换教授——世界学术沟通之捷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新课程——添设“近代文明科”》《美国最近教育之趋势》《美国教育的组织》《美国暑期学校的发达》《美国夜学校的专校学科》《美国学校教授社会科学之现状》《美国新出的一种教育杂志(Progressive Education)》《文纳特卡制的大要》《美国都市教育的特种设施》等文;介绍英国教育的有《最近英国教育界的倾向》《英国的六个新学校》等;介绍德国教育的有《德国之劳动教育》《德国的新学校》;关于日本的有《日本最近教育思潮概观》《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日本教育论之一》《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日本教育论之二》《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官学与私学——日本教育论之三》《论日本各政党在总选中所提的教育政策》《高唱“思想善导”之最近日本教育界》《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关于朝鲜的有《朝鲜教育的现状》;介绍俄国教育的有《介绍<新俄之新学校>》《介绍<苏俄之学校、教师与学生>》;还有介绍瑞士(《瑞士的教育》)、意大利(《最近意大利的教育》)等国教育的文章。有些文章则是跨国性的世界教育信息,如《德比二国之新学校》《英美德俄四国教育改造之实况》《万国学生大会开会矣——我国学生如何?》《“教育劳动者国际”之勃兴与其发展》《世界成年劳动者教育之实施鸟瞰》等。内容领域主题包括幼儿园、中小学直到高等教育,还有成人教育;既有宏观的教育政策,也有微观的教育教学实践。限于篇幅,对其具体内容就暂不在此文中加以介绍和分析了。
杨贤江还翻译了很多外国教育的文献资料,翻译较集中的时间也是在南京高师和在《学生杂志》做编辑的时期,译文主要刊载于《教育潮》《少年世界》《教育杂志》《新教育》《学生杂志》《新感潮》《妇女杂志》等期刊。根据任钟印编《杨贤江全集》,杨贤江共发表关于外国教育的译文41篇。杨贤江翻译的外国教育文献资料主要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苏联等,其中翻译美国的教育文献最多,有22篇。译文包括教育理论,如《现代教育主张与教育哲学》《庶民之学校》《教育的改造》《汤申(Townsend)氏之美国教育哲学论》等。翻译对象包括泰勒(Ralph W. Tyler)、杜威、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等人的作品。译文中也包括对世界各国教育的介绍,如《美国初级中学发达之经过》《日本小学校体育科的新教材》《德国教育的现在与将来》《法国的师范教育》《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欧美劳动教育的近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译文是对国际教育发展动向的介绍,如《最近的国际教育运动》《最近的两大国际教育会议》等。
杨贤江对外国教育的研究涉及的国别和内容十分广泛,有理论,有政策,也有实践,即使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学术期刊上刊载的外国教育研究文章相比也毫不逊色。
在日本避难期间和回国以后,杨贤江还翻译和撰写了多项领域非常重要的大部头作品,如翻译了《世界史纲》(1928)、《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1929)、《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1929)、《今日之世界》(1929)等著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撰写了《教育史ABC》(1929)和《新教育大纲》(1930),此间他翻译的外国教育著作《新兴俄国教育》(1931)在他去世后出版。
五、结语
对于多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介绍和传播外国教育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究其原因,第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们多是“教育救国”论的真诚信奉者,他们希望通过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改造中国的教育,并通过新教育开启民智,建设新国家。然而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在思想上开始抛弃教育救国的思想,认为向外国借鉴教育经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第二,多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由文教工作者向职业革命家转变,他们的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和军事斗争。陈独秀、毛泽东自不必说,即使如杨贤江入党后有5年没有放弃编辑岗位,但之后还是成为职业革命家,用最大的精力投入到党的工作。只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而远走日本,才为他继续进行教育研究和介绍外国教育提供了条件。第三,鉴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他们开始由广泛地借鉴外国经验向主要借鉴苏俄经验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5]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初开始就积极介绍和传播现代国家制度与社会政治思想,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政治的角度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外国教育的介绍与传播是他们政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他们实现救国理想的重要途径。从教育的角度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外国教育的介绍和传播是20世纪早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股重要力量,为改造中国教育积累了知识、更新了观念,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比较教育发展史的角度看,与欧美的借鉴时代相似,中国也在比较教育专业化(可以1929年庄泽宣的《各国教育比较论》的出版为标志)之前也经历了广泛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借鉴时代,包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对外国教育的介绍与传播在客观上也为比较教育的专业化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