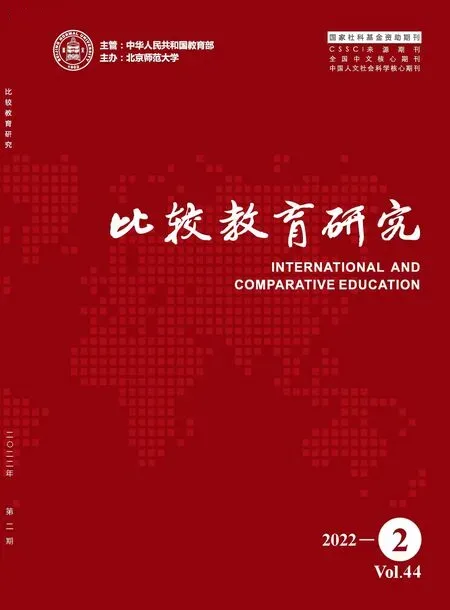全球教育治理视域中公立学校教师法律地位的重构
王俊,秦惠民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北京 100089)
21世纪以来,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韩国等国家以表现性(performativity)和问责制(accountability)为主线,推动公立学校教师法律制度改革,教师职业身份逐步走向契约化,教师法律地位亦随之重构。近些年,主权国家的教育改革趋同特征愈益明显,其集体行动的深层逻辑不仅表现在各国回应本国教育质量提升的现实需求,而且体现了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对主权国日渐明显的合规拉动(compliance pull)。在这一进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组织在教育治理权上的竞合,以及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在互动中达成的合意,均对各国教师法律制度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全球教育治理视域中审视主权国家公立学校教师法律制度的改革趋势,探究教师法律地位重构的逻辑意涵和脉络机理,为深入理解教师法律制度的基本功能提供有益参考。
一、国际组织对教师职业的符号控制
国内外学术界对“全球教育治理”尚未形成明确概念,但一个基本共识是,主权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不可或缺,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是关键主体。[1]随着“二战”后国际组织登上全球治理历史舞台,教育成为攸关人类发展的重要治理议题之一,教师亦被囊括其中。借用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编码理论,可以认为国际组织长期以来通过全球教育治理,在教师职业符号控制(symbolic control)场域具有主导地位。在伯恩斯坦的理论框架中,“分类”与“架构”是两个核心分析概念:“分类”表示不同范畴之间的区隔程度,蕴含不同社会范畴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架构”是由规约性话语和教导性话语所组成的调控规则系统,前者传递“有关行为、品格和举止上的期望”,后者传递“选择、排序、进度和评价标准”,架构的功能是确定如何选择标识(label)。[2]
(一)“强分类”:以“教师教学能力”标识教师质量
在“二战”后全球教育治理发展的初期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构建了对教师权利与责任的规范性理解,明确了其作为专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两大国际组织在1966年共同颁布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中指出,教师的地位赋予教师身份并对其表示尊重,它体现了社会对教师职能重要性和履职能力的肯定,同时也表现为,相比其他职业群体应给予教师更优的工作条件、报酬及其他物质保障。[3]该建议高度契合主权国家在“二战”后朝向福利国家发展的目标,为各国立法确定教师法律地位、保障教师职业权利提供了法理基础,也将公立教育及教师职业作为镶嵌在福利保障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例如,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几乎所有州都确立了公立学校教师长聘制度,保障教师获得稳定的职业发展。[4]作为早期主导全球教育治理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很长时间中以“教师教学能力”来标识谁是“好的教师”,对教师职业的符号控制是“强分类-弱架构”。在“强分类”中,“每个范畴都有其独特的认同、独特的声音,以及内部关系的特殊化原则”[5]。这意味着,教师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与其他职业有较强的区隔,具有较强的专业自治性,在不同国家可以存在多元的教师质量标准,社会对此也可以有不同的评判结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建立之初就以促进全球教育发展和文化交流为己任,它将受教育视为现代社会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强调教师因教育在社会进步乃至民众福祉中的关键作用而应受到尊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教师质量,在搜集、分析和发布不同主题的全球教育报告时,也会包含涉及教师质量的数据,如《全球教育监测报告》(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等。但相关数据强调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和保障,不以等级排序为目的,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在教师质量关键指标上的表现也侧重警示并提出改进建议,较少对结果做出结论性判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旨在以此描绘全球教育的发展图景,推动各个国家和地区自主捕捉教育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案。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本地情境中可以对教师教育和专业发展设计不同的实践路径,甚至教师专业组织和地方政府部门在实施教师质量提升措施时,也能具有相当的自治权。教师职业的稳定性受到法律制度的明确保障。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与新公共管理在政治经济实践中勃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经济领域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的权力版图中迅速崛起,在全球范围内重视教育市场的跨国公司和关注教育公平的慈善组织也在其间遥相呼应,为教育质量和“好的教师”提供了一套替代性的话语符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倡议,已经不能满足主权国家和地区对便捷高效教育治理模式的渴望。
(二)“强架构”:以“学生学业表现”标识教师质量
在全球教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国际组织对教师职业的符号控制逐渐转向“弱分类-强架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积极打造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体系,将教育和技能视为知识型经济体的政策核心,竭力倡导“教育政策的经济化和经济政策的教育化”[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0年率先开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开始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承担新的制度角色,以裁决者的身份对各国教育系统进行诊断、评价并提供政策咨询。[7]由于教师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仅次于家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8年启动了“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继续将教师职业和教学效果视为影响各国教育改革以及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2018年,分别有79个与48个国家和地区及经济体参与了PISA和TALIS的数据搜集和分析评价,均超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本身的成员规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弱化了教师的“分类”,降低了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区隔程度,以“学生学业表现”来标识“好的教师”,将其视为“吸引学生并促进其学习的一线工作者”。[8]基于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首次TALIS报告中直接批评韩国公立学校教师的终身聘任制,称其评价和奖惩机制不足,引发韩国国内激烈争论,最终促成韩国政府建立全国性的教师评价制度。[9]
与之相类似,世界银行在为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教育政策重点也从过去强调对教育系统的物质投入,转向关注改善学生学业表现。世界银行在设置教育改革议题时,充分融入了其长期倡导削减政府公共开支,推进公共事业私有化的理念。[10]2011年,世界银行启动“为了更好学习结果的教育系统测评”(Systems Approach for Better Education Results, SABER),其中包含“教师”评测模块。该模块确立教师政策的八大核心目标,搜集和分析世界各国教师政策的综合信息,并按照四个等级进行评价。相比PISA,SABER吸纳了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目前是教育领域适用范围最广的国际评估项目。当类似的评估项目成为衡量国家教育质量及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时,教师职业的“架构”逐步增强,教师所要满足的期望和所要达成的标准日渐清晰明确。
此外,一些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在关注教育发展时,也在积极宣扬“教师质量决定教育质量的上限”这样的观点,包括全球最大慈善组织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全球咨询业务主要服务商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全球教育培训市场领导者培生教育(Pearson Education)等。例如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有效教学测量”(Measures of Effective Teaching)项目,辨识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学业表现的教学方法。这些组织超越主权国家边界,以自由市场和资本效益的角度重新解释、规制甚至干预本地教育。[11]
二、主权国家教师法律制度的改革趋势
(一)合规拉动: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的立法互动
在全球教育治理符号控制的竞技场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以新的概念体系对教师职业进行符号加工,进而改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互动形式。当国际组织以全球共同利益为依据,就教师质量设置改革议题、监测分析数据并提出政策改进建议时,其基于广泛证据所形成的认识论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隐含了期冀各国应当接受并遵循建议的要求,进而对各国制度改革产生最低程度的合规拉动。[12]一旦教师职业“弱分类-强架构”的符号控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确立起来,各国政府可以重新界定教师职业的属性与价值,在竞争社会的话语规训中将教师个人责任与国家未来发展融合为整体,为启动教师法律制度改革构造合法性基础。[13]诚如苏珊·罗伯逊(Susan Robertson)所敏锐观察到的,教师的全球治理机制从“规范的制定”迈向了“竞争的比较”。[14]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试图从多国数据比较中探寻全球教育“善治”的最佳实践和标准程序时,教师往往首先成为教育改革中的可治理对象。面对PISA结果带来的国家危机感,德国政府紧急采取教育改革措施,重视教育产出和测试评价,使得德国教育系统逐渐演变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特殊混合物”,为柏林州和萨克森州率先废止公立学校教师公务员制度提供了契机。[15]
国际组织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模型,将影响教育质量的各种因素进行标准化处理,使之成为可衡量、可比较的数字和排名。一旦将不同情境中的教育质量转变为共同尺度,并且提供一种能够剥离复杂因素的解决方案,“强架构”的调控规则体系必然超越国家领土边界,从而导致各主权国家在参与全球教育评价时,实际上让渡了部分本国政府在教育治理中的基础功能。这种让渡表现为各国政府不必充分地在本国情境中对教师质量问题进行循证调研,研制适切的解决方案。20世纪90年代,美国试图拆解福利国家时代建立起来的职业保障,推行弹性而非固定的劳动制度,但各州的改革在教育领域举步维艰,遭到学校尤其是教师工会等专业组织的强烈抵制。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民众再度重视知识技能的市场价值,联邦政府对国际教育评价排名的不利结果进行了危机式解读,进一步营造了改革势在必行的紧迫氛围。之后,各州教师立法势如破竹,消解了累积多年的改革阻滞力量。当国际组织的治理范式、国家政府的改革议程和社会民众的价值情感相一致时,一种解决方案可以获得最大化的权威,他国有效实践和国际广泛共识成为推进教师法律制度改革的外部合法性来源。国际组织传递教师质量提升的最佳实践和标准程序,本质上是在制度趋同逻辑下将不同国家涉及教师的“各种组织模式的优点整合进一种制度的混合色拉”[16],但它为本国立法者提供了更具影响力和解释力的证据,响应了新自由主义与新公共管理理念。作为传递者的国际组织与作为接受者的主权国家,在新的合理性互动中达成合意。
新自由主义与新公共管理实践起始于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却是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支持,才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霸权话语。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幸福。”[17]因此,新自由主义改革倡议者认为应当调整公立教育目标,强调培养学生具备重要领域的标准化知识与技巧,使其掌握参与竞争所必需的能力。不论是“歌颂转瞬即逝的事物和短期合同”[18],还是认为“每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的拜物教信仰”[19],新自由主义呼吁拆解公立学校教师自福利国家时代以来的职业保障,试图以教师的个人责任体系取代其专业人员地位。新公共管理是以新自由主义理念改革公共服务部门的概念化结果,它要求抛弃过去“由文明的技术官僚进行独立的管制活动”[20],采纳市场术语将公共服务概念化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类交易行为,“以明确的目标对产出设置绩效测量标准并对达成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严格测量”[21]。对于公共服务部门的雇员而言,“这些改革试图用以市场为基础、由竞争驱动的策略来取代传统上以规则为基础、由权威驱动的过程”[22]。在全球教育治理的规训之下,主权国家在教育立法中以表现性与问责制为主线,改革教师法律制度。
(二)强调精准展现,细分教师评价结果
表现性以符号化和物质化的奖励或惩罚为基础,采用评判、比较和展现的方式,用规制手段激励和改变教师行为。当教师与学校的质量及价值被框定在一个接受评判的场域中时,政府成为掌握评判控制权的关键行动者,可以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有效的或者令人满意的表现,也可以决定采用怎样的指标体系和测量方式。[23]为了精准衡量教师教学行为的输出能力,提高评判结果的清晰度,主权国家在立法中细化教师评价机制的指标体系,特别将学生学业表现纳入其中。
2012年,英国在进行教师评价改革立法时,将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标准”(Teachers’Standards)确立为法定评价基准,同时赋权校长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可视待评教师具体情况,增加使用教育部发布的其他标准。①The Education (School Teachers' Appraisal) (England) Regulations, 5(1), 6(8) (2012).波兰在2019年修订《教师宪章》时,加强了对公立学校教师尤其是任命制教师的评价,教师评价的间隔周期最短可至一年。②Karta Nauczyciela, art. 6a, ust. 1 (2019).在美国,多数州已经摒弃简单评价教师表现“是否满意”的做法,逐步通过立法采纳以多级体系为主的教师评价制度,少数州甚至采用了五级评价体系。[24]2019年得克萨斯州《教育法典》规定,教师评价标准必须基于“可观察的、与工作相关的行为”,包括“教师执行纪律管理程序的情况和教师所教学生的表现”两个部分。①Texas Education Code § 21.351 (2019).相应地,在“得克萨斯州教师评价与支持制度”(Texas Teacher Evaluation and Support System)中,学生学业成长测量是重要组成部分。密歇根州也在2019年修订法律,将学生学业表现相关数据在教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从25%提高至40%。②Michigan Compiled Laws § 380.1249 (2020).以增值(value-added)评量的方式估算教师对学生学业产生的影响,目的是为了精准甄别教师表现。
(三)推定行为标准,明确教学责任要求
问责制采用教师未能达成预定目标后的潜在威胁,推定教师任务环境中的指导原则、规范框架和行为标准,试图明确教师在承担教学责任时的限制性要求。新的教师评价制度以探究和区分表现性为目的,为问责制提供了明确且适当的工具,“分数等级产生了一种潜在的修补服务及其诊断理论、诊断实践和责任分配”[25]。问责制源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一种先验不信任,延续这样的逻辑,教师质量的评判以其达成预定目标的情况为依据,而不是公立学校获得的强制授权或者教师个人赢得的资格证书。[26]
一方面,强化教师职业准入考察,根据新任教师入职期的评价结果决定是否留任。2019年,希腊立法要求教师在入职公立学校两年后必须就其教学适任性接受评价,评价不合格的教师会进入阶梯式退出程序。③Νόμος Υπ'Αριθμ 4589, άρθρο 62-7 (2019).美国多数州也在近几年修订法律,延长了公立学校教师获得长聘身份前所需完成的试用期,并且以常规评价结果作为前提,以期充分审慎地考察教师的教学能力。[27]另一方面,强化评价结果利害性,要求教师在履责效果未达预期要求时承担相应后果。西班牙在2020年修订《教育组织法》时要求,如果判定教师无能力履行教学工作,或教学表现恶劣且拒绝改进,学校可依法将其调离教学岗位。④Ley Orgánica de Educación, disposición adicional cuadragésima octava (2020).在美国,新泽西州法律规定,如果长聘教师的评价结果连续两年是“无效”或“部分无效”,学区教育委员会可判定该教师“无效率”(inefficiency),可依据法定程序撤销其长聘身份。⑤New Jersey Revised Statutes § 18A:6-17.3 (2020).在田纳西州,基于负面评价结果也可判定教师“无效率”,这在法律上构成对教师停职或者解聘的正当理由。⑥Tennessee Code § 49-5-501 (2019).
三、公立学校教师法律地位重构的潜在风险
(一)弱化教师法律地位
国际组织通过全球教育治理的影响,推动新自由主义与新公共管理治理范式在教育领域渗透,各主权国家在教师法律制度改革中相应地重构了公立学校教师法律地位。自然人的法律地位是法律人格的属性之一,决定其在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同样,教师法律地位决定了教师的权利与义务,也决定了教师在各种法律关系中的位置,更决定了教师行为受到法律规制的边界和教师职业受到权益保障的程度,因此是教师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
在不同国家,公立学校教师法律地位一般为公务员(civil servant)和公共雇员(public employee),部分仍处于试用期或者未获得长聘资格认定的教师被视为一般雇员(employee)。教师法律地位的实质内涵是由法律制度规定的具体权利和义务同构而成。当各国以表现性和问责制改革教师法律制度时,缩限职业保障中的权利和扩增履责要求中的义务,使得教师法律身份从过去“强分类”下的权利导向转向“强架构”下的义务导向。即使在形式上没有改变教师法律地位的称谓,但是教师权利与义务构成的权重导向发生变化,仍然实质性地重构了教师法律地位。美国各州近些年的教育立法已经打破了教师长聘制度原本提供的实体性与程序性保障,常规评价中的负面结果可以作为撤销教师长聘身份,甚至直接解聘教师的法定依据,教师作为公共雇员的法律地位遭到弱化。[28]
(二)降低教师职业吸引力
对于公立学校教师队伍而言,教师法律地位重构会降低教师职业在社会分工中的吸引力。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与新公共管理治理范式倡导市场竞争与责任意识,对于提高教师队伍质量,尤其是破除教育系统中部分存在的组织臃肿和教学无效现象,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教师法律地位表明了教师在社会体系中的位次,具有象征性的敬重与尊严特质。当教师职业在社会分工中的区隔被打破,日渐趋近自由市场中的一线工作者时,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就有失去其原有认同的危险,很难让人信服这一职业群体在社会体系中可以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尊严、利益及保障。
德国萨克森州在激进改革中废除了公立学校教师公务员制度,造成教师流向其他仍然保留教师公务员身份的州。面对教师队伍持续短缺的问题,萨克森州修订法律,将2019-2023年作为恢复教师公务员制度的过渡期。①Sächsisches Beamtengesetz § 144a (2018).在法国,由于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近年来报名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人数持续降低,作为一种补救措施,政府以立法设置教育助理预聘制度,聘任尚未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本科师范生到公立学校完成一定教学工作。②Code de l'éducation, article L916-1 (2019).在美国,改革的确提高了新任教师质量,但是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数下降了,学校教学岗位的空缺期延长了。在少数族裔和贫困学生聚集的薄弱校,教师聘任难和留任难的问题更加突出。[29]
(三)导致教师自我异化
对于公立学校教育质量而言,教师法律地位重构会导致教师在教学行为中的自我异化。在法律地位重构进程中,关键指标数据日渐成为界定教师专业职责的重要依据,而契约化的聘任关系使教师在劳动力市场中愈益面对失业风险。[30]当表现性和问责制变成教学行为本身的理由并产生恐慌时,教师很可能出现史蒂芬·鲍尔(Stephen Ball)所形容的“自我异化”(alienation of self),违背教师的职业道德与专业精神。[31]
在与学校的法律关系中,教师的教学能力仅仅体现在能否协助学校在学生学业表现上达到关键指标的预期要求,这样的后果贬损了教师在传统概念意义上所拥有的教学知识与专业能力。学校采用的种种监督与评价技术不仅会分散教师的精力,也会束缚教师创造性地解决教学问题所必需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中,教师的教学能力集中表现在能否持续改善学生学业表现,特别是提高测验分数,这样的后果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疏离教育的本质要求,在设计教学内容和决定教学方式时都以确保学生获得更高测验分数为目标,会忽略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发展需求。而这个时候所实现的教育质量提升,不过只是可衡量指标上的数据化改善而已。
四、尊师重教:回归教师法律制度的基本功能
教师法律制度在形式上明确教师行为规范框架,配置教师权利义务,提供纠纷解决机制,其基本功能在于稳定教师队伍并提高教育质量。通过初步分析主权国家教师法律地位的重构,可以反观全球教育治理中对教师职业的符号控制与合规拉动,也可以管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积极传递以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理念为基础的治理范式。应当肯定,这些理念在教师法律制度改革中具有积极意义,如奖励有效教学工作、激发教师努力进取等;也应当肯定,全球教育治理尤其是教育评价为各个国家提供了互学互鉴教师政策的平台。但从各国经验来看,表现性和问责制的改革主线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教师法律制度的实施结果背离功能预设,教师法律地位重构中的义务导向使得公立教育的系统需求面临挫折风险,潜在破坏了制度改革原本旨在完善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引入评价与问责机制时,仍应以清晰的教师法律地位构造教师法律制度,厘清教师法律关系的逻辑起点,确保教师权利与义务整体平衡。
回归教师法律制度的基本功能,才能实现尊师重教、教书育人的价值理性。目前,我国正在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修订工作,根据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这一表述,不仅凸显了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而且体现了教师与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将教师与学校的关系认定为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的雇主与雇员,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自由市场模式,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认定为市场中的教育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既要建立完善的教师评价与退出机制,也要避免简单地用学生学业表现评价教师,不能将教师完全置于等级式的表现评价和高利害问责的惩罚中。只有遵循教师成长与职业发展规律,赋予教师应有的法律、政治与经济地位,尊重教师的专业属性和保障教师的职业稳定,才能真正使教师具有职业尊严,从而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