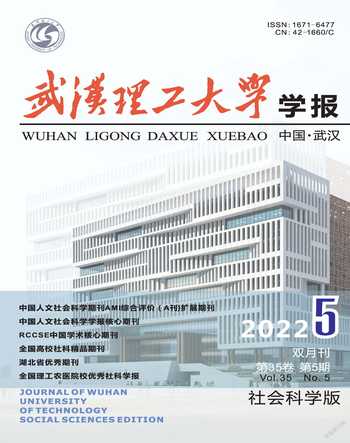“乐”与中国古代审美体验
高越, 黄念然
摘要: “乐(lè)”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重要的理论范畴。其美学意蕴有三:是审美过程中主体的审美愉悦感的重要体现;是对中国古代以诗、乐(yuè)、舞为代表的艺术创造或审美活动所引发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的重要理论提摄;是审美体验活动之高级阶段审美主体的超越性精神体验的表征。“乐(lè)”作为审美体验,贯穿于审美体验活动的全过程中,并呈现为“即身”之乐、“会心”之乐、“神游”之乐三个依次递进的不同体验层次。就其审美体验中所蕴含的超越性而言,“乐”又主要呈现为以“和”为旨归的儒家之“乐”境界、以“妙”为旨归的道家之“乐”境界和以“圆”为旨归的禅宗之“乐”境界。“乐”比“美感”更适用于描述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活动的层次性、超越性以及对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美学特色。
关键词: “乐”; 审美体验; 美学意蕴; 审美层次; 境界形态
中图分类号: B283-09; B83-02文献标识码: A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2.05.001
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审美心理学的发展,美学学科的研究重心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即从研究“美”的本质的“美学”转向研究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尤其是审美心理活动的“审美学”。“审美体验”作为审美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出现在美学发展史上,是较为晚近的事情。据伽达默尔对“体验(Erlebnis)”概念史的考索,直到19世纪70年代,受传记文学的影响,“体验”“才成为与‘经历(Erleben)’这个词相区别的惯常用词”[1]。学者陈伯海在其《走向“体验美学”》一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美学理论思想时,“偏偏选择‘体验’而非‘经验’来指称审美活动的特质所在,其中蕴含的意义颇足玩味”[2],同时他还注意到,西方学界从狄尔泰开始,虽不否认“体验”中蕴涵的情感因素,但他们始终更关注“体验”的认知功能,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学人却始终偏向“審美体验”中情感心理的一面。从陈伯海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察觉到中西方美学对审美体验思想在认知上的差异,并有意识地倡导建立符合中国思想传统的“体验美学”。
从审美体验切入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的。原因在于,体验性是中国古代审美活动的基本特征[3],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是将对人生的深切体验作为基础的。对于“审美体验”,皮朝纲教授曾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他指出,美学意义上的“体验”是指“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聚精会神的审美观照时在内心所经历的感受”[4],他进一步强调,此处的“体验”不只具备普通心理学意义上的情感功能,“而是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多种心理功能的有机结合的整体”[3]。关于中国古代审美体验问题,理论成果较为丰富,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是以“味”为中心范畴的,并衍生出“体味”、“味象”、“品味”、“滋味”、“意味”、“韵味”、“趣味”、“情味”等系列范畴①;有学者提出,“兴”才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的核心范畴,由此形成的“感兴”、“兴会”、“兴象”、“兴味”等序列范畴涵盖了中国古代审美体验活动的各个阶段②;还有学者将“悟”视为理解中国古典美学独特的审美体验方式的关键所在③;亦有学者将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中的“游”、“物化”、“涵泳”等与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论相关联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乐”⑤也是体现中国古代审美体验思想的重要范畴。综观前人的研究成果,少有学者从范畴论的高度或角度去探析“乐”在中国古代审美体验活动中的美学意义,事实上,“乐”范畴已然渗透到中国古代审美体验活动的全过程,并以不同的体验层次以及对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呈现在中国古代审美体验活动及其理论总结中,很值得对此作深入探讨。
一、 作为审美体验之“乐”的美学意蕴
“乐”的美学意蕴首先体现在对主体审美愉悦感的描述。古代有很多可以表达“快乐”这种情感色彩的语汇。《尔雅·释诂》中就列出了十二个与“乐”词义相通的字词:“怡、怿、悦、欣、衎、喜、愉、豫、愷、康、妉、般”[5],尽管都可以表达“愉悦”的情感趋向,但唯有“乐”发展为美学范畴。因为,“乐”具有其他词汇所无法传达的情感特征。“乐”在情感表达上凸显了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精神,“乐”之“和”体现有二:其一,“乐而不淫”,即在情感强度上把握“适度”的原则,“乐”在情感性质上是积极的,但古代圣贤秉持过犹不及的理念,认为“乐”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便会失其正而成为“淫”;其二,“忧乐圆融”,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和”与“同”的区别,即“和”是承认差异性的,因此,在情感体验上,“乐”与“忧”并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甚至在古代儒者眼中,“忧”、“乐”本就是一体的,正所谓“是故君子终身忧之也,是其忧也,乃所以为乐”[6]。
从词源学上讲,“樂”的字义演变过程是比较复杂的,至今未有定论⑥。尽管无法确定“乐(yuè)”与“乐”到底孰先孰后,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乐(yuè)”与“乐”最初在字形和读音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常常出现二者混用和互训的现象。刘成纪教授曾详尽地论证了“乐(yuè)”、“乐”在中国文化初始时期的互训关系,认为这种互训关系表明在中国社会早期,作为情感形式之“乐”与作为艺术种类之统称的“乐(yuè)”之间是交互生成的关系[7]。在他看来,两者之间的交互生成关系首先体现在:先秦两汉时,“乐(yuè)”代表了“乐”的“高度聚集形态,以至于它被赋予了指代一切快乐的性质”[7]。张法教授同样肯定了“乐(yuè)”对于“乐”之美学意蕴发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乐”之所以能超越“欢”、“喜”、“雅”、“佳”、“妙”、“旨”、“休”等词而成为代表美感和快感的普遍性语汇,是因为“乐”反映了远古时期包含音乐在内的仪式之乐(yuè)所产生的主体审美快感[8]。由此可见,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萌芽期,“乐”在产生之初便与艺术密不可分,尽管“乐(yuè)”并非是“乐”的唯一来源,但“乐”之美学意蕴集中体现在对诗、乐(yuè)、舞为代表的艺术活动所引发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的描述上。
在中国文化的早期阶段,“乐(yuè)”是作为诗、乐(yuè)、舞三者一体的艺术形式而存在的,这在留存至今的乐(yuè)论文献中就有鲜明的体现。《尚书》在追溯三代以前的艺术活动时曾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9]的艺术发生学构想。《礼记·乐记》以“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10]221来解释“乐”。《诗大序》亦曾论及诗、乐(yuè)、舞的关系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0]24。由此可见,“乐(yuè)”作为艺术种类在其产生之初,便是诗、乐(yuè)、舞三者的有机统一体。或许正是“乐(yuè)”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表达形式,使其在早期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有的古代艺术文献资料表明,在远古自然崇拜阶段,“乐(yuè)”就是沟通神与人的重要手段,原始先民在敬神仪式中一起歌咏、舞蹈、演奏乐器,试图借此感动鬼神,通过“神人相和”的方式向自然神獲取力量,“乐(yuè)”由此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到殷周时期,以“帝”和“天”代指的至上神观念已经成型,在“乐由天作”的观念影响下,“乐(yuè)”被视为是天地和谐的代表,蕴涵着天人合一的文化理想,并渗透到天文、历法、政治、文化之中。概言之,正是由于“乐(yuè)”在古代早期社会文化体系中的突出地位,从而使与之相伴而生的“乐”成为了描绘主观艺术体验的重要范畴。
尽管“乐(yuè)”是“乐”的重要来源,但能够使人“乐”的对象却是十分广泛的,其中有一些难免会使人沉湎于感官愉悦的低级快乐,同样属于“乐(yuè)”的雅乐和“郑卫之音”,它们所带来的审美体验在圣贤眼里也是有本质区别的。为了避免“乐”停留于“声色之乐”的低层级,春秋战国时期,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就开始将“乐”与人的精神境界相连,“乐”由此上升到哲学高度,“乐”的美学意蕴与哲学意蕴交融于一体,成为了人之精神的超越性体验的表征。嗣后,宋明理学家以“孔颜之乐”为精神标杆,进一步将“乐”升华为“心理合一”的本体境界的象征,出现了“乐是心之本体”[11]79的哲学命题。又由于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论美学,这便意味着中国古典美学的归宿在于对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探寻,这种审美追求表现在审美活动中,使得中国古典审美观念不太注重对“美”的客观认识,而是更为关注审美对象感召下主体心灵的感受,试图在主客体的交融中达到一种超越的审美境界,其落脚点是为了获得精神的自由与高蹈。因之,“乐”对于主体精神体验的描述,实质上就是人生论美学在“乐”之美学意蕴上的体现。
总之,“乐”的美学意蕴可以从一般审美愉悦、艺术创造中的审美体验以及哲学意义上的精神超越三个主要方面加以把握或理解,它不仅呈现出审美这种精神活动应当具备的不断生成的内在特质,而且在理论内涵的延展上呈现出一种逻辑自洽性,这也正是“乐”能成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中的重要审美范畴的根本原因。
二、 作为审美体验之“乐”的审美层次
现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完整的审美体验的动力过程,呈现出由初级层次向高级层次,由外部体验向内部体验,由浅层感受到深层体味的层递性”[12]。对于审美体验的结构层次,中国古人也有很多真知灼见。如《庄子·人间世》便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13]152,其中,“耳”、“心”、“气”分别代表了三种依次递进的主观体验层次;宗炳《画山水序》更从“应目”、“会心”、“畅神”三个层次描写了赏画之体验:“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应会感神,神超理得”[14]。画家李日华也认为“凡画有三次”,分别是“身之所容”、“目之所瞩”和“意之所游”[15]。可见,在古人看来,审美体验就是与人之身体感知息息相关且不断提升的活动。而从“乐”的审美体验过程看,它也具有从“身”、“心”、“神”这三个由外而内且层层递进的总体特征。
(一) “即身”之乐
“即身”不只包括“耳目之所接”,而是容纳所有的官能体验于其中。正如荀子所言:“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16]63。在中国传统认知理论中,五官之官能体验都是可以上升到更高层面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专有一词来描述身体感官的这种敞开、通畅的状态,即“窍”。《庄子·应帝王》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13]315,“七窍”指的便是耳目鼻口的七个孔窍。《说文解字》云:“窍,空也,从穴敫声”[17]344。这实际上也表明,在审美体验伊始,审美主体之“身”并非是封闭的,而是向天地万物敞开,随时准备接纳五色、五声、五谷、五味、臭香。
所谓“即身”之乐,是指在审美体验的低级阶段,审美主体处于“虚而待物”的状态中,身入其境,五官百窍向外舒展张开,受外物之感应而产生的乐感体验。“即身”之乐凸显了审美主体在对审美客体的审美观照中兴起的直接的感官感受,故“遇乎月,则见之目怡,聆之耳悦,嗅之鼻安”[18]。尽管如此,但并不能将“即身”之乐与纯粹的生理快感划等号,其原因在于,“即身”之乐是审美体验活动中主观感受的有机组成,是可以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的,它依赖于“身”,但并不过分刺激“身”之孔窍,更不执著于“身”之体验。在中国古代的审美创作心理学中,非常强调“身之所历”对于审美创作心理的发端意义,并有大量相关论述。可以说,“即身”式审美是审美主体在审美体验活动中激发内在情思、推动审美体验过程深入的重要途径,正如刘勰所言:“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19]47。
更为重要的是,“即身”之体验是与古人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审美主体可以从不经意间发觉的某一事物的审美意味中淘洗性灵、感悟人生,“味象”而“悟道”,“即身”而“道在”,因此,“即身”之乐并非是浅尝辄止的愉悦体验,而是可以蕴涵无限哲思的。苏轼《超然台记》云:“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20],苏轼之旷达正体现在他可以从日常所见所闻中独具妙心、自得其乐,故他观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后,便能超越人生的有限时空,与万物相与为一,共适宇宙之无穷,获得深刻的生命体验。
(二) “会心”之乐
“心”之于审美体验的重要作用源于中国古代身体观中“心者,身之所主也”[21]的观念。在古人看来,五官、四肢、百骸,莫不听命于心,供心所役使。如王守仁便说:“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11]41。这种“心为身主”的传统思想表现在审美体验之层次中,就是由“即身”之乐上升到“会心”之乐。“会心”最早见于魏晋时期关于艺术欣赏的谈论中,《世说新语》云:“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22],不难看出,在最初的艺术理论语境中,“会心”便表达了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之内心所感到的快适。
所谓“会心”之乐,是指随着审美体验活动从审美主体之外感官对审美客体的观照,进入到审美主体之内感官对审美客体的感应之中,审美主客体邂逅于主体之内心灵境中,相互缱绻交融,审美主体之“心”在此过程中深刻感悟到的审美乐趣。由此可见,“会心”之乐的产生首先离不开审美体验过程中“心”与“物”的交互运动。对此,古代理论家一方面承认审美体验源于“物”对“心”之感发,认为人虽禀七情,但人之天性是处于静的状态,之所以会从内心流露出不同的情感,是因为受到外物的刺激;另一方面,古代理论家又格外强调审美体验过程中“心”之于“物”的能动性,认为随着人之心境的变化,“心”所赋予外物的情感色彩也是不同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审美活动中“心”与“物”之互动关系有着精彩的描述,他将“心”、“物”之互动关系形容为“赠”与“答”的交互模式,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19]313。
滕守尧教授在吸取西方现代审美心理学之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审美快乐之产生源于“主体克服重重干扰与类生命的审美对象本身的图式发生同构或契合时,内在紧张力便幻变出与审美对象同形的动态图式,有了确定的方向性和动态的奋求过程,愉快便随之产生”[23]。与之类似,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中的“会心”之乐,实际上同样强调审美过程中主客体内在的契合和类同。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始物质,天地之间,无论巨细,皆为气攒聚而成,不仅如此,天与人同样禀赋喜怒哀乐四种性质的“气”,即:“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24]。在此基础上,天地万物又因为气类的相通而可以实现“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25]的相互感应。而审美体验中所谓的“会心”之乐的产生,其根源正在于此,当审美客体所携带的“气”与审美主体之“心”所感发之“气”正好气类相和时,审美主体便体会到一种心意被印证的欢愉。
(三) “神游”之乐
《说文解字》释“神”曰:“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17]3。“神”之本意是指原始信仰中有人格的神灵,后被引申为与“人”之形体相对的精神。在中国古代的身体观中,“神”被视为是“心”之精华所在:“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26]520。当“心”、“神”并举时,往往更突出“心”之生理上的实体义,“心”被认为是“神”之居所:“心者,生之本,神之處也”[27]。或许正是由于“神”本意所带的神秘色彩和超脱于“心”之血肉载体的虚灵不昧,使其常常被应用于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思维的描绘中,衍生出“神思”、“入神”、“神妙”、“神奇”、“神游”等概念范畴。
在古代文献典籍中,“神游”最初是用来形容人在形体不动前提下的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如列子云:“(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28];《淮南子》亦曰:“是故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26]112。至汉魏六朝,刘勰正式提出“神与物游”的审美活动命题:“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19]182-183。这其中,“神游”可以创设出高妙的审美境界,使审美主体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审美对象,而是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思维营构出可供心灵优游的艺术意境;此外,“神游”式的审美心理活动还可以超脱于现实时空之上,使主体在身心寂然不动的状态下神游象外,跃入大化流行之中,与天地万物浑然合一。
综上,所谓的“神游”之乐,就是指在审美体验的高级阶段,审美主体放弃了一切生理层面的感官、脏腑对审美对象的观照,用无声无象之“神”去感悟蕴含于审美客体之内的杳杳冥冥之“道”,从而超越具体生活经验和现实时空,由此获得了极度自由的精神愉悦。在古人看来,审美体验从来不是为满足耳目之欲和情感宣泄而存在的,而是要通过“游于艺”以明乎宇宙之大道,并参赞天地之化育,获得有限生命的无限永恒。但“道”之存在“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13]252,故“神游”在存在形态和运化节奏上是与“道”最为切近的。
由此观之,“神游”之乐已不再停留于审美体验,而是一种生命体验,乃至是一种审美式生存境界。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飘颻於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飧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29],便是这种“神游”式的至乐之境的鲜明写照。
三、 作为审美体验之“乐”的境界形态
上文主要是从动态的、历时的视角剖析“乐”之内在层级及其审美体验内涵,实际上,还可以从静态的、共时的逻辑理路来探究“乐”之审美境界形态。钱穆曾言,中国之学问,在于人之相处,心之相通,其精髓当为一“乐”字,“乐”乃人生本体,人生最高境界[30]。钱穆此言点出了“乐”之于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哲学意义,审美式的“乐”境界确实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共同的精神追求。但由于哲学观念和思想修行的不同,他们所神往的“乐”境界也呈现出各异的美学形态,其中影响最为深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家、道家和禅宗的“乐”之境界形态。
(一) 儒家之“乐”境界:归于“和”
《孟子·尽心下》曾谈及“美”与“善”的关系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31]334。在儒家看来,“善”是“美”的基础,道德体验是审美体验的基础。儒家的道德体验之“乐”是围绕他们的“修己以安人”的理想信念而构建的,于内表现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1]302的内圣之乐;于外表现为“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16]209的外王之乐。这种道德体验之“乐”中蕴涵着圣贤对周代以来以“礼”为核心的社会伦理秩序的认同与维护,表现了天道、王道、人道相“和”的道德伦理境界。但道德体验之“乐”境界并非是儒家之“乐境”的最高境界形态,因为道德体验之“乐境”的实现受限于很多外部因素。当邦国无道,天命难违之时,儒家强调要“知命”,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32]218。但顺应天命的安排并不意味着放弃道德体验之“乐”境界,而是将之融合于对审美体验之“乐”境界的追寻中,在审美式的生存中深体生命本真的快乐。
儒家的审美体验之“乐”境界就是以审美情感观照内在人格、体验生命本身,摒弃外在现实因素对自身的牵绊,通过保持情与志、天与人的相和而达到的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儒家审美体验之“乐”境界以“和”为归宿,表现出以下两大特征:
其一,以内在人格的自足为乐。当圣贤无法施展自身抱负之时,他们选择回归自身的人格世界,通过内在本心的自洽、自由而自得其乐。“孔颜之乐”就是这种内在人格自足之乐的典型形态,强调的是外在的世风日下、困顿贫穷皆不能入吾心,亦不能改吾乐。孔子曰:“仁者不忧”[32]102,仁者之所以能够乐以忘忧,就是因为其内心情、志的相和。当天下有道,则志于弘道行仁,虽九死其犹未悔;当天下无道,则“反情以和其志”[10]228,以审美情感颐养内在人格,保持本心的平静与超越。
其二,以人与宇宙精神的相和为乐。儒者内心的悠然自得并非是封闭本心,而是向天道敞开,求得本心与天心的契合无间。这种天人相和的审美式“乐境”集中体现于孔子“吾与点也”的喟然之叹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32]127,对这种审美式精神境界的体察不能执着于表象,而是要体会圣贤回归生机勃发的自然灵境中,超然物外,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精神乐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32]163,孔子将“天”视为唯一的知己,认为其心与天心可以默然相识,这是因为圣贤与天地合其德,与天地万物源于一道,故圣贤可以比德于山水,拥有与天地精神相通的乐境。
(二) 道家之“乐”境界:归于“妙”
道家并没有直接对审美体验进行理论阐释,但这不妨碍道家认为体“道”的过程与审美体验之间在深层次上是相通的。“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在道家看来,“道”是“无”与“有”的统一。“道”为宇宙本体,先天地而生,但“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搏之不可得,是不可描述不可感知的,此为“道”之“无”也;“道”虽具有“惚恍”的特征,但“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不可捉摸中又有可确定的本真,杳杳冥冥之“无”又可向形形色色之“有”衍生,此为“道”之“有”也。
道家常用“妙”來形容“道”之无限性、无规定性。老子曰:“故常‘无’,欲以观其妙”[33],这其中,“道”是无法用理性和逻辑进行规定和描述的,只能用虚静之“心”去体验和感知。庄子更进一步发展了“妙”的抽象意涵,使之成为“体道”之最高境界的表征。《庄子》一书两处出现“妙道”一词,“妙”是作为“道”的修饰语出现的,“妙”与“道”的联系愈加紧密。《庄子·寓言》云:“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13]948在这种“大妙”之境中,个体人格实现了绝对自由与无限,人不再受现实生活中一切利害得失的束缚,即无“物役”,而回归天地万物之中,与万物相统一,从而在生死之际也能自然顺任,参赞天地之化育,实现了人的本体存在与“道”的存在相合一的境界。
道家所营构的这种“大妙”之境蕴涵着道家对个体之人生和生命的安顿。道家从一开始就秉持着“保身”、“贵生”的理念,在此基础上,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家开始思考最理想的人格境界为何以及如何达到人生的绝对幸福。可以说,道家所追求的最理想的人格境界和人生的绝对幸福,不是道德性质的,也不是宗教性质的,而是一种无功利的、自由而无限的审美乐境。与“大妙”之境相通,道家的审美体验之“乐境”同样建立在“体道”的基础上,追求物我一体、“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立足于“天道”,提出了“天乐”之说。“天乐”与“人乐”相对,具有“赍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13]467的特点,因此,“天乐”是一种“与天相和”的大乐,超脱于世俗的道德伦理追求之上,顺应天地万物之自然秉性。因此,“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13]467,“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13]467。可见,道家之“乐境”就是要超越了世俗之寿夭、贵贱、荣辱、贫富等世俗差别,达到一种与“道”顺化,和天地共生死的“大妙”之境。除“天乐”之外,庄子还提出了“至乐”一说,其曰:“吾以无为诚乐矣”[13]610,故“至乐无乐”[13]610,不难看出,“天乐”和“至乐”本质上是一致的,皆以“妙”为旨归,体现了“妙”之“无”的特性。总而言之,道家所追求的“乐境”就是站在“道”的立场上观看万物,这样就超越了有限,参与到万物生生不息的远、返、复的运动中,无为而任随自然顺化,由此消除了一切世俗中一切有限的快乐,而获得无限的、永恒的“大妙”之“乐”。
(三) 禅宗之“乐”境界:归于“圆”
佛教常用“圆”来表现佛教体验之最高境界。比如:“大圆镜智相应心品,谓此心品离诸分别……性相清净离诸杂染,纯净圆德现种依持”[34],这句借用外形具有圆浑之美的“大圆镜”来形容佛教“涅槃”境界的圆满具足。禅宗在宗教体验之“涅槃”境界上同样以“圆”为旨归:“诸佛体圆,更无增减,流入六道,处处皆圆”[35]224,故“禅”对审美体验之“乐”的深刻影响也表现在它以“圆”为美、以“圆”为乐的境界追求上。
“禅”之审美乐境以“圆”为旨归,首先体现在它“不执一端”而力求精神圆满、圆融的苦乐观上。在“禅”看来,最高的精神灵境应当是“梵我合一”,断灭一切之分别的,所谓“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真常寂灭乐,涅槃相如是”[35]54-55。更进一步看,“禅”审美体验之“乐”境界也正是建立在禅宗“不二法门”之上的。所谓“不二法门”就是要超越一切之分别而臻于“一”之圆满。禅宗对“分别智”的破除绝非仅仅模糊对立双方的界限,也并非如老庄思想那般,将对立双方统一于绝对的“无”或“浑沌”之中,而是彻底根除分别性的思维,同时否定对立的两边,进入“不有不无”、“非此非彼”的圆通之境。“不二法门”在“禅”之“乐”境界中就体现在它不单单消泯了世俗的苦乐,更断灭了产生苦乐分别的世俗思维。故而,在禅看来,在最高的境界体验中,并非是排除一切世俗的苦痛而享受极乐,也并非是将苦乐皆归于虚无,而是不起苦乐分别的念想,没有“苦”也没有“乐”,不苦不乐、圆融无碍才是“禅”最高的乐境形态。“禅”审美体验之“乐”境界恰如王维诗云:“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36],显得异常静谧闲适,似乎没有任何情感的涟漪。唯有人消除分别智,与“境”冥合为一,让一切自在兴现,才能真正体会到“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圆融乐境。
“禅”审美乐境之“圆”还体现在它在成佛悟道的过程中以“圆”为轨迹的境界超越上。在佛道修行上,慧能所创立的禅宗(南宗)是以“本心”为支点,以“顿悟”为方法展开其精神境界提升过程的。在南禅宗看来,外在世界是虚妄不实的,一切佛道真谛皆在“心”中:“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37]47,因此,向“涅槃”乐境修行的关键就在于从被凡俗声色迷惑的“妄心”回归清净自然的“本心”。但禅宗相信“世人性本清净”[37]115,“妄心”和“本心”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故而,禅宗向“涅槃”境界的修行过程就是“心-悟-心”的圆形过程,前一个“心”是处于“迷”状态的“妄心”,后一个“心”是顿悟之后的“本心”。当凡夫俗子以“妄心”观世事,并不知何为真正的“苦”,也不知何为真正的“乐”,念悟成佛后,又进入不苦不乐没有苦乐分别的境界中,由此不难看出,“禅”之乐境演进过程也表现为“不知乐-悟-不知乐”的圆形轨迹。青原惟信禅师参禅的“三般见解”[38]很好地阐明了禅宗审美心境的圆形超越,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最后又回到“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山水是自然地兴现,改变的只是人的心境,表面上看修行的过程似乎是从原点出发再次回归原点,但实际上心境已经经历了从“凡”入“圣”再从“圣”入“凡”的圆形超越。
四、 结语:“乐”与“美感”
综上,“乐”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它与“美感”在美学意蕴上具有相通之处。所谓“美感”,“历来有广狭二义:广义泛指人的整个审美心理活动,包括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审美领悟和审美愉悦各个阶段在内,代表着审美体验的全过程;狭义则专指审美愉悦”[39]。劳承万教授曾用“乐(yuè)学”概括中国心性艺术哲学,他认为,中国只有“乐(yuè)学”而没有西方所谓的“美学”,唯有“乐(yuè)学”才能体现中华文化体系的特质——“礼—乐(yuè)”精神[40]。在此基础上,笔者也倾向于认为,“乐”比“美感”更适用于描述中国古代的审美活动中客观对象所带给主体的具有审美意义的体验本身。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中曾主要从审美直觉论、心理距离观和审美移情说三个方面分析了“美感经验”的理论内容[41],祁志祥教授也认为,美感活动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愉快性、直觉性和反应性[42]。不可否认,上述“美感”的美学特征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观念,但却无法凸显中国传统审美体验观念的独特性。因为,从总体来看,中国传统的审美体验观念具有节奏化表现、身体化感知和内在化超越的特征,它在“乐”这一重要审美体验范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些特征都是“美感”所无法全面展现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乐”范畴成为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的重要范畴,并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注释:
①参见吴建民的《“味”:古代审美体验的基本方式》一文,原文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②参见张猛的《“兴会”的多重建构及其理论特征研究》一文,原文载《绥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③参见毛金凤的《“悟”:中华民族审美体验中的一把金钥匙》一文,原文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④可参见李斯斌的《“梦游”之古典美学特征探析》(原文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张晶的《审美物化论》(原文载《求是学刊》2004年第3期),李根的《涵泳: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视域下的审美体验思想》(原文载《嘉兴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等文章。
⑤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中,收录了“乐”的五个读音:五角切(yuè)、卢各切(lè)、五教切(yào)、力角切(luò)、力照切(liáo)。本文中所有出现的“乐”若无特別说明,均读作“卢各切(lè)”。
⑥关于“樂”的造字本义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第一,认为“乐”源于“乐(yuè)”,“樂”的造字本义为“五音八声总名”;第二,认为“乐(yuè)”源于“乐”,“樂”的初始字义为“喜乐”;第三,认为“樂”造字之初的取义另有其它,“五音八声总名”之义与“喜乐”之义皆是“樂”的引申义。
[参考文献]
[1]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77-78.
[2]陈伯海.走向“体验美学”[J].江海学刊,2021(1):28-34.
[3]皮朝綱.中国美学体系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8.
[4]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13.
[5]邵晋涵,撰.尔雅正义[M].李嘉翼,祝鸿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35.
[6]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723.
[7]刘成纪.中国社会早期“乐”概念的三大问题[J].河北学刊,2016(4):84-90.
[8]张法.乐:中国美感的起源、定型、特色[J].山东社会科学,2020(5):85-90.
[9][汉]孔安国,传.尚书正义[M].[唐]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06.
[10]叶朗.中华美学文库:秦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2]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5.
[13][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
[14]叶朗.中华美学文库:魏晋南北朝卷(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92.
[15]冯晓林.历代画论经典导读:(学术版)[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95.
[16][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
[17][汉]许慎.说文解字注[M].[清]段玉裁,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18]李梦阳.空同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471.
[19]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0][清]吴楚材,[清]吴调侯.古文观止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09.
[2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
[22][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107.
[23]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06.
[24]二十二子: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96.
[25]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83.
[26]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7]张灿玾.黄帝内经素问校释[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70.
[28]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41.
[29]阮籍.阮籍集校注[M].陈伯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170-171.
[30]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6:250.
[3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3]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一章[M].[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1.
[34]成唯识论校释:卷十[M].[唐]玄奘,译;韩廷傑,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688.
[35]石峻,楼宇烈.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6]张勇.王维诗全集:汇校汇注汇评[M].武汉:崇文书局,2017:346.
[37][唐]惠能.坛经[M].丁福保,笺注;哈磊,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38][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卷第十七[M].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1135.
[39]陈伯海.审美体验与审美超越[M].北京:三联书店,2012:103.
[40]劳承万.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9.
[4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46.
[42]祁志祥.乐感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55-471.
(责任编辑文格)
“Le”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Aesthetic Experience
GAO Yue, HUANG Nian-r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Hubei,China)
Abstract:“Le”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category of aesthetic experientialism in ancient China.Its aesthetic implications are threefold: “le”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aesthetic pleasure of the subject in the aesthetic process; “le”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to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triggered by artistic creation or aesthetic activities represented by ancient Chinese poetry,music and dance; “le”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transcendent spiritual experience of the aesthetic subject at the advanced stage of aesthetic experiential activity.As an aesthetic experience,“le”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ctivities,and is presented as the “le” of “body”,the “le” of “heart”,and the “le” of “fugue”.In terms of the transcendence contained in its aesthetic experience,“Le” is mainly presented as the Confucian “le” realm with “He” as the purpose,the Taoist “le” realm with “miao” as the purpose,and the “le” of Zen realm with “yuan” as the purpose.“Le” is more suitable than “aesthetical feeling” to describe the hierarchy and transcendence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ctivities in ancient China,as well as the unremitting pursuit of aesthetic realm,so it has distinct national culture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le”; aesthetic experience; aesthetic implication; aesthetic level; realm 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