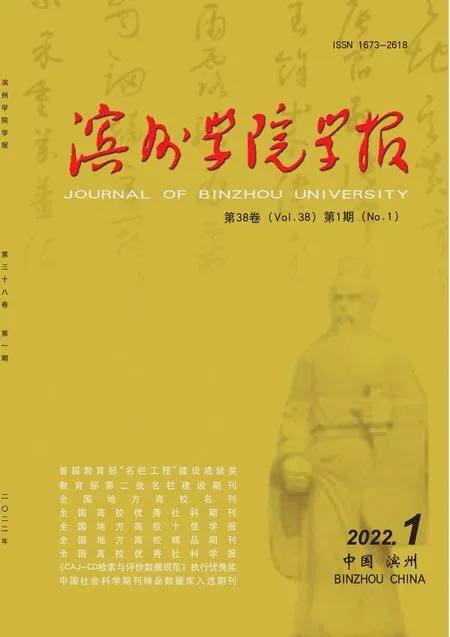清代民国两家《补宋书·艺文志》考
姜亚男,顾乃武
(1.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2.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1 )
正史《艺文志》是我们了解一代艺文名家名作的基本文献。但我国正史二十四史中专为艺文志编写目录的,仅有《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六种。自清代补艺文志之风兴起至民国时期,正史的《艺文志》基本补齐,其中有王、聂两家《补宋书·艺文志》(简称“两家《志》”)。学界已对各类补史《艺文志》的优劣进行过比较研究[1],对某些补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也做出过集解[2]或勘误[3],但尚未对两家《志》进行必要的讨论。事实上,两家《志》在著录体例、收书部目卷额、类目设置、著录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比较研究的空间。
一、两家《志》的著录概要
《宋书》是南朝梁沈约编纂的纪传体史书,所载诸志中独缺传统的《艺文志》一目。后世学者补《宋书·艺文志》之阙的,当以清人褚德彝为最早。褚德彝(1871-1942),字礼堂,浙江余杭人,其出身书香世家,精于篆刻学和金石学[4]219。褚氏对《宋书·艺文志》的补录不载于文,仅在王仁俊《籀鄦簃杂著》中记有“余杭褚德彝学,吴县王仁俊补”[5]3,可推断其补志时间大抵是在清光绪年间。褚氏补志研究到何种程度、因何而止,我们无从知晓,幸而清人王仁俊在褚氏补志工作的基础上加以增补,才不至于让其成果付之东流。
王仁俊(1866-1913),字捍郑,号籀许,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以经史、金石、考据及目录之学著称[4]219。王氏自幼嗜好“搜辑奇书”,于光绪十四年(1888)至二十年(1894)间撰《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6],书中辑录了唐以前佚书227种,则其对《宋书·艺文志》的增补(简称“王《志》”)也应在此前后进行。今通行本以北图所藏的王仁俊《籀鄦簃杂著》稿本为底本整理而成的,现收录入《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
到民国时期,学者聂崇岐(1903-1962)在其师陈援庵的授意下,开展了对《宋书·艺文志》的增补工作(简称“聂《志》”)。据聂《志》序所记,此本《补宋书·艺文志》撰成于1935年,次年即收入了《二十五史补编》[7],由上海开明书店刊印发行,后又多次影印出版。今通行本即以上海开明书店印本为底本,勘误整理后收入《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中。
二、两家《志》存在的差异
以增补褚氏目录而成书的王《志》、与30年后成书的聂《志》之间存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两家《志》著录体例的差异,表现为著录的著者、卷数、书目依据的不同;二是两家《志》收书的部目卷额不同,聂《志》较王《志》多著录典籍446部,共计3862卷;三是两家《志》的类目设置不同,聂《志》较王《志》多设置18个类目;四是两家《志》著录的具体内容不同,主要体现在对同本书书名著录、对著书著者断定上的差别。
(一)著书体例的差异
王《志》的著录以著者名标目,著者名前冠以官名,次列书名与卷数,再次以小注字列书目依据,如开篇在经部《易》类录入“东阳太守卞伯玉,注系辞二卷(原注:《七录》)”[5]3;若有一书记于两处、且所记卷数不同的,则并以小注字指出,如在经部《总经》类录入“雷氏五经要义五卷(原注:《隋志》。《七录》十七卷)”[5]6。
与王《志》不同,聂《志》的著录以书名标目,次以小注字列卷数和书目依据,再次列撰者名或注者名,标明“某某撰”或“某某注”,如开篇在经部《易》类录入“周易系辞注(原注:二卷)卞伯玉注”[5]18;若有一书记于两处、且所记卷数不同的,同样以小注字指出,如在经部《易》类录入“周易义疏(原注:十九卷。两《唐志》作二十卷)明帝(原注:集群臣讲)”[5]18;若遇有著录书籍不知卷数,又或是为《隋书》、两《唐志》遗录的著作,则特以小字注明“见某书某著”,如在经部《诗》类录入“毛诗序义(原注:不知卷数。见《释文序录》)”[5]19。
两家《志》除了在著录体例的前后次序上有细微差异外,王《志》相较聂《志》而言,在著者名前多著录了官名。
(二)收书部目卷额的差异
两家《志》在收书部目卷额上有较大的差别。王《志》在经部收书60部、585卷,其中7部不知卷数;史部收书98部、1592卷,其中7部不知卷数;子部收书28部、304卷,其中2部不知卷数;集部收书25部、270卷,其中1部不知卷数;书后附收书3部、10卷。王《志》各部共收录著作214部、2761卷,17部不知卷数。
聂《志》在经部收书74部、714卷、40余条义、21部琴曲,其中8部不知卷数;史部收书114部、1721卷,其中18部不知卷数;子部收书60部、486卷,其中5部不知卷数;集部收书241部、3214卷,其中5部不知卷数;书后附收书171部、427卷,其中4部不知卷数。聂《志》各部共收录著作660部、6623卷,其中41部不知卷数。
则聂《志》较王《志》多著录446部典籍,其中以集部增补典籍216部为最多,释典部次之,增补168部典籍;以集部著录卷目2944卷为最多,释典部次之,增补417卷。可见两家《志》在集部与释典部中的收书差距最大。
(三)类目设置的差异
两家《志》在收录古籍的分类设置上差别较大,为了更直观地进行对比,现将两书类目设置抄录如下:
经部:王《志》分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总经、小学十类,聂《志》分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小学九类。
史部:王《志》分史、仪注两类,聂《志》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杂传、地志、谱系、薄录十二类。
子部:王《志》记兵家一类,聂《志》分道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历数家、五行家、医方家九类。
集部:王《志》分楚辞、别集二类,聂《志》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
书后又王《志》记职官一类,聂《志》分释典一类。
王《志》共设十六类,而聂《志》的类目设置两倍于王《志》,共设三十四类。特别是王《志》在子部中虽按次序著录,但并未进行具体类目的设置,因此仅记《兵家》一类,聂《志》则依据《隋志》分设了九大类,可见差异之大。
(四)著录内容的差异
两家《志》在具体书目的著录内容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同本书的书名、著者的著录上,这些差异同样不可忽视。
如王《志》中常有著录书名为“注某某书”的,如其在经部《易》类著录“东阳太守卞伯玉,注系辞二卷(原注:《七录》)”“太中大夫徐爰,注系辞一卷(原注:《隋志》)”[5]3,收书有卞伯玉所撰《注系辞》、徐爰所撰《注系辞》;而聂《志》在经部《易》类著录、“周易系辞注(原注:二卷)卞伯玉注”“周易系辞注(原注:二卷)徐爰注”[5]18。尽管两家《志》依据了同一条史料,但却著录了不同书名。
再如王《志》在子部著录“徐叔向等四家,体疗杂病本草要钞十卷(原注:《七录》)”“又谈道述(原注:《七录》)”[5]11;而聂《志》在子部《医方家》类下著录“四家体疗杂病本草要钞(原注:十卷)徐叔向撰”“体疗杂病疾源(原注:三卷)徐叔向、谈道述、徐悦等撰”[5]30-31。两家《志》不仅著录的书名截然不同,连著书著者都存在差异。此类例子更是多不胜数。
三、两家《志》撰写差异的成因
两家《志》之所以在著录体例、收书部目卷额、类目设置、著录内容上有如此差异,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两家《志》著录所依据的书目不同,同时两位学者对著录依据的取舍又有所不同;二是两位学者对书籍分类的性质的认识不同,当然,收书数量的增加也对类目设置造成了影响;三是由于两位学者对史料的不同解读,同时两人对所著录书目的考证疏密程度也有差异。
(一)收书部目卷额差异的原因
两家《志》收书部目卷额有如此差距,首当归因于二《志》收录文献的著录依据的不同。
王《志》著录的文献主要来源于两类书目,一是《宋书》所载的纪、传,二是《隋书》、两《唐志》中所载文献。而聂《志》的著录依据,除上述王《志》所涉及的两类书目外,还包括有以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为代表的类书、总集、古注类所载书目;以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唐代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及《续藏经》等为代表的释家目录所载书目;《南史》《宋史》中纪、传所载书目;再加上以清人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中所增补书目。
尤为特别的是聂《志》中增设的对释典部的著录,这是王《志》所没有的。南北朝时期的佛学发展空前兴盛,大量释家著作的涌现成为南朝的时代特点,王俭在撰写《七志》时便在书后增补道经、佛经作为附志,《隋志》同样如此。聂《志》著录体例依照《隋志》,在补志时收录了大量的释家著作,成为造成两家《志》著录书目差别的一方面原因。
收书部目卷额的差异不单单是著录依据造成的,两位学者在著录古籍时对著录依据的取舍的不同,也是造成收书差异的原因之一。
单就著录的卷数来说,王《志》著录时以《隋志》所载卷数为先,当遇到两处所载“隋代”卷数与其下小注所载“梁有……”卷数或《宋书》不同时,则以隋代卷数为准,以小注字形式列出他书中的不同卷数。例如王《志》在经部录入“雷氏五经要义五卷(原注:《隋志》。《七录》‘十七卷’)”[5]6、在史部录入“徐广,晋纪四十五卷(原注:《隋志》。本传作‘四十六卷’)”[5]7,皆以《隋志》所载卷数为先。聂《志》在著录中遇到两处所载卷数不同时,则首选《七录》所载卷数,并以小注字形式列出他书中所见的不同卷数。
如此看来,两位学者所选取的著录依据不同造成了两家《志》在收书卷数上的差异,但仅就著录依据的取舍方面来讲,笔者更倾向于聂《志》的方式。客观来说,为《宋书》补志理应选取与刘宋一朝最相近的目录材料进行补足,以达到最大限度还原刘宋史志目录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聂《志》在材料的选取顺序上比王《志》更为可取。
(二)类目设置差异的原因
从类目设置上看,两家《志》在经部、集部中的差异较小,而在史部、子部中的差异较大。王《志》虽在逻辑上大体按四部分类编写,但并未明确分出四部以及四部下各类目,不过考虑到此本《志》是以王氏的《籀鄦簃杂著》稿本为底本而出版的,既是底稿,则可能是其在辑佚工作中即辑即写而成的,不能对格式与次序作过多的要求。
聂《志》的类目设置则按其序所云,以经、史、子、集四部次第著录,各部下的分类基本参照《隋志》的类目设置,又依据《开元释教录》体例在后附《释典》一部。聂氏以其严谨治学的基本素养补史志,以多部文献作为著录依据,这使得聂《志》的目录分类相对于王《志》而言更加精细。
收书数量的增多必然会使得分类设置更加细致,这不必多说,更应关注到的是各类目设置下,两家《志》对书籍分类性质的不同认识。如王《志》在史部著录“武康令沈怀远,南越志那八卷(原注:《隋志》)”[5]10,按其排列顺序,则归于地理目之下,聂《志》则在史部《杂史》类著录“南越志(原注:八卷。两《唐志》作五卷,‘沈氏’作‘沈怀远’)沈氏撰”。《南越志》一书实则记载上至三代下至东晋岭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奇闻异物、建置沿革等,内容广泛,归入地志类是较为妥当的。
又如,王《志》在经部《总经》类著录“孙畅之,五经杂义六卷(原注:《隋志》)”[5]6,聂《志》则在经部《论语》类著录“五经杂义(原注:六卷)孙畅之撰”[5]21。聂《志》应是参照了《隋志》的著录形制,“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论语)”[8]939,《旧唐志》则将此类书目归入《七经杂解》类[9]1983,《新唐志》将其类归入《经解》类[10]1446,可见两家《志》对《五经杂义》的著录皆可取。
尽管这种著录的例子不多,但两家《志》在对书籍性质上的不同认识,确实成为造成分类设置差异的原因之一。
(三)著录体例、内容差异的成因
两家《志》在具体书目的著录内容上,同样有较大差别,如上所提到的例子:王《志》在子部著录“徐叔向等四家,体疗杂病本草要钞十卷(原注:《七录》)”“又谈道述(原注:《七录》)”[5]11;而聂《志》在子部《医方家》类下著录“四家体疗杂病本草要钞(原注:十卷)徐叔向撰”“体疗杂病疾源(原注:三卷)徐叔向、谈道述、徐悦等撰”[5]30-31。两家《志》的著录依据皆为《隋志》所载“徐叔向等四家体疗杂病本草要钞十卷”“徐叔向、谈道述、徐悦体疗杂病疾源三卷”两条[8]1041-1042,按《隋志》中载有“李谠之本草经、谈道术本草经钞各一卷”[8]1040,可见“谈道术(述)”为人名,聂《志》的句读合情合理。此外,既谈道述、徐悦为徐叔向同时代之人,则《补宋书·艺文志》还应增补“本草经钞(一卷)谈道术撰”“龙衔素针经并孔穴虾蟆图(三卷)徐悦撰”两条。
又如,王《志》在经部录入“明帝,集周易义疏十九卷(原注:《隋志》)。又国子讲易议六卷(原注:《七录》)”[5]3;而聂《志》在经部《易》类录入“周易义疏(原注:十九卷)明帝(原注:集群臣讲)”“国子讲易议(原注:六卷)明帝(原注:集群臣讲)”两条[5]18。两家《志》的著录依据皆为《隋志》所载“周易义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讲;梁又有国子讲易议六卷,宋明帝集群臣讲;易义疏二十卷”条[8]911。按《隋志》所载,除以上二书外,还有“宋明帝集群臣讲,易义疏二十卷”,则《补宋书·艺文志》还应在经部易类增补“周易义疏(二十卷)明帝(集群臣讲)”一条。
可见,两位学者对史料的不同解读是造成收书分歧和具体著录内容差异的主要原因。
四、两家《志》编纂的优缺点
两家《补宋书·艺文志》对刘宋人的书目按部类罗列,不仅反映了刘宋一代的图书著录情况,而且为后世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如赵静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琅琊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11]、张嫚的硕士论文《补魏晋南北朝史〈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12],都是以聂《志》著录小说为对象而展开讨论。两家《志》的编纂各有优点,同时也存在着些许不足。
(一)两家《志》的编纂优点
王《志》著录的最大优点即在著者名前加其官名,这使后世学者在利用王《志》对照检索书目时更加方便,聂氏在进行补志工作时或多或少也受益于此。王《志》的这种著录形式也为以后《宋书·艺文志》补遗工作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便利。在为收录图书归纳类目时,王氏对书籍分类性质的认识多加考量,有自己的见解,如前所提到的沈怀远《南越志》的分类等。
聂《志》最大的优点则体现在收录依据的扩充上。通过收录《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续藏经》等释家目录所载书目,所增补的释家著作多达171部、427卷,同时所增设的释典部,使《补宋书·艺文志》的内容更加完善,也更具有时代特点。
从著录内容上来看,后成书的聂《志》对王《志》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勘误、增补作用。如王《志》在经部《易》类著录“太中大夫宋蹇,注系辞二卷(原注:《隋志》)”[5]3。按今见《隋志》记载:“周易系辞二卷,梁太中大夫宋褰注”条[8]910,《周易系辞注》著者为南朝梁太中大夫宋褰,非王《志》所载的、系于南朝宋的“宋蹇”。此书实为王《志》误收,聂《志》则未做收录。
又如,聂《志》在经部《易》类录入“难顾悦之易义(原注:不知卷数,见《宋书》九十三。)关康之撰”[5]18。按《宋书》“晋陵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条[13]2296,东晋顾悦之为问难王弼《易》义,撰《难王弼易义》,刘宋关康之则“申王难顾”,据上书撰《难顾悦之易义》。王《志》则未做收录,聂《志》则加以收录。
(二)两家《志》的编纂缺点
王《志》编纂的不足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著录书目卷数时,王《志》以《隋志》所载卷数为首要著录依据,而理论上当遇到不同著录依据所载卷数相异时,应以编纂时代先后作为选取著录依据的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接近《宋书·艺文志》的目的。二是在收录图书时,王《志》忽视了正史中纪、传所载书目,如此在进行补志工作时便多有遗漏。三是王氏在解读史料时,不免有讹误之处,如王《志》在子部《兵家》类录入“武康令沈怀远文集(原注:《沈怀文传》)”[5]12。按《宋书》“(弟怀远)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怀文文集,并传于世”条[13]2105,沈怀远所为其兄沈怀文撰写文集,文集名应为“沈怀文文集”,但由于王氏对史料的误读,造成王《志》误收。
聂《志》虽对王《志》多有增补,但本身也有许多错漏和值得商榷之处。如聂《志》在经部《易》类录入“难王弼易义(原注:四十余条,见《宋书》九十三。)顾悦之撰”[5]18。按《晋书》有传,顾悦之为东晋晋陵无锡人,所撰《难王弼易义》一书为刘宋藏书,而非刘宋著书,聂《志》遵循记“一代所著”之书的收录原则,则此书应为聂《志》误收。这类考证不精而造成的收书错误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
不过从整体来看,聂《志》相较于王《志》而言,类目设置更详细、著录依据更丰富、考证材料更合理。当然,即使是后成书的聂《志》也有许多错漏之处,不仅刘宋一代,中国古代各时代的史志目录,也都尚待学界做进一步的增补完善,就如聂氏在序中所言:“然刘氏七主,享国几六十年,其间著述,固当不止此数。拾遗补阙,是仍有待于世之博雅君子焉”[5]17。
两家《补宋书·艺文志》在著录体例、收书部目卷额、类目设置、著录内容上存在种种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受到了历史客观因素的影响,如补志时可用著录依据的多少、选取著录文献范围的广狭;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两位学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他们对著录依据的取舍、对史料的解读、对书目考证的深浅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王、聂两位学者对刘宋时代典籍的梳理与学术考证,不仅向后世展现了刘宋一代的典籍著录情况,也让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尽管两家《志》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讹误,但在对后世研究一朝的艺文名家名作上、在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需求上,两家《志》的出现、补史志目录工作的开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学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