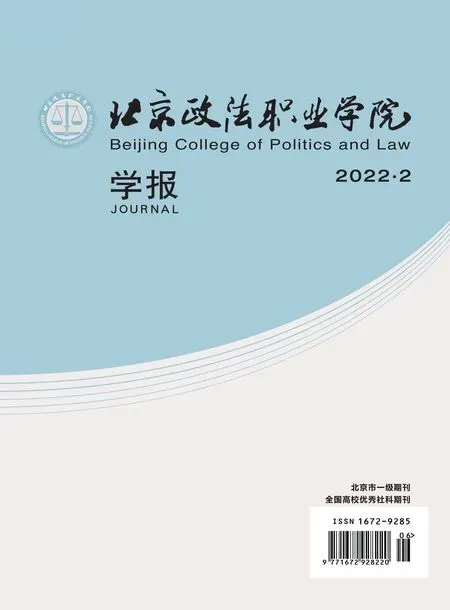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与比较法[1]
约阿西姆·赫尔曼著 颜九红译
对于造访罗马的学者而言,参观梵蒂冈博物馆无疑就是高光时刻。从教皇宫到西斯廷礼拜堂,人们将会经过署名厅,以前这里是教皇的私人起居室。在署名厅的一整面墙壁上,便可看到拉斐尔的绝世名作《雅典学院》。著名画家拉斐尔大约在500年前绘制完成了这部超过22英尺宽的湿壁画。尽管拉斐尔以细腻柔美的圣母画作著称于世,但《雅典学院》这幅巨作则成就了拉斐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4]在拉斐尔的时代,流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思潮。这一思潮主张美是不生不灭的永恒,并在艺术中追求理想美的创造。人文主义大师在艺术创造中,更重视对生活美的发现,他们在艺术中描绘的一切美,都是那样具有现实美感。信徒的美誉。在这幅湿壁画中,拉斐尔将过去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神学家以及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以可甄别出“谁是谁”的精美生动特征,绘制在一起。拉斐尔把这些学者[5]拉斐尔聪慧地把不同历史时代中的不同人物,分别按其独有的思想特点,以最易让人理解、感知的方法绘制出来。分为不同的群组,分列在想象中的学术殿宇台阶之上。在画作的中央是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位列左侧的是柏拉图,位列右侧的是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哲学家被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著名人物环绕,这些人物堪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创建的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学派的追随者。对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不同信奉,彰显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如何影响人类以后不同世代的思维生活。本文旨在揭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怎样对当代的法律理论产生影响。
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思维范式
在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中,柏拉图抬起他的右手指向天空。通过这一手势,柏拉图关注的是形而上学的理念世界。柏拉图在其著名的“洞穴之喻”[6]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作了一个比喻: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有微弱的阳光从通道里照进来。有一些囚徒从小就住在洞穴中,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朝前看着洞穴后壁。在他们背后的上方,远远燃烧着一个火炬。在火炬和人的中间有一条隆起的道路,同时有一堵低墙。在这堵墙的后面,向着火光的地方,又有些别的人。他们手中拿着各色各样的假人或假兽,把它们高举过墙,让他们做出动作,这些人时而交谈,时而又不做声。于是,这些囚徒只能看见投射在他们面前的墙壁上的影像。他们将会把这些影像当作真实的东西,他们也会将回声当成影像所说的话。此时,假如有一个囚徒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起来,可以转头环视,他现在就可以看见事物本身了,但他们却以为他现在看到的是非本质的梦幻,最初看见的影像才是真实的。假如有人把他从洞穴中带出来,走到阳光下面,他将会因为光线的刺激而觉得眼前金星乱蹦,以至什么也看不见。他就会痛恨那个把他带到阳光之下的人,因为此人使他看不见真实事物,而且给他带来了痛苦。中认为,真实世界中的事物来来去去,它们不过是这些事物之永恒理念的不完美反映。永恒的真理乃是事物本质理念,而人类通过内赋之理性的帮助,能够认知这些理念并运用这些理念来指导他们的行动。与柏拉图并肩而立的亚里士多德,则将他的手放平,平向指向大地。亚里士多德曾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后来就如很多优秀学生那样离开他的老师。可以说亚里士多德颠覆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并不独立于真实世界中之事物而存在。与他的老师相反,亚里士多德笃信理念仅仅是人们在看见真实世界中的个体事物以后形成的一般概念而已。如果说柏拉图张开双眼仰望理念的天堂,那么亚里士多德则关注大地上的真实世界。因此亚里士多德将他的兴趣拓展到可以发见的真实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并从未停止对事物予以蒐集、归类。在柏拉图的纯粹唯心主义哲学中,我们看到的真实世界中的事物仅仅是永恒的理念在先验世界中的微弱反映。这必然意味着实定法也仅仅是正义理念的微弱反映。与之相对,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念仅仅是真实世界之事物的单纯反映,因此实定法与正义理念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法与正义的不同思维范式,对于世界不同地区的法律思维已经影响了两千余年。因此,《雅典学院》绘制的两位伟大哲学家的不同手势可以为比较法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简而言之,可以说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思维范式对于欧陆各国的法律理论产生影响,而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思维范式则对盎格鲁——美利坚的法律领域产生了支配性影响。至于现代日本法,则处于上述两大法系之间的折衷地带,自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年间日本法首先受到欧陆法律的重要影响,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法则深受美国法律的影响。
二、西方两大法系与日本法
(一)欧陆法系
17世纪以前,欧洲法哲学曾将法律与基督教道德观结合在一起。但17世纪以后,这一传统法哲学被新的理性法律观所取代。随着新的理性人类的认识论代替了神启论,法学理论便从道德神学之束缚之下被解放出来。这一哲学上的“大爆炸”所产生的辐射作用,仍可以从1811年制定的、现在依然有效的《奥地利民法典》中发见端倪。《奥地利民法典》在开篇中的一款写到:“每个人均生来就因理性而获得天赋的权利,因此必须把人当作人来对待。”崭新的理性背景成为处理法律问题的基础,法律问题的处理应严格遵循科学路径。理性人的唯心图景,辅以逻辑推理,成就了“自然法”体系。这一新的法学理论自具体条文开始,随后发展为一般规则和原则。与此同时,新的政治理念被整合入这些法律制度之中。由此,欧陆国家制定了包含抽象的概念和总则部分的综合性的民法典。
(二)盎格鲁-美利坚法系
在盎格鲁-美利坚世界,法学理论一直崇尚实用和实际,很像亚里士多德手势的寓意。往昔,普通法几乎全部是判例法。但今天,普通法已成为判例法和各种制定法的结合体,但法律分析仍首先以判例为中心。只要看看英国和美国法院的判决,就可以发现,英美法官的习惯做法是引用判例而非制定法的规定。从一个判例到另一个判例的推理,是通过在普通法法庭的庭审中进行的激辩而发展的,与此相对,欧陆法的发展路径,则是通过学者的沉潜研究而对法律文本进行原则为导向的体系性解释。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美国和英国的法律工作者倾向于保证其解决方案能与既有的判例链条相契合。与欧陆法律同行不同,英美法律工作者不习惯于首先追问其解决方案是否与其法律制度的一般理念及价值观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当欧陆国家的法官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判决此案”时,英国和美国的法官提出的问题则是“上一次我们怎样判决此类案件的”美国著名法官、法哲学家奥利佛·万德尔·霍尔姆斯曾经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霍尔姆斯所指的法律是指全部法而非专指普通法。霍尔姆斯显然站在典型的实用主义立场,即亚里士多德的立场,而没有考虑欧陆法律的重要发展。这里只需略举几例欧陆体系性、逻辑性法典,诸如6世纪中期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查士丁尼法典》,还有诸如19世纪从拿破仑五大法典开始随后逐步风行欧陆各国的法典化浪潮。
如果阅读美国的制定法文本,也可以看出其以判例为导向的实用主义法律思维进路。与欧陆各国的立法不同,美国的制定法通常缺乏体系性结构,其依赖的是辩论详情而非一般的、抽象的概念。尽管《加利福尼亚州民事法典》或许可能不是以上论点的最典型法例,因为在相当程度上《加利福尼亚民事法典》的立法基础是戴维·D.菲尔德的研究成果和欧陆民事法律思维,但是,加利福尼亚州刊行的一篇法律评论似可以恰当说明这部法典的一系列条款确属于普通法系国家立法的典型的辩论详情模式。在该法典“人身权利”一章中,在规定了概括性条款之后,又规定了胚胎的权利、母亲在任何场所均可哺乳自己婴儿的权利、对因虚假的结婚许诺而造成的损害不予赔偿。这一系列规定更像是典型的无体系性普通法立法进路。另一个立法例更加引人注目,那就是两大法系在刑事法典中对正当防卫条款规定存在明显的差异。德国刑法典仅规定正当防卫系“为了使本人或他人免受迫急的非法侵袭时所需要的防卫。”其他则留给法官去判断,法官需要依据此前法院的类似判决做出的一般性解释规则以及在法律文本之中找寻到的解释,来做出其判决。与此不同,美国刑事法典则采取典型的实用主义进路,一般来说,其关于正当防卫的界定得有好几页,简直可以说判例法的荟萃。譬如,美国刑事法典关于正当防卫的类型就分得很细,有防卫本人受到的袭击、防卫第三人受到的袭击、防卫对物的侵袭。法典还进一步详细规定,针对何种类型的侵袭者可以使用何种类型的暴力,而侵袭者又进一步分为持武器的侵袭者和未持武器的侵袭者。还规定对于侵权者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暴力,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侵害人在反击不法侵害时可以使用致命暴力。
(三)日本法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慢慢向西方法律开放,开启社会现代化,开放国际市场。起先,日本法律以法国法和19世纪初叶拿破仑法典作为蓝本制定法律。后来,1871年德国各邦统一以后,在19世纪末德国迎来法典化浪潮,于是日本遂转以当时最新的德国法典作为蓝本修改其法律。1908年日本刑法典和1924年日本刑事诉讼法典,均以德国法作为主要参照文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美国影响,日本法以美国法为蓝本进行改革,首当其冲的改革领域就是刑事司法制度。
尽管日本法在1945年后以美国法为蓝本进行过改革,但是今天欧陆法律人仍能感到日本法与欧陆法的趋同。这是因为日本法典文本,即使是修改过的刑事诉讼法典,所使用的概念和体系都带有典型的欧陆法典特性。当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日本法是否受到欧陆法律传统的影响、在什么程度上受到这一影响。与日本法律人对话时常常发现,日本在进行法律问题分析时,常倾向于采取比西方世界更谨慎、更微小的步骤。日本法律人往往或多或少地对模糊概念情有独钟,而对于这些概念,西方法律同行则常常能够提供清晰、准确的界定。由此观之,柏拉图的手势对于日本法律理论影响有限,而日本法律理论自有其哲学根基。
三、比较法乃深入理解各国法律的基石
通过以上的一般性介绍,以下两个事例可以用来阐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手势在理解各国法所采取的不同思维进路时,仍然富有启迪性。
(一)个人权利的哲学底蕴
1.德国。德国基本法开宗明义,在第一条明文规定了两大最重要的人权: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以及自由发展个性的人权。这两大人权所代表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均可回溯到启蒙时代、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基督教教义,所有这些都令人想起柏拉图指向天空的手势。在这两个最重要的人权之后,德国基本法还依次列举了一系列具体人权,即使这样,这些人权名单也远远不够周详。为了填补这一缝隙,德国法院和其他机构,尤其是德国宪法法院,倾向于将“人的尊严”和“自由发展个性的人权”的立法条款做宽泛的、富有魄力的解释。以秉持无处不适用人权保障条款的理念为出发点,这些人权保障条款已经成为一般性的安全伞条款。
2.美国。美国采取的进路属于普通法国家的典型做法,最早的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对公民人权的保护,并不使用一般性的、具有哲学抽象性的概念,例如人的尊严、发展个性的个人自由等等。对人权的保护,则是以一份详尽的具体人权名录为基础的,例如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持有枪支的权利、以及刑事司法领域(administr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的一系列权利。这种权利规定模式采取的是亚里士多德脚踏实地式务实性哲学思想,而不是柏拉图仰望星空式的形而上哲学思想。当然,坦率而言,美国联邦宪法理论也有柏拉图式哲学思想的影子。譬如,美国立国先父们就是天赋人权概念的忠实追随者,但这种哲学思想,在美国宪法文本的字里行间却难觅其踪,也未主导美国宪法的法律理论。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却是一个例外。其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都不得受到剥夺。这一条与德国基本法所规定的保护人的尊严以及公民个性的自由发展权利,可谓殊途同归。经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努力,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范围被大大地拓展了。但与德国基本法所规定的权利保护条款不同的则是,正当程序条款首先指向程序性权利,并继而通过程序性机制的护佑,来保护实体性价值。
3.日本。日本宪法规定的人权名单很长,其参照模本是美国联邦宪法,但比美国联邦宪法更全。由于日本宪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946年制定的,而德国基本法是在其后制定的,因此日本宪法中没有德国人权理念的影响。日本宪法规定的人权有一项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这项人权显然以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一个条款作模本。尽管这一项人权并未列入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但日本却将其作为保障人权的基石。日本法官和学者将公民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与“尊重人之为人”的权利这两项基本人权,作为兜底条款,在所有那些无法适用日本宪法规定的具体人权条款的案件中,仍然可以适用公民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或者“尊重人之为人”的权利来保障人权。另外,在这两项基本人权之下,又引申出隐私权保护和环境保护,其适用范围也至为广泛。由是观之,日本人权保障哲学理念的扩展,与德国和美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在刑事审判中追寻真相
刑事审判的庭审模式主要有纠问式和抗辩式两种模式。在德国和其他欧陆国家采取的纠问式庭审中,对被告人和证人的询问,是由法官进行的,调取与案件审理有关的一切证据,也是由法官进行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可以进行补充性提问,也可以提出其见解,他们的角色具有补充性、辅助性。至于说纠问式庭审背后的理念,则是负责做出最后裁决的法官最了解什么样的证据最能实现裁判目的。众所周知,在美国以及其他普通法国家,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角色则大相径庭。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展示各自的证据,虽然某些情况下法官也有权要求调取更多证据,但相对而言,普通法法官在庭审中的作用具有消极性,正如一位英国法官所言“在庭审中,法官仅需安坐听审和思考”,这是普通法国家庭审的大背景。在德国,常有学者对抗辩制庭审模式提出强烈批评,他们认为,刑事审判的主要目的乃是去“发现真相”。如果将证据的调查权交给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则要达到“发现真相”的目的,要么不可能,要么问题丛丛。因为,控辩双方对于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并不负责,检察官就与法官不同,检察官不可能总是秉持客观中正的立场,检察官的职责就是如何寻求对被告人定罪。尽管有这些批评意见,但毫无疑问,抗辩式庭审模式追求的目的也是“发现真相”,抗辩式在判定被告人有罪时采用的超越任何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是对“发现真相”的清晰而务实的表述,只是其表述并不围绕“发现真相”本身做太多理论讨论而已,而这正是普通法的典型思维进路。如果那些对抗辩制持批评意见的德国学者去观察日本的刑事司法,他们将会看到“发现真相”原则与抗辩制是怎样紧密结合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美国法的影响下,以抗辩制代替了此前采用的具有德国特色的纠问制。与此同时,日本明确宣称其刑事庭审持守“发现真相”原则。由此可见,更多地立足于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主义而非柏拉图的理论帝国,或许有助于那些对抗辩制持批评意见的德国学者纠正其固有执见。
当下,全球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比较法的重要性因之愈益凸显。不同国家之间,各种交往日益频繁而紧密,纷纷呼唤确立新的法律,以便适应这一需求。以欧盟为例,欧盟法已形成为居于欧盟各成员国法律之上的一种新的法律位阶。来自不同国家的公民个人、公司企业之间,商业往来日趋频仍,跨境贸易不断增长,尤其是伴随着大量传统贸易订单转移到线上成交,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需求亦在不断地增长,亟需法律制度创新,以便适应迅捷而灵便的商贸往来的迫切需求。值此之际,我们更应常记两位伟大哲学家的手势,进一步探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远见卓识,怎样对当下的法律创新发展产生持续性影响。这样的法律创新设计,必须与相关各国的法律制度均可契合。为此目的,这些法律创新设计,应主要侧重实务操作性和法律技术性设计,包含很多详细而具体的条款。当然,除了进行亚里士多德式偏重实务性具体详细条款的法律设计之外,柏拉图式偏重理论和原则的体系性思维进路也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契合频繁跨境交往之需的法律设计,不仅应当具有完美的内在丰富性,而且应当具有充足的逻辑延展力,在琐细技术性条款堆叠之外,还需要确立那些能够满足各国人们交互活动所需的一系列基本法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