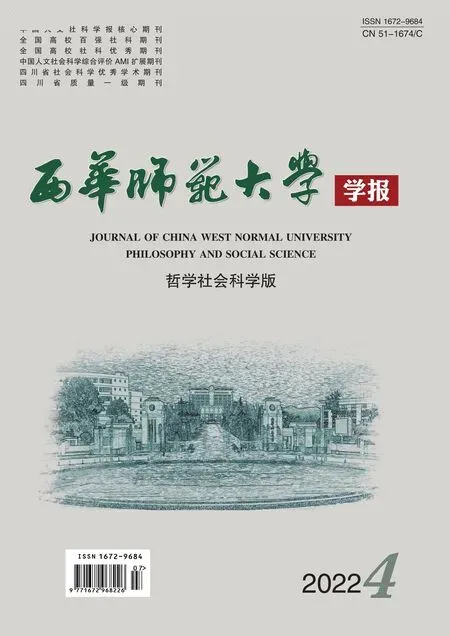论古代小说文学地图元素
——空间距离
张袁月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随着近年来学界对文学空间维度的不断强化,文学地图继文学地域、文学地理之后,成为研究文学的又一重要空间视角[1]。文学地图是将文学要素转化为地图形式以分析文学现象的空间批评方法,其优势在于通过可视形式呈现与揭示隐性的文学、文化信息。目前常见作法是利用文学地图的空间区域以研究文学地理分布,而文学地图的空间元素如地名、距离、路线等则很少被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在古代小说中,人物须在不同地理空间中活动以推进情节发展,会出现至少两个地点,因而小说天然地包含距离这一文学地图元素。但在注重人物情节的传统分析模式下,小说的地理信息很容易被忽略。事实上,古代小说文学地图的空间距离,不仅具有特定的文学功能,还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探析古代小说叙事策略、时代特征等具有独特价值。
一、标示方式:显性距离与隐性距离
古代小说对距离的标示方式可分为三种:一是用数字标示距离;二是用时间感知距离;三是用远近来反映距离。如《西游记》介绍黑熊怪时说“这观音院正南二十里远近,有座黑风山”[2]199,属于第一种标示方式;《金瓶梅词话》写西门庆上东京祝寿,“自山东来到东京,也有半个月日路程”[3]719,属于第二种;《雪月梅》写王进士“家在碧浪湖村居住,离府不远”[4]12,则为第三种标示方式。这三种形式在表示距离上有具体和概略之分,但都有距离词,均可转换为地图。用数字表示距离是转换为地图的最直接方式;以月、日等时间单位来表示距离,一般用于对路程的描述,由于古代车马每日的行走路程有一定上限,因此也可转换为空间距离;用“远”“近”“不远”等词表示两地距离,虽无法确定精确位置,但也可在地图上进行示意性注记。因此,它们都可归为“显性距离”。
古代小说受史传传统影响深远,即使小说人物为虚构,地点却往往为实有,故显性距离可用于考证小说的作者、成书等。如王辉斌据唐律计算,认为《西游记》中唐僧从长安行“一二日”[2]154到法门寺、“三日”[2]155至河州卫、不足一个月却行“五千余里”[2]193等,在实际地理距离中都无法完成,由此判断小说作者唐代地理知识的缺乏,进而推测《西游记》不大可能是吴承恩这样博学多才的文人所作[5]141-143。再如,阎增山据《金瓶梅词话》中提到一日约行七十里的路程计算,清河到东京(明代北京)应相距一千余里,即小说中所说的“半个月日路程”[3]719,按此距离,则《金瓶梅词话》中的清河应在东平府附近,而非广平府的清河县,这样与小说中关于清河到兖州、枣强等地的距离描写也能对应相符[6]249-263。此外,孙楷第根据《醒世姻缘传》中关于绣江县“离府城一百一十里路”[7]339的描写,考证小说中的绣江县在今章丘[8]1501;纪德君通过《水浒传》中方位距离与实际地理的出入,发现《水浒传》“聚合式”的成书方式[9]等,都是基于文本距离与地理距离的对应关系来加以论证。
除了显性距离,还有一种距离值得注意,这就是“隐性距离”。隐性距离是指文本中未出现距离词,但涉及地点的地名真实可考,则可通过在地图上注记地名,显示两地距离。由于隐性距离未在文本中直接标示,在地图上才显示出两地距离,故这种形式尤能体现地图的视觉化优势。
自唐代起,小说作者已利用地名、距离等空间元素来建构叙事。但历史地理学者多着眼于唐传奇对长安里坊空间真实准确的书写,将其作为一种特别的史料,借以还原唐长安城的地理格局,从文学角度深入探讨长安里坊空间意义的,只有妹尾达彦[10]509-553、朱玉麒[11]85-128等少数学者。不过,他们仍更多强调地理空间转换的隐喻性意义。例如,妹尾达彦认为《李娃传》中荥阳生从街西布政坊到街东平康坊,意味着主人公进入繁华区,并开始迷失,而耗尽钱财后故事空间转移到街西凶肆,意味着主人公的堕落[10]509-553。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唐传奇中的里坊转换为文学地图,就会发现不仅里坊地名可能包含特别的空间意义,里坊之间的距离也常具有特定的文学功能。《李娃传》中有一处不引人注意却颇具意味的情节是,李娃在询问荥阳生的住处时,荥阳生并未回答布政里,而是谎称在“在延平门外数里”[12]184。如果从空间的隐喻意义来分析,则殊不可解,因为延平门显然看不出有何深刻寓意。但如果将其转换为地图,那么里坊城门之间的距离却能揭示答案:布政里与平康里距离并不算远,而延平门与平康里距离则远得多,“在延平门外数里”更拉长了两地距离。这样,荥阳生就无法在坊门关闭前返回,方可自然地留宿,后文中荥阳生在李娃宅耗空钱财也才有了合理前提。可以说,距离成为小说建构情节逻辑的一种特别手段,并且在唐传奇中运用相当普遍[13]。
后来的明清小说也经常利用距离来推动叙事。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即深谙此法。冯梦龙所作“三言”中有不少故事改编自前代小说,改作与原作之间的变化恰可清晰反映出作者如何利用距离设置来链接情节逻辑,强化叙事主题。
例如,《喻世明言·吴保安弃家赎友》是对唐传奇《吴保安》的改编,在主要情节上并无太大改动,却通过添置若干细节,将唐传奇中处于隐性层面的距离叙事以显性方式凸显出来。在《吴保安》中,小说仅交代了因仲翔伯父身死,保安便以己力赎友,行为有些突兀;《吴保安弃家赎友》则增加了保安亲赴长安送信的细节,“长安”这一地点的添置,一方面是古代作家“长安情结”[14]的外化,另一方面也使原本孤立的地点姚州具有了相对位置,在姚州与长安之间形成了一段遥远距离。对照地图,“这姚州到长安三千余里”[15]133的小说文字所言不虚,这就以路途之远衬托出吴保安不怕困难、乐于助人的性格,也为后文弃家赎友的行为做好了铺垫,使之更加真实可信。《吴保安》中仅写到保安在嶲州经营,十年不归,如果不借助地图,这一行为难免显得不近人情,而《吴保安弃家赎友》则明确点出保安是因为“又怕蛮中不时有信寄来,只在姚州左近营运”[15]133。由图1可直观看到,姚州与南诏接壤,且比嶲州离南诏更近,也就保证了吴保安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友人消息;而另一方面,姚州与吴保安在遂州的家相隔遥远,往返多耗时间和财物,若回家经营,则不能及时得知仲翔的情况,这样吴保安前往异地、与家相绝的行为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正是这种家庭与友人之间的两难抉择,更体现出保安的重情重义。《吴保安》写吴妻寻夫到泸南,因粮乏路远在路边大哭,而《吴保安弃家赎友》则以行程距离来描写吴妻在路上的艰难:“夜宿朝行,一日只走得三四十里”[15]134,并把吴妻“计无所出”的地点具化到戎州界边乌蒙山下,边界的荒凉、重山的阻隔更凸显出吴妻的困境。后仲翔背负保安夫妇骸骨还乡,《吴保安弃家赎友》特意添置了仲翔在途中客店求祷的情节。这一情节的发生背景是“自嘉州到魏郡,凡数千里,都是步行”[15]139,加上仲翔因钉板双脚尚未痊愈,行路更显艰难,也更能体现仲翔负骨还葬的精诚之心。由此,吴保安故事作为重情知义的典范,其教化主题在《吴保安弃家赎友》中借由距离设置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在被视为明清小说最高成就的《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将地名、距离、路线等文学地图元素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由于《红楼梦》的空间书写非常细致,后人根据小说文本描述绘制大观园地图并非难事。不过以往研究多是借助《红楼梦》的文学地图去考证大观园原型,仅张光英等少数学者将大观园作为《红楼梦》文本人物的行为空间,以揭示作者的空间设计意图[16]。将大观园文本空间转换为大观园平面示意图[16]后,小说中的隐性距离也就转变为显性距离,可直观呈现人物行为空间特征。比较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三位核心人物居所的距离会发现,贾宝玉的怡红院与林黛玉的潇湘馆距离较近,而距薛宝钗的蘅芜苑较远。因此,无须去情节中搜寻事例证明在作者心里“木石情缘”重于“金玉良缘”,仅从距离设置来看,作者的情感倾向已经非常明显。这并非臆测,因为作者的有心距离设置不止一处。如贾母作为贾府的最高权位者,贾母院也代表着权力空间,而王熙凤与探春曾在贾府主政(即参与权力管理),两人居所恰是“金陵十二钗”中与贾母院距离最近的。怡红院则与贾母院距离较远,保持着与权力的一定疏离,而与代表出世空间的妙玉居所——栊翠庵相距较近,实际已暗示了贾宝玉不愿进入仕途、最终选择出家的情节走向。此外,贾、林、薛三人有不少共同活动空间,但葬花冢处、共读西厢处作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共有空间,却是薛宝钗活动轨迹未到之处。而这属于宝黛二人的两处空间,恰好位于与贾母院成对角线、距离贾母院最远的东北角。由此可见,曹雪芹不仅考虑了居所地名与居所主人性格的对应关系,还充分利用了居所的位置来预示情节、塑造人物。
地理学者认为,每个人都会在脑中形成“具有一定方向和距离的、有一定度量特征的不同空间类型的认知地图”[17],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是将认知地图转换成文本地理空间及地理事象,而在转换过程中,由于“距离衰减规律”[17],作者的认知地图(即小说文学地图)必然会因其地理感知程度不同而与实际地图之间存在偏差。因此,无论是显性距离或是隐性距离(两者都是作者呈现在文学地图上的认知距离),如果与实际距离越接近,则说明作者对本区域地理越熟悉,也越能充分运用距离叙事手段;相反,作者地理经验不足时,就可能在距离设置中“露出马脚”,从而为考证作者、成书及分析小说时代、地域特征等提供辅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将文本转化为文学地图,进而比较地图距离与实际距离的分析方法,已从传统的“文史互证”转换为“文图互证”的思维,这也正是文学地图不同于其它研究方法的显著特征。
二、相对位置:遥远距离与邻近距离
无论以哪种形式表示,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无非是远或者近。因此,根据两地之间的相对位置,空间距离又可分为“遥远距离”与“邻近距离”两类。遥远距离会产生两种效果,一是“距离产生美”,当两者相隔较远时,对方在感知中会变得美好;二是间隔阻断,信息传播慢,交流不便。早在《诗经·蒹葭》中,作者就利用远距离为诗歌创造出独特的审美效果。“在水一方”的距离导致了“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的阻隔,这种阻隔和距离使诗歌产生了一种朦胧、惆怅的氛围,增强了审美性。古代小说也常利用遥远距离的设置来达到阻碍人物活动及信息交流等功能,本文将其称为“间阻叙事”。与遥远距离相反,邻近距离则有利于人物突破外界障碍,促进信息交流,可称为“助推叙事”。
在很多时候,小说作者倾向于设置遥远距离来产生间阻叙事,这是由于“文似看山不喜平”,小说情节若无障碍和波澜而一直顺利发展,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在一些情节类型中,遥远距离更是成为关键设置元素。古代小说中有两种重要情节类型——“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18],论者或从叙事学角度探讨其叙事意义的实现,或从地域文化角度分析地域意识对情节要素的影响,若从距离角度观之,这两种情节类型都应用了遥远距离来推动间阻叙事。以《原化记·崔尉子》《青琐高议·卜起传》《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三篇不同时代的“水贼占妻(女)型”小说为例,虽然出发地、遇害地、目的地设置在小说文本中各有不同,却在地图上呈现出这样的共同特点:首先,出发地与目的地距离遥远,均跨越多个行政区域,需要长时间的行程,故赴任官员会携带较多行李财物,易使人见财起意,从而合理产生遇害情节;其次,两地相距遥远所造成的通讯不便,使遇害者亲属短时内不易发现异常,使歹人暂时逍遥法外成为可能;再次,遇害地都在水路沿线,与陆路相比,遇害者的尸体被投入江中或湖中,不易被发现,真相也被数年藏匿。因此,遥远距离成为此情节类型不可或缺的要素。另一类型“万里寻亲型”与遥远距离的关系就更为明显,该类型正是借助“万里”的遥远距离与锲而不舍的寻亲行为形成张力,从而强化小说的孝义教化主题。有的情节类型则倾向于使用邻近距离来产生助推叙事,例如志怪小说的常见模式之一是精怪谈话或现出原型时,恰被不远处的主人公听到或窥见,即是利用邻近距离以助推叙事。
对遥远距离或邻近距离的设置倾向,除了与情节类型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特征。由于唐代街鼓宵禁制度的存在,以长安为叙事空间的唐代小说通常倾向于利用里坊的遥远距离来形成间阻叙事。有时即使里坊的地理距离较近,但由于唐代里坊互相隔绝及夜间关闭的特点,邻近距离并不一定发挥助推叙事功能。如《李娃传》写荥阳生被李娃骗至宣阳里的姨宅,日晚返回平康里李娃宅,已人去宅空,待天明再去李娃姨宅,亦不复有人。从地图上看,宣阳里和平康里距离邻近,故这段描写常被质疑,清代学者俞正燮即认为“作传者信笔漫书之”[19]108,现代文学家戴望舒则指出这恰是利用里坊隔绝与夜禁制度使荥阳生两头扑空的精密诡计[20]21-23。换言之,在唐代小说中,遥远距离或邻近距离的设置都带有以时间制约空间的特征,若将叙事时空更换为其它时代,则会出现情节逻辑的裂隙。
到了宋代,坊市制的瓦解带来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这不仅直接促进了“说话”艺术和话本小说的繁荣,也使距离设置产生了新的特征,临街的店楼往往成为邻近距离的关键设置。如《西湖二集·吹凤箫女诱东墙》,小说的叙事时空是南宋嘉熙丁酉(1237)年间的临安,女主人公黄杏春因听到潘用中吹箫推窗相望,开启了一段才子佳人故事。“推窗”是女性突破空间界限的重要举动,但仅此并不能促使新的情节生成,人物居所的邻近才是关键因素:“那杏春小姐之楼,可可的与潘用中店楼相对,不过相隔数丈”。[21]201正是这样的近距离才使两人的眉目传情及掷胡桃表心意具有了成功的可能。这种邻近距离的设置之所以在宋代以后更为常见,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居民区和商业区的界限被打破,青年女性只需从后楼到前楼即可临街以望,大大增加了和外界男性接触的主动机会,而不像前代那样,只能依靠各种偶然性实现。此外,不同于唐长安城街道的普遍宽广,宋东京城除御街广场外,其余街道均较狭窄,楼屋之间、行人之间、人屋之间的空间距离因而被大大拉近,这就有利于邻近距离叙事的展开。尤其是宋代以来突破坊墙在街道上建造房屋的“侵街现象”,不仅加速了里坊制的崩溃[22],也大大缩短了街道两边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人身接触机会。如《水浒传》和《金瓶梅》中,潘金莲与西门庆的首次会面,即源于在临街店楼前潘金莲的叉竿被风刮倒,正打在走过帘下的西门庆头巾上。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沿街楼屋鳞次栉比,不少店铺的门帘都伸到了街道中央,这正是多年“侵街”的结果,因此西门庆在街上刚好从帘下走过亦合情合理。
在明清时期,小说中出现了大量舟船书写。前人对舟船叙事功能已多有研究,但一般将舟船视为单体分析船头、船舱各空间的文学功能,关于两船的相对距离则少有人探讨。事实上,利用舟船之间的距离来助推叙事可视为明清小说在距离设置上的又一显著模式。如《鸳鸯影》写柳友梅乘舟游湖时,“船与官船相近”[23]310,故他做的诗能被耳聪的佳人听到;也正因两船邻近,对船侍儿掀帘时,才子才能刚好看见船上的国色佳人。从题材来看,该小说与上文《吹凤箫女诱东墙》同属才子佳人小说,而《鸳鸯影》的叙事时空为明嘉靖年间,则以舟船邻近而非店楼邻近来展开助推叙事。再如《警世通言·唐解元一笑姻缘》写明代吴中才子“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因两船距离较近,唐寅才能看清“眉目秀艳,体态绰约”[24]380的秋香,同时秋香看见唐寅,也“知君非凡品,故一笑耳”[24]385,正是这“一笑”引出了千古佳话。因此,两船邻近的距离设置成为了引发整个故事的前提。将小说与其本事相比较,《情史》载唐寅在岸边遇见华府家眷乘舆而来,对丫鬟桂华一见倾心,而《唐寅附》与《茶余客话》虽对男女主人公的名姓有不同说法,却均认为两人初见是在登虎丘时[25]324-335。无论哪种说法,相遇之事皆在近距离的空间中发生,而《唐解元一笑姻缘》最终选择了舟船邻近的方式,这是作为明清小说主要创作群体的江南作者地域意识之投射。
结合叙事时空与距离设置,可以更好地解读小说所蕴含的时代信息,而如果将距离设置与小说评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方式相结合,则可能对小说文本及小说批评有更深入的认识。例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回目之一,向来颇受重视。早在金圣叹评《水浒传》时,对这一回就密集地批注多处“妙绝”“奇绝”,如小说写林冲出草场去沽酒,路过一古庙,金圣叹评道“妙绝奇绝,安此一笔”[26]212,又在林冲去古庙夜宿时,再评一次“行文如此,为之叹绝”[26]213。但金圣叹并未说明“绝”在何处。有论者认为,林冲受难仍在古庙祈求,是其“安分守己的性格”的体现,后在庙前杀人祭神,则完成了“性格的彻底转化”[27]220。但如果注意到这个古庙并非随意设置在道旁,而是“行不上半里多路”的地方,那么就会发现小说的距离设置也是金圣叹称绝之处。
首先,“半里”是特意设置而非闲笔,因为在后文草厅被压塌,林冲发愁夜宿问题而想起古庙时,小说又一次强调了“离了这半里路上”[26]213。正因为离得不太远,在已经天黑的背景下,林冲去古庙夜宿是合理且可行的。如果距离很远,那么林冲很难看清路,且他作为看管草料场的差使人,易获擅离值守之罪。不仅如此,正因距离较近,在草料场被放火时,林冲才能听到爆响,看到火光,陆虞侯等三人边走边议论刚才的放火并被林冲听到,也才合情合理。换言之,半里之外的古庙设置是“沽酒—夜宿—放火—杀人”这段情节的关键铰链,起到了助推叙事的重要作用。
其次,对距离的特意设置不止这一处,且金圣叹有意识地关注了这一点。如金圣叹认为,小说安排李小二夫妻的出场,是为下文交代陆虞侯三人害林冲之事埋伏线;但林冲既然是李小二恩人,后者理应追随,如何让李小二在完成文学功能后退场呢?小说利用了遥远距离的间阻功能,以“只是小人家离得远了”[26]210让其合理淡出情节。金圣叹在此句后特意指出,他人认为这句闲语可删,是没有看到小说作者“以此一语为李小二作收束”[26]212的巧妙用意。在另一处,林冲为沽酒而离开草料场,逃过了一场雪难。李卓吾容与堂评本中写林冲想起“五里路外”[28]141有市井,故去沽酒,而金圣叹评本中则作“二里路外”[26]212,也可证明金圣叹有意识地要去凸显这种邻近距离设置。
在以人物情节为中心的传统小说批评模式中,像距离这类主要情节以外的“非情节”因素,去掉后“几乎不影响情节的完整性”,故往往被视为“闲笔”[29]而被忽略。金圣叹却相信“作者之腕下有经有纬”[26]204,认为这些闲笔隐藏着作者的精心意图,他自己也以评改实践来揭示这些叙事构思。因此,留意小说中的距离设置,不仅可以更好地分析小说叙事,也可能为古代小说评点研究拓展新的思路。
三、形成原因:自然距离与人为距离
为了让情节曲折生动,小说往往要“进行间阻—助推—间阻—助推”的交替叙事。因此,小说中的遥远距离或邻近距离并非一直不变。如果将两地之间由于相对位置而形成的距离称为“自然距离”,那么,借助人物活动来改变原本的距离,这就形成了“人为距离”。
自然距离与人为距离的区别,这里用唐传奇中的“传书”故事来说明。《三卫》和《柳毅传》都是由于托书地和传书目的地之间距离遥远而需找人代为传书,距离不仅成为故事情节得以产生的前提,还反衬出主人公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凸显小说主题。将小说转换为文学地图后会发现,这两篇小说的托书地到传书目的地须跨越多个行政区域,且龙女的夫家都位于山脉旁,从地图上可直观地看到山脉的阻隔切断了水域网络,这也为龙女作为神灵却须求助凡人传书提供了合理逻辑。因此,这两篇小说情节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山水之间的自然距离。
唐传奇《淮南军卒》也是一篇“传书”故事,主人公赵某从淮南至长安送信,两地距离遥远,对普通人来说,这样的自然距离可能会形成间阻,但赵某善于行走,可“日数百里”[30]770,因而自然距离在此并未发挥推动情节的功能。当赵某在华阴被金天王要求去成都送私信时,距离才成了影响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由图2所示,淮南(图中①)、长安(图中③)、成都(图中④)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也就是说送私信之目的地并不在送公书路线的途中地点,而是在方向相反的另一端。无论赵某选择“华阴—长安—成都—淮南”的路线,或是选择“华阴—成都—长安—淮南”的路线,他都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返回,从而陷入两难的选择困境。因此,正是金天王的命令人为地延长了传书距离,才成为小说的关键情节,并使小说产生了戏剧性的冲突。
在宋元话本和明清拟话本中,为了用曲折离奇的故事吸引听众或拟想听众,小说作者也会经常制造人为距离。在《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与新婚妻子三巧儿本来在襄阳府枣阳县一起生活,夫妻恩爱,如何让人物出行以产生人为距离呢?小说让蒋兴哥“一日间想起”[15]4父亲在广东的生意,以此造成夫妻分离,给陈大郎提供了可乘之机。襄阳与广东的空间距离较为遥远,由此产生的信息隔绝和往来不便,使三巧儿的偷情之事有发生并可被隐瞒的合理逻辑。襄阳与广东的自然距离本在蒋兴哥婚前即已存在,但并没有对夫妻感情造成影响。新婚三年中,蒋兴哥未去广东,即使在决定去广东后,因路程遥远,蒋兴哥又延迟一年出发。因此,蒋兴哥到广东后,与留在襄阳的三巧儿所产生的距离属于人为距离。
再如上文所论《吹凤箫女诱东墙》,小说主要利用邻近距离展开助推叙事,但男女主人公姻缘将成时,潘父却“定要迁去与一个乡里同住于观桥”[21]208,才子佳人霎时分隔两地。潘父为何“定要迁去”,小说并未交代,但显然作者是要借助迁居的设置制造人为的距离,让叙事再起波折。将小说正话与其本事《情史》卷三《潘用中》比较,后者只述及“潘父迁去与乡人同邸”[31]59,而前者则具化到“观桥”这一地点。如果参照“南宋京城临安府城图”[32]6将小说转换为文学地图,就不难发现作者的意图:潘用中居住的六部桥与后来迁居的观桥分别位于临安府城的南边和北边,故作者是特意通过“迁居”这一人为因素来制造遥远距离,从而形成间阻叙事,以强化男女主人公的苦恋相思。《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中也写到潘、黄之事,但男女主人公订情后选择了“走离京师”[33]235,这就使小说的叙事焦点发生了偏移,原本“爱而不得”的哀婉风格因人为距离设置的移除而被大大削弱,包公英明断狱的形象则被衬托得更为鲜明。由此可见,距离并非小说作者随意设置的地理元素,而常常是作者基于小说题材类型、情节逻辑等做出的自觉选择。
除了出行、迁居,明清小说中更为常见的距离设置手段是“移舟”。舟船本身具有可移动性,因此利用舟船的停/行、近/远设置人为距离显得更为合理自然。当然,并非这些小说作者更为高明,而是由于认知地图具有地域性,因而作为明清小说主要创作群体的江南小说家在绘制文学地图时,会优先择取更熟悉的水路区域,也能够更为熟练地使用舟船叙事手段。
以明代白话小说名篇《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为例,杜十娘赎身后,故事本是朝向美好结尾发展,情节发生转折,是从孙富移舟“泊于李家舟之傍”[24]470开始的。正因有了这样的近距离空间,孙富才得以近睹十娘容貌,也才有了下文孙富劝李甲将十娘转归自己,十娘悲愤沉箱的高潮情节。
另如《醒世恒言》卷二十八《吴衙内邻舟赴约》,题目中的“邻舟”已暗示出小说将借助近距离的设置来推动叙事。吴衙内的船本是“一路顺风顺水”,将近江州时“倏忽之间,狂风陡作,怒涛汹涌,险些儿掀翻”[34]600,这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忽闻江风大作。及晓,彤云密布,狂雪飞舞”[24]470类同,显然是小说家使用的同种手法,都是借恶劣天气来阻断行程,为泊船相邻的近距离设置做铺垫。果然,吴府官船靠近岸旁时,“那边已先有一只官船停泊。两下相隔约有十数丈远”[34]600,这让吴衙内得以看见“半卷”帘内的贺小姐,撩动了情思,继而又借口要两船相帮以求安稳,移船靠近。然而,贺夫人却叫丫鬟下帘掩门进去,重建空间界限。后贺司户邀吴府尹父子上船赴宴,吴衙内与贺小姐有了接近的机会,但隔着舱门,仍无法传情。后来二人得以成事,仍是依靠两船相帮、两窗相对所创造的空间条件。
无独有偶,《二刻拍案惊奇》卷七《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也使用了同样的叙事策略。故事起因于两只官船路线相同,均是从水路由汉州至临安,故“栖泊相并,两边彼此动问”[35]108,为下文晚孺人和吕使君调情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直到在一个码头泊船时,使君吩咐船家“要两船相并帮着,官舱相对”,他从小窗跳进孺人舱中,才得以成事。梳理小说情节的发展会发现,尽管两人一直在试图打破空间界限,但唯有通过移舟相邻创造出近距离的空间便利时,他们的意图方可达成。“开窗”和“掀帘”常出于无意,“移舟”却是采取主动,因此舟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情欲的空间隐喻,移舟越近,欲望越盛。这也成为舟船故事中人物打破空间界限的独特叙事特征。
除了通过“移舟”来设置邻近距离,小说也可通过“移舟”来制造遥远距离。如上文《吴衙内邻舟赴约》中,当吴贺两人睡去时,因风浪平静,船只各自开动,阻断了吴衙内的退路,叙事再起波折。不过,在舟船距离变远而使吴衙内无法回到船上的同时,也使男女主人公同处一室,两人感情也日益升温。由此,《吴衙内邻舟赴约》可视为利用距离层层推进叙事的典型。其情节模式可概括为“同地(近距离)—间阻—邻舟(拉近距离)—间阻—同舟(更近距离)—间阻—同舱(零距离)”。这也是舟船空间近距离设置的总模式,各小说中不一定具有上述全部环节,但基本可归为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利用近距离设置助推叙事时,通常不会一次促成,而是与间阻叙事(不一定是距离间阻)交替进行,以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也正因如此,近距离设置选择的空间多为本身具有间阻功能的花园、楼屋或舟船。而当空间设置于没有间阻功能的户外或路上时,则需要借助特定的时间,如清明、元宵等节庆时,这一方面为女性制造了突破闺阁空间与男性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另一方面,人群的流动性又让男女难以长久近处。总之,近距离使双方“可见”,间阻使双方“不可得”,在“可见”与“不可得”之间,小说产生了审美张力,读者也产生了阅读期待。
如果说诗文常以片段化、意象化表达来呈现地理空间,那么具有“内在地理学属性”[36]44的小说,其地理空间往往具有更多可感的细节性,也更容易转化为文学地图。不过,文学地图元素的作用机制在不同文体中仍具有相通性。如远距离产生间阻效果,近距离产生助推作用,唐宋词中就常常通过设置“不在场的情人”,拉远男女双方的空间距离,以产生时空阻隔,由此反映出唐宋文人心态、词的文体特征等[37]。因此,留意作品文本中的距离等地理信息,充分利用文学地图作为文学地理学“第二语言”[38]的优势,将在更大程度上还原被传统线性文学史遮蔽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