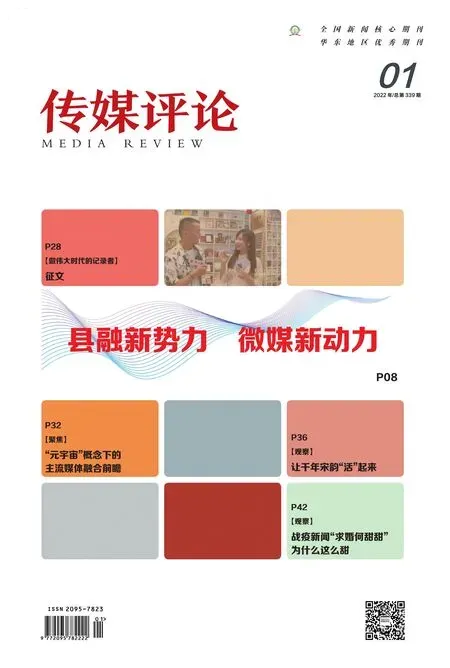滋养阅读品位的新闻作品,永远值得期待
文_石天星
移动互联时代,新闻简化的趋势日益显明。如果说短新闻凭借的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那么,以洞察和发现见长的深度报道,在时代潮流面前,未能占得先机。在普遍焦虑的现实氛围里,非但记者难以保持沉静,细致深入地采访、探究,读者也对大长稿“一望辄止”。然而,潮流也是轮回,回归本原,才能做到极致。事实是新闻的写作基础,但新闻也是讲故事的艺术,深度报道以文字为“武器”,从文学写作中汲取营养,在可读性和感染力上下功夫,也是从竞争中突围的一线生机。10年前,笔者入职浙江日报,10年来业态急剧变化,但可读性始终是从业者关注的大课题,今以深度报道中的文学性为切口谈谈浅见,权作献芹之心。
文献学家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一书中把古今人的写作分为抒情、纪实、说理三大类,并认为,后世著述虽繁富之极,但推本穷源仍然是这三大类写作不断发展的结果。“所谓抒情的作品,便是文学;纪实的作品,便是史学;说理的作品,便是哲学。”[1]一篇深度报道中,往往既有纪实,又有抒情,还有思想性,因此,史学、文学、哲学方面的学养积淀,可以延展观察和写作的边界,提升新闻文本的质感。可读性强的新闻文本,更是明显具有文学品质的追求。
一、细节与闲笔,让历史从细微处走来
关于新闻写作,真正口耳相传的理论其实相当贫乏,因为大部分人认为好记者是天生的,是不可教的。“比如细腻,比如敏锐,比如观察力和天然的代入感,比如轻易获得他人信任的天赋。”[2]但“细节”恰恰是口耳相传的写作秘诀。
“细节”对于新闻写作而言,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细节让故事可读,让历史可感觉;细节,是在场的证据,通过细致的观察以及提携关键意义的细节,可以呈现不能过多用言语去探求的真相。
但细节有时候又容易被人们泛化地理解。实际上,细节并不是越多越好,我们不需要一些孤立的、琐碎的细节,而是需要精心挑选的细节。
有研究者专门分析过《左传》的叙事特点:在叙事紧张处,常宕开一笔,写起了小事件、小情节。这些小事件、小情节,是游离于叙事主题、主要情节之外的枝节,谓之“闲笔”。《左传》中的“闲笔”,既能造成一种紧张与悠闲参差错落的美学效果,还能揭示大历史发生的具体情景,“从细微处展示历史人物真实的心理动态,让宏大的历史从细微处走来”[3]。
2016年,笔者在温州永嘉大山深处的石公田小学“蹲点”近一周,每天和师生们吃住在一起,后来写成《石公田小学的乡村笔记——山水田园里的乡村教育》(2016年4月15日《浙江日报》第20版)。
在第二部分“【第二天】石滩上的课堂”中,笔者写了这样一句话:
雨过天晴,山间公路旁,开满小黄花的山胡椒树伸出山崖。
写山胡椒树的“传说”是为了从一种“亲历”式、充满现场感的叙述转入对过去的追叙。部主任告知,这篇稿子上版后,当晚值班副总编在签版时看到此处,便念出了声。部主任在部门例会上评价道,这便是“闲笔”。
“闲笔”写的都是细节,但细节不一定都能起到“闲笔”的效果。
古代文论研究大家王达津先生说得好:“闲笔不闲,使文有节奏、张弛,在闲文中伏线埋根,闲中可以有冷笔,有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
谈论细节,并非只是强调要如何细腻传神地描写,更深的层面指向我们观察世界、解释世界、呈现世界的方式。正如南方报业高级记者南香红所说:“细节的运用精准巧妙,才是一个写作者成熟的标志之一。”[4]
2018年,笔者独家采访了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中科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张弥曼,写下了《浙江的女儿 科学的赤子》(2018年3月30日《浙江日报》第4版),在这篇人物通讯报道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手机响了,是有媒体希望采访她。“你看,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很可惜,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剩下来的时间,还是希望能安安静静做一点事,没什么牛可吹的。”挂断电话时,她嘟嘴。
再有电话打来时,她微笑着看着我说,不接了。
这个场景本是访谈张院士过程中的意外“闯入”,可以放过,也可以不放过,不放过就成就了一个“细节”。在当年4月一篇题为《我有国士,天下无双》的人民日报微信图文中,包含张弥曼、袁隆平等在内的十多位老科学家入选,每个人有一句话展现其思想境界。张弥曼院士的这句话是——“剩下来的时间,还是希望能安安静静做点事,没什么牛可吹的”。好的细节,自会“说话”,也会流传。
二、诗性笔调,难以被模仿的个人化风格
新闻写作和一般写作的不同,在于新闻写作的质量主要取决于采访是否扎实深入。新闻写作提倡“低温”的叙事,“‘低温’的叙事,基本叙而不议,或关键处偶尔议之,目的正是‘尽可能地把客观事实和本质最准确地传递给受众’”[5],但议论并非赘余,恰恰需要“少而精”的议论来增强叙事张力。诗性笔调,需要拿捏好叙与议的比例,处理好感情的强弱与遣词造句,体现文章的格调和思想性。
诗性,首先是一种抒情性,张舜徽说:“何谓抒情?一个人对外界接触或内心活动,要如实地抒发出来,写成诗歌,这便是抒情的作品。”
抒情性展现在文字上,或可借用闻一多对新格律诗倡导的“三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美在音节、节奏,长短句间隔,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绘画的美,美在词藻带来的视觉画面,诗人认为好诗必须有“浓丽繁密而具体的意象”;建筑的美,在韵文化的文本中是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在散文化的文本中,也有结构类似的句子,形成相互间的呼应和回环复沓之美。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有看重诗歌社会功能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孔子,“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性”与“说理性”有着天然的交叉重合,很难截然分开,诗性笔调往往寓情于理。
新华社高级记者张严平以人物报道见长,看她的简介,有这样的评价:坚持深入生活、深入人物心灵的采访作风,文章质朴真切,充满情感,富有诗性,受到读者喜爱。前面的话都好理解,唯独“富有诗性”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何定义“诗性”?这既需要回到诗歌的本原,认识诗歌的特质,又需要结合张严平的作品来具体分析。
在张严平的代表作《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最显著的诗性笔调,是其中四个以“如果”开头的句子: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一种“心”的冶炼,他在这冶炼中锻铸了最壮美的词句——“忠诚”。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一条连接党和人民的纽带,他就是高原上托起这纽带的脊梁。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一个人的长征,这条长征路上凝结着他全家人崇高的奉献。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高原上的彩虹,他就是绘织成这彩虹的索玛。
这四个句子,放在一起,就仿佛是一首诗,放在整篇文章中看,则是以诗为文,叙议结合。不光呈现诗歌意象,更是文章架构中的转捩句,高度凝练了四个部分的“中心思想”。
诗性的笔调,是非常具有个人化风格的创造性写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唐诗研究文章,最后汇编成一册《唐诗杂论》,笔者在中文系读书时就震撼于论文居然还能这样写,考据与欣赏融为一体,文章是诗的风格。后世评价《唐诗杂论》“冲破了传统的学术方法、学术研究的狭隘和封闭”,而这种冲破,诠释了“文无定法”。
诗性,是体现作者个性与特质的文体装饰,属于文章美学的范畴。新闻写作固然有条条框框,但也受记者笔力驱遣。越是个人化风格明显的文体,越难以被模仿,也难以被复制。
三、情节与人物的细腻呈现,撑起故事化写作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速变动的时代。新媒体兴起以后,由于“流量”与吸引广告投放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因果,阅读量、粉丝量正逐渐作为直观反映内容好坏的标准。人物报道在吸引阅读上拥有天然优势。2019年1月10日《人物》杂志微信公众号推出了一篇《一个好脾气的中年男人决定离家出走》,这个普通人的故事,瞬间击中了许多中年人渴望欢脱一把、逃避一把的心理,好奇与共鸣迅速将阅读量推升至10万+,留言区热闹非凡。而这个故事,依然符合新闻业讲故事的古老原则:严格以现实来源作为依据,尽可能细腻呈现情节、细节、挖掘人物的内心。
在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南方周末》特稿版为标杆的传统媒体的精品写作时代,新闻精品的概念被如此总结——在文本上彻底建立故事化写作的模式。我们的深度报道,已经牢牢树立起新闻是作品的观念,要有任何时候来阅读都会觉得有价值的自觉意识,时刻将报道的可读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突出细节、现场感、虚实结合和文学技巧。
今天,只有持续不断的内容生产力,才是制胜的武器,因此,对记者抗压能力和体力的要求比以往更高。但无论处于什么条件下,好记者依然渴望讲好故事。
潮流总是周而复始,每个人在忙于应变的同时,也都渴望守住一个舒缓、优雅的精神避风港,滋养阅读趣味的新闻作品,永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