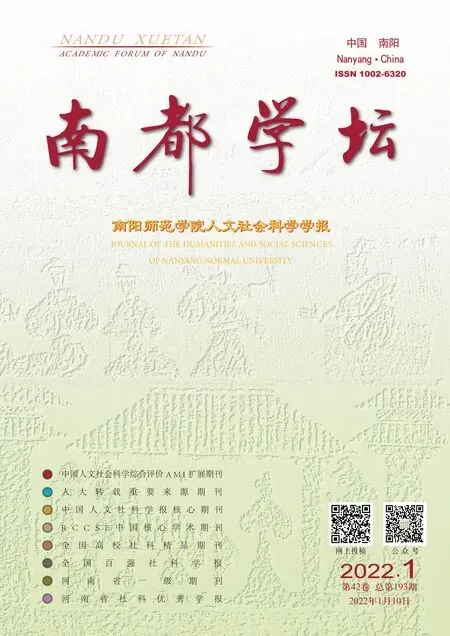《史记》民族书写与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刁生虎, 王 欢
(1.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2.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学校办公室,河北 廊坊 065000)
《史记》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为少数民族单独述史,作《匈奴列传》等6篇少数民族专传,并与该书其他传记中涉及少数民族的诸多文字,共同构成了彼此呼应的系统化民族书写格局。可以说,《史记》以恢宏的民族书写记述了境内外少数民族的起源史与演变史,全方位呈现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民风民俗等基本状况以及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展现了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动态演进历程,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史记》民族传记书写与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早在上古时期,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神话传说便已大量出现,《山海经》即存有毛民、匈奴、东胡等少数民族的记录,如《海内南经》圈定了匈奴的地理方位:“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1]先秦以降,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字记载更为多见,《尚书》《周礼》《逸周书》《诗经》《春秋》《国语》《战国策》等诸多经典中都有涉及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述。如《尚书》有“窜三苗于三危”[2]、《周礼》有“四夷、八蛮、七闽”[3]的记载。不过,这些关于民族的早期记录多属碎片化记录,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而为少数民族专章设传、系统开展民族书写,则始于《史记》。《史记》共130篇,记载了自远古至武帝时期的3000余年历史,反映了少数民族历史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构建了先秦两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记忆,迄今为止都是学界研究先秦至汉代中国民族史必须阅读和引用的重要文献资料,并因高超的文学造诣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将少数民族作为记传对象、创设民族传的书写模式、承认少数民族在历史书写上的特殊性是《史记》少数民族传记的显著编纂特征。这给予了少数民族独立的历史出场权,使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在历史著述中相依相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谱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支撑。《史记》民族书写内容集中在《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6篇少数民族专传中,此系列传记将某一少数民族整体作为撰述对象,系统书写了匈奴等少数民族从上古传说时代直至汉朝当代的衍生发展历史。除6篇少数民族专传以外,《史记》中的其他传记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少数民族、民族关系等,它们虽实为中原人物传记,不能归入少数民族专传的范畴,但其或为古代中国境内外少数民族的演变历史作了细节填充,或内含司马迁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与少数民族专传共同书写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比如《史记·韩长儒列传》记写了御史大夫韩安国反对与匈奴开战的历史,即表现了司马迁对以战争解决民族纠纷这一做法的批评态度。
若要使若干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彼此有机分布、相互沟通联系而成一部完整的史书,制定史书编纂体例是必经之步,也恰恰更能直观反映史家排列素材所依循的创作原则甚至政治主张、思想倾向。注重联系性、系统性、全局性,使撰述对象既各自独立又有机统一,是《史记》遵循的著史原则,这在民族书写的撰述体例上亦得到了贯彻,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亦彰显在形式上。《史记》“列传”可分为“人名传、国名传和类传”[4]135三种形式,少数民族传记即被集中纳入主叙将相大臣及社会各阶层重要人物言行事迹的列目之下,以上三种体例均有涉及。国名传又称族名传,是为少数民族专章所设传记。《史记》中的《匈奴列传》等6篇少数民族专传显然是以民族为名的族名传,其中《大宛列传》虽在命名上看以民族为名,但在位置上却与类传同列,这或是出于《大宛列传》将在性质上同属域外之族的多个民族合为一传的考虑。在《史记》少数民族传记中,就族名传与类传而言,《大宛列传》在传名设置上可归入族名传之属,但司马迁将它归入类传之列,这或许是司马迁出于《大宛列传》中各个民族具有境外之族这一共同特性的考虑,也可能出于“初创之时体例尚疏”[4]139的原因。不过,无论司马迁用意如何,这样的安排已然能够显示出《史记》少数民族传记中族名传、类传两种体例的交融性、联系性。就人名传与族名传的位置关系而言,司马迁并未将它们严格区分开来,而是相互杂糅穿插在一起,虽各自为传,却又上下联系、有机统一。比如《匈奴列传》上接《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下连《卫将军骠骑列传》等,这是因为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等都有与匈奴有关的经历,他们或曾就匈奴问题上书建言、或曾带兵征战匈奴,也就是传记与传记之间存在着历史的联系。赵翼对此评价称:“《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5]究竟司马迁原本便如此写成、还是写成后又重排了各传,已未可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历史本就无法截然分割成彼此不相联系的片段,少数民族历史更是时间跨度长、矛盾盘根错节、局势复杂多变,且同时牵涉中原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物,其传记虽然受限于“纪传体”体裁特点而必须划分成一个个独立的专篇,但《史记》少数民族传记最后呈现出的依照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联系性而排列的状态,揭示了司马迁注重联系性、整体性的潜在写作思路,令各篇少数民族传记在收放自如中既各自独立成传、又具备一体性,使史传编排符合读者的思维逻辑与认知规律,便于读者充分了解、查阅少数民族历史。此外,这种不将记载中原人物史事的篇目与民族传记严格划分开来的编排方式,彰显了司马迁的民族平等观。司马迁没有对中原、少数民族赋予严格的内外之别,而是对各少数民族与汉朝将军大臣等而视之,与“朝臣与外夷相次为不论”[5]之类的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张大可即称此为“四海一家之观念。”[6]
二、《史记》民族同源书写与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史记》各篇少数民族传记中,司马迁均交代了各族历史源流情况,从各族上古时期的祖先开始书写,再按照时间顺序述说各族如何从上古一步步发展到汉代,各族起源清晰。对于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来说,司马迁不仅清楚交代其本源,还在本源层面将其与中原相连,建构了贯通古今、囊括四海的黄帝谱系,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谱系精神应用于各族源流之上,主张他们与中原祖出黄帝、血脉相系,本质上同中原是从同一树干上分生出的枝丫:“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7]1475流露出同根同源、天下一体的大一统民族主张。司马迁将黄帝视为华夏始祖,开篇《五帝本纪》从黄帝写起,认为其他四帝都是其后代,故黄帝是华夏各族的共同祖先。《匈奴列传》开篇即言:“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7]2879指出匈奴祖先是夏禹后代,而夏禹是黄帝子孙,因而匈奴始祖可以追溯到轩辕黄帝。《越王勾践世家》言:“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7]1739即越王勾践亦为夏禹后代,属黄帝一系。《东越列传》言:“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7]2979可见无诸与摇的祖先都是勾践后裔,而勾践的祖先则是禹后裔,东越族祖先自然可以一直追溯至禹。再如《朝鲜列传》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7]2985《西南夷列传》言:“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7]2997以上诸多记述无不显示出太史公少数民族祖出华夏的思想主张。
在对少数民族地位的认识上,相较于前人,《史记》歧视、轻蔑的程度降低,对少数民族施以了关注与重视,折射出了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平等内核。先秦时期,华夏族对周边少数民族抱有偏见,华夷之辨思想严重,将文明与否作为区分华夏与少数民族的标准,认为少数民族是化外之民,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8]强调少数民族地区文明落后,虽有君主统领但也形同虚设。那时候,人们对于少数民族的态度不仅仅是划清与自己的区别那么简单,贬低、排斥、藐视心理严重,比如孟子以鸟语与楚人徐行说话相比:“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9]100认为蛮夷之地文明落后,从来都是中原礼仪影响蛮夷之人,蛮夷从未将中原同化:“未闻变于蛮夷者也。”[9]99更别提将少数民族写入历史了,故《史记》以前史书未有为少数民族作传的先例。而《史记》开为少数民族述史之风,并且认为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即可见司马迁相较于前人已开始对少数民族予以特别关注,是一种朴素民族平等观的体现。此外,《史记》多处记述了中原与少数民族杂处、互通有无的事实,这种对于少数民族与中原保持友好往来关系的歌颂,亦彰显了司马迁对他族抱有的尊重。比如关于西南夷与中原的交往史,司马迁写道,楚庄王后裔庄跷到达滇池地区后,发现那里方圆三百里,平原一望无际,土壤肥沃丰饶,于是便派兵平定使之归于楚国。庄跷打算回去上报时恰逢秦国攻击夺取了巴楚一带,道路中断,无法通达,因此又回到了滇池,凭借军事力量做了滇王,更改服饰,融入当地:“变服,从其俗。”[7]2993做了该地方首领,史称“庄跷入滇”,促进了中原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情感往来。当然,司马迁虽然在民族起源与地位上流露出民族平等的思想倾向,但也绝非能与当代倡导的民族平等概念相等同。从本质上来看,司马迁将匈奴等他族传记归入“列叙人臣事迹”[7]2121的传目之下,赋予了少数民族以等列天子臣民之身份,这一方面彰显了司马迁对于民族一统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司马迁对封建等级秩序的强调与中原王朝地位的维护,并未使其拥有绝对意义上的与中原相平等的地位。而且,司马迁既提倡少数民族与中原的平等交好,也意识到少数民族与中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地域上,更体现在文明上。司马迁在描述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精神风貌等的基本特点时,常常将华夏族作为潜在比较对象,认为华夏族属文明、进步的一方,少数民族属落后的一方。如《史记·匈奴列传》中“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7]2879、“苟利所在,不知仁义”[7]2879等关于匈奴族民族特质的否定性记述,显然均是将中原作为隐含标准、将少数民族与其进行比较参照来书写的。
三、《史记》民族关系书写与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必须予以考虑也必然会面临的问题,它影响着各民族的交流效率与沟通质量,可以有平等共存、敌对分裂、依附从属等多种形式,融洽无间的民族关系常常需要在人为干预与运营下才能顺利形成与保持,各民族间和睦安宁或动荡不安的相处状态会在一定程度上波及社会民生的演变动态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势。司马迁在记录各民族诞生、壮大、兴盛、衰亡的存续历史时,亦或多或少地将远古至汉武帝当朝的民族关系状况即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以及中原与各少数民族的交流交往史注入各篇民族传记中,其中,不仅记录了各民族互通有无、交战征伐等有关民族关系的社会历史事件,亦记载了当朝统治者制订的一系列规定政策,反映了国家维护民族和平、处理民族矛盾争端的方式与过程,由此,民族关系史从《史记》民族史中脱胎而生。历史是经司马迁的搜整、筛选、鉴别及加工后才得以在其笔触下写就,因此,从《史记》民族关系书写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于民族关系这一问题的考虑与设想以及他对于有关民族关系的当朝政策的意见与态度。具体来说,在解决民族纠纷、处理民族矛盾方面,司马迁反对华夏族主动出兵侵暴他族,他同情弱小,倾向于对境内他族采用封王、赏金、和亲等柔性主张,向少数民族施以恩惠来拉拢对方、使其归附。究司马迁柔化矛盾、安抚局势的民族关系主张之内里,本质是向往各民族的长久稳定与共同繁荣,是倡导各族亲如一家之共同体意识的显著体现。
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在先秦尤其两汉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重要一支,历经冒顿、老上至且鞮侯单于等数代,不仅世系源远、统辖范围辽阔、人口规模众多,在政治管理、军事力量、经济状况等方面也在诸多少数民族中居于首位,几乎与中原抗衡,加之匈奴并不安于平静生活、屡屡进犯中原,因此,对于两汉时期的中原统治者来说,匈奴堪称诸少数民族中对中原威胁最大的一支。汉匈关系深受汉朝统治者关注,司马迁对汉匈往来及汉朝对匈政策的记载由此也十分详尽,不仅少数民族专传《匈奴列传》中载有大篇幅记录,内容上涉及少数民族的其他传记如《韩长孺列传》等中亦有记写。比如,《匈奴列传》除了对其地理概貌、风俗人情做了详尽描述以外,对秦汉以来匈奴与中原间的战和关系也做了细致论述,其中司马迁即围绕汉朝的对匈战争作了一定篇幅的记录,折射出了司马迁在民族关系方面的观点理念。在《匈奴列传》赞语处,他即就征伐匈奴的鲁莽决定作了批判,指出对匈出战这一决策并非是基于中原和匈奴双方的现实状况作出的,而是朝臣为了谋权夺势、争名逐利而轻易下的结论。明面上,司马迁将矛头指向了提出对战建议的王恢以及带兵出征的卫青、霍去病等,将失利泛泛归罪于将相而非汉武帝,其实,他深知汉对匈的大举征伐是汉武帝决策的结果,这一点在他在赞语中引用的古人之例即可看出,他认为“尧虽贤,兴事业不成”[7]2919。尧是一代明君,但如果仅仅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做成一番大事的,其基业在大禹辅佐下才得以稳固,这句话表面重点在大禹作为臣子的忠心与效力,实则重点指向尧作为一国之主的不称职。在《匈奴列传》末尾处,司马迁连用两次“唯在择任将相哉”[7]2919,更是以隐晦之语倾吐了对汉武帝出战匈奴这一决策失误的遗憾与痛惜,展示了他柔性处理汉匈问题的坚定立场。再比如,就中原与南越的民族关系而言,在《南越列传》中,司马迁对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与汉文帝刘恒对南越所施行的和平政策给予了热情的赞颂,他们与南越互通有无,汉越实现和睦相处:“遂至孝景帝时,称臣,使人朝请。”[7]2970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来了民族间和睦相处的大局面,这是满足司马迁内心之期待的民族关系处理范式。而对汉武帝时期的大肆扩张、举兵征战以致南越被灭的史实,司马迁则持含蓄的批评态度,比如《平准书》写道:“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7]1421体现了司马迁对以暴力求安定、令他族臣服于强权之下的民族关系处理方式的不满情绪,展现了他向往和平、友好待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司马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因及价值
《史记》民族书写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司马迁民族思想与进步历史观的组成部分,这一意识的产生并非凭空出自其个人的独立创造,而是源于两汉时期大一统格局的完成和巩固,源于儒家关于家国一体、和合大同理念的认识,源于司马迁的著史意愿与品格。
首先,司马迁的著述活动发生于秦汉以来尤其是西汉时期多民族走向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这使其民族主张富有追求少数民族人民与中原地区人民和谐互动、和睦相处的倾向。从古至今,中国就是一个各族朝着多元一体构造而发展的国家。在上古时期,伏羲、炎帝、黄帝等氏族顺次迁徙至华北平原,在黄河中下游一带扎根,并将四方部族渐渐吸收,中原华夏族由此诞生。历经夏至周的承传与过渡,华夏族在王朝国土上的主要地位被逐渐加强直至确立,中原以外的境内四方周边民族则被普遍泛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在周朝初期,各民族融合的趋势愈发明显,分封制统率下的周王朝内已有了不少内附的“夷狄”之国,中原民族与边境民族间的通婚现象也逐渐显现。从春秋到秦朝,各民族间往来日益密切,一统成为历史的潮流。《史记》著录工作发生于司马迁受汉武帝赏识的时期,此时汉朝国力增进、国政趋稳:汉武帝革新图治,绌抑黄老,尊崇儒学,百家并进,经营四方,促成了国内建设的繁荣与对外联系的发展,文治武功,伟业空前。在举国繁盛的时代背景下,中原王朝与诸少数民族的关系亦趋于太平,民族政策以和亲为主,未发生重大民族矛盾。民族一统局面不仅作为外部条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司马迁对于少数民族的认知,还作为政治因素驱使司马迁从史家角度为大一统局面的正名、巩固与加强增砖添瓦。朝代更迭带来的大一统进程使司马迁认识到自己身担总结统一经验、为其寻找历史依据、歌颂大一统的史家责任。在此基础上,他坚信并将民族共祖理论条理化、系统化,对境内各民族平等视之,主张各民族间和平相处但又不完全反对为了镇压民族动乱而发起的有益于人民、国家的正义性战争……由此视之,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本质上围绕着大一统思想展开论证,思维缜密地为大一统思想服务。
其次,司马迁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继承并发展了先秦两汉时期儒家的天下大同观。虽然“民族”这一现代概念并未在中国古代出现,但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意识却是自始便扎根于华夏先民血脉中,蕴含于天下一家、家国一体、和合大同等思想深处。早在先秦,对天下一统的期待和向往便渗透于儒家著作的字里行间。《诗经》中的“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10]即传达了歌颂统一的思想。《春秋》最早提出正统论,追求构建以宗周为正的一统王朝。《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1]表达的也是对天下一统的祈盼。汉武帝时期,儒学大兴。在汉武帝和董仲舒等人的极力推崇下,“大一统”成为上至天子、中至廷臣、下至平民的时代主流意识,这种对于天下一统理想的渴望亦会渗透于司马迁著史过程中,使“统一”成为写少数民族传记的潜在情感基调。
最后,《史记》撰述伊始以私修为端,司马迁本人具有强烈的著史愿望,撰写《史记》的工作并非任何人强加于他的,他不必去刻意迎合别人的意思。这就使得司马迁在为少数民族述史的过程中拥有较高的自由度和站位,具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和充分的表达权。在审视少数民族关系时,司马迁也就有条件将自己作为置身历史之外、与历史无利益纠葛的旁观者,身处开阔高远之境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演变作客观反思。加之太史公本人天性刚直不阿、耿介正直、坦诚正义,不愿颠倒黑白、曲意逢迎,比如他遭受宫刑就是因为言别人所不敢言、从客观角度为李陵说了公道话。遭受宫刑后,痛苦自不待言,但司马迁为完成著史事业不曾屈服于现实,忍辱负重,始终昂头著史……足见其刚正不屈。由此,太史公能够站在公正化、人性化立场上审视少数民族历史,敢于在史书中用或直言或曲言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少数民族历史、汉匈政治活动等的看法,便也不令人意外了。
在《史记》民族书写中,司马迁倾注其中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承传千年,在潜移默化中渗入了中华各民族的集体意识,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52成为深深镌刻于民族心理上的印记,为以民族为题材的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情感基调,对于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形成无疑有着重大历史意义,从思想意识上促进了各民族走向协同互助、交流互鉴的和睦局面,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民族认同感的巩固与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访俄期间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即在其精神内核引领下应运而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期就处理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这一论题总结出的新经验、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休戚与共、同舟共济”[13],强调“用共赢思维取代零和思维才是合乎全人类长远利益的理性选择”[14],民族共同体概念亦坚持和合、合作、共奋进,以打造“心理契合点、情感共鸣点、利益结合点”[15]为内涵。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就对中华民族具备的命运共同体特质作了阐发:“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12]29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6],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被写入十九大报告。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中国的各项国家政策在文化上都具备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基础,中央传达的民族思想精华与《史记》民族书写中流露的民族共同体理念多有遥相呼应之处,《史记》中蕴含的诸多民族思想与现下中央倡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谋而合,可以说是当代民族主张的理论源起。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史记》民族书写中关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字记录了少数民族演变史以及民族关系发展史,记载了两汉时期尤其汉武帝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规定和努力,有益于从理论来源与实践经验两方面为我党制定民族政策、探索民族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贡献力量。在现下倡导、呼吁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共进的社会主义新时代,重温《史记》民族书写蕴含的天下一统、各民族平等、理性处理民族争端的民族思想与历史观,对其精华之处力求吸取,对其不当之处引以为戒,对于当代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与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The National Writing ofShiji(史记) and Sima Qian’s Community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DIAO Shenghu1, WANG Huan2
(1.Faculty of Art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2.School Office, China 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writing ofShiji(史记) or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shows that Sima Qian had initially produced and championed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at regards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world as one,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creation of ethnic biography written by ethnic minorities, the ethnic homology written by advocating the origin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Chinese ancestors, and the ethnic relations written by advocating the peaceful handling of ethnic disputes. Sima Qian’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was generated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comple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great unification pattern of the Han Dynasty,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family-country integration and harmony, and the author’s own historical will and character. This has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ethnic friendly family in ancient China and even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great unity and integrat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Shiji(史记); Sima Qian; national writing;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