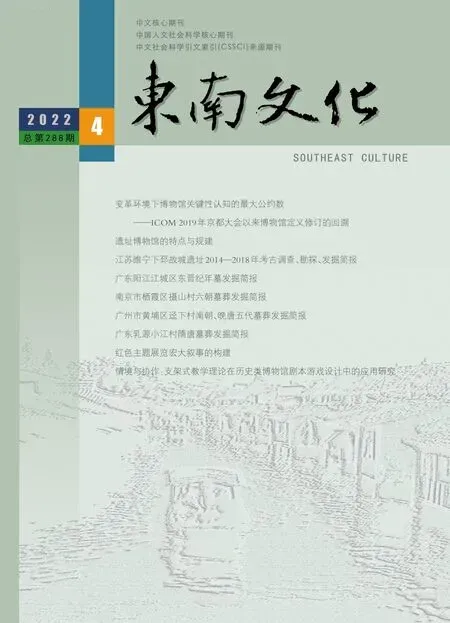红色主题展览宏大叙事的构建
张露胜
(山东博物馆 山东济南 250014)
内容提要:随着博物馆展览的叙事转向,宏大叙事理论在红色展览的策划中显得愈加重要。宏大叙事是将历史事件及实物史料串联成为具有因果联系的历史必然,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与认知。其理论旨在研究宏大叙事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和阐释原理,阐述其与历史真实“还原”与“超越”的辩证关系,探索叙事的故事性和整体性在红色展览实践中的应用,构建红色展览宏大叙事的理论框架。红色展览可采用宏大叙事,借助艺术化手段,将历史通过文字、图片和展品呈现出来,让历史的叙事融入观众的认知框架,从而为公众理解历史提供更为形象、直观的途径。
近年来,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众多红色主题展览(以下简称“红色展览”)相继推出,让更多珍贵的资料和史实为公众所了解,同时也发挥了“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1]的重要作用。与传统的以物为中心的展览不同,红色展览更强调展览的叙事性,将孤立的历史事件及实物史料串联成为具有必然因果联系的历史片段,是这一类展览的基本特征。历史事件不会自动成为展览展示的内容,需要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进行选择和阐释。红色展览的“叙事转向”是用史学理论的叙事方法描述一段历史,或以时间轴贯穿,或以类别统揽。这种跨学科的实践运用使得红色展览更具主体性与教育性,也为公众理解历史提供了更为形象、直观的途径。
叙事可以称为“讲故事”,它将特定的事件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被人们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2]。宏大叙事并非展览语境的原生概念,而是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一种历史的呈现方式,在人类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探索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然后再以必然性规律解释历史事件。宏大叙事与历史叙事又有明显的区别:宏大叙事旨在阐释历史,探索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再以规律解释历史事件;历史叙事旨在呈现历史,有主观意识地选择和阐释事件,叙事的方式多种多样。我国红色展览所体现的宏大叙事代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着重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审视历史的演变,通过宏大叙事类展览展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体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必然性。红色展览追求的宏大叙事几乎特指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流叙事”,由“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进而与中国共产党史相对接,描述从农民起义到工人运动、从落后挨打到民族觉醒,从“反帝反封建”、阶级民族双线交叉叙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红色展览根据主题大多选取上述体系的一个或几个部分,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军队建设、地区革命史、行业发展史等不同视角,阐述各个主体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其中整体叙事思路基本遵照宏大叙事的模式展开。
红色展览以宏大叙事为视角,综合运用文本、图片、实物、多媒体等方式形成合理的历史流线,达到历史与展示的统一。展览的宏大叙事逻辑与历史学的叙事有所区别,如何运用唯物史观从大量无序的偶然事件中选取符合主题的典型事件,构成符合因果必然的时间流线,是红色展览主题的核心要求,更是发挥其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作用的必然要求。
一、历史真实需要转化为宏大叙事
红色展览的组成元素需要选择和组合,事件与事件之间的阐述构成了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事件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历史叙事的目的或者说红色展览的目的就是建立重要事件之间的联系,组成历史发展的完整链条。历史的科学性以及展览的客观性体现在它完全依赖客观事实、反映历史真实事件,同时又强调阐释联系作用。
宏大叙事的展览方式具有主观能动性,是对历史真实的正确阐述。历史真实依据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标准建立了其客观性。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客观性,历史学才成为一门学科。然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基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共同认知,这些规律并不随人们的认知而改变,但作为展览叙事基础的历史文本却容易被多种因素影响。我们在历史认知过程中的研究对象并非是曾经发生过的、客观的历史事件本身,而是记录和叙述历史事件的文本,我们只有借助于历史叙述者的文本这一中介,才有可能触及历史的本体。可以这样认为,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认知是对历史叙述结果的研究,研究的是一种叙述的活动,不仅包括研究叙述的内容,而且包括研究叙述的活动本身[3]。因此,展览的宏大叙事所描述的是建立在历史本体上的历史叙述的“真”。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无限接近历史本源。红色展览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性的叙事活动,是探索历史真实的过程。
红色展览的叙事文本是对历史真实的“还原”与“超越”,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历史事件的主观阐释。展览策展人必须合理阐释材料,以便建构符合历史形象的认知,客观地反映历史发展进程。历史事件的记录存在着既太多又太少的两面性。一方面,一段时期的事件记录中会有很多事实,在以叙事方式再现某一历史进程时,不可能把全部事实都包括进来[4]。对事件的选择是红色展览叙事必须要做的事,排除与叙事目的无关的一些事实,保留能反映展览意图的重要事件。另一方面,当红色展览在努力重建历史上特定时期发生的事件时,事件与事件之间总会缺乏必要的、过渡性的重要事件来构成宏大叙事的因果链条,这就需要在叙事中对某一事件或系列事件进行适当地阐释。阐释就是用宏大叙事展现的一般规律去解释事件之间蕴含的必然联系,从而阐明这些事件何以发生。
历史事件本身并不能构成宏大叙事,需要使用阐释的方法将一个个看似孤立的事件串联成具有联系的故事,这些故事才能构成宏大叙事。事件的阐释具有明显的主观选择性,可以是悲剧性结局,也可以是喜剧性结局,但没有哪个历史事件本质上就是悲剧或喜剧,只有从某个特定角度或将其置于由一系列事件建构的语境中,才能看出其在这个语境中的悲喜剧因素。历史上某一事件从一个角度看是悲剧事件,而从另一角度看反而是喜剧事件。例如,西汉司马迁记录商末纣王帝辛沉湎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这一事件如果周族后裔站在周王灭商的立场上,明显是纣王昏庸无道,上天选择周武王治理天下并成就了周王朝,是一部史诗;如果站在商朝遗老的立场,帝辛严格祭祀、开疆拓土,但最终未能守住帝业,是一部明显的悲剧史;如果站在当代人视角,遵从朝代更替演变的规律,则认识到商周的朝代更替是生产力、阶级矛盾、统治制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无从验证历史事件究竟是什么样,历史叙事则取决于策展人根据哪种情节结构构造它们。同一个事件可以成为悲剧或喜剧故事的组成部分,是悲剧还是喜剧则取决于展览对情节结构的选择,取决于视角、立场,这也是构建红色展览宏大叙事的理论基础。
宏大叙事与历史真实是两个相互的概念。宏大叙事的素材来源于历史真实,并经过选择和阐释,但宏大叙事又超越历史真实,毕竟它强调历史事件的一般规律。红色展览是学术研究的成果体现,将红色展览阐释为展览文本的叙事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还原历史真实,但具备科学性和客观性。阐释的任务就是发现那些嵌在杂乱无章的事件中的真实故事,经过合理的组合,尽可能真实、完整、合乎逻辑地重述它们。
二、红色展览宏大叙事的故事性与整体性
红色展览需要将事件阐述为故事,将不同故事融入更大的历史进程中,用鲜活、感人的故事组成叙事的骨肉,形成历史发展的趋势。事件是客观的,而故事需要阐释和发现。宏大叙事需要用一个个故事去解释和证明更早的历史意义及规律。故事性叙述需要在宏大叙事的整体性中把握,即便是同一个事件也可以成为许多不同历史叙述的不同因素,在对这段历史叙述进行特定主题描写时,其故事的性质将决定这个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假如我们对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游行进行梳理和描述,这一事件可以是“五四运动”爆发的起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可以是法国巴黎“和平会议”(Paris Peace Conference)的结果,可以是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折的关键节点。显然,一个事件的故事性叙述需要整体考虑其故事因素的“功能”,以及在不同故事序列中的作用和地位。
在宏大叙事中构建某一段叙事,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组织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这一任务,包括“如何发生”“为什么以这种而非那种方式发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结局是怎样的”[5]。这些问题构成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将叙事塑造成一个有着前因后果的完整故事,这种叙事策略决定了宏大叙事如何展开。同时,“它的总体意义是什么”“它的主旨是什么”等指出了叙事的整体性问题,需要在展览的整体构建中揣摩这个典型事件所处的位置和所占的地位。红色展览中常有表现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面的内容,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常会选择“沂蒙红嫂”这样一组典型叙事,反映了水乳交融的军民鱼水情,代表了沂蒙山区女性群体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对于沂蒙红嫂中的明德英、祖秀莲、张淑贞等红嫂,红色展览一般通过图片、实物、影像构成各自的叙事,而这些独立的叙事由于其背景、时代、地域、事迹中的共性形成了以沂蒙红嫂为形象的历史叙事。沂蒙红嫂叙事发生在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后,此时日本侵略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了残酷扫荡,由于我方部队和政权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最终在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以沂蒙红嫂为代表的群众路线事件串联起抗日政权建立与抗战胜利两个事件,形成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因果链条,构成了一组完整的宏大叙事。沂蒙红嫂叙事的选择与阐释从史实上、逻辑上建立起抗日政权建立与抗战胜利两个事件的关联,体现了宏大叙事的整体性。
展览叙事作为一种讲故事的话语模式,需要将多种元素融入到展览的故事模式中,从而赋予红色展览所要表达的意义。博物馆、纪念馆的红色展览多以实物为基础,观众更关心的是展品究竟呈现了怎样的故事、被放入到怎样的叙事中、与周围的展品形成了怎样的历史序列。整个展览叙事流程既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也与历史真实有一定区别,需要结合两者的特征让宏大叙事中的故事更具科学性与真实性。整体性是展览叙事所要达到的目标,需要将大量不同时期、地点的展品与纷繁的图版、场景揉合,表达一个完整的核心观念。展览中的事件元素或文献资料如果只是被随意地摆放陈列,那么观众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也仅停留在表面,无法对事件的前后关联及其在主题中的意义获得系统性历史认知,观众只能获取过去的片段,而无法将展示的事件形成一种理解。如果说史书是将杂乱的过去转变为叙事,那么红色展览也必然要求将这些展品(即“过去的碎片”)转变为可以被观众理解的故事。在宏大叙事中,关于展览结构的整体与部分的策略,通常会采用转喻与提喻的方式。转喻的特征是将部分的阐述视作整体的代表,红色展览中表现抗战胜利的内容通常会选择展示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胜利成果,比如日本天皇裕仁(Hirohito)签订《终战诏书》的场景、日伪军向八路军投降的巨幅照片、大量缴获的武器等都被视作抗战胜利的标志,叙事的部分被赋予整体性的意义。提喻与转喻相反,是从整体引申到部分。如在红色展览初始便对整体叙事提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判断命题,然后通过展览呈现的一个个历史事件或事件组合去验证命题,并且这些历史事件在验证过程中也体现了其在宏大叙事中的作用。
红色展览就是将史料、展品、空间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将观众的关注点集中于展览本身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空间或几个毫无关联的展台,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将这些展示元素赋予相应的历史意义。这些挑选和阐释过的元素逐步被梳理出具备因果必然性的历史脉络,然后完整地呈现给观众,让更多的史学研究成果进入观众的视野,甚至可以推动公众层面对历史乃至当代的思索。红色展览的内容设计可以借鉴艺术创作的开放性,这样能够使展览有更大空间表达主题,更聚焦于表达的整体性和叙事故事的合理性。
三、红色展览的艺术性表达
如果将展览叙事的范畴扩展到艺术层面,这种叙事方式会赋予策展人更多的自主性,方便他们组织展品、事件和时间线。与历史学的方法不同,艺术是借助一些手段或媒介,通过塑造形象、营造氛围来反映现实、寄托情感的一种文化方式。它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更强调策展人的主观性,更强调展览带给观众的感受,将历史的故事通过当代的表达和展示,给人以当下的思考。以“人”的视角组织历史中的各个“点”,让那些孤立的展品和历史事件汇入展览的历史脉络,那么一个展览就不再是器物和事件的堆砌,而是一段完整的叙事,观众的参观就是重温历史,历史事件和展品证明了叙事的逻辑性。红色展览所展示的历史脉络代表了展览叙事的呈现方式,观众对这段历史脉络的接受和认同也代表了对展览策划的认可。
艺术化同时也是宏大叙事的表现手段。材料甄选和阐释是展览的准备阶段,若要让叙事更好地呈现在公众面前,需要用艺术手段组织材料并将其呈现出来。红色展览需要明确的主题色彩和宣传手段,转喻、提喻的手段常常能达到引导故事的发生和延伸、表达出展览本意的效果。关于同样的事件,不同的叙事策略能够达到不同的宣传效果,可通过故事化或英雄化的艺术手段发挥烘托氛围、弘扬主题的作用。红色展览除了叙事方式的艺术化,还需要展示方式的艺术化。如果文本叙述主题突出、符合逻辑,那么就需要将这些文本用艺术化的形式展示出来。场景复原、艺术品创作、多媒体展示、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等方式都可以将文本进行实物化呈现,让公众对描写的历史有更直观的、更深入的感受。这些呈现方式都要与叙事策略保持一致,包括展示项目的体量及其在整个展览中的比例、典型事件展示的位置及其在整体展线中节奏控制、多媒体设备的位置布点等方面。有些事件可能在文本中的内容不多,但对于展览的主题渲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需要用新手段、新形式扩大这一部分的展示面积,突出这一事件在展览中的地位,而不局限于叙事文本。比如很多涉及解放战争胜利内容的红色展览,常用群众支前事件揭示战争胜利的原因及正当性。相较于三大战役展出的图版资料和文物、实物,支前的内容似乎不像战场那样风云激荡、气魄雄伟,但是它代表了解放战争的群众基础,体现了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很多红色展览为了突出它的重要性,采用雕塑、场景、多媒体等方式表达,用大量图片讲述支前事件中涌现的英雄模范和感人事迹。
红色展览并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集主题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宣传展示。宏大叙事需要通过灵活的表达方式让更多公众接受,需要运用当代的技术手段提升宣传能力。如果以艺术视角审视展览叙事,除了能够还原历史的遗存与风采,还可以借史喻今、反思当下,让观众在观展之余对历史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6],“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要打造精品展陈,生动传播红色文化”[7]。这对如何用好宏大叙事、办好红色展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宏大叙事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与认识,红色展览是宏大叙事的呈现结果,展览正是用艺术手法将历史通过文字、图片和展品呈现出来,让历史规律融入观众的认知框架。通过创新红色展览的叙事方式,讲述红色文物承载的历史记忆,关注重大历史展览的时代表达,达到促进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构筑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