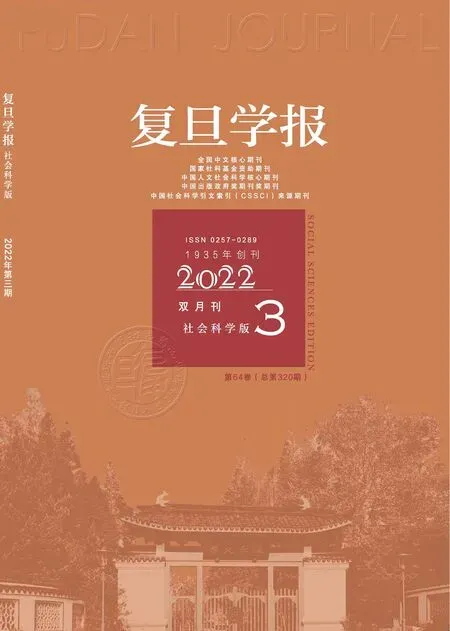南朝书札中山水书写的文献问题与文学评价
吴冠文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南朝书札向来是文学史上颇受人关注的一个领域,六朝或南朝文的各类选本中书札一般都是大宗。(1)史学界一般以宋、齐、梁、陈为“南朝”,本文从之。关于“六朝”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自古至今虽有差异,但宋代以还,除少数例外,一般均将“六朝“作为“汉魏”相对的晋至唐前的几个朝代。以许梿评选的《六朝文絜》为例(2)该书所选除一篇西晋陆机之作与几篇北朝作品,均为南朝宋以下人或由南入北作者所作。,该书收录最多的一体便是书,有十七篇,占全书近四分之一。其中,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萧纲《与萧临川书》和《与刘孝绰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宋元思书》和《与顾章书》、陈叔宝《与詹事江总书》、周弘让《复王少保书》,以及由南入北之王褒《与周弘让书》等作品山水描写的内容在后世广受赞扬。这类模山范水内容的南朝作品自唐以来一直受到论者的特别关注,逐渐被冠以山水尺牍、山水书札、山水小札、山水小品等称谓。细究起来,它们主要有两个方面特别吸引人。其一,变之前充满玄理色彩的山水书写的酷不入情为融情于景,或谓情景交融、情景相触。这类称扬在古今论述中在在皆是,毋需赘引。其二,变之前山水书写的冗长滞涩为素澹简练。如许梿评吴均《与顾章书》:“简澹高素,绝去饾饤艰涩之习。吾于六朝,心醉此种。”评吴均《与宋元思书》:“扫除浮艳,澹然无尘,如读靖节《桃花源记》、兴公《天台山赋》。此费长房缩地法,促长篇为短篇也。”(3)许梿:《六朝文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56、154页。无论是“简澹高素,绝去饾饤艰涩之习”,还是“促长篇为短篇”,着眼的都是这些书札文学表现上简练、素澹的风格。许梿之心醉六朝这类简澹高素之书,正与其《六朝文絜》一书推崇简练之文的宗旨相契,书名之“文絜”便来自《文心雕龙》“析辞尚简”(4)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24页。,崇尚遣词造句简练之作。
现代学者对这些书札的评价,大致类此。如钱锺书论吴均《与施从事书》《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三书:“按前此模山范水之文,惟马第伯《封禅仪记》、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二篇跳出,其他辞、赋、书、志,佳处偶遭,可惋在碎,复苦板滞。吴之三书与郦道元《水经注》中写景各节,轻倩之笔为刻画之词,实柳宗元以下游记之具体而微。”(5)钱锺书:《管锥编·全梁文卷六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6页。惋惜之前的辞、赋、书、志等涉及山水的作品虽然偶有佳处,却琐碎呆板,赞扬《水经注》和吴均三篇书札刻画山水轻倩灵活,正与许梿前后相承。
这些含有山水书写的南朝书札,是否果真如许梿、钱锺书等古今论者所言,均为绝去饾饤艰涩或琐碎板滞之习的简澹精炼之作?是否已由讲求实用性的书简演变成融情于景的纯文学美文?换言之,后人对南朝许多模山范水书札的美好印象,是否完全符合南朝相关文类的发展实际?若想回答这些问题,恐怕不能局限于单纯的文学领域,需从这些涉及山水的南朝书札的文献问题开始辨析。
一、 南朝书札中山水书写的文献问题
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南朝人作品,在商业印刷广泛流行之前的南北朝至唐五代,历经频仍的战乱和各种灾害,亡佚严重,不少现存南朝作品是通过唐代编撰的类书流传下来。早期类书常是这些现存作品后代重辑时的唯一来源,如历来享有盛誉的陶弘景、吴均等人的书札,由于诸人原集早就失传,现存这些文字全赖唐初欧阳询等修撰的《艺文类聚》(以下简称“《类聚》”)得以留存。作为分门别类辑录资料的《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等类书,所录内容都是按照特定主题摘录作品中最相关的文字,每则文字不但占原文篇幅比例往往很小,且多是跳着摘引的非连贯之文。对于依赖类书留存下来的唐前书札,若既未见流传有序的别集本存留,也无其他更详细的存录者,因此无从直接证明其文献原貌如何,便只能参照唐前同类作品的流传情况,推测其与原篇的大致关系。
一般来说,现存两部南朝编撰的总集《文选》和《玉台新咏》收录的诗、文都是完整篇幅。因此,同时被这两部总集和《类聚》等类书收录的现存作品,都适合用以考察类书收录的体例。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主要是书札,因此先从《文选》和《类聚》所录书札中择例说明。
首先看魏应璩的《与满公琰书》:
徒恨宴乐始酣,白日倾夕。骊驹就驾,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发。适欲遣书,会承来命。知诸君子,复有漳渠之会。西有伯阳之观,北有旷野之望。高榭翳朝云,文禽蔽绿水。沙场夷敞,清风肃穆。是泉台之乐也,得无流而不反乎?适有事务,须自经营。不获侍坐,良増悒悒。(6)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八《人部·游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08页。
与《文选》卷四十二《书》类所录相比,《类聚》所录应璩这段文字,仅占原文五分之二左右的篇幅。
再看丘迟的《与陈伯之书》,该书《类聚》仅录下面一段: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智,慕鸿鹤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展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慄,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鼔,感平生于畴昔。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亷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7)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五《人部·说》,第452页。
丘迟该书此段文字正是后人经常征引的一段,但仅占《文选》所录者五分之一多点。
不但将《文选》与《类聚》相比可以见出后者摘录原文的篇幅规模,将《类聚》摘录者与其他偶尔通过别集幸存下来的完篇相比,也可见到类似现象。如鲍照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根据其时所见鲍照集“文章皆有首尾,诗赋亦往往有自序自注”,认为鲍照集虽为后人重辑,但是“与六朝他集从类书采出者不同,殆因相传旧本,而稍为窜乱欤?”(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鲍参军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74页。集中《登大雷岸与妹书》一文,也见于《类聚》,但题目已简称作《与妹书》,所录文字非但存有不少异文,其篇幅也仅为别集所传版本原文的五分之二左右。(9)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七《人部·行旅》,第497~498页。按,《类聚》所引鲍文与鲍照别集本相比,尚有很多字词文字差异,但本文意不在校勘个别文字,故未予一一说明,仅在《类聚》未录文字下加下划线。为便于比较分析,现将别集本鲍书征引如下,有下划线者为类聚未录部分。
吾自发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无边,险径游历,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始以今日食时,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逾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去亲为客,如何如何!
向因涉顿,凭观川陆;遨神清渚,流睇方曛;东顾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隐心者久矣!
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淩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连。苎蒿攸积,菰芦所繁。栖波之鸟,水化之虫,智吞愚,强捕小,号噪惊聒,纷乎其中。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创古迄今,舳舻相接。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烟归八表,终为野尘。而是注集,长写不测,修灵浩荡,知其何故哉!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若潀洞所积,溪壑所射,鼓怒之所豗击,涌澓之所宕涤,则上穷荻浦,下至狶洲;南薄燕,北极雷淀,削长埤短,可数百里。其中腾波触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写泄万壑。轻烟不流,华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涟陇蹙。散涣长惊,电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飞岭复。回沫冠山,奔涛空谷。碪石为之摧碎,碕岸为之落。仰视大火,俯听波声,愁魄胁息,心惊慓矣!
至于繁化殊育,诡质怪章,则有江鹅、海鸭、鱼鲛、水虎之类,豚首、象鼻、芒须、针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俦,折甲、曲牙、逆鳞、返舌之属。掩沙涨,被草渚,浴雨排风,吹涝弄翮。
夕景欲沈,晓雾将合,孤鹤寒啸,游鸿远吟,樵苏一叹,舟子再泣。诚足悲忧,不可说也。风吹雷飙,夜戒前路。下弦内外,望达所届。
寒暑难适,汝专自慎。夙夜戒护,勿我为念。恐欲知之,聊书所睹。临塗草蹙,辞意不周。(10)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卷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3~85页。
如果单看《类聚》所录这些文字,是否也可加之以许梿所称“此费长房缩地法,促长篇为短篇也”?只不过促长篇为短篇者不一定是作者有意为之,原作很可能就是如同赋作一样漫漫铺写而成,只是类书编撰者依据时代文艺风气和个人偏好,强为之促长篇为短篇。如若不是鲍照该文大体内容有幸留存至今(11)按,根据古代书信格式,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严格意义上说还并非完篇,至少书札抬头和结尾题署均未留存。,论者对这篇书札很可能也会予以简絜一类评语。
鲍照该书最为近现代以来论者所称道的是其融情于景的表现特点。钱锺书《管锥编》推崇该书不但“鲍文第一”,也无愧“宋文第一”,并对书札中融情于景的语句极尽赞扬:
“思尽波涛,悲满潭壑”,按二句情景交融,《文心雕龙·物色》所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者欤。“波涛”取其流动,适契连绵起伏之“思”,……“潭壑”取其容量,堪受幽深广大之“悲”,……然波涛无极,言“尽”而实谓“思”亦不“尽”;潭壑难盈,言“满”则却谓“悲”竟能“满”。二语貌同心异,不可不察尔。“若潀洞所积,溪壑所射”至“樵苏一叹,舟子再泣”一节,按足抵郭璞《江赋》,更饶情韵。《文选》采郭赋而弃此篇,真贻红纱蒙眼之讥,尚非不收王羲之《兰亭集序》可比也。(12)钱锺书:《管锥编·全宋文卷四七》,第1313~1314页。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钱先生和很多论者击节赞赏的鲍书体现情景交融的语句甚至段落,《类聚》几乎尽数削落,如上引钱先生“若潀洞所积”以下一段,《类聚》所录文字仅存其十分之一左右。之所以删落这些文字,或许《类聚》编撰者对于后来论者日渐重视的融情于景的艺术特点尚无兴趣。且不论其删落的真实原因,这种删节行为本身难免令人怀疑:依赖早期类书留存下来的予人印象简洁的南朝其他书札,其原作是否也包括“漫无边际”铺叙的部分?
上述应璩、丘迟、鲍照三书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此处毋需一一罗列。由此已经可以确定,南朝文学不论是书札,还是其他文体文类,现存作品若未见其他更早的总集、别集收录,唐代类书是其唯一流传源头,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现存文字仅占该作品有限篇幅。假如现存的是模山范水的书札,其实现存篇幅很可能在原作中只是占很小比例的山水点衬,如丘迟《与陈伯之书》中“暮春三月”一节文字仅占原书篇幅两成——这两成的文字还并非尽是描摹山水。以此类推,后人交口称赞的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等,大概率也当作如是观,他们原书很可能另有衷旨,中心意旨非必山水。在原书文本中,这些模山范水的文字既非主体,后人所拟的“山水尺牍”“山水书札”“山水小札”“山水小品”的称呼,实属强为之名。这种强为之名看似将涉及山水的书信归为一类,方便后人把握和理解南朝山水文,实则顾此失彼。由于现存这些涉及山水的书札残篇几乎都出自刘宋中后期至齐梁,因此论者整体观照六朝山水文学史时,便会不加辨析,难免得出一些偏颇的结论,如前引许梿与钱锺书的评论等。我们不免疑惑,如果许梿、钱锺书所面对的不是由《类聚》存录下来的吴均三书断章,而是比现存文字多出三五倍的首尾具备的原文,这多出的文字中不但有其他叙事议论,还有类似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中承袭早期大赋按东西南北等方位平平铺写的景物,或者如谢灵运《山居赋》中巨细靡遗被后人评为涩滞的风景描写,他们是否会有不一样的阅读感受?
现代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文献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论述文献不足征的先唐文学更需要时时留意及此。南朝涉及山水书写的书札的这类文献问题辨析,其实不但关乎读者对其本身艺术价值的评价,也关乎我们对六朝山水文书写的整体认识。如果我们在论述六朝山水文时,晋和刘宋初期挑出的主要是孙绰《游天台山赋》、谢灵运《山居赋》一类中长篇作品,刘宋中后期以还罔顾沈约《郊园赋》、刘骏《山栖志》、庾信《小园赋》一类承续晋及宋初谢灵运《山居赋》等同类题材的长篇之作,专门撷取经过类书编撰者有意删节的残篇断章,如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等书札,通过比较这些案例得出的结论,必然会是六朝山水文的发展从晋、刘宋初期至齐梁时代发生了质的飞跃,从饾饤艰涩的山水长文突然进化至简澹高素的山水小品。
二、 南朝书札模山范水内容的程式化问题
论者之所以毫无保留赞扬南朝中后期具有模山范水内容的书札,除了未留意现存这类书札的残篇断章性质,还有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即在敦煌所存手抄本文献被发掘整理之前,人们几乎无由认识到,六朝人对山水的书写——尤其书札中的山水书写部分,实则从魏晋开始,便出现了程式化倾向,刘宋中后期以还的南朝山水观念的总体发展趋势,更使得这种程式化书写倾向在齐梁时代愈演愈烈。
日本学者小尾郊一在论述南朝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时,曾提到一个现象,即萧纲《答湘东王书》等南朝书札的自然描写,“大都位于每一篇‘书’的开头,很像现在的书简文开头的气候叙写”。译者邵毅平教授注释道:“作者这里所指的似乎是日本书信的书写习惯,因为日本的比较正式的书信在开头一般都应有气候叙写,称为‘时候のあいさつ’,而中国的书信则一般没有这种书写习惯。”(13)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译:《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7页。其实,我们现在书信中踪迹全无、日本尚保存的这种书札开头的气候叙写,正袭自我国中古时期的书信传统。这便是我国最晚西晋开始,在唐五代敦煌地区仍在流行的书仪。《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一书的作者和译者,无意中触及到了中日文学交流史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在古代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至今仍幸存一些我们已经失传并且陌生的文化遗产,书信开头的气候叙写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据现存唐前零散记载,古代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书札的重要性。东汉蔡邕曾云:“相见无期,惟是笔疏,可以当面。”(14)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文部·笔第六》,宋刻本配钞补。“笔疏”即书疏、书札。古代交通不便,亲朋好友一旦分别,经常是长久别离,互相传递信息和感情的书札在生活里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社交活跃、讲求繁文缛节的贵胄子弟和文人士大夫,书札更是日常交流必备。既然相见未有期,又受传统礼节影响,讲求雅致的古人就分外看重这类见字如晤面的社交书札,笺、札、书、启一类作品从抬头称谓到结尾落款,每个细节都草率不得。颜之推入北后所撰《颜氏家训》谓:“江南轻重,各有谓号,具诸书仪”(15)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二《风操第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6页。,说的就是南朝书札仪礼中对称谓的格外讲究。在书札本身的见字如面功能和交往礼仪的影响下,月仪、书仪一类作品应运而生。
或许与现今的教辅类材料无法流传久远相似,古代月仪、书仪类文字也很少长远流传的,在日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等书籍流行后,功用单一的月仪、书仪类作品更容易丧失其留存价值。因此可以理解,现存南朝书仪类作品,除了唐初类书《初学记》保存的一条王羲之《月仪书》“日往月来,元正首祚;太簇告辰,微阳始布;罄无不宜,和神养素”外,仅有西晋索靖《月仪帖》端赖法书幸存至今。现引其一组月仪,用以具体展示西晋书仪的基本面貌:
八月具书君白:南吕应化,中秋告凉,敬想令问,福履多宜。山川缅邈,信理希寡,谈面既阔,音问又疏。倾首延怀,无日不劳,想笃分好,不孤其勤。亦见信忆旧,裁因数字,行人彭彭,俱数相闻。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圣化光洽,明于博采、唯贤是务。足下以神龙之贾应景风之求,足陟天阁而德闻四海,允彼具瞻,副此群望,窃从草泽,慷慨增愿。君白。(16)严可均:《全晋文》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947页。
此帖无论是描绘时令气候,叙述友朋之间思念之怀,还是答书对朋友才行德令的赞扬和自谦之词,几乎都是文质彬彬的四、六字句。月仪、书仪发展到骈风美文盛行的齐梁,更讲求典雅优美。据史载,“沈诗任笔”之誉中的任昉,“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17)李延寿:《南史·任昉传》,《百衲本二十五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27页。从这则记载可见出,齐梁时人对月仪、书仪一类书札程式文字的热衷程度,也可见其撰作衷旨即在辞义极尽美丽。遗憾的是,《隋书·经籍志》所载数种南朝人所撰书仪均未能流传下来。
所幸,敦煌写本文献中现存一些书仪。因此契机,结合传世文献中涉及书仪的零散记载,敦煌学研究者对我国书仪传统作了细致的梳理和论述,关于先唐书仪周一良有过精到的分析:
所谓书仪,是写信的程式和范本,供人模仿和套用。这种性质的书,可以上溯到西晋著名书法家索靖。他留下了所书《月仪》,每月两通,以四字句为主。一通开始是带有标题性的“正月具书,君白”,接着结合月份说一些有关气候的寒暄话,再进入正文,如阔别叙旧之类,末尾又以“君白”结束。君字是用来代替人名的。另一通的性质,则是对前者的复信。……南北朝时,内容比月仪更广泛的书仪流行起来。……据《隋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所载,属于书仪性质的著作有十一种……值得注意的是,除《僧家书仪》之外,十种之中,出于王谢高门之手的书仪占五种。……大约王弘、王俭等人的书札和礼法,被当时士流所推重,成为模仿的典范。掌握他们写信的风格体裁,是士族高门文化修养的内容。(18)周一良:《书仪源流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这段梳理文字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至少从西晋起,书札撰写便已有程式范本可循,而且程式范本按月编排,每通去信都有抬头、时令气候相关的寒暄语、阔别叙旧一类正文和结尾组成;二是《隋书·经籍志》所载书仪类著作多有出自(或托名)王谢高门之手者,士族高门的书札范式或许格外受人推崇。
敦煌写本文献中现存一种唐朝前期书仪,鉴于唐朝前期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承续性,这一种幸存的唐人书仪或可供我们推测南朝人书仪大概情况。赵和平予以考证:
据斯六一八〇及写卷内容,我们定名为《朋友书仪》。这种书仪,除“十二月相辩文”外,其内容与唐人《月仪帖》相近,内容却远比之丰富。……据我们的初步研究,《朋友书仪》的撰写年代在唐朝前期,作者可能是高宗朝宰相许敬宗。……《朋友书仪》的主要特点是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写景、抒情的文字优美,对仗工整,用典贴切。不少书札都可以和齐梁时的丘迟、吴均、陶弘景等人的书札相媲美。(19)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代前言),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11~12、52页。
这种敦煌写本《朋友书仪》初衷是给“远在边陲的游子写给内地的书札”(20)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代前言),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11~12、52页。作范例,由于唐代边陲地理位置与南朝京都建康等地相距甚远,其山川物候与江南江北都存在很大差异,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能从唐代边陲书仪中看出它们与索靖、王羲之月仪,以及南朝书札之间的可类比之处。
赵和平提出:“《朋友书仪》的信札,酷似齐梁时的名篇,三月中说‘娇莺百转,旅客羞闻,戏鸟游林,羁宾赧见;’与丘迟《与陈伯之书》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仪中三月写景的另一段文字是‘方今游蜂绕树,戏蝶营林,翠柳摇风,相(杨)桃影烂’,写暮春之景清新可读。”现存文献中未见南朝书仪,但是由唐朝前期编撰的同类书仪现存面貌来看,它们与南朝友朋书札具有几乎一一对应的可比之处。结构上均是山川物候描绘+叙今昔之情+想象对方现况+盼望对方念旧回信,具体环节常有清晰可辨的抬头部分引领下文,如想象对方现况环节多用“想”字开头;遣词造句都是四六骈文,用事用典较多,“对仗工整,文辞雅丽,情景交融”。(21)吴丽娱:《敦煌书仪与礼法》,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0页。如《朋友书仪·九月季秋》一则开篇“九月季秋(上旬云渐冷,中旬云已冷,下旬云极冷。无射),飃飃落叶,犹思万里之林;眇眇秋黄,折于江南之客”。(22)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十二月相辩文》,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92~93、93~95页。与简文帝萧纲《与萧临川书》“零雨送秋,轻寒迎节,江枫晓落,林叶初黄”、《答湘东王书》“暮春美景,风云韶丽,兰叶堪把,沂川可浴”等开篇均属于一个模式,简文帝两书在这样的山川物候描写后面,所接着写的对方景况、自己景况,也均与《朋友书札》同构。
现将敦煌《朋友书仪》十月孟冬这则的部分文字与梁简文帝萧纲《与刘孝绰书》对读,以供具体领会两者的同构之处:
十月孟冬(上旬云薄寒,中旬云渐寒,下旬云已寒。应钟)丰州地多沙碛,灵武境足风尘。黄河带九曲之源,三堡接斜川之岭。边城汉月,切长乐之行人;塞外风尘,伤金河之役士。遥看柳谷,结念思而榆多;眺望石门,悲伤心于宁远。……想上官逍遥林苑,转月扇而进凉;散诞风楼,摇青漂之歇衽。……今因去信,附塞外之行书;如有回人,往边城之寸札。(23)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十二月相辩文》,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92~93、93~95页。
执别灞浐,嗣音阻阔。合璧不停,旋灰屡徙。玉霜夜下,旅雁晨飞。想凉燠得宜,时候无爽。既官寺务烦,簿领殷凑。等张释之条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龙之才本传,灵蛇之誉自高。颇得暇逸於篇章,从容於文讽。顷拥旄西迈,载离寒暑。晓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鸟归林,悬孤颿而未息。足使边心愤薄,乡思邅回。但离阔已久,载劳寤寐。伫闻还驿,以慰相思。(24)许梿:《六朝文絜》,第142页。
[作者简介]文帝这篇书札的大致结构是山川物候+刘孝绰景况+自己景况+盼望回信。比较之下,这则敦煌书仪篇幅很长,除了结尾盼望对方答书与一般南朝书札一样,只有短短几句话,其他部分无论是描绘山川物候、叙旧致意(敦煌书札一般都是相思之情),还是想象对方景况,都是不厌其烦罗列各种富有浓情厚意的华辞丽藻,目的不外乎为使用书札的人提供更多的文字选项。由这些唐代西北边隅流行的书仪文字,我们不难想象《隋书·经籍志》所载数种南朝书仪文字当是紧紧贴合长江南北的节物风光。
书札仪轨对于作者撰作的影响深远。王褒曾是南朝梁重臣,被俘入北后心怀江南,在南归希望破灭后,曾在长安写信给故人周弘让,托南朝使者带回。这封写于长安的《与周弘让书》在处理山川物候风壤时,王褒写道:“舒惨殊方,炎凉异节。木皮春厚,桂树冬荣。”(25)许梿:《六朝文絜》,第174页。由南入北之人不惯北方寒冷气候,作品中偏好表现平生少经的北方严冬景象。(26)庾信入北后也曾写过“木皮三寸厚”,王褒、庾信作品中的木皮、桂树均用汉代晁错《守边备塞议》“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和曹植《朔风诗》“桂树冬荣”典故。庾信:《和张侍中述怀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71页。在北方的王褒仍然沿袭之前在南朝熟悉的书仪模式,《与周弘让书》现存文字大致依然可见山川物候描绘+对方现状+自己现状的结构。
由上文论及的魏晋至唐五代的书仪和书札实例均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很长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在六朝文化高度发达的南方,还是南北文化融合之际和融合之后的北方,友朋往来书信开头都一度曾有兼具情景的山川物候叙写传统。唐代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开头“近腊月下,景气和畅”(27)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029页。等语,或也是书仪的痕迹留存。前述《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一书所提的日本书信保留至今的“气候叙写”开篇,正承袭自我国中古时期的书仪传统。(28)周一良先生的相关考述可以证明我们中古时期书仪无远弗届的影响:“早在唐代,已有书仪传入日本。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约成于宽平三年,即唐昭宗大顺二年,891)仪注类著录了传到日本的书仪达十种之多。刘宋的鲍昭《书仪》和谢朏的《书笔仪》大约由于不大适用,列在最后。……在藤原佐世之前,日本正仓院还藏有相传为奈良时期光明皇后(701~706)手写的《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一卷,也是从中国传入的书。此书包括三十六组书札,每组一题,如雪寒唤知故饮书、贺知故得官书、就知故乞粟麦书、呼知故游学书、同学从征不得执别与书等,皆附有答书。体裁以四字句为主,先结合季节寒暄,再进入本题。这种有往有来的体裁,与索靖《月仪》相同,但不是以月为题,而是涉及各个方面。”见周一良:《书仪源流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因此,南朝书札,尤其是出自贵胄和士人之手者,很多其实如同古人亦步亦趋模写的拟乐府,是按照特定的结构和遣词造句范例“填词”般填出来的。其中模山范水的文字,尤其是开头反映山川风土景象的部分,不能忽略书札的实用性质,毫无保留地称赞为情景交融或融情于景的书写。(29)如赵树功的《中国尺牍文学史》论萧纲《答湘东王书》“暮春美景,风云韶丽,兰叶堪把,沂川可浴”,“开篇16个字,……情深者情感幻象的自然流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45页),论萧纲《与萧临川书》“零雨送秋,轻寒迎节,江枫晓落,林叶初黄”,“神来之笔……造语新绮,感觉细腻。”(第145页)任昉“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虽说明当时有些人制作的月仪书仪有超出常人之处,但任昉月仪的“辞义甚美”,却难掩这样一个事实,即月仪一类文字的制作,基本都是闭门造车的文字游戏,我们很难期望八九岁的孩子已能融合需要生命历练体悟的情感到每月的物候景物中去。
若结合书札程式化问题和类书断章选录的文献特性,来看待现存依靠类书流传下来的南朝书札,我们可以辨析残章断篇文字的大致结构。参照现存唐朝前期的书仪样式,并根据现存这些书札共有结构和遣词造句模式抽绎出的大致“公式”,可以见出,除了开头的山川物候叙写,书札中的山水叙写还有一处也是书仪本有的范式,即中间叙旧情忆旧游时涉及的山水叙写。典型的如南朝齐刘善明致友人崔祖思书,其中间一段有云:
昔时之游,于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负杖秋涧,逐清风于林杪,追素月于园垂。(30)严可均:《全齐文》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893页。
这类忆旧游叙旧情的书札格式,可能比书札开头的气候叙写定型更早,因为现存汉魏之际曹丕等人书信中便已经常出现类似的段落,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清风夜起,悲笳微吟。(31)吕延济等:《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卷四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645~646页。
南朝书札中间这类忆念旧日游从的自然描写,虽也属于书仪范式之一,但往往比开头的气候叙写更带感情色彩。作者对此应该已有明确意识。如丘迟《与陈伯之书》本旨在于劝降,他在陈情说理之中特地加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几句写景文字,目的便是想用对方曾经留恋的风景触动对方,从而帮衬中心主旨的实现。
对南朝书札的开篇和中间叙旧部分的山水描写我们已有所了解:书札开头的山川风土景象多是程式化的套写,实无法证明其中是否有即景生情的自然情感流露;书札中间忆旧时的山水叙写虽较开头部分易融入感情,但也是书札一代代承续发展的范式之一。那么,南朝书札中是否存在其他非书仪范式可规拟的山水描写呢?揆诸南朝书札实际,除了开头山川物候叙写和中间忆旧游部分,还有两类目前看来并无书仪范式可依规的山水书写。
一类是书札中的行游山水叙写,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正如很多论者已经指出的,书札中这样大规模地书写山水,鲍照是第一人。该文虽是书札,却对铺叙山水的赋体多有继承,在南朝是创体,也是另类。现存文献中未见南朝人予以置评。正如上文所述,《艺文类聚》对该书仅录存其五分之二左右,将其按照不同方位铺陈和带有浓厚主观感情色彩的山水书写尽数削落,因为与其他南朝书札相比,这些都属于鲍照特立独行之处,尤其是融一己之情于山水的写作,即使在《类聚》编撰的时代也尚未获得尊崇。
另一类是陶弘景、吴均等人有隐逸之风的书札山水书写,由唐代山水文的发展实际来看,它们才是真正有持续价值和意义的所在。
三、 南朝书札中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山水书写
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现存文字,当类似丘迟《与陈伯之书》中占全书篇幅比例很小的写江南春景一节,是书札中的具体声色点衬,他们写信的主旨不在山水。但是与丘迟劝降书有别的是,陶弘景是有寻山之志者,其书被《类聚》收录在“隐逸”类,本旨大概是陈述隐逸之志或隐逸之乐。吴均其人虽非必如陶一样志在寻山,但其三书所写山水却不外乎表现山水逸趣。《与顾章书》之言“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山谷所资,于斯已办。仁智所乐,岂徒语哉”(32)许梿:《六朝文絜》,第155页。,《与施从事书》谓山水“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33)严可均:《全梁文》卷六十,第3305页。,《与宋元思书》之语“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34)许梿:《六朝文絜》,第153页。,均可见出“素重幽居”(35)许梿:《六朝文絜》,第155页。的吴均沉浸于江南山水并以山水本真之美散怀息心的逸兴,这正是他接续晋及刘宋前期山水文之处。
毋庸讳言,不论是陶弘景书札的山水点衬文字,还是段落较长的吴均三书山水书写,其中心意旨虽然非如地志类作品在于客观描述山水,流传下来的文字也不一定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一样具有比较完整的篇幅,但这类精美的模山范水断章对后世山水文学的积极影响却是无可置疑切实存在的。
统观南朝,除了陶弘景、刘骏、吴均一类有隐逸或山居之志者,仍然对寻山陟岭葆有热情,大体而言自刘宋中后期开始,士夫阶层稀见谢灵运那样“杖策孤征,入涧水涉,登岭山行。陵顶不息,穷泉不停。栉风沐雨,犯露乘星”(36)谢灵运:《山居赋》,顾少柏:《谢灵运集校注》,台湾:里仁书局,2004年,第459页。的山水爱好者。史书所载王羲之去官后遍游东中诸郡名山沧海,孔淳之在山水中穷尽幽峻乃至旬日忘归,宗炳遍览庐、衡、荆、巫,至老意犹未尽等等乐此不疲的行游现象,在齐梁时代也很少见到。很明显,随着魏晋以来玄、佛清谈之风的消歇和世家大族的整体衰落,南朝前期和后期人们的山水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魏晋至刘宋早期,无论是玄、佛之学,还是对山水的欣赏和晤对,几乎都为文化精英(主要由名士贵胄和少数精英僧道之徒组成)所专有。(37)值得思考的是,不但以玄学为基础的清谈大致止于谢灵运,与玄学之兴相伴随的山水之恋也似乎在谢灵运逝后发生了很大变化。陈寅恪先生曾言: “《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溯原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4页。而且,文化精英不但有玄、佛等教养可沉浸,有些还具备夹山傍水的庄园别业等物质保障(慧远等释道之徒也有东林寺周边的庐山可尽兴游玩)。即使无世家大族王谢那样的庄园别业地产,如宗炳等人,也还是有余裕余力畅游天下。文化和物质上的双重保障使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庄园别业中悠游容与,或者载欣载奔地归山归田,诗意地栖居于故山故园中,或者无所牵挂地畅游天下山水,这些生活阅历均赋予他们足够的能力写出视野高远阔大的山水作品。
南朝自刘宋中后期开始则不然,生存的环境日渐局促,留下山水文字的,除了对山水之游已逐渐丧失实际兴趣的皇子王孙,“居家之治,上漏下湿”(38)鲍照:《请假启》,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卷二,第80页。,必须躬自修缮的鲍照一类寒士自不用说已无暇晤对山水,即使登过高位的沈约、庾信等人,有些虽在荣宠时拥有京都建康郊区的园墅,但这类依山傍水的郊园显然无法望前代王谢等家族夹山傍湖的大庄园之向背。沈约《郊居赋》、庾信《小园赋》等作品形容自己园墅的“陋宇”、“蓬荜”(39)严可均:《全梁文》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099页。或“数亩敝庐”(40)许梿:《六朝文絜》,第35页。虽有自谦成分,但从具体规模上看,他们的京郊别墅规模上与前代世家大族的地产确实无法相比(41)李傲寒、陈引驰:《都城的延伸与分隔: 齐梁诗赋中的京郊别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谢灵运《山居赋》一类体裁题材作品,发展到沈约、庾信,已是《郊居赋》和《小园赋》,山水文学的发展变化从这些作品的题名变化中也可见一斑。
在玄、佛等文化思想背景和庄园地产等发生较大变化的同时,刘宋中后期开始的南朝文士们对待山水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均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了地志撰著者,大部分刘宋中后期的山水文作者只对京郊的园墅或寺庙道馆内外的山水津津乐道。不但孙绰对天台山和顾恺之对云台山一类的山水玄想开始稀见,晋宋之际宗炳等人那样有意畅游天下山水者,也是不复听闻。梁代萧恭曾有言:
下官历观时人,多有不好欢兴,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劳神苦思,竟不成名。岂如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42)李延寿:《南史·梁宗室下·南平元襄王伟传附萧恭传》,《百衲本二十五史》,第1011页。
萧恭所谓“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恐怕无意间揭露了齐梁时间“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43)颜之推:《颜氏家训》卷四《涉务第十一》,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295页。的贵胄文士们创作的一种风气。这种未曾亲自登山陟岭,多靠阅读累积的知识写出的山水,只能是“胸中丘壑”,也即萧统所津津乐道的:“不出户庭,触地丘壑。天游不能隐,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镜,一见何必胜于传闻。松坞杏林,知之恐有逾吾就。”(44)萧统:《答晋安王书》,严可均:《全梁文》,第3064页。
之前身体力行出游时欣赏的山水,到齐梁时代许多作者笔下,只剩下依傍园墅的京城郊区山水和郡斋目力眺望所能及的山水。后人在诠释《文心雕龙》“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45)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第六》,第65页。时,总是强调宋初开始兴盛的山水书写,而轻忽了一个文学发展趋势,即除了晋宋之际陶渊明、慧远等庐山诸道人、宗炳和谢灵运等人的山水之作,刘宋中后期开始的山水书写开始出现脱离实际行游体验,演变成文字游戏的倾向。
另外,在普遍“倦游”的情绪笼罩下,仕宦行旅中所历的山水几乎都着了作者悲凄的感情色彩,京都以外的山水似乎成了畏途,多了几分可怖可畏之处。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的“险径游历”、“思尽波涛,悲满潭壑”便是这种山水观的典型写照,山水仿佛不再是独立的审美存在,而被赋予浓重的主观情感色彩。
这种主观情感笼罩山水自然本真之美的作品,在真心崇尚自然的人士看来,自然是不会有兴趣的。身历宋齐梁三代的道教徒陶弘景晚年所作的《答谢中书书》(46)陈振鹏、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所收《答谢中书书》魏明安先生鉴赏中提及:“谢微任中书舍人的后限是公元526年,任中书郎在公元532年,都在陶弘景七十岁以后。故此篇当为陶弘景晚年所作。”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682页。,在具体描绘了山川之美后,论道:“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47)陶弘景:《答谢中书书》,《艺文类聚》卷三十七《人部·隐逸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69页。在褒扬谢灵运山水创作的同时,陶弘景对刘宋中后期以还一百多年间其他的山水书写似乎视而不见。因为山水不受世俗控制的本真之美已经被特定境况下难免狭隘偏执的情感熏染,山水景物被书写的张力越来越小。《艺文类聚》摘录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时尽削后人推崇备至的“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等语,或许正见出唐初之人尚无法接受这类主观色彩浓厚的山水书写。陶弘景对刘宋中后期至梁代山水书写的评价,并非纯属虚妄之言。如上文所述,刘宋中后期至梁代的山水观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由于玄学的消歇,魏晋至刘宋初精英人士登山陟岭穷尽山水之美的浓厚兴趣,自刘宋中后期开始逐渐寡淡。山水书写或者沦为文字堆砌的游戏,或者以胸中丘壑代替真实山水,沉迷书中“天游”,或者满足于京城依傍郊园别墅或郡斋附近山水,如建康的钟山附近。
以刘宋中后期以还的山水观念和山水创作趋势为背景,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三书等书札中的山水书写的可贵之处。只有性爱山水、且具备投身山水的行动力之主体,才能真正发现与自己相看两不厌的山水本真之美,并顺应文学语言发展实际,“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48)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第65页。,费心经营,将山水之美贴切而富有个性地表现出来。他们与六朝地志一起,成为唐代之后游记等类型崇尚简洁素澹的山水文学汲取营养的源泉。相比较而言,萧纲等人不少友朋书札中的山水书写,多是步趋模写特定书仪范式,虽不乏辞义甚美之作,却难免入于五四新文学时期陈独秀所批评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之流,“失抒情写实之旨也”。(49)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