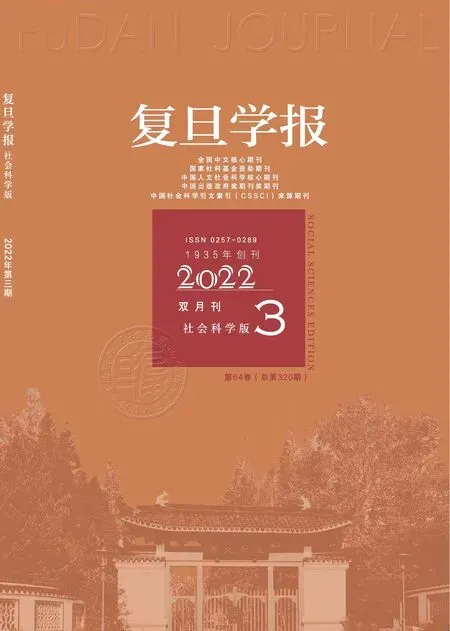《女狱花》与近代日本佛教东来
马勤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1904年问世的《女狱花》,是晚清小说界“描写当时女子的不幸与苦痛生活”(1)阿英:《晚清小说史》,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55页。的代表著作,也是近代意义上第一部女性小说(2)参见马勤勤:《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9页。。它在当时影响很大,不仅与《女界钟》享有同等声名(3)《(近世欧美)豪杰之细君》,《女子世界》第1~8期,1904年1月~8月。,还被冯自由列为“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4)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见《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492页。。究其原因,自然是《女狱花》中倡女权、兴女学的先锋思想,对此,前人已多有论及;然而,由于作者王妙如生平资料的缺失,相关讨论只能更多着眼于小说的文本细节和人物塑造,借此发掘其女性角色、女性意识和女学书写的特色等(5)关于《女狱花》,代表性的研究有:魏文哲:《〈女狱花〉与〈女娲石〉:晚清激进女权主义文本》(《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吴宇娟:《论〈女狱花〉中呈现的晚清女学、女权》(《岭东学报》2004年第16期)、蔡佩育:《〈女狱花〉的女性书写及其文化意涵》(《弘光学报》第65期,2011年12月)、黄锦珠:《妇女本位:晚清(1840~1911)三部女作者小说的发声位置》(《中国文学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第53~77页)。。这些研究对理解《女狱花》虽有助益,但无法知人论世,就很难彻底打开文本,终究会有遗憾。
事实上,《女狱花》中还蕴含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文本细节,迄今未受到学界充分注意(6)只有吴宇娟指出王妙如“企图以宗教家的热忱处世”,她以“佛婢”“普救主”来称呼许平权,是“欲效法诸佛菩萨渡众的决心”,但文章落脚点在“虽然王妙如崇奉宗教,但却反对一味的迷信”,有点可惜。参见《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东海大学中文学报》第19期,2007年7月。。本文从王妙如的丈夫罗景仁入手,考述其生平,发现他曾在日本东本愿寺创办的杭州日文学堂学习。这一特殊的求学经历,揭示出《女狱花》与明治日本在华传教事业之间的隐蔽关联。如此,《女狱花》中蕴含的大量佛教文本细节得以“解码”,展示出了一幅女权与女学、革命与救世、西学与佛学等诸多面向相互纠缠又暧昧不清的复杂图景,进而揭开日本佛教对近代中国思想影响的一脉潜流。
一、 罗景仁与《女狱花》的生成
《女狱花》又名《红闺泪》《闺阁豪杰谈》,共十二回,署“西湖女士王妙如”著,为光绪甲辰刊本。目前,学界对王妙如生平的了解,基本源于《女狱花》篇末所附“序跋”(7)西湖女士王妙如:《女狱花》,光绪甲辰刊本,页六九。注:本文所引《女狱花》文本俱出于此,下文不再出注。。此文出自王妙如丈夫罗景仁之手,故对其文学创作及思想倾向均有记录。据罗景仁记载,王妙如名保福,泉(钱)塘人,生于1878年前后,大约卒于1904年(8)罗景仁“序跋”提及王妙如“年二十三匹予为偶”,“乃结缡未足四年,而竟溘然长逝矣”。“序跋”写于“光绪甲辰仲春”,即1904年农历二月,以此推导,可知王妙如出生于1878年前后。。她自幼聪慧,且嗜书史,除小说《女狱花》外,尚有《小桃源》传奇和《唱和集》诗词,惜未传世。二十三岁嫁同乡罗景仁,夫妻感情十分融洽。王妙如不仅博学多才,而且非常关心现实,尤其热心于妇女解放事业;曾自述有感于“女界黑暗已至极点”,故而写作小说,欲以“秃笔残墨为棒喝之具”来进行女界“革命”之事。小说《女狱花》的写作也得到了丈夫的大力支持,王妙如每作一回,罗景仁即加批点。1904年前后,王妙如去世,罗景仁将《女狱花》自费出版,并亲自为小说撰写跋文,以志怀念。
罗景仁的跋文,是我们目前了解王妙如生平经历的全部资料。然而,关于他本人的生平经历,却向来不为人知。经细致的搜集与考证,笔者已基本掌握其情况。他本名罗嗣宗,景仁是其字(9)浙江优贡宣统已酉元年(1909)“来壮涛”条下“受业师”中,“罗景仁夫子,印嗣宗,本省日文学堂毕业生,法政学堂教习”,见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378)》,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又,《杭州市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库职员》表中,经理“罗嗣宗”下列“别号”为“景仁”,见《杭州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季刊》第1期,1936年。,浙江钱塘人,1898年应钱塘县试、杭州府试,均名列前茅(10)参见《杭试再志》,《申报》1898年4月9日;《杭试尾声》,《申报》1898年5月4日。,后入杭州日文学堂学习。关于罗景仁何年进入日文学堂又在何时毕业,具体时间不详,但略可推之。杭州日文学堂开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3月1日,分为二科,普通学科“以三周年为限”,专门学科“以四周年为限”,专门学科需由普通学科升补,“有成效方准升入”(11)《杭城日文学堂章程》,《宗报》1899年2月15日。。不久,杭州日文学堂堂长伊藤贤道受邀为浙江武备学堂讲授理化学(普通学)(12)「杭州日文學堂の發展」,[日]高西贤正编纂:『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上海:東本願寺上海别院,1937年,第85页。,罗景仁则与另外几位学堂学生徐青甫、陈福民、袁麟伯担任翻译(13)浙江武备学堂1907年毕业生傅墨正回忆:“在武的方面创办了一个浙江武备学堂……派给(徐)青甫、陈福民、袁麟伯、罗景仁等人为翻译,尽教授算术、地理、日文等。”见傅墨正:《辛亥革命前浙江新军的培养和发展》,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辛亥革命亲历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58页。。查《杭城日文学堂学友姓名年龄及住处》,在“第一年前期前三个月学友”中,已可见徐青甫(徐鼎)、陈福民(身)的名字(14)见『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第314页。;因之,罗景仁当与他们大体同期,应是杭州日文学堂最早的一批学生。浙江武备学堂开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农历三月,1907年5月彻底关闭(15)参见胡梦颖、郝飞:《清末浙江武备学堂聘请日本军事教习之若干问题探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农历二月,罗景仁又入浙江法政学堂担任日文教习,“出身”一栏已明确标注“日文学堂毕业”(16)《浙省各学堂教员姓名籍贯出身及担任年月一览表(宣统二年下学期)》,《浙江教育官报》第90期,1911年(宣统三年七月)。。辛亥革命期间,他还任教于蚕学馆(17)杭州市教育委员会编:《杭州教育志(1028~1949)》,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55页。和浙江陆军小学堂(18)周亚卫在《光复会见闻杂忆》中提到:“浙江陆军小学堂也是参与光复的一支力量……教员如韩澄、罗嗣宗……都是进步分子。”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631页。。20世纪20年代以后,罗景仁转到金融领域,协助他在杭州日文学堂的老同学及浙江武备学堂的旧同事徐青甫创办了浙江地方银行(19)洪品成:《浙江地方银行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39页。,并作《浙江省之财政(附表)》《浙江省之债券(附表)》《杭州之钱庄(附表)》等多篇经济文论(20)以上均见《杭州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季刊》,1936年第1期。;此外,尚有若干诗词作品发表于报刊,其中有不少长篇歌行(21)如《武劼斋先生六旬双庆诗以寿之》,《嘤求》第4期,1928年3月。;一些集句诗对李白、杜甫诗信手拈来(22)如“集杜甫句”《春日自遣》、“集李白句”《春游》、“集李杜句”《暮春即事》,均见《嘤求》第4期,1928年3月。,足见其在文学方面也颇有才华与建树。
现存《女狱花》为光绪甲辰刊本。小说卷首《叶女士序》署“光绪甲辰三月既望”、卷尾罗景仁《跋》署“光绪甲辰仲春”,可知其出版时间至少应该在1904年的农历三月以后。然而笔者发现,在1904年1月出版于上海的《女子世界》中,却有一则这样的广告:
都近世豪杰之细君而传之,美德、社交、爱情、热血,迸露纸上。《女界钟》耶?《女狱花》耶?……亦可以生女国民之气。(23)《(近世欧美)豪杰之细君》,《女子世界》第1~8期,1904年1月~8月。
由广告可知,至晚在1904年1月,《女狱花》已相当流行,不仅可与声名赫赫的《女界钟》并驾齐驱,同时还被《女子世界》的主持者丁初我用来当作其新书的广告宣传,此为《女狱花》的写作时间下限。
《女狱花》写作时间的上限,可寻其文本内证。第三回,沙雪梅说“我闻去年已有上谕改试策论”,此事当指1901年8月29日谕以策论取士、废除八股之事(24)《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谕以策论试士禁用八股文程式》,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页。又,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起于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但并未真正实行。变法失败后,科举考试恢复八股取士,至“庚子事变”之后才复戊戌之新政,推行“辛丑变法”。。又,第三回提及沙雪梅阅读《斯宾塞女权篇》之事,此书为马君武翻译,1902年11月由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再,第六回写到文洞仁房中四幅“西洋女杰”照片,即美利莱恩、奈经慨庐、独罗瑟女士、苏泰流夫人。经过比对,笔者发现此四位女杰均来自《世界十女杰》(25)尽管《世界十女杰》宣称“是书以《世界十二女杰》为蓝本”,但《女狱花》中所引4位女杰,除“苏泰流夫人”在《世界十二女杰》中也出现了,另外3位只出现在《世界十女杰》。见《例言》,《世界十女杰》,“序”,第1页,1903年。。该书大概译自1902年10月,出版时间必定晚于1903年2月(26)《世界十女杰》的《例言》称“此书于去年十月中译竢,而近见广告中知《世界十二女杰》一书已出”,而《世界十二女杰》出版于1903年2月,故《世界十女杰》的出版时间必定晚于此书。。另据周作人记载,他于1903年4月9日收到鲁迅“日本初五日函”,内有托人带来的《世界十女杰》一册(27)鲁迅博物馆编:《周作人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83~384页。。《世界十女杰》在晚清风靡一时,曾以各式文学体裁被反复地书写、言说(28)关于《世界十女杰》的研究,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晚清女报中的西方女杰——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中国之旅》,《文史哲》2012年第4期。。王妙如显然读过《世界十女杰》,故而在《女狱花》中特别提及并引为典范。
据此,《女狱花》大约写于1903年前后,按照时间推算,罗景仁在杭州日文学堂已经学习了几年时间,并在浙江武备学堂担当翻译,日文水平堪称日文学堂生之翘楚。此时的王妙如,也与丈夫在一起生活了两三年,夫妻感情融洽。可以说,罗景仁对《女狱花》的创作与出版过程参与度极高,是小说文本生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然而,这一点向来不为学界所重视。据罗景仁自述,他始终将王妙如视为“闺房益友”,并以之为“自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小说向来被视为“君子弗为”的“小道”,更鲜少有女性参与小说创作;罗景仁不仅支持妻子写作,还对《女狱花》每一回精心批注,以为夫妻“相互规励之举”。当王妙如不幸早逝,罗景仁十分悲恸,叹息“杀青未几,人已云亡。批览遗稿,我心惨惨”;因《女狱花》是王妙如生前的“得意之作”,为了告慰妻子,他不仅将小说出版,而且亲自向叶女士索请书序(29)《叶女士序》提到:“甲辰之春三月既望,罗君景仁出德配王妙如女士所著《女狱花》小说征序予。”见《女狱花》,页一。,并为《女狱花》撰写跋文。甚至,他还将自家作为了小说的“总发行所”。1905年8月10日,罗景仁在《南洋日日官报》上刊出广告:
新出小说《女狱花》。西湖女士王妙如遗稿,中国青年罗景仁加批。杭州总发行所:安乐桥边罗宅。上海发行所,中外日报馆、开明书店。
这里的“安乐桥边罗宅”,显然是罗景仁的家。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则广告刻意强调“王妙如遗稿”与“罗景仁加批”并置,可见罗景仁十分看重自己对《女狱花》的贡献。细读罗景仁的加批,也能看出他不将自己视为一个普通读者,而是以另外一种特殊方式,对《女狱花》进行有效的文本参与。例如第五回结尾,他这样讲道: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此小说书中出主人公之法则也。又有一法,于开卷数句中,即将主人翁叙出。但此书无速出主人翁之理,因改革之事,须由激烈党之破坏,方有平和党之建立。吾不知作者几许经营,才出“佛婢”二字,又不肯将真名姓轻易露出,真可谓得小说家之嫡乳。
这一回写到沙雪梅在逃亡路上经过一家酒店,于墙上看到一首署“佛婢题”的女权诗歌,心中欢喜。“佛婢”其实就是另一主人公许平权,直到第八回方才出现。那么,罗景仁是如何得知其“真名姓”的?王妙如这样安排又有何用意?罗景仁生怕读者误解,故加以解释:改革之事需要一定步骤,“须由激烈党之破坏,方有平和党之建立”,因而“此书无速出主人翁之理”。寥寥几语,不仅将《女狱花》的谋篇布局和盘道出,同时还点破了小说主旨,切中肯綮。
关于王妙如写作《女狱花》的过程,罗景仁在“序跋”中说“每作一回书,必嘱予略加批点”,也就是说,王妙如写出一回,他立即加批。那么,此时并未看到后半部故事的罗景仁,为何对王妙如的情节构思与小说意旨如此熟稔?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深入参与到《女狱花》的创作中来。前文说过,罗景仁富有诗才及文章造诣,具备构思并写作小说的能力。他与王妙如感情深厚,欣赏妻子的才华,“每自负得闺房益友”,更愿与之“互相规励”。那么,日常与王妙如一同讨论小说情节,提供想法与建议,似乎并不突兀。可以说,《女狱花》文本生成与出版流通的全过程,都凝结了罗景仁的付出与心血,甚至说是夫妻二人的共同作品,也不为过。因此,在目前王妙如生平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或可另辟蹊径,尝试借由罗景仁的教育背景,勘探《女狱花》的写作背景与思想资源。
二、 杭州日文学堂的新学氛围与佛学渗透
罗景仁就学的杭州日文学堂,创建于1899年3月1日,从时间上看,诞生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日语学习高潮中,但却与此前1897年京师同文馆增设的东文馆、1898年出现的上海东文学社与福州东文学堂等有着本质不同(30)刘建云指出,根据创办者身份,晚清东文学堂可分为三类,即“中国人设立”“中日共同设立”“日本人设立”。据此,京师同文馆增设的东文馆和上海东文学社属中国人设立的官立、私立学堂;福州东文学堂为中日共同设立。见『清末東文学堂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中国人設立の東文学堂と日本語教育を中心に』,『岡山大学大学院文化科学研究科紀要』,1999年第8号。,它是日本东本愿寺在近代中国独立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也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在中国传教的产物。
日本净土真宗由镰仓时代的亲鸾(1173~1263)所创,本是净土宗的一个分派,因吸收了中国隋唐时期许多净土宗大师的创造性阐释,又融入了日本国情与特色,在教义上自成体系,遂被视为佛教新宗。江户时代分立,影响最大的是东、西本愿寺两派;前者也称“大谷派”或“东派”,后者又叫“本愿寺派”或“西派”。明治维新以后,因外抗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之东侵,内抗神道教压迫,日本佛教界展开海外传教活动。其中,东本愿寺派不仅在中国开教最早、势力最大,活动也最为频繁(31)参见忻平:《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传教述论》,《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早在1873年7月,小笠栖香顶就接受东本愿寺派遣,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做开教考察,在华一年多,遍历京津沪佛教诸地,习汉语,撰《北京护法论》《喇嘛教沿革》等。1876年7月,小笠栖香顶率谷了然等4人再度来华,于上海创立“真宗东派本愿寺上海别院”,正式揭开近代日本佛教在中国传教扩张的序幕。然而,由于种种条件制约,东本愿寺早期在华影响十分有限,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进入了兴盛期。1899年1月,东本愿寺本山改革体制,设海外布教局主管海外开教;3月,于上海别院设立“清国开教总部”,制定了周密而庞大的开教计划。有感于此前“直接布教”的成本高、效率低,东本愿寺决议模仿西方基督教的传教模式,转向慈善、医疗、教育等“间接布教”方式,其中尤以“教育事业”为扩教核心(32)参见木場明志:『日清戦後における真宗大谷派アジア活動の急展開:「本山事務報告」「常葉」「宗報」の記事から』,『大谷大学真宗総合研究所研究紀要』,1995年第12号。。在此背景下,他们设立了杭州日文学堂、金陵东文学堂和苏州日文学堂。这三个学堂的设学宗旨与课程设置多有一致,常被并列提及(33)如杨文会《金陵本愿寺东文学堂祝文》:“今者,大法主现如上人属其弟子胜信公来华,设本愿寺于杭,以十人居之。复设本愿于吴,以三人居之。金陵为南朝胜地,而北方心泉上人与一柳等五人居焉。”见《等不等观杂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17页。;在日本东本愿寺一方看来,也具有某种先导示范作用(34)在东本愿寺制定的「開教本部章程」中,三个学堂并列其中,担任要职。见『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第312页。。
1899年3月1日,杭州日文学堂创建于杭州忠清巷,堂长为慧日院侍读、帝国大学文学士伊藤贤道,任教教师有铃木广阐、樋口龙缘等人。该学堂于1906年8月关闭,前后存续7年之久。在杭州日文学堂成立的同一天,金陵东文学堂也在南京城北浮桥马路创立;同年5月20日,又有苏州驸马府堂北师古桥西侧的苏州东文学堂成立(35)刘建云:『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東本願寺の東文学堂』,『岡山大学大学院文化科学研究科紀要』,2000年第10号。。关于杭州日文学堂的创办宗旨,笔者在1899年3月6日的《新闻报》上找到一则转录的“招学友启文”,记载颇详细:
今日之世界,非犹昔日之世界也,异洲如户庭,群雄似虎狼,眈眈环伺,岌岌堪危,国不富,兵不强,民不智,即使上有尧舜,下有皋夔,亦断断乎不能立其国于环球之上……地球之局势,祸福之因缘,而以天下最有用最有益之实学,为无补家国、无济民生,睨视之而不乐讲求。呜呼!是不亦大可哀乎?是岂非仆等之大心事乎?仆等佛教中人也。佛教之旨,曰“慈悲”,曰“方便”,与孔圣人存心毫无以异。为其弟子者,自号自善自利自私,不能推己及人,以己之所知所觉,觉人而知人,则与我佛悲心大相刺谬,罪过孰甚于此乎?而况仆等之与禹域,居同洲,种同色,书同文,其利害之相关,犹齿之于唇也。其情谊之亲切,犹弟之于兄也……仆等有念夫此,是以远涉重洋,偕来禹域,创建学堂,传授新法。(36)《东文招学》,《新闻报》1899年3月6日。
这则启文首先申明处当今世界大变局中,讲求“实学”的重要性。随后,又剖白远涉重洋来中国创办学堂的原因:其一是由于历史与地缘联系,中日两国唇齿相依、情感深厚;其二是我佛慈悲之心,推己及人,“以己之所知所觉,觉人而知人”。这则启文充分抓住当时中国处内忧外患、急切寻求富强的心理,反复以“实学”相标榜。类似说法,同样出现在杭州日文学堂的《开设东亚学堂启》:“近年来,时势多棘,内忧外侮,环伺迭乘……专重实学,屏斥虚文,当务之急,莫过于此。”(37)《开设东亚学堂启》,《亚东时报》第6号,1899年5月。
这里所谓的“实学”,可以泛指实用之学。作为一所“日文学堂”,语言学习自当是首要。查杭州日文学堂“日文课”课程设置,三个学年“日语”“日文”分科教授,前者主要以发音、常用语等语言知识为主;后者专注在万国地理、东亚历史、东西洋哲学史等语言实际应用。此外,第一学年后期还设有“翻译”课,分为日文汉译、汉文日译;第二学年虽不见专门的翻译课,但“杂课”中仍有翻译、阅日报、作文等内容。语言课程之外,还设有“算学”“格致”“伦理”“经济”“论法”“政法”“哲学”等课,广涉西学知识,如“格致”课又有化学、动物学、植物学、身理学、地势学、地质学、星学、电学、金石学、卫生学、农林学等科目(38)《杭城日文学堂课程》,《宗报》1899年2月15日。。可见,尽管在招生广告中,日本东本愿寺将传教扩张的意图掩饰得非常彻底,但主张“实学”这一点,倒也在日后的办学实践中落到了实处。
杭州日文学堂新学氛围浓重,1901年3月,学堂师生发起编译《译林》杂志,前后共出13期,于1902年停刊。该刊由堂长伊藤贤道发起,林纾监译并亲自撰写《〈译林〉序》和《译林简明章程》(39)林纾:《〈译林〉序》,《清议报》第69册,1901年1月1日。。译者有林长民、林文潜、陈福民、徐鼎等8位学生,其中,陈福民和徐鼎就是与罗景仁一同在浙江武备学堂任教的同事。《译林》的发行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刊登了很多西学译作,在当时影响很大。蔡元培、鲁迅都曾阅读过该刊(40)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朗轩、伯絅许取《译林》十一、十二。豫才(即鲁迅,笔者注)代购《译林》五册六角。”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7页。,浙江臬台许豫生还下发《饬通省购阅〈译林〉札》,令各府州县、书院义塾订阅学习,称“《译林》一书所列政学、史学、商学、法律等,俱深得东西各国富强之旨,可以大开民智,广导利源,洵非今日所行各报可比”(41)《置浙臬许廉访饬通省购阅译林札》,《译林》1901年第4期。。此外,译者还在杂志外出版了不少单行本,其中即有《斯氏哲学要义》,介绍了斯宾塞哲学(42)胡梦颖:《20世纪初杭州〈译林〉杂志的传播网络及编译群体》,《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可见,早在马君武翻译《斯宾塞女权篇》之前,罗景仁就已经对斯宾塞的思想有所了解,同时也接触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西方学说,故而尊重女性、持论通达。据此,再来反观王妙如在《女狱花》中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信手拈来,对希腊历史的随口演述,对达尔文进化论与斯宾塞女权篇的熟稔与化用,便知其渊源有自,绝非空穴来风。可以说,王妙如之所以能写出振聋发聩的小说《女狱花》,与杭州日文学堂的新学背景与罗景仁的日常影响不可分割。
必须注意的是,“教育事业”是日本东本愿寺此时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核心任务,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设立东文学堂,根本目的乃是在传教。选择日文作为教授对象,也是别有用心,因为“欲传教须先通各国语言”,否则“我佛世尊慈悲济世导俗之心无由窥测”,“此又我大法王选派僧徒,分往各国各州开设学堂,不谈元妙,先施却病成方之一片苦心”(43)《招致文启》,《新闻报》1899年5月8日。。尽管查杭州日文学堂的课程设置,看不到任何与佛学相关的内容,但据东本愿寺《开教本部章程》可知,其教师本就有“专门布教”与“兼任附属学堂教学”的双重任务。而且,其《学科课程表》也明确规定“宗乘”“余乘”的佛学课程,前者第一年为每周4课时,与“国语”(日语)课时间相当,包括“句读示教”“祖释通解”“经典通解”等内容;后者未标具体课时,有“佛教名目”“佛教史”“诸宗要旨”等课程(44)「開教本部章程」,『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第313页。。这里的“宗乘”和“余乘”均为佛教名词,“乘”为教法,一般来说,本教遵循的教法为“宗乘”,非本教宗承的教法都称为“余乘”(45)任道斌主编:《佛教文化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30页。。据此,“宗乘”自然是指净土真宗教法,并且在课程设置中分量不少。东本愿寺下设的日文学堂教授佛学,这在晚清著名居士杨文会的相关记载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其《金陵本愿寺东文学堂祝文》明确写道:“留学诸君子,或宣教旨,或受和文。”(46)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第16~17页。金陵东文学堂与杭州日文学堂同天成立,当日便举行了盛大的佛前勤行仪式,并奉读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在《金陵东文学堂大概章程》的“堂规”中,也明确规定“上堂退堂,必须恭立佛前,立定一拜,唱阿弥陀佛一遍”的宗教仪式;此外,还不断向学生宣讲“有本愿寺而后金陵东文学堂乃兴”,“诸生习东语东文皆原于佛陀之恩光也,受恩不报请自思之”(47)刘建云:『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東本願寺の東文学堂』。。这些举措无不致力于让学生对佛祖产生尊崇之心,进而报答“佛恩”,遵奉佛法——更进一步来说,自然是要信奉日本东本愿寺所属的净土真宗。
佛教的净土信仰源于古印度,本有弥勒菩萨的兜率净土、阿閦佛的东方妙喜净土、药师如来的琉璃净土、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等多种信仰;在中国,以阿弥陀佛净土信仰影响最大。日本平安后期,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信仰也开始兴起。之后源空(1133~1212)正式创立净土宗,继而又分立出亲鸾所创的净土真宗。不同于中国以唯心净土为主流,主张禅净双修,心净则土净;日本净土信仰的最大特色就是明确指出信仰对象是西方阿弥陀佛,这样净土就成为有形、具体的世界,特别强调本愿念佛、他力往生(48)参见姚长寿:《中日净土思想之比较》,《佛学研究》2017年第1期。。源空《选择本愿念佛集》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往生之业,念佛为先。”至亲鸾所创净土真宗,更是主张彻底的他力念佛,认为念佛可斩断一切“无明”与生死烦恼,甚至可以“除罪五百万劫”(49)参见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新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9、256页。。由此不难看出,金陵东文学堂要求学生“上堂退堂,必须恭立佛前,立定一拜,唱阿弥陀佛一遍”,正是净土真宗所倡导的“口称念佛”简易修行法门。有趣的是,这一教旨在罗景仁身上也有体现,其《除夕》诗曰:
形骸既落且随缘,空有偏观百虑煎。
静对美人都是佛,放怀酒客可称仙。
功名谈后无荣辱,生死明时忘几年。
一念弥陀消妄念,莲花香气发心田。(50)景人罗嗣宗:《除夕》,《嘤求》第4期,1928年3月。
首联的“偏观”一词具有佛学意涵,因佛教旨在使人由偏观达至兼观,再由兼观而使偏观所观者,自相对销,进而达到中观之境(51)参见刘梦溪主编,黄克剑编校:《唐君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36页。。然而在罗景仁看来,去除偏观、忘却荣辱的方式却非常简单,便是“一念弥陀消妄念”。最后一句的“莲花香气”也大有深意,莲花本就是佛教象征,而西方极乐净土与莲花的关系更为密切。因《弥陀四十八大愿》第二十四愿为“莲花化生愿”,即莲花化生,往生极乐(52)参见赵志刚:《论莲花的意象与佛教》,《中国宗教》2013年第8期。。甚至,净土宗因西方净土皆由莲花所生,又被称为“莲宗”。不得不说,罗景仁此诗正是净土真宗强调通过念佛即可与佛陀本愿相通的直接体现。
此外,在小说《女狱花》中,罗景仁也表达过“极乐世界”为女权革命的圆满境界,如第三回“吾尤望天多生女拜伦之作者,用着秃笔残墨,喝死魔王,引世人同登极乐世界”。可见,日本东本愿寺在中国设立日文学堂,表面上以群雄环伺、富国强兵相号召,倡导学习日文与实学(西学)的重要性,但其背后隐藏了非常强力的佛学渗透。在罗景仁身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出这种渗透对其思想产生了一定作用,并且在《女狱花》的批语中有所体现。
三、 《女狱花》中的佛学与女权
确定了杭州日文学堂的佛教背景及其对罗景仁的影响,返观可知,《女狱花》文本中的大量佛教细节全然不是可有可无的写作闲笔,而是我们重新打开文本、深入解读小说的一把钥匙。
在《女狱花》中,王妙如精心结撰了两个女性人物——沙雪梅和许平权。两人目标一致,都要解放女性、恢复女权,但手段和方式却迥然有异:沙雪梅声称要“杀尽男贼方罢手”,许平权则强调“不施教育,决不能革命”。在《女狱花》第一回,沙雪梅就隆重登场,她进入了一个“十九殿”的梦境,目睹了一幅生动的女性受苦受难“地狱图”。随后,小说又花费了很多笔墨描写沙雪梅受到丈夫压制后失手将其打死,及其越狱并逃亡路上的所见所闻。相较之下,小说另一位主人公许平权直到第八回,方才正式出现。《女狱花》总计十二回,可以说,故事的前半部分基本都以沙雪梅为叙事中心。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沙、许二人“看似矛盾,实为一体两面”(53)蔡佩育:《〈女狱花〉的女性书写及其文化意涵》,《弘光学报》第65期,2011年12月。。笔者以为,《女狱花》对两位女主人公是否有所偏倚,直接关系到王妙如本人的思想倾向,必须认真对待。
其实,尽管许平权出场较晚,但她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这在《女狱花》第八回“两党魁相逢旅馆,三伏夜大斗词锋”中有集中体现。本回作为全书主脑,主要写沙、许二人的一场激烈辩论,焦点是应该采取何种手段实现女权,结果自然是两方旗鼓相当,谁也没能说服谁,最后不欢而散。然而,罗景仁却在评语中这样评价“两党魁”之争:
此回口战,最难下笔,一须各肖声口,二须各有道理,三须归重许平权,四须顾全沙雪梅。此四条中,惟第二条、第四条为尤难。因作小说者,无不知侧重主人翁,若笔无分寸,必使沙雪梅说话,可以易剥轻击,则不成沙雪梅矣;必使许平权得胜,沙雪梅理缺事穷,则下回亦无激烈革命事矣。
在罗景仁看来,小说需要“侧重主人翁”,所以必得“归重许平权”;但若使许平权轻易得胜,则下文的沙党革命情节便无法展开,故要同时“顾全沙雪梅”。随后第九回,许平权没有再出现,但小说却透过沙雪梅党人张柳娟之口,交代了许平权的生平出身与教育经历。对此,罗景仁加批:“此回犹只叙沙雪梅,不叙许平权,亦未免喧宾夺主。”可见,罗景仁反复以主、客关系比拟许、沙二人,已明确点破许平权在《女狱花》中的绝对核心位置。至于为何先安排沙雪梅出场,《女狱花》也给出了合理解释:“且革命之事,无不先从猛烈,后归平和,今日时势,正宜赖他一棒一喝的手段,唤醒女子痴梦,将来平和革命,亦很得其利益。”换言之,在王妙如看来,倘若没有沙雪梅等人先行激烈之破坏,许平权的平和建立也就无从谈起,这两者前后相继,缺一不可。
确定了许平权在《女狱花》中的核心位置,返观沙、许二人的出场情景,就显得意味深长。小说甫一开篇,沙雪梅隆重登场,罗景仁加批:“女魔王出世了,我劝洞里蛇的男子稍敛些威福。”至第五回,许平权先以“佛婢”的署名出现在酒店墙头,一首洋洋洒洒的女权诗,引得沙雪梅赞叹不已,引为知己。此处伏笔已然埋下。随后第八回,沙、许二人首次相见,许平权的箱子上“贴着一个红条,竟是‘佛婢’二字”。罗景仁又赶紧加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出世了,善女人善男子皆当开一欢迎会。”于是,“女魔王”与“观世音”“佛婢”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对照。
观世音菩萨在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是阿弥陀佛的上首弟子,与大势至菩萨一道,被视为阿弥陀佛的胁侍,合称“西方三圣”;而她的首要任务,就是协助阿弥陀佛说法并接引众生(54)李利安:《古代印度观音救难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的融合》,释根通主编:《中国净土宗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317页。。如此,许平权自号“佛婢”,就与罗景仁谓之“观世音”之间产生了一种同构和互文,这也是《女狱花》受到佛教净土思想影响的又一明证。事实上,这一情节的设置绝非偶然,试看沙雪梅与许平权二人女权思想的获取方式与开悟途径。《女狱花》第一回写沙雪梅做了一个“十九殿”的梦:
里面上头高耸耸坐着老老少少、贫贫富富的无数男子,底下笑嘻嘻跪着老老少少、贫贫富富的无数女人,且与一群一群的牛牛马马一同跪着,旁边摆着从来未见过的各种刑具。
可以说,这一情景浓墨重彩,在沙雪梅心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成为她日后思想开悟、成长为一名女权斗士的重要契机。然而,梦醒之后,她“细把这梦思寻,终不能猜出有什么道理”。对此,罗景仁也批注说:“大梦初醒,还是痴迷。”懵懵懂懂直到第三回,沙雪梅在丈夫书房里阅读到《斯宾塞女权篇》,“忽拍案叫道,是了是了,我做女儿的时候,不明明做过一个梦么……我前时模模糊糊,不知这个道理,今日想来,一丝不错”,于是彻底醒悟,痛骂“男贼”,与丈夫展开激烈争执并将其打死。这里的《斯宾塞女权篇》为马君武所译,1902年11月出版,在近代中国女权思想发展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实为晚清诸种女权思想之源头(55)参见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4~78页。。因此,王妙如设计让沙雪梅通过《斯宾塞女权篇》领悟到男女平权的道理,从此走上女权革命之路,这一情节完全合乎情理。
相较之下,许平权的开悟方式就显得不太理所应当,甚至有些吊诡。在《女狱花》第九回中,与许平权自幼相识的张柳娟,长篇大论地讲述了她的生平经历,特别交代了其思想变化的过程:
妹妹那时,仍与他兄妹二人,一堂研究学问,且与平权结为异姓姐妹……岂知平权自她父亲死后,性质忽然更变,日日夜夜看着大乘佛经,为人甚是冷淡。与妹妹的意思,渐渐不合。故妹妹去叫她,一味推脱不来。到了去年,常因女权之事,与妹妹大起冲突。她的古怪话语,我也不欲尽说。
可知许平权与张柳娟原本关系交好,宗旨也相同,甚至还结为异姓姐妹。然而自从她“日日夜夜看着大乘佛经”之后,性质忽然发生极大转变,不久经常与张柳娟大起冲突,关系也渐行渐远。换句话说,许平权本也倾向于激烈之革命,与沙雪梅算是同道;之所以转向平和之建立、自取“佛婢”为别号,乃是因为读了大乘佛经,得其启迪。这一情节明确显示了王妙如对大乘佛教的推崇,这在《女狱花》中也并非孤例,第十一回写许平权在女学堂开学之际发表演说,再次表达了对大乘佛教的推崇:
我释迦涅槃说法,本为万古不灭的大教,应该人人皈依的。但那些(和)尚尼姑,非但大乘经典未曾入目,即小乘经典,亦未能了解。名为佛徒,实则佛教的罪人。
这段话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在许平权看来,佛教是“万古不灭的大教”,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应该人人皈依”;第二,“大乘经典”不仅是许平权女权开悟的重要途径,而且在她的思想体系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重大乘、轻小乘的倾向。这是什么缘故呢?
佛教作为反对印度婆罗门种姓特权制度的宗教,其创始人释迦牟尼以洞彻宇宙人生实相的觉照指出,众生男女具有相同之佛性,皆平等。作为原始佛教基本经典的《长阿含经》云:“尔时无有男女、尊卑、上下,亦无异名,众共生世,故称众生。”在此,“众生”的概念取消了性别、地位、品性等诸多差异,指共存于世间的一切有生命者,故形有男女,性无彼此(56)林伟:《佛教“众生”概念及其生态伦理意义》,《学术研究》2007年第12期。。可以说,佛教这种终极层面上的男女同尊究竟平等,正是许平权将其视为“万古不灭的大教”的原因之一。这在第五回“佛婢”女权诗中也有体现,试看第一首:
情天从古未偏颇,男女平权剏释迦。
只为后人功德缺,中郎灶婢尽韩娥。
佛典将世俗世界分为“有情世间”与“无情世间”两大类,“有情”指有情识的生物,如人与动物,亦即“众生”;“无情”指植物宇宙、山河大地等无情识的生物(57)林伟:《佛教“众生”概念及其生态伦理意义》,《学术研究》2007年第12期。,也叫“器世间”。据此,诗中的“情天”当指有情世间。“剏”本同“创”,这首诗大意是说:众生本就平等,释迦牟尼创制了男女平权之说,但因为后人缺功业、少德行,所以出现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像韩娥(58)韩娥,春秋人,精通音律。据《列子·汤问》所载,韩娥曾在齐国雍门卖唱,其歌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成为当地民众学习的典范。这样的优秀女子,只能沦为蔡中郎(59)蔡中郎,即东汉蔡邕,字伯喈,蔡文姬之父,官拜左中郎将。他本为品德高尚的名士,却在民间说唱文学《赵贞女与蔡二郎》中成为“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负心之辈。元末高明试图用《琵琶记》为他翻案,但仍保留了《赵贞女与蔡二郎》故事的基本框架。一类“负心汉”的灶下之婢。小说第十二回,在许平权与黄宗祥的对话中又再次重申“我闻天的(地)生人,无分男女,则男女应该平等的”,正是“情天从古未偏颇”一句的绝佳解释。
那么,王妙如为何要反复强调“大乘经典”?众所周知,佛教有大、小乘之别,据说是由于释迦牟尼在世时因人设教,其灭度后,诸弟子对佛法各有理解与发挥,经小乘各部派分裂之后,大乘又起而予以发扬。简言之,小乘佛教的出发点是“出离心”,即要求自我解脱,出离生死,趋证涅槃;大乘佛教的出发点则是“菩提心”,立志成佛,广度众生。因大乘佛教以人人成佛、举世解脱为最高目标,自然就出现了试图建立理想王国的“极乐净土”。相反,小乘以个人解脱为理想,故不可能出现“极乐净土”这样的信仰思想(60)何燕生:《近代文明对话中东亚佛教知识的重构——以“大乘佛教”为中心》,《哲学研究》2020年第5期。。据此,大、小乘佛教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女性观。原始佛教在“解脱上的男女平等主义”之外,本还具备“制度上的男性优越主义”和“修行上的女性厌恶主义”的特点(61)参见释恒清:《菩萨道上的善女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0~35、35~43页。;故小乘佛教将后两者进一步发扬,对女性采取相当极端的厌恶态度,认为女人有“九恶”“五秽”“五碍”等,并视其为淫欲、邪恶的标志,因此“女人入地狱多于男子”,甚至被排除在成佛的大门之外(62)参见释恒清:《菩萨道上的善女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0~35、35~43页。。相反,旨在“上化佛道,下化众生”的大乘佛教,则重拾佛祖本义并将其因应于时代,对待女性也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如作为大乘佛教重要经典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认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故“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从大乘般若经的空义出发,再次指出众生同一本体,无二分别;可惜世人以妄心取分别执着,遂产生男女、高下、优劣之差异,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虚妄幻相、障道之缘(63)参见永明:《佛教的女性观》,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95~96页。。
故此,许平权效法大乘佛教之“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试图回归佛陀本怀,以平等慈悲之心“行菩萨道”,故而反对沙雪梅等人“用强力夺权力”,也绝无可能赞同沙雪梅“我欲将你们男贼的头,堆成第二个泰山,将你们男贼的血,造成第二条黄河”一类的说辞(第六回)。她遵从大乘佛教的以社会教化为目标,提倡通过教育,使女性在思想道德和知识水平上达到与男子相同的程度,“今女子竟能自食其力,若男人犹行野蛮手段,无难与他各分疆域,强权是无处逞的”(第十一回)。为此,许平权东渡日本求学,归国后创办了女子学堂和师范学校。面对黄宗杰的情意,她不愿分心,与其相约“完姻之日,且待女学振兴之后”,大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决心。在许平权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十几年后女界大昌,“女子状态很是文明,与前时大不相同。做男子的,亦大半敬爱女子”(第十二回)。在小说结尾,黄宗杰激动地对她作揖道喜:“恭喜妹妹大事成了。”随后,他这样评价许平权的女权事业:
妹妹啊,你怀着菩萨心肠,舍身渡世,将直接之善女人,间接的善男子,从火坑提到金莲座上,非特我二万万裙钗女子,皆当焚香叩首,即我二万万须眉男儿,也当跪食慧果了。
这里的“金莲座”与阿弥陀佛的“莲花化生愿”有关,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不仅自莲花化生,而且以莲花为住所,“命终之时,心无怖畏,正念欢喜,现前得见阿弥陀佛及诸圣众,持金莲台,接引往生西方净土”(64)遵式:《往生西方略传序》,许明编著:《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2485页。,此金莲台即众生往生极乐后的座位。待到莲花盛开,就可享受亲自聆听阿弥陀佛讲法的殊荣,是为“花开见佛”。“从火坑提到金莲座上”意味着往生极乐、功德圆满。王妙如以此来比喻许平权女权事业的成功,将数十年的辛苦付出化为以“菩萨心肠”兴“舍身渡世”之事的至高评价,也是别有会心,大有深意。
综上,在《女狱花》中,反映出了两种不同来源的女权学说之间的缠斗:一是阅读《斯宾塞女权篇》而开悟的沙雪梅,其女权学说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平等的观念之上;二是从大乘佛经中得到启迪的许平权,其女权思想的源头是佛教众生平等、无二差别的平等观,同时在具体实践层面,又糅合了大乘净土思想。两相比较,《女狱花》无疑是坚定地倾向于后者,这也是王妙如与罗景仁的共同选择;若再进一步将之置于近代中日佛教交相往复的格局中加以观照,则更能抉发近代中国女权思想发端的一脉潜流。
四、 东亚佛教格局中的《女狱花》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一直遵循“大乘本位主义”,视小乘佛教为一种权巧方便,认为大乘佛教才代表了佛陀本怀。故中国佛教向来“判教”思想盛行,具有“学问佛教”的特色;与此同时,又融入“戒律”和“禅观”,具有山林佛教的“隐遁性”,故又兼有小乘特色。相比之下,日本佛教则更加重视大乘佛教的实践主义精神,甚至成为指导其发展的一种基本理念。不仅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提倡游历于社会,而且特别注重在平民中从事教化活动(65)何燕生:《近代文明对话中东亚佛教知识的重构——以“大乘佛教”为中心》,《哲学研究》2020年第5期。。因此,日本佛教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在教育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且不限于僧侣教育,更加诸于社会教化,甚至推动了近代平民教育的发展。净土真宗也是如此。早在德川初期,东、西本愿寺就兴起了办学之风,称为“学寮”或“学黉”,是为今日大谷大学与龙谷大学之前身(66)关于日本佛教与教育之关系,参见张玉姣:《日本佛教教育初探》,《佛学研究》2009年第1期。。
与此同时,日本佛教具有强烈的佛法护国观念,主张佛教与国家密切结合,所谓“佛法王法互守互助”(67)杨曾文等:《日本近现代佛教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11年,第34页。。1868年,明治政府颁布了“祭政一致”布告和“神佛判然”令,佛教在神道教、基督教、儒学和西学的夹击下,处境前所未有的岌岌可危。于是,佛教开始了海外交流,其中,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就是第一个来华传教的日本宗派,早于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20多年(68)1898年,净土真宗西本愿寺在厦门设立厦门别院,是第二个在华设立传教机构的日本宗派。其余各宗更晚,分别是日莲宗(1899年,上海)、净土宗(1905年,旅顺)、曹洞宗(1908年,安东)、古义真言宗(1914年,上海)、临济宗(1914年,青岛),参见《1876~1945年日本佛教团体在华所办佛教传教机构表》,肖平:《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1~125页。。1873年,小笠栖香顶首次来华时努力宣讲“三国同盟论”,力主以日本为主,与中国、印度结成三国联盟(69)木場明志、桂華淳祥:『東本願寺中国布教史の基礎的研究』,『大谷大学真宗総合研究所紀要』,1988年第5号。,其实就是应对本土危机的一种自救;“使我法教旨与日本之光一道放射万丈光芒”(70)「開敎幹部の渡航」,『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第7页。之类的宣言,也与“佛法护国”的传统观念一脉贯通,隐藏着更为深层的亚洲主义主张。
然而,当时的中国士人并不了解这些,他们看到东邻日本的成功,就认定佛教是可以兴邦安国的思想资源(71)事实上,这一认识也来自于净土真宗的自我宣传:“我国三十年前曾患此病,幸君民上下,同奉佛法,同契佛心,先通各国语言文字,痛服瞑眩重剂,渐起沉疴而臻康健,已获成效。”见《招致文启》,《新闻报》1899年5月8日。。那么,最早来到中国的净土真宗,自然最为引人注目,也就顺势成为了中日佛教交流的重要枢纽。不仅杨文会、沈善登、张常惺、许息安等著名居士都与东本愿寺的北方蒙、松江贤哲、松林纯孝有过密切交往,并成为其在南京、杭州和苏州三地展开活动的有力支持者与合作者(72)参见「東本願寺兩連枝の渡支」「江南清人有志の呼應」,『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第72~75页。;就连当时最著名的一流学者、僧人如俞樾、寄禅等,也与他们交往甚多(73)参见『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第97~98页。。随着净土真宗一派著作的广为流传,各种日本佛教研究如姊崎正治、村上专精、井上圆了、高楠顺次郎的著作也相继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兴趣。杨文会曾对小栗栖香顶包括《真宗要旨》在内的一系列著作展开了批评,但也大赞其在教育上发挥的作用:“真宗既有学寮讲肆,又开普通学馆,是世出世法兼而习之,人才辈出何可限量!”(74)杨仁山:《阐教刍言》,麻天祥主编:《20世纪佛学经典文库⋅杨仁山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7页。1900年3月,蔡元培撰《佛教护国论》,宣称阅读井上圆了之书而悟到“佛教者可以护国也”,提出“当仿日本东本愿寺章程,设溥通学堂及专门学堂”以为护国之策,并肯定净土真宗的食肉和娶妻(75)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6~107页。。此外,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都有相关论述,他们都从日本佛教大变革中,一眼看中了佛教的入世性,借此来汇通、阐释和介绍自己追求的政治理想(76)参见葛兆光:《论晚清佛学之复兴》,《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101页。,正所谓“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7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64页。。
纵观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尽管佛教所承传者多为大乘,但男女同尊、平等的女性观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究其原因,佛教传入时正值两汉,当时儒家文化被奉为独尊,“男尊女卑”已是道德价值之主流。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佛教只好拈出小乘的“女性卑弱论”,作为儒、释融合的切入点,不仅按照儒家纲常礼教思想诠释佛典,而且直接将儒家的“三从四德”贯彻到在家女性的修行中(78)参见彭华:《佛教与儒家在女性观上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哲学动态》2008年第9期。。到了近代,东亚佛学展开了一场剧烈的交流往复,晚清佛学也得以短暂复兴。于是,以日本东本愿寺来华传教为契机,通过杭州日文学堂这一枢纽,将正在苦苦思索中国女性如何出路的王妙如,置于这一世界性的佛学知识大变革的网络中。她在《女狱花》中提出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基本根义上是笃信原始佛教“众生平等、无二分别”的平等观,实践层面上则秉持“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大乘净土观,特别融入日本佛教“救国”的传统理念与“兴学”的实践特色。甚至,王妙如在《女狱花》中将“大乘”与“小乘”视为佛教的分类方法而非修行的境界,也是基于彼时日本学界刚刚新鲜出炉的佛学知识,来自日僧释宗演的发明(79)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大乘”与“小乘”这两个概念均是指称“教理”和“实践”,即两种不同的修行境界。释宗演首次将之视为分类概念,并与地理相结合,提出北传佛教/大乘佛教、南传佛教/小乘佛教的分类方法。参见馬場紀寿:『释宗演のセイロン留学——“大乘佛教”こうして生まれた』,载『图书』2017年第4期。。而同样受日本佛学影响与启发的康有为,尽管号称“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80)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页。,但对比了一圈,终于还是认定只有近代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念才是“人类公理”,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甚至认为女性长期不得解放,作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不能“辞其责”(81)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相似的出发点,不同的选择,于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渐行渐远中,开出了不一样的女狱之“花”。
日本东本愿寺最初来到中国,小心翼翼以“弟”自居,“唇有病而齿不为,兄及难而弟不为拯”之类的说辞(82)《东文招学》,《新闻报》1899年3月6日。,无不伏低做小、言语恳切,表达对中国“大哥”的提携报恩之意。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之晚清“庙产兴学”政策的加持(83)“庙产兴学”是晚清政府为了挽救政治颓势、进行教育改革而推行的政策,最早出自张之洞《劝学篇》。在他看来,欲改变国力,天下须设学堂万所,而朝廷无此财力,因此“可以佛道寺观改之”(见《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39~9740页)。于是,当时相继出现驱僧、毁像、占庙、提产之事,为了寻求保护,不少寺庙投奔日本东本愿寺。,东本愿寺在江浙一带的影响与渗透逐渐加深,本来掩盖得严严实实的“亚洲主义”倾向,也就开始慢慢浮出水面。1899年,东本愿寺率先与杭州弥勒寺、苏州南禅寺签订了“共同住持”协议(84)「杭州彌陀寺との共住契約」,『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第82~83页。;1900 年,杭州日文学堂的堂长伊藤贤道路过新昌,住在大佛寺里招收徒弟,要求每人出洋十余元(85)《日僧到新昌》,《绍兴白话报》第102期,1900年。;更有甚者,1904年前后,浙江发生了40余所中国寺院共同归属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的事件(86)据伊藤贤道回忆,天童寺的八指和尚及其侍者介石来杭州海潮寺拜访他,陈诉了最近中国“庙产兴学”之事,请求援助。随后,介石在伊藤贤道的帮助下,取得净土真宗法师位,杭州海潮寺住持随之效法。接下来,浙江四十余所寺院相继投奔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参见「歸屬問題の經過」,『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第97~98页。。佛教本来就是从中国传入日本,此时文化权力的攻守之势发生变易,挟东洋以自重本就是下下之策;谁知东本愿寺野心毕露,不可收拾,中国士人自然不能忍,终于在无数类似“吾不知日本屡以在吾国宣播佛教为要求,果何意也”的诘问之后,发生了一场不小的杭州风波(87)参见葛兆光:《世纪初的心情——1905年的杭州风波》,《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第67~76页。。
[作者简介]为这场风波的结果之一,1906年8月,伊藤贤道被逐,杭州日文学堂关闭;1909年,金陵东文学堂也关闭了。至此,日本东本愿寺在江浙一带苦心经营、作为中国开教“先锋”的三所日文学堂全部关闭(88)此前,庚子事变发生后不久,苏州东文学堂就已经关闭。参见刘建云:『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東本願寺の東文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被称为“当代昌明第一导师”、叱咤晚清佛教界的杨文会也去世了。于是,晚清热闹了十几年的佛学终于还是偃旗息鼓,悄无声息地退场了。然而,日本佛教界对中国的觊觎之心却没有随之退却,1915年,日本政府欲借“二十一条”对华争取“传教权”,虽未能成功,但野心不散。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卷土重来,“在挥舞利剑的皇军武力下和亲日傀儡政权的协力下,战时在华布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89)江森一郎、孙传钊:『戦時下の東本願寺大陸布教とその教育事業の意味と実際:主として「真宗」所載記事による』,『金沢大学教育学部紀要(教育科学編)』第43号,1994年。,制定战时体制,派遣慰军使,甚至提倡“利剑即是佛陀”,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恶(90)参见忻平:《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然而,1903年前后的王妙如与罗景仁,站在世纪之初的十字路口,并不知道历史的车轮将要滚向何方。他们与当时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还在努力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新思想,为中国这个“老大病国”寻找药方。更让人唏嘘的是,王妙如在《女狱花》中如此坚定地推重许平权,甚至不惜以“乌托邦”的形式为小说加上一个“十数年后”女界大昌的结局。无疑,这个结局遂了许平权自号“佛婢”时的初愿,但这又何尝不是王妙如彼时所发的“振兴女界之大愿力”(91)《俞女士序》,见《女狱花》,页三。?只可惜她“弱躯多病”,“不能如我佛释迦亲入地狱,普救众生”,故只能退而求其次,像小说中的文洞仁一样作书醒世,“以秃笔残墨为棒喝之具”。然而天不假年,王妙如竟在不久之后和文洞仁一样“一病而亡”,壮志未遂,一语成谶,只为我们留下《女狱花》这部“麟麟炳炳之文”(92)《叶女士序》,见《女狱花》,页一。,记录着那个时代女性的艰难探索与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