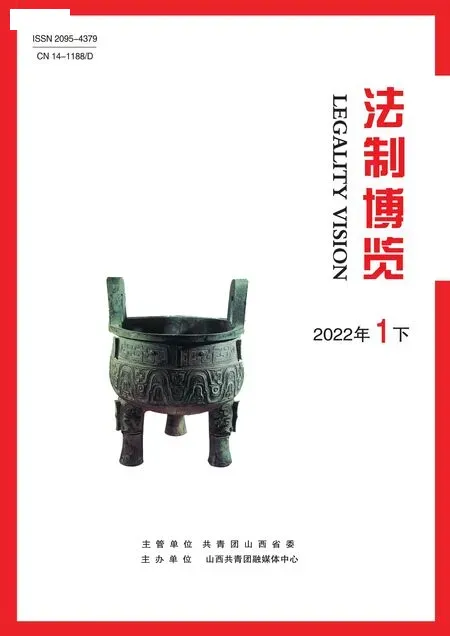居住权视角下“以房养老”的新进路
郑 波
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湖南 长沙 410007
据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载明:我国目前人口总量约为14.12亿人,60岁以上的人口为2.64亿人,占18.7%(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为1.91亿人,占13.5%),与2010年相比,60岁以上的人口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的持续老龄化,对我国的养老事业形成了很大压力。我国目前组建家庭的主力军为80后和90后,据最新调查显示,大多数的家庭结构均为:“4-2-1”“4-2-2”家庭,这也意味着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一对小两口要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和一到两个小孩的抚养和教育,两个人挣钱八个人花,压力明显很大,加上如今国家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并鼓励有条件的家庭生三胎,我们国家面临的养老形势将会日益严峻。基于此,笔者在《民法典》物权篇增设居住权制度的宏观背景下,尝试初步探索“以房养老”的新模式、新进路。
一、居住权的创设及本质
居住权制度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源自大陆法系的古罗马帝国,当时的奴隶社会生产工具相对简单,社会的整体生产力相当有限,因而古罗马当时的整体财产非常有限且实行家长制,当时的“家长”(奴隶主)为保障“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员(有贡献的奴隶)的居住利益,设立了居住权这种“为了照顾某一特定的人”的权利,作为用益物权之一种[1],换言之,居住权同时也是一种“为满足特定权利人的居住需要为目的”的人役权,它具有高度的人身依附属性,原因在于当时的古罗马社会“无夫权婚姻和奴隶的解放日多,每遇家长亡故,那些没有继承权又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因此丈夫或家主就把一部分家产的使用权、收益权等遗赠给这一部分‘特定的人’,让他们在生命复归尘土之前有所依靠”[2]。在原《物权法》的立法过程中,关于设立居住权制度更是一波三折,关于居住权制度的规定最早见诸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征求意见稿中,当时的全国人大为回应社会的需求和现实呼声,首次提出为“切实保护老年人、离异妇女以及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居住他人住房的权利”,设专章,共八个条文。在接下来的人大法工委三次《物权法》草案审议稿均保留了这一制度的规定。2005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关于居住权制度的条文甚至增加至十二条。然而在2007年正式颁布的原《物权法》关于居住权制度的章节最终被删除。是因为当时国内学术界的大多数声音认为房屋租赁等权利的设定,已然能满足人民的现实需求,增设居住权的实际效用并不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老百姓对住宅房屋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在国家确定“小步快进”编纂思路的《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立法机关认为,“为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主要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满足一部分特定弱势人群的居住需求,有必要创设居住权制度”①沈春耀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民法典各分编〉方案的说明》。。基于此,《民法典》在物权编增设了居住权的规定,这显然是对《民法典》“小步快进”编纂思路一个理论上的重大突破。[3]依据《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基于此规定,居住权最本质的特征在于通过将房屋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从而满足民事主体也就是普通百姓对房屋的多元化需求。也正是基于此,探讨“以房养老”的新进路才成为现实的可能。随着我国老龄化逐年加剧的趋势,且房屋自有率奇高,无论总体还是城镇房屋自有率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显而易见,我们的养老事业如果光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对于80、90后的肩膀而言明显不堪重负,因此老年人如何自食其力,自筹养老资金,既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有保障,又能给子女减轻负担,成为新时代养老事业的痛点和难点。基于我国目前房屋自有率居高不下的实际,目前最现实的途径莫过于如何盘活老年人手中自有的房屋资产,而房屋的高价值性和低流通性决定了盘活房屋资产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现实难题。居住权的创设为破解这个现实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进路。
二、养老事业面临的现实困境
目前我国流行的养老模式,除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之外,新兴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反向抵押模式(又称倒按揭),此种模式(英文名:reverse mortage)起源于美国,和传统的抵押模式不同的是,老人先以自己所有的房屋抵押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定期贷款,作为自己老年生活的必需开支,在约定的期限到期或者老人去世后,银行等金融机构再处置老人抵押的房屋一次性偿还老人生前的贷款。但这种模式与我国现行法律和制度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如果认定这一模式的实质是不动产让与担保,抵押人以不动产买卖合同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依照传统让与担保的视角,和我国原《物权法》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如果认定这一模式中的担保行为是虚伪意思表示,借款行为才是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民法典》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虚伪意思表示下隐藏的法律行为效力是否有效尚且待定,该行为如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则当然无效,如未违反,则该行为有效。自2006年两会期间有代表提出“以房养老”提案被采纳后,反向抵押模式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实践结果并不理想。第二种模式为售后回租模式,此种模式由老人将自有房屋出售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定期按每月支付老人生活费(其实质就是售房款分期给付),老人再向金融机构租回自己的房屋居住。但此种模式下,由于老人伊始将自有房屋出售给金融机构,已移转房屋的所有权(属于物权),之后回租房屋因租赁合同获取的房屋使用权(属于债权),基于债权的相对性和弱对抗性,这种模式对老年人这个弱势群体而言,毫无疑问具有较高的风险。同时这种模式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以房养老”模式的新进路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从根本上说,我国创设居住权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有利于尽快实现老百姓“住有所居”的目的,老子曾曰:“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可见“安其居”是老子倡导的理想,也一直是古往今来普通百姓对幸福美好生活最重要的向往,杜甫先生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愿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是普天下所有老百姓最殷切的愿景。[5]长期以来,我国调整房屋利用关系主要依靠的是租赁权,但通过契约或者占有制度规范的租赁权明显存在缺陷,租赁权仅仅只是一种债权,不足以有效制约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3]也难以对抗现实中的第三人,而居住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居住是“由人类系统发出,以寻求和获得更好的栖身场所为动机和目的,以建造、寻找、选择以及使用、利用自己居住空间的方式和手段为行使。”[6]居住权通过合同或者遗嘱的方式有效设立后,经登记公示后,具有绝对的对世效力。这是传统的租赁权作为一种债权所难以企及的,也正是基于居住权的这种内在特质,可以为我们国家新时代正处于改革探索中的“以房养老”模式提供如下四种新的进路。
第一种新的进路:针对目前城市部分老人“以房养老”的现状,有真实案例:南京有七旬老人A,老伴早逝,有自住房屋一套,为减轻独子的负担,决定自筹资金养老,于是与某金融机构B公司达成“设定居住权并以房养老”的协议,老人A在协议生效后将房屋所有权移转给B公司,同时B公司在房屋上为老人A设定居住权,直至老人A离世,由B公司每月向老人A支付养老金,确保老人A生活品质不下降。同时该协议规定,在老人A的有生之年,B公司虽然可以取得协议项下房屋的所有权,但还不能实际占有该房屋,而只有等老人A身故之后,B公司才享有该房屋完整的所有权。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老人可以通过提前变现自己的房屋,将“死”的财产变为“活”的现金,自筹资金养老,有三大好处:一则将本为死后的钱拿到生前来花,改善了自己老年的生活品质;二则通过设定居住权保障自己“老有所养”;再则提前处置了房屋所有权,避免子女众多的家庭因房屋出现遗产纠纷。[7]
第二种新的进路:针对目前城市部分老年人合资购房抱团养老的情形,有真实案例:成都市A女、B女、C女和D女因儿女大多已成年,几个人厌倦了大都市车水马龙的纷扰,于是集体逃离城市,在云南丽江乡间寻觅到一处青山绿水、风景秀丽的所在,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房重新装修,一起抱团养老。这个想法固然很好,但现实却面临一个重大的法律障碍:农民自建房的宅基地属于当地集体所有,非当地集体户口之间不得流通转让。在居住权创设以前,只能通过租赁合同以债权的形式取得房屋的使用权,毫无疑问,这对抱团养老的老年人而言具有较高的法律风险。而居住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它的诞生,则很轻松地破解了这一法律难题:A、B、C、D四女通过与当地农民协商,尽管目标房屋的所有权无法流转,但通过在该房屋的产权证上给A、B、C、D四女设立一个带有期限的居住权(比如30年)并公示,这样A、B、C、D四女就可以安心集资装修该房屋,一起抱团养老。
第三种新的进路:针对我国再婚的老年妇女或者保姆等无房的弱势群体,老人离世前往往想把自己居住的房屋所有权留给子女,毕竟在当今社会,房屋有可能是每个人能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大一笔财产,但老人又会担心一旦自己将房子遗赠给子女,等自己离世后,子女会赶走悉心照顾自己多年的再婚伴侣或者保姆,让其无家可归,甚至流离失所。居住权的设立则可以很好地为老人解决这一难题,老人可以通过遗嘱将自己居住的房屋的所有权留给子女,但同时在该房屋上设立一个永久的居住权,这样就可以既保证房屋的所有权留给子女,又能保障自己去世后,再婚的老伴或者保姆可以在该房屋上拥有居住权和使用权直至离世。
第四种新的进路:针对我国比较普遍的父母垫资购房的传统,在城市尤为普遍,有真实案例:A男和B女系80后,2018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想在北京买房,婚后定居北京,A男的父亲C和母亲D系长沙的普通工薪阶层,通过一辈子辛苦的工作,攒了一套大三居和一台车,银行小有存款20万,小日子本来过得不错,但为了儿子A的事业和未来,二老决定卖了长沙的房子,资助儿子A在北京购房的首付款,同时两人北上跟儿子一起生活,但又担心将来儿子A在北京购房后,将房子登记在儿子A及其媳妇B的名下,二老对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万一婆媳关系处理不好,有被扫地出门甚至流离失所的风险。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从来都是最无私的,但据法院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当今的社会里关于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或父母与离异子女争夺房屋产权的纠纷中,一开始中国的父母都是基于好意,倾囊甚至倾家荡产资助刚成年的孩子购房以自立,但往往父母并不在房本上署名,一旦发生争议,父母并不能就当初自己垫资购买的房屋提出任何主张,一旦家庭关系处理不好或者子女离异时导致房屋旁落甚至露宿街头者亦不在少数。但如今通过居住权的创设,则能很好地为垫资的父母解决这一难题,父母既能因为亲情为子女的购房事宜贡献一份力,又能为自己的“老有所养”留有一条可靠的退路。
四、结语
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养老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终究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居住权作为古罗马法的一种古老制度,其生命力已经历经了历史长河的检验,我们如何吸收其精华,结合我们国家层面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本土实践,探索“养老”模式的新进路,实现“老有所养,住有所屋”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