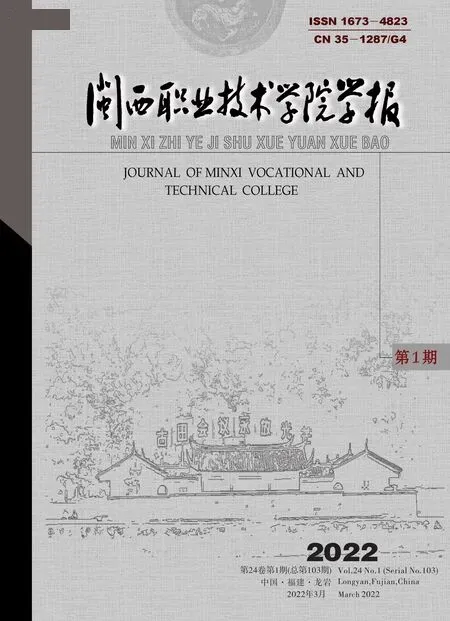“撕扯”:中国当下互联网传播现象观察
程 然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如皋 226500)
中国当下互联网的传播热闹非凡、纷繁复杂、花样百出,其中有一种现象特别令人关注,思来想去,笔者找到一个词来形容——“撕扯”。
一、“撕扯”正义
眼下描摹互联网上那种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词汇屡见不鲜,比如“怼”“对立”“撕裂”等等,有必要先将它们与“撕扯”作一比较。
“怼”,《古今汉语词典》释义有二,一是怨恨:“财尽则怨,力尽则怼(《榖梁传·庄三十一年》)。”二是凶狠:“怼妻狠妾,既嗟且憎(庚信《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可见,“怼”是人的一种情绪和性格,所“怼”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而互联网上的“撕扯”是人与人之间的“怼”,且不全是带着情绪的怨恨,其中不乏理性。所以,用“怼”不妥。
“对立”,《古今汉语词典》释义有二,一是两种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互相矛盾、排斥或斗争;二是敌对,相互抵触。第一个意义可以表示一种静态的现象,但是互联网的双方“对立”从来是不是静态的。且对立虽然说事物的两个方面“相互矛盾、排斥或斗争”,但在笔者看来,要形容当下互联网上的对立状态,不够生动和形象。又,所谓“敌对”“抵触”,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用语言或行动表现出来,而互联网上则只表现为语言,类似于嚷嚷着有人约架,也大多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已。
“撕裂”,查《古今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均无条目,百度百科解释为“撕开扯裂”。可以这样理解,“撕扯”是动作、过程,“开裂”是结果。而目前互联网的交锋的双方,或者至少有一方,根本就不是为了“开裂”,恰恰是耽于“撕扯”,不想“开裂”。
“撕扯”,《古今汉语词典》解释为“撕开扯裂”,这就与百度百科所释“撕裂”同义,似不妥。不妨分别看“撕”“扯”二义,“撕”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用手使东西裂开或离开附着处”,“扯”解释为“撕下”,可见“撕扯”是由两个并列关系的动词合成,“撕”与“扯”同义。在一般人看来,“撕扯”是过程、手段,“撕下”“撕开”“撕断”“撕裂”是结果、目的,它们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未必,《红楼梦》里面有“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晴雯撕了名贵的扇子目的并不指向“撕开”“撕裂”,仅仅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再以生活中的现象为例,两人闹矛盾,各自抓着对方的衣领不放,叫喊着“你想把我怎么样”;或者一方死抓住另一方,叫喊“我决不放过你”。这样的场景,显然不是为了“撕开”,甚至根本不想“撕开”,只是为了扯住不放,吸引别人关注,显得自己有理。所以,他们双方或至少他们中有一方是以撕扯为乐的,是把过程当结果,把手段当目的。借此观察中国当下互联网上互相“撕扯”的现象,互撕互扯的双方至少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弄清道理、明辨是非,而是死死揪住对方不撒手,一方面是为了吸引网民围观、参与,另一方面是想达到扰乱对方的生活和心情,让对方难受、不痛快的目的。
二、“撕扯”:新媒体下的互动
人是一种社群的动物,互动是人的本质需求和生存方式。互动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实践的,一是精神的。它们之间不可断然分开,往往实践的互动和精神的互动交织在一起,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建造一座大楼,互动服务于实践活动;比如围绕一个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互动属于精神需要。互动必有媒介,如肢体、声音、文字等等,没有媒介就无法将互动的内容传播出去,所以互动也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对象。
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洛根认为,迄今为止人类传播分为五个时代,即非语言的模拟式传播时代、口语传播时代、书面传播时代、大众电力传播时代、互动式数字媒介或“新媒介”时代[1]。从本质上说,传播出于人的互动需求,没有互动就没有传播。但是在人类传播的五个时代,互动的方式受到媒介的变革而呈现不同的形式,是一个不断突破时空限制的过程。最初的模拟式传播和口语传播主要靠人的肢体行为和口头语言来实现,互动的空间距离非常有限,如果双方看不见对方的手势,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传播和互动就无法进行;书面传播和电力传播有效地突破了时空局限,借助书籍、报纸的发行量,广播电视的信号输出,其传播的效应克服了空间的遥远和时间的久长,但是它们也有一大弊病,即互动方式不如口语交流那么方便、快捷。比如,16世纪路德为宗教改革写了一篇《九十五条论纲》,它通过印刷而流传,并且引起很大的争论,争论者也是通过书面的形式进行的,受制于传播速度,争论的时效性就打了大大的折扣。为什么当代传播学研究者把“新媒介”称为互动式数字媒介,除了其技术上的革命意义之外,极其重要的一点是,数字化“新媒介”彻底颠覆了以往传播媒介的互动模式。
罗伯特·洛根在回答什么是“新媒介”时这样说:“我们所谓的‘新媒介’是这样一些数字媒介:它们是互动媒介,含双向传播,涉及计算,与没有计算的电话、广播、电视等旧媒介相对。”又说,“‘新媒介’容许使用者积极参与,他们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内容和信息的积极生产者[1]”。不是说传统媒介、旧媒介没有互动,只是新媒介的互动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新媒介通过互联网将全世界联系起来,使互动超越了社群、民族、国家的界限,互联网构筑了“全球村”,那是一个全球网民在其中互动的巨大村落;其次,互联网让人们在空间上实现了隐身、化身的梦想,中国的《西游记》中有孙悟空七十二变的神话,西方也有西尔斯《隐身人》的小说,那些都是想象和幻想,但互联网让想象和幻想成真,网名让人隐身,变换网名让人化身;其三,咫尺天涯,天涯咫尺,你对门熟悉的邻居,在互联网上从不相遇,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陌生人却经常或时刻在互联网上交流。
互联网释放了人的互动天性,而互动必会产生矛盾。互动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也不必是一团和气的,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互动经常会有争论、争辩、争吵一样,互联网也不缺少这样的场景。中国自古就有争论的传统,远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近可以看改革开放之初的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这两次大争论或讨论都发生在社会面临重大变革或转型的特殊时期。当下的中国,也正处在经济、文化、社会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且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变化,更触发了人们争论的神经、热情和兴趣。冷静地看,古往今来的争论,有的争论是有结论、分对错的,如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有的争论是没有结论、不分对错的,如百家争鸣。但是不管有无结论,是否对错,争论双方皆应对理不对人,要有君子风度,要宽容,不纠缠,不以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中国当下互联网上由互动而带来的争论可以大体分为如下几种类型:摆事实讲道理型;拥戴附和型;含沙射影型;攻击谩骂型。每一种类型本都可以适可而止、不再纠缠,但是眼下怎么就在互联网形成了一种无休止的“撕扯”现状呢?
三、“撕扯”:疏离与黏附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集体与国家,一向缺少对人的独立性的培养和塑造,长久以来人们易养成一种依附性人格,进而在部分人那里成为黏附。所谓黏附,指的是像胶水或糨糊一样紧紧附着在他物上。中国人的黏附性较强,表现在家庭、宗族、社群、国家各个方面,可以分为两个形态,一是取悦型,二是嫌恶型。取悦型以讨好、谄媚黏附于他人,此不赘。嫌恶型指双方相互讨厌,或一方对另一方不满,但是双方互不分开,因为其中必有一方以向对方发泄不满为乐,或者从对方因为我的发泄而痛苦中得到快乐,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最典型的表现是感情破裂的夫妻双方,都不提出离婚,或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虽然不排除有其他原因,但是常听到有这样的表述:“我坚决不离婚,拖也要拖死他(她)。”还有一方与另一方有仇隙,会这样发誓道:“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这种黏附就是笔者认为的撕扯,是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撕扯。互联网的撕扯与此相类似,就是双方相互嫌恶,或一方嫌恶另一方,但决不放手,紧紧黏附,不将对方拖死决不罢休,其与现实生活的重要区别在于,生活中的撕扯双方是认识甚至非常亲密的,而互联网上撕扯的双方极有可能根本就不认识,生活上毫无交集,生活中的撕扯涉及的人非常有限,而互联网上的撕扯有可能像大兵团作战一样。互联网上的撕扯在中国当下愈演愈烈,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还得从互联网本身找原由。
互联网根本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这种改变可以借助于吉登斯的“脱域”理论来观照。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提出:“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2]。”此后他又说,“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各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2]。由此可见,吉登斯所说的“域”,是一种时空关联,或者时空情境,而正是这种时空关联和情境的不同,区分了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在吉登斯看来,前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紧密相联,不可分离,比如一句“太阳落山的时候”,既表述时间,也描述了空间,时间与空间的共在性,使得人的生存和活动是在场的,与情境不可分开。吉登斯认为随着时钟的发明,时间被“虚化”了,且由于“日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以及“跨地区时间的标准化”,进而导致“空间的虚化”,“脱域”由此而生[2]。亦即“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2]如果说时间的虚化带来空间的虚化,是现代社会下人的第一次“脱域”的话,那么互联网的出现就是人的第二次“脱域”,这比第一次“脱域”对人类的影响要重要得多。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式的“全球村”,其中聚集了巨量的人群,但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以网名示人。因此,比起人的第一次“脱域”,互联不仅使时间、空间虚化了,连人也虚化了。在互联网这个“全球村”里,人们相“见”而不相识、不相知,甚至不想、不愿与别人相知、相识,由此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冷淡、冷漠,进而冷酷,这种情况甚至传导到现实生活中。一家人在一起,各看各的手机,不谈心;一桌人在一起,各看各的手机,不交谈。这从根本改变了社会结构和人的生存方式——人类成为一群拥挤在网络上,不相识、不相知,却又在进行着频繁交流的群体,这充满着悖论,却又是严酷的现实。于是,互联网造成的“脱域”解构了中国人的黏附性,这本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真应了一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中国人(至少是部分)骨子里那种黏附性在互联网上换了一件“马甲”又出现了。
生活中撕扯虽然很不雅观,但是由于直接面对的情境性,以及看客围观的现场性,撕扯双方有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有所顾忌和节制。一旦进入互联网,节制一变而为放纵,因为“脱域”的互联网虽然拥挤着巨量的人群,但他们在身体上无法接近,在心灵上很少靠拢,这就大大减轻了人们之间的责任压力,而责任压力恰恰是人有所顾忌的原因。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认为“与人相处”这种人类存在最基本和不可撼动的特征首先意味着责任,“自打他人看见我甚至在他那方面还没有承担责任的时候,我就要为他负责”“我的责任是他人对我而言的一种、也是惟一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他人在场、他人接近的模式”“接近意味着责任,而责任就是接近”[3]。接近本来发生在现实世界,是人与人身体的接近,眼睛的对视,然后心灵的靠拢,在互联网中身体无法接近,眼睛也不对视,心灵无法靠拢,责任也就被放逐了。
中国古代学人早就意识到距离与人的道德坚守之间的关系,《论语》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也有这样的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说的是一个人,无论与父和君或民和君的距离是远还是近,都应该保持自己应有的担当和责任。当然,这是良好的发愿和理想,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距离与人的良知、责任有一定的相关性。鲍曼在分析二战时期德国大屠杀时发现,纳粹通过将犹太人的隔离,使得德国人对他们由于距离上的隔开而产生感情上的冷漠,从而为最后的大屠杀作准备,“由于不可解脱地同人与人的接近拴在一起,道德看起来符合视觉法则。靠近眼睛,它就庞大而厚实;随着距离增大,对他人的责任就开始萎缩,对象的道德层面就显得模糊不清,直到两者达到消失点,并逸出视野之外”[3]。由此可见,距离与人的道德感呈正相关关系,距离越近,相互间的道德感越强、越浓;距离越远,相互的道德感越弱、越淡。互联网让人与人之间形成无法丈量的距离,人们间感情的冷淡、冷漠,势必造成道德的滑坡和良知的丧失。
互联网的撕扯类型大体有如下几种:二人对撕、群体对撕、一群人与一人对撕。如果对互联网上撕扯者作一些推测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有过精神创伤,或者发生在过去,或者发生在当下,或者是二者的叠加。他们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让创伤得到愈合,由于现实社会道德和法规的限制,他们那种无限度的撕扯难以实现。于是在互联网上找到实施的空间。当他们稍微清醒,情绪也比较稳定的时候,他们会摆事实讲道理,但这些毕竟是以伤害别人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痛苦的,且由于网络让他们隐身,距离又让他们看不到被伤害者的痛苦,所以他们很容易就会越过底线,恶毒攻击、谩骂诅咒、刨祖坟、挖老底,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在现实中受到伤害越重,在网络上撕扯的欲望就越强。
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这种延伸是祸是福,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肢体媒介和口语媒介让人们近距离交往,文字的出现将交往延伸了,电话、电报的出现进一步作了延伸,互联网的出现将这种延伸发展到极致,结果就是鲍曼所说的“随着社会距离的寸寸增加,干不道德的事变得更加容易”[3]。
四、“撕扯”:操纵亦或被操纵
眼下,互联网的撕扯热闹非凡,乍一看撕扯者似乎随心所欲,无所不能。他们想撕扯谁就撕扯谁,今天对准明星,明天看住学者,后天攻击作家;他们想什么时候撕扯就什么时候撕扯,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平日假期;他们想利用什么话题撕扯就利用什么话题撕扯,有些是凭嗅觉,利用了话题的敏感性,蛊惑人心,有的是用手段把冷话题炒成热点。表面上看有些撕扯大咖,就像某些科幻电影中的海中怪兽,时不时会在互联网上掀起波浪。但是真以为他们在主宰、主导着互联网,那就未必,甚至是大错特错了。
罗伯特·洛根说:“实际上,互联网是民主的保障,因为国家或富人都不能控制网上的民主,这使之与报纸、广播之类的媒体形成鲜明的对比[1]。”洛根显然太乐观了,他没有注意网络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把控着互联网的动向。撕扯者需要互联网,他们是互联网上撕扯风波的客观基础,但是撕扯谁,什么时候撕扯,怎样撕扯,以及掀起多大的撕扯风波,撕扯者往往不是决定者而是被决定者。
互联网是个赚取眼球的地方,集聚人气是互联网掌控者的基本目的,而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可见,互联网虽然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但是它仍然摆脱不了谋利的本性。互联网的掌控者深知,光靠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以及那些八卦新闻吸引网民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没有那些多的新闻可用,互联网的新闻不是以天更换,而是要以小时、分钟更换的;另一方面即使八卦可以引起人的猎奇心理,但是网民阅后即走、不会久留、更不易参与,难以形成互动。互联网掌控者敏锐地发现了中国人喜欢撕扯的习性,并将其发展成互联网的一大商机。那么,事情就简单得多了,挑起争端,引发撕扯,就能最大限度地赚取眼球,攫取利益。
因此,我们今天在互联网看到的那些争得“面红耳赤”、你死我活的撕扯场面,莫不是互联网精心“导演”的话剧。一是排序,在一个互联网平台上,那些搅动人心的撕扯虽然那么富有吸引力,但绝对不可能排在热搜第一的位置,可见互联网掌控者是知利害、有分寸、懂得不能喧宾夺主的。二是选择,什么时候?放出什么人?展示什么样的观点?都需要经过反复斟酌,时间不早不晚,方能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用名人还是普通人?用多少名人?多少普通人?这些都需搭配合理,才能集聚各色人等;观点可以尖锐,甚至人身攻击,但前提必须是政治立场正确。三是扭住,撕扯是经营出来的,花费了互联网掌控者的心思、精力甚至钱财,所以决不能让撕扯双方轻易收手,一旦发现风波有平息的可能,就怂恿一方扑过去,死死揪住不放,让撕扯得以继续,实在不行,哪怕再导演一场虚假的撕扯也在所不惜,唯有热点才能带来利益的持续化。最后,套用一句名言作结——撕扯呀撕扯,多少正义假汝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