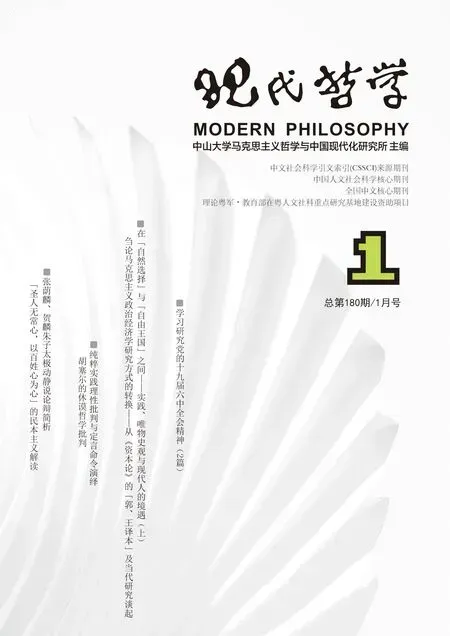精神分析语境中的移情
张浩军
“移情”一词是精神分析学、移情美学、移情心理学、移情伦理学和移情现象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但上述五种理论中的“移情”是一个同名异义词,其所对应的德语或英语并不相同。“移情”在精神分析学中对应的德语是Übertragung、英语是transference,而在后四种理论中对应的德语则是Einfühlung/Empathie、英语是empathy。由于Einfühlung/Empathie/empathy这些词在不同学科、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用法和含义,因此它们被译为汉语时又有不同的译法。在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的语境中(1)广义来说,精神分析学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但由于精神分析和治疗主要是在精神病院或私人诊所进行和完成的,而且具有临床性质,加之精神分析师和治疗师主要是精神科医生,所以笔者在这里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区别开来。,人们一般将其译为“共情”;在美学、现象学和道德哲学的语境中,人们一般将其译为“移情”或“同感”。如此一来,我们就发现在汉语思想中,“移情”“共情”“同感”等概念常常是混用的,而其中最易导致误解的混用是“作为Übertragung的移情”与“作为Einfühlung的移情”、利普斯心理学意义上的移情与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移情的混用。
鉴于此,笔者试图“正本清源”,通过系统考察和辨析“移情”(Übertragung/Einfühlung)这个概念在精神分析学、心理学、美学、现象学和道德哲学中的不同用法,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区别,揭示并祛除种种混淆和误解,同时为这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确定恰当的汉语译名。作为一项系统研究的起点,笔者将首先从精神分析学的移情概念入手,通过概念界定和辨析,澄清在精神分析学语境中,移情与投射(Projektion/projection)、移情与反移情(Gegenübertragung)、移情与共情(empathy)、移情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精神分析学的移情概念与心理学、美学、现象学和道德哲学中的移情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为我们准确理解和使用“移情”概念奠定可靠的理论基础,也为正确认识精神分析与治疗,理解医患关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一、何谓移情?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是清代文士纳兰性德《木兰花·拟古决绝词柬友》一词中的千古名句,讲得是一个“移情别恋”的故事。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说某某人“朝秦暮楚”“移情别恋”,这里指的是张三不爱李四爱王五,与精神分析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移情不是一个意思。“移情”(Übertragung/transference)这个概念最先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弗洛伊德在对病人做精神分析时发现,病人会像对待他们童年的某个重要关系人(如父母、兄弟姐妹、老师)那样对待分析师,把他所爱或恨的某个人的特质“转移”到分析师身上(2)参见[美]盖伊:《弗洛伊德传》,龚卓君、高志仁、梁永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86页。。精神病人把自己对某个人的情感转移到医生(特指精神分析师)身上,这种现象就叫做移情。后来,移情发展为精神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而弗洛伊德时代的移情概念和后弗洛伊德时代的移情概念在内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3)See Joseph Sandler, Christopher Dare, Alex Holder, The Patient and The Analyst, Revise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56-57. 以下文中注简称为PA,并标出页码。。在当今的心理治疗中,移情的工作定义是:“来访者对治疗师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由他/她自己的心理结构及过去经历所塑造,并包含从早期重要关系中转移到治疗师身上的感受、态度和行为。”(4)Jan Grant and Jim Crawley, Transference and Projection,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 以下文中注简称为TP,并标出页码。
弗洛伊德认为,移情是“为旧有的冲突创造出的新形式”,是“一种新制造出来的、变形了的神经症”,一种“新的、人为的神经症”(5)[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62页。译文有修改。。荣格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认为只有当神经症患者的移情也就是神经症的时候,这一观点才是正确的,但这种神经症既不是新生的,也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旧病复发”,唯一的新变化是医生被卷了进来,他更像是神经症的受害者而非制造者(6)参见[瑞]荣格:《移情心理学》,梅圣洁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7页脚注。。笔者同意荣格的观点。精神病人对医生的移情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她实际爱或恨的还是以前所爱或恨的人,只不过医生成了替罪羊,病人的移情本质上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欺”。如果医生真的以为自己是病人所爱或所恨的对象,并在认可和接受这种情感的同时做出积极的回应(即反过来爱上病人或对病人产生恨意),那么医生就陷入“双重身份”的境遇,“自作多情”的结果势必会破坏甚至中断治疗。
弗洛伊德认识到移情是一种矛盾的现象。病人对分析师的移情和爱,既是分析师最难克服的障碍,也是最可资利用的方便法门(7)[美]盖伊:《弗洛伊德传》,第253页。。如果分析师利用得好,就能让病人积极配合治疗;如果利用得不好,它就会变为阻抗(Resistenz)(8)参见[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61页。。因此,正确的做法是要告诉病人,他/她的情感并非源于当前的治疗情境,也与医生本人无关,而是重复呈现了他/她以往的某种经历。因此,医生应该让病人“将重演(repetition)化作回忆(recollection)”(9)同上,第361页。。如果病人能够和分析师展开积极合作,把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和记忆,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梦境和幻想,把人际关系、工作和原生家庭情况等,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分析师;而分析师在“共情”的基础上,邀请病人一起对他/她的心理问题进行探索和分析,对他们的创伤记忆或情感体验给出合理的解释,使他们认识到这些记忆或体验对他们当前生活的影响,那么就有可能“修通”(work through)病人的移情,使他们“撤回”或“升华”对分析师的情感投射。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对病人的心理进行改造,“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消除压抑的作用,或填补记忆的缺失”(10)参见[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53-354页。。
荣格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病人一旦出现移情,医生就必须将它作为治疗的一部分而努力去理解它,否则它就会变成另一种神经官能障碍;如果移情断裂了,医患之间的联系——无论是消极的(恨),还是积极的(爱)——就会中断(11)参见[瑞]荣格:《移情心理学》,第17、34页。。
二、移情与反移情
弗洛伊德通过对杜拉病例(12)参见[美]盖伊:《弗洛伊德传》,第279-288页。的反思认为,杜拉在接受治疗时,实际上把对父亲的暗恋转移到他身上,而他却无意识地对杜拉的移情实行了一种“反移情”(Gegenübertragung)(13)“反移情”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在1910年召开的纽伦堡国际会议上宣读的论文《精神分析治疗的未来前景》(“Die zukünftigen Chancen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herapie”)中提出的,后来在1915年发表的《对移情之爱的种种观察》(“Weitere Ratschläge zur Technik der Psychoanalyse III: Bemerkungen über die Übertragungsliebe”)中再度做了讨论。除了这两个文本,在弗洛伊德已发表的著述中几乎找不到其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论述。笔者对德文版《弗洛伊德全集》做了检索,Gegenübertragung这个词只出现了4次,2次是在《精神分析治疗的未来前景》,2次是在《对移情之爱的种种观察》。(See Sigmund Freud,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 -Love” (1905a), ed. and trans. by J. Strachey,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II,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8, pp. 160-161, footnote. 以下文中注简称为SE XII,并标出页码。。反移情是与移情相对置的概念,通常是指精神分析师对精神病人的移情的体验和反应。
在最先提出反移情这一概念时,弗洛伊德把它理解为分析师的一种“阻抗”:“我们开始注意到‘反移情’,它是病人对分析师的无意识情感施加影响的结果……分析师应该意识到这种反移情的存在并且克服它。”(14)Sigmund Freud,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 (1910d), ed. and trans. by J. Strachey,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I,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7, pp. 144-145.在这段话中,弗洛伊德揭示了反移情的起因(它是病人对治疗师的无意识情感影响的结果),但没有说明反移情是否是治疗师对病人的移情。不过,从他写给费伦齐(S. Ferenczi)的信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说:“在病人面前,医生应该是不透明的,他应该像一面镜子,只把病人展示给他的东西如实地展示给病人自己。”(SE XII, 118)镜子的背面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分析师是不透明的。分析师对病人的反移情不是“反过来”对病人产生移情,而是对病人的移情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应该是中立的,是基于共情的一种“理性的”理解和分析。
弗洛伊德之后,反移情概念的内涵逐渐变得丰富和复杂起来。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应该在这一概念的原本意义上使用它,即反移情是分析师对病人的非移情式的情感反应。霍费尔(W. Hoffer)和切迪亚克(C. Chediak)就持这样的观点,前者最早区分了分析师对病人的移情和分析师的反移情(PA, 88),后者认为分析师对病人的情感反应有很多种,这些反应都可以叫做“反-反应”(counter-reactions),而反移情只是其中一种。这些反-反应包括:基于病人提供的信息以及分析师的智识做出理智的理解;将病人作为一个人格的一般反应;分析师对病人的移情,即对由病人的某些特征所唤起的早年部分客体关系的再体验;分析师的反移情,即分析师对由病人的移情要求他所扮演的角色的反应;对病人的共情性认同(PA, 92)。桑德勒(Sandler)、达雷(Dare)和霍尔德(Holder)认为,“反移情的‘反’字意味着与病人的移情平行的一种反应(就像副本、配对物),也意味着对反应的反应(就像抵消、中和)”(PA, 84)。由此看来,反移情的“反”既不是分析师“反过来”(in turn)对病人移情,也不是“反对”(against)移情,而是分析师对病人的移情所做出的反应。格兰特(Jan Grant)和克劳利(Jim Crawley)也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反移情:“我们对来访者内心世界的深刻理解大部分来自于我们作为治疗师所体验到的移情与投射,以及我们对这些过程的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反移情’。”(TP, 12)
也有一部分人大大扩展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认为反移情主要源于分析师对病人的移情。例如,弗里斯(Robert Fliess)认为“移情来自病人,而反移情则来自分析师,依照定义,二者是对等的”(15)Robert Fliess, “Counter-transference and Counter-identifation”, Jou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No. 1, 1953, p. 268.;赖希(Annie Reich)认为“分析师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病人。在这些态度被意识到之前,它们与反移情毫无关系。如果这些情感的强度增加,我们就几乎可以肯定分析师的无意识情感、他自己对病人的移情,也就是反移情,被卷入进来了”(16)Annie Reich, “On Countertransfe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51 (32), pp.25-31.。格里格(R. J. Gerrig)和津巴多(P. G. Zimbardo)认为,反移情是指“治疗师可能会觉得来访者与自己过去生活中的重要之人很相似,进而对该来访者产生喜欢或憎恨的情绪及相应的反应”(17)[美]格里格、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王垒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第509-510页。。
桑德勒、达雷和霍尔德总结了反移情的11种含义(PA, 95-96)。在他们看来,将移情仅仅限定为分析师对病人的移情,这一定义过于狭窄,它与移情的原初定义(即移情是病人对分析师的情感转移或投射)捆绑得过于紧密。然而,如果认为移情既包括分析师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态度,甚至其全部人格特征,那么这一术语“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保留经典的反移情定义(弗洛伊德的定义),也“适当地考虑这一概念有用的扩展部分,这些部分包括不会导致分析师对病人出现‘阻抗’和‘盲点’的情感反应”(PA, 96)。
笔者认为,桑德勒、达雷和霍尔德的观点是可取的。如果仅仅固着于弗洛伊德的反移情概念,而不考虑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的发展,既不尊重历史,也否认了理论进步。但是,如果把反移情概念无限制地扩大化,将分析师的人格和内在心理结构的一般特征都囊括进来,那么这个概念就失去了分析的价值。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在尊重经典反移情概念的基础上,适度地将后来通过分析和治疗实践所总结提取出的具有普遍性的“新”含义添加到这个“旧”概念上,让反移情这个概念真正成为一个“有用的”、满足实践需要的分析工具。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几点:(1)分析师有反移情反应,这些反应贯穿于分析的始终;(2)反移情有可能导致治疗的困难或处置不当,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分析师没有注意到他对病人的反移情反应,或者虽然注意到了但却无法应对;(3)分析师对自己朝向病人的感受和态度的变化始终保持省察,有助于增强病人对自身心理过程的领悟(PA, 96-97)。
三、移情与投射
在精神分析学中,投射(projection)与移情密切相关,常常作为互释的概念一同出现。所谓投射“是一种将自身拥有的难以接受的想法、感受、特质或行为归于他人的心理过程”(TP, 18)。在移情中,治疗师被病人体验为与其重要他人有相似特质的人。而在投射中,病人将自我不被接受的方面“转移”到他人身上(TP, 18)。
弗洛伊德首次使用投射这个概念来指称将感受外化的过程。例如,通过将超我外化到某一权威人物身上,个体就将内部冲突演绎成与权威性或惩罚性他人之间的外部冲突(TP, 19-20)。弗洛伊德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认为投射是“针对难以忍受的内部焦虑的一种防御”,“防御的本质就是将易引发焦虑的压抑的内容归属于外部世界而不归属于自己的归因过程”(TP, 20)。荣格在《移情心理学》指出,“移情”和“投射”这两个概念“本是同根而生”(18)参见[瑞]荣格:《移情心理学》,第9页。。他通过“投射”对移情做了界定:
在无意识当中,与异性近亲的关系有着重要地位……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几乎常常被投射成父亲、兄弟,甚至是母亲……与父母之间产生的神经障碍如今转移到了医生身上。弗洛伊德最先认识、描述了这一现象,创造了“移情神经症”一词。(19)同上,第6-7页。
格兰特和克劳利认为,家庭是投射最容易发生的场所,特别是伴侣可能会否认自己的依赖、需要、攻击、野心、限制、控制等特点,而把它们投射到另一半身上。例如,男方将自己的依赖需要投射给女方,然后严厉指责女方的“过分需要”与依赖,从而使他可以远离伴侣身上属于他自己的过分需要与依赖,并维持自己独立自主的男性认同(TP, 20-21)。
沙尔夫(Jill Savege Scharff)总结了精神分析学家们对投射的不同定义:第一,投射是一种应对本能能量的防御机制,是对外部世界不愉快之内在认知的非正常移置方式(弗洛伊德);第二,投射是一个将不愉快的体验分配到外部世界的过程(费伦茨);第三,投射是这样一个过程,即自我用生理的方式将自己施虐的冲动幻想驱逐到外部世界,比如通过排泄有毒的粪便,投射到母亲或她的乳房上(克莱因);第四,投射是指某人将自体表象中不愉快的方面归因到了另一个人的精神表象身上,也就是说一种客体表象(桑德勒);第五,投射中,被投射的部分被体验为属于、来自某个客体,或就是这个客体的原因或属性(迈斯纳);第六,投射是一种正常的防御机制,它包括①表达某种不能被接受的内在心理体验,②将这种体验投射到某个客体上,③对被投射的部分缺乏共情,④作为一种有效的防御力量,会和这个客体保持距离或疏远它,⑤这个客体不会产生相应的内心体验,⑥与压抑相关,而不是分裂,⑦这在神经症中很常见(科恩贝格);第七,投射是自我中被驱逐出去的部分——(自我)抵赖不认,而归结到接收者身上(奥格登)。(20)参见[美]沙尔夫:《投射性认同与内摄性认同》,闻锦玉、徐建琴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0年,第37-38页。
从上述关于投射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它与移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移情本质上是一种投射,它是病人把过去对某个人的一种特殊情感(如爱或恨,本质上是乱伦的欲望)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而投射本质上是一种防御,一种逃避,它是把自己拥有的那些难以接受的、容易引起焦虑的想法、感受、特质或行为归属于他人,让自己感到“正常”“健康”“高尚”“无愧于心”,从而获得一种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2)移情与投射本质上都是情感或欲望的压抑,其病理学基础是神经症而非精神病。
(3)移情的方向是“病人→分析师”,而投射的方向则是“自体→客体”。这个客体可以是分析师,也可以是父母、夫妻、兄弟姐妹等。
(4)移情所“移”之“情”既可能是愉快的(例如爱),也可能是不愉快的(例如恨),它是移情主体本身具有的一种真实的情感,被移情者只是这种情感的承受者。而投射往往是自体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负面的、不愉快的东西从自己身上驱逐出去,投射到客体身上。投射者“认为”被投射者拥有被投射的某种特质,但被投射者实际上并不具有这种特质。相反,这种特质属于投射者自己。
(5)移情的结果是使被移情者产生反移情,但移情者与被移情者始终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或者说,病人最多把分析师看作他/她爱或恨的对象(例如父亲或母亲),但不会把分析师看作自己,与自己同一化。而投射则不同,投射的结果可能会导致自体认为客体具备了自体所投射的特质,因而会将自体与客体同一化。
投射这个概念在利普斯的移情美学和移情心理学中也是一个常见的概念。(21)这里的移情是“Einfühlung”,而非“Übertragung”。在移情美学中,投射指的是自我将自己的情感或意志“移置”到有生命的动植物身上或无生命的自然物体和人工制品身上,把它们“人化”,使僵死的、无生命的东西变成鲜活的、有生命的东西,使无意义、无价值的东西变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从而达到自我与对象的融合与同一,并在这种自我认同、自我肯定的活动中体验到一种精神的愉悦感(22)利普斯把移情理解为自我的一种投射或移置,所谓移情就是“我们把亲身体验的东西,我们的力量感,我们的努力、意志、主动或被动的感受,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物体中去,移置到在这些物体身上发生的或与它们一起发生的东西中去”。(Theodor Lipps, Raumästhetik und geometrisch-optische Täuschungen, Leipzig: Johann Ambrosius Barth, 1897, S. 6.)。在移情心理学中,投射指的是自我通过内在的模仿,将自己“移置”到他人身上或者他人之中,通过与他人内在地“一起做”(mitmachen)什么,去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和感受。投射的结果是自我与他人的同一化。(23)Cf. Theodor Lipps, sthetik. Psychologie des Schönen und der Kunst. Erster Teil: Grundlegung der sthetik. Hamburg und Leipzig: Verlag von Leopold Voss, 1903, S. 123.
由此看来,精神分析学中的投射概念虽然与移情美学和移情心理学中的投射共享“转移”、“投入……之中”的含义,但本质上截然不同。而且,这里的移情也不是“Übertragung”,而是“Einfühlung”。
四、移情、反移情与共情
精神分析学家或心理学家明确区分了移情和共情(empathy)(24)在心理学中,empathy一般被译为“共情”。在现象学中,这个词一般被译为“同感”。本文为了方便讨论,揭示“移情”“反移情”与“共情”之间的关系,选择前一种译法。。在精神分析或心理学的语境中,所谓共情是指分析师产生与病人同样的情感或情绪反应,这种情感或情绪反应也叫做“一致性移情”。弗洛伊德(1921)、费伦齐(1928)和巴林特(1952)都把共情看作精神分析和治疗的工具。(25)参见[美]莱瑟姆:《自体心理学导论》,王静华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63页。弗洛伊德认为,共情是我们理解他人心灵生活的一个“通道”(path)和“过程”(process)(26)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1921c), ed. and trans. by J. Strachey,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VIII,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5, pp.107, 110. 以下文中注简称为SE XVIII,并标出页码。,它“对于我们理解他人的那些本质上异于我们的东西来说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SE XVIII, 108)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或前意识的理解,这一理解使病人建立起对分析师的信任,并与分析师和治疗“联结”了起来。(SE XII, 139-140)肖内西(Shaughnessy)正确地评论道:“弗洛伊德一以贯之地使用了‘共情’这个概念(依照其词源学的结构);这个概念专门被用来刻画我们的一种深入感受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一个人试图(1)从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去完全地把握他人的内在体验;(2)进而把他人的体验与他自己的体验进行比较。”(27)Peter Shaughnessy, “Empathy and the Working Alliance: The Mistranslation of Freud’s Einfühlung”,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No. 12, 1995, p.227.
费伦齐把共情看作一种“心理学的机智”(psychological tact),它使分析师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告诉病人一些特定的事情”。(28)Cf. George W. Pigman, “Freud and the History of Empat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No. 76, 1995, p. 246.所谓“机智”就是“共情的能力”。在他看来,分析师在进行分析和治疗时必须把自己投射进病人的处境中,去感受病人的感受。分析师的移情不是在无意识中而是在前意识中出现的。(29)Ilse Grubrich-Simitis, “Six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and Sandor Ferenczi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d Techniqu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No. 13, 1986, p.272.麦克维廉斯(McWilliams)认为,共情“能帮助治疗师准确定义来访者的内心困扰,并使来访者感受到深深地被理解”。(30)[美]麦克威廉斯:《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鲁小华、郑诚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15页。科胡特(Heinz Kohut)将共情定义为“进入另一人的内在体验,去思考和感觉自己的能力”(31)Heinz Kohut, How Does Analysis C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82.。为了纠正精神分析临床实践中公式化-独断的普遍趋势,科胡特主张分析师要“持久地、共情地浸泡在病人的主体世界中”。(32)[美]莱瑟姆:《自体心理学导论》,第63页。在他看来,共情不仅是一种价值中立的观察模式,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回应模式。一方面,分析师通过内省和共情通达病人的感觉、思考和欲望,收集精神分析的资料;另一方面,分析师对病人的共情和充满关怀的回应可以缓解病人的崩溃焦虑,帮助病人管理痛苦的情绪体验。科胡特认为,我们共情和通达他人心灵的能力先天地内置于我们的心理组织内,是人类生来就有的精神装置,只不过在后天的发展中,非共情性的认知模式逐渐覆盖了原初的共情模式(33)同上,第66-70页。。奥默(Omer)提出了“叙事共情”(narrative empathy)的概念。他把临床工作的共情看作一个主动的叙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努力理解并表达病人内在情绪体验的逻辑,尤其是病人有问题的体验模式。在共情性叙事的语境中,之前看似不合理、病态的、费解的特定行为和感受方式最终得到了合理化的解释(34)同上,第70页。。
精神分析中常常存在一种对共情的误解,即认为分析师在共情体验中在自体身上产生了与病人完全一样的情感反应,获得了与来访者同样的感受(35)例如,贾晓明说:“那种与来访者(或病人)完全一样的情绪反应就是共情,是真的有了来访者的感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受同身。”(参见贾晓明:《现代精神分析与人本主义的融合——对共情的理解与应用》,《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换言之,分析师在进行精神分析时始终要和病人在情感上保持一致,而且必须在自己身上实实在在地产生相同的情感体验。当病人悲伤时,分析师要(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悲伤;当病人快乐时,分析师也要(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快乐。然而,果真如此的话,分析师是否能够承担起这种情感重负?特别是那些消极的移情或负面的情绪难道不会把他也变成一个“病人”吗?分析师的这种情感体验是否又需要通过精神分析来治疗?
在笔者看来,对共情的这种理解是精神分析或心理学的根本错误,而这种错误的根源来自利普斯。利普斯认为,共情是与他人的一种同一化,他人的感受就是我的感受,而我的感受就是他人的感受。胡塞尔正是洞见到了这一错误,才对共情做出了新的解释。在胡塞尔看来,共情既不是基于自我的情感体验而对他人的体验做出的一种类比推理(Analogieschlüsse),也不是对他人情感体验的一种“内在的模仿”(innere Nachahmung),而是以第一人称方式对他人内在心灵生活的经验,(36)Dermot Moran & Joseph Cohen, The Husserl Dictionary,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 2012, p. 94.是“对陌生主体及其体验行为的经验”(Erfahrung von fremden Subjekten und ihren Erleben)。(37)Edith Stein, 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 Freiburg: Herder Verlag, 2002, S.14.在共情中,进行共情的自我经验到其它自我的心灵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自我是像体验和感知他自己的意识那样体验和感知他人的意识的。(38)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 aus dem Nachlass, Erster Teil: 1905-1920, Husserliana XIII, hrsg. von Iso Kern,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S. 187.因为,“我”不是“他”,我不能“体验”他的体验,我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经验”他的体验,换言之,我们只能从对他人之身体的外在表现(leiblicheuβerungen)也即其表情、姿势、动作等的经验中来把握他人的心理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他人的经验只能是一种“陌生经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情在本质上是一种统觉,是一种“理解”。笔者认为,现象学很好地解除了精神分析或心理学的理论困境:分析师或治疗师只是“理解”了病人(或来访者)的情感体验,而并没有在自己身上实实在在地“感同身受”。
反移情与共情是精神分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间也存在区别。弗里斯指出,分析师的共情建立在对病人的“尝试性认同”(trial identification)上,它反映了分析师设身处地理解他人内心世界的能力。奈特(R. P. Knight)将共情与投射和内射过程(projective and introjective processes)联系在一起,两者都参与构成“尝试性认同”。罗森菲尔德(H. A. Rosenfeld)认为共情的能力是建设性地应用反移情的先决条件,但是,沃尔夫(E. Wolf)认为,在分析中反移情反应可以导致共情的失败。共情和反移情之间似乎存在双重关系,这种双重关系反映了反移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获得对病人无意识过程领悟的工具,另一方面,它是共情性理解的羁绊(TP, 94)。
五、移情与道德
弗洛伊德指出,病人与分析师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病人对分析师产生的温情和信任,很容易变质为一种爱欲上的渴求,结果,它非但无助于神经症的消解,反而使之强化和持续。而且,病人爱上分析师,这一点往往使精神分析成了笑柄。尽管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怀有恶意的闲话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精神分析冒犯了太多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所以注定会成为被中伤的对象,但他还是提醒精神分析师要注意移情之爱的危险,以避免这种尴尬的处境。(39)[美]盖伊:《弗洛伊德传》,第332页。
面对病人的移情,分析师通常会采取三种策略:一是与病人结婚,建立合法的婚姻关系,二是终止合作、放弃治疗,三是与病人发生关系后继续进行分析治疗。弗洛伊德认为,第一种方式比较罕见,除非分析师也反过来爱上了病人,而且他还没有婚姻家庭之累。第二种方式虽然更为普遍,但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病人的神经症依然存在,他/她还会继续寻求分析,爱上第二个分析师。如果跟第二个分析师的关系破裂,他/她又会爱上第三个分析师,如此不断进行下去。至于第三种方式则是被传统道德与职业要求所共同禁止的。(SE XII,160)因此,当一个分析师发现病人爱上他的时候,应该做的只是分析。他应该向病人揭示,她对他的迷恋,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爱,而只是在重演或复制一种早年的(而且几乎往往是儿时的)经验。(SE XII, 167)他应该带领病人追溯这种移情之爱的无意识的起源,把所有那些深深地隐藏在其爱欲生活中的东西带入意识,并让其处于意识的控制之下。分析师越是能够抵御移情之爱的诱惑,就越是能够从移情的情境中提取出分析的内容。而病人也会随着分析师的引导和分析,逐渐认识到她的爱产生的前提条件、源于性欲的幻想和恋爱的特点,从而找到移情之爱的幼年根源。(SE XII,166)在弗洛伊德看来,像移情这样的神经症多半是由传统的性道德造成的,虚伪和偏见让人的本能欲望得不到正常的满足和释放,结果便是压抑和扭曲。精神分析就是要向病人揭示他们致病的根源,使他们克服对于性的恐惧和禁忌,在放纵和无条件的禁欲之间选取适中的解决途径。无论何人,只要完成了这种分析和训练,认识了真理,便都能增加抵御不道德危险的力量(40)[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53页。。
弗洛伊德指出,预先认清病人的爱只是一种移情之爱,将有助于分析师对病人保持感情上乃至肉体上的距离。(SE XII,160-161)如果分析师禁不住病人的追求,认为接受病人的求爱,就可以取得病人的信任,从而加速治疗的进程,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病人可能会达到其目的,而分析师却永远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SE XII,165)对于分析师来说,他必须时刻保持诚实,因为诚实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基础,它具有教育效果和伦理价值。如果分析师要求病人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而自己却通过谎言和伪装骗取病人的信任,无疑会损害自己的权威。分析师始终应该通过反移情保持自己的中立性。(SE XII,164)精神分析的目的不是劝导人生或给人提供行动指南。相反,精神分析要力求避免扮演导师的角色,病人的问题要由病人自己去解决。为达此目的,精神分析师至多只能劝告病人在接受治疗时,暂时不要对生活做出重要的决断,如关于事业、家庭、婚姻等的选择,需待治疗完成之后再说。(41)同上,第352页。分析师在面对病人时,应该和外科医生一样,搁置一切个人感情乃至同情心,尽可能精准而有效地完成分析的任务。(SE XII, 115)
事实上,精神分析师是否可以接受并利用病人的移情进行治疗,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或医疗实践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可以说,精神分析与治疗的伦理问题,自这门学科诞生之日起就与之相伴而生。(42)参见高娟、赵静波:《发达国家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问题研究的历史发展》,《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年第3期。在弗洛伊德之后,各个国家的精神分析学会或心理学会相继推出了精神分析和治疗的伦理守则。1953年,美国心理学会(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以下简称APA)推出了《心理学工作者的伦理学标准》。这是第一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内的伦理性指导规范。在1992和2002年,APA两度对《心理学工作者的伦理学标准》进行修订,推出了《心理学工作者的伦理学原则和行为规范》, 这部规范已经成为美国心理学工作者的日常工作规范。继美国之后,其他国家, 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欧洲心理学会也都制定了本国和本地区的伦理学准则, 以指导和规范本国和本地区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在心理学工作者伦理准则的研究中,“保密原则”“知情同意”“能力胜任”“多重关系”始终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43)同上。
目前,我国也已经制定了专门的心理学工作者伦理学标准。在2007和2018年,中国心理学会先后颁布了《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以下简称《守则》)的第一版和第二版。(44)参见中国心理学会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一版),《心理学报》2007年第5期,第947-950页;《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二版),《心理学报》2018年第11期,第1314-1322页。《守则》对我国心理工作者的伦理要求做了严格而系统的规定,贯彻了国际通行的保密原则、知情同意原则、能力胜任原则和避免多重关系原则等,明确规定心理治疗人员应当建立恰当的关系意识及界限意识,按照专业的伦理规范与寻求专业服务者建立职业关系,促进其成长和发展。
六、结 语
综合上文对移情的本质定义、移情与投射、移情与反移情、移情与共情、移情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精神分析学、心理学、美学、现象学和道德哲学中,移情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是一个典型的“同名异义词”。“同名”是说,它们共同分有“移情”这个汉语词汇(尽管其西语原词也不尽相同);“异义”是说,它们赋予这个词的含义和用法有本质差别。
第二,移情和投射这一对概念往往捆绑在一起使用,而且具有非常形象且生动的用法:将A移置或投射到B之上或B之中。但它们在不同学科或思想流派中的用法也不尽相同:在精神分析学中,移情和投射常常被看作同义词,但这里的移情和投射特指病人对医生的移情或投射;以费舍尔父子、利普斯、福尔克特等人为代表的移情美学中,移情或投射特指审美主体对自然生物或无生命物体的移情或投射,其结果是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中、在无利害的主客体关系中获得审美体验;在以利普斯为代表的移情心理学中,移情和投射特指自我对他人的移情或投射,其结果是自我与他人的同一化;在道德哲学,特别是情感主义伦理学中,移情和投射特指对他人的痛苦和不幸的感同身受,被看作同情的前提和基础;而现象学则既反对上述意义上的移情和投射,也不主张将二者等同使用。现象学意义上的移情特指自我对他人的“同感”或“同感知”。这种同感或同感知是对他人的一种意向性分析和构造,是通过肉体对他人心灵生活的一种共现(appresentation)和统觉(apperception),兼具认知和情感意义,本质上是对他人之外在性和他异性的一种理解、尊重和保护。
第三,移情与反移情作为一对对置的概念,其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均有差别。狭义的移情特指病人对医生的移情,广义的移情则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移情。狭义的反移情特指医生对病人的移情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是“反过来”对病人产生移情,而是非移情式的情感反应。广义的反移情则指医生对病人的移情所做出的一切情感反应,其中包括医生对病人的移情。就移情与反移情的定义而言,我们既不应该完全固守传统,也不应该无边界地泛化,而是应该在尊重和保留经典定义的同时,重视和吸收新的理论成果,赋予旧概念以新含义。
第四,移情、反移情与共情,作为三种不同的意识活动,彼此之间有紧密关联。反移情是针对移情做出的情感反应,而对移情和反移情的识别或把握均需共情的参与。A对B的共情,既不是A产生或体验到与B完全一样的情感(意识层面的),也不是A对B产生同情(道德层面的),而是A对B的一种直接的理解或把握(认知层面的)。
第五,在精神分析中,移情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它是价值中立的,与善恶无涉。而精神分析师和治疗师如何对待病人的移情,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与病人的关系则涉及伦理问题。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分析师不应接受病人的移情,更不应利用病人的移情与其发生性关系或建立其他与治疗无关的双重关系。
移情关系首要的是精神病人与精神分析师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个自我与另一个自我(即他人)的关系。精神分析学为我们理解自我,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例如泛性论意义上的性关系、家庭伦理关系、职业伦理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在对移情、投射、反移情、共情这些意识现象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或偏差,而且无法得到实证分析和检验,因此,还需要我们借助其他的方法和理论(例如心理学、现象学、伦理学等)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