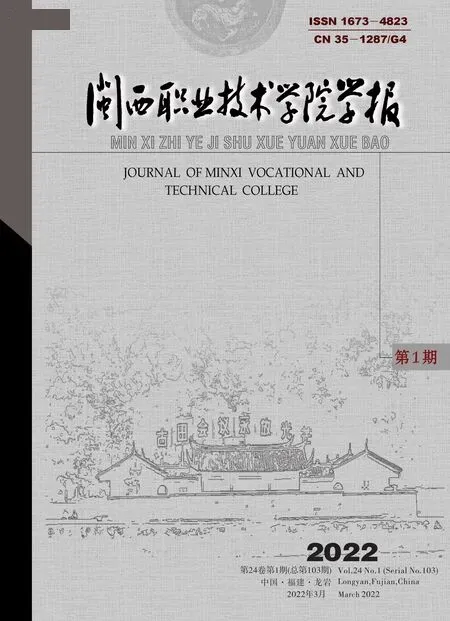交往合理化中人向自身的复归
——基于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
厉姝婴
(曲阜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现代科学的发展增强了人类对于自己生存环境的改造升级能力,同时也使现代人沉迷于工具理性的沼泽,一味地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技术异化情况下的劳动“合理化”和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为了挣脱技术异化的束缚,哈贝马斯提出了以生活世界理论为基础的自主、平等的主体间的合理交互关系。本文拟基于这种人与人即主体与主体之间平等的关系,探寻人向自身复归的实现。
一、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
(一)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形成
相比于批判社会,哈贝马斯更加注重批判作为基础理论的规范意义。韦伯在分析了传统理性由于涉及的范围广泛同时又难以进行系统的区别之后,对理性进行了重新分析和整合,将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哈贝马斯在吸收了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关的思想因素之后,从辩证的角度出发,认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基于人类的现实实践活动才得以实现,因此,哈贝马斯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辩证统一的结合,提出了调节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生活世界的概念最早由胡塞尔提出,但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局限于意识领域。哈贝马斯创造性地将实践这一概念引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进而构建出具有哈贝马斯特色的生活世界概念。
(二)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主要内容
文化、社会和个人是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三个重要部分。文化是交往参与者进行交往活动必需的“知识储备”[1],文化对交往行为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人在交往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又能够对文化进行反思和更新,从而实现文化的再生产。社会则是交往参与者的交往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合法秩序”[1]。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交往活动必然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交往参与者的交往活动又会反过来影响整个社会的秩序。因此,法律和规范必然需要社会的制定,进而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统一,使交往活动的参与者懂得如何更合理地在交往活动中实现彼此良性的主体间的互动。文化和社会为交往活动提供了知识储备和合法的秩序,作为交往活动的参与者——“个人”是“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1]。个人在交往活动中实现主体的交往能力和资质,同时在参与交往活动的过程中主体间的同一性也得到确证。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在交往过程中,作为主体在文化、社会和个人这三个要素中完成自我实现,从而达到主体的社会化,最终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生活世界是交往活动合理化展开的良好理想情景。在这其中预设了知识储备、合法的秩序和交往资质。生活世界在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展现了作为一种文化解释体系和规范传统体系的内在关系。“我无论是在肉体之中,还是作为肉体,一直都是在一个主体间所共有的世界里,集体共同居住的生活世界就像文本和语境一样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直到构成网络”[2]。生活世界正是通过交往活动的进行来影响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活动。人是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在一切实践活动中显得尤其重要。文化生活贯穿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大部分人最开始遵从着传统的交往文化,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向前推进,从而给原有的传统生活世界一个反馈。当这种反馈在社会整体人群中得到合法合规的检验后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统一性,合乎社会统一性必然也是合乎社会绝大多数的整体利益,这也进而促进了社会的统一。作为形成整体的个人在合乎群体的整体利益中得到确证,个人在社会中获得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可,实现自我的价值满足。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是个人、主体和自我三者同一性形成的外部力量,这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个人的作用。生活世界不是一个外在于其他独立系统的组成领域,也不会是存在于任何独立于其他存在领域的领域,而是各个领域或是系统之间交互糅杂、彼此影响的结果。
生活世界作为构成其他对象领域内在的一种文化机理,是以内在文化解释力量,从而投射到其他领域。生活世界内部的协调能够保证人作为主体需要的主体间的交往活动的进行,确保人作为主体的主体性。生活世界实现了人的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同一性,进而实现作为主体的个体超越性,推动社会化主体整体的超越进程。
二、人交往的现实分析
生活世界作为交往活动参与者进行交往行为展开的文化世界,在现实实践中受到各种系统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一种盲目的工具理性崇拜。人一味地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寻求对外部世界更大程度的开发利用。这种逐利性导致人们迷失了对自身的把握,沉迷于技术的研发和进步。人从“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定的尺度运用于对象”[3],演变成为冷漠的科学技术机器。
(一)人的现实境况
科学技术作为人生命的外化,应该是受人支配、为人所控制的。科学技术逐步的现实化,而科学技术的现实化就是人的非现实化,这无疑成为了一种与人相疏远的异己的力量。科学技术作为人的产品只有人在通过占有的方式获得时才给人“占有”的主观情感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影响到经济领域、政治领域,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工具力量。哈贝马斯认为,劳动是主体对于客体即人对于自然的改造,交往活动则是人与人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实践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哈贝马斯认为,劳动作为一种合目的理性的活动在技术异化的过程中将人从主体演变为工具性的、屈从于技术统治的物[4]。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为物与物的关系。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不断学习,增进个人的认知方式、解决问题方式和知识结构。
人生活在社会整体中,无法完全做到完全脱离社会经验。家庭在人早期生长过程中是社会在小范围内的投影。父母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得到的经验,不论好坏都会投射到父母与孩子的交往活动,这种好坏的投射并不能完全由父母控制。交往活动中的交往活动参与者的行为相互影响着每一个参与者,在经由参与者参与到其他交往活动中扩散到整个社会群体。现实中这种扩散无法做到完全保有原本的内涵,在“不合理”的交往活动中,往往会趋向于一种极端倾向的传播。科学技术在诞生之初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通过劳动适应社会和改造自然,“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5]。
自然界为人类劳动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料。人类从最初运用自身手足采摘到逐渐用大自然中的石块、树枝等制造原始的工具再到现在高级机械工具的制造,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越来越强,技术发展使人摆脱了自己的肢体限制,超越了肉体的支配和客观环境的限制。人为了满足自身的超越性,不断地进行劳动生产,不断地进行占有和改造物质世界。由于自然界资源的有限性,人渴望占有外部世界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也就加剧了人对于科学技术的依赖。作为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满足私有财产扩张的本质,疯狂地追求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人们完全被技术所支配。技术异化导致了劳动的“不合理化”,表面上人脱离了肢体的束缚,超越了物理的限制,然而已经被技术异化囿于一个新的“牢笼”。
(二)失去主体性的人
在这个被技术异化支配的社会环境中,人类自身以一种片面的方式即一个不完整的、单向度的人存在。人的自由时间被技术所占据,碎片化时间完全沦为技术异化统治人的温床。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被技术生成的“联想词”取代,机械输入淹没了文字书写等等。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与机械工具的“交互”远超人与人之间即作为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时间。人遗忘了自己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盲目地完成一个又一个“积累资本的任务”。人仅仅是为了满足粗鄙的物质需要,人的自我意识丧失在技术异化的统治下。技术异化给予主体一种越是被异化反而自我越是被肯定的错觉。在技术异化统治的实践活动中,人代替失去的自我意识获得的是物的商业价值,人已经被科学技术的有用性所遮蔽,沉浸于人用技术去改造和征服自然去实现特定的理性目标。
主体性的人失去了活动的丰富性,“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替代”[3]。人的自我意识被感觉的单纯异化遮蔽,失去了活动丰富性的人自然无法实现作为人的同一性和超越性。
三、人向自身复归的实现
(一)人是交往活动的主体
哈贝马斯的“交往活动合理化”表达了人作为主体的真正复归,不再被科学技术的异化支配。只有在消除了交往活动的不合理化和劳动的合理化之后,社会的人才能真正存在。科学技术异化的消除,并不是完全否认科学技术,而是将人的重点放到恢复人的本质即社会的人。科学技术仅仅只是作为一种人类用来改造自然、维持生存环境的工具,人作为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恢复对科学技术具有支配权。
在交往活动中,人才能真正地意识到自身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只有通过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人的目标不再是一味地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是如何更好地进行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人的活动在交往活动合理化之后也会更加充分、更加丰富[6]。人作为交往活动的主体在交往活动中获得了自我同一性和社会化的满足。在与他人的交往活动中,双重肯定了自我和他人的生命活动。在这种积极的交往活动中,个体的人和交往活动的另一方参与者都会获得情感和心理上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在交往活动中产生的,不能为其他活动所取代。交往活动的合理化既是对自身生命存在的肯定,也是对对方生命活动存在的赞许。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被唤醒,并在与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一步步提升,进而得到全面的复归,真正意义上的人在交往活动中得到确证。
(二)人的主体性在交往活动中的体现
哈贝马斯的“交往活动合理化”摆脱了人与技术之间的片面性,强调了人作为主体必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活动中存在。参与者通过交往活动中主体间的合作行为与外在客观世界和人的内部主观世界发生交互关系,协助主体在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中主体的地位。在历史过程中,交往活动的合理化维持了个体人的本质和整体的人之间的群体协同的稳定性,使人的历史能够不断延续发展。交往行为强调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发展,社会活动必然不是一个人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交互的过程,科学技术仅仅只能作为媒介,本质仍是人作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整体的发展以人的意志为导向,合理的交往活动取消了人被支配的状态,人的自我意识重新回到主体地位。社会人的社会化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人们以积极的态度思考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以整体为出发点,抛弃囿于自己私欲的需要牢笼。
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合理化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端,他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冷漠和人的困境。但是,哈贝马斯试图仅仅通过交往的合理化远远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如果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任何不触及根本的方式只能暂时缓解问题的发展进程,阻挡不了问题最终的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所包括的思想上层建筑都受到经济基础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之下,工人和资本家的实践活动都是以片面的满足个人生存欲望为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改变都是徒劳,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资本无限扩张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尽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没有从实质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处境,但却给出了在交往活动中人的思想文化的交流、人与人主体之间的交往中获得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的出路。
四、结语
尽管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是以晚期资本主义为背景提出,但是我们能从中提取到有效的经验和启示。在追求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从文化、社会到个人,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提出了良好的模型范式。他强调了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首先,从文化角度,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交往活动提供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回顾经典,从中吸取有益于现代交往活动的指导方法,从而改进当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其次,从社会角度,社会整体将重心放到人作为主体的交往活动中,为社会整体营造一个合法有序的交往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统一。最后,从个人的角度,积极地参与主体间交往活动。人在交往活动中体会到自身的个人同一性和社会价值,实现个人的超越性,从而达到整体的人的超越。
人的交往活动是人主体间必不可少的活动,是作为人的自由目标的实现。生活世界理论背景下实现交往活动合理化,帮助人作为主体在交往活动合理化中摆脱技术异化的困境,实现人的自我意识的复归,从而克服自身的束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