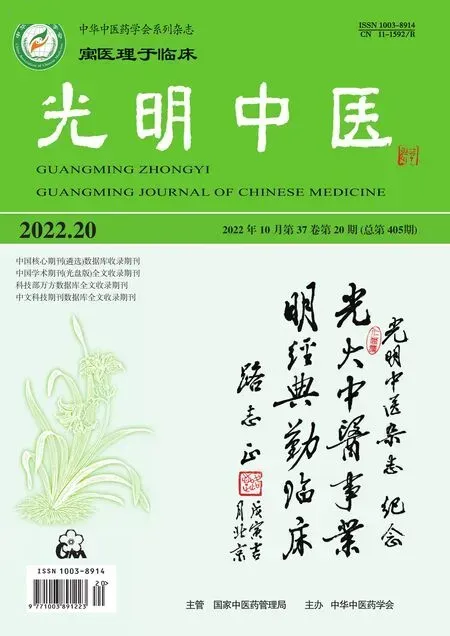唐代医学交流初探
——以敦煌医学卷子为例
张冀豫 梁尚华
敦煌医学卷子是指敦煌古籍中与医学相关的古籍著作,成书于六朝与隋唐时期。按《敦煌遗书遗书总目索引》[1]载总敦煌文献约2万多种。具体与医学相关文献《敦煌古医籍考释》[2]中载其有104种。医方达1100余首,居现有医学出土文献数量上占据首位[3]。其相关内容中,除医经、本草、诊断等医学书籍,更有非汉语医学文献的传译与佛教医学等相关内容。其医学文献数量相对集中,且能呈现一定时间内敦煌医学活动的全貌提供理论基础,因此对完善中医学唐代与唐以前交流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本文以近些年来敦煌医学研究为载体,以医学理论、医籍融合、医者形象、医学互动、药材使用为方向,立足敦煌医学卷子,探究唐代域外医学的交流情况。
1 医学理论
敦煌出土张仲景《五藏论》署名张仲景撰,已知抄本4份P.2115;P.2378;P.2755;S.5614。书中论述以黄帝与耆婆并提,四大五常并用[1]。显示出浓厚印度医学与中原医学的交融。其中P.2115V《张仲景五藏论》原卷题作“五脏论一卷,张仲景撰”。依其题目可知,五藏理论来源于中医,但同时其内容中亦有“四大五荫,假合成身。一大不调,百病俱起”[4]。关于四大说法,可与印度阿育吠陀医学寻找渊源,其四大指地水火风。吴天竺沙门竺律炎共支越译《佛说佛医经》:“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阐述了地水火风理论与身体的联系。而同时,关于张仲景《五藏论》是否为托名所做,目前尚未有定论。但五藏与四象理论的同时出现说明,敦煌地区医学的相互交融。尤其中印医学的交汇编纂,奠定了唐代医学交融的特点。
敦煌本P2675《新集备急灸经》云:“四大成身,一脉不调,百病皆起”。参照《大正新修大藏经》,此书为日本大正13年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的佛经编纂合集,收入中国历代各版藏经目录和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写本和刻本藏经目录。其中《说无诟称经疏》卷三经文“四百四病者:一大不调,一百一病生”。此处二者记载文字类似。关于“脉”与“大”的区别,有学者考证后,认为此处灸经为人体经络穴位所灸之处,灸经强调脉的重要性,因此作者便将“一大”改为“一脉”[5]。印度医学认为,构成人体的四大因素保持了人体的平衡,这与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相类似,四大理论在中医灸法中的吸收应用,强调灸法治疗疾病之多,与灸法脉的重要性。
2 医籍融合
2.1 《医理精华》《医理精华》由公元7世纪印度医学家拉维笈多编纂。《医理精华》(Siddhasara)音译悉昙娑罗,是印度生命吠陀(Ayurveda,音译阿输吠陀) 医学体系中的一部古代医学著作。记载了阿育吠陀医学理论及相关疾病治疗。其最初由梵语书写,随着书籍流传,转译为多种语言。其中于阗语本出自敦煌藏经洞,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及印度事务部。另可见该书籍,回鹘文医学残卷(Si.22.10;Si.6.31).回鹘本与梵文本存在差距,这可能与流传过程中多种医学(民间,印度,中医)等交叉融合相关[6]。
2.2 《耆婆书》《耆婆书》作为一部印度古典医学著作,是一部药方集。于阗—梵语双语写本出自敦煌藏经洞(IOL Khot87-110)转手斯坦因,藏于大英图书馆。可看作是敦煌地区医学交流的融合产物。敦煌在一段时间内属于于阗,因此该地区医学出现印度阿育吠陀医学融合。是与于阗本土医学的交叉融合[7]。
2.3 医学残卷敦煌医学卷子中,以藏语书写的医学残卷有医疗术残卷,火灸疗法写卷,针灸穴位图,藏医方残卷,脉诊残卷等。其中“火灸疗法”(P.t.1044)部分还明确指出:“本医方是从印度王土搜集的外科手术疗法之一”[8]。其中有“取自府库的治疗各种疾病的医方”以及“本外科手术疗法医方,并非出自库藏,是在搜集所有医方的基础上,再结合象雄的疗法而写成”[9]。这些写卷不仅体现了当时藏族人民的医学成就、宗教(苯教、佛教)与医疗的关系以及藏医疗的民俗特点,也体现了藏医与印医、中医之间的交流,甚至还反映中亚对其影响。
3 医者形象
活跃于敦煌地区的医者形象可大致分为中医,僧医,胡医。据现有医学材料可将医者以此暂且划分。
3.1 唐医唐代医学教育完善,唐太医署的设立为唐代医学教育标准化奠定基础。有文献指出,敦煌地区的医疗已与长安无恙[10]。包括医疗场所,医学官职的设置。P.2657载《唐天宝年间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令狐思珍,载五十一,翊卫,医学博士”。此为敦煌卷子中记载惟一敦煌地方医官[11]。医学博士在敦煌的设立,是唐代对州道地方区域医疗的重视,同时依照卷子标题,敦煌县差科簿而并非单设于敦煌郡。可看作是唐代官方医疗在郡县范围的普及。
3.2 僧医敦煌地区由于佛学东进的影响,大量僧人活跃于敦煌地区。由于僧人佛学的影响,敦煌地区的寺院乐善布施也成为其区域特点。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敦煌文献中记载10余人。僧医借助寺庙,以佛教为载体,中古时期的佛寺僧尼,在医疗活动中承担过较为重要的社会角色[12]。
比较显著的例子是,佛教徒在救治麻风病人时,能够身心投入,给予关爱。道宣《续高僧传》记载了数位高僧这样的事迹。如天台山瀑布寺释慧达:“有陈之日,疠疫大行,百姓毙者殆其过半。达内兴慈施,于杨都大市建大药藏,须者便给,拯济弥隆”。慧达法师为疠疫百姓在杨都设立大药藏,进行免费施药,救助了众多的普通患者。北齐的僧稠法师:后移止青罗山,受诸疠疾供养。敦煌斋愿文类型的文献中,有一类是患文,主要针对患者而用,旨在祈祷神灵,祝愿患者早日康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BD192《诸文要集》的第72~78行,也是“患差”和“妇人患差”的内容[13]。
3.3 胡医胡人在敦煌的出现伴随丝绸之路,粟特人生活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自东汉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 此处关于胡医的记载,敦煌文献中可见粟特人史再盈医疗记载。S.4363载其“习耆婆秘密之神方”“效榆附宏深之妙数”[14]。耆婆之术来源于印度,榆附为上古中原名医,中印两处医学汇聚于粟特人史再盈。其身上体现了粟特,中原,印度的三重特质。S.367《沙州伊州地志》伊吾县:“火袄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有袄主翟槃陀者……以发系其本”。翟槃陀是粟特人[15],此段记载肠外科手术相关,作为粟特人医疗实践的示例。
4 医学互动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塞,沟通了西域与长安经济的同时,也同样存在医事相关活动的互动。这其中就包括医药贸易、医籍以及药方相关。
于阗国(前232—1006年)是古代西域佛教王国,中国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于阗位于塔里木盆地南沿,处于长安,中亚,西藏交汇之地。圣彼得堡所藏敦煌文献中,至少有3件汉语医学残卷出土于麻札格地区。其中Or8212/720残简中出现“妇人不用”“两枚”“以骨石,鸡子”[16]。据陈国灿[17]推测,其内容涉及相关本草药物说明,但未涉及具体医书。除于阗地区出土资料外,敦煌地区亦出现先关于阗语书写卷方[14]。陈明对比了印度医学著作《医理精华》,发现敦煌出土的IOL Khot S.9“糖蜜与牛奶合煮。它应该温服。它(此剂药)可利尿”[13]。值得讨论的是,敦煌地区出土的该医简以于阗语书写,其内容由于印度医学《医理精华》内容存在相似性。因此有理由相信,唐代敦煌西域医学的交流已经出现,并且伴随经济,贸易,交流呈现出融合态势。
由于吐蕃在公元7世纪强盛后,敦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吐蕃的领地。因此在出土的相关医学文书中,可见到医学典籍与民间验方的集合。P.t.1057《医疗术》“取开自府库的治疗各种疾病的医方”此处,府库即为官方库藏。另有民间火灸疗法等疗法收集。如p.t127.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地区流传的吐蕃医学相关中,半数以上的植物药名为波斯梵语音译而来。说明其与印度阿育吠陀医学的深远联系[17]。
5 药材使用
中医学治疗强调三因至宜,即因时,因地,因人。因此不同区域的药物使用便出现一定的差别。敦煌本《张仲景五藏论》中引用敦煌道地药材“蓝田玉屑,中台麝香,河内牛膝,上蔡防风,晋地龙骨,泰山茯苓”[18]。此类药材的使用在中医中占有较大比重。药物治疗功效涉及解表、活血、安神、健脾等功效。
除相关本草类著作中所见药物。P.2882残卷亦有相关唐代医学方剂记载[19],其中染发方中涉及阿愚濡潬泥,其名称来源于印度。因此在药物的使用中,具体的治疗已经涉及中外药物的联合使用。
而同时关于另一味药物石蜜的使用,是中印,中波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20]。其在敦煌医学中用作眼疾,上气,咳嗽,吐血等诸多方面。P.3930医学卷子中载“治眼风赤痒方”“治上气气断方”“治上气咳嗽方”。以医方推测,其使用原理来自对蜜润下功能的发挥,因此对于咳嗽,风燥等一类需滋润类药物进行治疗,具有良好效果。而同时由于,外来药物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使用功能的改变。此外,在印度医学中,《大正新修大藏经》:“若令人转老作少者,取生石蜜和药涂面及涂发,即如三十五男女相似”[21],此处石蜜单独使用,用作养生延年佳品,在药材不同的使用背景下产生了差异。
6 结论
敦煌医学的出现伴随丝绸之路的兴盛。其发展考量可从2个维度进行考量。①六朝到隋唐时期见证了中古时期的发展,医学卷子见证了唐代的医疗与发展。②地理跨度,由于所处西北地区的区域独立性,使得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连接成为连接西亚与西藏,印度的重要枢纽。加之历史上,敦煌地区曾被于阗、吐蕃等占领,因此亦受少数民族等医疗文化的冲撞。因此医学卷子的出现常根植于中原文化,亦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这对研究唐代医学与域外医学的研究提供了文献的重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