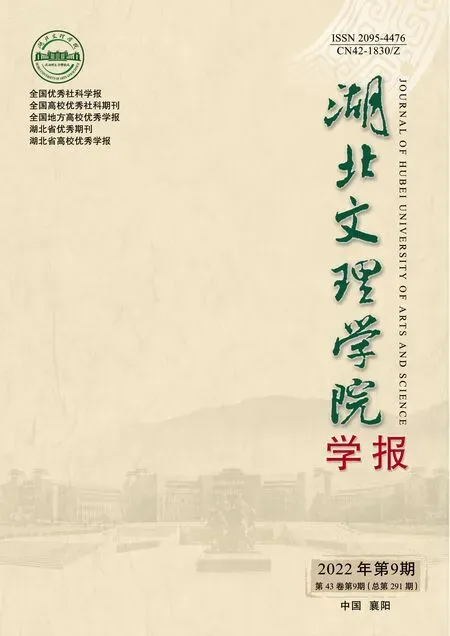道人忘我我忘言
——解读禅诗中的“我”
梅雪容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禅宗又名佛心宗,最初由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于公元520年带入中国,禅宗的思想随着禅宗中国化的广泛流传,其禅学思想注入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禅诗作为诗歌,是文学和宗教学的结合体,自然兼具古典诗歌和宗教文学的特征。纵观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唐时中国古典诗歌已然成熟,并产生了创作高峰。诗体形式成熟完备以前,人称代词“我”是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发声者及代言人,经常出现在集体创作的诗歌里,早期文人诗歌也会以第一人称来突出个人的情感,表达文学主体的精神。而当诗歌创作技法日益成熟并形成特有的审美范式后,尤其是自唐以来的近体诗里格律诗严密的规范要求,加上中国道教哲学文化里关于“坐忘”的浑然境界、文学理论关于“韵外之致”的要求,文人开始避免在古典诗歌中使用人称代词,所以古典诗歌里人称代词“我”的出现频率骤减。但是这种情况在禅诗里却不然。由明代僧人释正勉、性通同编选的诗集《古今禅藻集》共28卷,收录了自东晋至明万历年间366位僧人2829首诗歌,其中“我”出现了445次。由吴言生教授和辛鹏宇教授编选的《佛禅大智慧:禅诗名篇一百首》的100首诗里,“我”出现了20次。由姜剑云教授选编《禅诗百首:禅的智慧》的109首诗里,“我”出现了24次。
禅诗是参禅者表达理解禅、修习禅、参悟禅的心得体会的诗歌或者宣扬佛禅哲理、表现佛意禅趣的诗歌。狭义的禅诗[1]指禅宗传入中国后产生的具有禅意的佛教诗歌,且禅诗的创作者一般都是僧侣。禅诗作为诗歌,自然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但实际上,禅僧在示法时不一定完全遵守古典诗歌的形式规则,而是即兴吟咏出偈语,偈(梵文Gāthā,音译“偈陀”),是佛经中的唱词(Budhist’s chant or hymn),因为大多是诗的形式,有的四句,每句四至七言不定,有的会由梵文32个章节构成,僧人常用这种四句的韵文来阐发佛理。这种本身外来的诗歌体裁,与中国诗歌结合后,形成了很多韵白交替的体裁样式。故,禅诗里会频繁有人称代词“我”的出现,这里的“我”不再仅仅是单纯的人称代词,不仅仅代表个体的存在和个人的想法,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含义。这些“我”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禅意,反映了不同的禅思。
一、古典诗歌角度:有我之境中的“我”
中国古典诗歌美学里最讲求“余韵”,要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所以往往要求含蓄蕴藉,意境深远,言有尽而意无穷,而避免简明直白的描述。所以“我”的出现,往往就如同叙事类散文一样明白如话,直截了当地说出主人公的行为和感想,这在中国古典诗歌是不看好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将作词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2]
这里的有我之境不一定会有人称代词“我”的出现,但是皆通过“我”的行为暗示出了主人公的情绪,主观情绪的调动明显影响了创作心态从而产生了显性的情感表达作品。王国维认为“境界”是穿过了语言层面,达到了对作品中人的主体本真存在状态的把握。[3]就像存在主义萨特将存在分为“自体存在”和“自觉存在”,自体存在是物件自己本身的存在,而自觉存在是自我意识的存在,具有主动性和目的性,主导自身思想情感和行动,“自体存在”和“自觉存在”的对立统一就好像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统一一样。而王国维所说的“我”与“物”之间便是如此对立统一的概念,从哲学的角度,“有我”和“无我”都是认识世界的不同思维方式,有我之境是以自我为认识世界的中心,而无我之境,以物观物,虽然缺乏“我”的个人色彩,却是“大我”之所在。在王国维的叙述里,有我之境的质量远不如无我之境,诗人主体消失在诗外,自然万物来替代抒情主体发声,才更具有美感和境界感。在这种传统的美学价值影响下,创作手法越是娴熟的作品,人称隐匿的现象越是突出。[4]
由此,我们以认识世界的不同思维方式而判断有无我的境界,所以人称代词“我”的出现,并不能代表一定是有我之境。故而,禅诗里的“我”,既有有我之境的“我”又有无我之境的“我”。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寒山《吾心似秋月》)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郁山主《悟道诗》)
譬如寒山诗中“吾”“我”就是很明显的以我观物,把“我”与物相比喻,又以“我”作为主人公进行对话。第一次“吾心”的出现,是用秋月和碧潭两个清纯明亮的事物来比拟悟道时的心,圆满光华,了无杂念,用碧潭的清澈与秋月的皎洁互相映衬来形容开悟时心的皎洁程度。“教我如何说”中“我”的再次出现表达了“我”在参禅时的理解:禅的境界不可言说,只可意会。仿佛“我”是在给新来的沙弥讲禅,然而“道可道,非常道”,语言难以表达禅悟时候的心灵状态。这首诗是寒山的悟道诗,是典型的有我之境,在“我”悟道时的心理状态之下,天上的秋月、清澈的水潭都仿佛衬托着“我”的心境,却又难以与之比伦,万事万物万景皆着抒情主人公之色彩,为其烘托内心的氛围。
而郁山主的悟道诗中,出现了人称代词“我”,并且看起来似乎是一篇叙事的白话顺口溜。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明珠,就是人生来具有的佛性,然而长期以来被尘劳迥脱所蒙蔽,而今,终于去除了物欲的覆藏之后,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佛性之光熠熠生辉,放光动地,照破千山万水。这里虽然出现了人称代词“我”,但是却属于无我之境。因为无我之境中的“无我”是大我之体现,不局限于个人之本心本性,是芸芸众生之大我。这里的“我”不能够仅仅局限于禅诗的创作者本人,这里的“我”是郁山主为了阐述这种禅理用的,“我”代表着世间众人,是“大我”。而且“我”与明珠本是一体,明珠便是本我、本心、本性。郁山主是白云守端的受业老师,他想表达的是,禅的宗旨是让我们拨云见日,将原本应该纯净的本心去除尘劳迥脱而重放光芒。
从中国古典诗歌境界说的角度解读禅诗,禅诗中的“我”既具有给门生讲禅时、自己参禅悟道时的有我之境,也有将自己和芸芸众生化为一体时的无我之境。这种与中国古典诗歌“我”使用方式的不同,打破了王国维的境界说,禅诗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融为一体,从而揭示出更深层次的禅意。
二、禅宗哲学角度:般若空观下的“我”
禅宗哲学的重要思想渊源是般若空观。般若,梵文Praiā,智慧、明的意思,是成佛的特殊认识。这种认识视世界为因缘和合所生,诸法皆由众缘假合,万物缘起缘灭,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所以性空。“般若”即“空观”。般若慧是“空慧”或“中道觉慧”的最高智慧,也是佛教的最高、最完满的真理。禅宗哲学象征意象,以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为基石,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严密、庞大、繁富的象征话语体系。[5]禅宗哲学里公案颂古里的象征意象,与“我”密切相关的当属“本来面目”,而重现“本来面目”就是禅宗的终极关怀,超越性是“本来面目”的根本特征。基于吴言生教授揭示的禅宗哲学象征体系的本心论,“本来面目”下的“我”是“父母未生时”的“我”,我们刚诞生于世时就寸丝不挂,素面相呈。这也与孔子的教育思想相同,认为人先天本性纯洁,人性本善,个体的差异靠后天形成。正是如此纯洁的本来面目被世俗的尘劳迥脱所蒙蔽,从而迷失自我,舍父逃走,如同渴鹿乘阳焰,反认他乡作故乡,而最终开悟,坐断十方,才能够达成不二境界,重现了本来面目的光芒。所以说禅宗哲学象征以本来面目为起点,以明心见性为终点,终点即起点,本源即终极,表达了从更高层面上对人类精神纯真本源的复归,所以禅诗里出现的“我”既是第一层的“本来面目”,又是对“本来面目”的超越,达到了最高层的“触目菩提”的开悟境界。例如上述的寒山诗的“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和郁山主的诗里的“我有明珠一颗”,并非是单纯的譬喻,这是本心论下的典型象征:“心月”“心潭”“心珠”。混沌未分之时,明暗未分之时,日月未分之前,万事万物之初,又缘起缘灭,一切都是性空,当“我”参透禅理开悟之后,获得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境界。事事圆融,芥子须弥,秋月也是“我”,碧潭也是“我”,水月交融,澄澈宁静,是净裸裸的“我”,也是清寥寥的“我”;明珠也是“我”,光耀也是“我”,珠光交映,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这种芥子须弥、事事圆融的境界,不仅是参禅者、禅僧可以感悟的,很多具大智慧的人也能够体会到。像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曾有过类似的感悟。他一生处于北宋政治斗争风波后,历经荣辱沉浮,到了晚年思想深邃沉稳。南朝宝志禅师一生传奇,圆寂处建宝公塔。王安石于黄昏时分登上宝公塔,也获得了禅性的超越。
倦童疲马放松门,自把长筇倚石根。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鼠摇岑寂声随起,鸦矫荒寒影对翻。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
(王安石《登宝公塔》)[6]
登宝公塔的路程蜿蜒崎岖,山势时缓时陡,正如人生之路也坎坷不平。登上塔后,远眺长江,明月如白昼,浮云动黄昏,这是诗人眼前的景色。老鼠发出的窸窸窣窣与沉寂的景象形成对比,乌鸦矫健的身姿与静态的江面形成对比,动静之结合,有声和无声之结合。在壮阔宁静之景下,诗人被环境所感染,与自然融为一体,早已没有了物我之分,自他之别,沉浸在忘我的境界之中。
最后一句“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这里出现了人称代词“我”。道人忘我,而我忘言,这种宁静寂寥的氛围之中,已经没有了主客的概念,已经进入忘我与忘言、自他无二之境。此时的诗人是开悟的,身心明澈,正是禅宗所倡的顿悟,也是《庄子·外物》中的“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7]的境界。第一个“我”是道人自己进入了忘我的境界,第二个“我”是诗人自己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这种生命体验。而隐藏的话语,便是在如此氛围之下,万事万物皆已相忘,人心与万物的感应是生命的共感,我之中由此生命之存在,物之中亦由此生命存在,故人和自然浑成不可分割之整体,互相渗透,水乳交融。
从禅宗哲学象征的角度解读禅诗,禅诗中的“我”既具有“本来面目”下的纯真之“我”,又有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达成般若智慧的“我”。“我”的意义被扩大了,更加哲学化、宗教化,成为了般若空观中的一个独特的概念。
三、当代诗歌角度:俗世色彩下的“我”
禅诗虽属古代文学范畴,但依旧具有现代意义。其白话程度与传统古典诗歌不尽相同,而与现当代新体诗有一定的联系。故当代诗歌理论对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代诗人西渡在《守望与倾听》中写道:“当代汉语诗歌毫无疑问必须从我们日常使用的口语中提炼词语,但是那种在诗歌中不加选择地使用口语的做法同样是可疑的,事实上是放弃了诗人对语言的责任。其后果是使诗歌降低为语言,而不是把语言提升为诗。”[8]西渡认为,口语中常用的人称代词放在诗中,会增强诗歌的俗世色彩,会让人称代词获得自身独立的情感和意义。比如像“我”这样的人称代词,可以加大诗人个体化写作的力度,同时更加具有真实感和亲切感,使诗歌不仅能打动诗人本身,也能达到感染读者的作用[9]。
倪文尖教授在解读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重点关注了诗歌里面出现了很多次的人称代词:“我”和“你”以及“他们”。他认为,这首诗的起点是“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和“关心粮食和蔬菜”,是海子对世俗生活的拥抱。海子要的幸福既要是有世俗生活的幸福,还有那样一个周游世界、以梦为马的超脱的幸福。然而,当祝福到达“祝你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个事实象征了或是提醒了海子更深层的意识,他与世界上芸芸众生们是不一样的,芸芸众生是可以在尘世中获得幸福,这也间接影响了海子的卧轨。而这一个重点的提示就是人称代词“你”的出现。“你”和“我”是有区别的,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是对立的,不是一类人。这就是人称代词所能够带来的俗世色彩。
而禅诗深谙这层用法,大部分的禅诗里的“我”都是充满佛性禅意的,与芸芸众生是不一样的,唐代诗僧王梵志的《观影元非有》有云“众生随业转,恰似梦寐中!”众生迷失覆垢,而“我”是来度化解救众生的,我是明澈的。
三间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境闲;莫作是非来辨我,浮世穿凿不相关。
(龙山《示法偈》)
禅庭谁立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直待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
(可遵《题汤泉》)
龙山禅师又号隐山和尚,一生隐居,山中终身不入尘世。龙山大师的《示法偈》中,写到自己的物质环境是三间破小的茅屋,一生所居简陋颓然,然而开悟下的自己则在万种境界之下都能安然自若。只要心地安然,简陋的茅屋也是最好的居所。只要心中生起般若神光,不管什么环境之下都有无往而不适的安闲。这就与尘世中那些穿凿杂事、是非成败,完全无关,因为红尘世界早已被“我”置之度外。正所谓“心远地自偏”,心境到了,婆娑浊世也能化作清凉净土。在这里的出现的人称代词“我”,就是把“我”与浮生世间的众人化作对立,一个“莫”字,是对俗世红尘的相忘和割舍。浮生若梦,为心则安。
宋代诗僧可尊也在庐山汤泉题诗,借物抒怀,赞美了汤泉洗涤众生尘垢的慈悲。而这里出现的人称代词“我”,也是与众生对应,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流。可遵禅师以汤泉自比,觉得自己负有普度众生的责任,愿为汤泉水,功成身退后,和光同尘归。正是这种“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乘度化精神,与“我不下地狱,谁下?”的“我”充斥着同一种慈悲的宏誓大愿,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结合当代诗歌里关于人称代词“我”的使用效果,在这类训导性质的禅诗中,人称代词“我”的存在虽然拉远了创作主体与俗世的距离,但更加具有真实感和亲切感,才能打动读者,方便禅学思想的流传。
众人有口,不说是,即说非。吾师有口何所为,莲经七轴六万九千字,日日夜夜终复始。乍吟乍讽何悠扬,风篁古松含秋霜。但恐天龙夜叉乾闼众,畐畐塞虚空耳皆耸。我闻念经功德缘,舌根可算金刚坚。他时劫火洞燃后,神光璨璨如红莲。受持身心苟精洁,尚能使烦恼大海水枯竭。魔王轮幢自摧折,何况更如理行如理说。
(齐己《赠持法华经僧》)
当然,并非所有禅诗中的“我”都是去度化众生的存在,也有被度化的存在。比如在晚唐诗僧齐己的《赠持法华经僧》里,这里面的“我”就和众人一样,而度化众生的确是“我”遇见的禅师,也就是标题里的持法华经僧。法华经是大乘经典《妙法莲花经》的简称。这首诗是歌颂这位超越是非、口诵莲经的得道禅师。众人是非之口和吾师的莲花之口,仿佛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禅宗教育弟子,要不落是非、破除分别之心。那么,这位得道禅师到底说了什么呢?他日夜持诵多达七轴六万九千字的莲花经,乍吟乍讽,悠扬婉转,让他的心灵境界如风篁古松,秋霜早临,肃然宁静,连天龙八部的夜叉诸神都要洗耳恭听。然后出现了“我”,“我”是一个和芸芸众生一样,要接受禅师教育的存在。与之不同的是,“我”听着这莲花经,开悟了。“我”知道念经是功德圆满的重要法门,如同金刚坚利,能断绝是非妄念,破除尘世烦恼,能得六根清净。而念经达成的圆满功德,如不灭的火莲,能使烦恼之海水枯竭,能使“我”身心俱静,逃出苦海,外魔业障难以入侵。这首诗则是以一种学徒的心态去接受、感恩、赞美得道禅师的教诲,感恩,赞美,赞颂了法华经的种种功德。
这里的人称代词“我”的使用,将创作主体与众生化为一体,“我”就是普通众生中的一员,“我”可以通过参禅而获得境界的提升,那么“你”也可以。也是可以打动读者,让平民信徒阅读时更能够感同身受,有利于禅学思想的传播。北宋诗人苏舜钦《题广喜法师堂》的“我为名驱苦俗尘,师知法喜自怡神。未知欢戚两忘者,始是人间出世人”也当是如此。
从当代诗歌鉴赏的角度来解读禅诗,禅诗中的“我”既有和俗世红尘的众人一样、接受禅宗思想教导的存在,也有与芸芸众生对立、要去解救苦海众生的大慈大悲、充满佛性的“我”。禅诗里的“我”出现的对立性,也是为了让禅诗的受众更容易感同身受地接受引导,是禅诗创作的一种手段。
四、弗洛伊德理论:自我、本我、超我
精神分析学说的弗洛伊德提出了人格结构理论,他将人格模型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10]。
他认为,人刚出生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格结构,就是本我,本我遵循快乐原则,是人类的本能,不受任何约束,属于人格结构的生物成分,往往隐藏于无意识之中,人自己无法察觉到本我的存在。第二个人格结构是自我,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属于人格结构的心理成分,会调节本能与环境的关系,自我的任务将本我的冲动控制在无意识之中。第三个人格结构是超我,代表着社会的理想和价值观,属于人格结构的社会成分,对个体行为的好坏和善恶有着道德规范的限制。本我、自我、超我的相互补充、相互对立,决定了人格的动态性。中国文学的传统特色往往很难接触到人性最根本最真实的地方,多是伦理价值观下的理想化和善美化,而禅诗往往会接触到最本真的人性的“恶”,禅修为破“恶”而生,要明心见性。所以精神分析学说有着独特的参考意义。根据人格结构理论,禅诗中的“我”也可以对应到三个人格结构里去:本我就是人类初始的欲望,是贪嗔痴,是安禅要制的毒龙。自我就是僧侣或者参禅者通过戒定慧等外在的形式来约束来自本我的欲望。而超我的境界,则是是禅悟时的佛性,此时的超我是自信的、圆满的。但弗洛伊德理论的超我和禅诗中的超我有不同之处,前者往往会因为过多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以及过于完美的标准,而对自身的本我欲望的存在,以及不能够达到的圆满而感到羞耻罪恶和道德焦虑。但禅宗的超我不会,因为这一境界已然是圆满的,不二的,超脱的。
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这么会,方得契如如。
(良价《悟道诗》)
良价禅师是晚唐诗曹洞宗的创始人,有一天他乘船过河,看到河面上自己的倒影,豁然开朗,创作出这首诗,诗中借形体与影子的关系来表示对真我和佛性的体会。“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不要从别处寻找,因为会越求越远而偏离真正的大道。这里出现的第一个“我”,是佛性的大道,是不应该偏离的正确之路,要从自己的亲身历练才能求得。“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第二个出现的“我”,便是独自行走在追寻的路上的“我”,是一个求道者,有着自己的追求的人。然而独自寻求的路上却能处处就见到他(渠,古汉语是“他”的代词)的面貌。这里的“渠”应该对应的是第一个“我”,也就是佛性的超脱的那个“我”。他是如此庄严,正如本来的自己。而现在的我如此卑微,完全不能与他相比。“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里的第三个“我”,就是被尘垢覆盖、物欲横心的自己。在禅宗哲学象征里,“本来面目”既是起点,也是终极。他本来是我的样子,但是经过了世俗侵染的现在的我,已经不具本来的面目了。最后,“应须这么会,方得契如如。”就应当这样来体会本我与大道,才能契合得自性如如。
这首诗有点复杂,出现了三个意象。第一个是诗人正在寻找的“我”,是超我,是剥除烦恼心垢的“我”,是心怀恬淡闲适的“我”,是超越生死万缘顿息的“我”,是禅的最高关怀。第二个是正在寻找超我的“我”,是自我,是每一个参禅者,都希望通过修禅完成自己人生的追求,是自己对自己的约束。第三个是被原始欲望利欲熏心的“我”,是本我,本我堕于尘世之中的四大五蕴,以身为碍,逐物迷己,迷却自心。所以诗人是自我在追寻超我的路上,顿悟,发现本我的存在,超脱出本我的限制,还原本来面目,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所提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角度来解读禅诗,禅诗中的“我”也同样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贪嗔痴,自我是戒定慧,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方能达到超我的境界——明心见性。人格结构理论本身和禅学有一定的相关性,刚好在禅诗的“我”的应用上被直接显示出来了,这与禅宗追求本来面目、积极剖析自我的初衷有关。
宋代诗僧仲皎的《庵居》里写道“啼切孤猿晓更哀,柴门半掩白云来。山童问我归何晚,昨夜梅花一半开。”禅诗里有各种各样的意象来表现禅理,往往以浅俗易懂、明白如话的形式来表达诗人深刻的理解和体悟。然而根据王国维的境界说的理论,禅诗兼具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而基于吴言生教授提出的禅宗哲学象征的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形成的哲学体系,“我”是本心论和境界论的结合体。“我”的出现也让禅诗增添了俗世的色彩,时而是俗世中芸芸众生的一员,时而是拯救苍生疾苦的慈悲大乘。禅诗中的“我”也对应着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本我、自我、超我。禅诗里的人称代词“我”的大量出现,打破了传统古典诗歌审美要求的朦胧感,突出了抒情主体,这种自我观照与主体感受的投入也让禅诗更能够打动读者,宣示佛理,启发众生。
禅诗是开悟者窥见禅机、证悟佛道的大智慧之体现,是澄澈明了的人生境界之感悟,对现代人的生活指导,有着独特的现代意义。而禅诗中出现的“我”则是自我精神的分析和觉醒,是每一个修禅者对自我认知的开悟。只有澄澈清楚地剖析自我,才能够了解价值,体悟人生,才能够以自己为导向,开悟更多的人。这里的“我”不再仅仅是单纯的人称代词,不仅仅代表个体的存在和个人的想法,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含义。这是禅诗中的“我”与传统古典诗歌中“我”的不一样的用法,借于此,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禅机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