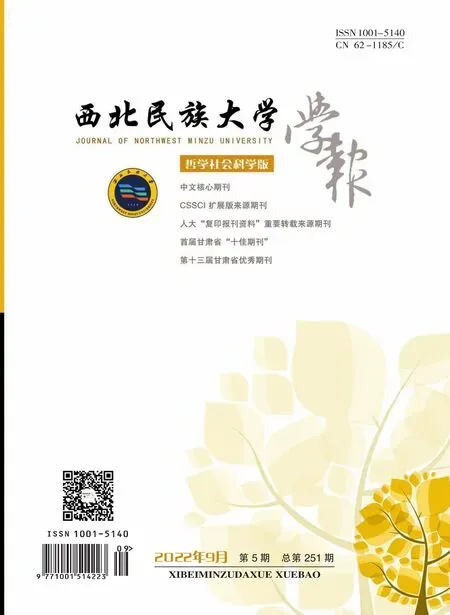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北朝黄帝祖源记忆建构与认同
董文强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有着密切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随着秦汉以来边疆与中原各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南北朝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无论是边疆民族还是中原民族,都自称炎黄等华夏先祖后裔,形成了各族“同源共祖”的历史记忆与“天下一家”的认同观念[1],这其中以北朝政治体黄帝祖源记忆的建构与认同最具代表性。由于北朝政治体的发展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其华夏祖源记忆的演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密不可分,将北朝黄帝祖源记忆的发展变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进行梳理与审视,对于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我们有必要以北朝政治体的黄帝祖源记忆认同为中心,从正史所载的建构历程、墓志所见的典型黄帝祖源记忆以及北朝天下一家的认同观念转变等诸多层面,考察共享黄帝祖源记忆的边疆与中原各族的融合与凝聚,以此揭示北朝黄帝祖源记忆建构的复杂文化内涵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影响。
一、从行为到法统:正史所载北朝黄帝祖源记忆的建构历程
在中古边疆各族进入华夏之前,经过先秦时期的历史建构,黄帝已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而从边疆进入华夏的拓跋氏在建立政权后,亦延续前代以黄帝作为共同体祖源记忆的传统。这虽为北魏政治体合法性与正统性需求的结果,然此种祖源记忆建构的背后,隐含着若干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与诸多胡汉民族的互动融合,同时包含着华夏共同体意识的演变[2]。因此,北魏拓跋氏黄帝祖源记忆认同的变迁,同样反映着中古边疆与中原各族互动融合共为一体的历史进程。
据相关史籍所载,首次将拓跋氏祖源记忆与华夏始祖黄帝关联起来的人物是卫操。昭帝拓跋禄官十一年(305年)[3]7,定襄侯卫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轩辕之苗裔’”[3]599。其时立碑所云拓跋氏为黄帝后裔的举动,并非拓跋集团的主动行为,卫操个人行为的可能性较大。但此举表明,彼时加入拓跋集团的汉族士人,意欲通过黄帝的华夏先祖身份将边疆民族纳入华夏系列[4],同时又反映出其时拓跋氏对黄帝等华夏先祖的象征身份及其在未来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而至天兴元年(398年)北魏立国时,太祖拓跋珪令,“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3]2734。可见,至北魏立国,在官方层面才开始确定拓跋氏为黄帝后裔的身份。此次拓跋珪下令在国家的礼仪祭典中选用华夏传统,尽管是基于北魏政治体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的需要,然却昭示出北魏政治体在未来的政治发展路径与主动进取方向。
另据《资治通鉴》记载,天兴元年(398年)北魏政治体“继黄帝之后”的行为,是选用了汉人崔宏的建议,由此拓跋氏开始“自谓黄帝之后”[5]3484。相较之前卫操的个人立碑行为,此时拓跋氏对黄帝等华夏先祖的主动认同已逐步开始。又据《魏书》记载来看,北魏立国后,对黄帝的祭祀行为越来越常见,已从早期汉人士族的个体行为,逐步发展为北魏政治体主动认同的政治活动。如天兴三年(400年)“车驾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3]36;神瑞二年(415年)“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3]55;泰常三年(418年)“侑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3]2737;泰常七年(422年)“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3]62;和平元年(460年)“历桥山,祀黄帝”[3]2739。虽然有以上一系列对华夏先祖黄帝祭祀与认同的实践行为,但以黄帝作为祖源记忆,在官方层面的建构始终比较模糊。如在太和十三年(489年),孝文帝与群臣讨论祭祀之礼时,仍没有形成共识。而至太和十四年(490年)中书监高闾上表:“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臣愚以为宜从尚黄,定为土德。”[3]2744-2745在此次廷议中,高闾对北魏以黄帝为正统的现实因由进行了解答,进一步推动了北魏政治体对黄帝祖源重要性的认识,从此黄帝祖源记忆逐步进入北魏政治体官方正式建构的视野。
至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大赦诏》中称:“惟我大魏,萌资胤于帝轩,县命创于幽都。”[6]至此,北魏政治体将“黄帝”正式建构为祖源记忆,且在朝廷的诏令中正式运用。此时以拓跋氏为中心的内迁北族开始认同“黄帝”后裔的身份,已超越北魏政治体最初对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需求的层面。在此次迁都诏令中,宣称对黄帝祖源记忆的认同,至少在意识形态领域减少了迁都洛阳的阻力,能够增加“洛阳”统合的“天下”各族的彼此身份认同,以此开启北魏政治体的新时代。
经过以上一系列的努力,最终在太和二十年(496年)春,北魏朝廷以诏令的形式,法定黄帝为内迁北族的祖源记忆。《资治通鉴》载:“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5]4393此段诏书中,明确展示出北魏朝廷对黄帝认同隐喻性的深层次理解,意味着内迁胡姓将会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融入华夏共同体。
北魏政治体以黄帝等华夏先祖作为共同体的祖源记忆,得到了胡汉士族的广泛认同。北齐魏收在撰著《魏书》时,延续北魏政治体最终法定的黄帝祖源记忆模式,并以此作为记载拓跋氏历史的开篇序言: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3]1
很显然,《魏书》所云黄帝为拓跋鲜卑的祖源记忆,是对太和二十年(496年)春北魏政治体法定黄帝后裔身份的高度认同与再度重构。
从以上史籍所载来看,北魏政治体对黄帝祖源身份的认同经历了曲折与复杂的历程,由最初汉人士族的个体行为,发展到北魏政治体主动认同的政治活动,再进一步建构为北魏政治体国家层面的法统依据。此后,北齐延续了北魏的黄帝祖源记忆。而北周宇文氏为了与北齐争夺正统,采用了区别于北齐所承继的黄帝祖源记忆形式。《周书·文帝纪上》载: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7]
值得注意的是,北周在以炎帝为祖源记忆的同时,刻意强调了炎帝与黄帝之间的关系。由于在华夏的祖源记忆中,黄帝、炎帝本为兄弟关系,北周虽然选择了正统性的另一种表述,但依然没有完全脱离与黄帝的紧密关联,事实上仍然在黄帝祖源建构的范畴体系之中。因此,北周的祖源身份建构,本质上仍然是对北魏政治体华夏祖源法统的延续。
二、从典范到普遍:墓志所见黄帝祖源记忆与北朝的华夏认同
北魏政治体以黄帝作为祖源记忆,主要是孝文帝时代建构的结果。虽然在太和改制之前已有断断续续的推进,然而并没有像孝文帝时代那般活跃,并将其正式纳入国家治理的法定制度之中。孝文帝太和中,将“黄帝”祖源身份正式制度化与典范化,并以北魏政治体官方的意志作为最终呈现,影响极其深远。此种认同带动了整个北方群体对黄帝祖源身份的普遍建构。
由于拓跋氏建构的姓族层次模式是以拓跋氏为中心,其次以帝室十姓、勋臣八姓、四方诸姓等环绕的众星捧月般的网状结构,因此,拓跋氏的祖源建构模式亦成为其他内迁北族祖源记忆建构的典范。受到典范的影响,作为依附皇权的内迁北族皆以拓跋氏的祖源记忆作为各自的建构对象,如此不仅能够进一步攀附与拓跋氏的亲缘关系,亦能获得华夏诸族的广泛认同。至北朝晚期,对于黄帝祖源记忆的建构大量出现在内迁北族成员的墓志中。
据吴洪琳研究,有关黄帝祖源身份认同的内迁北族墓志多出现在孝文帝改定姓族十年之后,即约在北魏政治体法定拓跋氏为黄帝后裔身份的时间以后。尽管北魏政治体的黄帝祖源建构从朝廷诏令到内迁北族成员的完全认可需有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4],然而太和二十年(496年)以后,在显现个人及家族自我认同较多因素的私人墓志中,开始出现大量追溯黄帝祖源记忆的情形,体现出其时整个社会对黄帝祖源记忆的普遍性认同。
对目前有关黄帝祖源记忆的墓志进行梳理可知,内迁北族对黄帝后裔身份的认同普遍出现在北魏晚期至周隋之际。其中典型者如:
永平三年(510年)《宁陵公主墓志》:“遥源远系,肇自轩皇,维辽及巩,奕圣重光。”[8]57
正光元年(520年)《叔孙协墓志》:“君讳协,字地力懃,河南洛阳人也。其先轩辕黄帝之裔胄。”[8]117
正光四年(523年)《奚真墓志》:“君讳真,字景琳,河阴中练里人也。其先盖肇傒轩辕,作蕃幽都,分柯皇魏,世庇琼荫,绵奕部民,代匡王政。”[8]142
孝昌三年(527年)《和邃墓志》:“君讳邃,字修业,朔州广牧黑城人也。其先轩黄之苗裔,爰自伊虞,世袭缨笏,式族命三朝,亦分符九甸。”[8]207
建义元年(528年)《陆绍墓志》:“君讳绍,字景宗,河南河阴人也。其先盖轩辕之裔胄。”[8]235
开皇三年(583年)《长孙璬墓志》:“公讳璬,字月符,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与魏氏同宗,犹轩辕之子,得姓者十二;颛顼之胤,分族者八人。”[9]13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涉及黄帝祖源追溯的墓志数量极大,于此不便统计。然就以上数例墓志亦可管窥其对黄帝祖源追溯的模式。从以上墓志体现的华夏祖源建构路径来看,与北魏政治体官方的建构模式没有任何区别。如北魏“帝室十姓”之一的《长孙璬墓志》,该墓志首先强调与拓跋氏的亲缘关系,在此基础上,认同拓跋氏为黄帝后裔的祖源记忆,很明显,这种模式是对《魏书》序纪的翻版。长孙璬葬于开皇三年(583年),此时虽“帝室十姓”的荣光不再显耀,然北魏政治体建构的黄帝祖源身份仍为内入诸姓后裔所认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除了与拓跋氏有亲缘关系的内迁北族,与此同时来自西域的边疆诸族亦以此类建构模式标识祖源记忆,如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安伽墓志》:“君讳伽,字大伽,姑臧昌松人。其先黄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世济门风,代增家庆。”[10]291安伽虽为西域安国后裔,亦以黄帝为祖源记忆,是进入中原的边疆族裔对华夏高度认同的典范。值得关注的是,此时边疆族裔对华夏的认同已超出单纯祖源建构的范式,如同样是西域安国后裔的开皇九年(589年)《安备墓志》,虽没有直接宣称黄帝祖源,但在墓志中表现出对自我华夏身份不同寻常的认同,其云:“君名备,字五相,阳城县龙口乡曹刘里人。起先出于安居耶尼国,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名沾典客……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此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11]安备祖上在北魏时进入中原,虽为内迁胡族,然在北魏朝廷为官且久已华夏化。如此边疆族裔对华夏认同的直接宣称,当与北魏政治体一系列华夏化措施(包括黄帝祖源建构)的持续推进与普遍认同不无关系。
除了以上所述内迁边疆诸族的黄帝祖源记忆建构,中原世家大族亦将黄帝祖源记忆在墓志中特意强调,兹举数例如下:
熙平二年(517年)《阳平王妃李氏墓志》:“鸿基肇于轩辕,宝胄启于伯阳,哲人之后,奕叶官华,龟玉相承,重光不绝。”[8]100
天统四年(568年)《薛怀俊墓志》:“君讳¨,字怀俊,出于河东之汾阴县。昔黄轩廿五子,得姓十有二人,散惠叶以荴疏,树灵根而不绝。造车赞夏,功济于生民;作诰辅商,叶光于帝典。”[12]159
宣政元年(578年)《宇文瓘墓志》:“公讳瓘,字世恭,京兆万年人也。本姓韦氏,后魏末改焉。若乃电影含星,轩辕所以诞圣;蜺光绕月,颛顼于是降灵。”[10]275
开皇五年(585年)《皇甫道爱墓志》:“君讳道爱,字九会,安定朝那人也。言其先世出自轩丘,语其苗裔分居若水。”[13]
开皇十一年(591年)《梁衍墓志》:“公讳衍,字庆衍,安定朝那人也。自轩丘膺箓,嘉瑞肇于游麟;华渚降祥,设官分于命雁。”[9]32
由以上墓志可见,中原世家大族亦同内迁胡姓一样强调黄帝祖源记忆。按理来说,中原各族无需像边疆诸族一样刻意强调华夏身份,但事实上,在中原世家大族的墓志中,对华夏先祖黄帝祖源的追溯,亦有着普遍性的出现。究其原因,其一,当与家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不无关联;其二,这种普遍性或与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法定黄帝为拓跋氏祖源有关。基于以上两点,当边疆诸族在大量书写与广泛建构华夏祖源记忆以表明华夏身份之时,由此刺激了中原世族对华夏祖源记忆的强调,二者之间在祖源记忆认同的层面既有竞争亦有互补。当然,即便是代居中原的世家大族,从生物学意义的祖源谱系来说,与黄帝之间的关系亦难以直接关联,至少无法证明自己确为黄帝之后裔。在如此情形之下,面对边疆诸族普遍性地宣称自己为黄帝后裔身份的历史情境,想必至少会对中原世族产生某种外部的压力。不论原因如何,但无可置疑的是,这种黄帝祖源记忆建构的普遍性,反映出华夏认同带来了边疆与中原各族之间的交融与凝聚。
另前述北周宇文氏以炎帝为祖源记忆,而中原世家大族亦同样有追溯炎帝为祖源者。如熙平二年(517年)《崔敬邕墓志》:“君讳敬邕,博陵安平人也。夫其殖姓之始,盖炎帝之胤。”[8]98因此从中原与边疆各族的祖源记忆来看,二者在华夏认同方面走向了趋同与互补。无论是中原各族还是边疆诸族,皆以华夏正统自居,在他们的祖源记忆中将黄帝与炎帝逐渐并列,并且普遍接受了“炎黄子孙”的记忆,华夏认同中不断容纳了诸多来自华夏域外的群体[14]。
北朝诸多墓志对黄帝祖源的普遍追述反映出北朝政权虽经数次更迭,但黄帝祖源记忆的共享却一直没有间断,是黄帝祖源记忆由早期的典范走向普遍性的最好说明,亦即边疆与中原各族持续互动融合的有力表征。以华夏先祖为祖源建构,本质上是通过血缘与文化的共享来促进不同民族的融合,这种融合直接促进了内迁北族成员对华夏身份的高度认同。
在北魏衰亡后,墓志中仍不厌其烦地书写黄帝祖源记忆,表明其已超越北魏政治体早期单纯的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需求的层面,成为边疆与中原各族融为一体的认同符号。而北朝晚期以来,社会层面对黄帝祖源的普遍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和消弭边疆诸族的冲击与挑战,由此带动了四裔各族更进一步的融合与凝聚。
三、从攀附到同源:北朝黄帝祖源记忆与天下一家的民族融合
经过对相关史籍和墓志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北朝的内迁胡姓在祖源认同上主动选择了华夏世系的先祖,这其中以黄帝作为祖源的最为普遍。在北魏政治体的带动下,内迁北族后裔在主动的认同与选择中,逐步完成了对华夏祖源记忆的建构。
北魏政治体将祖源追溯至黄帝,非其首创。早在战国晚期,“黄帝”已被建构为华夏群体的共同先祖,并蕴含领域、政治权力、民族与血缘的多重隐喻[15]。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无论是游牧还是农耕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有着对华夏祖源记忆建构的情形。北魏政治体延续前代建构黄帝祖源的模式,使得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在持续地交流融合中为内迁北族普遍接受,大一统的观念亦随之成为内迁北族的政治理想。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最高政治目标,以黄帝为祖源成为了“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16]。如此,除了能够获得北魏政治体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更进一步来说,北魏政治体以象征着正统与圣明的华夏先祖黄帝作为祖源记忆,代表着其行使华夏先祖的权力和意志来统合现实中的四裔群体。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黄帝祖源记忆的建构与北魏政治体追求“混一华夷”的政治理念相始终。在《魏书》中多次出现“混一华夷”[3]2455、“混一戎华”的观念[3]109,是北魏政治体官方意志影响的结果。作为北魏政治体“混一戎华”理念追求下的民族融合,黄帝祖源记忆是推进政治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路径之一,对胡汉共同体最终的形成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北魏政治体黄帝祖源记忆的追溯与认同,亦是政治体建构的未来文化走向与路径选择。尽管黄帝祖源记忆曾经一直在北魏政治体的建构视野中,然其真正发挥实际效用则是在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太和改制时期,北魏政治体的华夏化改革在各个领域显现出最为直接的成效,这与黄帝祖源的一体化建构不无关联。另极为关键的是,以黄帝及其后裔作为共同的祖源记忆还能够培养共同体意识,为胡汉共同体提供思想的保证,这一点的确在后来孝文帝的践行中得以实现。此后,虽然北魏王朝在六镇之乱的打击中迅速没落,然而,重新进入中原的内迁北族又一次努力践行共同体意识,最终在周隋之际得以完全实现。
质言之,北魏政治体最终选择黄帝作为“一体”的祖源记忆,是多元民族融合互动与主动认同的结果。黄帝祖源记忆最终在墓志中呈现出一种集体记忆的普遍建构,本身就是一种主动认同的选择[17]。这一主动认同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与反复的历程,本质上是华夏各族交流交融、集体互动,最终成为共同体标识的实践过程,但其中却隐含着从早期“攀附”到孝文帝以来“天下一家”华夏身份认同的转变。
以往多将内迁胡姓追溯华夏先祖祖源的行为解释为“攀附”,虽然“攀附”是对边疆诸族认同华夏祖源这一现象十分合理的概括,然而,如进一步深入分析,“攀附”仅仅可能是边疆诸族认同华夏先祖的历史表象。在北魏衰亡后,“攀附”已难以概括内迁北族祖源记忆复杂变迁的文化内涵。此点通过深入分析《魏书》序纪所载即可获知。
《魏书》开篇即言,无论“内列诸华”还是“外分荒服”皆为“黄帝”后裔,显然有更深层次的用意,绝非简单的“攀附”所能阐释。如果将“内列诸华”视为中原民族,“外分荒服”视为边疆民族,则二者之间当为同源共祖。这反映出北朝政治体已摆脱先前“攀附”的历史境遇,朝着“夷夏同源”的民族融合方向迈进,已对中原与边疆各族交往、交流、碰撞与融合的多源性与复杂性形成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反映出黄帝祖源已成为北朝政治体共享的历史记忆。
除此以外,在华夏疆域内广泛存在胡汉通婚,亦使中原与边疆各族持续融合,血缘纽带已不是想象的联结,而是客观的存在,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8]。北朝晚期,黄帝不仅成为中原与边疆各族具有共同起源的祖源记忆,而且在胡汉群体的心理和情感上已成为无可置疑的共同先祖。由此,内迁北族的华夏身份已定型,在血统、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融合与认同已非内迁胡姓先祖在北方草原游牧时代可相比拟。
从长时段来看,北朝黄帝祖源记忆的变迁,表征着华夏共同体内部各族互动与融合的历史过程,是多元文化整合之后主流认同的结果,最终以“一体化”作为具体呈现,这个“一体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胡汉群体转变为同源共祖。同源共祖更进一步地促进了华夏认同,使得不同民族在相互的碰撞与融合中,增强了共同体潜在的情感价值,形成了内向的凝聚力,这使得他们主动继承和运用旧有政治文化中的符号体系,重新定位其在华夏共同体中的位置,以此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夷狄变为华夏[19]。胡汉共同体以“共同祖源”来凝聚[20],共同祖源的建构与认同改变了内迁北族的祖源记忆,华夏认同由此进一步深入。原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对立思维已难得到认同[21],进一步转变成为隋唐时代“四夷可使如一家”的多元包容与一体凝聚[5]6216。
经过北魏政治体的整合与引导,北朝黄帝祖源记忆最终建构为以华夏先祖为主体的“一体化”聚合。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是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同步发展的过程[22],实质上是对“大一统”思想认同的结果[23],亦即将四裔诸族一并纳入王朝体系,重新建构起合乎“王者无外”和“天下一家”理念的统治格局[24]。这种“大一统”认同下的一体化建构,成为统合游牧与农耕、边疆与中原、边缘与中心的强力纽带,必然又一次推动边疆与中原各族的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华文化的绵延不断,起到了基础性、根本性的历史作用[16]。
综上所述,以拓跋氏为中心的内迁北族在边疆进入中原的过程中主动认同并接纳黄帝祖源记忆,使之成为北朝政治体华夏认同的文化符号,在华夏认同与民族融合方面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黄帝作为边疆与中原各族共同追溯的先祖,无论在历史记忆还是现实情境层面都能将四裔群体融合汇聚,从根本上扩大了华夏认同,使得各个民族之间彼此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由此在血缘、疆域、政治、文化的诸多层面,多元民族得以互动、融合、凝聚为一体。这一过程中,四裔群体共同追求的“天下一家”认同理念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因[25]。而“天下一家”共享的黄帝祖源记忆既是四裔诸族共同祖先及其共有家园生活的历史写照,亦是各民族汇聚为多元一体的真实记录,成为不同地域群体共有家庭祖先亲缘关系的延伸,从而形成以共同祖源记忆为核心的文化凝聚力[26]。这种凝聚力最终沉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思想意识,涵养和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潜在的情感价值。
北朝社会的黄帝祖源记忆演变,是一个不断层累建构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华夏认同与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内涵历史变迁的表现之一。从正史与墓志的相关记载分别考察,北朝黄帝祖源记忆的变迁经历了从早期的个人行为到北魏政治体的建构,再到北朝晚期胡汉共同体普遍认同的发展阶段,其与四裔诸族的华夏认同密不可分,实质上是“大一统”思想影响的结果。北朝晚期以来,内迁北族后裔通过“改族依汉,联宗系姒”的方式强调黄帝祖源记忆[27],已超越单纯的攀附冒袭,成为“天下一家”集体共享的历史记忆,黄帝祖源记忆由此成为胡汉诸族凝聚为统一共同体的表征。“黄帝”作为边疆与中原各族主动认同与普遍选择的祖源记忆,经过长时段的发展,已转变为持久不变的共同历史记忆,这种共同的历史记忆定会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识,进一步促进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形成的视角审视,北朝黄帝祖源记忆认同的发展演变,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见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评《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