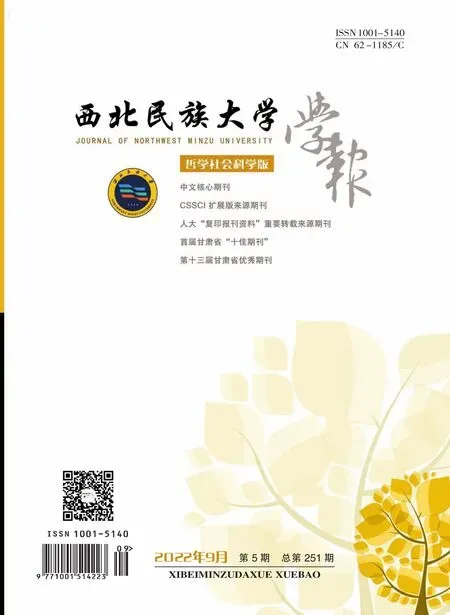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中国化何以可能
——论马克思主义与诸子语言观的共通
郑淑花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60007)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是马克思、恩格斯一以贯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考察人类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演变、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和宗教、语言与方言、语言的风格等的观点和思想,散见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人类学笔记和通信信件等文本中,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子语言观是先秦诸子在探讨哲学、政治、伦理学中形成的关于语言的本体、结构、演变、文化等的思想,凝聚着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是中华优秀传统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传入中国,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语言文化中具有滋养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文化土壤,首先表现于诸子语言观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蕴含着内在的契合性。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即“两结合”。同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习近平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精神,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与中华优秀传统语言文化更为深入融会贯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当前,如何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探究传统语言观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内在统一性,找到二者相融共通的语言文化纽带,激活中国传统语言观内部的精神力量,实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与中国传统语言观更为深入的融会贯通,这是仍需语言学界探索的理论难题。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和先秦诸子文献中关于语言的论述,发现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的实践性、符号性和主体性的思想与诸子救世建功的实践性、“名实论”和个体性思想具有相融共通性。正是这种相融共通性使得两者的结合具有深厚的内蕴和广阔的空间。
一、社会实践论与建功救世思想的共通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观为理论硬核的。”[3]“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表现在语言观上,马克思关注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将语言根植于社会生产和劳动实践中。“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4]91马克思主张从“社会性”和“实践性”两个视角来审视语言,认为语言是在社会实践生产中产生,并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为社会服务,调整、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产(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和秩序。而形成于先秦这个社会制度大变革时代的诸子语言观,是一种肩负着建功救世使命的,以“名实之争”“正名主义”为载体服务政治伦理重建的语言观。“为社会实践服务”是两者融通的一个基础和纽带。
(一)“交往需要”和“取实予名”的共通
关于语言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从劳动、交际视角进行分析。远古人类的群体性生活和劳动,促进了群体成员间的互助协作,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由此仅仅依靠原始的肢体语言已难以胜任日益增加的交际发展需要。而这种交往的需要却“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5]553,正是非说不可的交际需要催生了语言。“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6]145人通过生产实践提升生产力、改善社会关系、创新文明理念,同时也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交往方式、拓展交往广度,提升交往的密切度。在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交互促进的进程中,作为人类社会重要交际工具的语言应运而生,且随着社会实践和交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5]553也就是语言自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社会关系中,成为人与人交际交流的工具,是人们交往实践的产品,“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7]188人类之所以创造语言,是因为劳动使他们在共同协作中有彼此交际的必要。劳动决定创造语言的需要,同时劳动决定了创造语言的可能,它促使人的思维能力的产生发展、发音器官的完善,使语音和语义的结合物语言的产生成为可能。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认识到语言在交往中的作用。他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8]346也就是在语言交际中,用来称呼的是“名”,所称呼的事物叫做“实”。“名”是语言学范畴,相当于语言的构成单位词素或词语,而“实”是客观事物,因为需要称呼客观事物,所以产生了语言。墨子提出“取实予名”的语言观,认为政治制度、名物制度之“名”皆来源于社会实践的需要。“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8]337“狗”“犬”重名是不利于社会实践中区别事物的。同时,他主张“今人与此异者: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8]279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生产劳动。墨子“取实予名”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劳动生产决定语言的思想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都认识到生产劳动对语言产生的决定作用。
(二)“交往准则”和“明伦”的共通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7]533马克思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语言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实践是语言的基础,生活是语言的规定和限界;二是语言是在人和人交往的实践中产生的。这个人是具有社会性,是在社会交往中需遵循交往规则的人。孔子的“正名论”、荀子的“明贵贱”的语言交往论也强调个体遵循语言交往的准则,两者表述不同,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
孔子面对新兴地主阶级犯上作乱和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他极力维护以“周礼尽在鲁”的鲁国制度和鲁国权威。他提出“名实”观的宗旨是“正名”,认为“言不顺,则事不成”[9]193,并会导致“民无所措手足”[9]193,也就是“名不顺”会导致社会关系的混乱和礼乐的崩坏。马克思也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3人伦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主要内容,是名正言顺的基础。所以,孔子说:“政者,正也。”[9]186“正”是基于重建政治礼制的社会实践需要,他把“正名”当作是改善社会和改革政治的核心和手段,以实现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9]184的理想的人伦关系。
与孔子一样,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在语言观上凸显语言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功能,认为天下君子说话写文章的目的是“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8]308,是为了国家、邑里、万民的刑法政务。他重视语言在安邦济民实践中的作用,认为“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8]456,具有治国和修行的教化功能,并且这种言辞的功能远远大于“耕织”。尹文子在语言实践中认为要“先正名分,使不相侵杂”[10]136,以实现以名分定身份,以身份安社会的目标,如此人们就会安身立命,不争夺财产,社会也就不会盛行私欲了,强调语言“明伦”的社会价值。荀子也认为语言具有“明贵贱”的政治伦理功能。他说:“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11]360语言的“明伦”作用是语言交际工具性在调整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语言的工具性在社会各领域中的服务和规范功能。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分析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时指出:“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中的一切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工作。”[12]工具性使语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日常生活等各领域获得特殊的地位。如今,语言除了是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流工具之外,还是重要的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文化资源和国家认同工具,在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国家安全、“一带一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领域发挥关键性功能。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将“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成为新时代高质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方针。
(三)“斗争工具”和“救世功能”的共通
“马克思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13]马克思将语言作为其斗争、开展工人运动的工具。如他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无产阶级,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4]21这一战斗口号召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他认为语言是凝聚民族感情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号召人们为国家和民族繁荣发展而斗争的最有力的工具。在国家和民族内部,语言具有凝聚人心,形成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同时语言也能成为人心涣散、国家分裂、民族不和的根源。他说:“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早就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对抗,对抗的根源是语言和宗教的不同。”[15]702“语言的隔阂也阻碍了工联的国际主义团结。”[15]694“要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牺牲本乡本土的利益,为不同语言和不同民族的皇帝去打仗,这可能吗?”[16]在开展斗争中,马克思认识到语言的统一和掌握语言的重要性,主张要以通用的语言宣传国际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论,认为只有语言相通,才能消除交流融合的障碍,才能心意相通,才能凝聚人心共谋发展。“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普遍的、共同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把他们团结了起来。”[14]271由此他要求:“只有会说几种语言的人才能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担任主席。”[17]
春秋战国是社会制度大转型、社会秩序大动荡的时代,同样需要语言的一统天下。孔子倡导《诗》《书》、执礼都要用雅言,荀子主张“君子安雅”,他们强调雅言即通用语的作用,将语言视为实现政治上救世和建功立业的手段。
孔子提出“慎言”“信言”的语用标准,其目的是基于维护鲁国制度的实践需要。孔子在和学生的对话中,多次提到要“慎言”“讷言”,反对“疾言”和“巧言”,认为“巧言乱德”[9]243、“巧言令色,鲜矣仁”[9]4。
墨子提出“择务从事”的语言实践论:“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8]459他提出要根据社会存在选择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其标准是“言必立仪”。从他的言语标准可以看出墨子已充分认识到语言“废以为刑政”的实践意义,而这个用作刑法政令的标准是“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8]286。
尹文子从实践论的角度提出了“寻名以检其差”[10]133,并且要“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10]133,即不但要根据名称去检验具体的事物,还要以名称来检验事物的形状,以事物的种类来检验它的名称,其“检名”目的是基于护“法”的实践需要,而这个法也正是君王的“权势”。
荀子语言观的社会实践性体现于政治改革中,他认为正名是同“王者制名”相联系的。“王者制名”的目标就是要“迹长功成”,实现建功立业、长久统治的治国安邦的理想。他把“期、命、辨、说”看作“王业之始”,把是否符合圣人先王的礼仪作为言辞辩说的标准,认为:“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11]62,奸言兴起是由于“圣王没,天下乱”[11]364。他把语言看作是实现救世之弊、长久统治的工具。
语言是认识世界的中介,并能通过认识世界而改造世界。先秦战国时代,社会秩序混乱,而政治组织却软弱无力,孔子、老子等诸子目睹社会现状,想要寻求一种救世之法补救社会,由此产生了儒道法等哲学思想,而与之匹配的作为哲学思想载体的语言,也成为他们救世建功的手段和方式。以语言规范伦理道德,诸子语言观由社会现状所激发而产生的,并通过语言规范改造社会,这种强调语言的规范社会、调整社会的服务功能的语言实践观与马克思实践观所主张的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改造世界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是在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7]516。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家沉湎于语言的概念和词句中,认为只从词句批判词句,开展的只是纯理论的、脱离现实的语言革命,忽视了语言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从而将语言剥离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使得语言抽象为思想的产物,如此只是抽象的、思辨的语言斗争,不具有批判、改造现实的功能。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作为斗争工具,只有根植于社会现实的语言批判才具有生命力,故此他劝导青年黑格尔派“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18]436。不能只做言语的巨人而做行动的侏儒。夸夸其谈、言而不实无异议于纸上谈兵,于事无补,于改造现实无益,因此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言语转化为行动,即孔门所主张的言即行事,“先行其言而后从之”[9]24、“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9]58,这些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言行合一的言论贯穿于孔子一心念天下苍生,志在开万世太平的入世的社会实践中。
二、符号论与名实论的共通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系统中的每一个符号都有一个代表音响或书写符号的“能指”和代表其意义或概念的“所指”共同组合而成。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马克思和诸子在探讨语言的本质时都认识到语言的符号性,马克思关于名称源于现实、名称多元和诸子关于名生于实、名实不符的论述,皆将语言视为一种符号系统。
(一)“名称源于现实”与“名生于实”的共通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就语言符号而言,现实生活(实)是第一性的,语言符号(名)是第二性的;名称来源于社会存在,是对社会存在的标记,表现为名称的意义是有客观内容的,是以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作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19]406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大量的术语,认为名称是客观实在的记号,如“利息”是标记“利润”的,“积蓄”和“积累”是标记“劳动者产品”的,“租”是用来称呼“剩余价值”的,“价格和铸币”是“作为交换价值和交换手段的商品的交换用语”。“麻布=上衣”是因为它们具有商品这个“同一实体”,并且这些“名称绝不是从知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5]43,也就是符号根植于现实,与人的现实生活直接交织在一起。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尹文子、公孙龙、荀子等在研究哲学问题、政治问题中也探讨诸如语言的发生和发展、语言和思维等本质问题,其主要论说集中于“名实之争”中。
老子提出“常名”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0]1他认为,有了天地万物,才有了名,也就是名生于道;同时他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20]1。其“名”相当于符号的能指,“道”则是符号的所指。老子的“道”“名”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存在”范畴是共通的,揭示了名称与事物的关系。
墨子也认识到名实关系问题。他说:“有文实也,而后谓之;无文实也,则无谓也。”[8]350先有“实”(事物)才有称谓(名称),没有实(事物)就没有称谓(名称)。“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8]430在墨子心目中,语言同服装一样,只是一种表现“仁”的符号,和“仁”是没有本质联系的。
尹文子不仅论述了“名实”第一性的问题,“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10]137,即“名”是给“形”命名的;他还认为名、形是具有独立性的,两者是相互联系却又不能相互替代。
墨子和尹文子主张先有“实”后有“名”,“名”“实”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是一致的,马克思说:“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4]121
(二)“名称多元”和“名实不符”的共通
名称和事物是相互区别,具有各自的属性,在社会实践中,一个事物可能具有不同的名称,一个名称也可能同时可以指称不同的事物,事物和名称并不是完全地一一对应的关系,能指和所指往往存在诸多的不一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价格、价值、租、剩余价值、利息、积累、积蓄等概念的含义,认为一个事物往往具有不同的名称,正如“流动资本仿佛不过是商品资本的另外一个名称”[21]、“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润的一个特殊名称”[22]。商品、资本等客观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作为表现客观事物的符号也随之变化,在同一种语言系统中人们在使用符号往往各有所指。如在不同的国家操着不同的语言,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名称。他也批判那些把名称等同于客观事物的思想家:“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拿世界开玩笑。”[23]名称源于现实需要,而在现实生活中,言说者基于政治、经济目的而运用权力、舆论、欺骗等方式分离语言符号能指所指的确切关系而造成言意偏离得言不副实。这种歪曲语言与现实确指关系的符号论使得语言失去沟通性和创造性,走向工具的异化而成为任人摆布的工具。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异化而被资产阶级所利用的语言现实,他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批判省议会把“偷拿枯树或者捡拾枯枝也应归入盗窃的范围,并应和砍伐活树受到同样的惩罚”[24]242是隔离符号能指和所指来抹杀捡拾枯树与盗窃林木的差别,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7]552
符号能指和所指的不对称性,诸子从“名实”矛盾性的视角作了丰富的论述。孟子提出“言近而指远”的言指观,认为“言”和“指”关系不是一种“言近而指近”的平衡关系,而是“一种偏离关系,即言此而及彼、言浅而意深,言有限而意无穷”[25]。
老子和庄子认为思维(语言)是可以反映(描述)存在的,而另一方面也存在“非常道”和“非常名”的语言指称功能缺失的情形。
墨子提出“名、实、合、为”的关系,分析“名”“实”间存在的诸如“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的不对应关系。他说:“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8]84这种“名实”不统一的后果是“天下之乱,若禽兽然”[8]85。
尹文子也从“名实”角度分析语言之名“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10]137的重要性,以及“世有因名以得实,亦有因名以失实”[10]167的名实间的多元关系。
战国时代公孙龙也认识到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10]92,提出“天下无指”[10]92。这个“指”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直观的指称,而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化的认识。这种“名实”的辩证关系也体现于他著名的“白马非马”论中。“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形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10]52他认为马的概念外延包括白、黑、黄等各种颜色的马,所以“求马,黄、黑马皆可致”[10]54。但是白马、黄马和黑马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所以“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10]54。在公孙龙看来,有相同所指的“马”,而在“黑马”“白马”“黄马”的组合中,所指称“马”的内涵又是不一样的。
荀子第一次将名实关系明确化,提出“约定俗成”语言观,肯定名实的一致性,也指出“异于约则谓之不宜”[11]362的不一致性。对于“不宜”的名实关系要进行规范,其规范的方法则是:“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11]361-362由于万物众多的原因,还要以“大共名”“大别名”来归类。马克思也主张依据社会现实的发展“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19]405。
马克思和诸子都主张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都认识到语言符号与现实社会的多元关系。他们关于语言表达内容的现实性、语言表达内容与表达形式的不一致性等关于语言符号本质的认识是相融共通的。
三、“主体性”与“个体性”的共通
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中融合着言说者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马克思不仅强调语言的实践性、社会性,也将语言置于一定社会阶层中,关注社会中的人的语言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他说:“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金钱使资产者所处的那种可怜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痕迹。”[7]477“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26]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服务于全社会,具有全民性,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可既为统治者所用,也为被统治者所使用,没有哪个阶级或阶层可以垄断语言,但是每个社会、每个阶级或阶层都会把自身的意识、爱好、习惯、风俗甚至是文化尽可能地塞到为全体社会服务的语言中去。语言观是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态度和看法,留存着阶级或阶层的意识、爱好和习俗的烙印,也留存着言说者的个体差异性。如资产阶级语言思想家主张语言为资产阶级服务,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和铜钱的味道;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为人民群众利益而发声,具有鲜明的大众性和人民性;习近平提出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话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和天下担当。在中国传统语言观中,儒、道、名家语言学说各异,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特性的体现,也是他们个体性在语言思想中的体现。
(一)“语言是思想生命表现的要素”和“知言知人”的共通
语言不仅仅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还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以表达和传播。马克思说:“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7]194语言即是思想,体现生命要素,与思想、意识和观念相互交织,是知情意的统一体。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牟利精神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范畴来表现。”[7]478语言中留下的金钱的痕迹、小商人的气质和牟利精神,以及商业术语和经济概念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表征。诸如“贵族语言”“农民语言”“无产阶级语言”,这些所谓的语言通过特殊的词汇或习惯用语体现某个阶级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和情感。
在中国古人心目中,语言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是人性的体现。语言对人的认识具有启示的意义,人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思考人生,通过语言形成、表达、传播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孔子的慎言信言、孟子的“知言养气”、老子的“希言自然”、庄子的“不言之言”、墨子的“择务从事”、荀子的“后王成名”的语言观皆浸透着中国古代诸子的哲学思想和古代文人的气质。
不管是孔子的“正名”思想还是他的“慎言”“信言”的语言观,皆是他以道德行为主义为取向的哲学思想的体现,体现出孔子的人生志趣、道德品质及其所崇尚的伦理价值。此外,不止孔子的语言观体现了他的志趣和品质,而且孔子还认识到语言在表现语言主体个性的作用。“不知言,无以知人也”[9]305,他认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9]117马克思也认为:“只有深信自己的信念是真理的人们,才能用温和、打动人心的话语。”[24]988
为何会有“信言”“美言”还有“善言”之别呢?这与言语主体的差异性密不可分。言是知情意的统一,是主体体验情感和品德修养的载体。孟子重视“不忍人之心”的塑造,倡导“善言”,把“知言”和“养气”之道结合起来:“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27]“言”成为他“浩然之气”个体人格的表征。
老子主张“希言”和“行不言之教”,这和他“万物负阴而抱阳”[20]117、“弱之胜强,柔之胜刚”[20]187的哲学观念是互为表里的。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希言”是阴柔,“希言”能胜过“善辩”。庄子提出“言未始有常”[28]31,认为语言都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常),所言不同,所言说的思想、情感和风格也各异。他说:“言者,风波也。”[28]61这种风波是由于说话主体“知”的差异性而造就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29]语言中蕴含着言说者的思想、情感和态度,构成丰富多样的言语个性特征,或阳刚或阴柔;或严肃或活泼;或绚丽飘逸或婉约细腻。
(二)“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与“言尽意”的共通
语言是人们彼此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人们通过语言表情达意,达到相互了解。语言也是同人的思维直接相联系的,语言通过词和句子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知活动的成果记录下来,使交际和交流思想成为可能,语言离开思维,就成为“空洞的声音”;观念离开语言,就没有载体,都不能成为音义结合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
马克思认为,语言是一个人思想的体现。他批评巴枯宁“谈吐可畏,摆出一副吓人的样子”[30],因为他的思想极度贫乏;批评青年德意志是低等文人,因为他们用“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14]361,把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圣西门主义只言片语混杂在一起;批评格律恩是一个文字冒险家和骗子,因为“他企图用傲慢和狂妄的辞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18]465。同时,他认为卡莱尔的风格和他的思想一样:“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31]在马克思心目中,空洞抽象的词语、抱怨说教的热情、庸俗滑稽的辞藻都是思想贫乏的表征,而措辞锋利、色调丰富、语言生动是一个人深邃思想的表现。恩格斯也说:“他的思想富有诗意,是个非常善于讽喻的人;他的语言独标一格,所用词汇不同凡响。”[32]
关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在先秦诸子中则是“言意”关系的讨论。《说文解字》释“意”为:“意,志也,从心音,察言而知意也。”心中所思,未发出口为“意”,发出口为“言”,言意皆为人的思想,只是前者是潜在的言语行为,后者是现实化的言语行为。先秦诸子对言意问题的探索,形成两大流派:言尽意和言不尽意。
学者普遍认为,老子和庄子都是否定语言功能的。老子认为可以言说的“道”和可以指称的“名”,不是普遍之道、根本之名;在语言观上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20]147、“善者不辩,辩者不善”[20]191。庄子认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28]373和“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28]221,语言是不足以表达“道”和“意”的,因为“大道不称”[28]31、“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28]24。那是不是人类就不需要语言呢?不是的,老子和庄子是在解构语言表达“大道”功能缺失的同时,重构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不言之言”,即“意会”,言意之间通过“不言”的方式重新实现转换,由此可知,老庄的“言不尽意”是否定之否定的“言尽意”。
孔子关于言意的论述,其一是认为言尽意,所以强调言行规范要“信言”“谨言”“讷言”;其二是认为言意之间由于修辞而出现矛盾,所以他否定“巧言令色”[9]4,主张“辞达而已矣”[9]248,认为考察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9]67。此外,他与老庄一样,认为言语在赞美大道美德之时是难以言说的,“民无能名焉”[9]124、“予欲无言”[9]271、“天何言哉”[9]271,言语在天道盛德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中难以达意。孔子的“言不尽意”并不是否定语言是思想的体现。《周易·系辞》提出的立象尽意:“即在意和言之间加入象作为中介,由此难言之意便可通过象呈现出来,进而由言语表达出来。”[33]“言不尽意”的矛盾再次化解为“言尽意”。
墨子、韩非子是肯定“言尽意”的,都认为语言能准确地反映出心中之意。《墨子·经说上》云:“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8]329-330他认为人是可以通过语言理解内涵的。韩非子通过解说《老子》不可言说的大道后认为大道是可以言说的,由此认为语言是可以言说大道和理解意义的。在语言使用上,他们都注重语言的实务和功利,都倡导语言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8]319-320“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34]在他们看来,“言尽意”是语言文字使用的基本准则。
“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6]57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没有人能脱离语言来思考和表达观念;同时“言为心声”,儒、道、法、墨诸家“言意”之论虽内容各异,但殊途同归,皆指向“言尽意”,即一个人的语言是他的思想和品性的体现。
马克思和诸子虽然由于时代、地域及语言文字表述不同而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对于语言主体性的重视以及在主体性中蕴含着社会现实性的思考和对人性完善的追求,其精神本质是相同的。两者都内含着人文性和人本主义关怀,这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能够传入的传统文化土壤,也是中国语言文字进一步实现沟通心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文化源泉。
四、结语
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外来文化的传入有成功实现中国化转型的,也有昙花一现、未对当时社会产生影响的。“只有同本土的类似的或相适应的精神价值结成联盟,表明自己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认同,外来文化才能存在和发展。”[35]如东汉末,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释”学。
在语言观的传播中也如此,只有两种语言观的精神价值一致才能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与诸子语言观的共通性是两者结合、融通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建立在对现代文明高度批判的基础之上,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精华。”[36]就语言观而言,马克思主义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视角提出的语言和语言学的精辟论述,如马克思语言观关于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演变、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方言、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宗教、语言的文风等的言论,涉及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修辞以及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翻译学、风格学等语言学学科知识,是科学的语言观与语言方法论,代表了人类先进的语言思想精华。
诸子语言观是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先贤哲人在探讨哲学、政治、伦理等问题中对语言发表的言论,如关于语言与社会存在、语言与政治伦理、语言与逻辑思维以及著名的“名实论”,蕴含着语言本体(形、音、义)、修辞、方言、文字规范等语言思想,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绚丽多彩的奇葩和人类语言思想中的瑰丽独特的风景。
从语言观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和诸子语言观都是特定时代语言思想的总结,具有特定的时空局限性,也具有超越时空的语言思想精华,两者各有所长;从话语体系来看,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手段,诸子语言观有诸子话语的风格和气派。两者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对待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与诸子语言要一视同仁,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即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正确取舍,互融互通,不能只重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而陷入语言文化虚无主义,也不能以诸子等优秀传统语言观改造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而陷入语言文化复古主义。与作为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子语言观相比,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是一种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之后,需要一个改造与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与中国的语言文字具体实践相结合、与诸子语言观等优秀传统语言文化相结合,在语言观表达内容、表达方式上具备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而语言文化虚无主义不利于赋予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民族特色,阻碍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中国化、大众化进程。诸子语言观融合于哲学、经学中,其语言思想与社会、政治、逻辑思想融于一体,尚未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且语言文化复古主义不利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指导思想的确立。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37]作为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的指导思想,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为指导,吸收诸子语言观等中华优秀传统语言文化的精华,在语言文字的发展实践中相融会通,形成具有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底蕴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使其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一是树立语言源于实践而又服务实践的实践观,提升语言服务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能力,切实发挥语言文字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支撑功能;二是尊重语言文字发展规律,注重语言本体研究、基础研究,完善和发展语言文字法治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进一步贯彻和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语情和语言文字发展实情,聚焦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充分考虑、满足人民群众的语言文化需求,让人民共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成果。
恩格斯说:“要了解‘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族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5]338不忘本来,在中国传统语言观中守正出新,在与各种语言观兼收并蓄中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将日益历久弥新。面向未来,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进一步与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新形势结合起来,推进语言文字事业科学发展,推动语言文字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