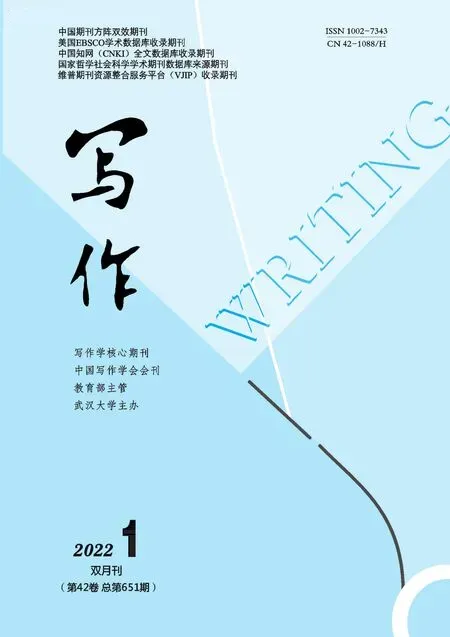“无形”与“有格”:沈从文写作教学活动的当代启示
金 鑫
作家、编辑、大学教员是1949年以前沈从文最重要的三个社会身份。丰产作家是其成为大学教员的基础,从中国公学到青岛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他都开设新文学相关课程,引发学生们的新文学创作热情。担任文艺副刊编辑便于他推荐学生作品发表,展示其教学成果,同时为新文学创作队伍输送新鲜血液。所以沈从文的三个身份是彼此关联,互相成就的。讲授新文学,开设习作课,以作家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是沈从文这位作家教员最主要的特征。
沈从文凡大学任教皆开设写作课,颇受学生喜爱,也常被学生回忆。但写作课并没有像他开设的其他课程那样留下系统、完整的讲义,一定程度上说,他的写作教学是“无形”的。但“无形”并不意味着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章法,沈从文重视将自己的创作经验通过赏析作品、评点试作、创作示范等方式传递给学生,更是将写作与新文学课程统筹起来,在一个小的课程体系中进行“有格”的写作教学。“无形”而“有格”的写作课,体现了沈从文作为作家教员对写作教育的独到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典范性,对今天的大学写作教学同样有着诸多启示。
一、沈从文大学写作教学的典范性
沈从文进入大学任教的原因与多数作家一样,都是为稻粱谋。民国时期多数作家无法只靠稿费维持生活,报馆、学校因文化氛围好、时间自由而成为作家们非常理想的去处,他们可以在这些单位一边工作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但与多数进入大学任教的作家不同,沈从文既没有当时颇被看重的海外留学经历,也没有国内大学的学历,所以他进入大学谋职颇费周折,而且入职后也仅能讲授与新文学创作关系较为密切的课程。
1929年沈从文向好友徐志摩表达了想到大学教书的想法,徐志摩便把他推荐给胡适,希望他能够到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沈从文深知自己的情况与大学选聘要求不符,主动致信向胡适表示:“在功课方面恐将来或只能给学生以趣味,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故范围较窄,钱也不妨少点,且任何时学校方面感到从文无用时,不要从文也不甚要紧。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关于各教学方法,若能得先生为示一二,实为幸事。”①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在胡适的推动下,1929年8月沈从文正式受聘为中国公学国文系讲师,开启了大学教员生涯。需要指出的是,胡适推动聘用沈从文,并非仅出于私人友谊以及对沈从文创作才华的欣赏,也与他的办学思路有关。1934年2月14日,胡适回想中国公学聘用沈从文等作家任教,引领新文艺创作之风时谈到:“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②胡适:《胡适全集》第3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沈从文任大学教员的起点,已基本决定了他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因为是作家,讲授内容主要偏于新文学的欣赏批评和创作,而教学经验和方法的欠缺,促使他产生了“给学生以兴趣”“改卷子”等想法。这些教学内容和方法虽然影响了沈从文在大学中的地位和处境,也在课堂上闹出过笑话,但客观上逐步催生出他写作教学的优长与特质。
1929年9月至1930年6月,沈从文在中国公学国文系任教,开设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两门课程,同时在上海暨南大学兼授中国小说史。1930年9月,经胡适、徐志摩推荐,陈西滢协调,沈从文到武汉大学国文系任助教,开设的课程还是新文学研究和习作,12月底学期结束即离开了武汉大学。1931年8月,沈从文受聘青岛大学国文系任讲师,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两门课,任教两年后于1933年8月离开青岛,回到北平。1933年9月,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钱玄同有意邀请沈从文到校任职,讲授西洋文学或新文学,虽经黎锦熙、郑振铎、周作人、杨振声等人几番邀请,沈从文仍坚持不再进入大学任职授课。
沈从文再次任教已是30年代末,从武昌几经辗转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附属师范学院国文系任副教授,开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三门课程,直至1946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因为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有个规定,因教学需要聘用新人,颁以西南联大聘书即可,如果三校之中有一校认为此人很好,准备联大结束后继续聘用则可以给他另加一份聘书,表示将来联大结束三校分家时此人的归属。所以沈从文1946年8月回到北平后受聘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继续开设现代文学选读和习作两门课③贺玉庆:《沈从文的写作教学思想与现代写作教学》,《写作》2016年第8期。,直至1949年初因精神疾病住院。1949年4月沈从文出院,北京大学国文系已没有他的课程。从1929年到1949年,沈从文近20年的国文系任教经历,始终没有脱离新文学和写作。其写作教学活动的典范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时空影响的广泛性。沈从文从1929年起开设写作课,虽然在时间上错过了现代大学教育萌生和快速发展的十几年,但就写作课而言,到1922年11月《大总统颁布实施之学校系统改革案》在大学推行选科制,才作为选修课逐步出现在大学国文系的课程体系中,直到1939年《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颁布,才被列为国文系必修课。所以沈从文的写作教学几乎贯穿了大学写作课的初创期、发展期和定型期,全程参与了大学写作课的发展建设。而空间上,沈从文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授写作,几乎涵盖了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的所有重要城市,在学术交流尚不便利的时代,教员的流动是教育教学、学术研究交流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沈从文用个人的流动推动着大学写作教学的交流和建设。
其次是教学内容和方式的代表性。民国大学写作课从教学内容和方式上可分为两支,一支以陈望道等学者为代表,他们授写作主要讲作文法,知识点明确,更具系统性,旨在通过知识的增加、认识的提升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另一支就是作家任教,他们因新文学创作取得成绩而开设写作课,授课多偏重文学,从创作经验出发,通过鉴赏作品、修改作业等方式指导学生。周作人、俞平伯、沈从文、杨振声、杨晦、张资平、孙席珍、许杰等作家都属于这支写作教员队伍,他们在大学写作教学方面的影响要超过前面的学者授课,而沈从文无论从授课时间还是影响力都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第三是教学效果的明确性。教育研究中教学效果是最难把握的,我们很难使教学内容、方法与学生的学习成绩形成明确对应,民国大学写作教育更是如此。一方面多数作家教写作较为随意,未留下系统完整的教学讲义,很难掌握其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学生的习作成果保存不善,难以统计并获得。但沈从文在开设写作课的作家中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其讲义《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由冰心到废名》等因在《国文月刊》发表得以示人,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其写作教学内容和方式。更重要的是以汪曾祺为代表的一批学生撰写了很多回忆文章,不仅利于钩沉当年的授课情况,还融入颇多学习感受和收获,这都使沈从文的写作教学效果更为明晰。此外,因为沈从文担任编辑,有推荐学生发表习作的便利,发表的学生习作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其写作教学效果。
沈从文的写作课在民国大学写作教育中具有典范性,同时与当下的大学写作教育也有一定对应性,可以为当今的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首先,自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议将“大学写作”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必修课后,越来越多的中文系开设写作课,大学写作课的主体也逐步由校级通识选修课转变为中文系专业课。而沈从文的写作课一直都是在国文系开设的,与当下大学写作课主流在学科归属、教学目标、授课对象等方面有颇多相近之处,这为今天的大学写作教学提供借鉴是可能的。其次,今天从事大学写作教学的教师全部是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有较为系统的中文学科知识储备,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积累,但绝大多数都缺乏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经验,课堂教学中这部分内容也往往缺失。而沈从文写作教学正是以创作经验为出发点和指向的,可以对今天的写作教学形成一定补充,为丰富写作课内涵、提升写作教学质量提供帮助。
二、以经验转化为目标的“无形”教学
作家在大学教写作,多以赏析作品和点评作业为途径,因此缺乏系统性,看起来也比较随意。比如朱自清在清华大学授写作,常用的方法是大声朗诵优秀的学生习作;胡山源在福建高师授写作,主要通过面批习作一对一指导学生;孙席珍在中国大学授写作,要求学生按时提交习作,自己随堂点评提出修改意见;白薇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授写作,要求学生多读作品,读后写读书笔记积累写作经验;冰心在燕京大学授写作,看过习作后要和每个学生进行半小时以内的谈话,还要求学生自办刊物,自行组稿;路翎在中央大学授写作,常把学生带到户外,边观察边讨论……
灵活自由的上课方式自然受到学生的喜爱和欢迎,但这样授课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即教学内容知识性不足,缺乏系统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上课多编讲义的大学国文系,作家的写作课几乎没留下较为完整的讲义。有迹可循的只有两部,一部是孙席珍文艺习作课讲义《诗歌论》,该讲义1935年曾在中国大学校内印发,但未正式出版。另一部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授各体文习作时结集的《习作举例》,未正式出版,其中3篇刊于1940年《国文月刊》的前3期。讲义的稀少,有一定客观原因,作家入大学任教往往首先开的就是写作课,教学经验不足,积累有限,编讲义不免遇到困难。但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多数作家认为写作主要依赖灵感的爆发和经验的积累,既然灵感无从把握,那就尽可能地传递经验。沈从文身为作家,很自然地也以经验传递为中心授写作课,他的写作教学是“无形”的。所谓“无形”就是放弃了对系统的写作知识的梳理和建构,教学方式方法也没有一定之规。
作家进入大学国文系任教,专任新文学和写作课的并不多,多数都要想方设法开设文学史、文学概论等骨干课程,以保住自己的教职。同时开设包括新文学和写作课在内的多门课程,为我们考察作家教写作的态度提供了便利条件。以沈从文为例,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开设新文学研究、中国小说史和小说习作三门课,到武汉大学后继续开设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三门课程中,新文学研究编有讲义,到1930年9月,讲义《新文学研究》已相当完备,并在武汉大学校内印行。小说史课也有与孙俍工合作编写的讲义《中国小说史》,虽然沈从文只参编了绪论和第一讲神话传说,但讲义他一直使用,到武汉大学任教后也曾校内印行过。与新文学研究和中国小说史不同,沈从文开设的写作课一直没有较为系统的讲义,直到在西南联大开设各体文习作,才有了《习作举例》作为授课讲义。不仅出现的时间晚,写作课讲义在形态上也与前两部有很大不同。《新文学研究》分上下两编,分别对应上下两个学期的新文学教学,上编有总括,有按照时序、特点对新诗发展分阶段的引例,下编则是六篇关于代表作家的诗论。对这部讲义,沈从文的评价是“那个讲义若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点”①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可见在追求授课内容的系统性的同时,他也重视课堂讲授的客观性。《中国小说史》仅第一讲为沈从文编写,但讲下设章,章下分专题,专题间逻辑清晰,章之间彼此呼应,体现出明显的学理性、研究性和文学史意识。而各体文习作的讲义《习作举例》从可见的三篇《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由冰心到废名》来看,都是各自独立的专题,结构上较为松散,没有时间、流派等方面的逻辑关系。
三门开设过的课程,两门早早就编撰了比较完备的讲义,一门很晚才有松散的讲稿,这种差异说明作为教员的沈从文是了解课堂教学的要求的,也具备将新文学知识化,建构成系统文学知识的能力。所以写作课缺乏完备讲义是他主动放弃了对写作知识的梳理和系统建构,是作为作家的沈从文的主动选择。在《给一个作家》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写作教学的想法:“关于写作事,我知道的极有限,近来看到许多并非是作家写的‘创作指南’一类文章,尤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若按照那个方法试验,我想若派我完成任何作品都是不可能的。”②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
没有系统的讲义也就意味着沈从文的写作课在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上都与其他讲授文学知识的课有所不同,修过沈从文“各体文习作(二)”课程的诸有琼就回忆说,“他讲课从来不成本大套地讲什么定义,什么写作方法等等”③诸有琼:《忆沈从文先生教写作课》,《新闻与写作》1988年第7期。。
没有成本大套的定义和写作方法,沈从文的写作课主要依靠文本赏析和习作评点。他在西南联大教育学院国文系授“各体文习作”的三篇讲义因发表在《国文月刊》得以保存,通过这三篇讲义可以窥探他用文本赏析授写作的方法。三篇讲义都讲抒情,这是写作中主体性很强的一个方面,从讲义内容看,有三方面特征值得注意:一是比较多地引用原文,比如《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就引用了《巴黎的麟爪》(包括引言)、《龙虎胡同七号》《云游》《我所知道的康桥》等四篇作品,占到讲义篇幅的七层以上;二是关注写作中的微观、细节问题,比较多地分析作品的语言细节,遣词造句;三是运用文本对照的方式更直观地呈现作家的创作个性。
习作点评也是沈从文一直运用的写作教学方法,他因重视习作将自己开设的所有写作课都称为“习作”或“实习”。通过学生回忆,我们可以大体把握沈从文习作课的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拒绝宏观、抽象的命题,让学生练习细微表现,进而培养写作基本功。例如他曾在黑板上写下“寒”“冷”“冻”“冰”四个字,让学生用文字形象描绘这四种不同气温状态。他还布置过“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灯下”等习作题目,都是需要学生细致观察、刻画才能完成的。二是坚持认真细致地点评学生习作。据乐黛云回忆,沈从文的写作课“要求我们每两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题目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我们这个班大约二十七人,沈先生从来都是亲自一字一句地改我们的文章,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代笔的助教、秘书之类。……先生总是拈出来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①乐黛云:《1948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北京大学校友会编:《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6页。除了写评语、分析佳作,沈从文有时还会将习作与同题材名篇进行对比,没有合适的同题材作品就自己“下水”示范,以此帮助学生查找写作方面的差距,指明未来提高的方向。
沈从文写作教育研究在学界已产生了比较多的成果,这里选择性地钩沉,旨在将其看似“无形”的写作教学与当下中文系普遍开设的大学写作进行对话,从中寻求可借鉴的东西。无论是鉴赏佳作,还是点评习作,沈从文的写作教学都显露出重视细节、尽量直观的特点。这体现了他对经验的看重以及在传递写作经验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如何在讲授知识的课堂传递写作经验一直是困扰写作课的一个难题,甚至因此产生了写作究竟能不能教的疑问。今天承担大学写作教学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已经习惯了概念、理论和系统的文学、语言学知识,而且在文学创作、应用文写作方面的经验也相对不足,写作经验的传递成了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时再看沈从文“无形”的写作教学,有一些方法是颇值得借鉴的。比如鉴赏佳作时,不做宏观的、整体性的评价,将视野尽量下沉到具体的字句表达,在字里行间汲取小的写作技巧;再比如教师也亲自“下水”和学生一起写,体会写作中的难点,与学生在“共情”的前提下实现经验分享;还可以尝试将整篇文章的写作拆解为零散的小练习,与学生在很具体的写作问题上进行交流;点评习作不做简单的定性评价,由细节着眼为学生找出写作中存在的优长与不足。概言之,让写作经验在化整为零的过程中浮现,在“共情”的交流中传递,不断地在习作中转化,是沈从文“无形”的写作教学对今天大学写作课的启示。
三、与文学教育融为一体的“有格”写作课
在大学教育已经高度学科化、专业化的今天,大学写作课往往会在学科归属、融入课程体系等方面遇到困难。以普遍开设大学写作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写作课虽然由中文系教师开设,但是从教学内容看,它无法归入文学或语言学的任何一个二级学科,与专业课相比写作更像通识课,而与通识课相比写作又更像实践课。这样的后果就是,写作课被孤立在汉语言文学的课程体系之外,难以与其他课程构成联系,无法融入学生不断系统化的专业知识,教师上课也显得底气不足。这个长期困扰大学写作课的难题,可以从沈从文“有格”的写作教育活动中找到一些办法,获得一些启示。
称沈从文的写作课“有格”,大体有两层含义,一是有格局,他在国文系开设的写作课都有明显的文学倾向,能很好地融入课程体系;二是有坚守,在授课中坚持以文学创作规律为重点,不为追求课程本身的知识性、系统性改变写作教育初衷。
民国大学开设最多的写作课是“各体文习作”,这门课最终也成为国文系的必修课,但从课名就能看出,习作的范围是很广的,决不限于文学,更不限于新文学。但多数开此课程的作家都将写作重点放在文学,尤其是新文学方面。这自然与他们的作家身份有密切关系,但应该看到,多数作家在开写作课同时还开设其他课程,他们具备不依靠创作成绩和经验独立开课的能力,所以作家写作课侧重文学创作不是简单的身份局限,其中也包含他们的自主选择。
以沈从文为例,他能够以新诗创作为中心开出颇为严整的新文学研究课,能与孙俍工合作讲中国小说史,而且在中国公学图书馆借阅大量的杂书,在武汉大学任助教期间,对金石学也有所研究,到了青岛大学更是对先秦的巫文化产生了研究兴趣,这都体现了沈从文极强的学习能力,其教员、学者身份随着其任教经历的增加日益凸显。到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在行文上已开始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像《见微斋笔谈——小说上吃人肉记载》《宋人演剧的讽刺性》等收在《沈从文全集》第14卷《见微斋杂文》集中的文章,都明显区别于一般的作家创作。所以沈从文有能力将各体文习作开成辐射更广泛的文体类型,以知识、文献填充的纯讲写作理论、写作发展史的课程。但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始终坚持将写作课作为文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基于此,沈从文的写作课无论开到哪里都得到众多学生的喜爱,这其中自然有新文学的拥趸,但也有相当多的学生是基于对国文专业的认同而接受进而喜爱写作课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沈从文新文学研究主讲新诗,中国小说史主讲小说,写作课无论是赏析名家作品还是布置习作题目都偏向于散文,在因人设课、教员自主性很强的时代,这种安排本身也可体现出沈从文的一种格局,他有意无意地从文体角度将写作融入了正在逐步建立的新文学课程体系。
在写作课就是文学创作课的大前提下,沈从文凭个人文学创作成绩成为写作课堂的权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课程因知识性不足带来的权威感的缺乏。
比如鉴赏佳作的写作课上,沈从文选择的文章多出自自己好友或熟悉的作家之手,这样他能更准确把握作品的特质,捕捉作品中作家的身影和精神,加上一些学生们完全无法知晓的作家间的交游往来故事,不仅成就了专深、充盈的写作课堂,也奠定了自己的权威性。再比如沈从文利用自己在报刊界的影响力,积极推荐学生的优秀习作发表,而他本人与各个报刊的熟络关系以及他担任主编多年所养成的敏锐的选稿眼光,也汇入写作课,拓展了写作课内容和学生的习作空间。汪曾祺曾说过:“我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①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页。学生的作品在报刊发表,一方面会提升学生写作的兴趣与信心,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沈从文在写作教学中的权威性。
以创作成绩和报刊资源成为课堂上的权威,获得学生的认可和信服,沈从文便可以摆脱写作经验必须知识化才能在课堂讲授的束缚,将那些抽象的、甚至有些难以言说的创作体会都带入课堂,这既是他身为作家所独有的,更是符合创作规律的。从他《习作举例》中的三篇讲义看,沈从文非常重视抒情这一带有很强作家主观性的写作方式。但他并不单纯分析写法和技术,他讲徐志摩的抒情,美质在于青年的“动”,他讲周氏兄弟的抒情,立足于中年人对世事冷热疏分的感慨与观照。徐志摩也好,周氏兄弟也好,他们的抒情,都离不开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沈从文在传递一种写作教育观念,单纯的写作知识、修辞技术是无法成就佳作的,创作者自身的精神气质、主观条件才是作品优劣的决定性因素。这是符合实际的,同时也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但如果不是立足文学教育的写作课,没有让学生信服的权威性,这些非常抽象、主观的东西是无法进入写作课堂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沈从文“有格”的写作课,它以明确的文学倾向融入国文系课程体系,以教员的创作成就和报刊影响力在学生中树立权威,以学科归属和权威性为基础,将作家精神气质、主体性等影响写作的主观因素引入课堂,克服了写作规律抽象、模糊、难以令人信服等弊端,进而实现了对写作教学的真正坚守。
陈平原曾总结沈从文的教员生涯:“不是大学教育启发了他的文学才华,而是他改变了学院里的教学方式。”①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这充分肯定了沈从文写作课对国文系教学的影响,而“无形”“有格”正是产生影响的两个重要推动力。在众多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恢复开设写作课的今天,回看沈从文“无形”与“有格”的写作教学,仍有颇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微观的教学方法上,正视写作经验的重要性,教学重心下沉,从细节着眼,在师生不断对话中传递写作经验,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宏观的教育观念上,要认识到学科归属的重要性,将写作课置于一定的课程体系中建构,以此获得更广泛学生的认可,再通过提升教员的课堂权威,弥补课程知识性、客观性的不足,最后将抽象、主观的写作规律搬上以传递知识为主的大学课堂,实现真正的写作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