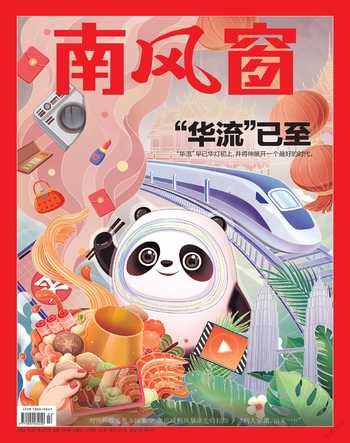埃博拉疫苗启示录
何承波

人类是否做足了准备,以应对一个长期公认的致命病毒的暴发?最近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带来了新的疑问。
10月初,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位患者患上了一种很致命的出血性热病,死在了当地的国家转诊医院,死因不明。
几天之后,医生和专家们才确定,这是埃博拉病毒,而且属于相对罕见的苏丹毒株。
事实上,埃博拉在乌干达已呈暴发之势。过去两个月里,确诊病例总计73例,其中38人死亡。
9月20日,乌干达政府宣布了第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人,而0号病人要追溯到什么时候,没人知道。此时,不少金矿区已经集中暴发了疫情。有的矿区比邻繁华的交通要道,曾一度引发国际社会的不安。
果不其然,病毒最终还是悄然进入了首都。坎帕拉拥有人口300多万,在东非算是一个繁华城市,作为经济枢纽,连通着卢旺达、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等内陆经济体。商客往来,络绎不绝。
埃博拉是一种很致命的病毒,平均死亡率在50%左右,有的地方甚至高达90%。1976年,该病毒首次发现于埃博拉河畔,并以此得名。病人始于高烧、头痛、喉咙痛、关节腹部疼痛等,很快,身体任何孔会出血,包括鼻、口、肛门、生殖器官或针孔。
目前已发现的埃博拉病毒有6个亚种。其中,波及人类社会的主要有两种:扎伊尔毒株,首次于扎伊尔北边城镇暴发;苏丹毒株,首次在苏丹棉花厂工人身上发现。
距离苏丹毒株的上一次暴发,已有10年了。这期间,一直没有任何该毒株的疫苗进入人体测试,也没有任何药物进入审批。如今仅有扎伊尔疫苗,也无法证明可对其生效。
眼下,苏丹毒株的卷土重来,打了东非国家一个措手不及。
那么问题来了,正经历新冠疫情洗劫的人类社会,将如何应对类似的传染病?后新冠时代的疫苗研发,能否跑赢病毒的传播?
每一种疫苗的研发,背后总有精彩纷呈的独特故事。埃博拉疫苗也不例外。
20多年里,数度搁置,不断流产,埃博拉疫苗经历了一系列的曲折,有些是偶然的,有些是不太偶然的,有些本不该如此发生的、但最终发生了。
埃博拉疫苗好像是成功了,但此消彼长,病毒家族的另一支脉,卷土重来。
20世纪90年代初,耶鲁大学一位名叫约翰·杰克·罗斯的科学家,一直在琢磨一种牲畜病毒—水泡性口炎病毒(VSV),他试图找出一种方法,将其改造成某种疫苗载体系统。VSV能感染人,但不会使人生病。免疫系统对该病毒的反应很快,而且诱发的抗体水平也高。
如果它能被设计成流感或艾滋病毒等病毒病原体的基因,那么它就可以成为一种疫苗的有效载体。
罗斯的小组在VSV中加入了一种流感病毒的蛋白质,将其注射到小鼠体内。中和抗体反应非常快,小鼠也得到了完全的保护。
罗斯证明,VSV可以作为禽流感、麻疹、SARS和其他病原体实验性疫苗的载体。
但是,没有足够安全的实验室,罗斯没办法验证VSV对埃博拉病毒的疫苗是否有效。理论上,它应该是可行的。
罗斯与全世界100多家实验室分享了他的VSV载体。其中一间,位于德国的马尔堡。正是在那里,1967年,实验室工作人员感染了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病毒—马尔堡病毒,它跟后来的埃博拉一样,来源于非洲,属于丝状病毒,死亡率也奇高。
当地的科学家汉斯·迪特·克倫克拿到罗斯的VSV载体后,开始反思:马尔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被发现已经20-30年了,竟然没有任何疫苗方面的研究,他决定改变这个现状,随即抛开了流感,钻进了埃博拉的世界。
有研究表明,埃博拉病毒具有治病效应的蛋白中,一种是糖蛋白。克伦克小组成功将其替换VSV病毒表面的糖蛋白与G蛋白,制造了一种混合病毒,但由于实验室封闭性不够,没办法进行动物实验。
彼时,全世界很少有达到4级生物安全(P4)的实验室,可用于埃博拉或马尔堡这种致命病毒的研究。
大西洋彼岸,加拿大温尼伯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建造了18年,终于在1999年投入运行。4级生物安全,是研究埃博拉病毒所需的安全等级。跟克伦克短暂共事过的病毒学家海因茨·费尔德曼,决定前往那里任职。临走前,他带走一份VSV载体样本。
但费尔德曼一心只想着用来研究糖蛋白,他对疫苗没有任何兴趣。
一个偶然的场合,他听到了美国NIH疫苗研究中心主任加里·纳贝尔的演讲,后者提出观点,说糖蛋白是埃博拉病毒感染动物和人时造成严重损害的原因。
他想证明,权威如纳贝尔之流,也可能出错了。他们用含有埃博拉糖蛋白的VSV病毒感染了小鼠。如果纳贝尔的理论是正确的,这种蛋白质应该对小鼠造成毒性,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伤害。
灵机一动,他们把这些小鼠暴露在埃博拉病毒下,小鼠依然完好无损。而没有接触过VSV病毒的小鼠,全部死亡。这说明,VSV病毒的确有疫苗作用。
埃博拉疫苗的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
研究工作还没怎么开展,另一种令人震惊的新疾病却来了。2003年,中国、越南、新加坡和加拿大多伦多,先后出现了SARS疫情。
费尔德曼的实验室,成立了特殊病原体小组,投入了关于SARS的研究,试图确定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新疾病,如何控制它。一些常规工作被搁置了,也包括埃博拉疫苗研究。
历史往往具有一定的巧合性。2012年,阿拉伯半岛的骆驼身上,另一种冠状病毒也跃入人体。这两次短兵相接,使人類科学家得以认识冠状病毒的基因结构。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疫苗研究得以快速响应,也得益于这样的斗争经验。
回到埃博拉疫苗,SARS疫情的几年后,费尔德曼团队的小鼠实验才得以复制到非人灵长类动物身上。接触到VSV的猴子,在本应是致命的埃博拉病毒中,幸存下来。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科学发现,加载了埃博拉糖蛋白的改良版VSV载体不仅安全,而且可以作为有效疫苗的基础。
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埃博拉被发现30多年来,死亡人数大约1300人。埃博拉只出现在非洲贫困国家,对此制药公司不会有任何兴趣。毕竟,疫苗的开发成本高昂,保底10亿美元。
对于费尔德曼来说,兴奋感转瞬即逝,如同在酒吧喝完一杯啤酒,接着投入了新工作。
2008年,他离开了温尼伯的实验室,似乎没人再记得埃博拉疫苗这回事了—此后在美国,他一次又一次地申请埃博拉研究的资金,一次又一次被拒。
但2009年3月发生了一个意外。一名德国研究人员在做小鼠实验时,被针头刺伤了手指,针头穿透了三层手套,她的皮肤被刺破。
要命的是,针头含有埃博拉病毒。
这种实验室事故,非同小可。
她被送到汉堡大学医疗中心,那里的专家跟加拿大的埃博拉研究人员取得了联系。结论是,暴露后的48小时内,注射“疫苗”,可以提高存活率。但问题是,现在的VSV埃博拉“疫苗”,只在动物身上测试过,在人体的效果如何,没人知道。
最终,这名女性研究员,还是接受了来自加拿大的“疫苗”—甚至不能称为疫苗产品,只是一份动物用的研究材料。
赶在第48小时,“疫苗”跨越大西洋,注射到了研究员的体内。
次日,研究员出现发烧症状,可能是免疫系统被激活,也可能是埃博拉感染的早期症状。
好在,没多久烧就退了。至于是疫苗起了作用,还是压根就没感染,没人知道。但这一结果,令科学家们感到欣慰,也间接推动了埃博拉疫苗的部署。
此时,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埃博拉疫苗项目,由病毒学家加里·科宾格负责领导。加拿大政府给了他们一笔200万美元的拨款,杯水车薪,但来之不易。
代价就是,此后每年,部门负责人都要向上级阐述,为什么要研究埃博拉疫苗。这笔钱其实是国防部拨的,用来资助关于生物恐怖主义工具的研究。
科宾格团队研究的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这是埃博拉病毒最主要的亚型之一。在此之前,这种病毒只在非洲暴发,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那里的疾苦,太过于遥远。
科学家们与各种大小制药公司交谈,寻找开发伙伴,唯一感兴趣的是一家名为BioProtection Systems的小公司,隶属于NewLink。
科学家很快发现,自己被精明的商人摆了一道。
按协定,该公司同意为其开发的每个产品向加拿大政府(专利持有方)支付约15.6万美元。加拿大政府还将从一些销售中获得特许权使用费。
但这是空头支票。一直到该公司并入一家名叫Lumos Pharma的公司,埃博拉疫苗的开发,都没有任何推进。
BioProtection Systems压根没有开发的打算,埃博拉疫苗不过是其捞钱的幌子,用来增加其资产组合,吸引外界投资。
时间来到2014年3月23日,世卫组织报告了几内亚的埃博拉疫情,80人感染,59人死亡。疫情迅速演变。一周之内,几内亚首都、邻国纷纷出现了疫情。
这是历史上最凶猛的一波埃博拉疫情,2014年12月17日世卫组织报告,在疫情肆虐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西非三国,感染病例达19031人,其中7373人死亡。
早在疫情之初,远在加拿大的科宾格密切关注着这一切。
他向世卫组织提出了疫苗供应的建议,但被拒绝了。毕竟,未经人体测试的“疫苗”,有多少风险,没人知道。世卫组织的拒绝,倒也无可厚非。
在可怕的埃博拉面前,这些风险又何足为惧呢?科宾格没有放弃,辗转找到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经由该组织的埃博拉专家Armand Sprecher的倡议和警告,无国界医生开始推动使用VSV疫苗。
2014年8月8日,世卫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9月,埃博拉病毒跨过大西洋和地中海分别抵达北美洲和欧洲,很快,美国和西班牙相继报道出现感染者。
国际社会,这回终于慌了。
世卫组织也得出结论:实验性疫苗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另一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开始了一期实验,以确定VSV埃博拉疫苗的合适剂量。
讽刺的是,VSV埃博拉疫苗的持有方,BioProtection Systems及其母公司NewLink,压根不具备疫苗生产能力,专业度也堪忧。
世卫组织只好选择了默沙东公司,后者企图跟NewLink谈判,以获得疫苗的制备和分销权。
但是,西非疫情还在肆虐,谈判却没完没了。
一直到2014年12月,以默沙东公司支付5000万美元为代价,事情才有了着落,实验终于启动。
但问题没完,而且看上去更严重,作为一期实验的参与者,科宾格发现,早期费尔德曼实验用的疫苗,是一种名为Mayinga的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糖蛋白。
但现在的实验中,科宾格发现,某些关键结构却变了,糖蛋白不一样了。现在用的是另一种扎伊尔埃博拉病毒。
原来,在温尼伯实验室长达十多年的工作迭代中,一位名叫阿利蒙蒂的科学家,根据上级指示,曾使用了不同的糖蛋白,这一更改,并未记录在案。
从医学监管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科宾格写邮件给美国FDA,没有收到回复。而此时,紧急疫苗的实验,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疫苗一出来,科宾格给美国蒙大拿州的费尔德曼紧急寄送了一批样本,让他能够在灵长类动物中测试一下,得到没有问题的答复后,他才安心下来。
停滞了十多年的埃博拉疫苗,也是在病毒威胁迫在眉睫的情况下,终于迎来了转机。葛兰素史克公司、强生公司,也纷纷开启了对埃博拉疫苗的研发。
2018年春,当埃博拉病毒在刚果暴发,刚果政府同意根据一项“人道使用”协议,使用疫苗。至今,该国已有超过26万人接种了疫苗。
2019年11月11日,欧盟批准了默沙东公司的埃博拉疫苗Ervebo,主要用于扎伊尔毒株的预防,这是首个获得监管机构许可的埃博拉疫苗。随后,美国FDA也予以批准。
长达20多年的埃博拉疫苗开发历程,走得跌跌撞撞,数度夭折,险象丛生,总算迎来一个不错的结局。
但真的圆满了吗?未必。
眼下的难题,又来了。
苏丹版本的埃博拉病毒,还在持续扩散,何时能扑灭,会不会蔓延到国际社会,还是个未知数。
可以确定的是,苏丹毒株和扎伊尔毒株有着很大程度的不同。默沙东和强生研发的两种疫苗,对此起不到作用。
当然,这个问题并非来自人类的短视和惰性。
现实在于,过去十多年来,苏丹毒株似乎毫无踪迹,科学家们也没有任何机会认识它。所以,疫苗与药物的开发,能不能跟上疫情传播的速度,谁也说不好。
疫苗的开发,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回顾一下,新冠之前,有史以来最快的疫苗—治疗腮腺炎的疫苗也花了四年时间。而大部分疫苗的研发周期都超过10年。
疫苗开发是个大工程,耗资巨大,周期漫长,既是个科学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地区的不平等,信息的不对称,有时也会加剧这个游戏规则的复杂性。
埃博拉疫苗的研发,更是一个典型案例,深刻揭示了人类面对区域性致命传染病的潜在态度。
好在,近几年的变化也是有的。毕竟,新冠疫情教会了我们很多。
2020年1月10日,从中国科学家首次发表新冠的基因序列,到第一款90%有效的疫苗诞生,仅用了10个月。随后的一年内,一半的人类接种了疫苗。这样的速度,搁在过去的医学史是很难想象的。
新冠疫苗的开发、实验、测试和制备、分销,堪称人类历史的一场奇迹。
一方面,是新冠疫情加速了新技术、新工具的革新。比如,mRNA疫苗的出现,让疫苗开发变得更加快速、便捷、廉价。
新冠疫情,正在加速这些疫苗平台的商业化,它们的应用前景,将逐渐打开。好消息是,最新的艾滋病mRNA疫苗已进入人体实验阶段。
更重要的是,疫情革新了我们应对病毒和疫苗研发的机制。
以往,病毒的基因测序、演化路径的追踪,都是单点突破。新冠疫情下,尽管国境多被阻断,但人类的响应力和合作效率似乎空前提高了,病毒演化树的构建和更新,几乎做到了实时进行。得益于全球协作,疫苗的生產和交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效。
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国际社会的响应速度,也是空前的。世卫组织表示,如果想在最多一两个星期内开始一项试验,我们会做所有能做的努力。
乌干达疫情暴发一个月内,已有三种疫苗开始了早期测试,以确保它们在人体中的安全性。另外还有6种候选疫苗,也在开发中。
这跟2014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彼时,因为一些荒唐的纠纷,硬生生拖了8个月,实验才开始。如果是传染性更强的病毒,局面将很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