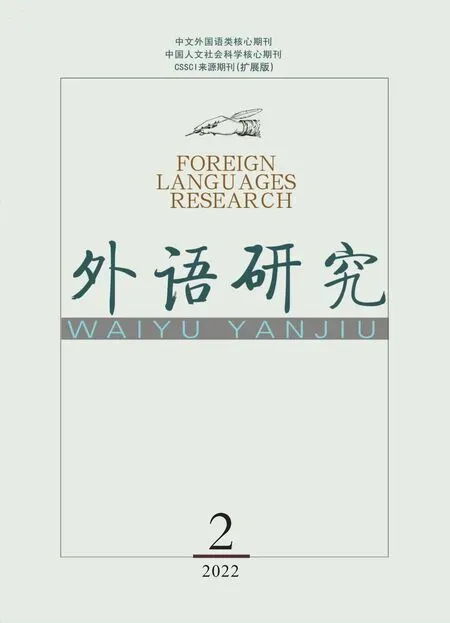蓄意隐喻理论及其在话语分析中的应用*
吴 迪李雨晨
(1.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广东 珠海 519082;2.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0.引言
隐喻经历了从语言层面的修辞学研究、语义学研究,到当下主流的思维层面的认知研究,体现出其巨大发展潜力与研究的精细化要求。传统的修辞格研究关注语言的表层,将隐喻看成一种文字游戏。20世纪80年代起,隐喻研究发生了“认知”转向,隐喻被定义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Lakoff&Johnson 1980:52-55,74-129;1999:45-59)。
既然是源自思维,那么隐喻的力量应该来源于有意识的刻意为之而非无意识的使用(Steen 2013:184-187)。事实上,很多隐喻对听者而言可能并未呈现为隐喻,例如“He attacked my argument”这句话中attack一词表示辩论中的反驳;“人红是非多”一句中的形容词“红”表示受欢迎程度等,说者和听者都能心照不宣地将它们辨别出来。也就是说,这些表达的产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有些隐喻会被发话者蓄意地当作一种修辞手段,以此邀请听话者在心理上建立跨域映射,从而引导听话者的焦点。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中有一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诗人有意地邀请读者在thee和summer’s day之间进行比较,目的也是使读者改变视角,关注summer’s day所投射的源域并从此重新审视thee,达到吸引读者对句末信息关注的目的。
又如张爱玲曾将“人生在时代中前行”这一状态置于“乘客乘坐列车行进”的场景框架下进行描述:
[1]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生存在车子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可惜我们只顾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张爱玲1993:172-173)
作者将时代的变迁比作轰轰前行的列车,被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人则被比作车上的乘客,其目的是使读者改变视角,也就是关注到“列车”所投射的源域并从此出发重新审视“人生”。文中的“几条熟悉的街”“一瞥即逝的店铺橱窗”等都成了源域所关指的场景。人在时代变迁中或被迫成长,经历坎坷,或历经平凡无味的琐事,最终仍不能在关键时刻选择自己的命运。这就像是乘客坐在列车上,忙着在路边一瞥即逝的店铺橱窗中找寻自己的倒影,然而最终却一无所获。
可见,隐喻不仅仅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方式,还具有交际功能。这就要求人们从语篇的层面重新认识隐喻,拓宽隐喻研究的外延,构建更完整的隐喻分析模式。
1.蓄意隐喻理论产生的动因
理论上将隐喻定义为跨域映射并不意味着在实际的隐喻加工中激活了跨域映射。将“交际”的维度纳入对隐喻的分析,判断隐喻是否被蓄意地使用可以解决这一悖论。
1.1 概念隐喻研究存在的问题
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CMT)的基本命题是:隐喻并非语言层面的问题,而是思维层面的问题,是概念系统的跨域映射。CMT深化了传统修辞学辖域下隐喻的内涵意义,使之蜕变为一种概念性机制、一种思维模式,把语言和思维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其本质是二维研究。
在CMT视角下,发生在思维中的在线跨域映射的构建是人们处理隐喻义的关键。例如在“Argument is war”一句中,argument和war分别投射出两个不同的概念域(作为靶域的“辩论”和作为源域的“战争”),人们会自动在这两个概念域之间建立一种互通,通过源域去更好地理解靶域。但是,也有很多词如attack、defend、win、lose等,在长期使用中已经形成了“辩论”这一隐喻义。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在使用其隐喻意义时可能已经不会构建关于“战争”的跨域映射(Jackendoff&Aaron 1991;Glucksberg&Keysar 1990;1993)。事实上CMT的后续发展也开始关注是否所有的隐喻加工都构建了跨域映射(Lakoff 2008)。Glucksberg(2001:1-15,90-107;2008)指出,大多数概念隐喻并不需要通过建立跨域映射进行语义加工处理。他区分了两种隐喻理解的方式:比较(comparison)和范畴化(categorization)。前者是指语言使用者在两个概念域中构建了跨域映射,后者是指将隐喻表达中的两个概念归类到一个更高的上位范畴去理解,这一过程并不产生跨域映射。例如在“My lawyer is a shark”一句中,shark一词属于上位范畴,包括了两个名词lawyers和sharks所指的实体,他(它)们都具有凶猛、无情、富有攻击性的特征,听话人并不需要建立概念结构的跨域映射就可以理解其语义(Glucksberg&Haught 2006)。隐喻历程理论(The Career of Metaphor Theory)(Gentner&Bowdle 2001;Bowdle&Gentner 2005)也认为,规约隐喻通过范畴化来理解,新奇隐喻才需要通过比较来理解。
Steen(2011a:50)指出,隐喻在语言使用中的比例只占13.6%,其中99%是规约隐喻,只有1%是新奇隐喻。结合隐喻历程理论,Steen的研究发现表明大多数隐喻理解可能并不需要构建跨域映射,这就与CMT中隐喻的普遍性特征(Lakoff 1993)相悖:语言层面上的隐喻可能在概念层面上不是隐喻;理论上,将隐喻定义为跨域映射并不意味着隐喻在使用加工过程中也呈现跨域映射(Steen 2008;2011a)。这一悖论的产生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局限在语言与思维两个维度下的概念隐喻理论,从新视角来看待问题。
1.2 交际维度介入的必要性
为解决在语言和思维两个维度上存在的隐喻悖论,Steen(2008)首次提出将“交际”纳入隐喻的分析模式。交际中的隐喻有别于语言中的隐喻和思维中的隐喻,它是指说话人在特定场合下选择特定的隐喻来进行表达,有意地使用该隐喻对听者的注意力进行调节,使其转移到源域上并形成在线的跨域映射。交际中的隐喻又叫作蓄意隐喻(deliberate metaphor,DM);而有时候,说话人所说的隐喻只是一种言谈途径,双方都心知肚明,并未产生跨域映射,这类隐喻在交际层面便是非蓄意隐喻(non-deliberate metaphor,NDM)。
不可否认,在语言使用中NDM的频率远高于DM,其语言形式多为广为人知的一些说法,如“山脊”“黑马”“建设美好家园”等等,这些表达对双方来说自然而然就能被理解。然而,话语交际中的DM是一种特殊的隐喻类别,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发话者邀请或在某种情况下强制听话者进行语义加工处理,从而在听话者心理表征中在线地、临时地建立跨域映射,使其将视角暂时性转移到源域概念中去。DM发生时,就好比说话人对听话者说:“从这个角度看……”,它像是一种特别的指令,引导听者转移注意力。DM是说话人的蓄意而为,使听者构建在线的跨域映射,通过比较的机制理解隐喻(Steen 2013:180),它揭示了隐喻不仅体现在语言和思想上,还体现在交流与沟通上。
当隐喻被看作是实际语言使用的一部分或一个话语事件,它就具有了交际功能。纳入交际维度后,隐喻研究就从语言和思维的二维模式扩容至包含语言、思维、交际的三维模式。从交际维度理解隐喻是指在隐喻表达传递过程中,该信息对言说对象产生了另外一种理解视角。隐喻在语言功能的描述上激发了词汇多义现象,在概念功能的描述上激发了相应的概念系统,而在交际功能上实现了语言使用者传递意义的初衷。
Steen(2011a:38-39)认为隐喻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呈现了“二选一”的表现形式:在语言形式上表现为明喻或暗喻,在概念结构上表现为规约隐喻或新奇隐喻,在话语交际中表现为蓄意隐喻或非蓄意隐喻。在三维的隐喻分析模式中,隐喻的语言形式、概念结构与交际属性形成了三维互补关系,每一个维度都与其他维度相互关联,是一种动态交融的关系。这种隐喻分析模型不再是单一的认知语言学或心理学的分析模式,而属于话语的分析模式,它是对隐喻理论研究的增容,既有利于独立地近距离观测隐喻的细节特征,又有助于全面综合地把握隐喻的总体格局(孙毅,陈朗2017:716)。
2.蓄意隐喻理论的内涵与认知基础
三维的隐喻分析模型即围绕DM的研究。Steen从2008年提出到2015年正式建立的蓄意隐喻理论(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DMT),其主要学术观点是:隐喻不仅是由语言表征的概念结构,也是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交际手段(Steen 2008;2010;2011a;2011b;2011c;2013;2015;2017;2018;Reijnierse et al.2018)。本节将扼要介绍该理论的内涵与本质特征。
2.1 蓄意隐喻理论的内涵
认知语言学以及心理学对隐喻的研究主要关注词汇意义,DMT在此基础之上把隐喻研究拓宽至语言文本的维度上:首先,语言表达生成了话语,继而构建了表层文本、深层文本、情景模型和语境模型等四个层级。表层文本即词汇,深层文本是指概念,情景模型对应所指(referent),语境模型对应话题和视角(Steen 2008:235)。在DMT理论框架中,首先要区分清楚文本中的“概念”与“所指”:深层文本中的隐喻概念,在情景模型中不一定是该隐喻所指,至于隐喻何时被加工识解为隐喻,取决于话语交际中的蓄意性(deliberateness),这种蓄意性就体现了说话人的话语策略。
区分了概念和所指之后,才能正确区分DM与NDM。Reijnierse et al.(2018:129-131)曾以美国总统预选的新闻文本为例,比较了二者的异同:
[2]The political battlefield is strewn with corpses.(...)‘Bom,bom,bom.Now I’m left with two guys.Hardly two guys.Maybe you could say one.A half and a half.’If this were Game of Thrones,(...),Trump would be describing some gory dismemberment.But in America’s Republican party equivalent,the businessman obsessed with gold has slashed his way through a field of 17 election candidates,as contemptuous of foes as Tywin Lannister(...).And although he put rivals to the sword in the New York primary this week,Trump appears to be looking over his shoulder,fearful of his own political demise.(Smith&Jacobs 2016)
在例[2]中,靶域“政治”是通过“战争”这一源域来进行描述的,尤其是共和党的总统竞选,被刻画成了电视节目《权力的游戏》中的场景,而特朗普临时地变成了该剧中的主角。共和党竞选被描述为“尸横遍野的战场”(“a battlefield that is covered with corpses”),这里的corpses指的是那些退出竞选的候选人。特朗普则一直“在战场上所向披靡”(“slashing through the field of candidates”),意指他在竞选中连续胜出、击败对手。另外,将总统特朗普与《权力的游戏》中最大势力家族的首领泰温·兰尼斯特相联系,暗示其政治政策与兰尼斯特臭名昭著的“红色阴谋”有相似之处。
与例[2]相同,以下三个例子也可以分析为通过“战争”来描述“政治”:
[3]Hillary Clinton attacks Bernie Sanders as New York primary looms.(Weaver 2016)
[4]The Battle for New York’s Key Voting Blocs in the primaries.(Fessenden&Almukhtar 2016)
[5]Ted Cruztakesanti-Trump campaignto Wyoming.(Associated Press 2016)
例[3]中,希拉里对桑德的批判是通过“使用暴力对其造成伤害(attack)”这种方式进行表达的。例[4]中,竞选纽约预选的场景则被描述为“一场战斗(battle)”。例[5]中,政治家们为赢得竞选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则被描述为赢得战争的一系列“军事行动(campaign)”。
根据DMT,例[2]属于DM,例[3]—[5]则属于NDM。四句话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使用了与战争相关的术语来描述政治竞选运动。不同的是,例[2]中,隐喻是作为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交际策略起作用的,这些隐喻性的表达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读者从《权力的游戏》中的战争场景这一角度来看待特朗普的政治成功,并且这一新视角在文中有显性标记,如“If this were Game of Thrones,(...).But in America’s Republican party equivalent...”;相反,在例[3]—[5]中则没有隐喻被蓄意地用作隐喻的显性标记,隐喻并未在表达中发挥引发新视角的交际功能。例[3]—[5]中的隐喻性表达如attack、battle、campaign等,在日常生活中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司空见惯的谈论政治的词汇。
DM是一种有意识的话语策略,旨在达到特殊的交际目的,说话人通常会迫使听话者有意识地比较并搭建跨域映射;而NDM并未如此,是通过归类或词汇歧义消解来理解。例[6]选自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2018年新年贺词:
[6]中共十九大描绘了我国发展今后30多年的美好蓝图。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要把这个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习近平2018)
这句话向听众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发展目标的要求,祖国的发展前景很美好,是一副“美好蓝图”,必须通过踏实的工作才能实现。“蓝图”是一个常规性的隐喻表达,新华词典上将其定义为“比喻为建设计划”,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归类就能理解这个隐喻词汇,而不需要在源域(“绘图”)与靶域(“计划”)之间建立在线的映射才能理解。因此,“蓝图”在这里是NDM。但是习总书记在两个“蓝图”之间,插入了一句话“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这句话描述九层高台的建造过程,是从一筐土开始堆积起来的。引用这句话,成功地把听者的注意力带到了建筑场景中,并在这个场景中继续理解后文提到的“蓝图”及其实现的要求。如果没有这句引用,那么听者的注意力始终会留在当下话题所关指的场景中;但是加了这一句引用,听者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了靶域中,并暂时地把视角挪到建筑这一场景中去理解当下的话题。因此,“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这个引用在篇章中属于DM,是说话人蓄意地把隐喻当作隐喻使用,临时性地让听者构建起源域与靶域之间的映射,回到源域的视角去理解话题,以实现交流目的。
2.2 蓄意隐喻理论的认知基础:注意力的分配
既然DM与NDM的主要区别是注意力是否被转移到话语指称意义的源域之上,那么当且仅当其语言结构表明听话人必须把注意力从当前的话题暂时离开,转移到隐喻表达所激活的源域之上时,该隐喻才具有蓄意性。也就是说,“注意力”在源域的呈现是DM的核心特质(Steen 2015:68;2017:7),是DMT的认识论基础。
DMT中“注意力”的内涵有别于“意向(intention)”和“意识(consciousness)”(Steen 2015;2017)。“意向”是指语言使用和会话都是有意向的言语活动,话语意向尤其能约束语言的使用意向,也就是说所有隐喻的使用都是有意向的,但有一些隐喻使用是蓄意的,而大多数隐喻使用不是蓄意的(Steen 2017:5-6)。“意识”是指说话人的觉知(ibid.:6),语言使用和话语是自主的、无意识的。在语言使用中,无意识的加工在话语的工作记忆中产生语言使用的思维表征,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能察觉到其细节,但却很少意识到他们自己已经察觉到了。人们只会在特殊情况下意识到这些细节,比如在进行诗歌创作中,有些语言使用中所呈现的不同寻常的特点会被人们意识到。
无意识的加工会导致注意力视窗中的内容以被察觉到的特征形式保存在工作记忆当中。所谓“注意力”就是指由这些凸显的特征在工作记忆中所形成的心理表征且符合语言交际的目的(Langacker 1987:115-116;Talmy 2000:258)。DMT将“注意力”定义为:它把隐喻源域中的指定表征形式当作话语处理过程中的一部分来处理,此时,源域中的所指就成为了话语所关指的对象,出现在注意力范畴之内(Steen 2015:68),并且在语言结构、概念结构或交际方面该表达也相应呈现出扩展性或新奇性等特点(Steen 2013:185;张建丽2017)。
可以看出,与CMT强调自动性的意识不同,DMT强调的是主动性的意向(张建丽2017)。例[7]选自2017年11月《新民周刊》官方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中国‘朋友圈’越来越大”,记者孔冰欣这样写道:
[7]习近平一次次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行程百万里,踏遍五大洲,五年来,作为中国的“首席外交官”,习近平将热爱和平、谋求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传递到世界各地。“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得到空前提升。亚洲邻居会记得,……俄罗斯伙伴会记得,……美国朋友会记得,……欧洲大陆会记得,……拉美人民会记得,……非洲兄弟会记得,……阿拉伯国家会记得……(孔冰欣2017)
这段话中,“国家是人”这一隐喻通过“中国主张”“负责任大国”等表达得以呈现。从“人”的角度去理解“国家”,继而理解国家肩负的责任,这种比较是两个概念域之间跨域映射,是概念隐喻,并且在频繁使用中其隐喻义已经固定,不需要通过源域理解。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思维方式,因为人们都认可了国家具有这些“人物”般的特征,很少意识到或知道自己对这种相似性的察觉。
与这种无意识的加工不同的是“‘朋友圈’越来越大”这句话体现了一种主动的会话意向,属于DM。“朋友圈”属于信息时代的新产物,现在使用“朋友圈”的语境无一例外都是指中国最大的社交软件“微信”上的一个功能。微信的朋友圈功能让用户可以发表文字和图片,也可以对好友所发布的消息进行评论或点赞,时下已成为人们互相交流、沟通、联络、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汇集圈内朋友状态,是一个属于圈内人的公开场所。该记者在谈到未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关系时,借用“朋友圈”这个概念成功地把听者的注意力从抽象的国际关系吸引到熟悉的社交场景中。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政治的敏感度并不高,这就需要政治家们运用一些话语策略来帮助传达抽象的政治概念。此时,作为新奇隐喻的“朋友圈”就在听者心中激活了与微信社交所关指的概念,在线构建了源域(“微信社交”)与靶域(“国家外交”)之间的跨域映射,并且在接下来谈到亚洲邻居、俄罗斯伙伴、美国朋友、欧洲大陆、拉美人民、非洲兄弟、阿拉伯国家的时候,听者的注意力依然停留在源域中,透过微信社交的场景去理解靶域中谈及的中国外交战略关系。
从交际的角度来说,当隐喻被蓄意地使用,就会出现交际表达的异化视角,而NDM仍然依附于当前话题,听话人不必将注意力置于隐喻表达的源域之上。
3.蓄意隐喻理论质疑与争辩的核心:隐喻与意识
DMT的提出也受到了质疑与批评(Gibbs 2011a;2011b;2015a;2015b;Gibbs&Chen 2017)。张建丽(2021:71)认为Gibbs与Steen对DMT的争论是隐喻研究的“体验观”与“话语观”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Gibbs的批评具体表现为:(1)没有必要区分DM与NDM,因为所谓的DM与传统修辞学领域的创造性隐喻和诗性隐喻没有区别,且在具体分析中也是难以确定的;(2)将交际纳入隐喻分析并不具有创新性,最关键的一点是DMT忽略支撑CMT的大量实验研究且无法提供DMT的心理实验证据;(3)DMT不支持实证检验,Gibbs(2015b)考察DM的话语标记如何影响语言使用者的隐喻理解,结果是对DMT的驳斥(同上:71-74)。
实际上,Gibbs与Steen争论的核心问题源于对隐喻意义构建过程中意识的不同认识(Gibbs 2011a;2011b;2015a;2015b;Gibbs&Chen 2017;Steen 2011b;2015;2017;2018)。DMT认为在交际维度上隐喻的映射过程是有意识的,而Gibbs则坚持语言、认知、交际在人类活动中是一体的,隐喻意义的映射过程是无意识但却复杂的,所以会认为没有必要区分DM与NDM,三维隐喻的分析模型没有理论意义。
3.1 Gibbs的质疑
Gibbs(2011a:49)认为DMT没有考虑蓄意思维的本质,完全忽略了人类的意识研究(Gibbs&Chen 2017:122-123)。语言、认知、交际是不可分割的,隐喻的意义建构过程虽然是自动的、无意识的,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复杂的概念过程和知识理解。
人类的意识和行为上的确存在相关性。认为某些隐喻可能是“蓄意的”,可能是我们察觉到有一些隐喻表达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与那些被自动地、毫不费力地产出与理解的隐喻表达有所不同(Gibbs 2011a:39-40)。不管人们是不是对他们所做的与隐喻自身相关有具体的觉知,在某些时刻人们确实会更加有意识地思考他们的隐喻语言(Gibbs 2011b:69)。比如,当莎士比亚从罗密欧的角度来形容朱丽叶时,他偏偏选择了“太阳”这一特别的表达而不是“月亮”“星星”等表达,这说明诗人有意思考了这一表达并希望引起读者的注意,从而从“太阳”这一视角来看待朱丽叶。从这个角度看,认为人们在某些时刻使用和理解隐喻的方式是所谓蓄意的,似乎是合理的。
DMT区分了有意识地产出的隐喻和不是有意识地产出的隐喻,其假设是:NDM是自动出现的、而DM是在交际维度上的跨域映射。在这种情况下,DM的产出不需要像规约隐喻这样的NDM所需要的那种自动过程。但是,“行为中自主性只是意味着行为可以不必经过蓄意的思维而快速完成,而不意味着概念过程和知识在理解过程中不起作用,包括各种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Gibbs 2011a:39-40)。也就是说,行为自主性与复杂认知过程并不相悖。行为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加工过程中不涉及高度结构化的、具身性的概念知识。“人红是非多”这一规约隐喻中,“红”的意义加工虽然是自动的,但这一过程中也包含了各种概念结构知识,比如“红”与人联系起来的各种意义映射路径。
Gibbs认为DMT认为所有的隐喻都是自动的,甚至可能不是隐喻,完全是错误的。虽然有一些表达似乎是被快速且自动理解的,无论隐喻是通过分类还是比较的过程,各种隐喻解读都需要复杂的推理过程(ibid.:44)。蓄意隐喻的假设与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在概念的、具身的隐喻映射的研究证据相悖(Gibbs 2015a:79),并且DMT并不能经受实证检验(Gibbs 2015b)。尽管DMT对意识有所提及,但是并没有说明有意识的体验的不同维度,隐喻意识的觉知层次会不会可能产生不同的隐喻意义的体验?这些问题DMT都没有给出回答,而这正是由于其在语言、认知、交际之间以及蓄意和非蓄意之间进行人为的区分而造成的(Gibbs&Chen 2017:123)。
3.2 Steen的澄清
Gibbs对DMT的质疑与批评促进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对于Gibbs的批评与质疑,Steen(2011b;2013;2015;2017;2018)也进一步回应并澄清了DMT的一些关键概念。
首先,所有语言加工的一个事实是所有的有意识加工是从无意识加工中显现的,并且会对它进行反馈(Steen 2011b:55)。隐喻的有意识加工和无意识加工的过程并不相互冲突。蓄意隐喻通过比较的方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这并不意味着无意识过程不在蓄意隐喻中发挥作用,无意识过程在其中也发挥作用(ibid.)。在DM、NDM和意识的关系上,DMT认为,NDM不涉及有意识的隐喻加工,并且也可能不涉及无意识的跨域映射。另外,DM不必是有意识的,但是会导致有意识的加工,并且这一加工过程是基于跨域映射的(ibid.)。DM之所以提供有意识的隐喻思维,是因为源域和目标域的概念是分别激活的,并出现在工作记忆视窗中。他们是隐喻地关联的,来自一个表达中的不同域和共同发生的概念和所指(Steen 2013:187)。
隐喻是无意识的,但是DM的理论观点也是可能的。DM关注当人们蓄意使用隐喻时,在隐喻接收和产出中借助跨域比较的加工的重要作用,与非蓄意使用的隐喻相对(Steen 2011b:55)。这种类型的加工本身包含着许多无意识过程,并且十分复杂,与非蓄意的语言使用涉及的认知过程不同。Gibbs认为DM与规约隐喻是对立的,或者DM的涵义能够概念化而不考虑语言的神经认知和意识,实际上是对DMT的误解(ibid.:56),而Gibbs(2015b)的实验也是建立在对DMT的错误认识上,因此是不可靠的(Steen 2015:71)。也就是说,NDM常常是规约隐喻,规约隐喻却不一定是NDM(Steen 2017:14)。“人红是非多”这一规约隐喻并非一定就是非蓄意隐喻,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能是被蓄意使用的隐喻。
总之,DMT反对CMT的一些主张,但并不是对CMT的全盘否定———相反,它是对CMT的补充,提出了新的关于无意识和有意识隐喻加工与表达结构和功能、意向性、注意力的关系等问题(Steen 2018:108)。目前,对DMT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看具身认知中和社交互动中的隐喻是如何与CMT关联的。既然CMT是隐喻的主流理论,DMT需要将CMT产生的证据联系起来并且看它可以如何进行解释(ibid.:98),这一点可能是DMT未来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地方。
4.蓄意隐喻理论与话语分析
DMT作为对CMT的补充与发展,为话语中隐喻的分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能够解决CMT在隐喻的话语分析中所忽略的“交际”维度造成的问题,而且DMT在话语内部结构分析与话语事件类型分析上也有独到的优势。本节主要介绍DMT在话语分析中的作用及实践应用。
4.1 话语中概念隐喻与蓄意隐喻的分析比较
DMT与CMT在对话语中的隐喻进行分析时有不同的结果,更能凸显话语接受者注意力的转换。Reijnierse et al.(2020:16-17)借用了下面的例子来说明用DMT与CMT进行话语中隐喻分析的不同:
[8]Snacks and slow food for intellectual hunger(Steketee 2012)
[9]Develop a hunger for knowledge(Redmond 2016)
CMT视角下,例[8]和例[9]都被分析为同一个概念隐喻,即DESIRE IS HUNGER。然而,当以隐喻的第三个维度,即“交际”维度,对“hunger”进行分析时,这两个例子会产生不同的分析结果。例[8]是报道第四届TEDx阿姆斯特丹会议的一份报纸文章的标题。[8]中,“hunger”一般用来描述对食物的渴求,此处被用来描述一些对抽象事物“知识”的渴求。并且,[8]中包含了两个名词来表示“获得知识”这一目标域与“食物”相关的源域之间的对比。满足对知识渴求的TED演讲,不同寻常地被描述为“snacks”和“slow food”。这些食物相关的表达呈现出表达的目标域的新奇视角。这样一来,“hunger”这一食物相关的源域的意义也被突出,并且这一隐喻在交际的维度上被凸显为隐喻。[8]中的“hunger”结果就成了潜在的蓄意隐喻。同样地,[9]中“hunger”也是以对食物的渴求来描述对知识的渴求。但是,与[8]中不同的是,[9]中没有凸显“对食物的渴求”这一源域的提示。因此也可以说[9]是NDM。
DM本质上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关注人们动态的话语交际中的注意力问题。在一个话语事件中,表达被产出、接收、交换(Steen 2017:4)。对话语中的DM进行分析,关注话语接收者的注意力的转换,有助于发现在话语的接收与理解方面,人们是怎样将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结合起来达到推理和理解的。
4.2 蓄意隐喻在话语结构与类型分析中的作用
在话语结构的内部分析上,从DMT的视角进行分析也是有益的。DM有各种各样的派生形式,出现在不同的语言形式和概念结构中。其语言形式涵盖单一的语词、词组、句子、语篇甚至整个文本,DM可能以格言、谚语、新见解、玩笑或者其他明显的修辞手法的形式来激发局部洞见(Steen 2013:183)。DM也可能会围绕诸如童话、寓言、预言以及神话这些规约文本形式中所表达的隐喻模型,在段落之间或者言语转换之间延展隐喻比较来达到解释或者引导的目的(ibid.)。因此,在通过语言特征对话语的结构和层次进行考察时,DMT提供了一种连贯、明确、可操作的分析方法。
此外,DM的功能取决于交际功能如何界定。DM可能在标示特定话语事件的特定风格(如:谈论的方式)或者语域(如:使用的语言)、内容(如:话题)、类型(如:叙述或论辩)、目标(如:说服、信息或引导)、领域(如:文学或宗教)以及话语的其他方面起作用(ibid.)。特别是在话语事件类型的分析上,DMT对不同类型的话语事件分析有着天然的适切性。DMT的目标之一是从话语的角度强调语言使用中隐喻的不同变体,其主要假设之一是:语言使用中隐喻的各种性质(语言、概念、交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话语事件包含的关注点所驱动和限制的(Steen 2017:6)。所以说,一些类型事件要比其他类型事件更倾向于使用蓄意隐喻,比如文本设计、心理咨询、诗歌写作与阅读等等(ibid.)。
当研究语言使用和话语中隐喻的互动时,研究者必须考察的不仅有隐喻的符号结构和功能及个人的隐喻心理过程和结果,还有互动的语言使用者中隐喻的社会过程和结果(Rasuli c'2017:146)。DMT实际上是跨学科的隐喻研究框架,能够为所有的隐喻研究者提供统一的框架,以免他们被迫同时考虑所有的现象、视角和方法(ibid.)。
4.3 蓄意隐喻理论的实践应用
有关DMT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隐喻语料库的建设,二是话语分析。
在语料库建设方面,DM的研究历经了其在不同语域的个例研究(Cameron 2003:100-119;Nacey 2013:25-30;Ng&Koller 2013;Perrez&Reuchamps2014)到DM的识别程序研究(Reijnierseetal.2018)。Reijnierse et al.(ibid.)研发了蓄意隐喻识别程序(Deliberate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DMIP)。Reijnierse et al.(2019)将DMIP应用到VU阿姆斯特丹隐喻语料库(VU Amsterdam Metaphor Corpus),对DM与NDM在学术文本、新闻文本、小说、对话等不同语域中的分布进行研究,发现NDM的语域分布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学术文本、新闻、小说,而DM的使用语境分布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小说、新闻,几乎不在学术文本与对话中出现;并且隐喻在不同的词汇层级(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及其他)也呈现了不同的分布:大多数DM是由名词和形容词表达,而NDM在词汇的各个层级均有分布。这一现象正是与语域的整体的交际性质与这些语域中词汇层级的不同作用有关。
将DMT运用至话语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即考察DM在文本中所构建的隐喻框架是否会对读者的推理产生影响(Beger 2011;2016;Thibodeau&Boroditsky 2013;Krennmayr et al.2014;Steenetal.2014;Reijnierseetal.2015)。例如,Krennmayr et al.(2014)研究了人们何种情况下会依靠隐喻框架建立新闻语篇中的文本表征,结果发现当新闻语篇中包含新奇隐喻时,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会更可能建立新闻预判的文本表征;Thibodeau&Boroditsky(2013)研究了不同隐喻框架下的犯罪文本是否会影响读者选择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策倾向,研究结果验证了隐喻的框束效应,发现隐喻框架确实会影响人们的推理,但是该研究并未对隐喻框架文本和非隐喻框架文本进行对比分析,也没有对受试在实验前的政治倾向进行调查,研究结果仍有待探讨;Steen et al.(2014)基于Thibodeau&Boroditsky(2013)的研究,对上述实验变量进行控制后,发现并不存在隐喻框束效应,至于隐喻框架到底会不会影响读者的推理则需要更多实验研究。由此可见,DMT作为当下的新理论,其实验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仍然有待发展。Musolff(2016)从跨文化视角对DM的解读进行了相关研究。来自十个不同国家且具有ESL或EFL背景的人被要求使用隐喻性俗语“body politic(政体)”对“国家是身体”与“国家是人”两个基本隐喻进行解读,结果显示,隐喻理解偏好具有系统性差异,隐喻性的解读表达会被用作辩论的论据,还有一些与主流文化传统有关。这表明,当关注到语言表达的隐喻性时,说话人可能会在多个隐喻解读版本间有意地选择一种,以此来达到某种交际目的。该研究发现隐喻解读存在蓄意性,不仅为DMT提供了证据,也为DM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5.结语
交际中大部分隐喻的语义处理很可能是通过范畴化的加工模式进行,但也有一些隐喻是通过跨域映射进行加工理解。将交际维度引入隐喻的分析模式后,可以在语用层面对隐喻进行分类:蓄意隐喻通过跨域映射的模式进行加工;非蓄意隐喻通过范畴化的模式进行加工。增加语用的维度后,把隐喻研究从原有的二维拓展到三维,是概念隐喻理论的延伸,而非完全忽视或与之抗衡。DMT与CMT同样关注心智模型构建与维系的不同层面以及隐喻表达在话语处理过程中的具体角色。DMT实质上是对当下隐喻研究问题的细化与深入,有助于隐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