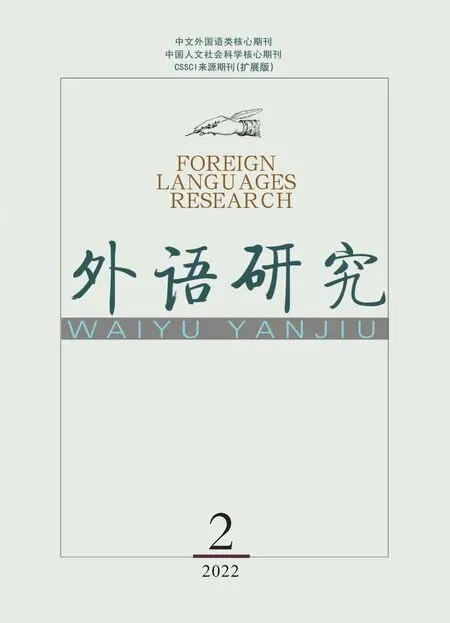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艾约瑟《辨学启蒙》换例译法研究*
——兼与严复《名学浅说》对比
梅晓娟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0.引言
自19世纪80年代起,西方逻辑学的汉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到20世纪初已经发展成一股译介热潮(熊月之2008:131)。1886年,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翻译的《辨学启蒙》,列为其译编的《西学启蒙》丛书第十三种。这是晚清首部完整译介的西方逻辑学著作,在逻辑学东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少逻辑学名家,如严复、王国维、林祖同等都曾读过此书。王国维还沿用艾约瑟对logic的译名,将自己的译著定名为《辨学》(同上:127)。《辨学启蒙》的底本为英国逻辑学家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编写的Logic,是英国知名出版社MacMillan&Co.1876年推出的Science Primers中的一种①,分27章199节论述演绎逻辑、归纳逻辑和逻辑谬误,是西方逻辑学界相当流行的优秀教科书。鉴于原著的启蒙性质和逻辑学本身的工具性,Jevons阐述逻辑学概念和理论时会辅之以大量细致的例证分析。学界关于《辨学启蒙》的研究较少,熊月之曾提及其中的例证翻译方法,指出艾约瑟将原著部分西方例证替换成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内容,但未做详细论述(同上)。本文拟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译者角色化视角,分析艾约瑟的西学传播者角色对《辨学启蒙》换例译法的影响,并通过与严复同底本译著《名学浅说》换例译法的对比,透视译者的身份和角色是如何决定译者行为的。
1.译者的身份、角色和角色化
周领顺(2008:80)首次区分了“求真”和“求效果”两类翻译方法,2010年起发表译者行为研究系列论文,逐步构建起独树一帜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两部代表性专著(2014a;2014b)出版后在译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多位知名学者对其作出高度评价(刘云虹2015;韩子满2019;王克非2019)。许钧教授称其“有足够的学科意识”(2014:112),研究处于“国际前沿”(同上),其著作是“近年翻译批评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2018:223)。由于该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相关研究论著逐年增加,目前已达近200篇(部)。多家学术刊物开设研究专栏,2019年和2021年还召开了两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
译者行为批评是“以人为本”的研究,它突破文本批评视域只关注翻译内因素的局限,将翻译内外结合起来,以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三要素评价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更加客观、公正、科学。“身份”“角色”和“角色化”是该理论的一组核心概念。其中,“身份”是译者以“译者身份”呈现的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行为特征,是显性的、稳定的。同时,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角色”主要表现为译者的社会性表演特征,是隐性、临时的(周领顺2014a:215)。为了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作为翻译活动执行者的译者会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行为角色,译文也因此留下译者个人意志性的痕迹,这种社会性选择过程即为“角色化”。译者角色化是译者从不变的译者身份向可变的社会角色的转化,角色化程度的高低决定译文“译”的状态。译者作为社会人,在翻译社会化过程中呈现多种角色特征,从而直接导致译者行为和译文的多样性(周领顺2014b:269)。在周领顺提出的“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中,角色化程度低的译者指向左端(作者/原文),更加偏向语言性求真,即翻译基本层意义上译文与原文的对应性,译文中“翻译”的成分较多;角色化程度高的译者指向右端(读者/社会),更加偏重社会性务实,即翻译高级层意义上译文所能实现的社会效果,译文中“非译”的创造性成分较多(周领顺2014a:85)。不管译者的角色化程度如何,求真和务实都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理性的译者总是努力在作者/原文和读者/社会之间、在文本求真度和效果务实度之间维持理想中的平衡,以求实现译者行为的合理度(同上:160)。
2.艾约瑟的西学传播者角色
《辨学启蒙》的译者艾约瑟1844年毕业于伦敦大学,1848年受英国伦敦会派遣来中国传教,之后在华生活57年直至去世。他长期在墨海书馆从事西学译介活动,曾翻译《格致新学提纲》及其续篇(与王韬合译,1853/1858)、《光论》(与张福禧合译,1853)、《重学》(与李善兰合译,1859)、《圆锥曲线说》(与李善兰合译,1859)、《植物学》卷八(与李善兰合译,1859)等多部具有开拓意义的科技著作,还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等合编包含大量科学内容的年鉴《中西通书》(1852-1860)。同时,他还是《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万国公报》等晚清著名西学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汪晓勤2001:75-78)。
艾约瑟虽身为传教士,但他在传教方面的成就却远不及对西学传播的贡献。他在诸多学科领域孜孜以求、笔耕不辍,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传教士。他着力求原文之真,译作并不像许多其他传教士的译著那样夹杂着浓重的神学色彩,这一点从《植物学》卷八与前七卷的对比中看得尤为明显。《植物学》卷一至卷七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与李善兰合译,译文中多处出现“乃造物主之妙用”(林德利1859:1)、“上帝随意赐体,各殊其形”(同上:129)等对上帝的赞美之辞;卷八则为纯学术性论述,通篇找不到此类话语。1880年,艾约瑟还辞去伦敦会职务,应聘到总税务司署专门从事翻译和文化传播事务,历时五载将“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哲分斯1886:译者自序)译成中文,加上他本人“博考简收”(同上)撰写的《西学略述》,编成《西学启蒙》丛书十六种。与其他十五种一样,《辨学启蒙》旨在传播西方相关学科知识,从自序到译文均不包含直接宣扬基督教义的内容。
王扬宗曾对比丛书第六种《格致总学启蒙》、其原本Introductory Science Primers以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的译本《格致小引》,发现《格致总学启蒙》对原本的求真度要高得多。《格致小引》尽管译文简洁流畅,却因删略过多导致内容残缺不全;《格致总学启蒙》虽有文辞略嫌艰涩之弊,但内容与原本大体一致,篇幅几乎是《格致小引》的4倍。对于《格致小引》中略去的较难用中文表达的抽象概念,艾约瑟不仅勉力翻译,有时还会增加相关说明以保证译文的可接受性(王扬宗2000:210-218)。这种注重学术传播、不掺杂译者个人价值判断和意识观念的翻译风格贯穿于整套丛书中,其他多部译著也是比较严格地依照原本翻译的,章节内容完全对应或仅有局部调整,增删改动之处极少(付雷2008:2-3;赵少峰2012:30;陈德正2013:1;叶璐,田锋2016:77;赖某深2017:2)。
3.《辨学启蒙》的换例译法
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翻译应将“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在信于原作的基础上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采取适当的变通手段,以便原作能更有效地通过译作服务于读者(周领顺2008:79-80)。艾约瑟注重还原文本的核心信息,具体到原著中的例证,若不涉及西方文化背景和英语语言知识,翻译时则依照原文。对于那些可能会造成理解障碍的例证,他尽量保留原例的基本面貌,再辅之以译语读者相对熟悉的补充说明,如阐述笔的分类时增加狼毫、羊毫等中国书写工具(哲分斯1886:48),在植物分类部分提及传统的五谷之名(同上:55),解释霓虹现象时添加明末启蒙思想家方以智《物理小识》中的类似论述(同上:202)。此外,他还将原例的具体细节作适合汉语读者的调整,如采用中国计量单位:“伦敦城中韦斯珉德大堂,长非五十丈有五尺乎”(同上:150),或古代帝王年号和官职名称:“英国尚书贝根氏,名法兰西者,生于嘉靖时,卒于天启时”(同上:157),或传统职业划分:“第国中人民,不能如彼之将善良强暴均匀调和也。……于贫富贵贱、士农工商中均见者”(同上:264)。
原著部分例证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若采用直译加说明的方式未免显得译文冗长累赘、芜杂生涩,同时也会偏离作者的论述重心。为了不影响关键信息的有效传递,艾约瑟换用了与中文语境相一致的新例。Jevons讲解“单独概念”(singular term)时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大英博物馆、埃及亚历山大城城徽庞贝柱为例:
Sometimes a term points out only a single person orthing,as“TheQueenof England”,“The British Museum”,“Pompey’s Pillar”.By the Queen of England we mean thepresentreigning Queen Victoria,and thereis,of course,only one Queen Victoria.There is one British Museum,and onesinglegreatobelisk called Pompey’s Pillar.Hence termsof this kind are called singular terms,because each termisthe name only of asingle thing.(Jevons1890:15)
上述三例在英语国家属于基本常识,再缀以作者的简短解释,足以阐明singular term的单一属性。但在西学尚未普及的晚清社会,这些知识对于缺乏相关背景信息的中国读者显然还相当陌生。艾约瑟不仅致力于西方科学文化的译介,对中国文化也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他在中国政治、历史、宗教等领域发表了多篇(部)颇有分量的学术论著,是19世纪后期一位举足轻重的汉学家(陈喆2013:122-123)。考虑到目标读者的西学接受能力,他没有沿用原例,而是主动适应本土文化语境,代之以“唐明皇”“景教碑”“泰山”三个与中国社会现实相一致的专有名词,以说明singular term的含义和基本特征:
有时语句中之一界语,专指一人,或专指一物,如云唐明皇、景教碑、泰山。唐明皇为单指一人,即唐玄宗;景教碑即指在西安府之一碑,非指他碑;泰山即指山东泰安府之一名山。若此之语,因独指者止一物,可名之为“专语”。(哲分斯1886:21)
Jevons谈及分类问题时以书为例,先按学科分类,继而指出不同类别之间可能会重合,即容易犯“子项相容”(李芳凡,张蓉2013:45)的逻辑缪误。具体而言,同一本书可能会被归入不同学科门类,如科学史书籍既可以归入历史类,又可以归入科学类,有些书既属于传记类,又属于历史类:
Books might be divided into those which treat of History,Geography,Biography,General Literature,the Physical and Moral Sciences,the Arts,Political Economy,Theology,Poetry,Fiction,Periodical Publications.But in making such classifications,we are almost sure to fall into logical blunders.In the first place the species or small classes are likely to overlap each other,unless we make the divisions with much care....In dividing books,again,itwill befound impossibletomakeanyclassification in which a book shall always belong to one species and only to one.The species will be sure to overlap.There may be book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which might be equally well placed in the class of histories,or in that of books on physical science.There may be books which are half biography,half history.(Jevons 1890:31-32)
艾约瑟翻译《辨学启蒙》的19世纪80年代,“学有专科”的西方近代学术分科观念和学科门类名称虽然已经通过西学书籍和西学课程等途径传入中国,但尚未被知识界广泛接受,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以“六艺”为核心、“四部”为框架的分类方法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袁曦临,刘宇,叶继元2009:242-243)。有鉴于此,他首先按照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法划分出“经、史、子、集”四大类,再进一步列举当时国人较为熟悉的“格致、地理、诗与小说”四小类,同时省略其他尚无固定译名的学科门类,并将用于说明“子项相容”的history of science等学科门类替换成更为具体直观的中文典籍名称:
书之中分为经、史、子、集,复分为格致、地理、诗与小说各等小品类。第如是辨分,即辨学观之,未免有走入差误途路处耳。由大类分为小类,首难者,每因此物类,与彼物类,如不谨慎析分,恐有互相侵占地步处也。……更言及书类,既繁且多,分辨不易。归是类中者,据理而论,难防其不归于分列之他类。譬犹《史记》中之天官书,理宜列于天文类。自司马迁创首,而与原不属史书之食货,并礼乐、地理等,同载于史书内矣。佛教之书中,有唐玄奘之《西域记》,要亦应归入行人见闻纪录书内。(哲分斯1886:57-59)
原著第六章论及词汇的正确使用,自然包括不少涉及英语语言知识的例证。Jevons谈到歧义现象时指出,尽管一词多义有时会引起误解甚至逻辑谬论,但是某些义项之间并无太多关联的多义词在特定语境下也能产生双关、幽默等特殊语言效果,如rake(“耙子”或“浪子”)、sole(“鳎鱼”或“脚底”)、bore(“无趣的人”“枪的内径”或“涌入江河的海潮”)、diet(“饮食”或“议会”)、ball(“球”或“舞会”)等:
In many casesthemeaningsof aword areso distinct thattheycannot really lead usintomorethanamomentary misapprehension,or give rise to a pun.A rake may be either a garden implement,or a fast young man;a sole may be a fish,or the sole of the foot;a bore is either a tedious person,a hole in a cannon,or the sudden high wave which runs up some rivers when the tide begins to rise;diet is the name of what we eat daily,or of the Parliament which formerly met in Germany and Poland;ball isa round object,or adance...Fromsuch confusions of words puns and humorous mistakes may arise,but hardly any important errors.(Jevons 1890:24-25)
艾约瑟精通多国语言,在汉语语言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出版7部汉语语言学著作,并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等晚清著名汉学期刊发表多篇有关汉语语言学的论文,涉及语音、词汇、语法等不同方面(何群雄2010:125)。鉴于Jevons所举例证并无对应的汉语多义字/词,艾约瑟换用了四个能产生幽默效果的同音词/短语(“李八百”“行礼已毕”“最大”“河上”)和一个双关的多义短语(“京都外七十二连营”)。他同时指出,语言歧义导致的误解大多可以避免,几个中文例证引发的语义不确定现象实是“喜道戏言者”为追求特殊语言效果而刻意为之:
聆人言对谈之际,将其语言之意,分辨清楚,十之八九,即不惧有误会意处矣,以其声音入耳而心即通也。惟喜道戏言者,每用一字二三意之字,或以自然音同字异之言,令人听闻。如云“李八百”,原古昔仙人姓名也,误会意者谓言“李果八百枚”;“行礼已毕”,原言所行之礼已完也,误会意者谓言“出门之行李也齐毕”矣;止言“最大”,误听者以为“罪大”;止云“河上”,误听者以为“和尚”。更有双关之语,如“京都外七十二连营”,原属邻村七十二,俱以营名也,误听者以为“七十二营兵,连环驻于京外”矣。(哲分斯1886:42-43)
除了少量因词源不同等原因导致的义项几无关联的多义词以外,大多数英文多义词的义项之间都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其中在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的意义为词汇本义,其他在本义基础上推演而成的新意义为引申义。Jevons用bench和board说明词汇意义的发展变化以及引申义与本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In mostcasesaword changesitsmeaningby degrees,and we use it for anything which is close to,or connected with,the first meaning.A bench means a board to sit on,but“the bench”is a common expression for the row of magistratesittingon the bench.A board meansabroad flat piece of wood,but being often used to support the dishes at a meal,people speak of the food itself as the board.(Jevons 1890:25)
bench的本义为“长凳”,the bench可以表示“法官”,二者之间的联系是长凳为法官在法庭的坐具;board的本义为“木板”,就餐时也可作摆放菜肴之用,于是便有了引申义“伙食、膳食”。由于汉语不存在与这两个单词本义和引申义均对应的多义字/词,艾约瑟分别用“案”和“席”代替:
人于平时恒道之言,由渐变更正用之字意。余等用字时,每藉与正用意紧贴附之第一旁意用。如案字,本意原属几案也,缘于公堂陈设,继乃变而为词讼案件。宋之包拯、国朝施仕纶,俗间相传,谓其能决断奇怪巨案,实乃无稽之谈也。世并有犯案、定案、完案、到案,去本意远之若等语矣。珍馐殽馔陈于桌面,每谓席设何处,或云为喜筵,俱古昔肆筵设席之意,至今时虽未见铺陈有席,仍藉用也。其他由渐变移之事,可类而推之。(哲分斯1886:43-44)
不难看出,“案”和“席”并非艾约瑟从数量繁多的汉语多义字中随意拿来,而是深思熟虑后慎重遴选的结果。“案”与bench的本义均与法官、法庭相关,引申义也有共通之处;“席”与board的本义均有陈列食品之功能,引申义更是几乎完全一致。从bench到“案”,从board到“席”,两个汉字例证清楚地表明原著阐述的西方逻辑学概念和理论对汉语具有同等的适用性。艾约瑟虽然换用了中文例证,但并未偏离原例的核心信息,而是努力使新例在适应中文语境的同时尽可能与原例保持文本意义和语言形式上的相似度。
4.趋于求真与偏向务实——与严复《名学浅说》的换例译法对比
1908年秋,严复应知名女政治活动家吕碧城之请为其讲授逻辑学。他以Primer of Logic为原本,“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耶方斯1981:译者自序),翌年以《名学浅说》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严复最后一部西学译著,连同他此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等七部著作,并称严译八大名著,在近代中国产生空前的影响,读者遍布社会各阶层。尽管严复以“信、达、雅”三字标准著称,他还是在这些译著中屡屡采用增补、删减、改写、添加按语等方法“取便发挥”(王栻1986:1321),旨在唤起民众觉醒、拯救国家危亡。他曾谈及自己翻译《名学浅说》时对原文的取舍原则:“中间义指,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耶方斯1981:译者自序),即通过换例表达个人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以达到“补偏救弊”(王栻1986:25)的目的。正缘于此,他将Jevons用于解释歧义现象的church换成“国”字,指出“国”在不同语境下的多重含义,或指土地疆域,或指人民种族,或指风俗政教,进而引出对时事的针砭:“至于今日党派滋多,虽人人皆言爱国,而其意中所爱之国各异。是以言论纷淆,虽终日谈辨,实无相合之处也”(耶方斯1981:15-16)。其他如用“气”代替house、“五行”代替books则是借西学反观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不精确、逻辑不缜密等流弊(张德让2011:77)。
甲午海战之后,严复经过深刻反思,意识到中国惨败的关键原因不是缺少声光化电和坚船利炮,而在于政治体制和思想意识层面的落后。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5篇政论文,批判中国社会文化弊端,倡导向西方寻求富强的真理,之后又以翻译、著述、演讲等多种方式宣传维新变法。昔日的海军军官逐渐转变为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王栻1986:27)的启蒙思想家,翻译成了严复“借他山之力,唤醒国魂”(同上:1558)、实现救亡图存目标的一把利器。他虽然也通过翻译客观上宣传了西学,但其最终目标是借西学疏通、诠释中学,进而推动中国传统学术和社会的现代转型。他关注的重心始终是中学而非西学本身,换用中国例证更多地是通过西学反观中学,以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改造。因此,他才会在序言中声明:“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耶方斯1981:译者自序)。
侯昂妤和文学锋曾论及严复、王国维翻译西学著作的不同目的和特点,指出前者社会功利性较强,将西学视作开启民智、强国保种的工具,后者则更加关注西学理论本身的细节和学术价值(侯昂妤,文学锋2006:178)。从这一点看,艾约瑟对待西学翻译的态度与王国维相当一致,即注重译本的学术传播功能而非其对民众的教化启迪作用。他努力保全原著例证的形式和意义,全面求真无力时首先考虑的是在原例基础上添加解释说明,其次才是换用与中文语境相一致的新例。翻译有关church的例证时,他沿用了原文对基督教各教派的论述,并提及中国本土盛行的儒释道三教以作补充(哲分斯1886:39-40)。他采用了house的汉语对应词“房”,将那些以house为中心但无法直接译成“-房”的复合结构,如ice-house、green-house、hot-house、bathing-house、counting-house等,替换成“厨房”“正房”“厢房”“营房”“刑房”等汉语偏正复合词(同上:45)。Books一例在《辨学启蒙》中依然是关于“书”,只是原例中的西方学科门类名称被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法和古代典籍名称所取代(同上:55-57)。
与艾约瑟相比,严复不仅更为频繁地采用换例译法,他使用的中国例证也更加偏向务实。原著第95节以Manchester为例讲解假言三段论(hypothetical syllogism):“If Manchester contains a cathedral,it is a city.Manchester does contain a cathedral;therefore,it is a city.This is an affirmative hypothetical syllogism,and it hastwopremisesand aconclusion,likean ordinary syllogism.”(Jevons 1890:69)
译者的身份和角色决定译文走向(周领顺2014a:218)。尽管艾约瑟和严复均采用了换例译法,两人的目的和旨趣却大相径庭。艾约瑟以中国城市济南府代替英国城市Manchester,新例和原例一样,仅起辅助说明作用,论述方式、行文结构也与原例基本一致:“譬云如其城中有巡抚衙门,必为省城。是首出语有如若字矣,次出语即可谓济南府有巡抚衙门,断定语可谓为因知济南府为省城。是即冠首用如若字之正面三语句也,有首出语、次出语、断定语,与平素之完全三语句无异”(哲分斯1886:136-137)。西学传播者的社会角色决定了艾约瑟翻译时以求真为本,即便是为了减少文化隔阂采取换例等务实之举,他还是尽力在新例中保留原例的核心信息。
严复显然不满足于像艾约瑟那样就事论事,而是借换例关注社会现实,表达他对立宪与国家存亡之关系的见解:“如有人云:假使立宪,中国可以不亡;今立宪矣,故中国可以不亡。此首乃有待之词,中用两原一委,与常式连珠正同。”(耶方斯1981:57)在其后的第96-98节他又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以达到托译言志的目的。严复早年留学英国,对立宪政体颇为了解,认为这是英国强盛的根本原因。1895年3月,他在《原强》一文中提倡学习西方宪政制度,“建民主,开议院”(王栻1986:13)。之后,又通过《群己权界论》《法意》等译著的凡例和按语多次批判君主专制统治,论证实行立宪政体的必要性。1905年立宪运动开始后,他发表《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等长文,并赴上海青年会和安徽高等学堂宣讲立宪思想。这些译著、论文和演讲既揭示了民族危机,又提出了救国之策,即渐进式社会改良而非暴力革命,在全国上下产生强烈反响,严复也因此成为立宪运动的思想领袖之一。在《名学浅说》中,他将原著侧重于解释说明的例证替换成政治色彩浓厚的立宪主题,以此重申“立宪救国”的社会政治理想,呼应了清政府此前刚刚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②。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换例是为了实现“译以致用”的效果。新例重在表达个人对社会问题的意见和态度,具有明显的务实倾向,对原例的求真度自然有所降低。
5.结语
德国功能学派代表人物赖斯(Katharina Reiss)将文本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侧重提供信息和陈述观点的信息型(informative)、用于表达情感和态度的表情型(expressive)和旨在感染读者并呼吁其采取行动的操作型(operative)(2004:26)。艾约瑟注重其语言人身份,翻译时着力“求原文之真”(周领顺2014a:218),同时以换例等务实手段“兼顾译文之用”(同上),再现了原著的信息功能,《辨学启蒙》因此“足以窥见辨学之门径”(徐维则,顾燮光2003:259)。严复刻意凸显其社会性角色,翻译时“求译文之用,兼顾原文之真”(周领顺2014a:218),藉换例为译本增添原著不具备的表情功能和操作功能,其中蕴含的经世之心、警世之言、救世之道已经超出单纯的知识传播范畴。晚清社会处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艾约瑟以西学传播为旨归、趋于求真的换例自然不如严复重在思想启蒙、偏向务实的换例更容易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共鸣,但他为适应本土语境勉力在源语译语之间徘徊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踯躅前行的努力不应被翻译史所遗忘。
注释:
①本文所引原文依据的是美国American Book Company 1890年的版本。
②《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于1908年8月27日,《名学浅说》翻译于1908年9月11日—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