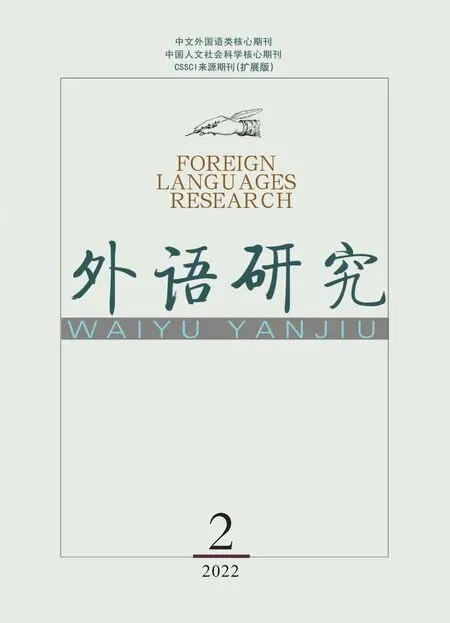《棋王》走向英语世界的历程*
——隐性进程的损伤与“寻根”的变异
高佳艳
(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北京 100091)
0.引言
寻根文学集中产生于中西方文化思想激烈碰撞的20世纪80年代,体现了中国文学家在现代化全球化大潮中急欲确立“中国叙事”身份的集体举动,代表着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早期努力。“寻根”作家群体共同表现出“与‘世界文学’对话”,重塑世界文学中中国文学地位的迫切诉求(洪子诚2010:352)。而这一诉求也的确引起一些反响,汉学家杜迈可(Michael S.Duke)(1991)甚至认为以1984年阿城《棋王》的发表为起点的80年代后半期代表着当代中国小说的重大转折期,当代中国小说从那时起开始“走向世界”“接近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那么以“走向世界”为初衷的“寻根”主题在这一历程中到底是以怎样的面目呈现给英语读者?本文将着重考虑专业文学读者的视阈,从文本出发,以《棋王》为个案对此展开探讨。除了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小说翻译中“寻根”主题意义的传递进行深度文本分析,本文还试图综合考虑国内外文学批评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海外文学批评可能对译语专业读者产生的影响,深入剖析“寻根”主题在《棋王》走向英语世界过程中的遭遇。
1984年12 月,“杭州会议”召开,随后“寻根”文学思潮兴起,《棋王》逐渐成为“寻根”小说的代表作。这一过程正如陈晓明(2007)所言:“《棋王》等小说与‘寻根文学’是相互阐释的。《棋王》意义依赖‘寻根’的历史语境;‘寻根’的意义也通过《棋王》之类的作品得以建构”。《棋王》最早发表于1984年《上海文学》第7期,在国内文坛引发热烈反响后,紧接着便开始走向英语世界。1985年夏,《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刊登了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的译作,题为“The Chess Master”。与此同时,汉学家陆续在英语世界的期刊上发表评论,构成了《棋王》走向英语世界的主要推动力。《棋王》,有着翻译和文学批评的共同推动,翻译使原作双重叙事进程遭到改变,译作主题意义的解读因此受到限制,而文学批评强化了这一限制,于是呈现给英语读者的“寻根”虽有其名,但其丰富内涵实际上变得浅显而单一。
1.“寻根”背景下《棋王》的主题内涵
回顾国内现有文学评论,《棋王》之“寻根”体现在大的方面是重塑中国文化制约下的民族文学身份;体现在个体方面,则是中西文明碰撞中遭遇精神困惑的个体通过探索生活和人性重塑文学自身的生命力。前者是评论界主流倡导的文化复归主题,后者便是被少数批评家和作者再三强调的世俗主题。
传统文化复归主题体现了“寻根”第一个方面,即通过确立民族文学的身份与世界对话,这类阐释更多涉及的是小说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小说被视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而世俗主题则体现了“寻根”的另一方面,即主体对于自我和存在的探索和审视,这方面更多涉及小说的叙事艺术。世俗主题极为重要,它恰恰是一些批评家指出《棋王》“寻根”及现代性的主要依据(李庆西1987;Lonergan 1989;黄伟林2007;李钧2019),并且更多地契合了作者阿城的“寻根”初衷。
1.1 “寻根”之一:传统文化复归——“棋”
《棋王》最初发表时,首先引发评论界注意的便是王一生及其下棋的事件(许子东1984;王蒙1984;曾镇南1984)。虽然王蒙、曾镇南等人当时并未指明王一生所体现的“中华棋道”就是作者寻找的民族文化之根,但回顾历史,王蒙等人对王一生形象的关注和有关“中华棋道”的解读无疑奠定了小说被纳入“寻根”文学的基调。
主流意见认为《棋王》之所以“寻根”,主要当归因于作品内容中蕴含的道家文化以及小说叙事所蕴含的古典审美情趣。比如苏丁和仲呈祥(1985a;1985b)认为王一生棋道、精神气质、人生态度和美学追求都符合道家美学特征,指出“只有在大胆地消化西方文化的同时又不忘吸取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我们的文学才能带着中国民族的特有血脉,健壮地走向世界”。二人的文章基本上奠定了《棋王》作为“寻根”文学代表作的地位。此后,更多评论家将王一生和象棋看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或代表道家,或代表儒家,或禅宗,或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基本心理素质和观念方式(辛晓征1985;郭银星1985;王灿1986;朱伟1991),他们着重挖掘小说在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的意义,在迅速将《棋王》纳入“寻根”文学阵营的同时也进一步确立了“寻根”文学的身份和内涵。
1.2 “寻根”之二:世俗人生探索——“吃”和“我”
对世俗人生的探索是阿城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主题,这一主题传递出作者对生活和个体存在的思考。小说发表之初,有评论家指出了小说对王一生所代表的平凡人生命价值的关注(王蒙1984;季红真1985;朱伟1991)。刘建华(1987)提到小说对王一生这种平民知识分子“非英雄化”的书写符合世界文学潮流,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思想标志。李庆西(1988;2009)一再指出“寻根”的意义是回到人的基本生存面,回到日常的经验世界,指出《棋王》的民间视野并非道家所说的隐遁精神的推崇,而是体现在对本来就在世俗世界里的平凡自在人生的关注和欣赏。阿城表示“寻根”与世俗生活密不可分,认为“‘寻根文学’意外地撞开了一扇门,就是世俗之门”(阿城1998)。针对小说的世俗主题,他写道:“普通人、小人物……常有一种英雄行为……当然更多的是他们日复一日毫无光彩的劳作。地球于是修理得较为整齐,历史也就默默地产生了”(阿城1984b)。但可惜的是,小说的这一世俗主题在当时并未得到更深入更广泛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世俗主题同时还融合着“寻根”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主体的自我实现。小说中“我”的成长实质上就是“我”对世俗人生的认知领悟过程。季红真(1985)明确指出“我”的重要性:“他(阿城)以‘我’的存在为起点,深入自我以外的现象世界,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人生故事或片段的叙述,又返回到一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自我之中。他笔下的全部故事,都在‘我’一次一次的认知感悟过程中,完成着感情与思想的升华。这种圆周式的叙述结构,是我们理解他作品全部意旨的内在枢机,而在‘我’内外交通的丰富性格中,则既体现着一种人生态度,也反映着作者的审美态度。”
识别这一世俗主题,需要读者在理解小说内容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小说的叙事结构,区别叙述者的叙述功能和人物功能,把握小说的双重叙事进程。遗憾的是,国内主流评论对此缺乏深入挖掘,翻译并没有完整再现这一叙事结构,而英语世界的文学评论也并未弥补这一遗憾。由于过分强调小说中王一生和象棋所代表的道家文化,《棋王》“寻根”所蕴含的世俗主题在作品走向英语世界的过程中被遮蔽了。
2.《棋王》初译:双重叙事进程的损伤
詹纳尔译本发表于1985年夏,是小说走向英语读者的最初译本,也代表了海外汉学家对小说的最初阐释。细读该译本,可以发现译本凸显了传统文化复归主题,淡化了世俗主题。从深层叙事结构来看,原作的隐性叙事进程受到损伤,导致王一生形象凸显,而人物“我”背景化。
2.1 原作的双重叙事进程
“叙事进程”(narrative progression)强调,叙事是由人物和事件向前推进的、邀请读者参与并作出反应的动态进程(Phelan 1996:90)。申丹(2013)发现在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的背后还存在隐性叙事进程(covert progression),在主题意义上与情节发展形成一种补充性或颠覆性的关系,旨在表达与情节相对照甚或相对立的主题意义,塑造相异的人物形象,体现不同的审美价值。她指出在文学翻译研究中有必要关注隐性进程的挖掘和翻译,对含有隐性进程的作品,“需要将针对情节建立的翻译标准和规范改为针对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双重叙事运动的标准和规范”(申丹2015)。《棋王》的世俗主题正是在隐性进程中得以体现。
从表面看,小说讲的是主人公王一生从“棋呆子”成为“棋王”的故事,但在表面情节背后,隐藏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兼人物的“我”对世俗人生的体认和对英雄叙事的摒弃。可以说,小说叙事进程沿着A和B一明一暗两条线推进。A线是随着下棋和“棋王”王一生的成长推动的表层故事情节,是传统文化复归主题的重要依据。王一生从“棋呆子”变身“棋王”,“我”和脚卵等知青与王一生参与并见证了这一成长。B线是“我”通过对世俗人生的体认获得成长的隐性进程,是解读小说世俗主题的关键。“我”从理想主义革命青年到最终领悟世俗人生的生命真谛,王一生推动了这一成长。
原文中,作为人物的“我”在故事开始和结束时明显存在认知上的差距,这也是体验自我与叙述者自我的差距。故事开始时,人物“我”对普通人以及以普通人为代表的世俗生活的价值缺乏认知,典型表现是一味抬高精神追求,贬低物质追求,崇拜刘邦、项羽一类的英雄人物,忽视小人物;故事结束时,“我”有了顿悟,对精神和物质以及英雄和小人物的价值实现了认识上的平衡统一,此时体验自我在认知层面才与叙述自我接近。正是二者之间差距的缩小,才形成阿城所说的王一生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我”的世界。“我”在这个故事中不是一个简单的见证人,而是随着故事发展不断发生心理变化,不断成长的一个主要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讲,与其说王一生从“棋呆子”到“棋王”的转变是王一生的成长,不如说是“我”的成长,因为这一称呼的改变,直接反映的是“我”对生命认知的变化。
事实上,作者阿城认为B线才是更为确定的主线。他曾表示,《棋王》里其实是两个世界,王一生的一个客观世界和“我”的一个主观世界,小说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的参照,小说结尾的时候“我”开悟了,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王一生不知是否开悟,但是实际上两个世界都完成了(李欧梵等1986)。正是这一明一暗的双重叙事进程,赋予了小说的叙事张力,赋予“寻根”复杂丰富的主题内涵。
从叙事学角度看,认识到隐性进程的关键是挖掘表层情节背后对情节发展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我”的叙述话语细节,区分叙述者“我”的叙述功能和人物功能,认识体验自我和叙述自我认知距离的缩短到实质上就是“我”的成长,即“我”对生命的认识逐渐圆满,故事结束时人物“我”才与叙述者“我”在认知水平上接近。
2.2 翻译对原作双重叙事进程的损伤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再叙述,这一再叙述会使文学作品与读者的叙事交流进程发生改变(高佳艳2018),《棋王》初译对原作双重叙事进程造成了损伤,主要表现为译文中情节进程A线的凸显和隐性进程B线的模糊。译作很大程度成了A线单线叙事,“寻根”世俗主题被淡化。
2.2.1 翻译对A线的凸显
原作隐含作者对王一生及象棋的渲染是构成A线的主要依据。译作对A线的凸显主要表现在对道家文化元素的凸显,一个突出例证就是译文改变了隐含作者对于冠军老者的贬抑态度,反而将之塑造成传统道家文化的代表。
在原作中,作者对老者的态度不乏讽刺。阿城(1998)曾表示:“那个老者满嘴道禅,有点世俗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是虚捧年轻人,其实就是为了遮自己的面子”。隐含作者通过叙述者对周围人物的态度的描述,制造出“我”们和老者之间的距离,侧面反映出老者的负面形象。但是译文中人物之间的这一距离消失,使读者很难看出老者的负面形象。比如:
例[1]:
原文:有一个人挤了进来,说:“哪个要下棋?就是你吗?我们大爷这次是冠军,听说你不服气,叫我来请你。”王一生慢慢地说:“不必。你大爷要是肯下,我和你们三人同下。”(阿城1984a:32)
译文:Someone pushed through and asked,“Which of you wants to play chess?You?Our uncle won this championship.He’s heard that you aren’t happy about the result and he sent me to invite you over.”“That won’t be necessary,”said Wang Yisheng.“If your uncle would like to play I’ll take all three of you on at once.”(Ah Cheng 1985:124)
在原文中,为老者传话跑腿的人用“大爷”和“哪个”分别来称呼和老者和王一生,两个称谓形成对比,传达出仆人对主仆关系的认可和对其他人平民身份的不屑,隐含作者由此给读者刻画出仆人的奴颜,以及主人凌驾于王一生们平民阶层的身份地位。而王一生对“大爷”这一称谓的重复则体现出刻意和不悦。但译文中“uncle”一词传递的是辈分关系,丢失了“大爷”有关人物关系和身份地位的文化涵义,隐含作者和读者的这层交流也就难以传达出来。
例[2]:
原文:专有几个人骑车为在家的冠军传送着棋步,大家就不太客气,笑话起来。(阿城1984a:33)
译文:There were several messengers carrying the moves to and from the champion’s home by bicycle.We were no longer on our best behavior,and had started joking and talking.(Ah Cheng 1985:127)
这一句直指人们对老者的不满态度,属于侧面刻画老者形象的叙述话语。原文由三个分句组成,一个“就”字暗含了后两个分句和前一个分句之间的因果联系。从整体语境看来,老者坐在家里差人跑腿是摆身份和傲慢无礼,与王一生赤手空拳一人战九人的气魄形成鲜明对比,这难免会让“我”们心生不满。因此“不客气”是不友善(our patience/respect being consumed),“笑话”并非没有目的地讲笑话,而是“笑话起(他)来”(to tell his jokes),意为嘲弄戏谑老者。而译文将三个分句拆分为两部分,使得后两个分句成了单纯的场景描述——观棋的人们不再矜持,开始聊天讲笑话。原作中众人对老者的不客气态度不见了,因此译文丢掉了对老者负面形象勾勒的关键一笔,无法传达隐含作者对老者所代表的正统权威之虚伪矫情的讽刺态度。
由于这一人物的隐士身份,以及话语中诸多道禅名词,再加上译作对隐含作者态度这一改写,这位冠军老人很容易被读者解读为A线叙事中道家文化的象征,于是A线变得更为丰满。随后的文学评论也证明了这点——这一人物与捡破烂的老者一同被视为道家文化的正面代表(杜迈可1985;Duke 1987;Ling-tun 2005)。
2.2.2 翻译对B线的遮蔽
A线被强化的同时,B线被遮蔽。原作中,“我”对“吃”和小人物的态度转变是B线的重要构成。“吃”代表世俗人生不可或缺的物质需求,原作故事开始即呈现了“我”和王一生针对“吃”的冲突,“我”将“生命”看作是远远高于“吃”的话题,对“吃”表现出明显不屑。而王一生认为“吃”就是最基本的物质追求,“吃饱就是福”。对“吃”不屑的“我”与结尾认识到俗人乐趣的“我”形成认知差距,是B线形成的关键。但是在翻译中,“我”对“吃”的不屑态度被淡化,导致这一距离被淡化,B线被遮蔽。比如下面这处罕见的心理独白,是对人物“我”对“吃”的态度直接呈现:
例[3]:
原文:讲老实话,我不太愿意复述这些事情,尤其是细节。我觉得这些事情总在腐蚀我,它们与我以前对生活的认识不太合辙,总好象在嘲笑我的理想。(阿城1984a:18)
译文:To be frank,Idid not want to go over all that again,particularly the details.I felt that the experience had corrupted me.It had been too sharp a contrast with what I had known before,and always seemed to mock my ideals.”(Ah Cheng 1985:91)
这句话是关于生命的讨论的一部分,直接呈现了出自体验自我视角的理想主义价值观,与王一生对“吃”的执着构成冲突。原文语境是王一生向“我”追问挨饿体验的细节,“这些事情”代指与“吃”相关的事情,“我”则认为这些事情在“腐蚀”我,甚至是对理想的嘲笑。“腐蚀”一词直接呈现了“我”作为一个理想主义革命青年的价值观,即认为有理想的青年不应当在乎生活中类似吃饭这样的小事情,也不应当在乎物质生活。但在译文中,读者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译者对“吃”和“生活”的话题进行了模糊化处理,首先将“这些事情”被总结泛化为“the experience”,即“文革”中这段经历,其次,“生活”这个核心词被省略了。于是传递的信息成了:我觉得这段经历毁了我,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好像经常在嘲笑我的理想。于是原文与小说结尾叙述者“我”存在认知差距的理想主义革命青年形象便被呈现为一个对文革历史颇具反思批判意识的青年,体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之间的差距被遮蔽。
原文中作为人物的“我”的理想主义与后文中体现的英雄崇拜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小说结尾,“我”有一个重要的顿悟时刻。随着对王一生认识的加深,在车轮大战结束时,“我”终于放弃了英雄崇拜的价值观,悟到平凡人生的价值。这个顿悟时刻是构成小说世俗主题的重要内容,但在译文中却没有得到有力再现。
例[4]:
原文: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在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阿城1984a:33)
译文:Xiang Yu and Liu Bang,those legendary generals of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ago I so much admired,were glaring at each other in stupefied fury.But the dark-faced soldiers whose corpses littered the plain were rising from the ground and slowly moving,not making a sound.(Ah Cheng 1985:126)
对比来看,原文凸显出“我”此时价值观发生颠覆性改变,而译文仅呈现了两组人物对于王一生夺冠的不同反应。原文中,“我”放弃以前崇拜的民族英雄,开始欣赏小人物的价值,这恰恰体现了作者反复强调的世俗主题。项羽、刘邦与黑脸士兵分别代表着英雄和小人物,“目瞪口呆”和“慢慢移动”形成一静一动的对比,暗示着英雄崇拜在“我”眼中失去了生命力,而黑脸士兵这样的小人物开始显示出生命活力。而在译文中,“目瞪口呆(dumb-struck)”被译为“in stupefied fury”,即愤怒、惊讶、无语,原文的静态强调此时转为具有爆发力的愤怒情绪。而“哑了喉咙,慢慢移动”原文的语义重心在“慢慢移动”上,翻译后重心落在了后置伴随状语“not making a sound(不发出一点声音)”上面,强调的是静态。如此一来,原文的“静——动”对比在译文中变成“动——静”对比,“英雄失去生命力——小人物获得生命力”这一对比自然也无法突显。此外,我敬佩的英雄“目瞪口呆”被译为“fury(愤怒)”,具有误导效果,读者会想:愤怒从而来?答案只能指向前面王一生夺冠的事件。这也就是说,英雄们都被王一生的精湛棋艺惊呆,无法接受王一生获胜的结局,译文于是暗示了英雄和小人物的冲突,从侧面烘托了王一生的英雄光芒,进一步导致译文中体验自我和叙述自我认知距离淡化,B线被遮蔽。
除了模糊化,译作中还有些细节对B线叙事造成直接破坏。比如:
例[5]:
原文:画家把双臂抱在胸前,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脸,看着天说:“理想没有了,只剩下目的。倪斌,不能怪你。你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求。我这两年,也常常犯糊涂,生活太具体了。幸亏我还会画画儿。何以解忧?唯有——唉。”(阿城1984a:32)
译文:The painter folded his arms,rubbed his cheek with one hand,looked up at the sky and said,“Ideals have all gone:all that’s left is ambition.I don’t blame you,Ni Bin.Your demandsare nothing very much.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I’ve often done stupid things.My life is too much tied up with trivialities.Luckily I can still paint.What is there to ease melancholy,save...”He sighed.(Ah Cheng 1985:123)
倪斌将父亲传给他的棋送给书记换取自己的进城机会和王一生的比赛资格,认为“棋不能当饭吃,用它通一些关节,还是值的。”画家对此表示理解,理由是“生活太具体”。“理想”作为小说中的关键词,这里指包括了过程和目的的纯粹理想,“目的”其实专指最终目标,即“practical ends”,“生活太具体”其实是对特殊年代纯粹理想无法实现表示无奈,即现实和理想有悬殊,需要采用一些不太理想的手段解决特殊问题,才能达成理想目标,“具体”或可译为“astray from an ideal path”,而非“tied up with trivialities”(被琐碎所束缚)。译文将矛头指向生活的琐碎——世俗生活的特点,于是本来是感慨生活的困难,变成了对世俗生活的谴责。由于小说中的画家和隐含作者属同一立场,译文此处相当于间接表示隐含作者对世俗生活报以否定的态度,这无疑对B线叙事造成破坏。
而译作的结尾更是格外凸显了王一生的形象,强化了这一损伤:
例[6]:
原文: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阿城1984a:35)
译文:I smiled and thought that only by being one of the common people would one enjoy such pleasures.My family had been destroyed,I had lost my privileged status and was now having to do manual work every day,but here there was a remarkable man who I was very lucky indeed to know.(Ah Cheng 1985:131)
对比来看,原作是故事发展到最后叙述者对自我和“真人生”的领悟,强调自我认知和对世俗人生真谛的领悟,可是译文却变成了:虽然生活很苦,但幸运的是“我”能够结识王一生这个奇人,显然是翻译时断句有误,即将“真人生/在里面”断句为“真人/生在里面”。这一结尾作为小说主题阐释至关重要的一笔,无疑将英语读者的注意力进一步引向王一生这个人物以及两个人之间的友情。
从以上分析来看,翻译对局部词句处理不当,导致原作叙事机制发生改变,而背后原因多半是由于译者对原作的隐性叙事进程缺乏应有的关注(如例[3]、例[4]、例[5]、例[6]),或者是由于译者汉语语言能力有所欠缺而导致出现误译(如例[1]、例[2]、例[6])。这里姑且不论背后原因,单从翻译结果来看,《棋王》初译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改变了原文的双重叙事进程,这会直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欣赏,将读者引向王一生及象棋相关的传统文化复归主题,而忽略更能引发读者普遍共鸣的世俗主题,那么在此意义上理解到的“寻根”,便只有寻找传统文化这一简单面向了。再结合当时英语世界的相关文学评论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一损失进一步被强化。
3.《棋王》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批评
译作是小说走向英语世界时呈现给英语读者最直接的阅读材料,而文学评论则是辅助性的阅读材料,尤其是面对专业读者时,文学评论对于读者理解作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棋王》在英语世界的评论主要为汉学家所书写,作者包括了杜迈可、雷金庆(Kam Louie)、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危令敦(Nagi Ling-tun)等人,发表在各大英语类期刊上,或者作为译本序以译作副文本的形式对作品进行批评阐释。综合看来,汉学家的批评阐释共同聚焦传统文化复归主题和小说的颠覆意义。
首先,汉学家大都聚焦于王一生和象棋及其象征意义,将小说置于“寻根”背景下对其传统文化复归主题进行阐释。比如杜迈可(1985)认为“阿城藉一个传奇棋手的故事,写出人的生存意义、尊严和传统文化的续传价值”,强调小说中的“棋道”象征着传统中国珍贵的精神遗产,“小说最重要的主题是人的精神需求,这一主题是贯穿整个故事结构的线索,通过分析众多反复对比和主人公王一生思想上的复杂变化这条线索得以充分展现”,而王一生身上体现的孝顺、正直等美德同“棋道”一样都代表着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传承(Duke 1987)。雷金庆以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abstract inheritance method)”为基础,同样将关注重心放在了王一生和象棋以及二者代表的文化传统上。他同样认为象棋,尤其是“棋道”,代表着一种更为抽象和普遍的传统样式,一种抽象的“中国性(Chineseness)”,一种无形的“民族精神(nationalessence)”(Louie 1987)。胡志德认为王一生和象棋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他指出王一生在吃和棋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是中国中庸文化的体现。象棋可以变化无限,给人提供精神慰藉而不假于外物,通向一种超验的、永恒的境界,通过这种抽象阿城有意无意地将象棋和“民族精神”联系起来(Huters 1988)。杜博妮指出小说并非关于下棋,而是有关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哲学基础虽然不甚明确,但小说暗示出作者对道家思想的偏向(McDougall 1990;2011)。危令敦指出小说不仅仅是关于象棋,而是关于生活之道。象棋代表着逃避现实和精神追求,下象棋是一种“充满形而上色彩的心灵逍遥游”,通过王一生的刻画,小说突出了精神生活远远高于物质生活的重要性(Ling-tun 2005)。
其次,对作品的阐释和推崇主要凸显了小说的颠覆意义。小说主要被阐释为两大主题: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的继承;二是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杜迈可指出包括《棋王》在内的寻根作品通过对乡下生活和传统价值观以及精神生活的描绘,与之前的革命小说形成鲜明对比(Duke 1991)。胡志德认为象棋代表着一种理想的逃避之所(Huters 1988)。杜博妮的译本序言花了一半篇幅来介绍作者阿城及其家庭背景和经历,通过强化社会现实和小说的相似性,强化了作者和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联系,借此强化小说的批判主题(McDougall 1990,2011)。
从“寻根”的译名来看,汉学家将“寻根”简单定义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或民族精神,忽视“寻根”之“寻”的意义及其回到生活和文学本身的初衷,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解读。“寻根”被译为“the‘roots’school”(Huters 1988),“primitivism/search for roots”(McDougall 1990),“nativist(return toroots)fiction”(Duke 1991),“‘Search for Roots’movement”(Ling-tun 2005),译名突出了根和本土的意象,而这“root(s)”被简单阐释为中国传统文化或民族精神,比如胡志德将之简单概括为“整理民族传统寻找传统永恒价值观(to sort through the national tradition in search of its enduring values)”(Huters 1988)。杜迈可(Duke 1987)和雷金庆(Louie 1987)没有采用“寻根”这一命名,但却分别在传承“中华之道”和抽象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阐释,并无本质差异。危令敦(Ling-tun 2005)虽然指出了中华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却也没有脱离传承文化传统的思路,指出阿城是在民间寻找“中华棋道的奥秘”和“不平凡”,同样遮蔽了作者反对英雄叙事还原平凡世俗人生的初衷。“寻根”思潮虽然为相关作品“走向世界”造成浩大声势,成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注意,但同时这一命名及翻译也对具体作品的解读形成限制、误导。
在文献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内主流文学评论对英语世界评论产生影响的痕迹。首先,海外批评延续国内主流文学评论的阐释方向,而忽略了关注世俗主题但影响力较弱的那一派,并且很难在主流评论的基础上开创新的阐释路径。从参考文献和评论内容来看,海外评论家大量参考了国内评论(Duke 1987;Huters 1988;Louie 1987;Ling-tun 2005),尤其是苏丁、仲呈祥、曾镇南、郭银星、王蒙等人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上海文学》以及在《九十年代》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如前文所述,这些文章强调了小说的文化复归主题,而对这些文章主要观点的引用构成了海外批评的基调。只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对文化复归主题的阐释,汉学家凸显了其中的政治颠覆意义。
4.结论
在《棋王》走向英语世界的过程中,翻译使原作的双重叙事进程遭到损伤,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相关世俗主题被淡化遮蔽,作品叙事机制简单化,“寻根”复杂丰富的内涵单一化。而海外文学评论同样一致强调了王一生及其棋道,并以此为基础凸显了“寻根”的传统文化复归主题以及这一主题的颠覆意义。通过大量文献参考的痕迹我们可以看到国内主流文学评论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海外评论风向。在翻译和文学批评的共同阐释下,呈现给英语读者的《棋王》成为一篇通过呼唤传统文化复归实现突破的批判作品,这很可能会导致作品及“寻根”在专业文学读者眼里被误解和低估。
众所周知,作品阅读与接受必然受到接受语环境的制约,但如果译作面对的是文化背景相对复杂、态度也因此更为开放包容、对文学性更为讲究的专业文学读者,比如来自世界各地的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者,那么不妨单从文本出发来看作品的阅读与接受。此时译作文本构成作品阅读审美的基础,而文学批评文本则可作为译作的辅助阅读材料,对作品的阅读和接受发挥引导作用。在本个案里,翻译呈现给读者异于原作叙事艺术机制的译作文本,成为读者对译作作为独立叙事艺术审美客体进行评价的先决基础,而源语文学批评尤其是主流文学评论可能会对译语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继而共同影响专业读者解读作品的方向。
本个案或可带给我们有关当代文学“走出去”的一点不一样的启示。首先,翻译可能改变文学作品整体的叙事结构,如果考虑到专业文学读者的眼光,为了减少作品文学性的损失,尤其注意要从整体上挖掘作品的叙事艺术,除了关注小说情节发展,还要关注情节背后隐藏的叙事进程和文字细节,以此观照局部的理解和翻译,做到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叙事艺术机制,以便专业读者对当代文学作品做出较为客观的欣赏和评价。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学评论是专业读者进行译作阅读时的重要辅助材料,国内外文学评论的深度会影响作品解读的深度,继而影响译作的接受传播,而国内文学批评对海外文学批评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为了对译作的进一步传播保驾护航,除了保证本土文学批评的深度和多样性,或许可以在输出翻译作品本身的同时,输出以不同视角解读原作的文学评论,尽可能给潜在的专业读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