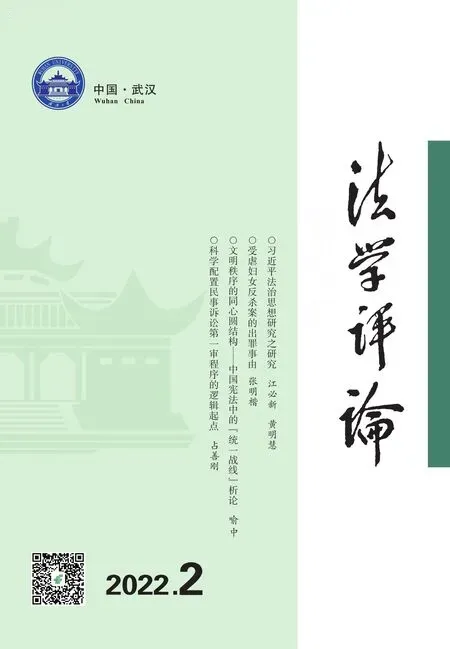商标恶意抢注法律适用研究*
宁立志 叶紫薇*
引言
我国现行商标注册制度中的在先申请原则、自愿申请原则、分类申请原则和地域性原则作为制度源头,催生了抢注未注册商标、跨类抢注已注册商标、抢注域外商标、商标囤积等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给商标注册管理、市场竞争秩序、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持续负面影响。2021年3月1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行动方案》,旨在进一步加大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打击力度,以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助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同时也侧面印证我国商标恶意抢注治理依然面临着屡禁不止的严峻形势。如今一旦新产生了知名度或影响力较高的人物或事件,就会有大批投机者闻风而来,争先恐后地将相关标志申请注册商标。譬如,新冠疫情爆发后就出现了申请注册“钟南山”“雷神山”“火神山”等疫情相关标志的行为,东京奥运会期间也出现了申请注册“全红婵”“苏炳添”等奥运健儿姓名的行为,引发了大量社会关注,具有强烈的负面社会影响。尽管这些商标注册申请已经被驳回,但足以说明我国特定群体甚至部分社会公众的商标注册意识尚存缺陷,未充分认识到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危害性和违法性,抑或是即便认识到其危害性和违法性也依然选择铤而走险,不惧恶意抢注行为可能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导致商标恶意抢注行为难以杜绝。面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屡禁不止这一现实难题,必须加强相关法律规制,明确相关法律适用,维持良好的商标注册秩序,以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商标恶意抢注的类型化分析
作为知识产权体系中的重要保护客体之一,商标不仅是一种商业标志,更是一种无形财产,与经营者良好开展市场经营活动息息相关,宛若经营者的生命线,不可分割。某种程度上,对于经营者而言,其商标被抢注所引致的危机甚至比商标假冒侵权更严重。(4)See Michele Ferrante, Strategies to Avoid Risks Related to Trademark Squatting in China, The Trademark Reporter, Vol.107, No.3, 2017, p.727.所谓商标抢注即指抢先在特定商品或服务类别上申请注册商标以取得该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而商标恶意抢注则是指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侵害他人在先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的商标申请注册行为。换言之,商标注册制度背景下,商标抢注为中性概念,并非当然违法,(5)参见李扬:《我国商标抢注法律界限之重新划定》,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3期;曹新明:《商标抢注之正当性研究——以“樊记”商标抢注为例》,载《法治研究》2011年第9期。所谓商标恶意抢注应当是指明知或应知他人在先权益的存在,但依然不避让地将与相关标志相同或近似的标志申请注册商标,或不以使用为目的大量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
(一)针对特定或不特定主体的商标恶意抢注
依据商标抢注对象的主体是否特定,可以将商标恶意抢注划分为针对特定主体的和针对不特定主体的商标恶意抢注,前者属于可能侵害他人在先权益的行为,后者则属于可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1.针对特定主体的商标恶意抢注
(1)对他人在先商标权益的抢注
在先商标权益既包括注册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也包括未注册商标所有人对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享有的合法权益。
首先,依据被抢注商标是否注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抢注注册商标、抢注未注册商标以及抢注期满未续的商标。其中注册商标权人享有排他性的商标专用权,有权禁止他人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服务上注册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可直接对抗恶意抢注,而未注册商标所有人仅享有先用权,只有同时满足“在先使用”和“有一定影响”的条件,才可对抗“以不正当手段”实施的商标恶意抢注。“在先使用”却并未达到“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则无法对抗恶意抢注行为,商标法甚至还对该种抢注行为持鼓励态度。(6)参见刘铁光:《规制商标“抢注”与“囤积”的制度检讨与改造》,载《法学》2016年第8期。期满未续的商标实质上等同于未注册商标,但稍有不同的是,期满未续的注册商标注销一年后,(7)《商标法》第50条规定:注册商标被撤销、被宣告无效或者期满不再续展的,自撤销、宣告无效或者注销之日起一年内,商标局对与该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核准。其所有人才会与尚未注册的商标所有人面临同样的商标抢注风险。
其次,依据抢注商标与被抢注商标所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类别的关系,还可以划分为同类抢注、跨类抢注以及同类兼跨类抢注。混淆可能性是商标侵权的试金石。(8)Danielle C. Jones, Remedying Trademark Infringement: The Role of Bad Faith in Awarding an Accounting of Defendant's Profits, Santa Clara Law Review, Vol.42, No.3, 2002, p.872.商标所适用的商品或服务越类似,造成相关公众混淆的可能性就越高,抢注行为人具有主观恶意的可能性也就相对越高。因此,相较而言,同类抢注的恶意最为明显,跨类抢注的恶意认定则较为复杂,需结合其他具体情形综合判断。而在同类兼跨类抢注情形中,同一主体一并实施了同类抢注和跨类抢注行为,可将存在同类抢注行为作为认定跨类抢注是否具有恶意的参考因素。
最后,依据被抢注商标的知名度高低,还可以划分为驰名商标抢注和普通商标抢注。被抢注商标知名度越高,抢注行为人在申请注册前接触到该商标的可能性越高,具有主观恶意的可能性也越高,商标法对其保护的范围和强度也就相对更大。由于驰名商标知名度极高,商标法较为慷慨地给予了已注册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使其可以有效对抗跨类商标恶意抢注。对未注册驰名商标,商标法则仅给予其同类保护,即未注册驰名商标只能拥有与普通注册商标同等级的对抗恶意抢注行为的力量。而普通商标无论注册与否都无法获得跨类保护以对抗跨类抢注行为。
(2)对他人其他在先权益的抢注
其他在先权益主要是指商标抢注申请日前他人享有的,除商标权益以外的民事权益,包括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以及商品化权等民事权益。
自然人享有姓名权、肖像权,法人、非法人组织则享有名称权。现实中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公众人物姓名极易成为商标抢注的对象。恶意抢注的姓名、肖像商标不仅会误导公众,使相关公众误认为该商标所附着的商品或服务来源与该自然人有特定联系,还可能导致该自然人声誉受损或产生其他不良社会影响。(9)例如,体育明星迈克尔·乔丹的姓名曾被乔丹体育公司在中国申请注册为商标,最终法院判决认定乔丹体育注册的“乔丹”商标损害了迈克尔·乔丹的在先姓名权。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27号行政判决书。姓名商标不仅限于自然人的正式姓名,还有笔名、艺名、译名等其他指代本人的特定符号,司法解释中也已经明确规定,商标与自然人之间存在指代关系并容易导致混淆的即可认为损害了该自然人的姓名权。(1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同样地,抢注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名称也并非仅限于组织名称的全称,若其简称具有一定知名度并且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有稳定对应关系,则对简称的恶意抢注也应被视为是侵犯名称权的行为。另外,企业名称中的字号是企业名称中最具有识别性的核心部分,但由于企业名称的保护范围一般仅限于登记机关管辖的地域范围和所属行业,(11)《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6条规定:企业只准使用一个名称,在登记主管机关辖区内不得与已登记注册的同行业企业名称相同或者近似。只有当企业字号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且申请注册与之相同或近似商标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时,未经许可将他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申请注册商标才可能构成对他人在先权益的侵害。(1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另外,知名虚拟角色形象虽然不具有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但其上却仍可能具有应当保护的商品化权益(merchandising right/ right of publicity),(13)参见郑成思:《商品化权刍议》,载《中华商标》1996年第2期。其持有者拥有对相关形象进行商业性使用的权利,也拥有禁止他人对相关形象进行商业性使用的权利。(14)商品化权,是指对知名真实人物形象或虚构角色形象进行商品化利用并享有利益的一种私权,其起源于人格权,但有别于人格权。参见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载《法学》2004年第10期。广义的商品化权的保护对象还包括了其他知名的标记、符号、作品片断和作品名称等。(15)参见刘春霖:《商品化权论》,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因此,擅自将与知名虚构角色形象相关标志相同或相似的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如虚构角色的名称、声音、特定造型等,属于侵犯他人商品化权的商标抢注行为。例如,“邦德”商标纠纷案中的“007”“JAMESBOND”就属于具有商品化权益的电影人物名称。(16)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行终字第374号行政判决书。
著作权客体是具有独创性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作品。未经许可将与他人在先创作的独创性作品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行为属于损害他人著作权的侵权行为。而对于仅将作品名称或作品中的角色名称申请注册商标的,则属于前述可能侵犯他人商品化权益的情形,需要进一步考察作品名称和角色名称的知名度以及是否容易导致混淆,才能判断该商标抢注行为是否损害了他人在先权益。(1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专利权客体则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其中,发明和实用新型是具有创造性的技术方案,不具有申请注册商标的可能,而外观设计是对工业产品外观上的形状、颜色、图案的设计,其构成要素与商标具有一致性,具有成为商标的可能性。因此,未经许可,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类别上,将与他人在先享有的外观设计相同或近似的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将会侵害其独占实施权,即损害他人在先外观设计专利权。同时,需要注意著作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期限的有限性,法定保护期限届满后,作品和外观设计将进入公有领域,权利人原则上也就无权禁止他人将其申请注册为商标。
除了前述在先权益,商标抢注还可能损害其他的他人合法权利和利益,包括但不限于有一定影响的商品特有名称、商品包装或装潢、域名、网站名称、网页等,其上虽然尚未形成类型化的民事权利,但仍然具有法律所应保护的合法利益,将其申请注册为商标亦有造成相关公众混淆的可能,同样会损害他人在先权益。例如,在著名的加多宝和王老吉红罐纠纷案中,(1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三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广药集团和加多宝公司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特定款式的凉茶红罐包装、装潢的权益归属问题。
2.针对不特定主体的商标恶意抢注
针对不特定主体的商标恶意抢注主要指大量注册公共符号资源的商标囤积行为。
囤,即为储存;积,即为积累。通常而言,商标囤积是指缺乏真实使用意图的大量申请注册行为。(19)参见孙明娟:《恶意注册的概念、类型化及应用》,载《中华商标》2018年第3期;孔祥俊:《论非使用性恶意商标注册的法律规制——事实与价值的二元构造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2期。而所谓“大量”一般是指其注册数量超出使用需求,(20)参见周丽婷:《商标恶意注册的司法规制实践》,载《中华商标》2017年第7期。商标囤积行为人自身完全不具有真实使用商标的意图或具有真实使用部分商标之目的,但其所注册的商标数量过大,明显超出经营需求,因此对超出需求部分的商标不具有真实使用意图。与针对特定主体的商标恶意抢注不同,大量抢注公共符号资源的商标囤积行为侵害的对象并非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标或他人在先权利相关标志,也不具有攀附他人、搭便车的目的,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并不会对他人在先权益造成直接损害。但商标囤积行为人并不具有真实使用商标的目的,注册大量商标的真实目的是待价而沽,通过商标转让、许可使用和提起侵权诉讼来实现不劳而获。这种商标囤积行为将商标视为商品,虽不会损害特定主体利益,但会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挤占符号资源、浪费行政司法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显然不符合商标法的立法目的和诚实信用原则,具有不正当性和违法性。
(二)注后使用或不使用的商标恶意抢注
依据抢注后是否使用,可将商标抢注行为划分为注后使用和注后不使用两种情形。
1.注后使用的商标恶意抢注
注后使用又可划分为自行使用和他人使用。自行使用者的目的通常在于搭便车,即意图通过抢注商标所蕴含的商誉吸引消费者注意力,不劳而获地享受他人劳动经营成果或攀附他人良好声誉。而对于他人使用的情形,则应当进一步考察被许可人或受让人与商标抢注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关联。若被许可人或受让人与抢注行为人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其他利益关联,则应视为抢注行为人仍然具有自行使用的意图。反之则表明抢注行为人本身并无实际使用的意图,其目的可能是通过收取许可费用和转让费用直接获取利益,尤其是当许可、转让费用为不合理的高价时,其具有主观恶意之可能性可谓极大。同时,即便许可、转让费用并非不合理的高价,也往往远高于商标抢注成本,即相关的商标注册申请费用,抢注行为人同样可以凭此获利。例如,2004年,我国的新科康佳商标就遭到了俄罗斯莫奥斯泊罗夫公司抢注,对方抢注后要求以4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商标,属于典型的意图通过收取高价转让费用牟利之商标恶意抢注情形。(21)参见《新科康佳商标在俄遭抢注,商标局出三点建议》,http://www.cnhubei.com/200503/ca790647.htm, 2021年9月5日最后访问。
2.注后不使用的商标恶意抢注
注后不使用的商标恶意抢注则包括诉讼,转让、许可以及无异动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注后仅有提起诉讼行为的商标恶意抢注,与专利蟑螂(patent trolls)类似。所谓专利蟑螂是指通过购买受让或收购企业等手段聚集专利,但不将专利用于产品生产或提供服务,不具有实施专利的意图,通过诉讼或诉讼威胁以达成和解等途径,获得侵权赔偿或专利许可费用的行为。(22)高戚昕峤:《专利蟑螂:法理危机与遏制之道》,载《河北法学》2016年第10期。此种抢注情形中,抢注行为人同样没有实际使用商标,也无使用意图,就像住在桥下的向过桥人索取费用的怪物,(23)See Michael S. Mireles, Trademark Trolls: A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pman Law Review, Vol. 18, No.3, 2015, p.819.通过对他人提起诉讼或以诉讼相威胁,以期获得高价转让费或许可使用费。
第二种情形是指注后没有实际使用注册商标,仅有单纯的转让、许可、公布商标注册信息和声明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等行为的商标恶意抢注。(2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注后使用中的他人使用情形中也存在转让、许可行为,但那种情形中,受让人或被许可人实际使用了抢注商标,而在注后不使用情形中,受让人或被许可人并未实际使用抢注商标。但无论如何,受让人或被许可人是否实际使用抢注商标,商标抢注行为人本身都不具有真实的使用意图,并且有通过转让和许可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可能。
第三种情形则是注后无异动的商标恶意抢注。无异动不代表无恶意,且一时无异动不代表永远无异动。首先,抢注行为人可能具有垄断符号资源之目的。优质的商标符号是有限的,通过大量注册商标,抢注行为人可以提前占据大量公共符号资源并待价而沽,由于商标注册申请成本并不高昂,只要在未来能够顺利高价“售出”其中一小部分,就足够抢注行为人收回成本并获得额外利益。其次,抢注行为人可能有谋求独家代理的目的。为谋求独家代理而实施的商标抢注常出现于海外商标抢注中,即抢注行为人为了在某国或地区取得某海外商品的垄断利益,以自己名义在该国或地区将该商品上的商标抢先申请注册,从而阻碍他人代理该产品,迫使品牌原权利人授予其独家代理权。最后,抢注行为人还可能是出于阻碍竞争对手之目的,即阻止竞争对手使用该商标从事正常经营活动。尤其是海外商标抢注,通过利用商标权的地域性限制在外国抢先注册商标,可以直接阻碍竞争对手的相关商标产品进入该国相关地域市场,从而扰乱竞争对手的经营策略和安排,削弱其在相关地域市场内的竞争力量,最终实现损人利己之目的。
二、商标恶意抢注的商标法规制
对于商标恶意抢注行为,首先可以适用《商标法》予以规制,通过商标异议、商标撤销、商标无效宣告等程序令抢注申请被驳回,以及令已注册抢注商标被撤销或无效。目前,我国《商标法》中其实并不缺乏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具体条款,主要涉及第4条、第7条、第10条、第13条、第15条、第32条、第44条以及第49条,但从这些条款的序号和数目中不难发现,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相关条款极为分散,于《商标法》全文随处可见,并未形成完善的体系。而不同条款的适用条件颇具差异,故需对其适用关系予以研究和厘清,依据具体情况恰当、准确地选择适用不同条款,以实现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全面有效制约。
(一)商标恶意抢注相关条款的选择适用
1.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一般条款
在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时,被援引最多的条款是《商标法》第32条,(25)《商标法》第32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该条款也被视为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一般条款。
对于普通未注册商标所有人而言,第32条后段“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可谓其商标被抢注后的救命稻草,但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其实并不容易。从条文表述中不难看出,“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已经使用”和“有一定影响”均为适用该条款的独立要件,而每一个独立要件都需要单独进行认定,只有满足了全部要件才可适用该条款。其中,“不正当手段”的解释和认定更是商标恶意抢注规制中的重点问题和复杂难题,需要综合考虑商标标志的近似程度、商品或服务类别的类似程度、抢注行为人与被抢注人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被抢注的未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抢注行为人是否存在其他恶意抢注行为或其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抢注行为人是否具有申请注册的正当理由等。同时,是否符合“在先使用”和“有一定影响”要件也并非是可以轻松判断的问题。“在先使用”涉及对是否构成来源识别性使用的判断,而来源识别性使用的判断需要以相关公众的认知水平为标准进行综合判断,其结果同样具有主观不确定性。而“有一定影响”的界限和分寸更是难以精准把握,无论是行政审查标准还是司法解释,目前都未能明确回答这一问题,只能在个案中以抢注行为人申请注册时是否明知或应知在先未注册商标为判断标准,(26)参见张鹏:《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规范的体系化解读》,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7期。依据具体情形进行个案认定。由此可见,第32条虽然适用范围广泛,但需要被抢注人承担的举证责任较重,这也会导致恶意抢注行为的法律认定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并给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带来一定困难。
同时,第32条前段“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亦可适用于规制侵害商标权益以外的其他他人在先权益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目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在先权利”的内涵均已扩大至“在先权益”的范围,即无论他人在先法益是否上升至权利高度,只要该法益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正当合法利益,则侵害该法益的商标抢注行为都属于违反了《商标法》第32条的情形。适用该条款有一个关键点,即需要证明异议人或无效宣告请求人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其必须是在先权益人或在先权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否则即便该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确侵害了他人在先权益,也无法由与该在先权益不存在利害关系的主体提出异议或请求无效宣告。适用该条款还有另一个关键点,同时也是难点,即判断他人在先权益的保护范围,从而确定恶意商标抢注行为是否侵害他人在先权益。在先权利一般较为确定和稳定,其权利内容、权利保护期限和权利保护范围也较为明确,因此判断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是否侵害在先权利一般具有较为确定的认定方法和原则。相较而言,其他未上升至权利高度的合法利益的内涵十分广泛,保护范围更是十分模糊,甚至该法益本身是否应当受到商标法保护都可能需要首先打上问号并进行法律解释和论证。目前较为典型的可受《商标法》保护的法益主要包括有一定影响的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和域名以及知名形象等,而这些法益之所以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商标法》保护,也是基于此前由相关行政司法实践而总结得出的经验和规则,其他尚未明确的法益是否能够对抗恶意商标抢注则同样有待行政司法实践的具体探索和检验。
2.特殊关系人抢注的规制
在《商标法》第32条适用条件较为复杂和严格的情况下,若恶意抢注行为人与被抢注人之间存在代理、代表关系,则宜优先选择适用第15条(27)《商标法》第15条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就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与他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申请人与该他人具有前款规定以外的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而明知该他人商标存在,该他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第一款之规定;若不存在代理、代表关系,但存在合同、业务往来等其他特殊关系的,则可优先选择适用第15条第二款之规定。
从立法沿革和司法实践来看,第15条的适用范围整体呈现扩大趋势,代理、代表关系和特殊关系的内涵在不断扩张。(28)同前注,张鹏文。相对于第32条,第15条第一款的适用条件相对更加简单明确,只要代表人或代理人未经授权以自己的名义抢注了被代表人或被代理人的商标,被代表人或被代理人就可直接提出异议或请求无效宣告,并且禁止恶意抢注行为人使用该商标,而无需再进一步去证明代理人或代表人具有主观恶意,亦无需证明其已经在先使用了该未注册商标并产生了一定影响。第15条第二款的适用条件相对于前款规定稍显严格,需要满足“在先使用”要件,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比第32条更宽松。因此,适用第15条的关键和难点其实在于证明被抢注人与恶意抢注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代理、代表关系,或存在其他会导致抢注行为人明知其未注册商标存在的特殊关系。例如在江小白商标无效宣告案中,(29)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1213号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2122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再224号行政判决书。关于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足以知晓抢注商标的特殊关系,法院从一审到再审的认定结果就经过了否定、肯定再到否定的曲折历程。虽然实践中的某些特殊关系可能牵连着复杂的关系链条,使对第15条的理解适用产生模糊性,(30)参见张今、卢结华:《商标法第十五条的价值定位与适用规则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2期。但举证证明存在特殊关系依然比举证证明“不正当手段”和“有一定影响”要简单得多。换言之,若恶意抢注行为人与被抢注人之间存在法定特殊关系,被抢注人的举证责任将会在极大程度上得以减轻,能有效规制该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
3.驰名商标抢注的规制
若恶意抢注行为人与被抢注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特殊关系,则应当考虑被抢注商标是否达到驰名程度,若答案是肯定的,则可优先适用《商标法》第13条(31)《商标法》第13条规定: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驰名商标保护条款。
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和扩大保护不仅体现在商标侵权保护方面,也充分体现在对抗恶意抢注方面。只要申请注册的商标标志与他人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且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的,即应视为应当禁止注册的情形,而无需考量商标注册申请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已注册驰名商标权利人更是可以突破商品或服务类别相同或类似的限制对抗跨类抢注。同时,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还体现于被恶意抢注的驰名商标所有人请求无效宣告不受五年除斥期间限制。而驰名商标的知名度极高,已经达到了在全国范围内被相关公众知晓的程度,在抢注人无反证的情形下,一般均可认定其明知他人在先驰名商标,即可以推定其具有主观恶意,这显然十分有利于规制驰名商标恶意抢注行为。
但《商标法》第13条的适用难点在于,驰名商标的认定遵循被动认定和个案认定原则,是否驰名只能在被抢注人请求驰名商标保护后才能进行审查认定,同时被抢注人需要承担证明其被抢注商标在他人申请注册前已经驰名这一较高程度的举证责任,(32)See Chang Sunny, Combating Trademark Squatting in China: New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Trademark Law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 Vol. 34, No.2, 2014, pp.337-358.即使该商标曾经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也不能百分之百确信在新案中该商标依然能够被认定为驰名商标。驰名商标的认定需要由审查或审理人员根据其近期使用情况、广告宣传情况、销售情况等方面的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判断。换言之,驰名商标的认定结果取决于被抢注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足以证明其商标已经达到了广为人知的程度。而被抢注人的举证能力对驰名商标认定结果的影响实质变相提高了《商标法》第13条的适用难度,因此适用该条款时需要格外注意应当满足被抢注商标为驰名商标这一适用前提。
4.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抢注的规制
(1)《商标法》第4条新增条款
《商标法》2019年修订以后,第4条新增条款“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无疑为遏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加大了对缺乏真实使用意图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打击力度,直接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纳入了绝对禁注情形,也为被抢注人寻求商标法救济提供了另一条可供选择的有效路径。该条款仅有两个适用要件,即“不以使用为目的”和“恶意”,(33)同前注,孔祥俊文。或亦可将“不以使用为目的”视为“恶意”的定语。(34)参见王莲峰:《新〈商标法〉第四条的适用研究》,载《政法论丛》2020年第1期。与第32条相比,该条款多了“不以使用为目的”要件,但是适用的范围却从抢注他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扩大至抢注他人在先标识和公共符号资源的情形,即侵害他人在先权益的恶意抢注和商标囤积行为亦属于第4条可以规制的对象。同时,相对于第32条而言,适用第4条提出异议或请求无效宣告的被抢注人还无需受到主体资格和五年除斥期间的限制,任何人都能够随时以违反第四条为由提出异议和请求无效宣告,而这一点对于有效规制商标恶意抢注具有重要补充意义。
第4条新增条款的进步意义不止于此。实质上,第4条中“恶意”要件的内涵比第32条中“不正当手段”要件的内涵更加广泛。所谓“不正当手段”是指抢注行为人明知或应知他人在先商标的存在,而“恶意”不仅包括了“不正当手段”的内涵,还包括了侵害他人其他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之内涵,因此无正当理由大量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同样属于具有恶意的商标注册申请,即落入了第4条的适用范围。因此,只要恶意抢注行为人同时还抢注了大量其他商标,则其行为有可能构成商标囤积,若被抢注人以构成商标囤积为由申请宣告无效,则无需再证明恶意抢注行为人明知或应知其在先标识的存在,更无需证明抢注商标与在先标识容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或误认,即可以避免十分复杂的混淆认定问题,不必再纠缠于商标相同或近似认定和商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认定相关问题。
但举证责任的减轻往往也伴随着适用范围的缩减。第4条仅适用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抢注情形,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具有搭便车目的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难以进入第4条的规制范围。同时,并非所有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抢注都属于商标囤积情形,也有的恶意抢注行为人是出于排除、限制竞争目的针对性地抢注了竞争对手的未注册商标,其抢注的商标数量一般并未达到“大量”的程度,不构成商标囤积。因此,对于不构成商标囤积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恶意抢注,若被抢注人要适用第4条新增条款对其请求无效宣告,则除了要证明抢注行为人缺乏真实使用意图,还需要证明商标相同或近似,并结合其他相关事实证明抢注行为人存在主观上的恶意,其所需承担的举证责任也就与适用第32条并无本质区别了。
(2)连续不使用商标的撤销
注而不用的商标就如同枯木,既不利于追寻实质正义,也不利于追寻程序正义。(35)See Rebecca Tushnet, Registering Disagreement: Registration in Modern American Trademark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30, No.3, 2017, p.918.因此,对于缺乏真实使用意图的恶意抢注行为,除了可以依据《商标法》第4条进行规制,还有机会通过《商标法》第49条所规定的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可撤销规定依申请撤销恶意抢注商标。
事实上,《商标法》第49条与第4条所规制的恶意商标抢注行为具有一定重合性,都以“不使用”为适用要件,但二者的适用条件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存在本质差别。适用第4条需要商标注册申请人在申请时就不具有真实使用的意图,并且存在其他恶意,而适用第49条无需关注商标注册申请人在申请注册时的主观状态,只要求在法定期限内,并且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注册商标权人连续不实际地使用商标便可。因此,第4条既可以适用于商标注册申请被核准以前,作为提出商标异议的理由,亦可以适用于商标注册申请被核准以后,作为请求商标无效宣告的理由,而第49条只能适用于商标注册申请被核准的三年以后。而被抢注人自然更希望在恶意抢注行为发生后及时地发现该行为,并提出商标异议,直接将其阻拦在商标核准注册的门槛之前,或在其核准注册后及时请求无效宣告,避免恶意抢注人利用注册商标专用权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加重损害结果。因此,通过商标撤销规制商标恶意抢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节省力气的妥协方案,但这一妥协方案有时也能起到补救作用。例如,当被抢注人因超过五年除斥期限而丧失无效宣告请求权时,由于连续不使用可撤销的法定期限为三年,被恶意抢注的商标很有可能符合可撤销的情形,此时至少可以撤销抢注商标来及时止损。
5.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补充、兜底条款
(1)“诚实信用”条款
《商标法》第7条明确规定“商标注册申请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而商标恶意抢注显然属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违法行为。且由于具体条款规制范围的有限性和法律解释上的目的限制,诚信条款在规制商标抢注方面仍具有适用的必要性。(36)张铃:《商标抢注行为中诚信条款的司法适用研究》,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但诚实信用原则是一项法律基本原则,其内涵具有模糊性,其主要功能是为适用其他具体法律规范提供方向指引和原则性标准,难以直接在具体案件中被独立适用于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实践中,行政司法人员也一直在尽量避免向诚实信用条款逃逸,一般是将诚实信用原则具体化、类型化,结合其他具体法律规范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予以规制。并且从《商标法》所规定的可以提出商标异议、申请撤销和请求无效宣告的情形来看,其中也并未列举违反《商标法》第7条之情形。因此,在通过《商标法》规制商标恶意抢注时,原则上不能仅凭抢注行为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而直接驳回注册申请、撤销抢注商标或宣告抢注商标无效,必须要寻找到《商标法》中相应的其他具体条款。但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性地位仍无可动摇,商标申请注册仍然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是判断是否构成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关键所在,故诚实信用原则条款宜作为一种宣示或补充,与其他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具体条款一同适用。
(2)“其他不良影响”条款
实践中,对于具有不良社会影响的商标恶意抢注,例如恶意抢注公众人物姓名或肖像的,亦有适用《商标法》第10条第一款第(八)项中的“其他不良影响”对其予以补充规制的可能性。
事实上,第10条所规定的禁注情形主要是容易损害公共利益、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情形,一般并不包括侵害他人在先权益的恶意抢注情形,而“其他不良影响”条款是第10条中具有兜底性质的条款,因此从立法体系上来看,“其他不良影响”与前款中所规定的情形应当具有同质性,即指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消极、负面影响。(37)参见马一德:《商标注册“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而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领域公众人物姓名、肖像等申请注册为商标,即属于可能具有前述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3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领域公众人物姓名等申请注册为商标,属于前款所指的“其他不良影响”。因此,对于恶意抢注公众人物姓名或肖像等具有不良社会影响的情形,除了《商标法》第32条,还可以适用《商标法》第10条中的“其他不良影响”条款驳回申请或宣告无效。此外,不同于第32条,第10条属于绝对禁注事由,被抢注人依第10条提出异议或请求无效宣告还无需受到主体资格和五年除斥期间的限制。
在规制恶意抢注公众人物姓名、肖像等方面,第10条还可以弥补第32条第一款对于已故公众人物保护的不足。由于姓名权、肖像权均属于人格权,自然人逝世以后其人格权也就随之消灭,因此已故公众人物的姓名或肖像并不属于“现有”在先权利的范畴,难以满足第32条的适用条件。但已故公众人物姓名和肖像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却并不会随着其逝世而直接消逝,同样具有应受法律保护的权益,而第10条补足了这一缺陷。但需要清醒认识到,第10条中的“其他不良影响”条款并非是专门为了恶意抢注他人姓名、肖像而设置,其之所以能够适用于部分恶意抢注他人姓名或肖像的情形,是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特定领域公众人物的形象与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该等公众人物姓名一般已经广为人知,形象也已经深入人心,将其姓名或肖像申请注册为商标容易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团结等社会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产生不良影响,刚好落入了“其他不良影响”条款的规制范围。因此,对于其他的非特定领域公众人物的姓名或肖像被抢注的,或普通人的姓名或肖像被抢注的,则不属于《商标法》第10条的规制范围,应当转向适用其他条款。
另外,第10条中的“其他不良影响”条款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规制其他非典型商标恶意抢注行为进行补充和兜底。司法实践中也经常扩大适用“其他不良影响”条款,将其作为禁止非诚信注册行为的一般条款。(39)同前注,张鹏文。例如,在“阿京腾百”商标异议案中,(40)参见张翼翔:《“BATJ”缘何大战“阿京腾百”?——“拼贴型”商标规制与知名企业联合维权背后的法理与情理》,https://mp.weixin.qq.com/s/XzDp6jE9g-Tdi-FEF_HlOg,2021年9月8日最后访问。异议商标是由他人知名商标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百度剪切拼接而成,客观上并不与他人在先商标相同或近似,一般也不会导致公众混淆,难以适用一般的商标恶意抢注规制条款,但由于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百度四个在先商标知名度均极高,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人显然具有不正当利用他人商誉的意图,其行为构成商标恶意抢注,理应受到商标法规制,故国家知识产权局以违反了《商标法》第10条中的“其他不良影响”条款为由,决定了对全部类别上的异议商标都不予注册。
(3)“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条款
《商标法》第44条对于规制商标恶意抢注也具有一定补充和兜底作用。
第44条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对具有绝对禁注事由的注册商标应当予以无效宣告,而该条款中除列举了违反第4条、第10条等条款的无效情形外,还规定了“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作为补充兜底。(41)《商标法》第44条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中“欺骗手段”主要是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伪造文书或其他证明文件的情形,而“其他不正当手段”则与第32条中的“不正当手段”内涵并不相同,是指44条第1款列举情形以外的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侵占公共资源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因此,从文本含义来看,第44条中的“其他不正当手段”条款似乎可以起到对商标恶意抢注规制条款进行完美补充和兜底的作用。然而若对其采用体系化的法律解释方法即可发现,该条款规定在《商标法》第44条中,属于具有绝对禁注事由而应当宣告无效的情形,而非第45条中所规定的具有相对禁注事由而可以宣告无效的情形。因此,若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仅仅只是侵害了特定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不应属于第44条所调整的范围,也就无法纳入第44条中所谓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的情形中。
在以往的行政司法实践中,所谓“其他不正当手段”主要针对的是商标囤积行为,包括不以使用为目的申请注册多件与他人在先标志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行为,和不以使用为目的大量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因此,若被抢注人想要依据《商标法》第44条中的“其他不正当手段”条款请求无效宣告,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即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人应当同时抢注了多件与他人在先标志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具有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等损害公共利益的可能,否则该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仅损害了特定主体的民事权益,不具有损害公共利益的性质,也就无法适用该条款,必须转向其他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具体条款。
但需要注意的是,《商标法》2019年修改以后,以往实践中适用第44条“不正当手段”条款规制的商标囤积情形基本可以直接落入第4条新增条款的规制范围。从第44条的立法逻辑来看,其所指的“不正当手段”应当是除了该条款已经明确列举的条款以外的其他情形。而第4条已经涵盖了不以使用为目的大量申请注册商标的商标囤积行为,同时也包括了不以使用为目的抢注了多件与他人在先标识相同或近似的恶意抢注行为。因此,在《商标法》2019年修改以后,应当注意将第4条所规制的情形排除在第44条的“不正当手段”情形之外,仅将该条款适用于“不以使用为目的”之外的其他损害公共利益的恶意抢注情形,例如,申请注册多件与他人在先权益相关标志近似的商标而损害公共利益,但数量并未超出正常经营需求,具有真实使用意图的情形。若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已经落入了第4条的规制范围,则应当直接以违反第4条为由宣告抢注商标无效,而无需、也不应当适用第44条中的“不正当手段”条款。
综上所述,《商标法》中并不缺少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条款,只是各个条款之间的适用关系尚未在立法中予以明确,同时由于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类型过于多样和复杂,难以直接通过一个或几个具体条款完整地覆盖所有类型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不免导致商标恶意抢注的相关条款显得过于分散和零乱,令被抢注人在寻求商标法救济时容易陷入适法选择的迷茫中。但总体而言,商标法中的各个具体条款已经分别涉及到了各个类型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立法者已经考虑到了抢注未注册商标或已注册商标的情形,也考虑到了侵害其他他人在先权益的情形,还考虑到了未侵害特定主体利益的商标囤积情形。
(二)商标法适用的局限性
尽管《商标法》已经较为全面地考虑到了各种商标恶意抢注情形,但其对商标恶意抢注的处置方式主要是驳回恶意注册申请、撤销恶意抢注的注册商标和宣告恶意抢注的注册商标无效,仅能使本就应当被驳回的商标注册申请被驳回或本就应当被消灭的注册商标权被消灭,而无法使恶意抢注行为人承担与其恶意程度相适应的其他法律责任。(42)参见魏丽丽:《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立法检视与完善》,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除了在恶意抢注驰名商标和存在代理、代表关系的恶意抢注情形中,恶意抢注人需要承担“禁止使用”抢注商标的责任,其他的商标恶意抢注情形中均未见“禁止使用”的相关规定。而驰名商标抢注人之所以受到“禁止使用”的限制,是由于其知名度极高,在商标法上,未注册驰名商标已经可以被视为与普通注册商标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因此可以享有与普通注册商标同等程度的专用权,同时,已注册驰名商标的专用权则同样因其极高知名度而得到了在商品或服务类别上的一定程度延伸。而其他被抢注的在先标识原则上都属于未注册商标的范畴,即便是已经注册的商标,在其他未注册的商品或服务类别上,其仍然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未注册商标。至于代理人或代表人之所以受到“禁止使用”的限制,则是由于其与被抢注人之间存在特殊的信赖关系,基于这种信赖关系,代理人和代表人在法律上应当具有忠诚、勤勉义务和不得抢先注册、不使用的不作为义务。因此,二者均属于商标恶意抢注中的例外情形,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在普通商标恶意抢注情形中,被抢注人能够获得的商标法救济仍然主要仅限于驳回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和宣告恶意抢注商标无效。
这是由于商标法只赋予了注册商标以专用权,其所保护的对象也主要只是注册商标,因此其所规定的各种侵权责任条款也都是围绕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情形。而商标恶意抢注所侵害的对象严格意义上讲均为未注册商标,在商标法中,未注册商标所有人所能够享有的权利仅仅只是先用权抗辩和对抗恶意抢注,也就无法同样适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各项责任条款。与此同时,商标法目前又并未专门针对商标恶意抢注设置侵权责任条款,这也就导致商标法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规制和惩戒力度十分有限,需要适时结合其他部门法方能全面遏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
三、商标恶意抢注的竞争法规制
(一)商标恶意抢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由于未注册商标并未取得商标法上的排他性权利,对于恶意抢注并实际使用他人未注册商标的行为,无法直接通过商标法进行惩戒,此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有效进行补充规制。
事实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与知识产权法具有部分一致性,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一直被视作对知识产权法的一种补充。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的关系同样如此,商标法通过权利保护模式为注册商标提供专用保护,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通过行为规制模式为未注册商标提供反混淆保护。(43)参见张玲玲:《论未注册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与保护——兼评〈商标法〉第十三条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的适用》,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11期。因此对于超出商标法保护范围,但又应受法律保护的未注册商标之利益,往往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补充保护。
1.《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对抢注未注册商标的补充规制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主要体现于第6条禁止混淆条款,该条款明确禁止擅自使用他人具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名称、姓名、域名主体、网站名称、网页等标识,引人误认,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若恶意抢注行为人注册他人在先标识的同时实际使用了抢注商标,则可能属于擅自使用他人在先标识、容易引起混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可适用该禁止混淆条款对其进行规制。即便恶意抢注行为人获得了注册商标专用权也不能作为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排除因素,因为该注册商标专用权仅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并不具有实质合法性。例如,在歌力思商标纠纷案中,(4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617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综合考虑了歌力思公司的在先权利状况以及王碎永取得和行使权利的正当性等因素后,认为王碎永申请注册及使用“歌力思”商标是攀附歌力思公司的商誉、搭歌力思公司“歌力思”的企业字号之便车的行为,会导致相关公众对其产品与歌力思公司生产的相关产品产生混淆和误认,于是认定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中同样存在“有一定影响”之表述,与《商标法》第32条的表述相同,而这并非纯属巧合。事实上,《反不正当竞争法》(原第5条)在2017年修订前所采取的表述是“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2017年修法以后才改为“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这一修改内容不仅印证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对于商标法的一种补充地位,也体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在未注册商标保护的制度设计方面的一致性。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中的“有一定影响”应当与《商标法》第32条中的“有一定影响”采取同义解释,即只要未注册商标的影响力达到了《商标法》第32条中的有一定影响程度,具有对抗恶意抢注的权利,则同样应当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保护,具有禁止他人实施混淆行为的权利。
另外,《反不正当竞争法》还专章规定了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包括违反第6条的民事责任及其赔偿数额的确定方法,(45)《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规定: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商品、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责任,(46)《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8条规定: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以及将受到行政处罚纳入信用记录并依法予以公示等法律后果。(47)参见《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6条。因此,若恶意抢注行为人在抢注同时还使用了被抢注人的在先标识,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所禁止的混淆行为,则恶意抢注行为人除了应当承担抢注申请被驳回、抢注商标被撤销、无效等法律后果,还应当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承担赔偿被抢注人的实际损失、返还侵权获利等民事责任以及其他相应行政责任和法律后果。
2.《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补充规制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48)《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中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而对于能否适用第2条补充规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学理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分歧。
司法实践中,有法院直接独立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认定了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拜耳公司与李某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49)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862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李某在将与原告拜耳公司在先使用的商品包装、装潢相似的图形申请注册为商标后,并未将该商标投入实际使用,而是在淘宝平台上对原告进行大量投诉,并向原告提出“付费撤诉”和以70万高价转让抢注商标的要求,同时被告还同时申请注册了大量其他商标,存在商标囤积行为,因此,该案被告的行为构成商标恶意抢注无疑,审理法院认为被告这种通过侵犯他人在先权利而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市场的正当竞争秩序,并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认定其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0万元。
但有学者对该案的法律适用是否正确和合理持保留态度,认为审理法院对于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已经偏离《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前提,也不符合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界定,有不合理扩张适用“一般条款”之嫌。(50)参见魏丽丽:《商标恶意抢注规制路径探究》,载《政法论丛》2020年第1期。与《商标法》第7条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条款类似,《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内涵具有高度概括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一般不能直接将其单独适用于具体案件中,通常只有在出现了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规制,已有具体条款无法涵盖其范围,又尚未来得及对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具体规定时,才有单独适用第2条的必要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扩展保护至少应该考虑被告的主观意图、原被告之间的竞争关系等因素。(51)王太平:《知识产权的基本理念与反不正当竞争扩展保护之限度——兼评“金庸诉江南”案》,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10期。在拜耳公司与李某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李某并未将抢注商标投入实际使用,根本就没有实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具有经营者身份,也就更不会与拜耳公司存在竞争关系,而双方主体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前提,因此,李某的行为虽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了商标恶意抢注,却并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规制的范畴。
由此可见,尽管理论上有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可能,但该条款的规制范围并不能无限延伸至所有类型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仍应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传统分析框架下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进行分析,首先判断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人和被抢注人是否属于经营者,界定双方主体是否存在竞争关系,再来分析恶意抢注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混淆行为、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
3.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的局限性
前文已提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一般以经营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为前提,只有直接或间接损害了竞争对手利益,进而损害了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才宜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52)焦海涛:《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的实用主义批判》,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因此,司法实践中一般仍然坚持以存在竞争关系为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逻辑起点,(53)参见王永强:《网络商业环境中竞争关系的司法界定——基于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考察》,载《法学》2013年第11期。若恶意抢注行为人与被抢注人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则难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可见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规制亦具有一定局限性。
狭义的竞争关系一般指同业竞争关系,即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之间具有替代性的经营者之间存在的相互争夺市场交易机会的关系,即直接竞争关系。(54)王先林:《论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范围的扩展——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完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6期。但如今,竞争关系的内涵和外延都呈现了不断扩张的趋势,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学理上均已突破同业竞争限制,对竞争关系采取了广义解释,即认为只要在市场交易中侵权者和被侵权者在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方面存在可替代性,或者招揽的是相同的顾客群,或促进了他人的竞争,或不正当地削弱了后者的市场竞争优势和能力,都可以认定存在竞争关系,甚至认为在部分类型案件中,具有竞争关系并非是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必要条件,应当直接弱化对竞争关系的认定。(55)参见李胜利:《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和经营者》,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8期;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创新性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周樨平:《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的认定及其意义——基于司法实践的考察》,载《经济法论丛》2011年第2期。例如在小拇指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56)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0046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高院就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竞争关系或从事相同行业,经营者之间具有间接竞争关系、行为人违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应当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百度诉奥商、联通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57)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鲁民三终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院也同样指出,竞争关系不以同业为限,只要在市场竞争中存在一定联系或一方不当妨碍了另一方的正常经营活动并损害其合法权益,就应认为存在竞争关系。
同时,存在竞争关系的主体一般也应当限于市场经营者,一般是指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或经营业务虽不相同但其经营行为违背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竞争原则的经营者。而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人和被抢注人有时并非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者,难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在湖南王跃文诉河北王跃文等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58)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长中民三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对“经营者”进行了扩大解释,认定了原、被告之间具有竞争关系。该案中,原告为作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营者,而法院将作品视为作者经营的商品,从而主张作者也是文化市场中的经营者,认定了该案双方主体存在竞争关系、被告涉案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暂且不论将作者视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经营者是否合理,至少从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角度来看,由于在诸多侵犯非商标性权益的商标恶意抢注情形中,被抢注人往往并非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者,若能够将竞争关系的主体作扩大解释显然可以扩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更有利于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标法的补充作用,从而加强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规制力度。
(二)商标恶意抢注的反垄断法规制
注册商标专用权实质上是一种合法的排他性垄断权利,注册商标权人可以通过禁止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类别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标志,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垄断。商标法正是通过赋予注册商标权人这种合法的垄断权利来激励经营者积极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积攒商誉,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当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人在获得注册商标专用权后滥用权利实施了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则会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构成违反《反垄断法》的非法垄断行为,此时则可通过《反垄断法》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予以规制。
单纯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一般并不涉嫌非法垄断,但若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人在注册成功后不当地行使了注册商标权,则有可能因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而落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其主要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
涉及知识产权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情形主要包括以不公平的高价许可知识产权、拒绝许可知识产权、搭售、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以及差别待遇等。(59)参见《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第7-11条。在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恶意抢注情形中,有一部分恶意抢注行为人是基于阻碍竞争对手之目的而实施了恶意抢注行为。(60)See Jessica Martin,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A Need for China to Further Amend Its 2013 Trademark Law in Order to Prevent Trademark Squatting,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2, No.2, 2017, pp.993-995.这部分恶意抢注行为人将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的未注册商标抢先注册后,往往并不会将该商标使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即不具有搭便车目的,而是利用所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禁止竞争对手使用其未注册商标。对于被抢注人而言,该商标承载了其通过长期经营活动所积攒的商誉,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理论上商标并不具备不可替代性,但实践中如果要更换商标则会使其丧失通过勤恳经营所获得的现有市场竞争优势,需要付出巨大成本,不啻为剥皮抽筋之打击,相关经营者甚至会因此而直接选择放弃相关市场,这也就达到了恶意抢注行为人的阻碍竞争对手之目的。换言之,恶意抢注行为人的拒绝许可行为可能具有一定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有的恶意抢注行为人并未拒绝许可,却意图将该商标权以不公平的高价许可或转让给被抢注人。尽管商标权人有权自主决定其商标权的许可、转让费用标准,但若其所要求的许可、转让费用过高,超过了该商标权的合理价值,使被抢注人难以承受,或即便可以承受但会导致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的,则这种以不公平的高价许可、转让商标权的行为同样可能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构成垄断行为。此外,也有部分恶意抢注行为人既未拒绝许可,也未开出不合理的许可费用或转让费用,却在许可、转让协议中附加了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基于谋取独家代理之目的的商标恶意抢注就属于这种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情形,同样可能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但要注意,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前提是恶意抢注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拥有商标权虽然可以作为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考量因素之一,却不能仅凭拥有商标权而直接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需要依据反垄断法的传统分析方法对其是否在相关商品市场和地域市场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认定或推定。(61)参见《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第6条。相较于专利权而言,经营者凭借商标权所能取得的市场控制力其实是有限的,商标难以像专利技术一样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必需设施,从而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他经营者仍然可以自由进入相关市场,而被抢注人转向使用其他商标虽然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其难度大小与寻找专利技术的可替代技术不可同语。因此,想要凭借拥有商标权而认定恶意抢注行为人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在实践上仍具有较大难度,也就难以认定其行为构成滥用商标权的非法垄断行为。
事实上,商标的作用在于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若经常地将商标权许可或转让给他人,则不利于保持商品或服务质量的同一性,容易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因此商标法并未鼓励商标权人积极地许可或转让商标,反而对商标许可和转让作出了严格限制,要求受让人保证商品或服务质量。同理,反垄断法实则也不应对商标权人的拒绝许可和拒绝转让作出过多干涉。另外,反垄断法真正所要保护的并非是单个经营者的特定利益,而是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和公共利益。在商标恶意抢注情形中,一般只有在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人实施了大规模抢注行为时,才有较大可能构成损害竞争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从而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因此,反垄断法对商标恶意抢注的规制亦存在局限性,且在适用反垄断法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人滥用商标权进行规制时,本就有必要保持审慎态度。
四、商标恶意抢注的其他法律规制
(一)商标恶意抢注的著作权法规制
若被恶意抢注的在先标志具有一定独创性,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的,则恶意抢注他人在先标志的行为会构成侵害著作权的侵权行为。将他人在先创作的作品申请注册为商标的行为显然不属于《著作权法》第22条、第23条所规定的可以不经作者许可而实施的合理使用情形,不仅可能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等著作人身权,还可能侵犯作者的复制权、发行权等著作财产权。著作权法完整地规定了侵害著作权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故除了可以通过《商标法》驳回抢注申请或宣告抢注商标无效,还可以通过《著作权法》规制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商标恶意抢注,令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适用著作权法进行规制的便利之处在于,著作权可以自作品完成之日起自动取得,不以登记备案为权利取得或生效的要件。因此,即便被抢注人创作作品的本意并非是为了取得著作权,例如未注册商标所有人设计商标标志可能只是为了能够使用合适的、便于识别记忆的商标标志,其主观上可能并没有创作出具有独创性作品的意图,但只要其商标标志客观上具有著作权法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独创性,就属于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被抢注人就可以自其作品完成之时实际地取得著作权,并在其作品被擅自申请注册时通过著作权法获得救济。
适用著作权法进行规制的另一便利之处在于,依据《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等著作权相关的国际公约之规定,作品应当在其所有成员国内受到法律保护,且作者为成员国国民者,无论作品是否已经出版,都受到保护。(62)参见《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第2条、第3条。这意味着,即使著作权作为一种知识产权而具有地域性,但在《伯尔尼公约》等国际条约的影响下,其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至国际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可自然延伸至参与了相关国际公约的其他成员国地域范围内。因此,在规制海外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方面,著作权法领域相对完善的国际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即便被抢注人尚未在抢注行为地实际地使用其未注册商标,但只要其未注册商标具有独创性,则其未注册商标就可以作为作品而在抢注地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从而阻却侵害其著作权的在后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并且商标抢注行为人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著作权法在商标恶意抢注规制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其只能用于规制侵害了著作权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而著作权法对作品有独创性要求,虽然独创性中所要求的创造性程度并不高,只包含了较低程度的创造性要求,但也绝非普通未注册商标所能轻易达到。因此,在恶意抢注未注册商标的情形中,通过著作权法寻求救济固然是一种更为便捷有效的方法,但这一捷径并非人人都可以行走通过,只能适合于被抢注的在先标志具有独创性的这一小部分情形。这也从侧面提醒经营者,在选定商标时应当尽量选择具有独创性的、固有显著性程度较高的商标标志。这不仅是由于具有独创性的商标标志可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也是由于具有独创性的商标标志不易与他人商标标志相同或近似,更易获得商标法上的禁止混淆保护。
(二)商标恶意抢注的侵权责任法规制
知识产权法的本质是私法,属于民法范畴,商标法自然也属于民法范畴。因此,对于符合侵权行为构成要件、(63)王莲峰、康瑞:《法律责任视角下商标恶意抢注的司法规制》,载《中华商标》2018年第7期。侵害了他人在先权益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当商标法中缺乏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侵权责任规定时,被抢注人原则上可以适用民法中一般的责任法——侵权责任法,要求恶意抢注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尤其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实践中,这种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还具有优先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并不仅限于损害赔偿这一种方式。事实上,由于民事权益既包括了财产性权益也包括了人身性权益,有时单纯的损害赔偿无法完全弥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故民法中所规定的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方式十分多元,包括损害赔偿、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损害赔偿责任只是其中主要和常用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而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同时一并适用,商标恶意抢注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亦应如此。
一般而言,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其中,无过错责任原则一般适用于特殊侵权责任,需要法律明确作出特别规定,一般的侵权责任则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商标法中并未对商标恶意抢注的侵权责任进行特殊规定,商标恶意抢注亦不属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所规定的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监护人责任、产品责任、污染环境责任等特殊情形,因此,商标恶意抢注的侵权责任应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意味着,应当将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有过错存在方才有责任存在。
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本质上是一种不良的、不正当的心理状态或行为目的,过错一词本身也表明了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对其价值评价的否定性和批判性。过错一般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而从商标恶意抢注的构成来看,商标抢注行为人主观上对他人在先标志应当是处于“明知”或“应知”状态,即其主观上可预见损害他人在先权益的可能,却希望或放任这种损害结果发生。因此,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人显然具有主观上的过错,并且这种过错还是一种严重的过错即故意,需要由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故对于侵害了他人在先权益的商标恶意抢注情形,若该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给被抢注人的合法利益造成了实际损失,则可适用侵权责任法对其予以规制,要求恶意抢注行为人依据侵权责任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其他方式的民事责任。
将未披上权利外衣的法益纳入侵权法的保护范围是侵权法的国际发展趋势,(64)田晓玲、张玉敏:《商标抢注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司法治理》,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1期。侵权责任法可以对侵犯他人在先权益,尤其是非权利性质民事利益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予以良好补充规制。但也须注意,适用侵权责任法的前提是被抢注人对其在先标志享有民法上的应保权益,若被抢注人对该在先标志并不享有确定的权利,只是享有一定的民事利益,则这种利益应当具有重大性,(65)参见王燕利:《民事“利益”独立保护之司法证成》,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并具有独立内涵,有受法律保护之必要,才能进入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因此,被抢注人对其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是否享有应保利益需要通过综合考察该未注册商标的持续使用时间、使用范围、广告宣传程度等因素,只有具备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未注册商标才是能够获得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利益,若该未注册商标未满足公开性和重大性要件,被抢注人则难以通过侵权责任法获得相应法律救济。这一点也与商标法上所规定的,仅在先使用并已经具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才能对抗他人恶意抢注具有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
结语
国家正在加大力度重拳打击专利和商标的非正常申请现象。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常申请行为不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还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公共利益。屡禁不止的商标恶意抢注现象无疑会严重阻碍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打击力度以遏制该现象。而实践中,不同类型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需要适用商标法中的不同具体条款予以规制,明确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类型、特征及其相关法律适用依据和法律适用关系是全面有效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重要条件。同时,在以商标法为商标恶意抢注规制主力的基础上,也不应忽略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著作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其他法律的重要补充作用,应灵活适用不同部门法保护被抢注人的合法利益,使恶意抢注行为人承担其应当承担的全部法律责任,令其最终无利可图且无路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