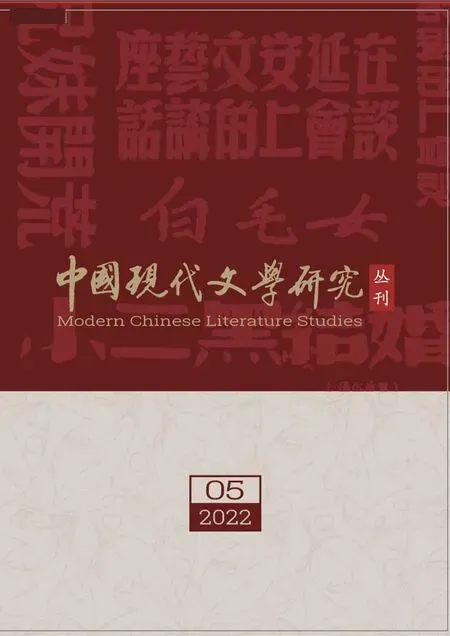编者的话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我们特别推出“《讲话》和延安文艺研究”专辑。《讲话》是开辟新的人民文艺的经典性文献,如程凯文章中所说,应把《讲话》的生成、实践及其演化的“整体经验”作为严肃的历史考察对象和理论思考对象。这也意味着,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创新发展的视野中,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文艺走过的高扬人民性的百年道路。
世界正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洲震荡风雷激,历史巨大的总体性运动正在向着我们展开。当此之际,我们更清晰、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的探索、决断和奋斗,而文艺一直是、仍将是这一进程中有机的主动性力量,中国式的现代文艺深刻地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经验。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文艺家,一如我们的前辈,都将在对这个历史进程的回应中确定位置、再造主体,这也为我们敞开了理论与学术的广阔天地,我们在思考何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艺的同时,也是在探索和发展关于文艺的中国话语。
为纪念《讲话》80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题为《向人民大地》的展览,其中一个重要单元是《讲话》与世界。魏然的文章论述了《讲话》在阿根廷的传播,《讲话》与千里万里之外的异国文艺家和革命者的对话,使我们在世界性的结构关系中认识《讲话》的意义,认识《讲话》所召唤的创造未来的革命性能量。
杨慧、刘岩关于历史和现实中的东北叙事的文章,周子晗关于延安公营工厂的师徒叙事与技术政治的文章,从观念史、文化史、社会史的角度展现了文学与它的外部之间多端缠绕的“摹仿”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重建批评对象,意味着由文学理解世界与历史,也在世界和历史中动态地确立文学的本体。我们分两期连载了张旭东论鲁迅文学风格的复杂性、统一性与历史性的长文,此文不仅为理解鲁迅提供了新的整体性思路,也为我们在当下境遇中的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镜鉴。
2022年,当我们言说文学时,我们在思考什么?当“破圈”“无界”“跨文体”等在各种场合被言说时,我们是否真的意识到我们的焦虑所在? “圈”和“界”和那个似乎不得不“跨”而“跨”了也不知道“跨”到哪里去的“体”,都喻指着一种幽闭焦虑,小说已经盛不下我们,诗已经盛不下我们,散文已经盛不下我们,我们已经盛不下这个时代的庞大经验,水满欲溢,这看上去是一种“器”的危机。但这种危机不是在文体上变幻花样换更大的碗和盆和游泳池就能解决的,“器”之“破”、“器”之“无”,意味着“道”需要重立,这不是文体问题,这是在世界、历史、精神的总体性上重新衡量和确认那个“文学”,在这个时代无穷无尽的书写和表意活动的整体中去思考文学何以是文学。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读一肚子书,攒了一堆坛坛罐罐,下笔就知道我在写小说、写诗、写散文,有规矩有方圆,但或许,我们也可以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在奥尔巴赫的意义上、在鲁迅的意义上思考一下作为“道”的文学,坛坛罐罐破不破不是多大的问题,真问题是,文学之“道”安在?
这篇《编者的话》写完,重看一遍,发现频频出现“总体”与“整体”,是的,这就是立意所在。也是为了某种整体性视野,这一期刊发了竹内好的两篇文章,均是首次译成中文,在此感谢两位译者,也感谢孙歌先生的译校。
李敬泽
2022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