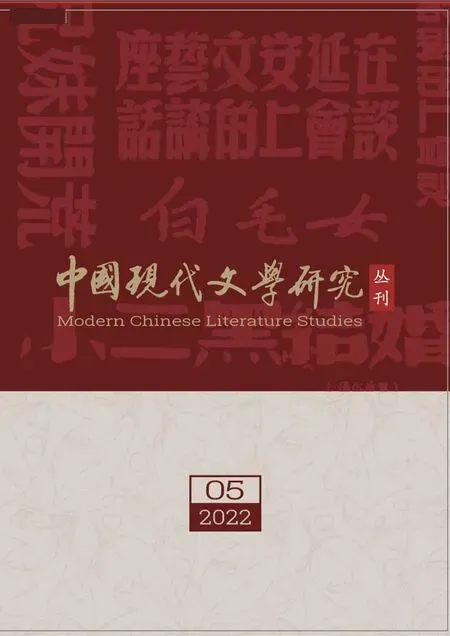译者手记
曾 嵘
《叶绍钧〈小学教师倪焕之〉译者序》一文,写于1943年5月23日。正如题名所示,这是作为大阪屋号书店同年9月发行的《小学教师倪焕之》的《译者序》发表的,现收录于《竹内好全集》第14卷。
竹内好最早翻译的是谢冰莹的《梅姑娘》(1935年),后来陆续译出沈从文的《黄昏》、郁达夫的《所谓自传也者》、海戈《孔子的国籍》、鲁迅的《死》、刘半农和商鸿逵的《赛金花本事》、萧红的《逃难》。直到1941年7月1日,竹内好才开始着手翻译《小学教师倪焕之》,1943年4月提交译稿。①参照「年譜」、『竹内好全集』第17巻、筑摩書房、1981年、299頁。
1932年夏,竹内好在北京购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倪焕之》。②参考竹内好「本のことなど」(1972)、『竹内好全集』第13巻、筑摩書房、1981年、51頁。1937年2月7日,他在日记中如是记录:“晚,读《倪焕之》一百二十页。兴致勃勃。这就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小说!日本是否有此类型的东西呢?一时想不到。”③竹内好「北京日記」(1937)、『竹内好全集』第15巻、筑摩書房、1981年、141頁。又于2月9日记载“昨夜躺床上读了六十页《倪焕之》”。最后一次是2月13日,在日记中留下了大段读后感:
读罢叶绍钧的《倪焕之》。无甚称道之处。作为1930年出来的东西,就算是第一个长篇,与茅盾相比难免也有稚拙之感。前半与后半相差悬殊。(如茅盾所评。)前半的五四前后的乡村教育状况写得不错。从五四至五卅主人公在上海的活动模糊不清。可以看出他试图描写理想主义的革命在现实的漩涡中的发展。虽说态度认真,奈何笔力不济才是悲惨。卷末茅盾的评语中肯。读郭沫若《划时代的转变》五十页。从《倪焕之》中活了过来。生气盎然,不得不感叹才气之差别。约莫是沫若中的佳作了吧。①竹内好「北京日記」(1937)、『竹内好全集』第15巻、筑摩書房、1981年、142頁。
日记的前后内容比较跳跃,能感受到竹内好读完《倪焕之》之后心情欠佳,通过郭沫若的《划时代的改变》才得以缓和的情绪变化。第一晚读《倪焕之》时,竹内好曾欣赏其作为教育小说的稀有,可读到最后却说“无甚称道之处”,并对叶圣陶的笔力与写作手法多有保留之词。
尽管如此,1941年为了配合日本的中国语教育改革,竹内好决意翻译这篇仅有的教育小说。②可参考秋吉収「『中国文学月報』と中国語—竹内好らの活動を軸として—」(『中国文学論集』第35号、2006年12月)。只是在翻译的两年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竹内好对《倪焕之》的评价也受到日本思想界的影响而发生了转变。在《译者序》中,他虽然也提到小说前后部分不协调、文笔稚拙等问题,却以“是作家缺乏经验、且现代文学的历史尚短所致”作为解释,转而更偏重于强调该小说的社会价值。
《译者序》主要从两个方面肯定了《倪焕之》的价值。其一认为“这是把五四精神形象化的一篇杰作”,是“五四纪念碑”。其二认为该小说用稚嫩的手法写出了“近乎西欧小说的东西”,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现代性”。对于前者,竹内好在1952年和1963年修订《倪焕之》翻译的解说中,都是一贯坚持的。至于后者中“内在现代性”这一表述,他改成了“朴素的自然主义”的手法,认为这“是文学研究会派共通的东西”。竹内好在《译者序》中对《倪焕之》的阐释,受到当时日本“现代超克”论的影响,体现了他在战争期间的中国观。③关于这个问题,董炳月在《“内在现代性”与相关问题——论竹内好对〈倪焕之〉的翻译与解读》中做了缜密分析,见《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概言之,出于日本中国语教育改革的工作需要,竹内好翻译了这篇教育小说,后来因为日本“现代超克”论的影响,对此小说的解读也脱出了单纯文学研究的范畴。因此,《译者序》是为数不多体现了竹内好参与战时日本思想建构的文学研究作品,是研究竹内好早期思想的重要资料。是以为记。